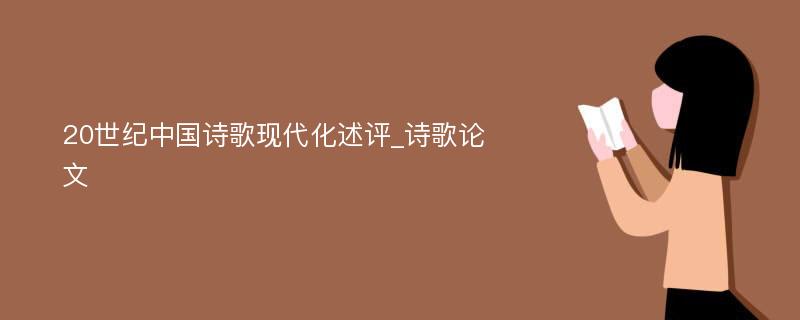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诗歌现代化历程的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诗歌论文,历程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百年中国诗歌的历史在整个中国诗歌约三千年的历史长河(《诗经》是一部周代诗选,周代以前即公元前1066年以前的时期算作诗歌的起源时期)中,也只是短暂的一刻。然而这占了中国诗歌历史三十分之一的20世纪诗歌创作,又正是中国诗歌的而立之年。从这一方面看,我们有理由要求卓然超群跻身于世界之林的伟大诗人的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20世纪中国诗歌它不单是中国诗歌三千年历史的一个年龄的增长,在这一百年内中国诗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转型。这一百年是中国古代诗歌向现代诗歌蜕变的转型期,是中国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容纳新潮,全面走向世界,实现中外诗歌大融汇的历史的崭新时代。在这一转型期的一百年,它给中国诗歌提供了任何一个世纪都无可比拟的新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并不成熟,但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中国诗歌未来的发展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一
19世纪末,即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夏曾佑、黄遵宪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大胆地把口语中的词汇与现代科学知识词汇写入诗中。“诗界革命”反映了维新派改革传统诗歌的愿望。但是,他们却没能打破旧诗壁垒,实现中国诗歌新的投生。其主要原因,在于维新派是从社会改良出发,缺乏文学观念变革的现代意识,不敢从根本上颠覆文言文的霸主地位与传统诗词的旧格律。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在旧诗体的框架内装进“新思想”、“新意境”、“新名词”。
20世纪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历程是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开始的。作为中国诗歌现代化开端的标志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文言合一”的旗帜下,彻底地否定了传统诗歌以文言文为诗歌书面语言的正宗地位,代之而起的同大众口头语更加接近的白话文;从“五四”白话诗歌运动开始,白话文便成为了一种现代书面诗歌语言的主要形式。而且这种现代白话诗歌语言较之文言文,它更能自由地接纳外来诗歌语汇与语法形式,为创造新的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提供了更加自由的条件。当现代白话语言成为中国诗歌的语言载体时,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变革才成为可能。其二,以“诗体解放”为旗帜,对传统诗词的旧格律予以彻底否定。在白话诗歌运动中,胡适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注: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95页。)这场语言文体形式的变革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诗词格律形式与现代语汇、现代人的现代生活感受相悖的矛盾,是中国诗歌得以面向世界,接纳新潮,具有真正现代化意义的一个开端。
与胡适在白话新诗运动中语言文体革新的成果相比,郭沫若则实现了中国诗歌思想观念与审美观念的更加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深层变革。郭沫若对中国诗歌的贡献表现为:其一,在20年代,贡献了最富有新世纪时代色彩的现代思想。他的《女神》以对自我新人格的极力推崇与张扬,以“力”与“动”的精魂与气概形象地浓缩了狂飙突进的20世纪创世精神与宇宙意识,郭沫若成了一个英雄时代的代言人。其二,面向世界的先锋意识,赋予了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的开放性品格。郭沫若广纳外来新潮,他的《女神》表现出宏大气概与超越陈腐、奔向现代的新进品格,把中国诗歌带向一个与外来诗潮相呼应相激荡的新时代。其三,他的《女神》已较少《尝试集》的旧胎记,初步实现了对中国古代诗歌形式的真正取代。《女神》以其新时代的理想,壮阔的力量,磅礴的气势,火爆的抒情,紧张、粗砺的形态,不拘一格的文体,大大地开阔了中国诗歌的表现领域,鲜明地改变了中国诗歌的审美格调。至此,一个具有现代审美意义的浪漫主义艺术体式开始确立。
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运动与郭沫若代表的现代浪漫主义诗潮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歌现代化的开端。传统的诗歌观念与诗歌体系受到了根本性动摇。“五四”新诗运动依仗着强劲的“五四”思想文化解放运动,迅捷地夺取了古典诗词垄断了几千中国诗坛的霸主地位。
20年代初期的中国诗坛面临的是旧诗的大厦已经倾颓,而新诗的殿堂又尚未建立的一种无序状态。“五四”新诗人在初创期探索中的稚嫩与缺失又成了守旧派攻击的把柄。在新诗的这一茫然期,出现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与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他们继续致力于“五四”新诗运动的现代化探索,总结“五四”新诗运动的成败得失,各自开出了救治无序状态的“药方”,李金发奉西方象征主义为“中国诗坛的独生子”(注:李金发:《卢森著疗〈序〉》。),期望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直接接轨同步。他的象征诗以其“怪异”诗风与陌生化形式,表现出与传统诗歌和谐优雅诗风的格格不入。而新月派诗人不赞同“五四”诗潮对传统诗歌的极端化对抗,主张从传统诗歌中汲取有益营养,自觉容纳欧美近代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韵,试图建立一个以“节制”与“和谐”原则为核心的新格律诗规范体系。尽管象征派诗人与新月派诗人的探索都有各自的片面,但是他们共同改变了20年代初期诗坛的散漫无序状态;并以各自新的价值规范的确立,把失范中的的新诗纳入到了现代化探索的不同航道中。从此,新诗结束了新旧蜕变期的尝试,开始了向新格律诗派追求的唯美方向与象征派提倡的“纯诗化”方向发展的新阶段。他们的探索代表了中国新诗在20年代向着现代化方向的新开拓。
二
30年代中国新诗走向了成熟期。五四时期开始的现代化的播种,经过20年代的耕耘,到30年代结出了较为成熟的果实。成熟期的代表诗人首推现代派诗群中的中坚人物戴望舒、何其芳。戴望舒、何其芳较成功地将中国传统诗歌的和谐、优雅、含蓄、意境化的抒情艺术与西方象征主义注重多重暗示、朦胧隐晦、婉曲跳脱等意象化的表现艺术相结合,较为自觉而巧妙地实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与西方现代诗歌艺术的融合,在近百年诗歌史上第一次较成功地调合了中外诗歌、古今诗歌的关系。同时,他们的创作又表现出对五四时期以及20年代各种新诗现代化艺术探索的综合与超越。他们从“五四”白话诗歌派中汲取了注重意象的方法,采用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讲究意象的多种暗示性,将写实性或单纯的比喻性意象发展为寄兴式、隐喻式的象征性意象;对浪漫主义的坦白奔放的抒情形式极为反感,但是提倡诗歌的“诗情节奏”或“内在韵律”的主张却与郭沫若的观点不谋而合;不满新格律诗派的“三美”原则,却注重采纳诗歌传统,在中西诗艺的沟通中形成的和谐典雅的颇具现代古典主义的诗风与新格律诗派又如出一辙;不满象征派诗人的神秘晦涩,但是在诗歌的审美价值观念、意象艺术诸多形式方面皆表现出同宗象征主义的共同特征。正是这种广采博纳、多方融合才有了戴望舒、何其芳在30年代的现代化探索的新贡献。
在本世纪30年代中国诗坛发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诗人是艾青。艾青在中国诗歌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将30年代上半期互相对峙的普罗诗潮与追求“纯诗”的现代派诗潮统一纳入了他艺术视野中。本世纪以来,时代精神的表现与艺术审美的追求在艾青手中第一次得到了较成功的统一。其二,他的诗歌以现实主义诗学原则为基础,自觉容纳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的表现方法,形成了独具开放性品格的现实主义诗歌美学体系。从此,五四时期新诗运动倡导者胡适尝试的写实主义新诗歌,在艾青手里结出了饱满的果实。也正是艾青的努力,使作为新文学主潮的现实主义在诗歌领域第一次获得了与之地位相称的成就,这也宣示了在现代化探索中现实主义诗潮有着它独特意义与旺盛的生命力。
40年代的诗歌的现代化探索的突出成就体现为智性诗化方向的发展。代表诗人一是40年代初期创作《十四行集》的冯至,另外一位是九叶派诗人中的先锋穆旦。冯至与穆旦较多地接受了后期象征主义诗潮的影响,告别中国传统诗歌与“五四”以来新诗感性诗化的抒情传统(包括冯至对自己20年代感伤的浪漫主义抒情告别),自觉追求诗的智慧性思考与经验的传达。他们的诗歌在感性与智性的有机交汇中,在官能感觉与抽象观念的艺术整体融合中表现出一种沉思的美与智性的美。在诗思方式、意象经营、语言技巧等各个方面更加拉大了与传统诗歌的距离,使中国新诗从形式本体上更加接近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而九叶派诗人在“现实、象征、玄学”的诗学原则下的艺术实践,又赋予了现代主义诗歌以开放性品格,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三
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新诗进入了政治抒情诗的一统天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豪迈激情,共产主义蓝图的美妙前景,把近30年的诗歌带入了一个充满理想激情的革命化与浪漫化时期。在与外来世界的隔绝中,近百年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诗潮的演变进入了一个低洄的时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突出代表是郭小川与贺敬之。他们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现代生活气息,他们甘愿作时代的歌手,让人们从他们的歌声中感受到时代前进的声音。郭小川自觉追踪具有历史感或现实感的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高奏时代精神的凯歌。因此,他们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具备了某种意义上的史诗性特征,这正是近百年中国新诗所欠缺的。在充满热烈、昂扬的理想激情的颂歌中,显现出某种道德力量的人格美与情感力量的阳刚雄强之美。他们诗歌中对生活的美化,对美的歌颂,美的向往,美的思考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写照。他们诗歌中的某些虚妄与空洞也是特定时代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真实映现。应该说,郭小川与贺敬之所代表的这个时代的抒情诗也给我们提供了某些中国古代诗歌乃至现代诗歌中没有的新东西。
与五六十年代的大陆诗坛不同,台湾诗坛继承了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探索,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再度推向高潮,使中国诗歌又出现了一个纯诗化探索时期。台湾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群包括现代派、蓝星、创世纪三个诗社。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的西化思潮,殖民地经济孕育的反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化意识,与大陆隔离的疏离感造成的漂泊心态似乎都成了现代主义诗潮发育生长的最合适的气候。他们在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探索中,既有共同的主张,也有相悖的差异。现代派诗社的发起人与领袖纪弦继续他30年代化名“路易士”时期的探索,明确提出我们“要的是现代的”诗,“唯有向世界诗坛看齐,学习新的手法”,“才能使我们的所谓新诗到达现代化”。他对达到现代化的具体阐述主要包括: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智性之强调;追求诗的纯粹性。以覃子豪为代表的蓝星诗社不同意现代派诗社的“贸然作所谓横的移植”,也不同意纪弦的“打倒抒情”的“主知”原则,认为诗应倾向于抒情。他们的相异主张形成了诗学上的补充和牵制。以洛夫、痖弦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一开始表现出与现代派、蓝星的相左倾向。他们开始提倡“新民族诗型”,具体主张:诗是美学上直觉的意象之表现,意境至上,不是散文的;中国风、东方味。不久他们抛弃了“新民族诗型”主张,转而提倡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和“纯粹性”;认为梦、潜意识、欲望是探索人性最重要的根源。在艺术上强调以“自学”、“暗示”为前提的语言和技巧的多种实验,包括色彩与声音的交感,想象与听觉的并启和切断,外在形式与内在秩序的矛盾和调和,强调直觉、感性、潜意识和意象的经营等。他们把由现代派的“主知”和蓝星的“抒情”互相牵制的现代诗运动,推向了以“超现实主义”为特征的阶段。台湾现代主义诗潮是一种强调诗歌本体探索的纯诗化诗潮,较为具体全面地接触到了新诗现代化的形式特征。这股诗潮整体上的疏离现实与疏离民族文化传统的趋向终于导致了在70年代的低落与消歇。
四
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新诗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变革的现代化多元性探索期,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复兴期。80年代上半期最重要的诗歌现象就是朦胧诗的崛起。这一在80年代上半期主导中国诗坛的新诗潮以新进、敏锐、活跃的先锋姿态和浩大气势构成了本世纪继“五四”后的又一次中国诗歌的造山运动,实现了中国诗歌观念又一次大变革与现代化跃进。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为代表的朦胧派诗潮的文学变革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他们大胆冲破现代蒙昧主义思想观念的禁锢,率先在诗歌世界里复归人性与自我,又一次高扬起五四时期现代人性意识的旗帜,在自我心灵伤痕的传达与体验中,溶入反思民族历史、忧患祖国未来的崇高使命感;他们的歌唱是新时期文学觉醒的先声。其次,以艺术变革的新锐姿态,突破僵化的政治化的抒情模式,复归了被放逐的诗情与诗本体,建构起了诗歌的新的美学原则。他们摒弃单一的表现模式,主张突进精神世界的多层次开掘中,以象征意象的模糊性、朦胧性为手段,使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潜隐性的表现成为可能;恢复幻想、想象的艺术功能,将直觉、幻觉、智性、思辨、潜意识等艺术心理机制注入诗歌,让现代主义诗美之性灵直接汇入当代诗潮。至此,中国大陆诗潮在与隔绝了近30年的西方现代诗潮再度沟通、交汇,使新诗现代化探索经历了曲折与低洄后再次回到正道。第三,朦胧诗开创了现代化艺术探索的多元景观。朦胧派诗人经历了“文革”的沧桑岁月,带着心灵伤痕,也带着变革初期新旧观念转换的烙印步入新时期。他们的歌声中人文主义的理性观照,浪漫主义的感伤情调与理想主义色彩,转向人性关怀与内心思索时对象征主义的审美认同,都是这一批诗人共同的艺术倾向。然而,他们各自的诗歌都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北岛的超现实模式的象征,舒婷的情感复调,顾城的幻型世界,江河的原型与个体同构境界,杨炼的智力空间(注:陈仲义:《〈今天〉十年》,《百家》1989年第1期。)等,并形成了各自特有的风格:北岛的深沉、炽热的冷峻,舒婷温馨、美丽的忧伤,顾城的悲凉、纯静与幻美,杨炼的苍劲而古拙,江河的浑厚与沉静,这一股股充满蓬勃生机的清新诗风,奏响了近百年中国诗歌现代化探索的最动人心弦的一段乐章。
朦胧诗以反叛的姿态打破了僵化的传统的格局,刚到80年代中期,被反叛的命运随后也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这一批被称之为新生代或第三代或后新诗潮的诗人,吸吮了朦胧诗的乳汁,又不满朦胧诗的某些诗学原则,以对朦胧诗的否定与超越显示了他们现代化探索的更为新锐或激进的姿态,从而构成了中国新诗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现代化探索的多元化的沉思与调整时期。
新生代诗潮对朦胧诗人的对抗与超越(也是他们探索新诗现代化的独特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放逐主体,消隐自我的“非个人化”倾向。他们反对朦胧诗将主体高高凌驾于客体之上,不赞同用主体的心灵尺度规范并役使万物入诗。他们将主体逐出虚幻的中心,打破以人为中心的视点。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消失,代表自我的主观感性被消隐,非人化的客体现象世界开始以自然的原生态进入诗中,让诗与世界以其客观存在保持其独立意义。情感的“零度状态”和“物的叙述”方式成为了新的表现策略。其二,非文化倾向。他们认为朦胧诗之所以没有彻底挣脱泛化的社会政治意识的藩篱,主要是源于传统文化观念形态理性积淀的这种非诗因素的干扰,正是这种文化干扰使朦胧诗人没有真正实现诗的本体的重建。新生代诗人从整个生存世界感到的是文化的笼罩、压力与文化的异己力量。人创造了文化,而文化却以各种手段控制人、束缚人。新生代诗人由此对文化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与忧虑。他们竭力主张撤除文化罗幔,在自觉淡化消解文化的创作过程中,让人与诗还原到本真的存在状态,呈现出一种非文化的“原在”;在“归真返朴”中,让诗与生命得到同构,且相互诠释。其三,非崇高形态。这也是新生代自觉消解文化的一种新的美学形态的建构。他们用觉醒了的平民意识对抗英雄主义的崇高意识。朦胧派诗人的现实悲剧感,历史使命感,道德启蒙的神圣感,在新生代诗人眼中成为了应该与旧时代一同告别的一种神秘的贵族化倾向。诗人不是“高雅而且优美”的鸟,“老是飞在高高的空中”,诗不再是某种典雅、堂皇的圣物,诗应该返归到平凡的世界。他们的创作不仅要消解和淡化朦胧诗英雄主义的崇高感,又要使人切实地回到自身,使诗走下神殿回到诗本身。其四,非意象方式。这种非意象手段成了一种消解文化的艺术方式。朦胧诗恢复了30年代意象隐喻抒情的表现方式,创造了新诗艺术世界新的智力空间。新生代诗人反对把诗的阅读变成一种释义活动,他们主张用非意象化的直接性语言。“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要求“把语言从一切功利观中解放出来”,(注:韩东:《自传与诗见》,《诗歌报》1988年7月6日。)不能将语言做为营造意象的手段,要让诗回到自足的语言本体。新生代非意象主张,直接促成了以语言为核心的实验诗的大潮,带来了具有诗本体意义的语言的自觉与革命。80年代后期的新生代诗潮在诗学观念变革上,比起他的前辈诗人的诗歌来,更加具有切近诗歌本体的纯诗意义。然而,新生代诗潮众多流派的标新立异,并没有留下丰硕的创作实绩。他们大胆叛逆的偏激与探索中的稚嫩留下了许多让人众说纷纭的话题。
90年代诗歌新潮与80年代后期的新生代诗潮表现出众多诗学意义上的整体性与相关性联系。从抒情主体的边缘化角色,到抗拒崇高、消解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认同市民的审美心理;从诗歌话语的个人性探索,非意象化主张到反对外在的隐喻意征方式,崇尚冷讽、俏皮的戏拟风格等,都是在80年代后期新生代诗潮中萌生的,90年代诗歌使上述具有现代化本体意义的探索更加成熟。并且出现了像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西渡等一批有代表性的诗人。当下诗歌正处在一种个人化的探索的冷滞时期,这正是世纪末中国诗歌的大调整,大变革的沉思阶段,一场新的诗歌大变革正在孕育之中。
五
中国诗歌在近百年现代化探索的历程中逐渐获得了自己的现代品格。这种现代品格是在外来诗潮的民族化转换与民族传统诗歌的现代化改造这种双向交融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既区别于中国诗歌的传统品格,也不完全类同于西方诗歌的现代特征。我认为20世纪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现代人性意识的确立。中国诗歌从五四时期郭沫若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潮开始,以关注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人性意识得到了确认与张扬。郭沫若的《女神》以空前高昂的人格自信的理想激情与自由意识的超越力量否定了囊括黑暗历史与腐败现实的一切不合理的存在。自我成了宇宙万象的主宰,成了创造宇宙的本体。这样一种充分肯定人格主体力量的自我崇拜与生命意志力量的张扬是具有鲜明现代性文化意义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次革命性的转换。从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集中表达的是对人的生存价值与生命意义的体认,是对现代人的精神归属的追问。这样一种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潮影响,把文学集中转向关注现代人的内在世界与人本身的诗潮,正是中国传统诗歌中所真正缺乏的。自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的表现现代人性意识的生命主题常常都是与对民族命运的忧患,诗人自我理想探索中的迷惘联系在一起,打上了特定的民族文化的心理印记。
第二,意象抒情体系的变革。中国古代诗歌有着较为丰富而细密的意象抒情艺术的谱系,从意象的对象的选用到意象的组织传达都形成了相对规矩的传统。然而近百年的中国诗歌对意象这一个最为核心的诗歌形式系统作出了重要的变革与发展。这种变革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打破了以和谐美、典雅美为中心的优美意象体制,扩大、丰富了意象内容,给意象注入了鲜活的现代审美气息。郭沫若的诗歌创造了象征“力”与“动”的现代意象群,打乱了传统诗坛的优雅宁静的秩序。象征派代表诗人李金发,引入了以丑为美的“恶之花”怪异意象,与“风雅”传世的诗歌传统大相径庭。三四十年代现代派、九叶派诗人把都市生活的人生世相大量写入诗歌,告别了古典主义的田园诗、山水诗营造的恬静与淡泊。到80年代中期后,新生代诗人以求真求实的本真方式,直接摄取生活中原始、粗砺形态的种种意象,这种泛意象的艺术与传统诗歌苦心经营意象的条条框框更是格格不入。其二,革新传统意象艺术的方法。从“五四”以来的现代诗歌,特别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借鉴西方象征主义艺术,将传统诗歌中的比喻性的确定性内涵意象改造为复合型内涵的象征性意象,使古典诗歌意象内涵的相对单纯、确定、透明变得朦胧、抽象、复杂。意象的智性化倾向是现代诗歌区别于传统诗歌意象的又一重要特征。现代诗人不把意象仅仅当作抒情的载体,而且开始把意象作为体悟人生、表达心智、传达经验的媒体。其三,打破了古典诗歌意象的常规性逻辑组合原则,表现出无限度的自由化结构特征,实行了意象组合的常规思维向意象组合的“诗的思维”的现代性转化。
第三,诗歌话语及其方式的转换。古典诗歌语言,是一种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书面语言,它的表达要严格受到诗歌格式、韵律的限制。这种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分工自然是与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相一致的。从本世纪之初的“诗界革命”中提出的“我手写我口”,到“五四”白话诗歌运动提出的“文言合一”,至20年代中国诗歌基本完成了话语的转换。白话文话语中心地位的确立带来的不仅是诗歌形式与表达方式的革命,它也进一步地引发了深刻的文学的思想观念与审美观念的现代变革。中国近百年自由体诗歌形式的主导地位,外来诗歌艺术的吸纳与融汇,现代人的现代心理与现代情绪,包括对传统诗歌具有生命力的语词的借鉴化用,离开了现代口语这一现代诗歌媒体都是不能实现的。中国诗歌话语形式的现代转换早已实现,而它尚没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一方面存在着与传统诗歌语言、外来诗歌语言艺术的进一步调合(只能是现代话语为本位的调合),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清除非诗因素的干扰,让诗歌真正回归到诗语言本体上来(90年代以来后新潮诗人表现出了他们可贵的探索)。
第四,感性与智性交汇形成的智性诗化特征。中国古典诗歌是一种感性化的抒情诗。中国诗歌注重的是直接感悟与模糊体验,忌讳理性分析,诗往往表现的是一种情调、气氛或一种境界。这与中国哲学观念对自然与现实注重感性经验的体验的文化心理是一致的。而中国的现代诗歌既不脱离又无法脱离这一感性思维的传统,同时,又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诗人明显表现出智性化倾向。40年代九叶派诗人提出的诗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认为“诗不再是激情,而是表现人生经验”。他们的创作用经验的传达,智性的强化取代了传统的感性主宰。最终他们的诗表现出来的是智性与感性的融汇,思想与形象的凝合。从30年代卞之琳开始,经冯至、九叶诗派,再影响到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新潮诗歌,智性化倾向似乎越来越鲜明。
第五,象征主义艺术的潮流趋向。中国古代诗歌中从来没有过象征主义,周作人曾把《诗经》中的“兴”视为象征,实际上是他的附会。象征主义从20年代被引入中国,成为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现代主义诗歌方法。从李金发把象征主义作为拯救中国新诗命运的“独生子”开始,经过30年代梁宗岱与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的大量引入与介绍,现代派创作的象征主义诗歌创造了30年代中期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40年代的冯至与九叶派诗人主要借鉴了以里尔克、瓦雷里、瑞恰慈、艾略特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他们的创作无疑代表了中国40年代诗歌的最高成就。80年代朦胧派诗人重新树立起象征主义旗帜,继续了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传统,带来了中国新诗的复兴。90年代的诗坛纵然有人打出了非意象,反象征的旗帜,但是他们抛弃的只不过是表面的象征手法,他们并没走出一种向着生命意识纵深掘进的深度象征的象征主义范畴。得其皮毛者是为经验的象征主义,得其精髓者为超验的象征主义,自然皆为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在20世纪中国曾遭贬斥,但仍然与中国新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探索是多角度、多层次意义上的。像20年代象征派诗人提出的“诗的思维术”,30年代现代派诗人追求的“纯诗”方向,40年代九叶派诗论家兼诗人袁可嘉提出的“非个人化”主张,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出现的平民化、口语化、泛抒情与讽喻化、虚构现实与反向修辞等,无不一一都是我们反观20世纪中国诗歌现代化探索的透视点。期望大家对中国诗歌现代化变革作出进一步的总结与思考。
标签:诗歌论文; 象征主义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女神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朦胧诗论文; 现代诗论文; 和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