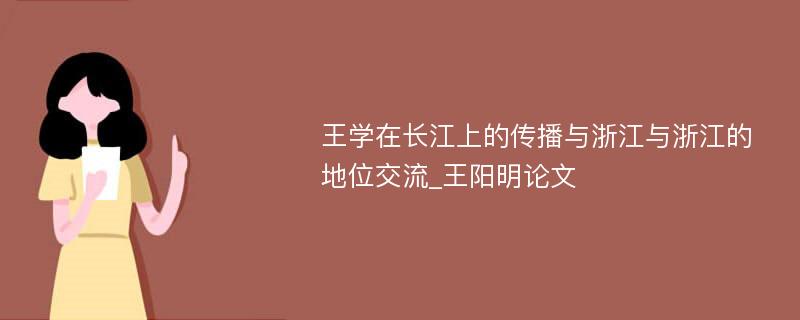
王学的跨江传播与两浙的地位互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王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说的“江”即钱塘江,而所谓“两浙”便是以此江为界而划分的“浙东”与“浙西”①。以余姚人王阳明为代表的阳明学派诞生于浙江的绍兴地区,兴盛于江西的吉安、赣州地区,展开于江苏的泰州等地区,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而所谓“跨江传播”,就是阳明学的传播区域从浙东(以绍兴、宁波等地为中心)向浙西(以杭嘉湖、苏南等地为中心)的移动。本文即拟以兴盛于中晚明的阳明学的传播与展开为主线,对这一尚未被学术界明确界定的、发生在两浙区域的文化互动及地位互换作番全景式的考察,以图从一个侧面来揭示两浙文化的异同、互动之关系。
王阳明一生以讲学为首务②,书院乃其讲学的主要场所,诚如其弟子薛侃所言:“书院,先师精神所绥、道之所在。”③尽管贵州龙场是阳明的悟道之地,其地位在阳明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如其再传弟子张元忭所言:“阳明先生学脉契千古,勋烈盖一世,然动忍之助,得于龙场者为多。”④所谓“动忍之助”,语出《孟子·告子下》,比喻历经困苦而磨炼身心。反过来说,阳明对龙场及其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所进行的教化,也是功不可没。然而,阳明所从事的以书院为平台的讲学传道活动,黔中的地位就远不如以浙江绍兴为中心的浙中地区和以江西吉安为中心的江右地区。⑤阳明去世后,吉安作为王学传播的中心区域依然十分活跃,同时,江苏泰州也在阳明高足王艮的推动下,迅速上升为王门讲学的中心区域,而绍兴的地位则逐渐被钱江对岸的杭州所取代。
绍兴地位的下降,一方面源自于因天真书院的建立而使杭州在王门中影响力的迅速攀升,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阳明学者在绍兴讲学的相对沉寂和绍兴王府的逐渐衰落。除此之外,两浙地区阳明学地位的相互转换,还与当时阳明学派的两大领袖钱德洪、王畿把居住地和注意力由浙东转移到浙西有一定关系。⑥
阳明在世时,绍兴的讲学活动称得上是名振四方、辐射全国,尤其是阳明晚年,因深感自己已来日不多,所以“逢人便与讲学,门人疑之,叹曰:‘我如今譬如一个食馆相似,有客过此,吃与不吃,都让他一让,当有吃者。’”传道的使命感与紧迫感溢于言表。正是在王学的新颖吸引下和阳明的真诚召唤下,成百上千的读书人乃至普罗大众云集绍兴,许多人甚至从“数千里外来”。⑦据称当时绍兴“四方鸿俊,千里负笈,汉氏以来,未有此盛”;⑧受邀和未受邀的聚会者最多时竟有二、三千人之多。⑨故而后来有人说:“当时及门之士,相与依据尊信,不啻三千徒。”⑩如果考虑到嘉靖前十年,阳明学遭朝廷学禁、备受压制的现实,在绍兴能有数千人的聚会,实属不易。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阳明在世时绍兴地区的讲学活动不仅次数多,而且规模大,要超过阳明的其它所有讲学之地。虽然阳明去世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使该地区的讲会活动迅速走向衰微,但当年的盛况,却在好多年后仍令人难忘。出生余姚的钱德洪,尽管是余姚中天阁讲会的主持,却对阳明在越时的讲学活动评价极高,其曰:
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11)
在这种充满自由的思想氛围和学术环境下,善于进行思想创设的王阳明,自然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而其“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12),思想日趋成熟,亦当在情理之中。所以阳明本人对绍兴也是极尽赞美之词:
会稽素号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13)
其实,与其说是幽静的山水之地引得“良朋四集,道义日新”,倒不如说是阳明晚年对讲学事业所投入的巨大热忱,才使得绍兴成了当时学术研究和讲会活动的中心。阳明殁后,玉山知县吕应阳撰祭文称“稽山还英灵之气”(14),而不说四明(指余姚)还英灵之气,其因盖在于此!
正是由于阳明很早就已迁居绍兴,后来又在越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讲学活动,故而世人常有把绍兴直接视为阳明故里者,如巡按御史储良材在阳明祭文中说:“东望会稽,先生故里也。”(15)陶望龄也说:“文成阙里,钱(德洪)、王(畿)先生相与阐道之地,太守(指萧良干,万历年间迁守绍兴)幸来,今愿以仕学矣。”(16)陶氏还说阳明是“于越所称乡先生”(17),甚至认为:“当正、嘉间,越有乡先生者,起而一划其陋,撤胶固之像设,而洗虚谬之王称。……先生之教始于乡而盛于大江(指钱塘江)以西。”(18)黄宗羲的弟子李杲堂则干脆把王阳明与出生山阴的刘宗周视为“同里”之人,他在《修绍兴府学序》中说:“然而王子、刘子则俱越人也,固越中人士所谓国之先师也。……国有先师,此古今所不易得,而越人乃有两先生,亦甚幸矣。”(19)这种把王阳明与绍兴紧密联在一起的话语环境,与绍兴王府的兴旺和王学在绍兴的成长壮大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然而,这种繁盛局面在阳明去世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就再也没有在绍兴地区出现过了,甚至可以说,从阳明去世到万历初的五十余年间,随着阳明后学者在绍兴讲学的沉寂,致使该地区逐渐被王门边缘化。
归有光说:“自阳明殁,学者稍离散,公(张寰)尝游其门。至是吉水邹谦之、余姚钱德宏(洪)以师门高第,会讲怀玉之山,公欣然赴之。”(20)据王宗沐《怀玉书院记》和夏浚《易简堂记》载,钱德洪应聘怀玉书院讲学是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与其共赴者,先后有山长吕怀及胡子庵、桂学愚、吴暨、夏浚等人。(21)邹守益则是先来杭州再去怀玉的。而嘉靖三十八年,正好是阳明学者聚会天真书院讲学的高潮期,当时除了浙江的阳明学者,其周边的赣、苏、皖、粤等地的阳明学者也纷纷前往杭城讲学。怀玉山地处浙赣交界处,距离杭城约350公里,为往来浙赣的必经之地,于是便成为阳明学者讲学的又一个中心。当时,凡来杭州讲学者,有不少人会被接着邀请去怀玉山讲学,就连首届“江(西)浙(江)大会”也是在怀玉山召开的。需要追问的是:距离杭城只有60公里的阳明学诞生地绍兴,为什么就没有成为当时的另一个讲学中心呢?难道一条不太宽的钱塘江就能把阳明故乡与其学脉阻隔开来?其中之原委,不是很有必要深究吗?
尽管归有光所说的“自阳明殁,学者稍离散”,指的是阳明学派讲学之全貌,但绍兴讲学活动的前后反差似乎最为明显(详见后述)。虽然后来在薛侃等人的努力下并成功利用天真书院等平台,使全局的情况有所改观,但绍兴则不仅未见好转,甚至还继续恶化了。
薛侃在《寄冷塘》中曾相当痛心地对比过阳明在世时绍兴的讲学盛况与其逝世后不久的萧条景象:
先师还越积六载,兴起友朋数百人,征广时至大书院尚聚以百,龙山会以百,不肖求差会葬,寓天真,犹动以百,此行初至,如履无人之境,过越落莫尤甚。夫力田而耕,犹或有馁,集肆而贾,尚未必裕,况弗田弗肆,尚何稼与殖之有?龙溪得先师之髓,心斋得先师之骨,已为知学者趋向。有庠生范引年颇善迪后辈,可以延主天真之教,能为小立一室于近左,免致往返余姚,尤便而可久。杨汝鸣与张叔谦倘未即第而归,亦可延守越之祠。心斋小祥后亦可惇请往来其间。庶几风教一振,人知翕向,陶习将来,一以衍十,十以衍百,则此学之明犹有可企也。师逝十年,萧条若此。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复何如也!(22)
阳明在世或者刚去世时,无论绍兴还是杭州,动辄百余人聚会,讲学风气极盛,然而当薛侃到天真书院时,“如履无人之境”,过江到绍兴一看,“落莫尤甚”,所以薛侃感叹道:“师逝十年,萧条若此。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复何如也!”这反映出王门在阳明去世后一段时间的凋敝情形。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与当时的政治阻隔有很大关系,但王门弟子不够努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用薛侃的话说,便是“夫力田而耕,犹或有馁,集肆而贾,尚未必裕,况弗田弗肆,尚何稼与殖之有”?这可以说是对王门弟子懈怠的严厉批评。薛侃甚至细心到对来天真书院主讲者的住宿安排,目的就是想让主讲者能“免致往返……尤便而可久”,进而使讲学之地“风教一振,人知翕向,陶习将来,一以衍十,十以衍百,则此学之明犹有可企也”。
绍兴的讲学活动之所以会低落到“落莫尤甚”的程度,其中固然有绍兴王氏家族的过早衰落以及钱德洪与王畿的不和等因素,但越人讲学过于空疏狂野也是导致绍兴王门讲学落寞的重要原因。张元忭曾对此作过中肯分析:
越人往往以讲学为谈笑,固彼言是行非者,无以取信,然惩火而废炊,见亦左矣。顷自吾辈为二六之会,友朋中颇不加姗,且有勃起兴起者。斯文未丧,天其或者有意于越乎!
也就是说,讲学在越人那里犹如游戏玩耍,不当正经事做,“固彼言是行非者,无以取信”。张元忭则希望同门中人对越地讲学不要加以讥讽,而是要多发挥促进鼓动的作用,同时他又要求越地人士对讲学也不要“惩火废炊”、因噎废食。而他的心愿乃是“诸友如约为会,互相激裁,毋使越人复以半途为诮”(23),即通过“互相激裁”,来实现讲学明道、移风教化之目的,以免使绍兴再度被世人讥诮为讲学教化运动中的半途而废者。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热心在绍兴讲学的阳明传人,也似乎只剩下了张元忭一人,诚如许孚远在写给元忭的信中所言:“吾乡习俗颓靡,朋友寥落,莫有甚于此时。如吾兄挺然卓立,迥出尘表,真弟所敬服,弟所倚赖也。”(24)说明当时绍兴的学术氛围已寂寥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而张元忭等人力图复兴讲学的诸项举措也的确起到了一定效果。
然而,就在绍兴讲学趋于衰落的同时,与其一江之隔的杭州,却在王门讲学运动中扮演起了领导者的角色。两地相较,反差之大,令人咂舌!
尽管王阳明在杭州居住过的时间加起来只有半年多时间,他在杭城设坛讲学的具体经过和时间亦无明确记载,但他生前就有在杭州创办书院的设想,并试图把杭州作为传播王学的一个中心。因此,在他去世前一年,钱德洪、王畿便已商定把天真山麓的几座寺庙改建成书院。后来钱、王两人又分别把常居处从绍兴府余姚县和山阴县迁至杭城——钱德洪住在表忠观,(25)王畿住在金波园。(26)这两个住所都在西湖南边,相距不远。钱、王两人把常居处迁入杭城,最初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两人要经常在天真书院开办讲会,往返于钱江两岸很不方便。但这样做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浙中王门乃至整个阳明学派的中心从钱塘江南的绍兴逐渐转移到江北的杭州,并且又从杭州逐渐扩散到浙西北、苏南及皖南的广大区域。陶望龄所谓的“夫文成之后,驾其说以行浙之东西者多矣”(27),“先生之教始于乡而盛于大江(指钱塘江)以西”,便道出了这种转移的历史轨迹。
正因为此,“大江以西”的几个重要讲学处也成为万历初年禁学运动的主要区域。张元忭在写给王畿的信中曾谈到天真书院的被毁经过:“许敬庵辈从旁沮之,以为拆毁书院屡奉严旨,况天真、水西又其(指张居正)所注意者,言之无益且有损。”(28)说明在当时的讲学运动中,要数杭州的天真书院和泾县的水西精舍的影响力最大。而这两处被重点关注的讲学处,一个在浙西,一个在皖南,且皆与王畿等人所讲的“虚浮”之学有关。从杭州到宣城、徽州这条学术走廊,是当时王畿等人讲学的重点路线,也是朱子学主导下的各种思潮、学派交汇碰撞的主要区域。由此亦可反衬出王门讲学从浙东向浙西乃至皖南、苏中扩散的移动轨迹。
需要指出的是,以杭州为中心的浙西讲学之风的兴盛,与薛侃这个外省人有很大关系。薛侃在天真书院的地位,可与阳明相提并论。薛侃“素慕王阳明先生学,早出其门,精思力践,师门以勇锐见称。既以罪废,遂徙家于杭,筑天真精舍,以祀阳明,而时与同志讲学其中”(29)。是故徐象梅将其记录在对浙江有过巨大贡献的《两浙名贤录》之“寓贤”中。王学后来之所以能在浙西地区广泛传播,薛侃的作用不可低估。以薛侃为代表的王(阳明)陈(白沙)、王湛(甘泉)折中派,在杭州等地传播阳明学的同时,还顺带传播了白沙学和甘泉学,使得该区域涌现出不少折中王陈、王湛的学者,如唐枢、许孚远、蔡汝楠、顾应祥、钱薇、(30)孙景时、(31)王爱(32)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王学在浙西地区传播的成色,显示出与浙东地区不同的文化个性。
如果说薛侃对“大江以西”阳明学兴盛所作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杭州天真书院的话,那么绍兴人王畿的活动范围则远远超出了杭州,他还在广义的浙西地区乃至邻近的皖南等地传播和推广阳明学说,可谓阳明学跨江传播的最大推手,从而使之成为拥有最多浙西弟子的阳明学者之一。
比如沈懋孝是浙西地区相当活跃的阳明学者,著名的东林党人赵南星、史孟麟、叶水盛等皆出其门下。(33)据沈懋孝(34)《沈太史全集》之《洛诵编·水南徐先生当湖会语叙》载:“往嘉靖乙丑(四十四年),龙溪王先生尝止于陆与中之天心院(地处嘉兴平湖),讲良知学脉,从游士数十百人。而水南徐君从焉。余时侍养家居,亦与其末从。”又据《沈太史全集》之《石林蒉草·滴露轩藏书记》载,在嘉靖三十九年以后的五六年间,沈懋孝就经常向王畿问学。据沈懋孝《湖上读书堆六先生会语》载:“嘉靖癸丑(三十二年)夏四月既望,念庵罗先生自北还道经浙河,东廓先生赴默林胡公之招馆于武林山间,于是一庵唐先生、龙溪王先生、荆川唐先生、黄州湛一方先生,与邹、罗二先生咸会于我当湖(在嘉兴平湖),将纵观海上之胜。明日携同学六七人过湖上读书堆,因相与论格物之指焉。……因诵白沙诗云:‘语道则同门路别,任君何处觅高踪。’令在座诸友歌再阕而起。明日诸生送至盐官,再越日至水西而别当湖。”(35)因为平湖等地是王畿从杭州天真书院到泾县水西书院讲学的必经之路,而王畿则像播种机一样,不失时机地在沿途传播和弘扬阳明学,所以每次北上,沿途都会举办讲会。此次当湖之会,主要围绕朱子和阳明的格物说而展开,其中一庵的立场是调和朱王,龙溪、念庵的立场是尽力阐释阳明的主张,荆川的立场与一庵相近,东廓未发表任何意见,方湛一则认为诸友的意见都对,所以质疑“何必纷纷论辨以发之哉”,并且诵白沙诗以证明自己的立场,令在座诸友歌诗领会之,从中透露出的王湛协调、朱王归一的强烈信号值得重视,而沈懋孝作为东道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所以其弟子刘芳节说:“先生(沈懋孝)之学,实有渊源。龙溪以姚江为蓝染,先生青出于龙溪。”(36)
浙西还有两位明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袁了凡、丁宾,包括袁的父亲袁参坡,也是王畿的弟子。袁了凡(1533-1606),初名表,改名黄,字坤义、坤甫,号了凡,吴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晚明流行一时的“功过格”的提倡者之一,其思想在明末清初影响颇大。丁宾(1543-1633),字礼原,号改亭,嘉善人,隆庆五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王畿晚年的得意门生,尝编刻《王龙溪全集》。关于袁了凡、丁宾从学王畿一事,可参见袁了凡的《两行斋集》卷十四《光禄寺署丞清湖丁公行状》。(37)王畿与浙西的密切关系,还可以从玉芝法聚、唐一庵、许敬庵以及后来的张杨园(38)等人那里找到不少例证。
除此之外,包括王畿在内的阳明学者还在浙西地区创办了不少书院、举办过一系列有影响的讲会活动。笔者曾据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一书作过统计,其中较有影响的大概有以下几次:嘉靖十六年十一月,沈谧建书院于秀水县文湖(今属嘉兴市),祀阳明;(39)嘉靖二十二年秋,顾应祥、唐一庵等结社于湖州岘山;(40)嘉靖三十二年夏,罗念庵、邹东廓、唐一庵、王龙溪、唐荆川、方湛一等“携同学六七人”会于当湖;嘉靖四十三春,王龙溪与李见罗会于武林金波园,有湖上浃旬之会;同年秋,复与万思默相会于武林;(41)嘉靖四十四年,王龙溪赴嘉兴平湖,宿于陆与中之天心院,“讲良知学脉,从游士数十百人”;嘉靖四十五年秋,唐一庵、王龙溪、管南屏、王敬所、孙蒙泉、胡石川等聚会于杭州金波园,与会者达百余人;(42)隆庆二年,王龙溪主讲于当湖天心书院,与丁宾、陆云台等八人结为“天心会盟”;(43)同年冬,王龙溪自云间趋过嘉禾(云间、嘉禾分别为松江、嘉兴二府之雅称),会于东溪山房,讲“愤乐之说”,后又应蔡春台之邀,赴姑苏,举竹堂会;(44)隆庆三年,王龙溪应曾见台之约,趋会武林,举武林会,就王学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研讨;(45)万历五年秋,王龙溪应邀“赴阳羡之会”(阳羡为宜兴之雅称);(46)同年秋,邓定宇、张阳和、罗康洲聚会于杭州,与王龙溪论学;(47)万历六年春,许敬庵、张阳和、赵濲阳、罗康洲“聚会于武林西湖之上,论心谈道”(48)。万历七年,张居正毁天下书院,包括天真书院在内的与王门讲学有关的诸多重要书院均在禁毁之列,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年春,王龙溪仍应约讲学于平湖,刘允玉、沈懋孝等185人与会;(49)翌年,王龙溪又赴松江参加“云间之会”,后又与平湖人陆五台会“于嘉禾舟中”,畅讲佛学。(50)
有见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王畿是浙西阳明学的主要传播者和教授师。故此光绪年间修《嘉善县志》,编入《龙溪王畿会籍记》,以凸显其对浙西阳明学的传播与发展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也是合情合理的。
值得深思的是,从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王畿只在浙东地区参与过两次讲会活动,即隆庆四年周海门参与的“剡中讲会”(事见《东越证学录》卷五《剡中会语》)及万历二年与张元忭一起主讲的越中“云门会”和“天柱会”(事见《龙溪会语》卷六《书同心册后语》、《天山问答》)。(51)然而在同一时期,他在浙西地区的讲学活动却明显增多,甚至称得上是当时活跃于浙西学术舞台上的耀眼明星。这固然与其当时安家杭州金波园、常要途经浙西地区北上讲学有一定关系,但同样安家杭州钱王祠的钱德洪,为什么就没有像王畿那样积极参与浙西地区的讲学活动呢?这就不能不从钱、王二人的思想性格、工作职责以及当时两浙地区的思想环境中去寻找答案了。(52)
与王畿并称为“二溪”的罗近溪,也曾在浙西地区授徒讲学,以至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把罗近溪、李见罗和唐一庵、许敬庵分别视为“姚江身后其高足王龙溪辈”在江西和浙江的传人,他们“分曹讲学,各立门户,以致并入弹章”(53)。唐一庵和许敬庵是湖州人,由此亦可看出王畿思想在当时浙西地区的广泛影响力。此外,罗近溪还著有《两浙游记》,其浙西弟子朱廷益则为他撰写过祭文。(54)如果再联想到嘉靖四十五年嘉兴知府徐必进命王门同志董启予刻阳明《文录续编》六卷并《家乘》三卷于嘉兴等历史实况,那就更有理由说:阳明去世后的浙江学术中心,不在浙东,而在浙西!
至于为什么阳明以后王门讲学会在绍兴日渐衰微的问题,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其中既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硬”道理,又有文化、思想等方面的“软”道理,而在传播过程中顾此失彼、首尾不能兼顾,则可谓是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对此,王畿在其所撰的《约会同志疏》和《白云山房答问纪略》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和分析:
先师祠(指绍兴王文成公祠)中旧有初八、廿三会期,频年以来,不肖时常出赴东南之会,动经旬月,根本之地反致荒疏,心殊恻然。人不可以不知学,尤不可以不闻道。会所以讲学明道,非徒崇党与、立门户而已也。……哲人虽萎,遗教尚存。海内同志信而向者,无虑千百,翕然有风动之机。而吾乡首善之区,反若郁晦而未畅、寂寥而无闻。揆厥所由,其端有二:一者不肖在家之日少,精神未孚,虽间一起会,及予外出,旋复废弛;二者不肖徒抱尚友之志,修行无力,凡心未忘,虽有圣解,无以取信于人。是皆不肖不能自靖有以致之,于人何尤也?……况年逾七十,百念尽休,一切远涉尘劳,不惟日力不逮,势亦有所不能。惟是一念改过,不忍负于初志,所望同乡诸友怜予苦心,修举月会之期,以是月廿三为始,不肖虽有少出,亦望互相主盟,弗令复废。(55)
先师祠中旧有初八、二十三之会,屡起屡废,固是区区时常出外,精神未孚,修行无力而过日增,无以取信于人,亦因来会诸友未发真志,徒以意兴而来,亦以意兴而止,故不能有恒耳。……哲人虽逝,遗教尚存,海内同志信而向者无虑千百,翕然风动。而吾乡首善之地,反若幽郁而未畅,寂寥而无闻,师门道脉仅存一线,此区区日夜疚心不容已于怀者也。今日诸君来会不过二三十人,越中豪杰如林,闻有指而非之者,有忌而阻之者,又闻有欲来而未果,观望以为从违者矣。其非而忌者,以为某某平时纵恣,傲气凌物,常若有所恃;某某虽稍矜饬,亦是小廉曲谨;某某文辞虽可观,行实未着,皆未尝在身心上理会,今欲为学,不知所学何事。此言虽若过情,善学者闻此,有则改之,无则勉之,莫非动忍增益之助,以舜之玄德,皋陶陈谟,尚拟以丹朱,戒以漫游傲虐,若命项辈然者,舜皆乐取而无违,此同人大智也。若夫观望以为从违,却更有说,此皆豪杰之辈,有志于此者,但恐因依不得其人,路头差错,为终身之累耳。言念诸君平时虽不能无差谬,然皆可改之过,五伦根本皆未有伤,譬之昨梦,只今但求一醒,种种梦事皆非我有。诸君不必复追往事,只今立起必为圣人之志,从一念灵明日着日察,养成中和之体,种种客气日就消减,不为所动,种种身家之事,随缘遣释,不为所累。时时亲近有道,诵诗读书,尚友千古,此便是大觉根基。或平时动气求胜,只今谦下得来;或平时狥情贪欲,只今廉静得来;或平时多言躁竞,只今沉默得来;或平时怠惰纵逸,只今勤励得来。浸微浸昌,浸幽浸着,省缘息累,循习久久,脱凡近以游高明,日臻昭旷。不惟非者忌者渐次相协,其观望以为进退者知其有益,自将翕然闻风而来,无复疑畏,是长养一方善根,诸君锡类之助也。若夫徒发意兴,不能立有不可夺之志,新功未加,旧习仍在,徒欲以虚声号召,求知于人。不惟非者忌者无所考德,一切观望者不知所劝,亦生退心。譬诸梦入清都,自身却未离溷厕。斩截一方善根,在诸君尚不能辞其责也。(56)
笔者之所以要引述这两段冗长引文,是想完整展示阳明去世后发生在绍兴学术圈里的真实场景。本来阳明所留下的“遗教”即思想学说,“海内同志信而向者,无虑千百”,这是通过讲会而使阳明学说获得广泛传播的极好机会。然而,作为首善之区的王畿家乡绍兴,在隆庆、万历年间却已是“郁晦而未畅,寂寥而无闻”,遂使“根本之地反致荒疏”。在王畿看来,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多年来其本人“时常出赴东南之会,动经旬月”,而只要他一离开,“间一起会”的绍兴讲会就会无人领头,“旋复废弛”。二是王畿自认“徒抱尚友之志,修行无力,凡心未忘,虽有圣解,无以取信于人”,亦即他的学说很难获得绍兴诸友的认同。这并不是王畿的自谦之语,其同乡门人张元忭在谈到王畿思想在家乡的影响时也说过:“盖先生唯自信其心,而吾乡之人每不能无疑于其迹。忭于先生固不敢疑乡人之所疑,而犹未能信先生之所信。盖尝以吾之不可学先生之可而期,先生不以为谬也。”(57)这说明,除了王畿很少在家乡举办讲会活动外,其学说不受乡人信任也是以王畿为代表的阳明学者在绍兴难以有效传播阳明学说,至使绍兴出现短暂的讲学“荒疏”的重要原因。对此,王畿本人曾作过深刻反省。他尤其对于因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禁毁书院事件的发生深表自责:“近见当时录文(指王畿在京师时的讲学语录),有谈性说命,假禅幻以为表异之说,令人惕然发深省。吾党之学果有假于禅幻,自当创悔惩艾,以图自新。”(58)正是基于这种自我反省精神,王畿不仅不指责当局下达的禁毁书院的命令,而且还为这种政策说好话:“吾人虚辞缪张而实践未至,激成纷纷。所谓新法之行,吾党有过,非剿说也。”(59)不过他对一些人无端斥责自己溢出名教的说法,却明确提出了反论,而且喊出了“岂肯甘心自外于名教”的心里话。所以他不仅要求诸友:“各各自靖,不为虚声浮响所撼动。”“但愿诸贤牢立脚跟,默默自修,养晦待时,终当有清泰之期。”(60)甚至还以略带危机感的央求口吻对同乡诸友倾诉说:“况年逾七十,百念尽休,一切远涉尘劳,不惟日力不逮,势亦有所不能。惟是一念改过,不忍负于初志,所望同乡诸友怜予苦心,修举月会之期,以是月廿三为始,不肖虽有少出,亦望互相主盟,弗令复废。”从中所流露出的一位古稀老人的无奈和期盼,令人感佩!
不惟王畿,王门的另一领袖级人物邹守益对绍兴的落寞也颇有同感。邹守益曾主持或参与过南岳、冲玄、齐云、庐山、怀玉、天真、武夷等地的讲会活动,“每会至数百人”,(61)但唯独没有主持或参与过绍兴地区的讲会活动。即使去绍兴,他也是为祭扫凭吊阳明而去。在他的心目中,杭州才是当时两浙地区的讲学中心,所谓“既趋会稽,哭阳明公,与同志大会于天真书院”,(62)就道出了绍杭二地分别以祀奉和讲学为重心的基本格局。所以宋仪望的《邹东廓先生行状》称:“其在各邑,以企抚、虔、南昌、袁、广、江、浙、徽、宁诸郡,或一至再至,未有厌倦。至赴冲玄、齐云、象山、庐岳、天真诸会,动经数月,其答同志、企门人问辨,皆随器成就,因事辩析,其言明白简易,学者多所启悟。前后会语,俱载集中。”(63)耿定向的《东廓邹先生传》亦曰:“自南雍免归,纳玺之嘉礼甫成,踰月即出西里讲学。明年游南岳,寻游庐阜,若越之天真、闽之武夷、徽之齐云、宁之水西,咸一至焉,而境内之青原、白鹭、石屋、武功、连山、香积,岁每再三至。远者经年,近者弥月,常会七十会,聚以百计,大会凡十会,聚以千。”(64)都把天真书院作为浙江讲学的中心,甚至连王学传播的边缘区域闽中,邹守益也去武夷山讲过学,并有《武夷答问》存于世:“循闽,游武夷,谒文公书院及阳明、甘泉祠,语具《武夷答问》中。”(65)可就是不去曾经的王门心脏绍兴讲学。邹守益的选择只不过是阳明学派中的一个案例,其他人的选择亦概莫如此。由此也反映出当时绍兴讲学的“荒疏”之程度。
王门在绍兴的讲学活动,直到万历初年才开始恢复正常,后又渐趋活跃,直至明代末年。这一时期,王畿及其弟子张元忭在家乡的学术活动显著增加。从文献上看,王畿的《白云山房答问纪略》、《白云山房答问》、《天柱山房会语》、《天山问答》和张元忭的《跋云门问答》等,记载的都是万历二年王门在绍兴的讲学之事。但即使如此,张元忭仍隐隐自责道:“若余不类,幸生文成之乡,窃闻绪论,乃竟未能奋身担荷,为诸士友倡,视先生(指倡水西会的沈御)其何如也?”(66)
到了万历中期,在周汝登、张元忭等人的努力下,绍兴的讲学活动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而且相当活跃,不过离当年王阳明在绍兴讲学时动辄几百上千人的盛况仍有很大差距,而在讲学质量上更是有质的区别。据周汝登《越中会语》记载:
己亥(万历二十七年)秋季,先生(周汝登)同石匮陶公及郡友数十人共祭告阳明之祠,定为月会之期,务相与发明其遗教。先生语诸友曰:“我辈去阳明先生之世几八十年矣。阳明先生初倡此学时不知经多少风波,后赖龙溪先生嗣续,亦不知受多少屈抑。今日我辈得此路头坦然趋步,可忘前人之恩力耶?盖当时人士只疑良知之教不切躬修,是以非诋,曾不知所示格物处俱是日可见之行,何等着实!今遗教具在,我辈正当以身发明,从家庭中竭力,必以孝悌忠信为根基。……越有阳明,犹鲁有仲尼,龙溪一唯参也。今日正须得一孟子,而后仲尼之道益尊。谁其任之!各自力而已矣。(67)
周汝登是把阳明比作孔子,龙溪比作曾子,而自比孟子,于是绍兴就成了儒家之圣地。所以汝登一方面要求诸友“以身发明,从家庭中竭力,必以孝悌忠信为根基”,以挽回人士对“良知之教不切躬修”的指责,另一方面又鼓励大家要勇敢的担当起振兴阳明学的历史重任。
五年之后的万历三十二年,曾在万历三十年聆听周汝登在婺源霞源书院讲学的新安人余舜仲来令绍兴山阴,使绍兴的讲学活动得到进一步复兴,这从汝登所作的《文成祠讲学图序赠山阴令舜仲余君入觐》及《拜文成先师墓偶有侵损之虞赋慨》中可窥见一斑。前者称赞余舜仲说:“君月谒文成祠,联缙绅文学,共昌明其旨。近且增饬斋宇处,廪饩为会,盛会之翼。……吾道其又昌哉!惟舜仲之心不自满,假余每扁舟过郡,则出郭邀迎,入祠论证,执礼弥恭,心弥下而请事弥勤。……今时事纷纭,特务文成。有文成何忧世道?吾以望之学文成者,舜仲其重自念哉!”(68)后者则将阳明墓直接比作孔林:“参天松桧郁森森,夫子高坟是孔林。露浥喜看千叶茂,神呵谁许一枝侵。西风拜礼瞻依切,碧草摧残感慨深。到此若无双泪迸,世间何事更关心?”(69)由此可以看出周汝登利用各种资源以复兴绍兴讲学的雄心壮志。
延续张元忭、周汝登在绍兴讲学的是刘宗周。如果说在王学初创时期,阳明门下在两浙的展开还是东强西弱的话,到了第二代传人王畿等人时,王门的学术中心开始由浙东向浙西转移,那么到了被视为王学殿军的刘宗周时,稽山门下在两浙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则大致趋于均势。这种局面的形成,无疑与王学中心从浙东向浙西的转移有一定关系。万斯同指出:
往山阴刘忠正公绍明绝学,四方士多从之游,其卓然可传于后者,大都以忠义表见。如吴磊斋、叶润山、祁世培、金伯玉、王玄趾、祝开美诸君子其尤也。其后死而坚岁寒之操以学问表见者,不过盐官陈乾初、毘陵恽仲升及吾师姚江黄太冲三先生而已。恽先生又逃之方外,其学不专于儒。黄先生余所亲炙,信哉为山阴之嫡传。陈先生则闻其名而未识其人,然稔知先生学最深,品最高,为乡人所矜式。而先生有子敬之及从子惕非,克承家学,力敦行谊,不愧其前人,余敬而慕之,欲与之缔交,而余久客天涯,竟不获与二子把臂,耿耿此中,未尝不自怅也。念忠正公一代大儒,传其学者无几,幸陈先生守其坠绪,二子又克守先生之绪,此正余欲奉为师资者。(70)
在“以学问表见者”著称的刘子门人中,万斯同只列举了盐官陈乾初、毘陵恽仲升及姚江黄太冲三人,并说“恽先生又逃之方外,其学不专于儒”;“黄先生……为山阴之嫡传”;“念忠正公一代大儒,传其学者无几,幸陈先生守其坠绪,二子又克守先生之绪,此正余欲奉为师资者”;试图以此来凸显对以陈乾初为代表的刘子浙西传人的敬重。有学者指出:刘宗周弟子在思想创新、形成新学派上最具代表性的是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史学派与以张履祥为首的杨园学派,刘宗周的再传弟子所发扬的亦不外乎梨洲史学和杨园理学。(71)尽管在刘宗周的171位弟子中,浙西与苏南合起来只有28人,仅占总数的16%,而浙东地区的弟子却有107人,占总数的62.9%,但是浙西有杨园理学、乾初心学与浙东的梨洲史学相呼应,彰显出较强的学术创造力和亲和力。而在可以统计出的刘氏171位弟子中,真正有影响力的只有十几位,如《清史稿》、《小腆纪传》之《儒林传》所著录的刘氏弟子只有16人,其中4人是浙西人,即张履祥、钱寅、郑宏、沈昀。说明浙西刘氏弟子的分量并不轻。若就学术统治力而言,恐怕只有余姚的黄宗羲和桐乡的张履祥当之无愧了,这两人可以说是由蕺山学派而开新学派的创始人。另外刘门中学行笃实、道德高尚的山阴人王朝式与海盐人吴蕃昌,亦被世人视为能传蕺山学的代表性人物。这说明,发生在阳明以后的浙江学术中心由“东”到“西”的转移,到了明末清初,的确出现了东西并重的局面。刘宗周传人在钱江两岸并驾齐驱、互为补充,便清楚证明了这一点。
从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去世到万历二年(1574)王畿、张元忭在绍兴恢复讲学,这中间有近五十年时间几乎是绍兴王门讲学的空白期。反观杭州,由于天真书院的兴盛,在此阶段倒逐渐成了浙中王门乃至整个王门讲学的中心,以至使祭祀王阳明的主要活动也从绍兴转移到了杭州。这些都证明了王门中心从浙东向浙西的转移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地域文化史现象,其中所透露出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深度解读。
本文为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立项课题之论文。
①关于“两浙”在地理环境、学术传统、文化性格上的差异,详见钱明:《浙中王学研究》第1章《浙中王学形成发展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另见钱明:《“浙学”的东西异同及其互动关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近世“浙学”的东西之分及其走向》(《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两浙人文地理与价值观念之差异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朱晓鹏主编《浙学传统与浙江精神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②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12《念山余先生传》:“昔有谓阳明子文章、功业、气节三者具足名世,除却讲学乃全。而阳明子愿尽除三者专事于讲学。学固不离三者,而三者匪学则余不足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65,第644页)
③薛侃:《薛中离先生全集》卷12《与钱君泽》。
④张元忭:《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3《复邹南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4,第378页。
⑤宋仪望《校编邹东廓先生文选序》:“海内豪杰之士,得闻其(阳明)说,莫不翕然从之。然在当时,惟绍兴、吉安为盛。盖先生起自于越,从游最先,既官南赣,吾吉诸君子从先生游凡数十人,至今宗其学者,不敢废坠。”(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0页)按:与吉安地区以乡会、族会为平台的讲会运动不同的是,王门在绍兴举办的讲学活动,大多集中在书院、寺庙,而且一般以王学精英为主要对象。如果说吉安讲学是以王学庶民化为主要表现形态的讲会运动,那么绍兴讲学便是以王学精英化为主要表现形态的讲学活动(参见钱明:《中晚明的讲会运动与阳明学的庶民化》,《儒教文化研究》第18辑,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2012年12月刊)。
⑥关于天真书院因政治原因而导致的兴衰,以及浙中学者在其中所发挥的正负面作用,可详见钱明:《杭州天真书院的历史沿革及功能转换》,《浙江历史文化研究》第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⑦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上册,第590页。
⑧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38《临终自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94,第850页。
⑨董澐尝赋诗曰:“二三千个同门聚,六十九季今夜除。”(《从吾道人诗稿》卷下《丙戌除夕》)
⑩王宗沐:《敬所王先生全集》卷1《阳明先生图谱序》,明万历元年刻本。
(11)《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8页。
(12)《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册,第201页。按:“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最早由王畿提出(见《王龙溪先生全集》卷2《滁阳会语》),其中虽不能排除王畿对阳明晚年讲学越中的过度赞誉,但若联系到阳明本人对自己晚年思想的评价,则可谓一语中的。
(13)《王阳明全集》,第81—82页。按:此语出于嘉靖五年阳明《答聂文蔚》第一书。
(14)(15)《王阳明全集》,第1435、1433页。
(16)陶望龄:《歇庵集》卷10《陕西布政使拙斋萧公神道碑》,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
(17)《歇庵集》卷6《重修阳明先生祠碑记》。按:王应麟曾对“乡先生”作过如下界定:“古之有道德者,教于乡里,谓之乡先生。在乡而祠于学,犹在国之祭于瞽宗也。”(《先贤祠堂记》,《全宋文》第353册,卷820,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18)《歇庵集》卷6《修会稽县儒学碑记》。
(19)李杲堂:《杲堂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48页。
(20)归有光:《通政使司右参议张公寰墓表》,收入焦竑《国朝献征录》,上海书店,1987年,第2941页。
(21)朱承煦编纂、曾子鲁校注:《怀玉山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2、760页。
(22)《薛中离先生全书》卷17《寄冷塘》。
(23)《张阳和不二斋文选》卷3《与毛文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4,第395—398页。
(24)许孚远:《敬和堂集》卷4,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二十二年叶向高序刻本,第69页。
(25)即钱王祠,明嘉靖三十九年浙江督抚胡宗宪建祠于涌金门外灵芝寺(又名灵芝崇福寺,原为钱镠故苑)址,塑吴越国钱氏三世五王像,春秋致祭,令钱镠十九世孙钱德洪守之。
(26)金波园在杭州诸史志中找不到任何记载。杭州有金波桥弄,东起光复路,西至中山中路,与太平坊巷相对,弄名始于清,沿用至今。金波桥、金波桥弄与金波园可能有一定关系。据喻均《勋贤祠志·土地纪二》载:金波园在杭州城西(第2页b)。另据《邓定宇先生文集》卷3《秋游记》载:“出戟门,闻龙溪翁至,廿二日候于金波园,寻谒表忠观,读苏长公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6,第357页)故推测金波园的位置大致在今清波门一带,离表忠观不远。钱德洪有《金波园中送鹿园先生入山》(万表《玩鹿亭稿·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76,第182—183页)。王畿抵杭城,一般都住金波园,而不像其它学者那样下榻天真书院(参见《张阳和不二斋文选》卷4《秋游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4,第406—409页),故金波园可能是王畿在杭州的住所。另外,阳明学的一些重要著述亦作于金波园,如唐枢的《咨言》、王畿的《金波晤言》等。
(27)《歇庵集》卷3《又潜学编序代左景贤侍御》。
(28)《张阳和不二斋文选》卷3《复王龙溪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4,第377页。
(29)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54《寓贤》,《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7册,第1547页。
(30)以上人物请详见钱明:《浙中王学研究》第二、三章。
(31)孙景时,字成叔,杭之右卫人也。性耿介,于世寡谐,与越人汪应轸、仁和邵锐、江晖、钱塘吴鼎为友,慕章文懿、胡端敏之为人,师事阳明、甘泉二先生。学成,正德丙子举于乡。……作《武林文献录》、《杭州府志》。欲勒成郡乘,副在名山,惜有志未究而卒(参见《两浙名贤录》卷2《儒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7册,第82页)。
(32)王爱,字体仁,秀水人……父训以圣贤自期。已而闻一庵唐先生讲学苕中,负笈从之游,得闻讨真心之说。已又受业于王龙溪先生,尽闻王文成致良知之旨。爱往来吴越间,以两先生言相印可,益悟良知不参情识,即是真心,一落情识,即非真心。两家互相发明,初无抵牾。自是学益有进(参见《两浙名贤录》卷4《理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7册,第143页)。
(33)参见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191、265页。
(34)沈懋孝,生卒年不详,字幼贞,号晴峰,平湖人,隆庆二年进士,嘉靖四十四年从学于王畿。
(35)沈懋孝:《沈司成集》卷1,《四库禁毁书丛刊》集159,第106—107页。
(36)沈懋孝:《沈太史全集·洛诵编》卷首《长水先生集叙》,明万历年间刻本。
(37)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第277—278页。
(38)上田弘毅:《朱子学者张杨园の阳明学批判》,《阳明学》第21号,明德出版社,2009年,第65—92页。
(39)《王阳明全集》,第1333页。按:据湛若水《湖州宗山精舍阳明王先生祠堂记》(《湛甘泉先生文集》卷13,嘉靖十五年闻人诠刻本),可知当时嘉兴、湖州一带建有阳明祠堂的书院不在少数。
(40)顾应祥:《崇雅堂文集》卷12《岘山逸老堂铭》。
(41)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16《书见罗卷兼赠思默》。
(42)唐枢:《木钟台集》之《六咨言集·金波园聚友咨言》。
(43)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5《贺奉常陆安石先生膺封司寇郎叙》。
(44)王畿:《龙溪会语》卷3《愤乐说》;《王龙溪先生全集》卷5《竹堂会语》。
(45)《王龙溪先生全集》卷16《别曾见台漫语摘略》。
(46)《王龙溪先生全集》卷13《书贞俗卷序》。
(47)邓以瓒:《邓定宇先生文集》卷3《秋游记》。
(48)许孚远:《敬和堂集》卷10《祭罗康洲宗伯》。
(49)《沈太史全集》之《石林蒉草·龙溪王先生过当湖邑人士一百八十五人集于五老峰塔院会讲记》。
(50)《王龙溪先生全集》卷17《重修惠民桥碑记》;卷6《答五台陆子问》。
(51)参见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第296—297、311—312页。
(52)参见钱明:《浙中王学研究》第6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5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97年,第690页。
(54)载《罗明德先生文集》卷首,明崇祯五年刻本。
(55)吴震编校:《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3-54页。
(56)(57)(58)(59)(60)《王畿集》,第747—748、789、329、285、314页。
(61)(62)(63)(64)(65)《邹守益集》,第1364、1368、1387、1392、1391页。
(66)《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5《沈文池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4,第443页。
(67)《东越证学录》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6,第471—472页。
(68)《东越证学录》卷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6,第541—542页。
(69)《东越证学录》卷1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6,第721页。
(70)万斯同:《题松菊图为陈愓非八旬初度寿》,载《石园藏稿》,清抄本,无卷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
(71)(参见张瑞涛:《蕺山弟子考编》,《浙江历史文化研究》第4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