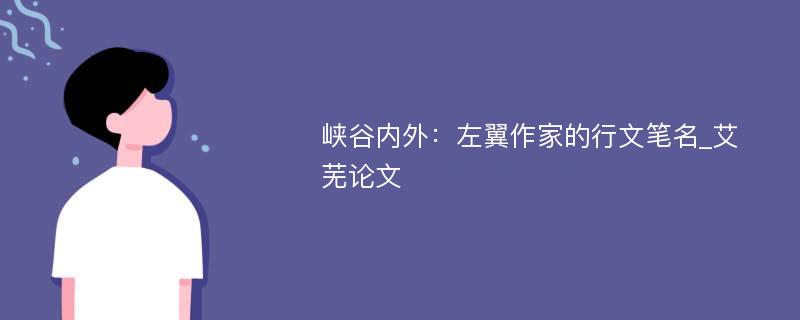
“山峡”内外:一个左翼作家的行走、书写与笔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峡论文,左翼论文,笔名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文学研究中“文学性”标准的浮现,现在提及左翼文学写作,人们脑海浮现的多是阶级斗争模式,特定意识形态的规约,题材、内容、风格、情节、人物等“差不多”的现象。① 因此,左翼文学的研究目前更多地来自文化批评和知识考古的视角。这显然是时代研究兴趣的转移所致,似乎也是一个必要且可能的角度。
不过,左翼文学写作中所透露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信息?
他们中的多数人既没有左翼阵营内部如鲁迅等人对中国传(正)统文化的了解,也没有左翼以外的如梁实秋等人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浸润。即便如经常被研究界所提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可能确如王富仁所说,②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社会上感受到压迫,在经济上也陷入困境,他们非常盲目,但有热情、追求,不过他们接受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没有设计,他们也脱离了对文学的真诚追求,只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作为一面旗帜,不无求名得利的动机。而且在我看来,左翼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和思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其实是具有足够代表性的很大一部分人。
本文从文学文本的分析入手,借用王学泰有关游民文化与中国(主要是古代)社会的相关观点,通过细读左翼作家艾芜的小说《山峡中》来试图回答前面提及的问题。《山峡中》远不是左翼写作中最有名的小说,但如果从文本分析与传记、文化批评的角度看,它也许是最能体现其时左翼文学写作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中非常复杂而有趣地缠绕着一个流浪汉写作者加入“左联”组织后对自身的身份认证,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杂糅,革命的浪漫理想与残酷的现实挤压之间在写作上呈现的张力等等,也许可以由此敞亮中国游民文化的“现代化”情景,并由此对于把捉左翼文学写作的性质及其文化意蕴有所助益。
一人物及其身份认证:流民、游民与游民知识分子
艾芜在1933年冬天集成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共收入8篇小说,③其中多是滇缅边界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这些人物无一例外地被生活抛到了社会的最低层,现代文学学术界包括文学史教材往往称之为“下层人民”、“劳动人民”或者“流民形象”④。这种说法固然没错,但却失之笼统和模糊,难以敞亮其文化内涵。如果借助王学泰的专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一系列富有启示意义的研究成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艾芜这个时候的写作,笔下所涉及到的多是社会游民。⑤
据王学泰界定,游民乃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主流秩序(因为更多涉及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因此这里主要是指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乏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以出卖劳动力为主(包括体力与脑力),也有以不正当手段来牟取财物的。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而游民中的腐败分子就是好逸恶劳、欺压良善的流氓地痞。
与此相似却又性质不同的是另外一群人——流民。流民是指成为“流”状态而离开故土的人们。他们有可能没有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秩序。因为波及甚大的天灾人祸都会导致大批的农民脱离自己的土地。这个过程中许多人是整个家族或宗族作大规模的迁移,在这种情况下,家族的宗法秩序没有被破坏,只不过是举族或全家换了一个地方。但也有一部分的流民变成了游民,他们脱离了“流”,进入了城市,成为溷迹社会底层、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游民;或者闯荡江湖、冲州撞府过着漂泊不定生活的游民。
小说《山峡中》中的人物也正是一些流民、游民,乃至两者复杂的混合体。这些人往往都具备王学泰所谓的“游民意识”:⑥ 强烈的反社会性;在社会斗争中最有主动进击精神;注重拉帮结派,注重团体利益不重是非;失去了宗法网络中地位的游民同时在社会中也没有了角色位置,丧失角色位置的人们也就没有了角色意识,因此,由角色位置所决定的自我约束、文明规范以及社会生活必需的文饰均无必要,由此,游民意识也就往往表现出中国传统思想意识中最黑暗、最野蛮的一面。而这种游民意识构成了游民文化的主体。
《山峡中》叙述一个流浪读书人跟一群盗贼在山中相处的时光。其中人物活动的环境——江湖社会、刀光剑影的生活、对义气的遵从、对知识的嘲弄等等,无不显示出游民文化的特性。
武侠小说流行以后, “江湖”一词便活跃在人们的口头,而游民的活动领域就是“江湖”。它充满风波艰险、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血仇报复;它又是变幻无常的,在普通人眼中神秘莫测,很难一履其地。而那些出没于江湖的盗贼侠客,如果褫去了武侠小说作家对他们的神秘化和美化以后,其实就是脱离了社会正常秩序、勇于冒险、富于主动进击精神的游民。《山峡中》不是武侠小说。它既不是一个武术技击世界,也不是一个超现实的剑仙神魔世界,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现代小说形式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故事中人物的名字,比如野猫子、鬼冬哥、夜白飞、野老鸦等本身就带有浓郁的江湖气味,而小说中魏大爷之“大爷”,小说中反复提到的其他人对魏大爷的称呼“老头子”等,也都是江湖、秘密会社中隐秘的习惯称呼;加之他们生存的环境,也的确是一个主流政治社会以外的亚社会, “民间社会、江湖社会”,这一点却颇类似于侠义小说。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对艾芜以《山峡中》为代表的《南行记》的描述,其措辞是“用特异的边地人民传奇生活为题材,开拓了现代文学反映现实的新领域。并且,在左翼革命现实主义流派之内,发展起一种充满明丽清新的浪漫主义色调与感情、主观抒情因素很强的小说。”⑦ 其间带有“传奇”、 “浪漫”色彩的“新领地”,其实也很难说与武侠小说中所渲染的那份神秘传奇色彩有多大的区分(后面会看到,艾芜本人最早的文学或者说小说教育也就是来自对中国传统的武打、侠义小说的阅读)。由此看来,《山峡中》讲述的其实就是典型的社会游民的生活,故事环境就是一个典型的江湖社会:小说一开始对巨蟒似的索桥、黄黑斑驳的神龛、残破的江神的描写,并不仅仅是小说作者对盗贼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描摹,更是成了游民们整个生存环境的一种寓意性修辞。
《山峡中》同样有着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虽然并非武侠小说中武术技击的论剑斗棍,但一样显示了生存的艰难,他们在这里挣扎、冒险,有时仅为觅得一食也要付出很大的气力;他们在这里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获得生活的权利,甚至或许可以取得发迹的机会,同时由于游民缺少文化,他们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手段更加残酷,争斗的目的更加赤裸裸。
美丽而野蛮的野猫子是这篇小说中唯一真正动刀的人。当“我”打算离开这个团伙,并告知野猫子时,她流露出的只有鄙视,在她那里退出就意味着怯懦——野猫子把“我”带到黄果树前比试刀功,让读书人“我”一败涂地。这种刀光剑影的日子使得他们往往轻生忘死,夸强斗狠。听见小黑牛痛苦的呻吟,鬼冬哥一脸不屑:“我们这批人打断腿子倒是常有的事情,……你们看,像那回在鸡街,鼻血打出了,牙齿打脱了,腰干也差不多伸不起来,我回来的时候,不是还在笑吗……”。而老头子魏大爷的说法同样是:“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小伙子,个个都对我们捏着拳头哪!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得到今天吗?……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
在如此艰险的生存环境中,拉帮结派的团体利益当然可以高过一切。所以李慎之说:
他们的最高规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有时也叫“忠义”或“仁义”。既然“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⑧
他们尊重的不是主流社会看重的书本知识,而是江湖义气。小说中的流浪读书人“我”最好地体现了这种义气——因为流浪读书人面对兵士时,拯救了野猫子,从而也拯救了自己:因为“我”的义气,野猫子不但没有亲自杀“我”,也没有让其他同伙杀“我”,而且在读书人熟睡的时候,和其他同伙悄悄离开,甚至还把自己平日最喜欢的玩具——一个小木人儿以及三块银元留给了“我”。反过来,这个同样“义气”的举动,使得本来已经决心离开这个团伙的读书人,在他们悄然离去之后,并非暗自庆幸,反而倍觉寂寞:
但我看见躺在砖地上的灰堆,灰堆旁边的木人儿,与乎留在我书里的三块银元时,烟霭也似的遐思和怅惘,便在我岑寂的心上,缕缕地升起来了。
即使厌倦江湖的险恶,打算“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而不可得,甚至为此付出生命——那往往是不够义气的表现,是对义气这个最高规则和最高道德标准的冒犯,一种僭越。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僭越行为,由于游民缺少文化,他们之间的争斗的手段更加残酷,所以在这个游民江湖中就很容易看到那些异常残忍的举动。
“我”打算离开而受到野猫子的威胁,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只不过由于后来的义气之举而得救。小说中的小黑牛更是这方面惨烈的例子。魏大爷虽然也呵斥小黑牛的不机警,但那并非小黑牛致死的关键,紧要处显然是小黑牛的不够义气:他当面诅咒魏大爷和同伙,显然坏了规矩,加之用魏大爷的话说:“他又知道我们的……咳,那么多,怎好白白放走呢?”不够义气,再加上对团体利益的潜在威胁,使得小黑牛终于活活葬身江底。这里很轻易就可以看到游民意识中一方面的英雄豪迈,另一方面的欺压良善,而且两者之间丝毫没有矛盾,义气显然在其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
由于义气的绝对地位,一般主流社会所尊从的知识反而成了被嘲弄的对象。游民对主流社会的所谓“知识”带着一股难以排遣的仇视。杜亚泉在上世纪初发表的文章《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中说:“吾国之财产阶级、劳动阶级,历史上受贵族之剥削,为游民所蹂躏也久矣,故其对于贵族与游民,畏之若虎狼,恶之若蛇蝎,已成习惯的心理。而知识阶级者,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故彼等之厌恶之与贵族游民相等。且以嫉恶知识阶级之故,遂有并知识而嫉恶之者。”⑨ 在小说《山峡中》,不仅是财产阶级、劳动阶级对知识阶级甚至知识本身有着极深的厌恶,游民也一样痛恨知识和知识分子。而在一个社会中通常所谓的“知识”,总是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书本也往往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载体。因此,对知识或者书本的仇恨,其实也正是游民脱离了当时社会主流秩序的一种表现。
小说中有一段关于读书的生动描写。流浪读书人“我”总喜欢在火堆旁就着火光读几页书,这让其他人觉得不可理解——鬼冬哥一把将书夺过去,大家吵嚷着要烧掉“我”的书。正统士大夫的孔孟之道作为“大传统”⑩ 在这里对这些游民似乎没有丝毫的规约力量。本是作为经典规约的“书上的话”,不管是实际效果还是象征含义上讲,在他们那里的确都是“烧起来还当不得这一根干柴”的废话,变得一钱不值,实实在在显示出游民们对知识和文化的轻视、对知识分子的嘲弄。
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玩笑、打闹衬托出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物——跟那些典型的游民不一样的流浪读书人。读书人依旧把书本作为自己学问的来源,而书本成了整个主流社会的知识代表,也是主流意识或者说正统士大夫大传统的象征。
小说人物形象中,跟读书人类似的还有那个倒霉的小黑牛。虽然流浪读书人和小黑牛的结局完全不同,但在身份上两人倒比较一致,他们已然身处魏大爷的游民盗贼团伙,但都还不是魏大爷那类典型游民,而更像是流民。他们并不具备清晰的游民意识,事实上依然处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小黑牛向往的依旧是回到安定的、正当的居家生活,其中包括土地、牛羊和家人;而小说中的流浪读书人“我”,则是流民和知识分子的一个混合体。一方面他在市集里参与盗贼团伙的行窃;另外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读书人,而他的知识,并不是魏大爷的知识和学问,显然是主流社会所认同的知识。这就意味着,他并不认同这个团伙的行为,并不打算接纳魏大爷的学问,而总是打算离开他们,不断在故事的讲述中为自己参与的盗窃行为辩护: “今天去干的那件事,无非由于他们的逼迫,凑凑角色罢了,并不是另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他始终在破庙的火堆旁边就着火光读书,认同和吸纳着其中的知识学问,也显然是向往着对主流社会的回归。
这样一来,故事中真正让人感兴趣的,也许不是一直受到大家关注的野猫子,而是故事的讲述者——流浪读书人“我”。
二 时空的腾挪:川、滇、沪之间
小说作者跟故事的讲述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叠吻合。而艾芜的这类写作,其实有着相当深厚的渊源,这种渊源很容易让艾芜产生这类写作或者想象。
1.祖父辈与游民文化
在解释流民和游民产生的根源时,王学泰曾经提及,唐代《唐律疏议》颁布以来,历代王朝都明令财产和土地必须在诸子之间平均分配,而不是唐代以前的财产长子继承制。它的结果是导致中国农民经济的“小、少、散”局面,并进而成为农民生产和生活日益恶化、农民阶层的极不稳定和易于流亡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小小的震动都有可能使他们丧失这块很小的土地,而众多的破产失业者,又自然汇聚成最使统治者心惊胆战的流民。(11)
这种情形非常典型地体现在艾芜家里。1922年,艾芜的父亲三兄弟分家。祖父的60亩田产一分为四:祖父母和三个儿子各一份。父亲得到其中的15亩田产。但这份田产,很快就被(跟袍哥组织有着松散关系的)父亲拿去卖了抵债。这一家人在以土地为生的年代中,已经无法在土地上扎根。成都平原一望无际广袤的沃土,跟他们不再有什么关系。加之后来父亲的逼婚,结果导致艾芜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尚未毕业就离家出走、流浪(与现在看到的《山峡中》一样,艾芜本人也的确就是一个流浪读书人)。
而在艾芜从小的阅读中,他所接触的文学读物,恰恰就是作为游民意识载体的《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说唐》以及《七侠五义》、《小五义》等侠义小说。这些差不多就是艾芜进入文学领域的入门读物。正是沉迷在这些游民文化作品中,艾芜在自觉不自觉中有了对大传统以外的另一个传统——小传统(游民文化)的继承,这个小传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关王爷的“义气”。更不用说他的父亲曾经出入于游民组织哥老会,所可能给他的潜在但是直接的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难怪作者对游民和游民生活不由自主地有着某种同情,就像小说最后的惆怅感觉一样。
2.流浪、传闻与想象
小说《山峡中》的真实固然不用说:有着不止一代人的移民(人川的迁徙远祖)和游民(父亲)的家传,也有着自己流浪的切身经历,包括艾芜在流浪途中的经历与道听途说,在滇缅边境上关于土匪、盗贼的种种见识与传闻。艾芜曾在滇缅群山中的一个叫做茅草地的地方做过小店杂役,盗贼尤其是盗马贼见过不少,只要他们给钱,而且不偷店里的东西,都是允许住店的。(12) 在茅草地卑贱的工作和丰富的传说,甚至成了艾芜后来写作的源泉。1927年艾芜从昆明前往缅甸的路上,曾经走过一个叫做舍资的地方。四年后的1931年2月3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南行中也走到了同样的地方:
云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土匪,谁也记不清了。……大约在四年以前,土匪人数开始猛增。
……路边上的许多村落还留下被土匪洗劫过的痕迹。在舍资,墙壁坍圮,半数左右的房屋倒塌,断壁残垣之中还看得见被烧焦的梁柱。县长刚回到任上不久,他已经离开两年多了。许多人还流落在邻近地区。而舍资距省城不足八十英里,土匪占领达十八个月之久,却很少或从未遇到过抵抗。(13)
斯诺的“四年以前”,正好是艾芜走过时候的1927年。可见土匪、盗贼在艾芜南行时确是真事。不过,至今并没有材料说明,艾芜曾经在行走、流浪的路上碰到过甚至加入过小说中所提及的那种盗窃团伙,而小说本身也能说明这一点。
作为小说,《山峡中》的不少关键细节是很模糊、甚至是不合情理的。
故事中半夜时分魏大爷一伙瞒着“我”,悄然将小黑牛抬出去,扔进江底。既然是“瞒”,小说中却又写“老头子发出钢铁一样的高声,叱责着”——全然没有了瞒的意思。同时,艾芜这类小说往往惯于并长于写景(跟他亲见有关),而拙于细节的想象与刻画——虚构究竟是叙事中更为高超的技艺,其时的艾芜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他一时还周转不灵。
另外,在小说人物的话语中,也可以见出艾芜并未身临其境,而到处是想象留下的生硬痕迹。小说中人物对话中的用语多是艾芜自己的四川方言与书面用语的一种古怪混杂。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你是哪个的孩子?”在四川方言中,尤其乡下人——更不用说这些社会游民——是不会用“孩子”这样书面化的词语来称呼小孩的;“我的足怪疼哩”,其中“足”也是一种很奇怪的用法,四川方言中多用“脚”代替“足”,所以在那里“足球”被叫做“脚球”。(14) 而“比我小块的野女子”、“野猫子做出焦眉愁眼的样子”、“他真是个该死的家伙,不是爸爸估着他,说着好,他还不去呢!”等等又是典型的四川方言——“焦眉愁眼”是四川乡下人典型而生动的说法;“小块的”(人)也是成都郊区包括艾芜家乡新繁一带的地方方言;而“估着”(他)甚至在字典上根本没有这种用法,只是在四川方言中很常用而已。
从小说的这些情节细处与用语中可见,艾芜并没有真正遇见并参与过这种盗贼团伙。因此,小说本身在细节想象方面的欠精确,一方面可能由于写作技巧的不够娴熟,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作者本人缺乏相应的经历和体验。这也是艾芜此时小说写作的一个特色:真实的流浪,加上流浪途中听来的传闻和自己想象的一种混合物。
但他如何以及为何如此想象他的流浪与写作?
3.想象的方法与革命话语
流浪,传闻,侠义小说的阅读经验,这些还并非艾芜写作这篇小说的全部底子,这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强有力的牵引——左翼的革命文学话语。
艾芜并非在滇缅群山的流浪路上写作这篇小说的。当初的流浪与后来的写作之间,时间与空间都已经有所腾挪。艾芜1931年被缅英政府驱逐回国,1932年在上海开始左联的活动,1933年3月被捕,后被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同年9月经左联营救后交保释放。出狱以后的艾芜,对以前左联交待的“革命工作”(在此时很多左联人士眼中,似乎只有组织工作、政治运动,以至贴标语、散传单、飞行集会才算得上是“革命”,而文学写作并不重要)不再那么热心。这在当时就引起胡风等人的不满,认为艾芜被逮捕和坐牢吓怕了,甚至讽刺艾芜是“左上来,右下去”。(15) 可以想见,在自觉不自觉之间,文学写作成了艾芜说明自己的最好方式。胡风的说法也完全可能使得艾芜在以后的行为包括写作中,更加小心翼翼——免得被别人抓住把柄,成为嘲笑的对象:革命队伍中的懦夫。这种憋着一股“革命”劲头的方式,无形中规约着艾芜随后的写作。
《山峡中》正是写于这个时候,1933年的冬天,艾芜坐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对当初滇缅群山中流浪的回忆已经不可能是纯粹流浪经历的实录。左联内部关于革命尤其是政治革命的强烈诉求,无可避免地在艾芜的写作(尤其是当他试图用写作——“文艺工作”来证明自己的革命热情时)中有所流露,这在小说中表现得很明显:“山峡”内、外之间的张力尤其在小黑牛惨死的根源性问题上凸显出来。
小黑牛的死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件残忍的行为。在这一点上,小说中的人物和小说叙述者都没有否认,但吊诡的是,小说对魏大爷并无过多的责备,仅只表达了一种十分矛盾的价值立场:对魏大爷的言行既同情又谴责。究其根本,艾芜要引起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山峡“外”的话题——革命话语。
虽然将受伤同伙处死的是魏大爷,但小说谴责的真正对象却并不是他,而是将小黑牛“逼上梁山”作盗贼的张太爷——他夺取了小黑牛的女人、山地、牛儿。虽然小黑牛在山峡外面的“那个世界”和山峡中的“这个世界”之间闪避,最后仍免不了悲惨的结局。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叙述技巧而言,小说详细交代了小黑牛何以在魏大爷的世界中被处死的原因,而在张太爷的世界中,作者似乎根本不需要交代原因,似乎那是一个人人明了的情形,不需要解释——在他看来,阶级压迫和剥削是一个人人明了于心的普泛事实,这才是这篇小说所揭示的小黑牛悲剧的社会学根源。这意味着,虽然小说的叙述重心似乎在讲述“山峡中”发生的悲惨故事,但更深处埋藏的或者说小说的终极目的却是对“山峡外”阶级压迫的揭露。正是这种隐含的左翼革命目光,使得小说故事的讲述者对魏大爷一伙以及被他们处死的小黑牛都满怀同情,尽管这两者本来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被处决者,一个是死刑的决定者和执行人。
隐含的革命话语,反过来又使得小说的作者和故事叙述者的身份更加复杂。
如前所述,对于当初游走在滇缅群山中的艾芜而言,他(或者流浪读书人“我”)对魏大爷的盗贼团伙除了同情之外,更有批判和否定,这就意味着他认同的是跟魏大爷等人不一样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游民,而最多算是一个流民。但对于1932年加入左联参加“革命”、1933年坐过国民党政府监狱的艾芜来说,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他已经接受了跟1930年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新东西——社会革命理论,他要认同的已经不再是小说中那个流浪读书人所认同的社会秩序了。他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工作和写作,并为此坐牢。这个时候的“革命”已经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的专指政治上的激烈变革,含有为促使政权更迭的暴力手段合法化的倾向了,即是语出《周易正义·革卦》中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而不是广义的泛指一切事物的变革、更新之义。(16)
因此,从1930年代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上看,艾芜又可以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游民,而不仅仅是先前小说中的流民形象。作为作者的艾芜,他已经将魏大爷一伙人当成了社会革命的力量,因为游民意识、游民文化的非规范性特征的确对现实的社会秩序起着瓦解作用,游民就其本质来说是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而且他们不会使用现代的非暴力手段去保护或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即使采取这种手段,统治者也要镇压(就如艾芜的被逮捕与坐牢一样),而反映这个阶层意识的文艺作品也不例外,它们教给人们的除了暴力以及为了实现暴力的种种阴谋以外就没有其他。中国帝王社会之所以延宕了两千年,与暴君专制——“暴民乱治”——暴君专制这种恶性循环密切相关。
作者和叙述者对魏大爷、野猫子式的社会游民既同情赞赏,又批判反对,其实也是渊源有自。王学泰分析过会党活动:(17)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初组织革命力量时看到了会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有组织的力量,因而革命党与会党联合,一向为清政府严禁的会党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但随着清政府的倒台,对秘密组织的强大压力随之消散,会党这股人数众多文化低下而又有组织的力量真像出于柙的“虎兕”,令人恐怖。由于会党活动的公开,游民各种不正当的谋生手段都表现出来了,而且变本加厉。(18) 于是,许多地区政权在建立稳定之后马上公布取缔会党的文告。
而左翼之所以对这种作品感兴趣,又恰恰是他刻画了与1930年代的主流社会相异的生存空间,这正好和左联中被抛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群相似,他们共同起着冲击主流社会秩序的作用。所以,左联十分感兴趣的东西,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人士眼中,就是另外一番意味了:
云南伪省政府驻南京的办事处,就提出过抗议,说我关于描写滇东的文章,歪曲了事实。《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就作为来函照登,发表在《自由谈》上。(19)
因此,当初的流浪和事后的写作,以及期间艾芜所经历的种种,在时间和空间的腾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艾芜或者小说的叙述者身上其实混合着(对于魏大爷等人所反抗的社会来说)流民、(对于其时的国民党政府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而言)游民等多重身份,而更深处则是革命话语的制约,充满了革命者的想象。
三 命名与书写:本名、笔名与作家意识
艾芜对于自己复杂的身份,并非毫无自觉。
1934年,艾芜除了继续在报刊杂志上以“艾芜”这个笔名发表小说以外,还在《申报·自由谈》上,从1934年1月16日到次年的9、10月间,发表大量回忆自己当年流浪的散文、游记。艾芜的回忆性散文,得到了《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的赞赏。据艾芜回忆,早在1933年3月,《申报·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发表了艾芜的小说《我的爱人》,是用“艾芜”作笔名,紧接着艾芜被捕入狱, “后来他要我改个笔名,躲避国民党书报检查的麻烦,我便使用了刘明。这意思等于流民,又加我母亲姓刘。”(20)
艾芜本名汤道耕。从“汤道耕”,到“艾芜”,再到“刘明”,身份与命名的演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艾芜在个人与主流社会、组织之间不断的摇摆——不管是在仰光参加共产主义小组,还是在上海的左联时期,乃至以后的写作和生存中,艾芜与组织的关系都始终是相当独特的:一方面渴望组织、集体,另一方面又有流浪者个体对自由的向往。所以,从汤道耕到艾芜到刘明,可以揭示一个作家的一生,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在这个作家笔名的“一生”中看到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汤道耕,这是身为乡下读书人的祖父给艾芜的命名,意思很明显——耕读传家。这个名字恰好传递了民国以前(汤道耕生于清光绪30年)宗法和家族制度或者传统主流社会的全部内涵:不管是农民的道“耕”,还是读书人的耕“道”。从“耕”的方面讲,如前所述,艾芜家里很快就已经无地可“耕”;从“读”的方面讲,艾芜出生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即行废除,传统的学而优则仕道路已然堵死, “读”也茫然。当“耕”和“读”都不能传家的时候, “汤道耕”这个命名也就失去了意义。
于是,祖传的命名汤道耕被汤道耕自己的命名艾芜所取代。
“艾芜”这个笔名,来自胡适的“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也来自艾芜自小阅读的中国传统侠义小说,或者说中国游民文化载体的侠义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这是艾芜流浪途中在云南昆明给刊物投稿时的一些笔名:爱吾、汤爱吾或者汤艾芜。这些大同小异的笔名中,包含着道耕最感兴趣的两个东西:胡适的“大我”与“小我”之辨,以及《三国志演义》、《七剑十三侠》、《七侠五义》、《小五义》等小说中的侠义英雄。
当时我名字叫汤爱吾,吾就是我,爱我自己的意思。这里说明一下,我读过胡适之写的一篇文章,说社会是大我,个人是小我,小我一定要好,然后大我才会好。所以我那时不吃烟、不饮酒、不打牌,为的是要使社会好,首先要使自己好起来。我后来觉得要隐晦一些才好,爱我嘛,容易误会成自私自利,所以我才改成现在草头的艾芜两个字……(21)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科学与人生观序》、《不朽》等文章(22) 中的确反复宣讲过个人的小我与社会、人类的大我之间的关系。胡适引用易卜生的说法:“我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不算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认为这就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因为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从来不苟言笑的艾芜,颇能接受胡适的这些人生观念,这其实与祖父教给艾芜的所谓一介不以与诸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或者古人进退之间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都非常容易找到契合点,接受起来没有困难。而自己、个人或者说“小我”并不因此就没有意义和价值,相反,胡适赋予了这个贫穷得一无所有的小我以绝大的价值和意义。至少流浪途中的艾芜是这么理解的。正如胡适所许诺的“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世界的关键全在我们手里”,如此这般任重道远。千斤重担都压在一个人身上了——虽然这个人现在一贫如洗。
艾芜小时候读过的侠义小说,同样有力地影响着流浪途中的想象,也包括他写作时候的笔名——怎样为一个文字的自我、虚构和想象的自我命名。如果说,少年时代阅读侠义小说所产生的种种幻想:独来独往、腾云驾雾、云游天下,抡枪使棒,口里吐出一道白光,割人头于千里之外……这些还是少年儿童的天真想象,那么,经过真正的浪游,艾芜体会了到处都是不平,饥饿疾病,冷眼和嘲讽,处处都是无处诉说的委屈。儿时阅读时所产生的幻想,并没有因为年龄增加而消失,恰恰相反,这些奇幻的想法可能来得更为强烈,也只有这种不着边际的侠义的想象能够让心理得到一时的平衡,委屈得以舒解。艾芜后来解释自己笔名的来源时候说:
我对于《小五义》中的小侠艾虎,很为倾慕,觉得将来至少也得成为他那么一个小角色才好。我想我后来的笔名,同他是不能说没有一点牵连的。(23)
还有一个含意是取其谐音,我那时喜欢读《七侠五义》,这本书里面有南侠、北侠、双侠、小侠,记得他们的名字是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顺着排下来就是小侠艾虎。因为我喜欢这个人,所以我这个笔名就是谐艾虎这个音的。他们云游天下,到处打抱不平,我除不会武艺之外,不是到处都走到啦。(24)
这样看来,“艾芜”这个笔名,非常有趣地含混了许多不一样的内涵:从胡适那里,当然还有祖父那里,道耕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或者更准确地说,道耕似是而非地将从西方来的、胡适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和从中国传统来的、祖父教给的独善其身的思想混淆在一起;也从侠义小说以及包括父亲的袍哥身份中接受了中国文化中的小传统——游民文化。“艾芜”这个名字也就来自传统侠义小说、游民文化中的文艺作品与五四新思想的一种混合。
“刘明”这个笔名则来自艾芜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和定位,尤其是当他在上海的亭子间里沉浸于漂泊往事的回忆时——在川音中,“刘明”正与“流民”完全同音。在这里,艾芜明确地把自己定位成了社会“流民”。
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思想、五四新思想(西方思想)的影响,使得艾芜在流浪的过程中,始终把自己看成一个读书人,跟那些真正的社会流民(虽然从“流”状态上讲,他早已是个名实相符的“刘明”/流民)和游民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某种距离:在苦力们住的旅店中,他要在滑竿苦力老朱的烟灯旁读几页书——虽然如果听从苦力们的劝阻,在店老板面前假装成一个抬滑竿的苦力,就可以节约一些店钱。(25) 而所谓假装,其实对艾芜来说并不困难:他早已经一贫如洗,赤脚或者穿草鞋,跟抬滑竿的苦力们一道行走在川滇缅群山之中,唯一困难的是艾芜对自己的身份认定,他在意识和潜意识中还是无法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流民;同样,当他在茅草地山中马店里作杂役,店老板既要他作杂役该干的事——打扫马粪,又要他当先生教书,这让他感到很不自在——因为这两个身份在他看来有着很大差异,他在意识中无法调和(杂役的)“汤大哥”和(教书的)“先生”这两个称谓之间的矛盾;(26) 而在《山峡中》,他就真像那个流浪读书人“我”:要在盗贼团伙的篝火旁读几页书。而且,怎么也不会参加那个社会游民组成的盗贼团伙,虽然也在小说中表现了对他们的理解和同情。
但不管是游民还是流民,不管是旧时代的读书人还是新思潮影响下的知识分子,艾芜的这路写作,很快得到同样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左联的欢迎,艾芜也因此逐渐走上了文学写作的道路,并最终进入现代文学史,虽然事实上这之后关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以及左翼文学写作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确立,还有另外一个长长的故事。
结语
对于本文前面设定的论题而言,通过对艾芜《山峡中》小说的阅读,以及对其笔名、生平等的分析,可以见到这个左翼作家写作中的种种矛盾对立的因素:小说中读书人“我”、小黑牛与魏大爷、野猫子等人物形象之间;艾芜流浪的历史与小说的想象之间;作为中国社会大传统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与作为小传统的游民文化之间;古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之间,等等。当然,如果就这篇小说本身而言,在所有这些矛盾对立中,关于政权更替暴力革命的合法性论证以及游民文化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最高理想依然是其中交织着的一明一暗的主线。这些复杂资源的相互纠缠,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简单地用革命或者非革命的模式予以解说,进而也就当然无法简单地用一个笼统的“下层劳动人民”来概括这篇小说乃至艾芜甚至其他左翼写作者笔下的人物设定。
注释:
① 沈从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原载1936年10月25日《大公报·文艺》,见《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01~108页。
② 易崇辉:《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③ 由8篇短篇小说组成的《南行记》是艾芜于1933年冬集成,并于这年11月1日写成序言,交给北平利达书局。因迟迟不见出版,艾芜后来索回书稿,交由巴金任总主编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入“文学丛刊”第1辑1935年出版(其中的《松岭上》于1934年4月在《新中华》第2卷第7期(文学专号)上发表时题为《松岭的老人》)。本文所引该小说原文皆出自此书,不另注。
④⑦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1998年版,第308、309页;第308页。
⑤ 以下关于社会游民问题的描述,借鉴了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及其中李慎之的序言《发现另一个中国》,学苑出版社1999年北京第1版。
⑥(11)(17)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北京第1版,第618页;第72页;第565页及以下。
⑧⑩ 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言”,第12页。
⑨ 原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4号,1919年4月。引自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83页。
(12) 王毅:《艾芜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以下。
(13) [美]斯诺:《马帮旅行》,李希文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旧版书系),第61~62页。
(14) 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15) 艾芜:《出狱以后》,唐文一、刘屏主编《往事随想·艾芜》,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195页。
(16)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8) 艾芜在《大骡子》一文中,回忆过当年镇上袍哥在他祖父那里强行“借”骡子一事。见《童年的故事》,建国书店,1945年上海第1版,第37页。
(19)(20) 艾芜:《漂泊杂记·重印前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页;第2页。
(21)(24) 艾芜:《我是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的——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文联座谈会上的发言》,汪华藻选编《谈小说创作》,第16页。笔者于2002年11月18日访问艾芜家乡时发现,在新繁清流场,“艾芜”和“艾虎”这两名字发音完全一样。
(22)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胡适论学近著》,1935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引自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498~501页。
(23) 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艾芜文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
(25) 艾芜:《我的旅伴》,华夏书店,1946年2月初版。
(26) 艾芜:《在茅草地》,《南行记》,1935年12月初版,第103页等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