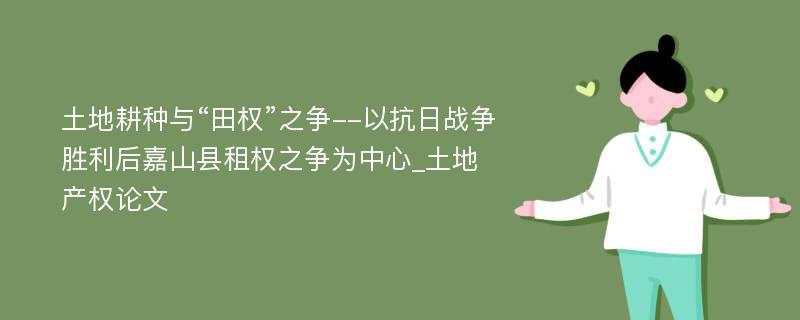
土地耕种与“田面权”之争——以抗战胜利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嘉善县论文,之争论文,抗战胜利论文,纠纷论文,土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7095(2008)02-0081-08
一、引言
以“一田二主”为特征的“永佃制”在江南地区十分普遍,对于这一现象,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有关“田面权”性质的讨论即是一个焦点。杨国桢指出,“田面权”是在永佃权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佃耕的土地能否由佃户自由转让,是区分“一田二主”和永佃权的根本标志。[1]96-102黄宗智认为:“永佃可以演化为双层土地所有权,也可与双层土地所有权混合或共存。两者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他们之间是“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连续统一体”。[2]103本文第二作者在最近的研究中,将上述表述进一步归纳为以下图式:
永佃权——相对的田面权——田面权[3]
“永佃权”指的是拥有较长的租期,却不可转让佃权的租佃方式;“相对的田面权”指的是拥有较长的租期,可以转让佃权,却因欠租或其他原因可以撤佃的租佃方式;而“田面权”亦称“公认的田面权”,不仅在租期及佃权转让方面与“相对的田面权”相同,而且还具有即便欠租也不可以撤佃的特征。也就是说,在“一田二主”的地权结构中,“公认的田面田”的分化形态最为彻底。
然而,此前几乎所有的相关讨论,都集中于“田面权”人(包括相对的田面权人和公认的田面权人)的法律属性和社会属性上。即便是上引本文第二作者的研究,虽较前人有所进步,但也只是讨论了土地产权从永佃至相对的田面再至公认的田面的分化之事实,却未见其对“田面田”的分化过程加以探讨(日本学者寺田浩明在相关研究中涉及了田面田分化的某些具体过程,他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田面田主和田底田主授予“一田二主”耕作模式以正当性的具体途径,其研究的着眼点在说明田底田面的法律属性上,并未对田面田分化过程进行具体的区分。见寺田浩明:《田面田底惯例的法律性——以概念性的分析为主》,杨一凡总主编,本卷主编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四卷,明清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4—422页)。江南土地产权的分化过程仍有许多模糊不清之处。
这是因为,实际的租佃市场并非静止不动。在一个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租佃市场上,“田面权”的分化过程极为复杂。对于产权尚未分化的土地所有者来说,“田面权”的出现似乎使他们拥有了更为灵活处理土地产权的可能,例如,他们可以在保留田底的同时,出租或出售田面。然而,当他们脱离与土地的耕种关系,将土地出租时,新的耕种者就可能成为其“田面权”的侵蚀力量。而对于那些只拥有“田面权”的所有者来说,他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田底”业主的束缚,但由于它的产权价值必须通过耕种才能实现,并依靠耕种行为来做保障,故当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正常耕种时,“田底”业主仍然有可能对他的“田面权”构成威胁。因此,仅从法理上讨论“一田二主”实际上是不全面的。
本文主要采用嘉善县档案馆所藏抗战胜利后的租佃纠纷档案,厘清土地耕作与土地产权的关系,藉以展示“田面权”的分化过程,并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二、从“久佃”到“永佃”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田面权的产生,其途径不外乎农民通过垦荒取得田面权;农民出卖田底,保留田面权;由于长期使用,习惯形成田面权;以预交押金的方式,取得田面权等。一般的看法是,“田底”与“田面”作为两个互相独立的产权可以分属不同的个体。“田底权”业主占有土地但无权干涉土地的使用情况,“田面权”业主则可以独立租赁、转让或者出售该“田面”。
因长期使用而习惯形成的田面权,在杨国桢看来,大抵属于这种形态:农民长期“守耕”,其永佃权得到地主的认定;这种“守耕”,往往又是“霸耕”。[1]96为了保证地租来源的稳定,地主一般不允许佃农将佃耕的土地自由转让。不过,佃农以各种形式“私相授受”,地主也逐渐认可了这种既成事实,最终产生了“田面权”。[1]100很显然,相较于“永佃权”而言,“田面权”无疑更具吸引力。
在嘉善县现存的1945~1949年国民政府法院档案中,有一批租佃纠纷档案,共有20多个卷宗,其中的案例显示,企图通过长期“守耕”、“霸耕”的方式而获得“永佃权”或“田面权”,过程漫长且曲折。
案例1:声请人许锦才,对造人陈阿发,时间:1947年。①
声请人祖遗水田十六亩座落治下车站北首,向为自行耕种,讵于二十六年间,突遭敌寇侵略……不得已暂放对造人租种,当时言明如胜利开始,当即收回自耕,幸前岁国土重光,向其要求再次拖延,最后挽人讨种,一年为期,决定三十六年度交还等语,惟声请人原冀息事为本,从其所愿,不图本年叠次催促其履行诺言,反以春耕为辞,似此得寸进尺,长此永不了期,使声请人如何忍受,为此不得已状请……谕令返还水田十六亩。②
在案例1中,“声请人”许锦才自称争讼之田系祖上遗下之“底”、“面”完整的产权。拥有土地完全产权的业主,有充足的理由收回自己的产业。问题是“霸佃”的佃农,之所以敢无视业主的要求,占地不还,其原因就在于,他耕种这16亩水田,历时已有8年。结合本文所揭其他案例分析,在民国时期的嘉善,有“久佃成永佃”的惯习,战争的结束破坏了佃农陈阿发的计划,由此而导致纠纷的产生。
案例2:原告张庭华,被告姚金生,时间:1947年。
缘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间挽中租种原告佃种本邑永七区北润圩水田八亩,约定三年为期,当付押租米三石,现届期满,向其取赎,拒绝不允,曾经声请钧院调解,亦无效果,为此万不得已状请钧院恃案审理,判令照约返还,并负担一切诉讼费。②
与案例1不同的是,案例2中原告自己并非田底的拥有者,而是一个田面权人。被告之所以敢在佃耕3年后,霸佃不还,就在于他在租佃时,交纳了三石租米作为押租。案例1中的原告是向被告“讨种”,而案例2的原告却是向被告“取赎”。“取赎”的难度高于“讨种”,这可能就是只有3年佃期的佃农也敢于霸佃的理由。
再看案例3。案例3与案例1颇为相似,争讼之田也是底面俱全的业田。与案例1不同的是,即佃耕者不仅“久佃成永佃”,而且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将佃耕土地转佃他人,企图成为事实上的田面权人。
案例3:原告朱祥龄,被告项尚贤、项善根,关系人鲍松泉,时间:1946年。
原告祖遗坐落本县四南区西旺圩水田十四亩四分,曾于民国二十二年间由被告项尚贤名义出面租赁,当时定有期间为五年,即二十六年度为届满。孰知二十六年间正拟收回自耕,突遭战事停顿,迨至胜利以后,被告等兄弟之间公然勾串一气,擅将是项土地全部转租于关系人鲍松泉耕种图利,同时收得押租糙更(粳)七石,私自朋比化用,故原告骤闻惊骇,一再交涉,虽关系人感觉明知错误,曾挽人在三十六年二月间直接向原告订立租赁契约,事实上已与被告间无关系之可言,何奈该被告等不仅贪而无厌,且抑罔顾法纪,频频妄加干预,侵害租赁,显有阻挠原告权利上行使,似此情形尤难容忍,核其所为,实背土地法第一百零八条及第一百十四条第二项之明文已无疑。故请求被告等终止租赁契约,排除侵害。③
被告在佃期期满之时并未退佃,是因为战争中止了正常的解约行程。5年租约加上8年战争,本案被告实际耕作本案水田时间长达13年。佃耕时间如此之长,使得本案被告敢将佃田转租他人。这一案例让我们猜测,在民国时期的嘉善,可能存在耕种时间长达10年以上即可获得“永佃”的俗例。只不过,本案被告似乎忘记了,“永佃”并非“田面”,从“永佃”至“田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其结果是,本案被告败诉,原告产权得到了维护。
对于产权并不完整的业主来说,如果面临类似的纠纷,其胜诉的难度就要大一些。只是因为至抗战之前,对于各种类型产权进行保护的法律,大体具备。案例4即是一例。
案例4:原告裘阿大,被告罗阿炳,时间:1946年。
原告将祖遗有地上权之租田十二亩让与堂兄裘善行……其不善耕作,转让被告罗阿炳,限期四年,凭中立有字据,并载明顶价三百元……民国三十四年,期限已届,因堂兄已故,由原告备价取赎,而被告要求留种一年,原告亦许之。时至今春,理应归还,竟恃强霸种……钧院传集调解,又无理要求赎价……恳请法院依法裁决,使赎回田亩,以利春耕。②
原告裘阿大实际上是以自己拥有“田面权”的名义要求赎回自种的,被告辩诉中却认为裘善行的土地决不可能是原告让与的,因此以必须证明被告是否拥有“地上之权”为由要求驳回原诉。经审讯得知,原来在裘姓之外,钱顾两业主才是该田“田面权”的拥有者,只是该田一直由裘家人耕种,“裘善行的父亲种过后,裘善行种,裘善行种过后裘阿大的父亲种,裘阿大的父亲种过后,裘阿大种”。②原告虽然没有“田面权”,但却通过长期耕种的方式获得了“永佃权”,这一权利得到了法院和业主的认可。因此,在警告原告今后“不得未经业主同意私自将田转让”的情况下,法院支持了原告将田赎回自种的要求。
在这个案例中,裘家自认为有了“地上之权”,即“田面权”。事实却并不如此,因为,再长期租种也不等于“田面权”本身之获得。当然,本案的关键不在于原告是拥有“永佃权”还是“田面权”,而在于被告的拖欠行为本身。裘善行的去世给被告罗阿炳以可乘之机,他利用该田“田面权”所有者的不确定性,在佃期已满的情况下试图继续耕种。如果业主未能及时追讨,长此以往,他就可能获得该田的永佃权。在几个转佃者本身还没有获得“田面权”的情况下,新来的承租人却想通过霸种来获得永佃,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久佃成永佃”的事实或可能性。
三、“永佃”侵蚀“田面”
案例4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永佃的时间越长,其转让佃权的可能性越大,永佃权也就越接近于田面权。于是,我们就能理解,各种霸佃行为的动力,其实都暗含着他们对于“田面权”的渴望。倘若足够幸运,业主未予追究,佃户就可能因此而获得“田面权”。
案例5:原告江明昌,被告王林鸿、颜义堂,时间:1947年。
原告所有坐落嘉善九南区结字圩底面水田十七亩,于民国十年二月间立约租于被告颜义堂耕种,定期五年,到期后仍以不定期限租赁,继续耕种,本年一月有被告王林鸿之子王阿漠未征原告同意,私自雇工开耕……王阿漠供称该田亩是向被告颜义堂以四十三石米顶来的,立有契据……请求确认该项顶田契约无效,与被告颜义堂终止租约,返还系争水田,责令被告负担讼费。④
底面产权均为原告江明昌所有的土地,被被告颜义堂绝顶与他人,颜义堂无疑是在行使“田面权”业主的权利。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租种原告土地已有20余年,事实上已经获得这17亩水田的永佃权。如果被告以此为满足,这一情状或许可以继续维持,然被告进而将土地转租他人,并收取高额顶金。然而,“久佃”即使能够转化为“永佃”,却并非获得“田面权”的充分保证。由于原告及时发现并积极制止这种越权行为的发生,法院最后判决被告将水田归还原告耕种,诉讼费用由被告平均分摊。
案例6:原告钟允若,被告卓森林,时间:1948年。
原告所有座落本县八中区南宙圩底面水田八亩,向由被告租赁耕种,在抗战时积欠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田租二熟,因原告避乱在沪,故置不追,该被告认为懦弱可欺,得寸进尺,竟将该田视为已有,私自转佃于关系人耕种,并预收押租米四石,原告于三十六年冬闻悉之下即向其交涉收还自种,被告一味延宕,置之不理,窃思产权之保障全恃法律,似此情形,原告若不加闻问,其田面权将从此消灭,为此依据修正浙江省佃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三项及第五项之规定,具状恳请钧院迅予传案审理,判令该项田亩交回原告自行管理耕种,借保产权而维法令。⑤
1933年7月23日公布的《浙江省二十一年二五减租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租佃定有期限者,依其约定。其未定期限,非有左(下)列情事之一时,业主不得撤佃。”其第三项规定,“业主收回自耕时”;其第五项:“佃农未经业主承诺,私行转佃时。”[4]603很显然,原告收回佃地的理由,是基于他与被告之间没有约定佃期,所以他可以自耕或佃农私行转佃为由,收回佃地。
然而,原告的这8亩水田,“向由被告租赁耕种”,这表明被告已经获得了“永佃权”。上引《浙江省二十一年二五减租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有永佃权之佃农,非欠租达二年之总额时,业主不得撤佃。但当地有特殊习惯者,从其习惯。”依此,如果不是被告转佃,试图将“永佃”转为“田面”,原告不可能剥夺被告之佃权。被告之所以敢于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战乱,原告无暇顾及出租田亩,被告则企图以既成事实,迫使原告承认从“永佃”到“田面”的转移。原告在状词中称“若不加闻问,田面权将从此消失”即是此意。
上述两案的被告均属在未获得“田面权”的情况下,擅自行使“田面权”业主的权利,他们的企图虽然没有得逞,但却使业主的“田面权”遭到了不大不小的侵蚀。除此之外,佃户霸耕不退的行为也牵制了业主“田面权”权益的实现。这类佃户虽然没有将田私自转让牟利,但是在业主意欲收回土地的时候,他们多半采取拖延战术,不愿将田退还。
案例7:声请人冯佐明,被声请人沈有福,时间:1946年。
声请人之父本自耕种为业,讵遭乡间匪劫,旋迁至城厢居住,不幸家父去岁因病故世。可怜身后萧条,丧费无着,将向来自己耕种坐落治下牌楼浜之水田十一亩急图出售,提前先向对造人通知,何奈不肯接受,于是不得已转售他人耕种,并同时通知对造人同意。不图迄今反以掯不退田,种种阻挠,伏查对造人既无永佃权关系,又不定有期间,如此妨碍声请人之权利,不得已提起本件调解。⑥
本案中的声请人冯佐明,一边声称这11亩水田“向来自己耕种”,一边又将佃户沈有福列为“对造人”。推想声请人所谓的自耕,是在佃出土地以前。从本件档案全宗中可知,被声请人沈有福是一个本分的佃户,他虽有欠租,但所欠极少且时间不长(欠上一年租米两斗五升)。在业主要将水田出售撤佃的情况下,他提出了异议,并在没有“永佃权”的情况下拒不接受调解,仍坚持不退佃。
主张撤佃出售土地的声请人,应当拥有这块土地的田底与田面。这里的“转售他人耕种”似乎是田底、田面一并转售。然而,在面对土地的耕种者时,他却显得很无奈。土地的耕作者,似乎已经认为自己获得了“永佃权”,于是,虽然还不能说田底的出售变得完全不可能,但至少业主的“田面”权为“永佃”所牵制,即理论上田面业主能够自由处置自己的“田面权”,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受到耕种者的牵制。更有甚者,业主的土地出租过程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新的“田面权”的产生过程。
案例8:原告孙奇僧,被告陈关祥,关系人孙全生,时间:1947年。
告诉人有祖遗坐落本县现编洪溪镇第十保内底面自田三亩,由被告人耕种,因告诉人经商外地,管理不便,复以经济拮据,乃于去年委托关系人兜售与被告人受业,经商洽数回,旋即定期定约,讵于农历年底,忽然反悔做罢,因是延至本年二月开始另售与同村孙五毛管业耕种,在定约之前,复问明被告人并无异议,迨孙五毛至该田内施工耕种时,陡遭被告人阻止,甚至身卧田内,不许施工,调解无效……被告人仍将该田强行耕种,迄今无法解决,但查该田在出售之初,因念及被告人耕种问题,特先向被告人兜售……被告人强行耕种,不可理喻,请求将该田让还,并赔偿损失。⑦
原告出租土地的底面原本并未分离,他完全有权力撤佃出售他人。不过,被告的长期租种使得原告的撤佃变得不可能。被告认为“是项租田租种已达百余年,早已取得合法之永佃权”,而且自己未曾短少租米,故原告的撤佃请求毫无理由。可见,被告以自己长时间的耕种为理由,声明获得“永佃权”,这一观点获得了法院的认可。
案例5和案例6的相似之处在于有永佃权的佃农,如果想进一步攫取田面权,就有可能不仅得不到田面权,反而失去永佃权。案例7和案例8则表明,只要固守永佃权,且不欠租,撤佃就会变得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告的“田面权”也已经遭到侵蚀,因为被告拥有的“永佃权”使得原告根本无法完全行使自己的“田面权”权利。究其原因,除了法律保护的专门条款外,其实原告暨不耕作者的“田面权”在被告的长久耕作中至少部分地遭到侵蚀。
四、“田底”牵制“田面”
“田面权”独立地位的确定一方面让部分土地所有者面临地权分化的危险,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新的土地产权所有者,即一批只拥有“田面权”的所有者。从理论上说,这批“田面权”的所有者能自由经营土地而不受“田底”业主的干涉,但由于“田面权”权益的实现关系着“田底权”价值的实现,因此,二者相互独立,却也互相依存。
案例9:原告谢亭侯,被告裘大发,关系人詹阿泉,时间:1946年。
原告上诉事件原委:原告曾于民国二十九年秋由吴阿牛顶给佃权计四十一亩,顶价六百元,翌年代缴汪业保证金二百念元,两共八百念元……告诉人于翌年冬欲求治气喘病,凭中谢品荣、赵阿泰暂顶与詹阿泉耕种,言定三十五年芒种双方凭中回赎……告诉人于今年九月初浣业已凭中与詹阿泉办理出赎准备春耕,告诉人曾于前月中浣适路经过南区润字圩,窥见田内二三工人操作,不胜诧异,探悉被告占其三十五亩,擅自指使工人工作,告诉人……与被告理论,置之不理,违反法律,侵霸他人权利,抑且彼此顶让,被告均系明白,并非有过接洽通知,盖由詹阿泉于三十四年份为日寇军米猖獗及乡间各种军队苛捐并地方杂税,实乏力维持,因此荒芜且报告洪溪镇公所在案……请求令其停止工作并判令负担本案诉讼费。②
原告谢亭侯自称从吴阿牛手中顶来41亩土地的“田面权”,后来转顶他人,并“代缴汪业保证金二百念元”⑧,我们暂且认为他拥有了土地的“田面权”。不幸的是,受顶土地的詹阿泉在1945年将土地抛荒了一年,当原告要拿回土地自种的时候,却发现了另外的耕种者,即被告裘大发。通过被告辩诉可知,原业主吴阿牛声称自己早于1942年就与谢亭侯脱离了佃业关系,而将土地租给了詹阿泉。这与原告讼词中的表述大相径庭,我们无法考证孰是孰非,只因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故搁置一旁。被告接着认为即使原告所述属实,他也应该与詹阿泉或业主交涉,而不应该将矛头对准被告。②
此案的关键是詹阿泉的抛荒行为,不管谢亭林是否拥有“田面权”,抛荒行为都直接损害了“田底权”业主的利益。因此,为了使“田底权”利益得到实现,业主将田另佃无可厚非。这其实出现了一个悖论,倘若“田面权”属于谢亭侯所有,“田底权”业主根本没有权力对“田面”进行处置。不过,倘若“田底权”人不对“田面”进行处置,他的“田底权”就会受到侵害。可见,这种行为虽不合法,却也合情合理。当然,此案中的谢亭侯究竟有没有“田面权”,还要看他与业主的交涉结果,可惜的是此案再无下文。不过下面一个情况明确的案例可以弥补这种遗憾。
案例10:声请人陈希汉,对造人杨作扬,时间:1947年。
窃声请人自于民国二十六年间突遭敌寇侵略,善地沦陷,仓促逃亡浪迹他乡……幸今重光国土,卷土归来……讵所有当时坐落治下南星乡地区共计土地五十亩,何奈已在敌伪时期分别遭人公然侵占……除黄光连被占念一亩已无问题外,查有被占吴应富土地十五亩尚存观望,须视对造人如何为转移,惟该对造人个性暴戾,被侵占土地十四亩复经同乡会劝令返还,不吝始终据不接受,卒无要领,伏查该对造人凭借当时无效政府状态而公然占有,既无永佃权之存在,又未征得永佃权人之同意,且声请人因当时无非为不可抗力而逃亡,显未有意抛荒,情非得已,请求调解,要求对造人返还十四亩土地,以维私权。⑨
在同一案卷中未见该案的最后判决,但从后来被告杨作扬的辩诉中可知,原告陈希汉的要求一度得到了法院支持。然而,被告不屈不挠,继续辩诉如下:
辩诉人自于民国二十七年间逃难回来,乏田耕种,生活艰难,至二十八年份央中向袁姓业主租种善邑九南区天字圩荒田十亩,在袁前业主名下种过一年,至二十九年份前袁业主将该田十亩放弃于朱培生业主,是以辩诉人又向朱业主续进租票至今承种,历有多年,……不料突有陈希汉出为争种……辩诉人当初向袁姓业主租来时已经荒田出草,均系辩诉人垦熟承种,一切农具物件由辩诉人自行置备起来,与原告陈希汉绝对无关,即使该原告有永佃权,自二十六年份逃难抛荒已历多年,且业主早经弃卖断绝,究属该田面谁归何人租种,无非凭由业主朱培生之主权,此案务求传朱培生到庭讯明其事实……判令原告之诉驳回,本审诉讼费归由原告负担。⑦
本案结果:陈希汉承认田亩归杨作扬耕种,杨作扬于当年津贴陈希汉白米二石,上访诉讼费用各自负担。⑦
与案例9一样,本案的关键也在于抛荒。原告陈希汉本来拥有土地的“田面权”⑩,但是战乱迫使他将土地长期荒芜,这就给形成新的“田面权”业主创造了条件。“田底权”业主在合理不合法的情况下,将荒田另佃他人,经过开荒加长期耕种,新佃户合法取得了“田面权”。虽然这项权力的转移并非通过“田面权”业主,而是通过“田底权”业主来实现的,但由于“田底权”业主的利益损害在先,使“田底权”人获得了处分“田面权”的主动权。因此,当陈希汉战后归来,要求重新拥有“田面权”时,法院没有支持他的请求。不过为了对他曾经拥有的“田面权”表示认可,法院判令新的“田面权”业主对他进行了一定的补偿。
总之,在底面分离的情况下,“田面权”业主必须保证土地有人耕种,否则不仅是他的“田面权”利益无法得到实现,“田底权”业主的利益也间接受到了损害。倘若“田面权”业主无法保证这一点,“田底权”业主就会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攫取不属于自己的“田面权”,将田另佃他人。这就使得“田面权”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可能通过“田底权”业主转移到新佃户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独立产权地位的“田面权”仍旧受到“田底权”业主的牵制。
五、讨论
有论者称,1932年以后,浙江省政府订立《浙江省二十一年减租暂行办法》,将业佃纠纷之仲裁权,从专门设立的佃业理事局收于法院,使得佃农因无经济能力,又无知识,无力提出仲裁,故而业佃争议之申请,只有富农有可能,“此类仲裁,实为保护业方之法律”。(11)抗战胜利后嘉善县法院受理租佃纠纷,却并不能作如是观。
这是因为,上文所引各案证明,政府的目的并不是保护谁的产权,而是维持社会的稳定。在这个案例中,法院可能保护了田面权人的利益,而在另一个案例中,法院则可能保护田底权人的利益,甚至在其他一个案例中,法院可能保护佃农的利益。这并不是说法律无章可循,而是因为战争的影响使得原被告双方都有一定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回到本文讨论的主题上来,“田面权”的产生对农村土地租佃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让土地耕种者看到了获得土地产权的希望,大大加快了土地的分化过程。然而,对于不同的“田面权”所有者来说,“田面权”的确定却有不一样的意义。
一方面是拥有完全土地产权的所有者。“田面权”的确定使他们的完整产权有可能一分为二,从而使得土地产权的转移变得更灵活、更容易。然而,这种双层产权制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地所有者与土地耕作的脱离。当他们将土地出租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田面权”无偿分离的大门。新的耕种者可能通过长期的耕种而获得“永佃权”乃至“田面权”,或者通过霸种方式阻挠产权业主“田面”权利的实现,产权业主常常陷入“田面权”的保卫战中。
另一方面是单一“田面权”的所有者。法律赋予了他们独立的土地经营权,他们因此摆脱了“田底”业主的束缚。但是,由于“田面权”价值的实现直接关系到“田底权”业主的权益,因此,在租佃实践中,“田面权”业主的此项权利就有可能因“田面”价值的无法实现而被“田底权”业主转移给他人。在某种情况下,这种转移也可能通过保证税收来源的基层官员来进行。
可见,不管是哪一类“田面权”所有者,其权利的实现都受到不小的牵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其关键就在“田面权”与土地耕种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田面权”通过土地耕种得来,因此,也必须通过耕种来保障。一旦“田面权”业主不再亲自耕种土地,就很容易引发租佃纠纷,甚至权利的易主。“田面权”的这种特性也大大增加了交易市场中的租佃纠纷。
于是,我们可以清晰地描绘土地耕作与田面权之争的逻辑意义:土地业主与土地耕作的分离使得佃农霸佃成为可能,佃农霸佃又为“久佃”变为“永佃”、进而变为“田面”提供了可能。在无荒可垦、无钱购地的前提下,佃农尽可能延长自己的耕种时间,应该是获得“永佃权”乃至“田面权”最为经济的途径。进一步的推测是,霸佃还为“相对的田面”转为“公认的田面”提供可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土地业主加速离开乡村,更加速了土地业主与土地耕作之间的分离,而以抗租与霸佃为特征的暴力则成为乡村生活主旋律。近代江南农村的革命所呈现的特征部分与此有关。[5]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案例中有3个案例只有原告的起诉,而未见最后的审判结果,对于这类没有审判结果的案例,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测:一、原告所言属实,被告自动与原告达成了和解;二、原告夸大其辞,无中生有。而笔者愿意相信推测一,是因为笔者对这批租佃纠纷档案有一个总体的评价。纵观整批档案,凡属原告无中生有的,被告多半会理直气壮的进行反驳而留下反诉的材料,这种案例持续的时间一般比较长,而且材料也比较多。同时结合有明确结果的案例来看,原告无中生有的情况比较罕见,即使不是与事实完全吻合,大致相符却是常态。
②《裘大发等赎田、追回贷款等案卷》,嘉善县档案馆,285-3-254,第91,页码不详,第49页,第64页,第36—37页,第43页。
③《陆象当等契约无效及收回田亩案卷》,嘉善县档案馆,285-3-326,第184页。
④《有关终止契约无效及收回田亩卷》,嘉善县档案馆,285-3-327,第33页。
⑤《陆才银等返还田亩、耕牛等案卷》,嘉善县档案馆,285-3-257,第94页。
⑥《曹金林等返还田权、放赎典物等案卷》,嘉善县档案馆,285-3-258,第123页。
⑦《杨作扬等返回田亩及清偿租米等案卷》,嘉善县档案馆,285-3-256,第78页,第12页,第55页。
⑧汪业可能是这几十亩土地的田底权人。
⑨《孟阿寿等确认所属权、返回土地、确认佃产等案卷》,嘉善县档案馆,285-3-317,第135页。
⑩原告在状词中认为被告既无永佃权,又未经得永佃权人之同意,就擅自耕种土地,是为不法。可见,原告认为在经得“永佃权”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告才能耕种,这就意味着原告所谓的“永佃权”有转租的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原告所说的“永佃权”也就是“田面权”。
(11)陈淑铢:《浙江省土地问题与二五减租,1927-1937》,第5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