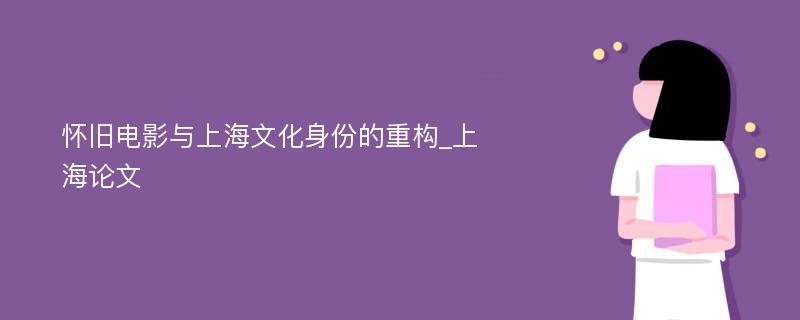
怀旧电影与上海文化身份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重构论文,身份论文,文化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幕上出现了一股“怀旧电影”的风潮,其中表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怀旧电影”尤为突出,并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研究的重要文本。本文所提到的“怀旧电影”,特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影片。银幕中的老上海与现实中的新上海形象在人们的视觉中交相辉映,彼此营造着上海这一都市空间中文化想像的共同体。“怀旧电影”生成的潜在前提是什么,其存在又有什么样的文化诉求,与当下上海的文化走向构成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怀旧电影这一角度对此展开相应的论述。
以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影片,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与影片描述的内容同期,即20世纪30年代前后,电影已经开始讲述上海当时的社会风貌。同一时间段落,同一地域空间,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得到反复的演绎,这本身就说明作为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具有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含义,具有可供多次演绎的可能性。与上海的发展相应,此时在上海兴起的电影艺术也已较为成熟,并形成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必然会留下这个繁华都市复杂的视觉文化形象。因此,对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的上海形象,有必要首先做一个回顾,以探讨与20世纪90年代怀旧影片中老上海形象的异同。
在以上海形象为表现对象的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现实主义风格的影片占绝大多数,这与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有着相同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起云涌,处于该时期的电影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左翼力量的介入。1930年8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1932年夏衍、钱杏邨和郑伯奇三人应邀加入明星公司,为20世纪30年代的银幕增强了客观描写社会现状的力度。这种新现象被当时的评论家称之为“新兴电影”。由于电影自身的特性和当时复杂的社会局面,新兴电影自身并不是一个严密一致的运动,在其内部有着不同的姿态。自然,在这样的语境下,讲述上海的影片也同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
首先是左翼思潮直接催生的电影创作。这些影片引入了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以阶级论调来剖析和批判社会,试图用这种价值标准来推翻旧的价值体系,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痕迹。被视为左翼电影运动“报春之燕”的《三个摩登女性》,通过三位女性不同的道路,指出只有面对劳苦大众,站在时代前列的女性才属于真正的时髦,显示出较强的政治化色彩。影片在塑造人物的同时,也致力于描绘上海当时的面貌。一方面当红明星每天出入于奢侈华丽的歌台舞榭,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工人、知识青年、艺人等下层百姓贫困凄凉的生活状态,影片中的上海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上下层严重对立。另一部代表作品《上海二十四小时》更加直露地表现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影片完全采用了格里菲斯式的对比剪辑法,一边是资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为富不仁,奢侈腐化,另一边是底层百姓贫苦挣扎,无法保障生命。“作者通过这种场景和人物行为的对比性描写,使财富成为罪恶的转喻,同时使贫穷者的不幸与富者的不仁建立了自然的因果性关系,从而不动声色地实现了自己阶级批判的意识形态意图。”[1] 这样,在左翼思潮直接催生的电影作品中,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被塑造成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并通过强烈的对比和赤裸裸的揭露,把上海变成一个用来剖析贫富对立,阶级冲突的典型空间,一个鼓动宣传阶级斗争的得力工具。
其次是受到左翼思潮影响的电影作品。在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中,费穆、孙瑜、蔡楚生、沈西苓等电影艺术家们也表现出直面时代的勇气和品格,创作出一批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他们的影片也表现出批判上海贫富对立、社会不公等左翼倾向,但同时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对上流社会占有的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又表现出比较中立的立场,体现出复杂的心态。如费穆的《都市之夜》通过描述上海贫民区一对父女的悲惨遭遇,控诉了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影片弥漫着浓重的悲剧气氛,有着很强的震撼力。黄子布(夏衍)撰文称赞该片:“无疑地,对于《都市之夜》,我们以为它的题材之‘接触现实’与‘暴露的有力’,是和最近明星的《狂流》异曲同工的一张前进的有意义的新作品。”[2]《马路天使》则用极其形象的方式暗喻出上海上下两个阶层的截然不同。银幕先是出现快速剪接的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物,在仰拍的镜头下,格外显得凌厉威严,狰狞诡谲,接着镜头再摇到建筑物的底部,暗示出在这天堂生活的下面,是下层人民赖以生存的地方,这样用居住空间的属性显示出社会地位的差异。但同时影片还表达出上海也是一座拥有西方文明的现代都市。如在位于高层大厦之中的律师事务所,在这样一个拥有现代名称的现代办事机构的空间里,饮水机、胶水等各种代表现代文明的物质,同样引起了下层人民的好奇与渴慕。再如孙瑜的《天明》用了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展示了高大的烟囱、飞转的机器、车水马龙的街道、炫彩夺目的城市之夜和新鲜刺激的游乐设施,对上海的现代生活进行了客观而充分的描述。当然诸如此类表现西方现代文明的画面还多次出现在其他影片中。这样在电影艺术家的镜头下,上海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既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不公平的社会,也是一个国际性的、现代文明比较发达的现代大都市。
此外,在以上海为表现对象的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大部分影片虽然是表达尖锐的阶级冲突,但并没有采取直接的阶级斗争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紧紧围绕着爱情婚姻这一线索展开叙述。这种叙事方式很明显是承接了鸳鸯蝴蝶派的手法,在满足上海众多市民观众欣赏口味的同时,来灌输影片中内含的左翼思想。如《三个摩登女性》就讲述了一位男子和三位女性的感情经历。张榆为逃避包办婚姻来到了上海,先后遇到了一位娇艳的摩登女郎和纯真的女中学生,并与两者产生感情纠葛,但最终在前未婚妻的感悟和帮助之下,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摩登和正确的人生道路。现实主义经典之作《马路天使》和《十字街头》有着同样的故事结构。幽默勇敢的小陈和善良天真的小红都是最下层的贫穷艺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依赖,深爱着对方,为帮助小红和其做妓女的姐姐小云摆脱恶势力的迫害,小陈和他的同伴们与之展开机智勇敢的斗争,在此过程中,老赵和小云也彼此相爱了。同样《十字街头》中同为下层职员的男女主人公,经过一系列的摩擦和巧合,两人经历了敌对—相识—相爱—分离—团聚,最终能够勇敢地面对种种不平与压迫,克服了苦闷和疑惧,坚定地走向前方。从这些代表性影片的叙述技巧和影片受欢迎程度可以看出,左翼观念与爱情婚姻结合起来,以图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性,虽然这仅是一个策略,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关注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领域和经验领域,关注自我生存价值的世俗性都市,新市民阶层的口味和思维制约并同化了整个上海的文化取向。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上海这个物质水平发达、世俗意识浓厚的现代化大都市被强化成为政治斗争色彩浓重的空间,是“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穆时英语),在乡土中国大多没有现代因素的时候,银幕上的上海被叙述成了负面的都市形象。
在20世纪30年代电影之后,对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进行影像塑造的另一个相对集中的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怀旧电影。怀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当其作为审美话语,站在当下的立场对过去进行回望时,必然要带上温润的感情色彩,不会像当时人那样作出相对冷酷的评判。因此,20世纪90年代怀旧电影中的老上海形象,与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的上海形象,有着较大的差异。
首先银幕中的老上海呈现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面貌。上海是一个传统文化薄弱的近代城市,再加上独特的租界制度,就成为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最得力的地域,可以说“上海的现代化是凭借外力被嫁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之中的”。[3] 国际化都市成为怀旧电影表现老上海的突破口,一方面体现为西方现代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普遍,深入到日常生活,支配和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等各种异质文化的并存与共融,并快速地流动,形成了文化开放性的显著特征。“很多年以前,我生活在老上海,和在这里的多数西方人一样,享受着这座美丽的城市所给予我们的各种特权。我们在这里如鱼得水,纸醉金迷,几乎忘记了回到自己的故乡。”这是《红色恋人》里佩恩回顾其1936年在上海时的独白,通过西方人对老上海的认可,凸显老上海已经具备了西方同质性。影片用西方人的视角强调了其国际化的特点。怀旧电影对这点的具体刻画,则用对西方现代物质——从老上海外在的景观风貌到内在的装饰摆设的细致描绘来体现老上海现代文明的进程,似乎“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比它的‘精神’层面更容易被中国人接纳”。[4] 首先外滩和南京路是老上海外在风貌的一个标志性的空间,成为许多怀旧影片选择的对象。《红色恋人》里远景拍摄的外滩租界地,影影绰绰、高低不一的西方建筑群表明了故事背景是现代化的都市。《风月》则把镜头对准了南京路给首次踏入上海的如玉和端午带来的惊异感,霓虹灯从高处压迫下来的五彩光影依次掠过两人的脸,他俩睁大恐惧而略显呆滞的眼睛,拼命承受着扑面而来的狂欢式的惊吓,充分显示出这个现代化大都市在传统中国中“异己”的身份。对于内在的装饰摆设,怀旧电影更是对每一个细节进行了渲染,极力张扬着国际化都市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在《风月》、《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阮玲玉》中,夜总会、咖啡厅、花园洋房等娱乐场所和居所成为其共同的描述对象。这里是中国人和西方人进行交流的活动场所,是洋酒、咖啡、雪茄、爵士乐、西洋舞蹈、洋装和中国的旗袍交融相处的文化空间。这样一个空间经过内外两方面的精心塑造,已经成为老上海的代名词,这里的故事就成为老上海的故事。在怀旧电影的银幕中,老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的巴黎”、“西面的纽约”、“地球上最世界主义的城市”。[5]
与国际性紧密相连的是老上海的消费化。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因为国际性的背景,迅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发展为一个繁华摩登的大都市。“‘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这句经典的论断就已经点出老上海商业气息浓厚,重视物质和欲望的特点。怀旧电影中对此表现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消费氛围的强调和女性身体的消费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影片中的消费氛围主要是指弥漫在夜总会、咖啡馆等娱乐场所精致而华丽的格调。无论是《风月》、《阮玲玉》,还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都反复出现了一个场景,即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夜总会里,时尚奢华的装饰显示出巴洛克式的浪漫和繁复,酽醇的红色洋酒、曼妙性感的女人体、亮如白昼或者暗淡迷离的灯光、轻柔的靡靡之音、缓缓飘荡的雪茄烟,在慢镜头和特写镜头的作用下,这里仿佛就是一个似真似幻的梦境,散发着精致优雅的贵族气息和唯美的情调。这种情调伴随着视觉上的愉悦,形成了完美的诱惑,其对物质文化的欲望,渗透进了观众的全身,然后再从每一个毛孔散发出去,与整个消费的氛围融合在一起,共同达到了精致而华丽的境界。
女性身体是欲望诉求的另一个对象。自梅里爱在《月球之旅》中夸张地呈现出一排表演女郎后,女性形象就开始成为银幕上的一种景观,进入人们欲望的视线。女性不再是绝对意义上的角色,不再承担这个角色的叙事功能,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可注视的女人体出现。对这点表达最彻底的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小金宝和其身后一排舞蹈着的女性的身体在中近景镜头的观照下,不断地夸大和凸现,已经遮蔽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人格意义上的存在,完全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其迷离的眼神、挑逗的身姿、火辣的朱唇、雪白的大腿,在近景镜头的放大下排山倒海般地压过来,动作、服饰、神态的一致性,消解了她们的个性意识,她们只是作为物质和肉体,在男性的目光中存在。再如有着浓郁老上海味道的《花样年华》,也把女性的身体放到了一个醒目的地位,连带着旗袍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视觉奇观。张曼玉说她是在“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那个女人”,于是在影片中,旗袍和旗袍包裹着的身体开始超出角色,与角色自身共同承担起叙事功能,在故事本身的情节之外,成为另一个关注的中心。张曼玉的明星效应、婀娜的身姿、华丽的旗袍共同营造出20世纪30年代女性的风姿,特别是当一个个中近景的镜头从各个角度呈现出的这个女人体时,更加渲染了上海女性的典雅气质与温婉风情,极大地满足了观众偷窥的欲望和期待视野。这样,在怀旧电影中,女性身体构成了一种新的消费语言,这既是怀旧影片的商业卖点,也是影片中对老上海的消费体验。
世俗化是怀旧电影中老上海的第三个特点。国际化大都市、经济中心、浓郁的消费氛围、充裕的物质享受,资本家、商人、职员和中产阶级构成的现代新市民阶层的兴起,这一切引起了社会文化价值的世俗化倾向。因此,怀旧电影充分关注起存在于一切时代的普通人的世俗追求,强调“性”或“利”等基本人性问题的合理性与价值。叶大鹰的《红色恋人》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这部影片试图讲述一个“革命+爱情”的故事,然而革命话语最终只是成为整个故事的外衣,真正占据故事中心的是介于靳、秋秋和佩恩三者之间的感情纠葛。革命者的革命行为仅仅限于少数几个演讲的镜头,大部分的时间则用来描述革命者背后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活动,靳最终的悲壮举动也因为是出于情感的责任,而被看作是远离神圣革命叙述的个人话语。传统中的革命叙事在这部叙述“红色革命”的影片中被悬置起来,生死爱恨等基本的人性问题成为建构中心话语的基点。在这一点上,陈凯歌的《风月》和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就显得更加纯粹和明确,爱情与人性也是他们所着力探讨的对象。正如陈凯歌所言,《风月》表现的是“极端强烈的爱情”,它的状态是“繁花似锦,盛到极处”,情感只有“达到忘我的境界”时,才能在非常态的状态下暴露人性中最隐秘的邪恶。《花样年华》中描述的是芸芸众生中凡人的爱情,然而由于爱情超越了道德力量的束缚,已经成为了不再平凡的情感,这种情感从充满烟火气的世俗中产生,又最终在世俗中升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怀旧电影中的老上海,世俗性已经具备强大的力量,它成功地消解了神圣的宏大叙事,世俗化的人性成为主导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怀旧电影中的老上海具有的国际化、消费化和世俗化三个特征,与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的上海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上海的新银幕形象已经淡化了政治色彩,对其描述不再局限于阶级话语中。这些影片抓住上海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特点,对之进行反复渲染,最大化地强调其世俗消费性的一面,从而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上海日常生活的魅力。
我们不难发现,60年前的电影与60年后的电影,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历史真实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彰显和遮蔽。其实,左翼上海与消费上海都是上海的真实面相之一,而新兴电影和怀旧电影中的上海,对真实状况无疑都存在着一种刻意营造。“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米歇尔·福柯这句话说明重返历史语境是回答所有疑问的最好前提。
怀旧电影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这段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没有谁能够否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变。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也发生了转变,以启蒙为核心的精英话语丧失了其中心位置,随之而起的是以消费和娱乐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这样的语境下,怀旧影片中的老上海出现了。老上海的出现,不仅是电影人对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身份的一种怀念,更是当代中国消费化、世俗化背景的要求,以及国人对于国际化的渴望,而老上海无疑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切入点。因此,为了满足人们对世俗化、消费化与娱乐化的欲望,为了最大化的票房收入,怀旧电影创造了一个老上海的视觉奇观。作为中国曾经的经济中心,老上海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且糅合了中西方文明,有着国际化的文化身份,成为体验浮华繁荣的都市经验的最佳空间。媒介即信息。当怀旧电影把银幕中的老上海带入到现实中来时,影片已经在建构一种“现实”,建构人们对现实的认知方式。可以肯定地说,因了怀旧电影价值取向的引导,观众已经接受和认可了老上海国际化之下的消费化与世俗化身份。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上海,确定了建设一个国际经济对话中心城市的最终战略目标。这样一个国际化的中心地位,决定了上海必然与中国其他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个体身份绝不是真正内含在个体自身,而是由差别构成的,要解释个体身份,就要考察建构个体的差别体系。因此,自从确立起这个中心位置,上海就开始了新的文化定位,致力于独特的文化身份,试图成为中国内部的“他者”。这个独特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其国际化的特色,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保持与国际的同质化。
在上海试图重现世界性都市身份伊始,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老上海怀旧成为了一种文化时尚。张艺谋等借电影于上海之外对老上海重塑的同时,老上海也获得了上海本地文化界的强烈关注。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为题材的《前世今生》、《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为代表的出版物不断获得市场上的成功,与怀旧电影一起构成了老上海文化怀旧的风潮。事实上,当上海重新确立了国际化的宏伟目标以后,几乎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一个是目标中的想像身份,一个是已然确定了的历史身份,国际化的共同点使两者能够超越时空,得以相互指认。因此,当新上海把老上海当作一种文化资源时,人们不仅对以老上海为表现对象的怀旧电影或出版物表示出更大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从中看到了新上海的未来,满足了对新上海的明天自我身份的想像。
与怀旧电影与出版物对上海文化身份同时重构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开始有意识地对老上海文化资源进行实际开发,最典型的就是衡山路酒吧街、百乐门、新天地等娱乐休闲场所的改造。这些具有老上海风味的历史空间经过斗转星移,再一次激起人们的梦想。暗黄的铜把手、袅娜的20世纪30年代老歌、穿旗袍点朱唇的淑女名媛、镌刻着葡萄藤叶的镂花扶梯、一袭不留足音的红色长毯、醇香的红酒和咖啡、忧郁的爵士乐,对这些具体物象的极致铺陈,隐喻着新上海通向全球化的文化想像,也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犹如30年代的上海,这里就是走向国际性经济中心的新上海。当置身其中的人们感叹“就像回到了老上海”时,上海政府对文化意义的苦心构建,对物质消费和世俗气息的缅怀与迷恋,已经与怀旧电影中老上海的影像重叠。
在上海政府有意进行的新上海文化精神的重塑中,怀旧电影、怀旧类出版物和怀旧建筑物等起着不小的影响,这些作品中塑造的老上海的“昨天”,已经为上海努力要达到的“明天”提供了依据和样板。但在目前的研究中,似乎没有人认识到怀旧电影在上海文化精神重塑中的作用。与怀旧出版物,以及现实中怀旧建筑之类的引导相比,怀旧电影无疑具有以下几个优势。首先是怀旧电影的国际化。作为各种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这一批电影,因着张艺谋、陈凯歌和王家卫等国际知名导演的声誉,而具有了国际知名度,其国际身份一开始就与上海的新目标相暗合。同时,也因着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非上海人身份,而使对老上海的怀旧跃出本地,成为一种集体想像。其次,怀旧电影的大众化。具有贵族遗风和异国情调的衡山路的酒吧和新天地,不是大众市民可以经常光顾的日常空间,而是精英们休闲的理想场所;同样从出版物来看,销量最好的《前世今生》等十几万册的数目,对电影观众的数量而言,也毫无优势,何况还不包括一些盗版影碟所带来的潜在观众。也就是说,在把老上海时尚向大众层面的普及中,怀旧电影的首要作用毋庸置疑。第三就是怀旧电影的视觉优势。酒吧和新天地是客观实在的,但对普通百姓来说依然比较遥远,带着一层拒人千里的面纱;而与出版物抽象朦胧的文字相比,怀旧电影影像的形象明晰不言自明。正是上述的这些优势,使得怀旧电影对于新上海文化的重构来说,承担起了首要的隐喻和样板作用。
当然这种隐喻和样板的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怀旧电影描摹出新上海的整体目标上。在怀旧电影中,正如前文所述,与其国际性的经济中心地位紧密相连的是日常生活的消费性和世俗性。现实中的酒吧、百乐门和新天地等属于精英分子的领域,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空间,而怀旧电影则采用了一些独特的拍摄技巧,使这种消费性和世俗性深入到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内化为生活的常态。比如作为重要表现对象的夜总会、咖啡厅等娱乐空间,怀旧电影经常是用特写镜头与慢镜头等特技和写意的手法来表现内在其中的具体物象。正如本雅明所说,“电影特写镜头延伸了空间,而慢镜头动作则延伸了运动。放大与其说是单纯地对我们‘原本’看不清的事物的说明,毋宁说是使材料的新构造完美地达到了预先显示。慢镜头动作也不仅只是使熟悉的运动得到显现,而且还在这熟悉的运动中揭示了完全未知的运动。”[6] 因此,当这种经过特技处理过的画面出现在银幕上时,不仅彰显出每一个物象满足欲望的功能,深刻地挖掘出消费和世俗的日常性特征,而且观众的视角和影片内在的视角合而为一,使观众充分地接受并认可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这种文化特征。这样,怀旧电影就凭借视觉优势,把这种消费性直接而形象地带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培养并制造了新的消费观念,使隐藏的欲望合法化,促使新的消费方式的形成,在日常生活领域塑造起新上海的文化想像。这点与新上海的整个消费文化环境对日常消费的诉求,再次不谋而合。
因此,当银幕影像和现实情景发生重合并彼此印证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怀旧电影与新上海文化建构之间具有暧昧的关系。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对当时上海的叙述是一种自发的表达,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怀旧电影与当下上海的文化建设就有了“互动共谋”的嫌疑,有了惺惺相惜的味道。两者之间已经难解难分,新上海对怀旧电影的文化认同,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后者的存在和兴盛,为其营造了一个积极的生存环境。而怀旧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也为上海形成国际化的目标身份和日常的消费文化,制造出一种上海城市想像,并最终与上海的文化建设构成互动共谋的关系,影响了当下上海的文化走向。如果借用上海新天地“昨天、明天,相会在今天”的这句话,也许可以更加简洁明了地说明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