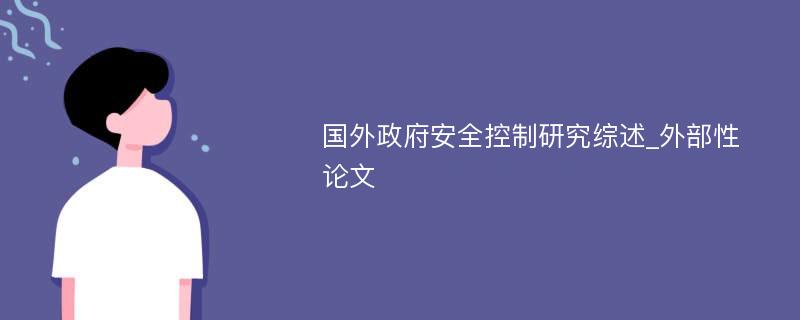
国外政府安全管制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制论文,国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制是指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或管制机构,依据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管制大体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社会性管制用以纠正不安全、不健康的产品及生产过程中的有害副产品。安全管制(Safety Regulation)是针对产品质量、工作场所安全、环境安全、核安全等方面的政府社会管制。国外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称产品质量、工作场所安全和环境管制的复合物为“社会的”或“新潮的”管制,并经常把它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①。
政府安全管制的目的在于减少或消除负外部性和负内部性。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由于没有得到市场的反映和计算,决策者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不一致,均衡的结果无效率,导致市场失灵。内部性是指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的成本和收益,主要针对购买某产品的消费者和企业雇员。例如,劣质产品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不安全的工作场所给工人造成的伤害等。内部性主要由交易成本引起,过高的交易成本,也会导致市场无效。当前国外对安全管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管制的效果、安全管制的替代方法、安全管制的责任分担等领域。
安全管制对负外部性的影响
Thomas L.Traynor建立模型分析了产品的安全管制对负外部性的影响。② 他假定当决策者面临的风险活动具有负外部性时,决策者选择的风险值要高于社会最优量。原因是由于风险成本没有完全内部化,负外部性致使风险活动过度参与。在此假定下,他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当面临政府强化的安全管制时,决策者可能会增加风险活动。假定安全事故发生率为P、决策者的损失为L、对他人产生的负外部性为E。作者的分析表明,旨在提高安全性的管制政策变迁通常不能同时减少事故发生率P、决策者的损失L以及对他人的外部性E。恰恰相反,管制政策要么减少事故发生的频率,要么减少事故发生损失的大小(L或E)。例如,强制性安全食品处理技术确实减少了疾病传播的发生率,但并不能减少借由食品感染患病而给受害者造成的成本(L或E)。改善道路照明系统的安全管制,减少了道路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但并没有减少已发生事故对司机和他人造成的损失(L和E)。汽车的安全气囊,不会对摩托车和自行车驾驶者产生积极的影响(E),也不会减少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P)。通过安全管制只是减少了事故对司机的损失,但并没有改变E或P,导致这种结果的行为被称为“补偿行为”。作者得出了两个重要推论:
(1)旨在减少事故发生率但不能同时减少事故造成的平均损失的安全管制将会减少预期的负外部性。如汽车安全气囊的反例,这些安全管制并不能减少事故发生率,但的确减少了对代理人的损失。
(2)减少对代理人造成平均损失的管制政策会增加预期负外部性。
其实践意义在于:旨在减少平均损失大小的管制政策会增加损失的发生概率;而旨在减少事故发生率的管制政策又会增加每个事故发生所造成的损失。
Thomas L.Traynor分析结论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政策制定者要考虑到危险物品或行为的固有的负外部性以及明确知晓安全管制政策对控制事故发生率和对每次事故中造成损失大小产生的不同影响作用。
当然,他的模型也有一定的隐含条件,如决策者具备完全信息以及是理性的;受损的第三方在此模型中是被动的,不会以某种方式防卫自己等。
安全管制的效果
政府安全管制的目标还在于减少负内部性,即预防或减少工作场所事故发生率以及事故发生后对工人或其他当事者造成的伤害程度。典型的安全管制机构如欧美的OSHA(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其法规的颁布、法令的强化以及管制机构监察力量的加强,对产业安全事故的影响如何?政府安全管制的绩效如何?国外学者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计量分析。
1.对事故发生率或工伤率的经验分析
美国于1970年颁布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是当时美国管制计划里最受争议的法案。赞同者认为该管制法案在减少工人伤害和患病方面的作用是较为理想的,虽然其积极作用可能会受到政府官僚机构低效率的影响而打折扣。该法案的批评者则认为,法案本质上除了徒增成本外, 没有什么显著收益。不论双方意见如何相左,他们均一致认为OSHA在工作场所伤害和患病抑制方面,缺乏可测量的积极效果。John Mendeloff③ 采用时间序列数据,首次将OSHA的影响剔除出来,着重分析管制政策实施后对制造业事故发生率的影响,最后并未发现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积极影响,只发现了一项工人伤害指标的下降趋势与OSHA标准的实施有关。Smith,Robert S④ 采用横截面数据对受到管制后的企业进行分析,并没有发现管制前与管制后伤害发生率的显著变化。Viscusi⑤ 使用横截面数据分析了监察概率对事故发生率的影响,发现结果也不明显。他们的实证研究也存有不足,就是数据集太少,影响了OSHA潜在作用的发挥范围和程度,同时也可能造成较大的统计偏差,影响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和无偏性。
与先前一些学者研究方法不同,随后Smith⑥ 采用大样本,分析了1973~1974年间OSHA对制造业的事故发生率的影响。由于样本数比较大,可以允许选择有效的对比组进行计量分析,同时还可以对监察行为的实施和事故发生后的时滞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1973年OSHA对抑制伤害发生率的效果显著,减少了16%,而1974的下降效果并不显著,大约在5%左右,并且OSHA政策的效果还有3个半月的时滞期。作者的结论认为,OSHA的安全管制的效果还是良好的,轻言OSHA没有良好效果是不谨慎的。
2.对安全管制和作业场所伤害严重性的实证分析
与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安全管制对事故发生频率的影响不同,William P.
Curinton⑦ 推测OSHA的安全管制只是减少了作业场所伤害的严重性,而并非事故发生的频率。随后,他使用面板数据,区分不同的行业以及不同的安全事故所造成的不同伤害,对安全管制进行经济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考虑到不同行业以及不同的伤害种类,政府安全管制的作用并非简单地一定就是减少事故发生率或事故发生所造成的损失;安全管制在降低事故发生率的同时并非绝对就能降低伤害的严重性;安全管制的作用,需要详细加以分析。政府安全管制的作用、对事故发生的频率和事故造成的严重性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并且还需要结合特定的产业来考察、分析政府安全管制的效果。
William P.Curinton之后,Paul Lanoie⑧ 模仿Cruinton的方法对加拿大魁北克OSH委员会安全管制(CSST,Commission de la Santé et Santé Sécurité du Travail)的绩效进行了计量分析,考虑到加拿大还采用了不同于美国OSHA的强化职业和作业场所安全的措施,例如工人拒绝危险工作的权力、组建由工人和资方组成的“作业场所安全委员会”等。作者将加拿大独有的安全措施也纳入进行分析,观察这些政策措施对安全是否有显著影响。此外,Paul Lanoie的模型更具有一般性,他建立了委托—代理模型来分析安全管制的影响,模型不仅考虑了企业行为对安全事故的影响,而且考虑到了工人对安全事故的影响,这比Cruinton仅考虑企业的单边影响更为符合现实情况。例如,企业无法观察到工人是否吸毒或者饮酒。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政策制订时,需要考虑到企业和工人都会对事故发生率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各自的风险相关行为可能存在对冲的可能性。例如,当企业增加了安全风险事故防范的投资,但是工人可能会变得疏忽和粗心大意,又提高了事故发生的概率。这样可能会减弱安全强化措施的效力。
以往对美国OSHA安全管制实施效果的研究和分析多集中于1979~1985年,通过这一时期数据来分析OSHA监管对减少制造业工人伤害率的影响。但是,从更长的时期来看OSHA的效果如何,限于数据条件则很少有学者触及。Wayne B.Gray和John M.Mendeloff⑨ 两位长期研究美国OSHA监察效果的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尤其是他们分析了1992~1998年OSHA的管制效果。他们的估计结果发现,OSHA以罚款形式进行的监察减少了1979~1985年期间的损失工时性工伤的约19%,但这种效果在1987~1991年减至11%,到了1992~1998年间,只有1%,并且在统计意义上也不显著。基于企业和监察本身特点的不同,安全管制的效果也不同。一般来说,处罚性质的监察效果更好些。OSHA的效果对小企业更明显,而大型企业由于通常安全管理较严格、工会的组织程度较高、工人的安全意识较强、发生事故后对企业的工时损失及诉讼成本较高,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小于小企业,导致OSHA监察对大企业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其分析结果对OSHA的政策意义在于,OSHA应该将稀缺的管制资源投入到更需要帮助的(例如小企业和工会组织程度较低的企业)地方去。
3.安全管制对生产率的影响
前述安全管制侧重于分析安全管制对于抑制外部性和内部性的社会效果问题。然而政府安全管制本身需要通过制定一系列法规、准则、标准强制被管制企业服从和遵守这些规定,从而达到政府安全管制的目的。由于政府通过规定、 标准和经济处罚来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企业的运行过程,因此,政府的安全管制有可能会损失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Denison⑩ 分析了不同要素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有很多因素导致了70年代美国生产率的下降。他估计政府的管制对1972~1975年间的生产率下降的贡献率为0.35%,在其后的研究中又发现1973~1981年期间政府管制对生产率下降的贡献率降为0.15%。随后又有不同的学者对政府管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研究的绝大部分结论都表明政府施加给企业的污染控制成本、总的政府管制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生产率下降的10%左右。(11)
在区分了对不同产业的政府安全管制强度后,Wayne B.Gray(12) 对OSHA以及EP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环境保护署)的职业安全和环境安全管制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作者采用了1958~1980年间450个制造业样本数据来分析政府管制对生产率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的安全管制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管制强度较高的产业的生产率下降要比所有受管制产业的平均生产率下降程度更大。Gray估计结果要比Denison的高,政府管制对这一期间美国生产率下降的贡献率为0.57%,而Denison的估计只有0.35%。
尽管很多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安全管制有损于生产率,但是这种对经济效率的不利作用,需要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政府安全管制的短期效果有损于生产率的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管制对生产率的某些不利影响将会随着企业在面临管制约束的调整中而消失或减弱。也就是说, 政府管制给企业造成的调整成本是一次性的,调整完之后,这种不利影响就会变得微不足道或消失。其次,政府安全管制制定标准、法规,做到事前的预防以及事后为工人和第三方提供经济补偿和公平,从微观上来看,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而且从宏观上来说对生产率的不利之处,长期来看并不显著。
民事责任追究与政府安全管制
安全事故发生后的民事责任的追究与政府的安全管制是两种控制风险的主要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单独使用时,都各自具有缺点。事后对工人的赔偿系统,可以从法律上保障工人得到一定的赔偿,保护工人的利益,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制约, 因为企业要考虑到事故发生后对企业造成的停工损失以及诉讼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这些情况都会逼迫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考虑到工人的安全问题,也有利于企业将外部性内部化。但是,这种民事责任追究可能需要良好的法庭机制,法庭不能受到强势集团的干预而发生不公正判决。(13) 而政府安全管制则不同,从效率角度出发,管制可能比私人的民事诉讼更有效。首先,管制者可能比法官更有强烈的动机去进行高代价的调查,以证实违法现象的发生。这种强烈的动机或者源于对职业生涯的考虑(如管制者是否会因为发现违法现象而得到奖励),或者源于管制者所受到的更专业化的训练。(14) 其次,管制比私人诉讼更有效是因为管制者能够代表原告方的共同利益,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所有附带问题。例如,一个铁路安全的管制者可以代表事故的实际和潜在的受害者,较受害者们自己更为有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制的影响类似于共同起诉的效果,它所起到的作用要超过单个的个人诉讼。再次,私人诉讼和管制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区别,即诉讼是在危害已经形成之后进行损害赔偿,而投入监管则是在进行事前预防。对企业来说,接受监管所需的潜在成本相对要低于在法庭上面对责任诉讼所需的资源。由于这一不同之处,监管可以被设计得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鉴别违法行为,并且其结果更为确定(例如,认定生产商是否已经安装了一个安全装置比认定他是否忽略此事要更加容易)。(15) Glaeser和Sheifer(16) 认为,低成本鉴别违法行为的理由解释了管制得以兴起的原因。他们通过进一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进行监管时发现违法行为的较高可能性决定了管制的罚金相对较低,因此,管制比诉讼更易于被违法者所接受,结果是罚金较低的执法形式受到的破坏较少。最后,由于由政府的公共独立监管机构实施社会政策,原则上与无私的法官相比,他们更难被劝说或贿赂。
上述学者未能分析民事责任追究和政府安全管制联合使用的情形,Steven Shavell(17) 建立数学模型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种方法单独使用时的缺陷和不足并着重分析了联合使用的优点。单纯的政府管制不能把事故的风险减到最低限度,因为管制者不具备完美信息;单纯的民事责任追究也不能达到合意结果,因为责任追究产生的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激励会被当事人未受到诉讼和无力完全支付事故发生的损失所稀释。作者分别分析了以下几种情况:
(1)把民事责任追究作为控制风险的唯一方法。假定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可能超过他们的财产,并且当事人可能逃避诉讼,那么企业规避安全风险的水平不是最优的。
(2)把政府管制作为控制风险的唯一方法。政府需要关于管制对象的完美信息,这通常难以做到;此外,由于管制者不能观察到事故发生后损失的大小,因此,管制标准对所有被管制者都是一样的,不会区别对待。这样做的结果是风险发生率较低的企业风险规避水平超过最优值,而风险发生率较高的企业风险规避水平又低于最优值。
(3)管制和民事责任孰优孰劣。作者通过分析得出推论:如果民事责任追究的激励要素可能会被极大地稀释,那么政府安全管制要优于民事责任追究;否则,民事责任追究优于政府管制。
(4)管制和民事责任的联合使用。作者分析,二者联合使用可以避免两种方法单独使用的缺点,从而提高安全管制效果。随后Steven Shavell进一步分析了政府管制和民事责任追究联合使用的技术细节问题,认为企业即使遵守了管制规定,但一旦事故发生,也不能豁免它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一旦豁免经济责任,企业就可能积极遵守政府的安全管制规定,而消极地采取其它政府未曾发现的减少事故的措施。因此,民事责任仍然要作为一种附加的控制风险的手段。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某些企业未能遵守安全管制规定,是否一定要追究其民事责任?答案是否定的。作者分析,倘若追究民事责任,某些企业会格外遵守管制政策,但其实这些企业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比通常的要少,故而管制对它们来说并不一定是完全合意的。现在它们因受到民事责任追究的威胁而遵守管制政策,但意识到民法中它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它们还是有意愿不去遵守管制政策。
政府的安全警告和安全管制信息
不完美信息表明政府安全管制的必要性,如果政府官员拥有公民所没有的信息,管制可以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然而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政府进行安全管制需要的信息是不完美的,这将影响安全管制的效果。假定政府官员的目标和普通居民对自己的福利评价是不同的, 不论是出于基本的价值观还是出于他们所面临的激励,政府官员比普通居民更注重安全。(18) Paul Calcott(19) 建立并运用几个博弈模型分析了安全警告和管制信息的作用,在假定政府官员可以得到完全信息但比普通居民更加小心谨慎的情况下,他发现授权官员安全管制是有利的,尤其是居民对风险的评价和官员一样高时;授权官员发布安全信息也是有利的;既授权官员安全管制又授权其发布信息要比只授权他提供信息糟糕得多,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
当然,作者的结论是在一定的隐含条件下得出的。其分析忽略了一些对安全管制和安全警告这两者来说都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居民可能存在判断错误、不完全理性等情况。居民可能低估某些事件的风险,或者对明显的风险过于乐观,这时安全管制要比政府充分的安全警告好得多。当然政府也可能存在失灵,如管制决策缺乏理性等。第二个因素是居民并非同质。在面对风险或危险时,其行为是不同的,对一种类型的人有益的管制可能对另外的人有害。这时官员发布信息的博弈模型的均衡不变,而管制博弈模型的均衡稍有不同,因为管制者对不同的人制定的都是同样的管制政策。第三个因素是管制和安全信息的提供都需要政府官员与居民支出资源成本和努力成本。然而政府官员支出的成本可以提高政府官员提供安全信息的可信度。第四个因素是面对政府的干预,居民可能发生不合意行为。例如,当被强制使用安全带时,汽车司机开车会更快,导致更高的事故发生率。第五个因素是在管制博弈模型里,政府官员和居民收集产品安全信息的激励会改变,政府官员会有更多的理由收集他有能力去影响居民行为的信息,而居民又会有更多的理由收集其行为不受严厉管制的信息。第六个因素是政府官员的目标被当成外生的。实际上很有可能一个有效和受到充分激励的代理机构极其重视增强安全性。例如,奖励官员在消减伤害率方面的成就会激励官员更加关注健康,同时激励官员努力收集和发布信息。(20)
考虑到这些因素时,Paul Calcott分析的管制效果也有一定合理性。其政策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在评估某种特定行为或某种产品的安全管制政策时,上述因素必须要考虑到。
安全管制责任的分担
前述文献中所涉及的管制机构或者管制者都是一个政府部门。现实中,可能有多个管制机构或不同代理机构负责对经济行为的风险进行安全管制。例如,环境管制中,有多个代理机构对设备安装、生产环节进行独立监察。企业监督危险车间的安全性、 政府有关管制机构例行常规或随机检查、保险公司强化安全控制标准,它们有各自的监控标准。然而,这种独立的安全控制只是相关的安全风险控制的特例。很多情况下,监督者并不负责同样的试验工作(例如新药的试验),但是他们的责任却发生交叉重叠,在此意义上,一个代理者有理由相信其它代理者的控制活动足以保证安全。以飞行安全事故为例,有不同层级的安全控制,如飞机制造公司、航空公司、地勤人员、服务公司、空勤控制、民航安全管制机构、飞行员等都对飞行安全产生影响,经常是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关环节出了问题后,就引发了飞行事故。
如果信息是完全的,设计一个有效的责任准则是不成问题的。在任何一种过失准则下,如果哪个代理者没有到达其应负的监管水平,他就负相应的责任,这种准则使代理者选择有效的监管水平。(21) 然而,现实情况下,有效率的过失准则需要法庭清晰地了解不同代理者规避风险的成本。以开发新药为例,人们难以清晰地知晓什么是合理的监管成本、制造商真正对新药的风险知晓程度、进行一项有效的试验的成本是多少。这些都是药品制造商倾向于隐藏的私人信息。同样,对于环境管制而言,每个代理者都会保持各自的监管行为的记录,以备事故发生时有据可查。但是一旦对风险活动的监管失败,环境破坏事故发生时,则无人能说清楚究竟是试验程序存在缺陷的问题还是监管人员责任问题,亦即对于负有相关责任的代理者来说,其有效监管的真实成本是多少无从得知。由于每个代理者(监管者)的监管成本是他的私人知识,这样,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过失准则就显得过于理想。这时,如何设计更加有效和更具操作性的激励机制,从而在各个管制部门之间有效分担责任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考虑到“过失准则”的缺陷,D' Aspremont和Gerard-Varet(22) 就曾提出了一种机制,它采用“责任准则”,即全部的责任赔偿不超过全部的伤害成本。这种条件被称为“平衡性”。其主要思想是相对于预期的监管努力水平而言,代理者支付其实际监管努力水平所导致的整个损失,这种机制在边际上赋予了代理者预期的激励水平。然而这种AGV机制存在的问题就是它的运用条件较苛刻,如果要将其付诸实践,需要评估代理者的有效行为是什么;如果代理人偏离了他们的预期行为,预期损失又是如何受到影响的。
针对AGV机制的复杂性,Eberhard Feess和Ulrich Hege(23) 设计了一种简化机制,即补偿性支付机制,它也采用“责任准则”,与AGV机制相似。在这种机制下,每个代理人承担事故的全部预期成本,这时,代理人的监管行为是有效率的。并且, 这种补偿性支付机制只需要最少的信息。Eberhard Feess和Ulrich Hege的机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由于所有的补偿性支付在代理人的预期和实际监管失败风险之间的比例是线性的,决策者只需要估计一下代理人预期监管水平和实际监管水平的不足或过剩就足够了,所以其规则相对简单些;其二,责任性支付依赖于实际发生的事故就足够了,这意味着法庭可以完全忽略假想的事故细节造成的影响。这种机制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节省法院和管制者的大量信息成本,且需要的假定条件和信息比较少,更加实用,可以使每个管制者有激励努力监管。
结语
安全管制是管制机构针对产品质量、环境、工作场所、特种设备以及其它一些可能造成负外部性和负内部性的客体或行为实施的管制政策与行为。国外的安全管制普遍存在于食品和药品、环境、作业场所安全与健康、道路、汽车、核电厂等领域。 目前安全管制的研究对上述方面都有所涉及,但总体来说,以往的研究显得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侧重于管制效果的实证研究,对于政府安全管制的原因、政府自身组织机构与行为对安全管制的影响、政府和被管制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相应的管制机制设计等其它理论和实践问题,则有所忽视或研究不足,表现出了实证性强但理论分析不足、重管制客体分析却轻管制者自身研究的倾向,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性的、一般性的理论分析体系和框架。未来政府安全管制研究需要拓宽研究范围、视角、层次和方法,并结合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进行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从另一方面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我国政府正在由以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经济性管制逐渐改革和放松,社会性管制包括安全管制正在得到重视和强化,这是政府理应提供好的公共物品,也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国外安全管制的成熟理论、经验、实证分析方法以及注重安全管制政策效果的价值导向,在我国不同的管制环境下,可以为我国政府安全管制实践所借鉴、吸收乃至丰富和拓展。
注释:
① 丹尼尔·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② Thomas L.Traynor.(2000),“The Impact of Safety Regulations on Externalities”,Wright Stat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2000.
③ John Mendeloff.(1976),“An Evaluation of the OSHA Program's Effect on Workplace Injury Rates:Evidence from California Through 1974”,Report prepared under contract to the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Labor for Policy,Evaluating and Research,July.
④ Smith,Robert S.(1976),“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Its Goals and Its Achievement”,Washington: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⑤ W.Kip Viscusi.(1978),“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gulati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⑥ Smith.(1978),“The Impact of OSHA Inspection on Manufacturing Injury Rates”,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XIV.
⑦ William P.Curinton.(2001),“Safety Regulation and Workplace Injuries”,University of Arkansas.
⑧ Paul Lanoie.(2001),“Safety Regulation and the Risk of Workplace Accidents in Quebec”,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Commerciales.
⑨ Wayne B.Gray and John M.Mendeloff.(2005),“The Declining Effects Of OSHA Inspections On Manufacturing Injuries,1979~1998”,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Vol.58,No.4 (July 2005).
⑩ Denison,Edward F.(1979),“Accounting for Slower Economic Growth: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Washington: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11) Norsworthy,J.R.,Michael J,Harper and Kent Kunze.(1979),“The Slowdown in Productivity Growth:Analysis of Some Contributions Factors”,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79(2),pp.387~421; Scherer,F.M.(1982),“Inter-industry Technology Flow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64,no.4,1982,pp.627~634; Christainsen,Gregory B.and Robert H.Haveman.(1981),“Public Regulations and the Slowdown in Productivity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1,no,2,1981,pp.320~25; Grandall,Robert W.(1981),“Pollution Control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Basic Industries”,in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n Regulated Industries,Thomas G.Cowing and Rodney E.Stevenson,eds.,New York:Academic Press.
(12) Gray,Wayne B.(1984),“The Impact of OSHA and EPA Regulation on Productivity”,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June.
(13) Galanter,Marc.(1974),“Why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Speculations on the Limits of Legal Change”,Law Soc.Rev.9,pp.95~169.
(14) Glaeser,Edward,Simon Johnson,and Andrei Shleifer.(2001),“Coase versus the Coasians”,Q.J.Econ.116,3:pp.853~899,Nov.2001.
(15) Pistor,Katharina and Chenggang Xu.(2002),“Law Enforcement under Incomplete Law: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Financial Market Regulation”,Columbia Law School mimeo,2002.
(16) Glaeser,Edward,Scheinkman,Jose,Shleifer,Andrei.(2003),“The Injustice of Inequality”,Journal of Monetary,Economics 50,pp.199~222.
(17) Steven Shavell.(1983),“Liability for Harm Versus Regulation of Safety”,NBER Working Paper No.1218.
(18) Nichols & Zeckhauser.(1986),“The Perils of Prudence:How Conservative Risk Assessments Distort Regulation”,Regulation,November/December pp.13~24; Viscusi,W.K.(1998),“Rational risk poli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Paul Calcott.(2004),“Government Warnings and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Safety Regulatio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24(2004),pp.71~88.
(20) Tirole,J.(1994),“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Oxford Economic Papers,46,pp.1~29.
(21) Shavell,S.(1987),“Economic Analysis of Accident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
(22) D'Aspremont,C.,Gerard-Varet,L.A.(1979),“Incentives and Incomplete Informati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1:pp.25~45.
(23) Eberhard Feess & Ulrich Hege.(2002),“Safety Regulation and Monitor Liability”,Rev.Econ.Design 7,pp.173~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