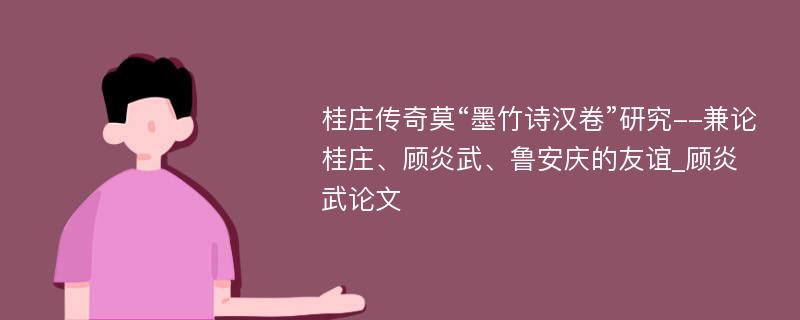
归庄遗墨《墨竹诗翰卷》述考——兼论归庄、顾炎武、路安卿之交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墨论文,墨竹论文,顾炎武论文,诗翰卷论文,兼论归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2)10-0054-03
一、归庄与《墨竹诗翰卷》
归庄(1613-1673),生于昆山李巷,字尔礼,又字玄恭,乙酉后,更名祚明。归氏是昆山的百年望族。曾祖归有光,是明代散文大家;祖父归子骏,屡试不中后绝意进取,以书史自娱终身;父亲归昌世,嘉定三才子之一,著名的书画篆刻家。归庄自幼聪慧敏捷,博览群书。在祖辈的影响下,归庄工诗文,善草书,精墨竹,与同里的顾炎武相互推许,不谐于俗,被时人称为“归奇顾怪”。归庄“善擘窠大字及狂草墨竹”[1],自称狂草近代无敌。太仓张应麟将归庄比作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张旭——“草圣张颠”[1]。《桐荫论画》亦称归庄墨竹题材书画不落寻常蹊径,应入“神品”[2]。
《墨竹诗翰卷》,纸本,墨笔,纵27.9厘米,横678.2厘米,清顺治十四年归庄为好友路安卿所作,中有归庄墨竹画五段、越游诗九首及顾炎武的题跋,堪称诗书画三绝,且归庄越游诗未曾收入《归庄集》中。此卷流传至道光时,归汉阳叶名澧收藏,叶曾请道咸名人题诗于两画卷中。后落入翰林院庶吉士广东番禺梁鼎芬之手。节庵殁没,此卷流入厂肆。浙江龙游余绍宋,于清季留学日本,民初宦游京师,不惜重金,求得此卷。余绍宋复又请梁任公等人题跋,余绍宋亦有咏此两卷之诗,现在此卷存浙江省博物馆。
《墨竹诗翰卷》作于顺治十四年,归庄45岁,正处于艺术生命力旺盛、艺术手法纯熟的年龄。《墨竹诗翰卷》前半部分画墨竹,后半部分题诗。墨竹分五段表现,每一段寥寥数竿,或疏或密,老干苍劲、新枝刚健。与父亲归昌世等其他文人画家笔下略显葱郁纤秀的墨竹而言,归庄的墨竹画笔法瘦劲,撇叶出锋劲利,枯淡却显刚劲。归庄曾自述作墨竹画,本“游戏为之,初无意求进,然相去十余年,亦觉大异”[1]。崇祯十七年明朝覆亡,顺治二年六月,昆山县令阎茂才下剃发令,归庄与顾炎武一起参加昆山抗清起义,后被清廷通缉,归庄只好僧装亡命。城破之时,归庄两个兄长先后殉节,两位嫂子和侄子女六人先后遇害,父亲忧惧去世。在十余年的磨砺中,归庄体验了家国覆亡的切肤之痛,也许是这种悲怆感诉诸笔端而有所不同,所以,归庄的墨竹画超越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文人画家,连归庄自己也说“相去十余年,亦觉大异”。
在各种绘画题材中,归庄对竹子格外钟情。墨竹画、有关墨竹的题跋屡见不鲜。归庄钟情墨竹的原因,不仅因为“籊籊竹竿,以垂钓可也”,外出游历时可“筏于水而杖于陆”;最主要的,在归庄看来,竹是高风亮节、傲岸挺拔的高士。归庄说,墨竹“冷淡竦直,非俗士之所好”,更“非俗士所之能绘”[3],画竹旨在言志。竹子“未出土时先有节”,在易代之际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归庄《墨竹诗翰卷》中的墨竹,根部并无土石,对此归庄解释说“画竹不作坡,非吾土也”,道出了自己作墨竹画不画土坡的原因:不认当朝。归庄以竹子自比并勉励自己:“荆棘在旁,终非其伍也。亭亭高节,落落贞柯,严霜烈风,将耐我何!”[1]
归庄画竹不作坡,亦如古代遗民画家笔下的无根之兰。宋室遗民与明代遗民,历史语境的相似,宋室遗民的华夷之辩犹如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在明代遗民民族沦亡的悲苦中迅速反应、升华。明崇祯十一年,宋室著名遗民诗人、画家郑思肖用生命与灵魂写就的遗民痛史——诗文集《铁函心史》在苏州承天寺的深井中捞起。《铁函心史》的重见天日,在广大士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即使是明朝覆亡之后,明遗民仍争相追和。《墨兰图》是郑思肖的绘画代表作,所画的是无地无根之兰,虽没有地,兰却张叶开花,飘洒秀逸,颇耐人寻味。郑思肖在《寒菊》题画诗中说“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4],表现他不向元人屈服的气节。归庄的《墨竹诗翰卷》,竹叶萧疏,不见土坡,亦借此表达自己无国土可依的凄楚和不认当朝并与之决裂的决心。
墨竹之后,是归庄的行草书,抄录诗七律九首①。这九首诗是归庄顺治十一年游浙东时所作。归庄在九首诗后有简短的跋文:
强圉作噩之岁秋九月,至洞庭东山,居停安卿道兄斋中者二旬。临行,以此卷索余书画,云:不拘时乘兴为之。是年冬十一月,寓檇李天宁禅院,偶一日无事,令老苍头磨墨,先作墨竹数丛,后附甲午秋(顺治十一年)游浙东时近体九首。兴会适到,殊觉远胜平日。朱子葆兄对案观予落笔如飞,为之击节。
跋文交代了此书画卷的创作缘由及时间、地点。顺治十四年,归庄游洞庭东山,居停路振飞之长子路安卿家中二旬。路安卿当然知道归庄诗、书、画俱佳,临行,索要归庄墨宝,并可以不拘时乘兴为之。十一月,归庄至嘉兴西南檇李,宿天宁禅院。归庄作此墨竹画,并题顺治十一年游浙东诗九首。归庄对此书画卷颇为满意,自“兴会适到,殊觉远胜平日”。完成后归庄践约将此书画卷赠给好友路安卿。
康熙十二年,归庄去世。顾炎武为好友遥祭于蔡家庄。归庄既殁之二年,顾炎武再访老友路安卿,安卿拿出归庄当年的遗墨。睹此遗墨,顾、路二氏不胜人琴之思,顾炎武遂于归庄跋文之后笔录旧作七律一首,末钤“顾炎武印”白文方印,“亭林”朱文方印。题识云:
玄恭既没之二年,炎武过广平,安卿世兄出其遗墨,见示,欲题所作哭玄恭诗四首,而时方忌讳,未便直笔,录去年报安卿一律于左,以志人琴之感云。
路光禄书来,叙江东同好诸友,一时徂谢,感叹成篇。
削迹行吟久未归,修门旧馆露先唏,中年久已伤哀乐,死日方能定是非。彩笔夏枯湘水竹,清风春昼首山薇,斯文万古将谁属,共尔衰迟老布衣。昆山顾炎武书,时年六十三。
题识中所及“欲题所作哭玄恭诗四首,而时方忌讳,未便直笔”,据《亭林诗文集》,哭玄恭诗共四首。
二、归庄、顾炎武、路安卿之交游
书画卷中涉及三个重要的人物:归庄、顾炎武、路安卿。他们三人均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义士,在易代的风雨飘摇中结为患难之交。
归庄与顾炎武是同庚同里至交,两人都是复社、惊隐诗社成员。清兵南下,两人一起参加昆山、嘉定一带抗清起义。失败后,两人的人生道路呈现不同的走向。对此《微云堂杂记》有记载:归庄先是僧装亡命,后枯守笔砚,整理曾祖归有光文集;而顾炎武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决史料[5]。一个成为著名的文人,一个成为著名的学者。即便如此,两人仍是坚持气节,同气相投,相互砥砺。
以明亡为界,归、顾交游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两人二十一岁时订交。归庄顺治十四年云:“余与宁人之交,二十五年矣。”据此,二人订交当在崇祯六年。顾炎武诗亦言“弱冠始同游,文章相砥砺”。明亡之前,归、顾二人时常一起饮酒赋诗,游山玩水。顾炎武《从叔父穆庵府君行状》云:“余与叔父洎同县归生,入则读书作文,出则登山临水,间以觞咏,弥日竟夕。”[6]明亡以后,归庄与顾炎武交游中有两件事关系尤为重大。一是反清复明;二是顾炎武被陷入狱。正是这两件事情,使得归庄、顾炎武、路安卿三人的交游有了交集。
归庄始与路安卿兄弟交游当在明亡后。路光禄,路振飞之季子,名泽浓,字安卿[7]。归庄《路中书家传》说道:弘光中,路振飞“避乱苏州之洞庭山”,已而公南入闽,“后卒皆流寓山中。余入山,获交君兄弟”[1]。《路文贞公行状》载:路振飞,天启五年进士,明末一代名将,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人士。崇祯王朝覆亡后,曾效力于南明福王、唐王,官拜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唐王事败第二年,路振飞于赴永明王召见途中死去。顺治十六年,路振飞之长子泽溥扶柩至苏州,第二年请归庄为父亲作《路文贞公行状》,并葬之于洞庭东山。归庄《路文贞公行状》卷末云:“庄为公部民,顾未尝相识。”[1]可见归庄与路振飞原并不相识。振飞子三:长泽溥,次泽淳,少泽浓。泽淳以病卒,归庄为作《路中书家传》。
从现有材料看,归庄与路氏兄弟在顺治十年左右过从甚密。《墨竹诗翰卷》记载,顺治十四年归庄“至洞庭东山,居停安卿道兄斋中者二旬”。归庄《路中书家传》中提到,“戊戌(顺治十五年)三月,余在洞庭山”,“五月复入山,则君之兄与弟皆丧服”,“五六年前来山中,周旋累日,犹仿佛忆君言笑举止”。从中我们可以推断,顺治十五年,归庄曾三次入山访路氏兄弟,顺治十年左右,归庄亦是路氏兄弟的常客。归庄另一遗墨《墨竹图跋》亦有“己亥(顺治十六年)九月,余在洞庭东山偶遇路光禄安卿”字语。
与洞庭东山路氏兄弟往来期间,归庄还结识了洞庭东山义商翁氏之后翁元闻兄弟,两次登览翁氏名园,并为其写了《湘云阁记》。湘云阁在东山翁巷,为翁彦博所筑。而翁氏为明清时东山首富。归庄还与翁氏另一后人翁澍相交善,翁澍,字季霖,明清之际著名的藏书家,与遗民归庄、黄周星、屈大均等多有往来。当时,“江南民讹言归生死”,从归庄语“接手教,知闻讹传而叹诧”可以判断,翁季霖曾写信以求证,遂有归庄《答翁季霖书》以辟谣。《太湖备考》云:“翁澍与下堡金侃交最善,延至家塾,商榷古今。”[8]金侃,即归庄之婿。据此,两家或有通家之好。归庄所结交路氏、翁氏均为洞庭东山抗清联盟的核心。
顾炎武应先结识路振飞,后与其子路安卿三人相交。洞庭东山是抗清武装的秘密根据地之一。崇祯朝路振飞巡抚淮扬,曾团练乡兵,得两淮间劲卒数万。《东南纪事》云:乙酉“振飞及其乡诸生韩雄都等聚兵大湖,不降”[9]。路振飞聚兵太湖实际上是组织“反清同盟”,一面抵御湖匪,保境安民;一面频繁联系淮安隐潜的抗清力量。当时加入“反清同盟”的成员有顾炎武、屈大均、归庄以及钱谦益、吴伟业等,东山富商翁氏、席氏为反清同盟提供主要的经济支持[10]。后隆武政权成立,路振飞举荐顾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炎武未果行。此后四五年间,“尝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仆仆往来,盖受振飞命,纠合淮徐豪杰”[11]。顺治四年,路振飞去世。其子路安卿兄弟三人秉承父志,成为顾炎武继路振飞之后的抗清联络人,“沟通着海上鲁王、粤西桂王与淮海以至鲁豫之间的消息”[12],顾炎武作为路氏兄弟的密友,实际上参与着谋划和联络的机密。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曰:“炎武每从淮上归,必诣洞庭振飞之子泽溥。”[11]
顺治十二年顾炎武擒杀叛奴陆恩,狱讼以是起。顾炎武《赠路光禄太平》诗自序云:有仆陆恩“见门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告余通闽中事。余闻,亟擒之,数其罪,沉诸水。其婿复投豪讼之官,以二千金赂府推官求杀余。余既待讯,法当囚系,乃不之狱曹而执诸豪奴之家。同人不平,为代诉之兵备使者。移狱松江府,以杀奴论”[6]。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详细记载了杀奴的前后经过:崇祯之末,顾氏“一时丧荒,赋徭蝟集,以遗田八百亩典叶公子”。所云“叶公子”者,名方恒,字眉初,官至运河同知推佥事。未仕乡居时,“素倚其父与伯父之势,凌夺里中”。见顾炎武家道渐衰,欲蓄意吞之。顾炎武无奈将田产券价仅十之六典押于他。后来,“适宁人之仆陆恩得罪于主,公子钩致之,令诬宁人不轨,将兴大狱,以除顾氏”[1]。《汉学师承记》云:“有为求救于钱谦益,谦益欲炎武自称门下,而后许之。其人(归庄)知不可,而恐失事机,乃私书一刺与之。”路舍人泽溥“识兵备使者,为之诉冤,其事遂解”[13]。归庄不仅求救于钱谦益,而且还直接去信叶方恒,陈以利弊,试图说服叶方恒中止诉讼。可见顾炎武在难时,归庄、泽浓、泽溥曾合力营救,这无疑加深了顾炎武与归庄、路安卿兄弟的感情。归庄、顾炎武、路氏兄弟的别集中多有他们之间的诗歌赠答、书信往来之作。这些作品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和忠于明朝并肩作战的相契之心。
事实证明,归庄屡过洞庭东山,与路氏等江淮隐士过从甚密,表面上是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更隐秘的意图是与协助顾炎武联络抗清志士。他们内心激荡着“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他们的志气抱负不甘仅作一名“隐士”。这可以从《墨竹诗翰卷》所题越游诗九首中看出。诗作表面上反映大家结伴出游、寄情山水,实际的活动是祭拜殉明的节士台先生、倪元璐、祈彪佳、钱肃乐,谒禹陵,这是名副其实的民族主义教育。“国破身存尚可为,怀沙何事放湘累”,“五千甲楯休悲叹,王气于今尚未消”,拜谒的目的无非让大家勿忘国事,鼓舞大家寄望中兴,为中兴而努力奋斗。惟其如此理解诗歌的含义,才能明白归庄缘何在此墨竹书画卷上作无坡之竹。康熙十四年,顾炎武在路安卿家见到归庄的遗墨《墨竹诗翰卷》,当然了然归庄当年的用意。时过境迁,故人已故,原来诸多志同道合的江南战友相继谢世,一半是碍于时局,一半是纪念其他的战友,顾炎武在归庄的《墨竹诗翰卷》后题下旧作《路光禄书来叙江东同好诸友一时徂谢感叹成篇》,但诗中“斯文万古将谁属,共尔衰迟老布衣”[6]仍然表达了与路安卿忠于明朝,矢志捍卫华夏文明的决心。
归庄与路安卿,是顾炎武的左膀右臂。他们不仅是顾炎武抗清的得力助手,而且顾炎武在江南被人陷害下狱时,亦多亏了这两位兄弟。归庄的《墨竹诗翰卷》正是三人易代之际在历史朝代的夹缝中惺惺相惜、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关系的写照。
①因版面所限,此九首诗的内容不再在此一一抄录,九首诗分别是:《同诸公发舟吴门赴山阴友人之约分韵得八庚》、《舟次石门同诸君再分韵得五歌》、《古小学拜念台先生祠》、《拜倪文正公像》、《拜祁忠敏公像》、《遥哭故刑部员外郎钱希声先生》、《山阴道中同诸公韵得二萧》、《会稽山谒禹陵分韵得十蒸》、《同诸公泛西湖分韵得七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