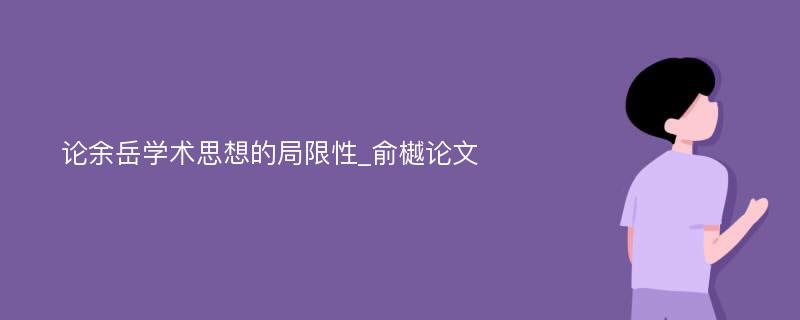
试论俞樾学术思想的几点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试论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晚清同光年间“最有声望”[1] (p.5)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着力重建传统文化,俞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大力揄扬。他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以“梯梁后学”为学术取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一方面遍注“群经”、“诸子”,对传统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并归纳出古文“文例”88例,为后学者从事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他潜心经史教育,主持杭州诂经精舍及其他重要书院达30多年,门生弟子数以千计,其中章太炎、黄以周、张佩伦、缪荃荪、吴昌硕、崔适、朱一新、戴望、吴大澂、谭献、宋恕等均在近代学术界享有盛誉。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特殊历史阶段,他对于传承以经学为核心的“国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对晚清学术乃至日、韩学术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晚清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俞樾的研究长期受到忽视。1972年台湾出版的《俞曲园学记》(曾昭旭著)是学术价值较高的一部著作,它对俞樾的学术成就进行了系统评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俞樾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大多局限于文学、方志学、考据学、中医文献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与经学思想有关的研究成果尚不丰富(注:近年来,俞樾在传统学术传承方面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台湾学者、《汉学研究》主编周昌龙先生2003年制定了研究专题《清末民初儒学的内在转化——以俞樾、章太炎、钱玄同学脉为中心》;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华人学者麦哲维的博士论题为《俞樾、陈澧、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浙江台州师院一位学者已初步完成《俞樾的学术传承》一书。但是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正式学术成果。近年笔者对俞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已发表论文有:“俞樾在日本韩国的影响及其与外国友人的交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2期;“俞樾的‘因文见道’思想及其学术风格”,《齐鲁学刊》2004年3期;“俞樾公羊思想发微”,《清史研究》2004年3期;“俞樾:‘务求通博’治经思想探析”,《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6期;“俞樾与经学人才的培养”,《山西师大学报》2005年1期。)。本文拟在笔者前几篇论文的基础上,对俞樾学术思想的局限性进行初步探讨。
一、被动顺应时代潮流,以淡漠态度对待西学
俞樾作为经学大师,其思想观念较为保守。他特别重视中国传统道德,认为施行仁政和强化道德教化乃是“自强之上策”[2] (卷六,p.12),指出“孝悌忠信即是兵法”。教化“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3] (《续五九枝谭》,p.1)。但另一方面,俞樾又吸收了《公羊春秋》的“改制”思想、《周易》的“穷变通久”思想和荀子的“法后王”思想,并且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有所认识,不仅肯定秦始皇变法等历史上的革新之举,而且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亦持理解态度。然而,他对于“变”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他说:“变也者,圣人之所不得已也。其已定之爻,无所用吾变也;未定之爻,而有可通,则亦不必用吾变也。穷而无所通,乃不得已而变以求通,此圣人所上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下以左右民也。”[4] (《易穷通变化论》,p.3)俞樾既站在维护传统道德的根本立场之上,又以“变”为圣人不得已之举,因此他对于现实社会变革必然缺乏主动精神,总是被动地随着时代潮流而一点一点地“变通”。由于他清醒地认识到晚清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清王朝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因此对举办“洋务”、“新政”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但他同时又敏感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5] (卷六.p.20),深知“洋务”、“新政”的开展,必将冲击乃至动摇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他内心对“洋务”及其西学又有抵触情绪。在他看来,“乌喙蝮蝎”之属,虽可以治“瘤疠痈疽”之毒,为医者“所不废”,但毕竟是有毒之物。有见于此,他对“洋务”、“新政”虽在总体上加以理解支持,对他人乃至自己子弟学习西学亦不反对,甚至还在遗言中表示,子孙“苟有能通声、光、电、化之学者,亦佳子弟也”[6] (p.99),然而他自己却“隐居放言,谨守包咸不言世务之义”,强调自己“于一切洋务、陆军、海军,皆非所知,亦非所欲言”[7] (卷八,p.4)。
从这种现实政治态度出发,俞樾虽身处西学东渐、中西交流日甚一日的时代,却对西学从来不去主动吸取。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西学已在“吾儒包孕之中”,只要“经史并通,即於体用兼备”,因而反对有些书院在常课之外别设一课,“专考经济有用之学”的做法[8] (卷三,pp.5~6)。由于对西学采取这种态度,因而终其一生,俞樾的西学知识可以说是极为贫乏。在他的著作中,除介绍过熊拔三的《西洋水法》和合信所著《博物新编》外,于西学仅有几处零星涉及。正因为他对西学茫无所知,所以直到1897年还坚持认为,如果精练20万藤牌军,持藤牌护身,佐以飞叉,则“破外夷之火器,有余裕矣!”[9] (卷二,PP.19~20)对西学之盲昧竟至于此!19世纪90年代初他还声称:“余惟农桑者,天下之本务,不可以末务参之。古人于此二事,至纤至细,事有一定之程,器有一定之制,而便宜苟且一切之谋,皆所不用。”[10] (p.7)他在《王梦薇本务述闻序》中亦有此说,且对“农事、织事皆欲以机器行之”颇不以为然,并为先民朴茂之美意渐失感到惋惜[5] (卷六.,p.20)。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俞樾对引进机器和西学的洋务运动持反对态度。在强调清吏治、严军政、端士习、苏民困为自强要策的同时,俞樾亦充分肯定彭玉麟提出的设海军、购枪炮、练新军的建议,认为这是“深识远虑”[7] (卷一,p.9);他还肯定浙江巡抚廖寿丰开茧纱厂、设蚕桑馆、颁焙茶新法诸举措,认为这些虽“从时尚,无诡经常”[9] (卷六,p.22)。细读俞樾的著作,诸如此类前后矛盾之说尚有不少。这与他对现实政治的矛盾态度密切相关,其为文势必随话语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前后失倨也属正常。
还需指出的是,俞樾对于学习西学的成效亦持怀疑态度。他从维护传统道德的基本立场出发,对西学的“消极”影响保持高度警惕。尽管认识到学习西学特别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必要性,但他反复强调“学于人者制于人”,因此要想克敌制胜,还必须在学习对方的同时另辟蹊径。具体而言,他认为西人利在火器等刚性的一面,中国在学习那些刚性事物的同时,还必须从柔性的一面发展自己,才能最终达到以柔克刚的效果。但是,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他认为能克刚的事物,除道德教化外,无非是“水器”、“藤牌”之类。
总之,与冯桂芬、郭嵩涛等同时代思想家相比,俞樾的西学知识是相当贫乏的,政治态度则具有鲜明的保守性;若与晚他一辈,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相比,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二、过于强化经学的致用功能,具有以学术比附道德教化的倾向
俞樾不仅对传统道德持保守立场,还特别重视道德实践。他一生以“卫道”自任,俨然传统道德的守护神,维护、表彰和阐扬传统道德,似乎已溶进他的生命之中。早在河南学政任上,俞樾就特别重视人伦教化,曾上疏奏请以公孙侨从祀文庙,以圣兄孟皮配享崇圣祠。罢官以后,他仍以人伦风化为己任,自言不敢“默然而息”[2] (卷四,p.1),于“名教乐地”“未肯多让”[11] (卷五,p.8)。他的杂文集收录约750余篇杂文,其中关系妇女的有130余篇(含夫妇合传),都突出歌颂“妇德”这一主题,其他杂文也以表彰忠节、孝行、义行为主,即使普通的人物碑铭亦多突出碑主德行。在他的诗集中,表彰忠孝节烈的内容也不少。他的笔记小说则几乎完全以“劝善”为主题,“刲股疗亲”、“以身殉夫”等愚昧行为都被作为正面典型大力表彰。他主持修撰的地方志,同样是这方面的内容连篇累牍。因此,当时人们对俞樾便有善于“写德”的评价。
俞樾强烈的“卫道”精神直接影响到他对经典的校勘、训释以及学术取向。他在校释群经时,一旦涉及道德教化,便会陷于先入为主和主观武断。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论语》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俞樾训释曰:“季氏聚敛,乃民聚而非财聚。盖冉子为季氏宰,必为之容民蓄众,使季氏私邑民人亲附,日益富庶。”[12] (卷三十一,p.1)
《论语》云:“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俞樾在训释中强调,子贡并非不受教命,只是“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12] (卷三十一,p.1)
《论语》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俞樾训诂该句时指出,两“不”皆语气词,“分”为“粪”之误,因谓“不勤,勤也;不分,粪也”。他认为此乃丈人自言:“惟四体勤,五谷粪而已,焉知尔所谓夫子!”并非以此责子路。[12] (卷三十一,pp.7~8)
《尚书·泰誓》云:“时哉弗可失。”俞樾认为:“武王为天下除暴乱,非争天下也。”因谓武王不可能有如此不仁之言。他断言:“《泰誓》之伪,即此可见,若徒推求於字句之间,抑末矣!”[2] (卷二,p.8)
以上训诂虽异于前人之说,却并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多为推论之言。揆其意,盖以为前人笺注有损圣人及门徒作为道德典型的形象,故出此言。俞樾之经说,诸如此类者尚有不少。
不仅如此,俞樾品评历史人物亦往往从道德教化出发,常以因果报应为说。例如他论晋文公:“有阴谋者,必有阴祸”;晋祚之所以不永,实乃晋文公“谲而不正”之报[2] (卷一,p.2)。他论马援亦与此相仿。为了宣扬因果报应,俞樾颇佑《左传》以成败论人。他说:“孔子作《春秋》,微其文,约其词,於当时诸侯大夫之罪,未尝斥言之也。夫使当时诸侯大夫之罪而皆著於后世,则人将以天道为疑,天道不信於天下,而天下乱从此起矣!”因此,他认为《左传》以成败论人,于齐之陈氏,晋之韩赵魏,以及陈、蔡、江、黄诸国,皆著其所以兴之之理,使善有所慕,恶有所惧,是“深得圣人之意”。他还强调:“左氏不以成败论人而务得其实,则可免后世之讥,然其为天下祸且愈以烈。”[2] (卷二,p.5)由此不难看出,俞樾本人未必真的相信因果报应,他之所以强调因果报应,主要是为了道德教化的需要。
俞樾对东汉王充所作的《论衡》的态度,进一步表现出他的这种倾向。他自言:“汉人之书……独不喜读王充之《论衡》,以为有大谬於圣人者。”其所以然者,缘于王充不信因果报应之说,认为世人受福佑并非行善所致,“实则遭遇使然耳”[11] (卷五,p.8)。但是就在同一杂文集中,俞樾又有《沈懋卿事释疑》一文,文中引王充“遭际有命”之说释沈氏虽称善士而不得善终之由,以“性善命凶为沈君定论”[11] (卷四,p.8)。俞樾之“实事求是”精神,于此完全被“致用”的需要所代替。以此观之,俞樾释经,凡关乎风俗道德,总以“教化”为首要考虑,即便其说有些根据,主观动机亦非纯以学术为目的。
俞樾既以“卫道”自任,其治学宗旨自然服从于道德教化的需要。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他还能够重视发挥传统儒学中的变革内涵,提倡荀子的“法后王”思想。以后随着洋务运动深化,西学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及生活方式的冲击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更多地强调自己为孟子之徒,要求“法先王”、“守先王之意”,并以“守先待后”为己任。1881年,他作《三大忧论》和《自强论》,前者强调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乃至整个民族面临的危机,后者则高扬孟子“返本”之说。俞樾一向不过问现实政治,这两篇仅有的政论文章绝非随意而作,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标志着俞樾治学宗旨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出于道德教化的急迫需要。尽管如此,直至“戊戌变法”以前,由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危机尚非十分尖锐,俞樾对“荀子之徒”的变革主张还能努力去适应。
但是从“戊戌变法”开始,俞樾再也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危机以及清王朝行将崩溃的命运使他惶恐焦灼,他不仅将“忧时之泪”在许、郑先师前洒了又洒,而且一再发出“久居人世待何如”[13] (卷十六,p.1)的哀叹。1900年他作“祈死”诗,又为“八十自悼文”,其内心之绝望可以想见。然而,就在俞樾惶恐绝望之际,其弟子章太炎顺应时代潮流,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俞樾对此极为愤怒,斥其为不忠不孝,并发表“破门声明”,将章太炎革出师门。章太炎毫不妥协,于1901年写作《谢本师》一文,表示与乃师决裂。从此两人分道扬镳。这也是俞樾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俞樾对传统道德执着、虔诚的态度来看,他将章太炎革出师门是严肃认真的,并不是为了掩人耳目、做做姿态而已[6] (p.72)。然而就章太炎而言,他仅仅是在政治上与乃师决裂,并不是从此不承认这位朝夕与共达8年之久的“先生”。1907年俞樾去世后,章太炎作《俞先生传》,高度评价俞樾的学术成就,其心中仍以俞樾为师,于此可知矣。
三、以疑似之见立说,以己意改经
学者们论及俞樾经学之弊,最突出的莫过于“好改经字”。此说最早由章太炎提出,他在《俞先生传》中说:“说经好改字,末年自敕。”[14] (p.211)以后学者相因为说,皆谓俞樾“务反旧说,一心标异,出言太易,论断亦近专辄”[15] (p.647)。
俞樾治经的确不如高邮王氏严谨,也的确存在以疑似之见立说、以己意改经的倾向。如《诗·天保》“君曰卜尔,万寿无疆”一句,旧注训“卜”为“予”,俞樾则谓“卜尔之‘卜’,当训‘报’。卜尔者,报尔也”[16] (卷三,p.4)。此即为疑似之见。俞樾在训释此条时亦多次使用“疑”、“殆”、“当”等词。诸如此类,在俞樾的经学著作中尚有不少。应当指出的是,俞樾之所以以疑似之见立说,与其治经思想和学术风格有关。俞樾治经喜欢“标异”,只要发现与旧说不符的新材料,即便其尚不足以推翻旧说,他也会本着“以疑存疑”的精神表而出之。所以后之学者常以“出言太易”病之。再者,俞樾以词章之士转而研治经学,且擅长逻辑思考,因此其治经风格倾向于从文章的整体结构和内在逻辑关系入手作训诂分析,而不是斤斤于片言只字;于是只要篇章段落乃至语句之间逻辑有所不协,语意有所不顺,他便怀疑经典原文本身,并在审慎考证的基础上大胆提出对经文的改动意见。他认定,古代经典在口耳相传乃至辗转传抄的过程中,本身出现讹误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他并不以改经字为非。他在《群经平议》序中明确指出:“或者病其(高邮王氏)改写经文,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罗者犹视乎薮泽矣。”[12] (《序》)在他看来,高邮王氏“改易经文”自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开阔的眼界,而以此为病者则往往是因认识水平有限而盲目批评。
任何一种治经思想和治经风格都有其长处,亦有其局限。俞樾既强调以疑存疑,其治经自然不那么严谨整饬;再加上俞樾务求“通博”,对一些问题缺乏专门而精深的研究,因此治经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亦当不少。然而他的这种治学思想和风格往往能发现和提出新问题,为后学者作先导。所以对俞樾的这种治学思想和风格,学界病之者固然有之,而赞成者亦不乏其人。梁启超就从未对此加以批评,钱玄同甚而号召学习俞樾的大胆疑经精神,宋恕则对俞樾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俞樾集“了真”、“洞至”、“入圣”、“极贤”、“擅鸿”、“兼文”、“践通”、“包儒”诸优长于一身,“学问至德清先生观止矣!”[17] (pp.105~108)宋恕此说虽然偏颇,但他能从“名学”出发把握俞樾的学术风格,强调俞樾“名家之学殆过实斋”[17] (p.90),的确可算是俞樾的学问知己。笔者以为,俞樾的这种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应当说是利弊互见,对之一味批评或过度推崇都是片面的。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重接受而轻思考,读者希望著者在书中提供精确无误的答案,所以对俞樾的标新立异、以疑似之见立说、以己意改经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如果读者同样抱着“以疑存疑”的态度去读俞著,发现他的与众不同和标异之处,从中得到启发,引起思考,进而深入钻研以求的论,从这个角度讲,俞樾的著作还是有其特殊价值的。
俞樾学术思想的局限主要是他对中西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使然。如果说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立场还含有一些合理成分的话,他对“刲股疗亲”、“以身殉夫”等封建道德的赞美则无疑是陈腐和落后的。此外,以“卫道”精神治学,让学术服务于“道德教化”的目的;以及“以疑似之见立说”、“以己意改经”的不甚严谨的学术风格,也都是俞樾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中显而易见的缺陷,后之学者对此不可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