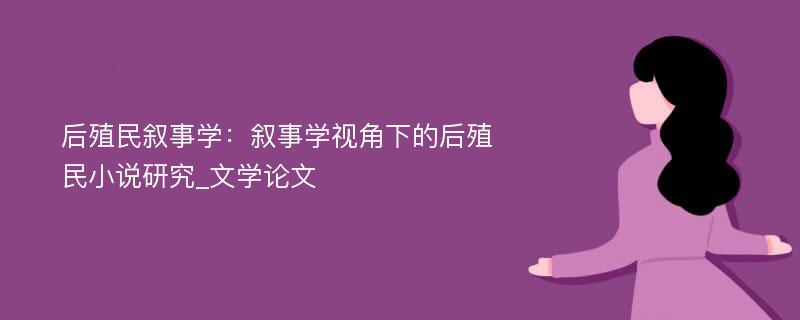
后殖民叙事学:从叙事学角度观察后殖民小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度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4)04-0096-10 “后殖民叙事学”(postcolonial narratology)出现在叙事学研究领域源于经典叙事学在90年代以后对此前结构主义模式的自觉反思,以及由此开始的语境化叙事学研究。随着“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修辞叙事学”(rhetorical narratology)、“认知叙事学”(cognitive narratology)等一系列跨界叙事分析模式的出现,后经典叙事学通常表现为“N-叙事学”的两相结合方式。(Herman,1999:1—39;2007:3—21)1996年,叙事学理论家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在《走向“自然”叙事学》一书中提出,叙事学分析与包括族裔文学在内的后殖民文学(主要是小说)在方法上可以互相借鉴,互为补充。首先,后殖民小说在文本语言层面通常具有显著的方言土语特点,代表了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历史,而这些特点一直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的关注点;同时,在故事内容层面呈现的压迫和抵抗冲突使得人物和叙述者的言语方式充满张力,呈现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特点,而这些特点可以通过叙事分析显示其文化冲突意蕴。再则,从阐释角度看,后殖民小说家对于帝国文化条件下的文学成规有着充分意识,并以此为参照用新的形式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叙述特点必然召唤读者对故事及其话语进行“对立模式”阅读(oppositional modes),而这些从形式修辞到伦理意义的互动模式为后经典叙事学提供新的理论视角。(1996:366—67)弗卢德尼克试图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批评进行桥接的努力在后经典叙事学发展史上并非首创之举,(申丹:2005)但是,与“女性主义叙事学”直接借用女性主义“抵抗阅读”(resistant reading)姿态不同,她的重点在于揭示叙事形式本身包含的形式差异以及由此对阅读产生的影响。以维多利亚小说叙事成规全知叙述模式为例,她指出,依照福柯权力话语的政治阐释将全知叙述模式理解为“圆形边沁监狱”(Benthamite prison)式的权威叙事和监控力量,并由此认为全知叙述模式代表了作品对故事和人物的绝对控制;然而,从叙事信息分析角度看,这种以点概面的解释混淆了全知叙述者作为信息提供者和利用信息进行控制之间的重要差别。(1996:369)从关注叙事形式及其叙事功能入手,揭示形式在具体作品中对于意义阐释的影响,这种在理论普遍性与叙事现象特殊性、形式意义与政治意蕴之间寻找中间动态结构的路径成为后来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1999年,法国叙事学理论家考德威尔(R.C.Caldwell Jr.)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分析方式。他认为,后殖民小说家在选择视角、编织情节、控制叙述节奏等方面通常表现出较强的自觉意识,并且以西方文学正典及其叙事成规为参照,通过挪用(appropriation)、改写(rewriting)、滑稽模拟(parody)等手法,在故事和话语层面凸显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以及对西方正典及其叙事成规的高度意识。(301—11)考德威尔这里的观点直接借鉴了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十分关注的“逆写策略”,以及与之对应的“逆向阅读”。不妨略说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萨义德(Edward Said)以法农(Frantz Fanon)的抵抗理论为基础,结合他本人的“东方主义”理论,聚焦于维多利亚经典小说,概述了“对位阅读法”(contrapuntal reading)对于揭示19、20世纪英国小说帝国意识的可操作性。(51)以交响乐中的“对位”现象为比喻,萨义德提出,帝国时期的小说隐含了作者写入文本的故事以及被排除在外的事实,因此,阅读这些小说必须参照帝国边缘地区的事实,对故事世界进行重新审视,揭示那些未被写入故事的暗示或附带性描述,揭示文本代表的“态度结构和指涉结构”。(Said:67、53)与此立场相似,考德威尔的“后殖民叙事”研究主要指一种阅读和阐释策略,所不同的是,这种逆向阅读立场不完全依赖于文本事实与历史事件之间的互为照观,而是立足于文本写作者对叙事成规的重新利用,以及由此体现在文本层面的形式差异。从这个角度看,“后殖民叙事学”采用英文表达式postcolonial,而不是用连字符号表述的post-colonial,说明其主要关注对象是殖民以后的文学叙事作品,即那些在形式上与帝国时期文学形成明显差异的叙事文本。这一点与后殖民文化理论中强调“后殖民”作为对殖民主义采取抵制与批判的姿态形成了差别。(Appiah:347—48)当然,除了与叙事学对文学范畴的文本的关注,后殖民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实验性质以及与传统正典、传统成规构成的差异使得叙事学界给予格外重视。从学科研究角度看,从叙事学切入的后殖民文学研究(以小说为主要类型)将有助于纷繁复杂的各种后殖民理论在彼此相关中各有所依,使得关于后殖民文学的研究凸显其“文学”属性。 在一篇名为《论后殖民叙事学》的文章中,普林斯(Gerald Prince)提出从叙事学理论和读者阐释两个方面构建后殖民叙事批评。普林斯认为,一种“有用的”后殖民叙事研究方法应该以经典叙事学理论为基础,同时吸纳后殖民文化批评对形式“差异”的文化成因探究,分析后殖民叙事文本形式层面的差异对阐释的影响。(2005:374)与弗卢德尼克不同,普林斯主张以经典叙事学为理论立场,参照后殖民批评的抵抗式阅读,观察后殖民叙事文本的形式差异,由此探究形式差异对阐释产生的认知和情感影响。这一认识与他对叙事学理论本身的强调有关。在一篇论述女性主义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关系的文章中,普林斯认为应该对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关系做如下解释:“一方面,叙事学为我们对具体文本叙事分析提供了工具和思想,使得叙事学成为一种叙事批评(narratological criticism)”;(1995:77)另一方面,“对具体文本的叙事分析‘有助于’对叙事学已有分类、特征和论述进行验证,对那些……可能被叙事学忽视、低估或误解的叙事要素进行辨析。”(1995:78)从表面上看,普林斯这里强调的是理论与阐释的互补关系,但他的重点落在理论对文本阐释的实用意义,而这也正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经过近三十年发展后开始出现的一个短板。在一篇回顾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文章里,有学者提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发展势头迅猛,但是,在这种强大的理论冲力下,“后殖民文学作品本身在西方学术界沦落为理论制造者的原料和消费品”,所谓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也大有“为理论而理论”之态势,成为后殖民理论圈内人士的某种特权话语。(Katrak:256)这一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至少表明关于叙事作品本身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而对于作品本身的关注一直是叙事学研究的重点。 回到普林斯的观点。与上述提到的叙事学研究者不同,普林斯并未从后殖民作家的“挪用”入手探究后殖民叙事学的理论构架,而是从叙事文本的基本要素出发,观察后殖民作家的作品在叙事句法(syntax)、语义(semantics)及语用(pragmatics)层面呈现的特殊性与差异性。(2005:375)从形式范畴提出的叙事差异,这一立场与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的“主导”(dominant)概念具有相似性。在论述文学语言诗性功能时,雅克布森把文学语言的诗性特点看作一种结构功能,并用“主导”一词来描述具有自我指涉特点的文学语言符号体系与非文学语言之间的等级关系。雅克布森认为,“主导在艺术作品中统治、决定、改变其余成分,保证了结构的统一”;但他同时指出,“主导”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在各种文学类型相交过程中互为影响,由此形成“主导”统领下的各种“变异”(deviant)。(Jakobson:82、87)也就是说,“主导”并非文学内部固定不变的封闭系统,而是在自成体系的同时外向发展并保持开放的动态结构。从叙事形式角度观察后殖民叙事作品与文学成规的差异,我们就会发现,作品在故事与形式层面隐含或明显的抵抗姿态并非与叙事作品的“主导”构成截然对立,而是在差异中形成对话关系,并由此产生族裔正典。或者说,后殖民小说通过模拟殖民文学样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创造自己的文本。(Boehmer,2006:359) 普林斯从叙事理论与叙事批评关系维度提出的“后殖民叙事学”设想,这一出发点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从文本“内部”进行的分析方法,其意义在于揭示后殖民叙事文学在形式层面与文学常规和叙事理论之间的差异,由此拓展叙事分析的理论视野和批评实践。据此,普林斯提出,关于后殖民叙事文本的研究可以依照经典叙事学的“故事”与“话语”二分法进行。例如,可以以所述对象(即故事内容)为考察对象,观察故事空间与时间结构关系:关于故事空间的描述是以“概述法”一笔带过,还是采用人物或叙述者视角展示;关于故事空间的描述在叙事进程中呈现为固定不变还是不断改变;情节编织过程是单个线型图式还是在多线条平行推进中构成多重故事空间。(2005:376)普林斯提出的第二个分析点是从话语层面切入,关注视角、声音和语言方式,尤其是那些以“叙述人称”为标识的个体或群体叙述模式,以此揭示叙述者与群体之间的认同或差异关系。(2005:379)众所周知,空间与身份是后殖民批评的重要概念,也是后殖民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对于“流散裔”写作而言,故事空间更是一个与身份杂糅、无根性(rootlessenss)等文化心理相关的基本主题。(Boehmer,2005:230—31)在巴巴(Homi Bhabha)提出的相关论述中,“空间”被赋予符号学和文化心理学意义,成为他阐述民族和文化“杂糅本质”的一个转义——“间质空间”(liminal space)。(1994:3—5)普林斯的“空间”与后殖民文学批评关注的“空间”,其概念所指固然不同,不过他指出,“总体上看,可以从一些与后殖民问题具有相关性的角度观察叙述层面的情形,必要时,可以对叙事学已有概念进行调整,以便能够适用于解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2005:379)事实上,关于故事空间在叙事作品中的结构功能以及相应的空间象征意义研究,都离不开故事空间以及叙述话语对空间的文化隐喻描述。(Boehmer,2005:24—28) 提倡从叙述行为(narrating)观察后殖民叙事文本与叙事成规和理论发生的偏离,由此对既定理论进行调整,这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后殖民叙事文学对叙事成规和理论的修正力量,同时也将作品形式差异视为叙事总体研究的一部分。基于同样立场,2007年,弗卢德尼克发表文章《认同/他性》,将认同与他性(Otherness)作为一种情感和认知概念用于包括后殖民文学在内的总体框架中。她提出,“认同”与“他性”(alterity)是后殖民研究的重点,但同时也是所有叙事文学的普遍特点: 我们从他人那里认识自己,正如他人从我们眼光里认识自己。……自我首先是作为一种投射,以回应他人的凝视。因此,认同强调的不是[我]与他人之不同,不仅仅是从众多人中抽取出来的某个单一体,而是在认同与差异交替发生中对我和他者关系的重新认识与重新建构。(2007:261) 弗卢德尼克指出,不论是传记或传记式小说以第一人称呈现的“我”的故事,还是用第三人称讲述的他人故事,都是关于经验世界的差异性,“叙事从本质上是关于他性/他人[经验]的重新展现”,(2007:264)而关于经验差异的展现同时又依赖于叙事行为某些普遍成规。就后殖民叙事文本与叙事普遍成规的关系而言,她认为,一个核心问题是:“后殖民叙事文学作品关于空间的文本描述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文本世界里的他性(alterity),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2007:269)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做如下表述:在何种程度上,后殖民文学批评关注的“他者化”(othering)问题显现在作品的形式差异方面? 围绕这个问题,后经典叙事学领域的研究者们进行了多方位探究。以下列举三个切入点进行介绍与阐述,展示叙事分析与后殖民文学批评之间的相交点,以供研究者参考。 多维度分析方法 1.语言多样性研究 我们熟知,后殖民文学批评强调语言使用方式蕴含的文化政治意义。为此,后殖民书写通常表现为“从中心攫取语言,将它重新置于被殖民者语境中,使之产生新的意义”。(Ashcroft et al.:38)“语言”在这里不仅指标准的英国英语,同时也指那些被视为与帝国文化相应的文学成规与阐释理论;对于后殖民作家而言,将这种“语言”从中心移至边缘实际上意味着对其进行改造,以便重新赋予话语以力量。换言之,挪用后的语言从能指符号到所指概念,包括所指之物,都将发生改变。以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语小说为例,以英语为基础,掺杂法语、西班牙语、非洲土语的语言混杂现象使得作品的语言、文体明显有别于传统的英语小说。如果考虑到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在帝国时代起不断强化的“主导”地位,那么这种语言杂糅则代表了与先前语言形成差异和对应的“小写的多样性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s)”。(Ashcroft et al.:45)这种语言差异同样受到叙事学界关注。吉姆尼奇(Marion Gymnich)在《语言学与叙事学:语言学与后殖民叙事学相关性》一文中提出,后殖民小说语言方面的混杂特点提醒我们,应该关注语言及其使用方式对作品结构和阐释产生的影响,因为这些特殊性将有助于揭示语言与文化身份之间的象征关系,显现语言形式蕴含的族裔、阶级和性别意识形态。(62)他认为,叙事作品在“故事”和“话语”层的二元结构使得作品包含了多种语言方式,这也是后殖民小说有别于一般叙事作品的重要特点。例如,如果聚焦者或叙述者是原住民,其“非标准”的语言方式(语音、拼写、句法)既是故事内容,同时又是一种“文学方言”(literary dialect);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作者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就叙事功能而言,“文学方言”为读者提供了言说者所属地区、文化与社会背景。吉姆尼奇认为,“文学方言”常见于第一人称叙述模式中,但是,在异故事叙述(heterodiegetic)情形中,即以第三人称为语法标识的全知叙述模式中,那些“非标准的”的语言现象常常被全知叙述者指称为“外语”,以翻译或直接引用的方式出现在文本中。除了提供故事外的信息,“文学方言”直接影响读者对故事,以及与叙述者之间的情感、文化认同。比如,在阿切布(Chinua Achebe)的小说《解体》中,叙述者提到伊格伯民族的茅草屋(obi)时附加了英文词hut。除了帮助读者理解,叙述者的“翻译”将两种语言及其文化一并呈献给读者,由此体现了后殖民小说通过故事传递给读者的“他性”体验。(68)值得一提的是,吉姆尼奇的观点与阿什克洛夫特对《解体》混杂英语的解释十分类似。略有不同的是,后者认为,将“民族语言”、土语与英语进行并置,这种语言方式看似属于作者以“注释”(glossing)对故事的介入,实质上展示了伊格伯语obi与英语hut两个能指之外的对象(referent)。读者由此看到,无论其中的哪个词,都无法指向符号之外的物本身,即伊格伯民族的文化历史。换言之,伊格伯语还是英语,都只是符号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文本外的经验与历史,而两种符号的并存现象则凸显了符号差异背后经验或文化身份的独特性。(Ashcroft et al.:60) 需要补充的是,吉姆尼奇从叙事角度探究的语言问题基本上囿于语言的标准性与非标准性这一二元项,以此为基础,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人物与叙述者的“非标准”。从叙事文本“故事”与“话语”两分法结构看,这一分析有利于我们细察由叙述者和人物构成的故事世界里多声部的语言方式,并由此揭示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不过,我们应该同时认识到,后殖民小说语言差异远不只是标准与非标准之差异,“非标准”内部还存在不同语言混杂产生的差异。或者说,语言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标准与非标准之界限变得模糊。例如,在非洲美国裔小说中,一个十分普遍的语言现象是黑人英语表意系统的双重意指结构:一方面是来自黑人土语方言、并且表述发音与拼写特殊性的“意指”(signifyin[g])符号,另一方面是通过模仿英语文学及其修辞方式获得的新的表意方式。正如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所说,非洲裔美国文学的表意系统具有“双声”(doublevoiced),看似黑白兼有的双声实际上是以黑白传统为基础的多重,是以“滑稽模仿”(parody)方式实现的对转义(trope)的再度运用。(xxii—xxiv)当然,族裔文学文本在语言方式上的多样性并非一向如此,而是源于作家有意为之的“逆写”(write back)。(Ashcroft et al.:3)但是,从阅读立场上看,若要观察“逆写”蕴含的文化历史意蕴,我们必须依赖于文本提供的形式依据或故事事件,而后殖民叙事文本语言方式的多样性显然不能简单地套用后殖民批评理论关于压迫与反抗的二元对立逻辑。在这一点上,巴巴的观点值得参考。他阐述了被殖民者通过“模拟”殖民者语言和文化方式混杂两种语言和身份,使得模拟者的话语在差异(difference)和“模棱两可”(ambivalence)中呈现出“双声表述”(double articulation),而边界的模糊化正是产生异质文本与文化“他性”的基础,也是“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得以发生的一个界面。(1990:209) 从对立、抵抗关系到逐渐关注差异与杂糅,同时从语言方式入手重新审视对抵抗中的差异与认同,这或许是后殖民文学批评与叙事分析开始走近的一个理论契机。 2.认知叙事分析 较之后殖民批评从社会政治角度对语言与权力关系的强调,后殖民叙事学倡导者倾向于从叙事认知角度探究文本形式(包括上述语言方式)与阅读视野之间的关系。借用经典叙事学理论的“隐含作者”概念,马戈林(Uri Margolin)提出了“认知文体”(cognitive style)概念,认为作者(真实作者)的叙事手法代表了个人化的文体与风格,不仅象征着作者本人对故事主题的价值倾向或立场态度,而且代表了作者对文本理想读者的预设。(277)马戈林重提经典叙事学概念“隐含作者”,意在强调真实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为依存关系,而“隐含作者”在叙事信息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中的结构意义显示了经典叙事学本身蕴含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叙事文本内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Shen:80—98)正如布思(Wayne Booth)指出,正是通过具体叙事策略(叙述声音、视角、语言方式等),作者与读者之间才有可能形成“秘而不宣的交流”。(300)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与读者在认知层面的共通性属于叙事交流过程的普遍规律,后殖民小说家预设的理想读者具有认知层面的特殊性。前文提到,基于文化历史原因,“逆写”被后殖民文学批评视为后殖民写作的重要动因,而“逆写”或多或少涉及对帝国文化时期文学成规的熟悉以及以此为参照对象进行的“改写”。例如,里斯(Jean Rhys)在谈到《藻海无边》的创作动机时明确指出,其创作初衷是因为她不相信夏洛蒂笔下的疯女人,(Wyndham and Melly:296)因而有一种迫切的愿望要让伯莎的原型——安托瓦奈特——叙述自己的故事。《藻海无边》通篇没有提到《简·爱》中的罗切斯特,但是,小说在情节结构、人物关系、故事空间方面与《简·爱》的高度吻合使得读者对两部作品之间的对照关系了然于心。(Spivak,1999:112—32)从文学阐释的角度看,《简·爱》构成了我们理解《藻海无边》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除了包含叙事作品普遍包含的作者编码与读者解码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还包含对前一文本及其叙事方式预设的阐释进行的逆向解释。宽泛而言,后殖民小说同时包含了帝国文化的经典以及对经典的改写,体现在故事和话语层面的“逆写”要求其读者在过去与现在、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等一系列对立关系中进行双向阅读。换一种说法,后殖民小说家通过叙事形式表述的“逆向写作”在文本内预设了“模范读者”(model reader)。艾柯(Umberto Eco)认为,为了使作品的意义顺利传递至读者,作者在文本中以特定的形式为“模范读者”预设了阅读立场,“这样的读者与作者共享文本依赖的形式符码,对文本的阐释与作者的思想保持总体一致。”(7)笔者认为,不同于后殖民批评强调的“抵抗”阅读,艾可的“模范读者”强调的是文本形式对阐释者的牵制作用,而不是可以摆脱文本形式、以“抵抗”为名的逆向阅读,更不是以意为之的政治批评。从根本上讲,后殖民小说家的叙事目的在于通过有差异的叙事形式讲述他们的故事,展示他们的经验与想象,并以此和熟悉这些经验与故事的读者建立认知与情感关系。(Aldama:7)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殖民小说叙事形式差异性是文学性范畴对于叙事成规进行的陌生化处理,而对于形式差异的细致观察也是文本包含的认知结构,要求阐释者对萨义德提出的“写入的、未写入的”(67)进行“对位阅读”。正是这种带有牵制作用的预设立场,使得关于后殖民叙事文本的研究在文本内外之间进行有效的叙事分析。 3.类文本叙事研究 如果说从叙事认知角度切入的后殖民叙事研究揭示了文本叙事形式差异对文化历史阐释的牵制意义,由法国叙事学领军人物热奈特(Gérard Genette)近年来提出的“类文本”(paratext)研究则从文本内外关系角度为后殖民叙事分析提供了一种内外兼顾的阐释方法。 在1982年出版的《隐迹稿本》中,热奈特提出了他称之为关于“超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研究计划,从他此前关于文本内结构关系的研究转向对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显性或隐性关系的探究,以期揭示各种不同文本间关系对文本阐释的认知影响。(1987:1)他认为,围绕某个文本以显性或隐含方式存在五种依附文本,与主文本之间形成类跨文本关系:文本之间在母题、形式方面互为借鉴的“互文”(intertextuality);文本通过标题、副标题、前言、后记等文内标识形成的“类文本”(paratextuality);“评价”或引用其他文本的“元文本”(metatextuality);直接引用其他文本使得文本中出现被“嫁接”文本的“超文本”(hypertextuality),以及以文类特征明示(如小说、诗歌)但让读者觉察到其跨文类特征的“统文本”(architecturality)。(1982:2—5)热奈特这一分类是否具有类型学上的一致性我们姑且不论,①这一观察揭示的文学文本内部关系、文类间关系,以及多文本形式对阐释视阈的牵制意义,对于后殖民文学本质上的“跨文化”与“跨界”特点富有启发意义。正如从事后殖民小说形式分析的学者们意识到的,不同于经典叙事学集中于文本内部关系的方法构成差异,后殖民叙事文本既有文本内部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同时也有关于真实世界的展现,更不乏实际与虚构之间的界面或临界区域。(Aldama:35、22)在1987年出版的《类文本:理解之门槛》中,热奈特详细分析了“类文本”作为连接文本之间、文本与作者和读者之间承担的各种叙事交流功能,并用“门槛”作为比喻,强调“类文本”在引导读者进入文本、获得叙事信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文本内的类文本”(peritext),如标题、副标题、署名、前言、题献、卷首引语、序言、小标题、注释、后记,和“文本的类文本”(epitext),如出版广告、新书通告、海报,以及作者书信、日记,既是主文本的一部分,也是与文本对应的某些事实。(1987:7、117、129、319)类文本在文本内部与文本间构建的互文关系,以及在互文关系中显现的叙事功能与后殖民小说的“跨文化”和“跨界”存在文学意义和文化象征意义层面的相关性。例如,在奈保尔(V.S.Naipaul)的小说《抵达之谜》中,故事主人公的经历与作者本人1987年(小说于同年出版)之前的生平存在很大重合之处,熟悉作者生平的读者自然联想到作品的自传性质。然而,副标题——“五部分的小说”——无疑强调了其虚构本质。如果说故事主人公对往事的回忆展示了“英国性”从中心到边缘(特立尼达)的弥散过程,这段基于作者从边缘到中心(成为英国作家)的亲身经历同时也揭示了对英国性的认同,而叙述者通过将故事切分为五个片段进行叙述,并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经验视角与叙述视角对三个空间(英国、特立尼达、印度)进行交叉叙述,使得主人公关于殖民史的纪实与文学想象同时呈现出来。此外,作者为小说撰写的序言,强调“摆在面前的[文字]与头脑中的[思想]存在差异”。(vi)游离在文本外的事实与虚构的故事,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序言”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互文结构,提醒读者以谨慎的态度对待作品的“后殖民批评”主题。② 与《抵达之谜》隐匿在虚构背后的传记不同,一些更具后现代实验性质的族裔小说则采用“文内类文本”策略,在模糊文类界限的同时将故事与历史一并呈现给读者。当代美国非洲裔作家里德(Ishmael Reed)的小说《芒博琼博》便是这样的例子。小说开篇之前是一则故事叙述者的序言(并非作者序言);序言末尾是一幅来自报刊的黑人舞蹈图片;图片下方是引自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关于黑人爵士乐的评论,其中用斜体表示的强调则被明确为真实作者所为;紧接其后是摘自《美国英语词典》对“Mumbo Jumbo”一词的解释。在阅读了这么多信息之后,我们仍然徘徊在故事之外。此后,我们读到三个卷首引语,分别来自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和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对黑人歌舞和黑人诗歌的评论。③重复出现在引语中的黑人土语jes' grew(意为“就这么长大”),令熟悉美国黑人语言的读者、尤其是熟悉《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读者立刻联想到jes' grew在这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用即兴歌舞表述情感的黑孩子托普西(Topsy)被人误解为疯癫胡闹,同样,《芒博琼博》围绕着黑人艺术灵感在美国精英文化条件下的困境的形容词编织情节。美国白人将黑人歌舞看作破坏文明的流行病,是“胡言乱语”(mumbo jumbo),而在黑人土语中恰是祈求安宁的“神灵”。在这部小说的情节进程中,介于故事内外、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类文本”成为引导阐释、推进题旨的一个隐喻结构,使得作品关于欧洲中心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书写文字与身体行为、神话与现实等一系列对立关系充分得到展开。(Butler:180—82) 以上介绍了“后殖民叙事学”涉及的理论立场以及相应的三个观察点,并对这一立场与后殖民文化批评关于文学研究和语言分析的相关论述进行了阐述与辨析,说明它们之间的交叉互补关系。需要重申的是,“后殖民叙事学”并非理论范畴自成体系的一个“学”,而是一种阐释方法,目的在于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文化阐释进行结合。从叙事分析入手反观后殖民小说在形式上与传统正典及其叙事成规的差异性,这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对叙事形式(审美)与意识形态(政治)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当然,这一努力虽然一直存在,而且从未间断。(Bennett:53—74)从叙事学角度做深入探究的空间也十分丰富,例如,巴特(Roland Barthes)关于阅读符码的论述,(19—20)文学形象分析与套话叙事之间的关系,(Bhabha:1984:99—100)这些都是这一方向的理论基础。总之,从叙事学角度探究后殖民小说形式差异背后的文化历史意义,以期揭示后殖民小说在“逆写”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族裔正典”及其诗学意义,这一努力本身蕴含了促使包括后殖民小说在内的第三世界文学从边缘迂回进入世界文学多样性的理想之地的努力。 ①对这一概念进行详细阐述的,国内有许德金文章,国外有格莱弗敦(Anthony Grafton)专著,均见参考文献所列。 ②关于奈保尔作品中的后殖民批评主题,评论界呈现为两极对峙态势:或者认为他认同帝国文化,或者认为他是殖民文化的批判者。形成这一对峙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套用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从作品中寻找支撑理论的文本证据。详见Bruce King,V.S.Naipaul(Palgrave),2003。 ③里德以实验手法将这些引文嵌入《芒博琼博》,并且有意略去页码标识。参见文献罗列Reed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