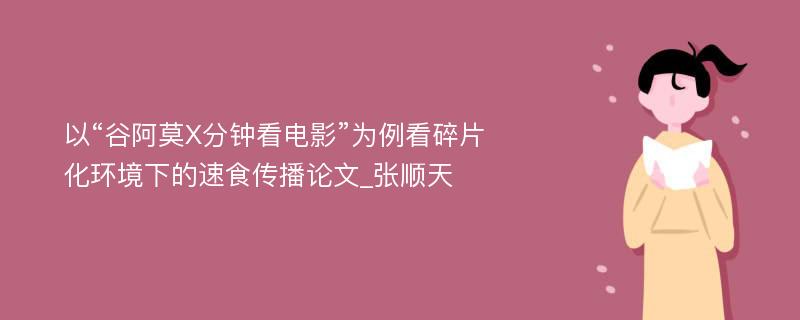
摘要:媒介最重要的作用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麦克·卢汉在1964年提出:“对媒体而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媒体本身,是媒体的形式规定着媒体的内容”。“媒介即是讯息”的呼告仍振聋发聩,令人信服。“碎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诸多相关文献中,其意本为将完整的事物分开、打破成零散的碎块。现如今,“碎片化”已紧密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相连在一起。
关键词:碎片化;谷阿莫;速食传播;信息
将传播的“馅”包进碎片化的“皮”
从传播学的观点来说,“碎片化”特指“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大量的信息涌现导致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受到媒体多样化的影响”。相对于碎片化在传播领域,更直白说是在影视传媒领域的具体结合,笔者以“谷阿莫讲电影”为例做简单分析,暂且称之为“速食传播”,顾名思义,简化传播流程,提高传播效率。
快节奏的时代使得每个人的时间似乎格外宝贵,更失去了原有的耐心去深入的了解一个事物,如果不是在电影院里,甚至会有更多的人没有耐心看完一整部电影,太多的事物转移了注意力。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人们似乎方向明确又无所适从,勇往直前却又瞻前顾后,对于俯拾皆是的冗杂信息,沉浸其中很难脱身。
高高在上、不可向迩的一本正经的电影解说不仅耗时较长,且听起来不对网络新生代的胃口,倒不如类似谷阿莫的X分钟带你看电影系列。
“碎片化”传播的特征
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主要针对所传播的信息内容。网络信息恰如汪洋大海,受众无时无刻不被流于表面的信息包围,而这些信息又无法给受众喘息思考的机会,只能被接踵而至的下一条信息吸引。
媒体表达的“碎片化”。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信息提供了丰富的表达平台,各种软件功能丰富之令人目不暇接,碎片化信息宛如使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受众无意识刷新页面,就像不受控制的木偶,源源不断更新的信息也就成了那些绚烂的烟花图案。
受众接受方式的“碎片化”。这里主要指受众在接收上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它直接影响了小众化、分众化的产生,而它们的出现又加剧了信息的“碎片化”,最终仍旧反映在受众接收零散的信息方面。
“碎片化”依靠信息传递的快速、便捷、多样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认知能力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年来,“标签化传播”成为新媒体发展过程中信息传播的新形式。“标签化传播”是指“抽取某一事件中最突出的特点,利用直白、形象、风趣、容易理解的词句对某一事件进行超浓缩的概括。往往通过最简单的语言浓缩事件内容,既便于受众了解事件内容,留下深刻印象,又利于事件的广泛流传,保留事件的热度”。除了热点事件的标签,人们每日关注的种种也在被“标签化”,生活在新媒体中的受众无时无刻不在被“标签化传播”影响。
“信息茧房”带来“娱乐至死”
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写到,“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
“信息茧房”的出现一方面为受众阻挡了多余信息的干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爆炸的威力,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更多信息以更多种类的形式出现,以满足越来越多不同喜好的受众。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受众对新闻时事的不关注、不重视正是因为“信息茧房”的长期存在,它看似有助于受众对信息进行分类和有目的的深度阅读,实际上却造成娱乐信息大面积覆盖,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受众深度阅读的能力。
一般而言,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十分有限,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自身的兴趣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拘束在好似蚕茧一样的“茧房”之中。尽管社会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给人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观点、种类繁多的信息,但是过于繁多的资讯,使得公众只能将其有限的注意力集中于其偏爱的信息领域。在此“信息茧房”中,人们只会看到与其态度一致的内容,听到与其信念一致的声音,接触于其立场一致的人群。长期以往,便形成了一个仅能容纳相同意见的“回音室”,身处其中的人们听到的只有自己被放大的回声。
“碎片化”的泛阅读风气
当“碎片化”已成为当今信息传播的主流,我们应该看到“碎片化”的传播环境对受众造成的影响,如何解决“碎片化”环境下的泛阅读现象是媒体与个人都亟待着手处理的问题。
针对目前“碎片化”带来的信息爆炸问题,“碎片化”理应得到适当的控制,而媒体在这里需要发挥重要作用。有效地控制信息“碎片化”,应该从加强新闻的深度报道入手。在新媒体发展迅猛、传统媒体举步维艰的今天,深度报道逐渐陷入困境,新媒体将重心放在新闻信息的速度和广度上,而忽略了报道的深度,因此出现大量“碎”新闻,新媒体时代如何做出有深度的报道一度困扰着媒体人。
传播的信息“碎片化”,一方面体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预示了人的认知能力在退化、思考能力在下降。在“微传播”“标签化传播”“信息茧房”这三重因素影响下,信息传播渠道不断增多,受众的认知力减退,深度阅读的能力受到束缚,全民泛阅读现象由此产生。面对当下“碎片化”的信息传播,媒体或个人都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碎片化”传播,并作出合理引导,以期更高效地解决全民泛阅读问题。
谷阿莫的“短平快”
谷阿莫的电影解说“短平快”——简短、平实、节奏快。《最好的我们》片长110分钟,被谷阿莫缩减到5分多钟,并称为“5分鐘看完2019等帥哥告白等七年的電影”。他用一句话将之概括为“哥们出卖你的故事”,解说平均五秒钟三十字。短片镜头剪辑比电影更快,提纲挈领的解说让观者脑海中只保留了电影的框架,取精去粕。他搞笑接地气的台词,如“一起去情人山种暧昧树”,及大量网络用语的运用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半叙半议且平实不做作的风格也让观众多了一份同感。
例如报刊业由二十年前空前绝后的传媒地位,言必称“泛众传播”,到现在的艰难转型,尴尬的小步紧跟走向“分众传播”,不得不说对碎片化社会可略见一斑。
传播技术的空前发展,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资讯则死的时代,信息海量,观点泛滥,人人都是受众,人人也都是传播者。在新媒体环境下,我们面对碎片化传播信息的全面轰炸,只有认清它,不受制于它,对它进行理性的思考、判断并加以利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当然,也许仍有许多人会以知识产权为由,质疑“速食电影”的兴起,这可能是谷阿莫们所遭遇到的最大的麻烦,这也是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中最严厉的一条规定:“对节目版权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影视制作机构投诉的此类节目,要立即做下线处理。”因为这一条规定纯从版权出发,甚至绕开了价值观是否正确。不过,在谷阿莫被诉侵权一案中,人们发现,迄今为止相关的法律判决仍然处于模糊地带,即便在美国,如何认定戏仿作品也并不那么绝对。也许从国家文化权力的生成来看待“速食电影”,我们才会对法律的制定以及是否认定它们侵权,获得一些不同的观察视角。
笔者认为,碎片化既是潮流,便有其退潮之时。潮退后,滩涂之上留下珠玉抑或顽石,只待时间证明。
论文作者:张顺天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1月4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0/29
标签:碎片论文; 信息论文; 受众论文; 媒体论文; 电影论文; 信息传播论文; 事件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1月47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