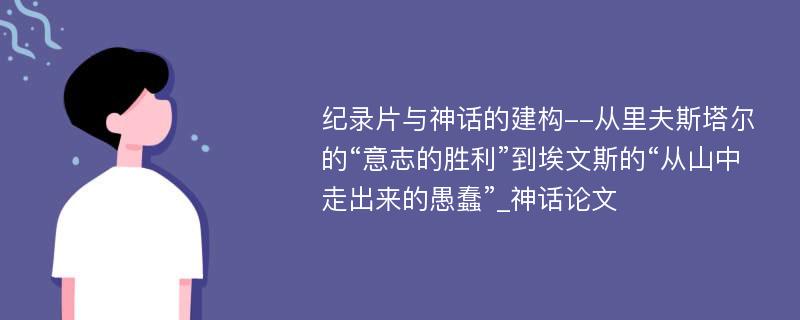
纪录片和神话的建构——从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到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愚公移山论文,文思论文,纪录片论文,意志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35.1 [文献标识码]A
Richard M.Barsam在他的《纪录与真实——世界非剧情片批评史》一书中谈到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影片《意志的胜利》时说:“在本片中,里芬斯塔尔精湛的融合了四项电影的基本元素:光亮、黑暗、声音及无声。也因为本片有其他基本的元素,所以它也不仅止于电影形式上的成就。这些元素包括:主题的、心理学的及神话上的叙事,而在上述这些元素的互相作用下,里芬斯塔尔已超越纪录片及宣传片作为一个类型的限制。她的艺术就是感知真实状况的本质,并把那个真实时刻的形式、内容与意义转化成电影。透过她对神话的运用,里芬斯塔尔丰富了稍纵即逝的时刻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并延伸了那一刻的意义。她也由此转化了实景的纪录性片段成为她自己观看现实的神话式视野。”(Barsam,1996:p.119)应该说,这是一个对于里芬斯塔尔影片的较为公允的评价。
在此,Barsam涉及到了一个全新的命题:具有神话意味的纪录片,或者建构神话的纪录片。Barsam也许只是偶然触及到了这个题目,因为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就此展开。这是一个有趣的提法,至少不同于直截了当的批评和赞扬,我们甚至很难从中体会到明确的褒贬意味。从批评的角度来看,“神话”似乎代表了“不可信”、“编造”。但从赞扬的角度来看,神话似乎又可以表示“美好愿望”、“纯洁向往”等。被认为对客体不准确的描绘和表现,被“神话”这样的评价在主体的层面上重新定义,这样一来,被认为是失真的客体就必须通过哲学的思辨,在结合历史反思的层面上重新作出评价。Barsam的批评便意味着这样一种再评价。如果“神话”的指称不再是嘲讽和挖苦,而是一种严肃的批评的话,那么制造“神话”的就不会只是里芬斯塔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文思的纪录片同样也具有神话的意味。并且,许多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纪录片或多或少都会呈现出相类似的这样一种特性。①
相对于纪录片的神话的概念
相对于纪录片来说,神话概念中有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一是信仰,二是时态。一般来说,神话必须在人们的信仰中才能产生,同时,在神话产生的那个时代,因为普遍信仰的缘故,神话并不成其为神话,只是后人看到了前人信仰中存在与事实不相符的部分,并因此而失去信仰,所以将过去那部分被认为的“事实”更名为“神话”(如果某人直到今天仍然维持着过去的信仰,那么我们认为的神话对于他来说依然是事实,而非神话。)。②
列维·斯特劳斯在他《野性的思维》一书中说:“巫术的仪式和信条似乎就是一种对即将诞生的科学怀具信仰的行为的种种表现。”(列维·斯特劳斯,1987:p.16)
弗雷泽在他《金枝》一书中说:“宗教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就是: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怒的种种企图。这两者中,显然信仰在先,因为必须相信神的存在才会想要取悦于神。”(弗雷泽,1987:p.77)
鲁迅在《神话与传说》一文中说:“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鲁迅,1994:p.63)
黄石在《神话的价值》一文中说:“我们绝不能说作神话的人,是存心自欺欺人,反之,他们只是诚实的表现出他们质朴幼稚的感想罢了。”(黄石,1994:p.102)
以上诸位专家学者的论述已经证明信仰之于神话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由于至诚的相信,许多事物可以不必究其所以然而先验地存在于信仰者的头脑之中,这也是宗教至今仍然能够存在的原因之一。Barsam指里芬斯塔尔的影片为神话,也就是指影片的作者过于信仰和迷恋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而将希特勒及其政党虚张声势、蛊惑民众的宣传和表演表现成了一种对于未来的充满信心的、必胜的仪式。伊文思笃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如果他将自己的信念毫无保留地倾注于自己的作品,那么他的作品必然也会是一个神话。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一个神话的构成不仅需要至诚的信仰,同时还需要另外的条件——某种仪式化的过程。
纪录片神话仪式的构成
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信仰都需要通过仪式来达成,仪式如果不是信仰的必由之路,至少也是那些非科学的、无法予以论证的集体信仰所不可或缺的。仪式是一种聚集大众的“凝合剂”,同时也是将人们从现实世界过渡至意念世界的桥梁。
神话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当人们需要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需要建立一个特殊的通道,只有在这个通道之中,人们才有可能摆脱现实世界的各种负担和羁绊,这就是所谓的仪式。在远古的人类那里,仪式需要载歌载舞,或需要流血,或需要至少是象征性地将人置于危险、困难的境地等等,由这些特殊行为唤醒的灵魂从主体与客体诸多的联系中脱身,投入纯粹的主观世界,神话便在那里鲜活地存在着。仪式是进入信仰世界的魔幻之门。对于不同的宗教可以有不同的仪式,那么,什么是纪录片的仪式?
托玛斯·吴沃在他纪念共产主义运动纪录片百年的论文中提到,大凡与人民、革命相关的这一类纪录影片往往会着力表现示威游行:“我在《印度尼西亚在召唤》周围所选择的这五个电影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们都属于“示威游行”的类型。一方面,它们很表面化,大多为忠诚纪录片公式化的俗套。示威游行对于所有糟糕的电影制作者和没有想象力的学派来说是一个陷阱,而对电影制作者们所创造的带有强烈的政治反讽和神秘而言,则是标志,……这些电影所展现的示威游行也是那个传统最容易唤起的,仍同它刚诞生之时一样鲜活,不管如何公式化地借用它用于文化和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能够在银幕上吸引我们的目光。确实,《印度尼西亚在召唤》这样一部没有什么预算、将相关的过去之事重组在一起的片子,在它制作的五十年后依然如此鲜活,是因为它从头到尾看起来都像一次长长的示威游行。”(吴沃,2010:p.345-355)我认为,正是这样一种有群众参与的游行或集会(群体聚集)构成了这一类纪录片的仪式。这样的仪式不但存在于伊文思的早期电影如《英雄之歌》、《博里纳奇矿区》,同时也存在于里芬斯塔尔的影片中,我国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新闻简报和纪录片中也充斥着这样的画面,正如吴沃在他的文章中所历数的,这样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群体聚集的形式同样也出现在那些关于流行音乐的纪录片中,如著名的《胡士托音乐节》。这同我们的理解并不矛盾,那些纪录片表现的本来就是梦幻、就是神话、就是革命(在流行音乐被主流意识排斥的时代),因此仪式的过程也是必不可少。
从某种意义上说,里芬斯塔尔影片的仪式段落导向的是政治的神话,但对于她的意识来说,更多的还是唯美的游戏。相对来说,里芬斯塔尔并不关心政治,也不属于探索电影语言的先锋派,她从未制作过纳粹战争的宣传片或实验电影。但是,对于形式美,她却有着强烈的表现欲。这可能同她学习和迷恋过现代舞有关。按照里芬斯塔尔的说法,她是为了求得纪录电影同新闻电影的不同而在自己的影片中大量使用移动拍摄和蒙太奇技巧。③这样一来,纪录片不再是相对客观的纪录,而成了主观情绪的一种宣泄。里芬斯塔尔直到晚年仍津津乐道于她所制作的那些有关纳粹党代会的影片,旗帜如何分散聚拢,人流如何左右运动,穿着皮靴的行列如何按照音乐的节奏在台阶上拾级而下……对于现实的、纳粹党的会议精神她并不是十分敏感,以至被问及如何处理和删减希特勒的讲话时,她认为首先是删除那些不好看的画面,如咳嗽、擤鼻涕等,其他亦无什么原则,她觉得希特勒讲来讲去都是讲的一个主题,因此对于剪接没有什么困难。而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则是,影片中留下了希特勒最为煽情的排比句和激情高涨的演说片段。也许里芬斯塔尔确实没有过于关注希特勒演说的内容,但是她却没有忽略任何能够给影片带来的打动观众情绪的细节。“煽情”可能是政治家在公众面前演说时最为根本的目的,里芬斯塔尔的影片尽管没有太多纳粹官方所希望的说教,但是她的唯美主义追求所带来的煽情效果,却正中希特勒的下怀。正因为有了希特勒的支持,里芬斯塔尔才成了当时世界上拍摄纪录片最为奢华的导演。④
里芬斯塔尔的《奥林匹亚》是一部艺术化纪录片的代表之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运动员跳水的段落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为了组合这样一个段落,里芬斯塔尔打乱了运动的正常过程,将所有运动员在空中滞留的镜头组接在了一起,成了一组并列的、非叙事的镜头段落。为了使运动员在空中稍纵即逝的动作更为舒展,她对运动的速度进行了处理,略微地放慢了速度。这样,一般的观众并不能意识到这是经过特技处理的镜头,但他们所看到的运动员在空中翻腾的时间已经被延长。不仅如此,为了节奏的变化,里芬斯塔尔甚至将某些镜头倒放,夹杂在正常的镜头之中。这样在视觉上起到了调剂节奏的作用,一般的观众同样不能觉察他们所看到的事实已经被人做了手脚。人们在欣赏电影《奥林匹亚》中的这个段落时,已经同奥运会、同比赛、同名次甚至同体育的本身没有了任何的关系;也就是说,影片所要表达的有关奥运会的内容,在这个片断中荡然无存。此时,里芬斯塔尔将奥运会变成了纯粹的形式美感的欣赏。这种大胆的、通过纪实材料的重新组合使纪实的意义只剩下一个表面的躯壳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回到了《柏林,一个大都市的交响曲》、《桥》、《雨》这样的影片所探索的电影形式语言的可能性,⑤这种可能性是将人类主观的节奏、美感或其他的各种感受,加之于他所不能控制的物理的影像,使之成为表现其主观感受的一个部分。里芬斯塔尔不同于伊文思(早期)和罗特曼的是,她将这样的语言组合进了一个纪实的系统之中,使之不再具有语言上的独立意义,成为了纪实转向表现、转向主观化的一种探索。从《奥林匹亚》我们可以看到,里芬斯塔尔正逐渐从神化仪式向着艺术“蜕化”。
与里芬斯塔尔不同的是,伊文思的作品未曾显示出这样一种“蜕化”的趋势。《博里纳奇矿区》是伊文思早期的代表作,这部影片结尾所展示的游行,使一场搬演的“戏剧”成为了真正的游行示威,并招致了警察的干涉。(伊文思,1980:p.81)当矿区的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自觉加入游行队伍之时,当他们为了争取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不是为了拍电影)而站出来的时候,艺术的殿堂为之轰然倒塌,因为艺术欣赏所需要的间离心态在观众那里已是荡然无存,他们看到的是生活直接而又具体的一面,他们可以为之激动、为之慨叹、为之愤怒等等,唯独不会去欣赏其中的韵律和节奏。影片中,人们的信仰同他们的行动结合在了一起,作为仪式来说,它不再是一种温文尔雅的诱导或者彬彬有礼的说教,而是如同身后猛掌直击,血液骤然沸腾。难怪托马斯·吴沃会说在几十年后观看这类影片依然觉得鲜活如初。伊文思的这一特点或多或少地保留到了日后的作品之中,在《愚公移山》系列的《大庆》、《上海柴油机厂》和《大渔岛》等影片里我们都能够看到仪式化的群体聚集,尽管这些聚集不再是游行示威。在托马斯·吴沃的笔下,《博里纳奇矿区》是一个开创了百年传统的开山之作,伊文思则是这一带有政治实用主义特点类型、也可以说是非艺术化类型纪录电影的开山鼻祖。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纪录片神话和仪式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纪录片和艺术的本身,进入了一个更为宽阔的社会的领域。
纪录片中的信仰:观念投射之下的事实
仪式必须导向某种信仰,不能同信仰相联系的仪式不成其为仪式。现实生活中的信仰不需要任何的推理和证实,而纪录片所表现的信仰则必须是事实,这是由纪录电影这样一种电影的样式所决定的。信仰是主观的,事实是客观的,两者的关系就如同舞台上的一束追光,纪录片所呈现给观众的是他们不可能看到的事实的发生现场,他们所看到的是为纪录片制作者的“追光”所照亮的事实。所谓“追光”也就是纪录片制作者的观念,不同的观念如同色彩各异、角度各异、强弱各异、组合各异、形态品质各异的“追光”,事实在不同观念的投射之下有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反之,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越不固定、越中立,观念的自主性就越弱,对事物的修饰成分也就越少,因此,事物呈现相对客观形态的可能性就越大。观念强势介入,有可能使事实趋向神话、谬误,或成为不可救药的谎言。
对里芬斯塔尔持否定态度的人首先注意到了她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政治观念的倾向,这种倾向具体表现在选择拍摄对象和素材时所出现的明显的政治含义。戴维·波德维尔和克里斯琴·汤普森在谈到里芬斯塔尔的《奥林匹亚》时说:“它的暗含涵义是突出纳粹的力量,这是相当容易解释的,特别是从现代观点回过头去看的话。虽然影片貌似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运动员,最着重的却是德国的获胜者和来自协约国意大利、日本的运动员。在《奥林匹亚》第一集中,有大量观众对希特勒的反应的镜头;在第二集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军国主义和卐字臂章频频出现使我们想到运动会背后的权力。”(戴维·波德维尔、克里斯琴·汤普森,1992:p.78)如果说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是无可避免地要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在第三帝国时代的影片中出现诸如此类的东西绝不会令人感到奇怪,要是没有倒是让人感到诧异了。克莱梅尔便试图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待这一问题,他在《德国纪录电影的双重困境》一文中说:“狂热的、颂诗般的空洞措辞已经布满了新现实的文化电影,这也是纳粹宣传中的典型的激情。……莱尼·里芬斯塔尔关于希特勒帝国党代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影片最终将激情、纪录的要求、‘事实’的说服力和具有节奏魅力、使人如醉如痴的画面组接合而为一,从而使美学的力度和真实荡然无存。纪录电影《信仰的胜利》(1933)、《意志的凯旋》(1934)和《奥林匹亚》(1938)同属一类。正如这些影片所达到的,走向贵族化的政治电影由于片面的美学批评导致了人道的毁灭,搬演的政治被翻译成了画面的搬演。”(克莱梅尔,2001:p.109)但是,让人稍存疑虑的是,如果在里芬斯塔尔的影片中“真实荡然无存”,那么她的影片的价值究竟何在?如果她的影片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岂不是全世界无数的观众都成了谣言的轻信者吗?事情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神话不同于谎言,神话中所蕴含的真实尚有被读解的可能。
从今天的立场来看,里芬斯塔尔的影片毫无疑问有着大量的纳粹意识形态,这些东西同样是历史的自然遗留,这与刻意宣传纳粹思想还是有所不同。神话在神话依稀尚存的时代往往被过于认真对待,无论里芬斯塔尔的主观意愿如何,人们还是认为她的影片在为纳粹做宣传,至少,在客观效果上起到了宣传纳粹的作用。因此,在二战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人们不能原谅她。里芬斯塔尔因此在十年时间里得不到相应的工作。
尽管伊文思站在了纳粹的对立面,但他所碰到的问题同里芬斯塔尔颇为相似。不同之处仅在于里芬斯塔尔在二战之后所受到的批评,伊文思从踏上制作纪录电影的道路开始便已经体会到了。从拍摄《博里纳奇矿区》开始,他对工人的同情和左倾的观念便很难得到西方社会官方和主流社会的认同,他同苏联的密切关系使他在当时几乎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的宣传者。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纪录电影史和评论都将他描绘成一个革命者:
“从伊文思拍片生涯开始,他就深信电影离不开政治。多年以来他相信电影工作者的职责便是要去‘直接(参与)世界最根本的问题’,因此他到许多处于政治动乱或发生革命的国家:中国、俄国、印尼、古巴及越南。”(Barsam,1996:p.213)
“一个站在世界革命前沿的电影工作者。”(Kreimeier,1976:p.1)
“伊文思是一个由于参与政治而浪费自己才华的艺术家。”(吴沃,1999:p.290)
“伊文思是一个‘飞翔的荷兰人’,哪里发生革命他就到那里去,支援各国人民的进步活动,宣传进步思想。”(夏衍,1979:p.22)
“伊文思同志从1928年就从事电影工作,五十余年来,他走遍世界各地,哪里的人民进行正义斗争,他就出现在那里。伊文思同志用他的战斗武器——电影摄影机,拍摄了世界五大洲人民创造的史迹,纪录了世界各国的革命风云,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貌。”(王阑西,1979:p.27)
其实,不论伊文思还是里芬斯塔尔的政治倾向如何,对于政治他们始终是门外汉,特别是伊文思,当他跑到东南亚或南美洲拍片的时候,他对那里的政治情况和一般的环境都是相当陌生的,以至于有时甚至会拍出纯粹猎奇性质的影片,如《愚公移山》中的《京剧改革》、《手工艺人》和《北京杂技团训练》,或在形式上进行实验的影片,如在老挝拍摄的《人民和枪》等。(单万里,2001:p.291)
尽管伊文思在任何场合都不曾表示放弃自己的理想,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对于“革命”来说,他是个外行。他对于革命的表现,尽管有许多个人情感的倾向,但也有他的观察和思考,不是一味的吹捧或盲目宣传。1979年,在一次记者的采访中他说:“不错,我一生有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从来也不是为了掩盖某种东西或者欺骗人。”(德瓦利厄,1980:p.19)如果我们相信他所说的,就能在他的作品和宣传片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对于某一事物,人们可以无知,可以幼稚,但只要不将自己的无知和幼稚当成事物原本的面貌,不要自信到闭目塞听的地步,他就会表现出某些观察和思考。因为摄影机的视听记录功能只有在人们强力干预(故意歪曲)的情况下才会“说谎”,其自身的物理、化学性质是对外部世界机械反映的一种保证。伊文思也曾幼稚过,也曾相信过“大跃进”这种荒唐的事物,他在五十年代一篇名为《我是怎样摄制“四万万人民”的》文章中说:“就在我回忆“四万万人民”的拍摄经过,撰写这篇文章的前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炼出了第一炉钢,我高兴地看到了这一炉钢。我也知道,目前,全中国人民到处都在炼钢,而这种全民炼钢的做法使我很容易地联想到中国人民的智慧、力量和中国人民最美好的未来,也使我联想到:当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后,他的力量是什么也不能阻挡的。1958年10月15日于北京。”(伊文思,1958:p.70)显然,由新闻电影制片厂炼出的“钢”,是否具有金属意义上的价值非常值得怀疑,但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大跃进时代的神话因此而成为“现实”。随着时代的推移,在20世纪六十年代曾相信共产主义的西方人,伴随着年龄的成长,地位的改变,大多改弦易辙,背离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唯有伊文思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但此时的他已经褪去了幼稚的热情,多了几分对事物的思考。当他在1979年被问及还打算去哪里的时候,他答道:“目前还不知道。我花了许多时间研究厄立特里亚⑦问题。是不是到那里去?那里是不是我的岗位?我还不能肯定事变的因素在什么地方。我相信正义的、革命的事业,但是现在事情不如我年轻的时候那样泾渭分明。那时候,西班牙是对的,别人不对,越南对的,美国人不对,事情没有两重性。拍一部关于安哥拉的影片,这很好,但是要让那边的人去拍,要帮助那边的电影工作者去表达。事情很复杂,尤其你是不知趣的老殖民主义者。要纵观种族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懂的。”(德瓦利厄,1980:p.14)由此可见,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伊文思从五十年代的狂热逐步走向了七十年代的谨慎,尽管他并没有对自己的理想产生怀疑。
伊文思这种审慎的影片制作态度往往被他理想主义的言论所掩盖,这特别是在冷战盛行的时代,许多人谈到共产主义往往如同谈虎而色变。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注意到了伊文思在拍摄《愚公移山》时的思考,考根在他为《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录》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道:“在《愚公移山》中,伊文思毫不掩饰怀疑的成分,以社会为代表的主流同跟不上集体的犹豫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几代人之间的矛盾,都作为题材而加以发挥。”(考根,1980:p.4)用一种简单化的、非左即右的思维来看待伊文思的影片,特别是对待像《愚公移山》这样的鸿篇巨制是非常不合适的。伊文思拍摄《愚公移山》时的态度,或者说指导思想,表现了他对客观事物的尊重,尽管我们不能从他的言论中得出他的作品一定不存在宣传的结论,但却可以从中发现,伊文思的视点往往会不自觉地倾向于观察。他说:“我同玛瑟琳·罗丽丹拍的影片,表现中国人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个各不相同的,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是存在个性的。可能这一点还不够,但是我当时无法进一步深入了,至于中国的政治斗争,除了中国人是无法谈的。我从来不敢说关于中国问题我都说了,都懂了。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我所表现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表现过的。”(德瓦利厄,1980:p.19)按照一般的推理,当一个人对某一事物并不十分了解的时候,即便他想进行宣传,往往也只能停留在表面的观察。那种刻意的取舍、那种故意的忽略和强调,那种有的放矢的煽情,我们在《愚公移山》中是很难找到的。
如果说伊文思的影片没有发掘出中国人心灵深处对文化革命的反感而给西方人造成了错误的印象,那责任应该不全在伊文思。首先,人们不可能要求伊文思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他并不是一位政治家,甚至连业余的都算不上。而具有顽固冷战立场的西方媒体所表述的相反意见,往往也是不可信的、与事实有出入的宣传。其次,经历过中国文化革命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试图造就各种理想的时代:无差别的收入、无差别的社会地位、统一的意识形态等等,伊文思记录的正是文化革命最一般的现象,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点同里芬斯塔尔有所不同,里芬斯塔尔关注的是重大事件。不过,他们都不属于政治上特别成熟和敏感的人,相反,他们身上更多的是艺术家和理想主义者的浪漫气质,当他们以自己的观念真诚地来“投射”(把握)事实的时候,事实无可奈何地在某种程度上被演绎成了神话。在拍摄完成《愚公移山》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伊文思没有得到相应的工作。这是因为中国在八十年代彻底背离了文化革命的原则,《愚公移山》因此而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从真实的纪录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神话”。
今天,人们尽管可以批评伊文思和里芬斯塔尔在政治上的幼稚,以及他们将这种幼稚带到了他们的作品之中。但如果这种幼稚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而是属于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那么,这一幼稚之中往往也就包含着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可悲的幼稚,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真实。今天,不论我们研究伊文思还是里芬斯塔尔的作品,都是试图通过对“神话”的读解了解当时社会的全貌,就像人们今天研究那些真正的神话传说,以图了解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一样,其荒诞不经的外表往往蕴含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至于那个神化了的故事本身,人们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不应该以诸如此类的喜好而轻言作品的优劣。
注释:
①托玛斯·吴沃曾在自己的文章《尤里斯·伊文思和他的忠诚纪录片遗产》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曾讨论过不论右派或是左派,可能的宣传暗示就是宣传,而且已经解释过右派纪录片相当于左派激进纪录片的特色。(后面这个说法看似荒谬,实际上是经得起考验的)”(吴沃,2010:p 351)
②梁启超在《神话史、宗教史及其他》一文中谈到《尚书》中的离奇故事时说:“那些反风起禾的故事,当时人当然相信,如不相信,必不记下来。我们虽不必相信历史上真有这类事,但当时社会心理确是如此。”(梁启超,1994:p.94)
③参见Ray Mueller的纪录片:《里芬斯塔尔——强力的图像》。
④参见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丁伟祥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
⑤法国电影史学家、理论家乔治·萨杜尔早有类似的看法,他在《电影艺术史》一书中说:“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这部影片里,曾充分利用了华尔特·罗特曼的理论和手法。”(萨杜尔,1957:p.215)
⑥参见拙著《纪录片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五章。
⑦译注:埃塞俄比亚省名。
标签:神话论文; 愚公移山论文; 意志的胜利论文; 伊文思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纪录片论文; 奥林匹亚论文; 德国电影论文; 纪录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