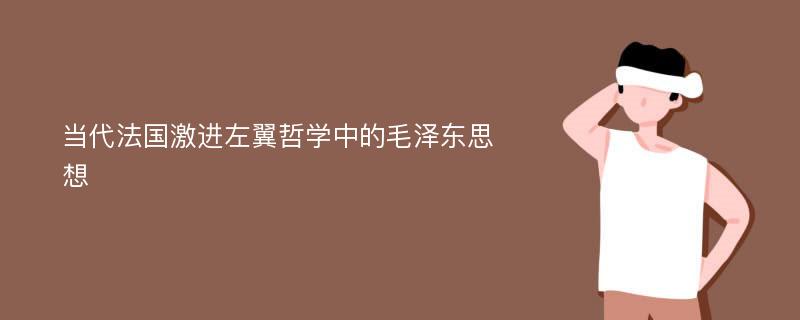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哲学文本在法国得到翻译和出版,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毛泽东思想视为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重要思想资源。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法国激进左翼实践的发展,以及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哲学家对毛泽东辩证哲学的转述,毛泽东思想成为法国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争取自由和民主的理论武器。然而,由于毛泽东思想在当代法国政治哲学中始终被选择性地塑造为既与资本主义政治霸权对立,又与一切形式国家机器对立的激进思潮,其完整的哲学方法论并没有真正得到呈现,其所揭示的矛盾不平衡发展的客观层面也并未得到重视。随着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对历史和政治的重构,毛泽东思想作为法国激进左翼的批判符号的意义更为明显。
【关键词】毛泽东;法国;辩证法;阿尔都塞
毛泽东思想(La pensée Mao Zedong)也许在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主义的语境中是极为突兀和不合时宜的,似乎只属于那个遥远的、与当代断裂的时空。但在20世纪至今的法国政治哲学中,毛泽东思想或毛主义始终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路标,指向对资本主义霸权的非正义性的揭露,鼓舞着法国左翼学者持续表达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政治秩序的不满,并坚持以唯物史观对各种抽象伦理原则发起批判。在当代法国政治哲学中,毛泽东是一个多元的形象,并非只是来自东方和异质性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或哲学方法论,而是指代了不同历史时期法国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特定目标。在至今仍然如雷贯耳的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家名字中,绝大多数都与毛泽东思想产生过(或仍在)密切联系,他们或是通过学术研究宣传过毛泽东哲学,或是亲自参与过毛主义组织,或是为毛泽东旗帜下的群众反抗运动积极奔走。例如萨特曾经是“革命万岁派”(Vive la révolution)等左翼机构的参与者,不断用他的世界性威望为毛主义期刊的编辑们提供支持,甚至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与妻子波伏娃一起上街散发进步报刊[注][美]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张金鹏、陈硕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3页。。又如,阿尔都塞等直白地表明自己是毛主义身份的哲学家——作为早期毛主义组织UJC-ML的理论启发者,曾经匿名为“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nion de la Jeunesse Communiste Marxiste-Léniniste)的机关刊物《马克思列宁主义札记》撰写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该组织的多位领导人(尤其是罗伯特·兰阿赫)大多是阿尔都塞的学生或朋友[注][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59—260页。。阿尔都塞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科学)的辩护,使得结构主义不再被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等概念所困扰,也使得大量进步学生“涌向”阿尔都塞,包括乌尔姆俱乐部(cercle d’Ulm)的学生[注][美]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第325页。。再如,福柯等在毛主义组织外围对毛泽东思想提供支持的学者。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法国进步运动对福柯的影响体现在,法国毛主义政治犯对拘留条件、政治和一般法律的绝食抗议,使得福柯开始关注监狱问题,并且最终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和纳凯(Pierre Vidal-Naquet)一起成立了“监狱信息组织”(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注]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1954-1988, II, Gallimard, Paris, 1994, p.24.。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福柯对左翼哲学家的支持和保护,他在文森大学任哲学系主任时所聘任的毛主义激进分子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是至今仍活跃于欧洲的左翼“四大好汉”。其中,巴迪欧的毛主义政治实践经验极为丰富,在1969年脱离社会党后,与出走“无产阶级左派”的娜塔莎·米歇尔(Natacha Michel)、席尔万·拉撒路(Sylvain Lazarus) 等人成立了毛主义组织马列主义共产同盟(l’Union des communistes de France marxiste-léniniste)。他坦言,哲学在其政治主体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萨特是他的第一个路标(balise),但是他的政治主体性是与现实事件相关的(如阿尔及利亚战争、五月风暴、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事件对他所要坚持的“真”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准确地说,巴迪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在后1968时代对毛主义的复归[注]Alain 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hilo éditions, Paris, 2014, p.21.。而与他同一时代的朗西埃,虽然方法论未必一致,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却是其半个世纪来最为鲜明的政治哲学特征。
一、阿尔都塞:《矛盾论》的结构主义嫁接
毛泽东思想首先引起法国政治哲学家关注的,并非是某种与中国传统相关的东方特质,而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一方面,这与毛泽东带给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初形象有关。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毛泽东哲学文本的翻译出版[注]1952年,《矛盾论》首次被翻译成法文,并刊登在法共官方刊物《共产主义手册》。,使得毛泽东思想摆脱了某种异质的东方符号(例如孔子之于启蒙政治哲人),成为能够直接与现代政治实践衔接的理论。对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毛泽东是“新列宁”,是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时是一位天才的政治战略家[注][法]路易·阿尔都塞:《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1955-1972年高等师范学校讲义》,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24页。。另一方面,这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需求有关。在理论上,战后受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学者,不论是为了法共的政治宣传,还是为了捍卫唯物主义,都急于对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和《巴黎手稿》译介以来的黑格尔主义进行清算。而毛泽东的矛盾论正好符合这一理论需求,能够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遗产的断裂”[注]同上,中文版序第20页。。在实践上,在与戴高乐政府对抗中处于弱势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理论与策略、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而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6页。正好符合这一实践需求。如果说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科耶夫和伊波利特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让法国知识分子开始辩证地、而非实证主义地看待政治现象,那么毛泽东的辩证哲学则促使法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方法论到实践指向都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在熟练引用《矛盾论》的哲学家中,阿尔都塞和巴迪欧较为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引用的意图和落脚点。
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负荆请罪》一文,和平常学的课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请大家睁大眼睛,去发现、寻找。
首先,《矛盾论》介入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激励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知识界,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不仅是一个学术之争,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是生死攸关的”的重大问题[注][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81页。。这是因为原先那种黑格尔主义的解读不仅会使得人臣服于冷战后西欧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理性,而且会使人囿于历史规律的教条而畏惧投身于可能“尚未成熟”的革命实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阿尔都塞借用毛泽东对矛盾的不平衡性的论述,一方面试图说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结构的改造而非“颠倒”,另一方面试图打破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等唯心主义教条,以启发马克思主义者去发现矛盾运动的多元决定的本质。当然,这种借用要在远离中国上万公里的资本主义的法国产生影响,首先需要对毛泽东的矛盾理论进行有效的澄清和辩护。阿尔都塞尤为关注矛盾的不平衡的发展(développement inégal)。在他看来,这是列宁和毛泽东的原创性概念,正确地解释了社会形成过程中多元决定的特征,并展现了历史真实(historique réel)的结构中共存着前进、后退、生存、发展的不平衡[注]Louis Althusser, Étienne Balibar, Roger Establet, Pierre Macherey, Jacques Rancière, Lire Le Capital,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2014, p.29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着的各种(发展的、生存的、意识的)不平衡,实际上说明了没有一个矛盾可以单独地发展,在不同时空的矛盾不平衡运动促成了多元的社会发展方式[注]Ibid., p.291.。他甚至认为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哲学笔记》和《矛盾论》)已经“在形式上已经相当完善”地解答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别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特性,以至于当代法国学者只要进一步思考、追根究源和加以发挥就可以了[注][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75页。。当然,时人对外来的毛泽东辩证哲学的责难对阿尔都塞形成挑战。针对毛泽东忽视一般矛盾运动的批评,阿尔都塞的辩护是:毛泽东所研究的对象并非是“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而是“包括许许多多的矛盾”的整个社会,同时革命实践的情势和时间也不允许脱离具体社会的抽象研究[注]同上,第188页。。针对一些人对“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原则的黑格尔主义误判——似乎毛泽东所说的普遍性“需要有一种附加普遍性才能够产生出特殊性”,阿尔都塞的辩护是:毛泽东所说的“特殊性普遍地属于矛盾的本质性”并非是普遍性的前提,而是针对作为普遍性抽象化或产生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欲念,强迫其回到具有科学特殊性的普遍性地位[注]同上,第176页。。阿尔都塞甚至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之间的断裂,不断试图将毛泽东的矛盾特殊性概念嫁接到社会作为结构的复杂统一体的论述,并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毛泽东1937年的论文中已经再也找不到黑格尔范畴的“丝毫痕迹”了[注]同上,第193—194页。。
在结构主义兴起的20世纪中期,阿尔都塞的毛主义辩证法及其历史科学几乎逼退了繁荣半个世纪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他对《矛盾论》基本概念的澄清和辩护最终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这主要体现为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和理论辩证关系的理解终于摆脱了第二国际以来的教条特征,离弃了实证主义传统下的实践-理论的二元理解。毛泽东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在阿尔都塞之前,这也许并不容易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广泛地接受。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某种“异质性”的理论,始终以德国哲学、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形象而成为某种“洋教条”;另一方面,从笛卡尔直至拉美特利、孔德、涂尔干,长达3个世纪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传统,使得法国唯物主义者始终处于一种理论“冒险”中,即谋求通过激进地运用特定理论来解决实践中复杂的问题。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一种辩证理解的匮乏,既无法辩证地认识实践-理论的矛盾关系,也无法辩证地对待作为实践对象的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在阿尔都塞看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从盖德主义者(guesdistes)到战后法共始终遭遇政治实践的失败,并非由于理论不具有真理性,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正视“具体的现实”和“当时的历史现实”。当“所有的矛盾都受不平衡法则的制约”,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注][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6页。。中国共产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历史出现断裂的“有利时机”,如果能够认识到矛盾的特殊性,把握到矛盾的主要方面,亦即掌握整体结构各环节间相互依存条件的复杂关系,就能够在落后国家或弱势地位实现革命的胜利[注][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02页。。当然,这种“条件”和矛盾特殊性的概念并不能满足具有理论洁癖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仅认为毛泽东和列宁的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论不过是权宜之计,更认为没有必要去解决这些离理论和概念十分遥远的“极端经验主义的问题”。阿尔都塞则认为必须“花九牛二虎之力去阐述一个早已经被认识了的真理”。正如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真理虽然在毛泽东哲学文本中已经十分清晰,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已经被证实,但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其自身的实践中承认这一真理并不等于认识了这个真理(上升成为理论)[注]同上,第157—159页。。结合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这种“与辩证唯物主义浑成一体的唯物辩证法”,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作为平衡论或均衡论的各种教条主义。作为一种以《矛盾论》为奥援的哲学方法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政治哲学通过矛盾主次方面的转化,赋予“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无产阶级左派”向帝国主义政权进攻的信心和勇气,并通过主次矛盾的关系部分地教会了法国进步学生和工人在实践中把握关键问题。在十月革命后,不断被动地接受第三国际理论指导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有在阿尔都塞及其毛主义辩证结构之后,才真正开始在本土政治实践中寻求法国理论的努力。各种毛主义政治组织在“五月风暴”前后震撼西方世界的理论和实践,初次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论,已经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327页。。
二、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重构政治概念的参照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片面选择。在20世纪早期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的文本或是被选择性地用来向柏格森主义和笛卡尔主义开火,或是被选择性地用来建构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哲学没有完整地在20世纪初的法国政治实践中出场,甚至直到20世纪中期都没有完整的马克思著作法文译本。从保罗·尼赞(Paul Nizan)、乔治·波利策(Georges Politzer)、诺伯特·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n)、萨特直到当代激进左翼的理论线索中,法国学者对本国和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警惕,最终使得他们一直没有正视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巴迪欧虽然肯定马克思所揭示的阶级社会政治程序的真理,并最终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描述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是它的一般辩证法并不正确。经典马克思主义最终将政治还原为赘余项(国家机器),而主张赘余项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注][法]阿兰·巴迪欧:《存在与事件》,第139页。。毛泽东思想在法国哲学中更为明显地遭到“切割”“挑选”和“重新包装”。一方面,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从发展脉络上并不具有马克思那样的首创性,而是被放置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乃至斯大林这一序列的延续之中。例如,卢西恩·比安科(Lucien Bianco)就认为毛泽东主义是列宁主义的一个变体(une variété),尤其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ligne de masse)和民主集中制(centralisme démocratique)的理论。尽管比安科承认毛泽东主义不是对列宁主义的复制(une copie),但也认为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中看到永久革命(la révolution permanente)的托洛茨基的影子[注]Lucien Bianco, Essai de définition du maoïsm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1979,Vol.34.。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从来没有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法国政治哲学中成为一种准则和方向,而是一直作为法国激进左翼政治的补充性思想资源。巴迪欧曾强调:“我从没有在过去或今天,成为马克思的盲目门徒,我甚至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于毛泽东,我对他的评价是选择性的(sélective),根据政治情势和我的知识兴趣。”[注]Alain 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73.在某种意义上,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矛盾不平衡性”的借用,将合理性赋予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选择性”理解。而罗兰·巴特的“试衣服”的比喻更为生动地解释了法国政治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形象:
首先,政治的定义。以巴迪欧为例,当代法国激进左翼既承接了《共产党宣言》,又融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叙事。作为1848年革命的指导纲领,《共产党宣言》中的政治(politisch)作为一个定语,所揭示的历史真理几乎被19世纪末以来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每一个阶段的斗争实践中。“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页。成为一个原则性的律令,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将革命政治首先定义为阶级斗争(Klassenkampf),而非那种王侯将相和资产阶级用以维持秩序的统治技艺。因此,不难理解巴迪欧所定义的政治是那种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相对立的阶级斗争状态,亦即国家和党派的那种“政治”只能产生“反政治的主体”。与之相反,正如巴迪欧“在毛主义中所发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念绝不能被付诸于国家机器(l’appareil d’état),而是要通过独立的群众运动,甚至区别于党的群众组织,“造反”也因此成为一种必要[注]Alain 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52.。他公开表示自己所支持的共产主义既不是某种停留于哲学文本的理念,也不是被官僚化的党派所代表的共产主义,即那种严重依赖于权力的苏联的共产主义,而是体现在法国变体(variantes)的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注]Ibid., p.18.。他甚至认为“列宁晚年对国家的长期存在感到失望”,而毛泽东则更加冷静和大胆,使得真正的政治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如火如荼地达到巅峰[注][法]阿兰·巴迪欧:《存在与事件》,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0页。。除了用法国化的激进毛主义强化了阶级政治的概念,对于巴迪欧而言,米利安·达隆妮、汉娜·阿伦特或其他自由主义传统下的“政治哲学家们”提供的通过投票/计数带来自由的方案,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政治”挑战。因为从启蒙时代直至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伦理原则,不过是完成了国家机器运转所需要的“政治幻想”(politischen Illusionen)[注][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0页。。作为巴迪欧多年“战友”的朗西埃则更为直接地向代议制民主发起了攻击,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症候,揭示民主政治的本质不过是统治阶级向人民索取的虚伪的赞同[注][法]雅克·朗西埃:《对民主之恨》,李磊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6年,第57页。。这些观点既能够回溯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也能够在毛泽东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本中找到极为相似的论述。
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双眼,我想到了阅读书的欲望。我想象了一个画面:一个知识分子决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开始为自己选择马克思主义。哪一种马克思主义将成为主流呢?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巴枯宁?毛泽东?还是波尔迪加(Bordiga)或者别的什么人?他走进图书馆,阅读所有的书,就像一个人不停地试衣服,选择最适合(convient)他的马克思主义,准备挑选最符合自己体型和经济状况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来开展关于真理的演说。[注]Roland Barthes. 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Seuil, Paris, 1980, p.159.
随着“五月风暴”的精英化蜕变和最终失败[注]“五月风暴”的“精英化”既体现在参与者的构成,又表现为抗争运动的场所。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五月风暴”的重要性原本应该体现在生产场所,最终却局限于被占领的大学或剧场等“文化庙宇”。(See Keith A. Reader, Khursheed Wadia, The May 1968 Events in France: Reproduc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Macmillan Press, London, 1993, p.4.),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的“火堆”在法国政治哲学中逐渐冷却。虽然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中叶法国无产阶级运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这毕竟是法国的具体客观条件下发生的政治事件。法国无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运用,最终必然遭遇客观历史所造成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局限性。“五月风暴”和法国政治哲学中的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大多数时候都“与巴枯宁及其支持者”存在着历史共性,服务于实现直接民主、否定国家和阶级社会的纯粹自由的意识形态[注]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 by Ken Knabb, Bureau of Public Secrets, Berkeley, 2014, p.43.。事实上,发展至今的法国政治哲学中的毛主义因素,随着巴迪欧和朗西埃对社会舆论的积极介入,仍然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继承自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毛主义的理论问题得到解决。具体而言,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对毛泽东思想的转述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三、从文本到现实:问题与未来挑战
其次,在实践中澄清和检验已有的政治哲学概念。毛泽东在《矛盾论》指出:“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疑为人)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这种被20世纪前结构主义思潮指认为“反映论”的认识论,被结构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视而唤醒。尤其在“五月风暴”作为起点而非终点的法国工人运动实践中,不断失败却又坚持反抗的斗争实践,启发了原先对权利、国家、阶级和秩序等政治哲学概念知之甚少的工人,让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也进一步走出概念的迷雾,在实践所带来的客观矛盾中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内在结构,从而更新了用以指导实践的理论和概念。这一过程较为典型地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初福柯与一些毛主义政治组织成员如邦尼·莱维和卡罗尔(K.S.Karol)的对话中[注]K.S. Karol的真名是Karol Kewes。。在对话中,福柯代表了进步“政治哲人”对毛主义组织的同情,以及对政治哲学概念之纯洁度的坚持,而莱维和卡罗尔代表了“哲人政治”在毛主义实践中对政治哲学概念的反思。在1972年2月5日的对话中,福柯、德勒兹和化名为维克多(Victor)的邦尼就人民正义展开辩论[注]由于无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étarienne)在1972年已经成为非法组织,因此福柯用笔名来保护对话者,Victor即Benny Lévy,他当时是毛主义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但在对话中伪装成萨特、德勒兹和André Glucksmann的秘书。(See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1954-1988, II, p.340. )。福柯根据国家政治和法权现象的历史特征,质疑毛主义者所要建立的“人民法庭”是国家机器的脆弱胚胎(l’embryon)的萌芽。因为一旦具备国家机器特征的法权秩序得到建立,不论其出发点是否超脱于阶级,都可能造成潜在的阶级压迫。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法庭是否能够“中立于人民与敌人”,因此能够区分真假、罪恶与无辜、正义与非正义?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反对人民正义的方式吗?作为人民正义之形式的法庭在历史上(例如资产阶级历史),难道不是最终都被扭曲了吗?[注]Ibid., p.341.邦尼并没有用概念来回击福柯,而是以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事例进行澄清。他认为举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不恰当的,因为真正的人民法院只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出现过。在中国革命中,最初出现的是群众的意识形态革命。在起义的农村,农民坚持反抗敌人,并通过处决专制者来回应数个世纪的折磨。在革命中人民处决敌人的案例不断增加,是被人民公认为是人民正义的实施。这说明农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有进步的事情都在农村快速发展。当革命政党成立红军(Armée rouge)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出场的不再只是起义群众和敌人,而是敌人、群众和作为群众的联合的红军。自此,人民正义的实施就被红军所支持和规定,复仇行为就需要通过司法权(juridictions),这种起点是人民正义直接行为的权利,与过去任何司法都是不同的[注]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1954-1988, II, p.341.。在1972年的另一场辩论中,福柯对毛泽东判断阶级立场的词句提出质疑,因为毛泽东所给出的判断左右的标准“总体上太模糊了”(en général très ambigus)。卡罗尔则更为巧妙地解读了这种模糊性,认为它是为了抓住“矛盾不平衡性”的内在意图。他认为毛泽东及其词句的确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权威息息相关,但毛泽东并不能直接干预革命,他只希望让群众自己发言。尤其在革命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即“四旧”(les quatre vieilles)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根深蒂固的,毛泽东的政治指示的“模糊性”赋予革命群众自觉性和自主性的空间[注]Sur La Seconde Révolution chinoise, 1re partie, Libération, No.157, 31 janvier 1974, p.10.。总之,毛泽东的辩证哲学和革命实践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构政治哲学核心概念提供了充沛的资源,但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收获与之对等的、足以撼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力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思想被法国毛主义者转化为某种单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非变革政治经济的革命实践导向。
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辩证哲学的方法论嫁接,在政治哲学领域最终体现为“读《资本论》”小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和历史的重新理解。虽然朗西埃等毛主义哲学家最终与阿尔都塞决裂,但是阿尔都塞用以定义“症候阅读”的辩证方法最终在当代法国激进左翼政治哲学中得到继承。对于文本,“症候阅读”是一种超越性的“远征”,它会使得文本中的问题得以澄清并传递到其它文本和症候。这要求读者在解读当代问题和《资本论》的时候,结合毛泽东哲学文本和马克思的1857序言所提供方法论的文本(texte méthodologique)[注]Louis Althusser, Étienne Balibar, Roger Establet, Pierre Macherey, Jacques Rancière, Lire Le Capital, p.30.。对于实践,“症候阅读”所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存在(existence pratique),即存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实践中的个人实践状态,存在于工人运动历史的政治经济实践。这将使得文本中不可见的问题变得可视化。正如在能动的政治(politique active)中所展现的那样——列宁通过革命实践中的沉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具体理论形态。而毛泽东的《矛盾论》进一步发挥了这一原则(ce principe),典型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政治实践中的反映[注]Ibid., pp.28-29.。“症候阅读”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的论述,但在法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情势下很好地推广和宣传了毛泽东的研究(实践)方法——“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这使得阿尔都塞之后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衔接起了文本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实践催生的新理论,并产生了延续至今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概念的激进重构。
如图1所示,路由开销随着节点停留时间的延长而降低,这是因为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不再频繁所致。图2表明网络整体的端到端时延随节点停留时间的增加而降低。图3表明分组投递率随节点停留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如图4所示,路由发现频率随节点停留时间的增加而降低。
本项目还拟建3个大型公园以及滨河绿廊,将生态和景观融入城市之中,发挥滨水空间的独特魅力,塑造城市艺术生活水岸,增强人与空间的互动。整个景观绿地面积达到约2.65×105m2,这些公园中设置了过滤带、生物洼地、雨水花园等海绵城市措施。
第二,对意识形态革命的过度重视。从政治组织、口号和运动目标看,“五月风暴”中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将想象中的文化大革命复制到法国。他们将文化大革命的反官僚主义转述为对包括法国共产党在内的法国国家机器、政党和权力秩序的颠覆,将群众运动转述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带领下的占领行动。但是,正如巴里巴尔批判阿尔都塞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想象,法国政治哲学中的毛泽东思想“很可能过于依赖一些在西方流传的神话,其中一些变形和过分的东西必须得到纠正”[注][法]路易·阿尔都塞:《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1955-1972年高等师范学校讲义》,第17页。。这种想象体现为对无产阶级实践的狭隘化,即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解放。例如,巴迪欧认为“在20世纪的所有冒险中,最为进步(le plus avancé)和具有希望的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注]Alain Badiou, Quel communisme? Entretien avec Peter Engelmann, Bayard, Paris, 2015, p.8.,同时坦诚自己“并不是对毛泽东的一切都知晓”。然而,尽管他认为自己认识到新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苏联“有着不可争辩的延续性”,二者官僚阶级所掌握的过剩权力(pouvoir démesuré)有着一定的共性,但是却对这些方面“没有关注”,因为他“主要感兴趣的是文化大革命”[注]Alain 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54.。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选择性的言说。这种既承认现实制度缺陷又坚持片面想象的悖论,在其他20世纪法国左翼政治中并不鲜见。例如,波伏娃主编的《女性主义问题》中的观点:艾伦·廷克(Irene Tinker)认为中国官方媒体热情宣传社会平等,但是在军队和政府首脑中几乎都是男性,甚至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女性——江青也只能在权力外围(périphérie)进行工作。那些访问过中国的人都被中国政府争取男女平等的努力而震撼,但那些到了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发现其他国家的男性根本无法理解女性应该被平等对待[注]Questions féministes, Sept.79, No.6, Editions Tierce, Paris, 1979, p.84.。又如,米歇尔·洛依在1974年10月访问中国之后,认为知识分子和妇女的问题是批判儒家妇女观的关键[注]Ibid., pp.40-43.。廷克和洛依的看法的确有现实参照,但仅仅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解放层面,并没有看到中国女性解放的经济基础,即对旧社会土地所有权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这两方面的问题虽然在20世纪中期可能只是体现为法国左派的路线之争,但在冷战结束后迅速发酵为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挑战。首先,新自由主义“保守革命”掀起“历史终结”的挑战。巴迪欧指出,由革命政治所开启的“20世纪”十分短暂,以列宁的1917年(实际上这可以更为久远地追溯到罗伯斯庇尔的1793年)为开端,在斯大林的1937年达到顶峰,而在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本质上走向结束[注]Alain Badiou, Le Siècle,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2005, p.12.。这个世纪之所在政治意义上仅仅持续了60余年,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几乎重构了关于政治的定义,代议制民主及其统计学“真理”成为终结历史的元叙事,而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给予人类的政治可能性被湮没在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喧哗中。一些对历史知之甚少的人轻信了新自由主义编写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历史,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法西斯的同谋。对此,巴迪欧试图为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运动进行辩护。例如,他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虽然保持了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形式,但毛泽东的确试图通过领导造反来抗击官僚化的不平等,这与重建的“总体主义”(totalité)是相去甚远的。这种所谓的“极权主义”实际上只是现代社会的强制分工(violentes divisions)的产物。因为共产主义的哲学完全是辩证的,依赖于矛盾的运动,而纳粹则固定于一种人类的“纯正”本质的生物根据。因此将历史上的共产主义与任何极权主义的宗教等同起来是高度悖论的,在本质上也是不合法的(infondé)[注]Alain 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47.。这个危机在国内学术界被标示为“历史虚无主义”。在从来没有无产阶级实行有效执政和治理的法国,这个危机不仅更为猛烈,而且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广。正如朗西埃所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历史”将以统计学的方式被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标示出来:对于那些满足于资本主义总体秩序(l’ordre général)的人而言,没有什么特别事件是值得研究的。[注]Jacques Rancière, Les noms de l’histoire: Essai de poétique du savoir,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92, pp.13-14.
大力治理农村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监管。变“定期整治”为“时时严打”“处处严打”,全面围堵农村市场问题食品。集中精力做好对农村集体聚餐的风险防控,加大监督检查和指导,严格落实自办宴席日报告制度,全县农村自办宴席备案率达到95%以上,有效降低了农村群体性食品安全事故隐患。
当代法国和西欧社会对于阶级政治的冷漠,或许体现了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对民众的意识形态重构,但其本质体现了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实践和理论的局限。也许“五月风暴”中的毛主义者仍然没有走出启蒙时代对中国和其他异质性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想象,在追求激进概念的政治行动中,试图实现某种巴特意义上的新词(sinité)[注]法国毛主义所坚持的并非是作为整体的毛泽东思想,更没有就此创造出与中国革命等量齐观的事件。那些通过片面想象的法国毛主义的政治术语,是将毛泽东的哲学概念嫁接到法国的现实政治运动,构成关于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当代神话。“造反有理”“群众运动”或“破四旧”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旧词新意”。这些术语在法国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巴特所说的sinité,例如将中国与法国小资产阶级这两类名称拼接起来,二者构成“铃铛花、人力车和鸦片室”的奇怪组合,因而并不是现有词汇能够描述的。(See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57, p.193.),而非真正具有经济基础的新社会。然而,值得肯定的是,法国政治哲学中具有多重面向的毛泽东思想,虽然具有各种内在冲突和断裂(例如巴迪欧/朗西埃,朗西埃/阿尔都塞,阿尔都塞/萨特),但至今仍然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批判的政治观点的重要依据。毛泽东思想在当代法国政治思潮中的先锋地位,不仅在于其反对资本主义政治霸权的本质要求,更在于其对一切已有的无产阶级政治的局限性的批判。正如巴迪欧所指出的,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反对政治的取消”,“他在接见红卫兵时,虽然被人们视为政治领袖,但是却告诉人民:‘将你自己和国家事务融合起来’”。这里,不仅是一种对斯大林遗产相反的姿态(un geste)[注]Alain Badiou, Marcel Gauchet, Que faire?, p.55.,更启发当代人去反思自我标榜为“自由”的代议制民主。在当代法国政治哲学中,朗西埃对代议制民主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巴迪欧的“元政治学”的建构,都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人民权利的洞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危机作为的矛盾的一方面,尽管在最近40年来呈现出霸权的表征,但始终无法遏制毛泽东思想及其代表的无产阶级抗争精神在当代法国的持续存在,更无法阻挡唯物史观以新的理论形态向人民提供关于历史进步的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4-0060-08
作者简介:包大为,(杭州 310028)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从启蒙到解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多元实践研究”(18FZX035)
(责任编辑 临 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