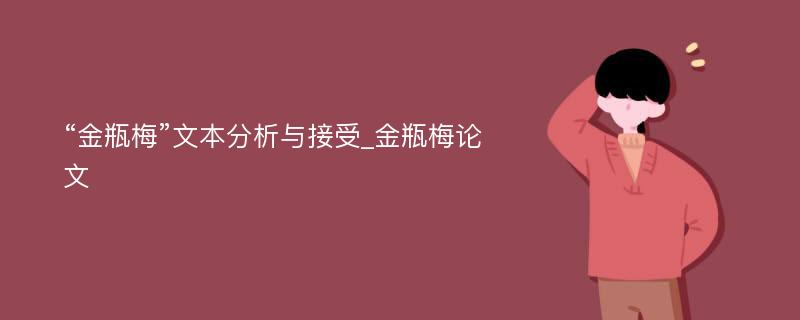
《金瓶梅》本文与接受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本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了《金瓶梅》的特点,指出正是《金瓶梅》本文的复杂性造成了《金瓶梅》接受中的歧见百出。同时,通过崇祯本批语与张竹坡批语的比较,分析了《金瓶梅》接受中的两种态度和方法。
关键词 《金瓶梅》 本文 接受美学 崇祯本 张竹坡
没有任何一部中国古代小说比《金瓶梅》更显示出读者的重要。现存最早的万历“词话”本《金瓶梅》东吴弄珠客序中,就提到《金瓶梅》接受中可能存在的高低四个层次的读者心理和社会效果: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此后,《金瓶梅》诸评家如张竹坡、文龙等,无不重视小说的接受问题。近代,人们重新认识《金瓶梅》也是从接受角度着眼的。曼殊在《小说丛话》中称许《金瓶梅》时说:
余昔读之,尽数卷,犹觉毫无趣味,心窃惑之。后乃改其法,认为一种社会之书以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凡读淫书者,莫不全副精神贯注于淫秽之处,此外,则随手披阅,不大留意。此殆读者之普通性矣。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盖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1〕
可见,不同的接受态度及效果直接影响着对作品本质意义的把握。实际上,这也是《金瓶梅》研究至今聚讼纷纭的症结。1980年台北召开过一次国际汉学会议,中外学者谈论《金瓶梅》价值时,仍不约而同提到怎样看此书的问题。如芮效卫博士主张“应从头看到尾,不应片断的看”,与清人张竹坡的观点(后详)遥相呼应。蒲安迪博士则声称他是“以美国人的眼光”、采用“明末清初”的方式来看《金瓶梅》的,又可谓别具慧眼、发人深思。〔2〕凡此种种, 都表明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察《金瓶梅》,是《金瓶梅》研究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
接受美学把文学作品的意义当作本文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文学作品既非完全的本文,亦非完全是读者的主观性,而是二者的结合或交融。〔3〕因此,我们在分析《金瓶梅》时, 应注意本文与读者间的关系,即《金瓶梅》本文传达结构的特点对读者的“召唤”与制约和读者对本文的接受态度。
《金瓶梅》本文的特点
本文的特点是读者反应的基础。《金瓶梅》本文的复杂性,前人早已意识到了。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谈到《金瓶梅》时说:“今人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这里,指出了《金瓶梅》本文中“显——隐”、“放——止”、“夸——刺”等矛盾关系。除此之外,前人还曾论及它的“劝——惩”、“前——后”、“零星——全书”等矛盾关系。这诸种矛盾涉及叙事、观念、风格、手法等方面。因此,当我们面对《金瓶梅》接受中歧见百出时,就不能不考虑到它的本文的这些特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金瓶梅》在叙事层面的特点。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它一方面容纳了大量的话本、曲词,保留着一些说唱文学的痕迹,另一方面又具有文人创作的性质。可以说它是由说唱文学向文人独立创作过渡的结果。这使得它在取材角度和表现方式上与以前的文言小说和纯粹的说唱文学都有许多不同。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曾这样比较过《金瓶梅》与其他小说: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
他所列举的多为文言小说,由于文言更讲究语言的凝重含蓄,与白话小说的“洞洞然易晓”相比,就显得不那么令人“畅怀”。而描写的酣畅淋漓正是白话小说,也是《金瓶梅》的一个特点,所以,明末那些思想解放的文人才激赏它“云霞满纸”〔4〕、“穷极境象,意快心。 ”〔5〕问题也随之而来了。以性描写为例,房中术著作自不必说, 文学作品也多有涉笔。其间虽偶见铺肆,如唐代署名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而以含蓄藉为主。于是形成了一系列性活动方面的隐语,如“云雨”之类。尽管它们的意义十分明显,但文人使用起来却全无顾忌,反而能在此基础上发挥想象、加以渲染,读之或亦心荡神摇,而作者终非具体挑逗,流于猥亵。以致李商隐《北齐》诗有“小怜玉体横陈夜”句,平直道来,前人已评为“极亵昵语”。词曲中颇有歌咏性爱之作,且不乏露骨渲泄者,若用语非俚俗,则仍不失含蓄之美。在小说、戏曲中,叙事成份增加了,如用文言描写,往往可在流荡中见节制。《西厢记》、《牡丹亭》中都有性描写,以其词语文雅,不常为人苛责。明代吴敬所著文言中篇小说《花神三妙传》,其中具体描摹了性活动过程,诱惑力则远逊于白话小说。《聊斋志异》也不乏性描写,但人们一般也不以为异,原因同样在于它使用的是文言。文言作为完全书面化的语言,与生活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为它的性描写造成类似遮羞布的屏障作用。
《金瓶梅》恰恰打破了这一屏障,它采取了一套新的、更生活化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作为艺术语言还不够成熟,有时甚至显得相当粗鄙。而露骨的性描写由于语言的接近“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更富于直感和挑逗性。应当说,语言的真切、描写的露骨与《金瓶梅》乃至当时整个俗文学的求“真”意向是一致的,然而,《金瓶梅》也像许多俗文学作品一样,还没有处理好“真”与传统的美善相济观念的矛盾。丁耀亢在《续金瓶梅》时即表露出这样的困惑:
如今说起二人(金莲、春梅)托生来世姻缘,有多少美事,多少不美事,如不妆点的活现,人不肯信;如妆点的活现,使人动起火来,又说我续《金瓶梅》依旧导欲宣淫,不是借世说法了。(31回)
“活现”要使人“肯信”(真)而不“使人动起火来”(违背善的原则),确非易事。当然,“真”与“美”、“善”的矛盾是普遍的。不过,它首先是通过叙事方式表现出来的。就这一点而言,《金瓶梅》招致物议的性描写与它使用的语言艺术化程度还有待提高不无关系。
与文言小说相比,《金瓶梅》的描写较少束缚,但与纯粹的说唱艺术相比,它的叙事方式又显得有所欠缺。说唱艺术的叙事不只是曲词,说唱艺人的声调、手势、对节奏的掌握等等,都是他叙事方式的组成部分,手段极为丰富。而《金瓶梅》只能通过文字叙述情节,塑造人物。在这方面,作为较早的供阅读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也还不成熟。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本文的意象结构存在各种方向、层次的空白和不确定性,这种空白和不确定性有一种刺激和召唤作用,可以调动读者的想象力。〔6〕《金瓶梅》却显然不善于创造这样的空白, 它在失去了说唱艺术的诸多表现手段后,唯恐交待得不充分,就把一切都写得很实、很足。不只是性描写如此,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毛病。例如在“词话”本中,总共选用了二十组散套和一百二十只小令,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一些曲子的穿插也符合特定情境的需要,起到了渲染气氛、表现人物心理和推动情节的作用(如第六十三回“西门庆观戏感李瓶”中所引《玉环记》曲词),但确有相当一部分曲子是多余的,至少是不必完整引用的。问题不仅在于有多少曲子游离于情节之外,成为作品的累赘,还在于过于琐屑的描写与交待对读者发掘本文的潜在意义形成了一种干扰,使读者在所谓“显——隐”、“放——止”之间为大量浮面的东西所左右。看来,作者还没有从说唱艺术到文人创作的巨大变化中,把握住二者接受过程的不同,没有充分估计到人们在阅读小说时比听人说唱时享有更多的联想自由。
《金瓶梅》在叙事层面上还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例如严肃与调谑、写实与夸张有时未能做到有机的统一。失度的调谑和夸张损害了作品严肃的写实风格。这实际上也是说唱艺术由于惯性作用对继之而起的文人创作的不当切入。因为说唱艺术为了招徕听众、避免冷场,常以插科打诨活跃气氛,这本无可厚非。不过,在一部文人创作的写实小说中,也袭用此法,势必破坏统一的构思和风格。如第六十一回的庸医自报家门、第八十回应伯爵等凑钱祭西门庆及水秀才代撰的祭文〔7〕, 既有戏曲和说唱艺术的痕迹,又有市井油滑和士大夫谈谐的特点,仿佛是在工笔风俗画卷上插进几幅漫画。与全书总体风格不合。
应当指出的是,《金瓶梅》在叙事上也是有所创新的,而接受中的有些歧异则是读者未能适应这种创新的表现。最突出的是《金瓶梅》塑造人物形象时,努力写出他们的不同性格侧面及其发展变化。即以西门庆为例,他为富不仁、滥淫无度,是作者否定的反面人物。但作者又没有将他简单化、脸谱化,还写了他慷慨大方、曲尽人情的一面。对于他复杂的性格内涵,并不是所有读者都能认识到的,尤其不是习惯了“美则无往不美,恶则无一不恶”的古代读者所能认识到的。比如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十分哀恸,大办丧事。玳安与傅铭谈到主人哀毁逾常时,认为他爱瓶儿是因为瓶儿当初带进门的财货丰厚。(事见六十四回)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如果只承认西门庆“不是疼人,是疼钱”,则又过之,因为小说确实大肆渲染了西门庆对李瓶儿的怜惜悲痛之情。所以,我们不妨把玳安的评论看成是对西门庆性格的补充揭示,是作者致力写出人物复杂心理的一个手段(在《红楼梦》中,这样的人物互评更普遍、成功)。遗憾的是,过去的读者似乎没有准确体会《金瓶梅》的这一进步,清人文龙评此段描写时说:
况此书皆作者所言,玳安之所褒贬,实作者之所平章也。此间议论,亦如吴神仙之相,龟婆之卜,因明明指示于人,阅者又何必自作聪明,妄出见解,而有所偏好偏恶于其间也。西门庆此番举动,玳安一言以蔽之曰:不是疼人是疼钱。哀梨并剪,爽利乃尔。吾故曰:是势利、非情分也。
显然,这种因书出作者之手,而视人物语言为作者语言的看法是十分偏颇的。文龙大约还只习惯于第二十九回“吴神仙冰鉴定终身”那种古朴的描写方法。在那一回中,吴神仙对西门庆及妻妾的评论,外在于具体描写之上,到是可以看作作者的评论的。
除了在叙事层面上的特点外,《金瓶梅》本文在观念层面也有自己的特点,或者说不协调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看自此书问世以来就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它究竟是“为世戒”,还是为世劝”(弄珠客序)?是否定淫乱,还是宣扬淫乱?
在一般人印象中,《金瓶梅》是中国“淫书”之最,其实不然。在《金瓶梅》中,淫秽描写只占极少数(全书近八十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洁本删去的仅一万九千余字)。而明清还有一些小说几乎满纸淫秽。如《昭阳趣史》、《桃花艳史》、《绣榻野史》等。其中有的连一点劝戒世人的表白都没有。《灯草和尚》就是这样的作品,它由咏人欲心如火入手,淫乱描写遍布全书十二回,仅结尾处略陈因果而已。更有甚者,公开为淫乱张本。《肉蒲团》虽宣称“要为世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但在开篇的《满庭芳》词中,却承认、肯定肉欲:
黑发难留,朱颜易变,人生不比青松。名利消息,一派落花风。悔杀少年不乐,风流院,放逐衰翁。王孙辈,听歌金缕,及早恋芳丛。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终。得趣朝朝燕,酣眼处怕响晨钟。睁眼看,乾坤覆载,一幅大春宫。
在古代小说中,开篇诗词往往是为作品定基调的,《肉蒲团》就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展示一个蝶亵蜂狂的春宫世界的。还有一部《春灯迷史》叙唐玄宗时杭州书生金华与二女从偷情到婚配事,全书充斥淫秽描写,几占五分之四。作者的开篇词也公然为他所写辩护:
俗语云:淫为万恶首,三纲败坏五常休。若非天缘造就,定然性命难周。惟此《春灯迷史》,实系生前配偶,三纲不败,五常不休。踰东墙而搂处子,真可谓搂之得妻。借冰人而结红丝, 亦不伤《关睢》雅化,虽偶尔淫,幸乃今古奇观,飘飘乎快事也,扬扬乎风流矣。
文中写及男女交欢时,还有“千奇万巧画春图”的诗句,结尾处作者更声称自己有“羡慕不已之心”,明清间“淫书”固多,然不以为耻如此书者,亦属罕见。相比之下,《金瓶梅》劝人戒淫的表白要突出得多。在全书第一回,作者就申明了这一主张。在以后的具体描写中,也穿插了不少这样的议论。特别是对潘金莲等人的此类行为,贬斥更多。然而,就在劝人戒欲这样一个基本动机和结构框架下,作者思想观念的矛盾也随处可见。例如第十回叙西门庆与应伯爵等十人“每月会在一处,叫两个唱的,花攒锦簇顽耍……整三五夜不归家”,作者写了一首诗:
紫陌春光好,红楼醉管弦。人生能有几,不乐是徒然!
这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显然有悖于作品的主旨。而类似的地方书中并不少见。第二十回的回前诗宣扬的是同一思想:
在世为人保七旬,何劳日夜弄精神?世事到头终有悔,浮华过眼恐非真;贫穷富贵天之命,得失荣华隙里尘。不如且放开怀乐,莫使苍然两鬓侵。
虽然还是及时行乐的老调,但联系下面展开的情节,作者又实在摆不脱“为世劝”的干系。不但如此,甚至在一回之中,也可以见出这种矛盾。第十五回回前诗曰:
易老韶华休浪度,掀天富贵等云空。不如且讨红裙趣,依翠偎红院宇中。
接下来写西门庆等被拉往妓院时,又有一首诗曰:
柳底花阴压路尘,一回游赏一回新。不知买尽长安笑,活得苍生几户贫。
一“劝”,一“戒”,对立鲜明。至于具体的性描写,与《灯草和尚》、《春灯迷史》之类单纯渲染肉欲相比,虽还能兼顾人物塑造,不失其社会意义,但有些地方仍不免夸肆过度,以致接近房中术“教科书”(如第二十七回对“牝屋”的说明了)。可以说,作者在理智上是否定西门庆们的滥淫生活的,而起伏于内心深处的情欲又常常使他产生背离理智的冲动,从而造成了本文观念上的上述矛盾。其实,这种“情”与“理”的矛盾在明中后期是相当普遍的,它体现了传统道德观念与新的社会风尚之间的尖锐冲突。就连《金瓶梅》的“为世戒”,也不全是出于维护传统道德的需要。小说第十一、二回写西门庆等耽于妓院,作者有诗感叹:
舞裙歌板逐时新,散尽黄金只此身。寄语富儿休暴殄,俭如良药可医贫。
构栏枝者媚如猱,只堪乘兴暂时留,若要死贪无足厌,家中金钥教谁收。
看来作者不反对眠花宿柳,只是提醒人们不要浪掷钱财。这与它标榜的道德训诫是有一定距离的,却符合市民、尤其是商人的思想。
假如我们超越前人所困扰的“为世劝”还是“为世戒”问题,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反观《金瓶梅》本文,我们会发现它在观念层面上的矛盾几乎涉及到它所描写的各方面。自然,我们还不应忽视叙事与观念之间的不协调。一方面,尚未成熟的叙事形式无法容纳新的观念,另一方面,陈腐的思想又制约着新的形式的成长。
袁宏道《与董思白书》曾称《金瓶梅》“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比较,《七发》中太子“久耽安乐,日夜无极”,客以“要言妙道”发之,通过极力铺陈音乐、饮食、车马、游览、田猎、曲江观涛之盛,逐步感发开导。《金瓶梅》正是继承了这种“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方式,前人亦多以此为之辩护,但动机与效果、手段与目的的背离也由此可见。
在细节上,叙事与观念的不协调也随处可见。如第十回武松被解送东平府,作者写东平府府尹陈文昭“极是个清廉的官”:
平生正直,禀性贤明。幼年向雪案攻书,长大在金銮对策。常怀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户口增,钱粮办,黎民称颂满街衢;词讼减,盗贼休,父者赞歌喧市井。攀辕截镫,名标书史播千年;勒石镌碑,声振黄堂传万古。正直清廉民父母,贤良方正号青天。
这是通俗小说称赞清官的陈词滥调。可就是这个清官,虽知武松受屈,却因西门庆通过杨提督打通蔡太师的关节而任其逍遥法外:
这陈文昭原系大理寺寺正,升东平府府尹,又系蔡太师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以此人情两尽了。只把武松免死,问了个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军。
也许不能对封建官吏提更高的要求。但从接受美学来说,读者通过前述赞词所诱导的“期待视野”却无法在后文“客观化”、“具体化”。而那种客观交待与具体描写之间又不构成反讽关系,这表明作品因袭的清官观念与他从生活出发的描写是矛盾的。这个矛盾后来到了曹雪芹、吴敬梓手中才得到解决。曹雪芹笔下的“葫芦僧错判葫芦案”抛开了清官观念的束缚,而吴敬梓则会把那段赞美之词变成人物的自我吹嘘,然后再用事实粉碎谎言。
又比如因果报应是明清许多小说的叙事模式。《金瓶梅》也宣扬了这一佛教观念,但在叙事上却没有受它的束缚。西门庆的暴卒及其家庭的败落并不是某种神秘力量支配的结果,而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对此,作者作了十分充分的描写与揭示。这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如第八十一回西门庆死后,来保私吞西门庆的布货,自己开办店铺,俨然一个小西门庆。此处作者有诗曰:
我劝世间人,切莫把心欺。欺心即欺天,莫道天不知:天只在头上,昭然不可欺。
话虽如此,却也没有具体写来保得到了什么报应。应该说,这是作者比明清许多小说家清醒的地方。
总之,《金瓶梅》本文存在着一系列新的特点与矛盾。作为作者给定的一个认知结构,这种特点与矛盾对接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如此,由不同的接受效果反求作品的本质,难免各执一端,对接受实践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也许,更重要的还是读者的接受态度和方法。
两种接受态度和方法:崇祯本批语与张竹坡批语之比较
接受美学把读者分为一般性读者和批评性读者,尽管两种读者间的界线并不总是那么清楚,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对《金瓶梅》接受的历史分析,也“基本上禁囿在文学的圈子里”〔8〕。从现存资料看, 士大夫是《金瓶梅》的第一批读者,传抄、评刻的都是这些人,至于其他读者的反应只能从他们的记载中看到片言只语。这种情况至今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有位学者曾感叹说:“阅读范围的限制使研究者不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精神活动的反馈,他的研究成果也不能获得专家范围以外的公众的验证,更谈不上研究中的智慧启发上的限制。这对于展开作品的艺术研究是很不利的。”〔9〕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是以读者为中心的〔10〕,即使只在文人的批评中,我们也能看到接受态度和方法的差异与变化。这里,不可能回顾《金瓶梅》全部复杂的接受史(批评史),但是,比较一下崇祯本的批语和张竹坡的批语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们显示了对《金瓶梅》两种不同的,同时又是很典型的接受态度和方法。
崇祯年间刊刻的《新刻绣像金瓶梅》,每回均有眉批、夹批,批点者待考,它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对《金瓶梅》最早的全面评论。而清人张竹坡评刻的《第一奇书金瓶梅》流行最广,其评语多达十几万字,开创了系统研究《金瓶梅》的新阶段。无论崇批还是张批,对《金瓶梅》都推崇备至,这是它们的共同点。有研究证明,张批还吸收了一些崇批的观点。〔11〕但是,比起这种共同点来说,它们的区别更大,也更值得我们注意。
接受美学有一个重要原则是“视野融合”,即认为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学本文相融合,才能谈得上接受和理解。而期待视野作为读者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往往因人而异,不断变化。崇批与张批的区别首先就在于它们是以不同的期待视野来对待《金瓶梅》的。崇批对全书没有提出总的看法,在一些具体批语中,指出了某些描写的劝惩意义。不过,它似乎并不像传统文化所偏重的那样,特别强调这一点,而是如明末一些文人那样,把《金瓶梅》当作“意快心”的“奇书”来欣赏。崇批认为《金瓶梅》“写情处,读者魂飞”(第四回),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位读者。在大量评语中,崇批都表现了对小说描写甚至那些格调不高描写的浓厚兴趣和无保留的嘉许。第二十七回是历来公认最淫秽的一回,崇批却啧啧称赏,盛赞其为“异想”、“好摹写”、“妙”等等。第五十四回“应伯爵隔花戏金钏”也是最低俗不堪的描写之一,崇批却称为“千古韵事”、“妙在此”。此时,他的思想境界和趣味与应伯爵之流已相差无几了。实际上,在不少评语中可以看出崇批者与书中人物的情绪是非常合拍的。第五十二回写到西门庆把潘金莲“那白生生腿儿横抱膝上”,崇批道:“那得不爱”。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接到王六儿送来的行房之物,崇批道:“虽明知其为送死之具,使我当之亦不得不爱”。第九十八回写“爱姐一双涎瞪瞪秋波只看敬济”,崇批道:“读者心痒活当局欤?”如此等等,都表明崇批者悉心体会了人物彼时的心理并产生了共鸣。所以,他对精通风月的潘金莲连连称之为“妙人”,而对像武松那样的“正人君子”则报以冷嘲热讽。第二回写武松不为潘金莲勾引所动,“自在房内却拿火箸簇火”,崇批道:“道学先生此时何不去了”,又说武松对潘金莲的态度“倒好做作”、“扫兴”、“忒卤莽”、“粗极”。后来武松声言:“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的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伤人伦的猪狗。”崇批道:“如此人世上却无,吾正怪其不近人情”。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崇批是以所谓“人情”体验作品的描写的。他的这种思想方法与明末反对伪道学的思潮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在接受态度上,他所取的是一种类似鲁迅说的钻进书中充当一个角度的沉浸,是对那些符合自己思想情趣描写的认同。
与崇批不重视主题的开掘而沉浸于具体描写不同,张批在总体上就十分强调《金瓶梅》的寓意性与劝戒意义,并在全书评语中努力补充,印证这种观点。他力辩《金瓶梅》非淫书,说:“凡人谓《金瓶梅》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12〕这里说的“史公文字”,不同于一般的史书,而是“世情书”。〔13〕可见,张竹坡在一开始就强调了自己的期待视野。而他强调寓意性与劝戒意义,也不像过去很多人那样,单纯从理念出发,从维护世道人心出发。他更重视通过个人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去观照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如果说张竹坡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非常突出的话,那并不是由于他的理论贡献。在这方面,他还没有完全跳出金圣叹的窠臼。他的卓异之处,正在于他的批评态度上,也就是他对《金瓶梅》的接受态度上。
接受美学十分看重读者的能动作用,认为接受过程不是对作品简单的复制和还原,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反作用。没有读者的接受,本文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张竹坡对《金瓶梅》的批评正是如此。更可贵的是,他是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去实践的。在他看来,要不被作者“瞒过”,即透过表面描写把握作品底蕴,必须把作品“当自己才去经营的文章”〔14〕来读。因此,他反复声称自己批《金瓶梅》不是一般的批评,而是“我自做我之《金瓶梅》”〔15〕,他还说:“故我批时,亦只照本文的神理段落章法, 随我的眼力批去”〔16〕,“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弟,变帐簿以作文章, 直使《金瓶梅》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板亦何不可”〔17〕。无论是在《金瓶梅》的接受史上,还是在古代小说的评点中,具有张竹坡这样强烈主体意识的都至为罕见。也正是由于他把批评与创作结合起来了,才能不受作者及原书的束缚,提出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
吴月娘在小说中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写的,这从作品为她安排的善终而亡的结局就可以明了。所以崇批及其他一些评点家对吴月娘肯定的居多。虽然在若干细节上,崇批也指出吴月娘为妇不当处。如第十九回吴月娘说:“我忘了请姐夫来坐坐”,崇本眉批曰:“处处是月娘作俑”,指责月娘引狼入室。但在第一回介绍吴月娘“却说这月娘秉性贤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随”,崇批道:“如此贤妇,世上有几”。说明崇批的看法还是受作品左右的。而张竹坡则不这么看,他指出:
看者只知说月娘贤德,为后文能容众妾地步也;不知作者更有深意。……[月娘]只知依顺为道,而西门之使其依顺者,皆非其道。月娘终日闻夫之言,是势利市井之言;见夫之行,是奸险苟且之行,不知规谏而乃一味依顺之。故虽有好资质,未免习俗渐染。后文引敬济入室,放来旺进门,皆其不闻妇道,以致不能防闲也。送人直出大门,妖尼昼夜宣卷,又其不闻妇道,以致无所法守也。……故“百依百顺”,是罪西门,非赞月娘。
在以后许多回评中,张竹坡都批评了吴月娘行为不合妇道的地方,认为作者是以阳秋之笔贬她的。张竹坡的深恶吴月娘(第十五回评曰:“月娘之可恨如此”)虽肇自崇批而接近金圣叹批《水浒》之深恶宋江,有些地方也带有鲜明的封建礼教思想(如第二十五回指责吴月娘春昼秋千非正道),但同时又能从生活出发,体会人物性格、行为的社会原因。如第一回回评在指出了“百依百顺”并非赞语后,他又说:
写月娘恶处,又全在继室也。从来继室多是好好先生,何则?因彼已有妻过,一旦死别,乃续一个入来,则不但他自己心上,怕丈夫疑他是填房;或有儿女,怕丈夫疑他不如先头的。即那丈夫心中,亦未尝不有此几着疑忌在心中。故做继室者,欲管不好,不管不好,往往多休戚不关,以好好先生为贤也。今月娘虽说没甚奸险,然其举动处,大半不离继室常套。
张竹坡的这种见解也许超出了作品直接的描写,但因为符合生活逻辑,所以能成一家之言。
当然,张竹坡的批评中也有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例如他经常从一些人物的姓名上寻索作者本意,个别不无道理,多数是强作解人的穿凿之语。这是不足取的。
崇批与张批在接受态度与方法上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崇批专注于细节描写,而张批更重视总体的把握。这一点从它们的批评形式上看就十分清楚。崇批主要是眉批和夹批,由批者在他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提出自己的会心之见。这也是早期小说评点的一般情形。而张批也有一些眉批、夹批,但更主要的却是回评,即在回前对本回情节和人物作一总的分析。此外,还有长达一百零八则、纵论全书的《读法》以及关于作品寓意的专论多篇。大体上,崇批相当于名胜游览区标识某某地“由此前进”的路标,张批则不但不有这样的路标,还有十分详尽的“导游说明”。事实上,张竹坡非常明确地提醒人们应以整体的观点看待《金瓶梅》,他在《读法》中说: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只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因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它历来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张竹坡要人们注意,《金瓶梅》的性描写是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不是以决定全书的思想意义。他还通过前后联系、相互比较指出:
《金瓶梅》说淫话,只是金莲与王六儿处多,其次则瓶儿,他如月娘,玉楼只一见,而春梅则惟点染处描写之。〔18〕
在第二十七回,他也有类似的批语:
此回是金莲、玉楼、瓶儿、春梅四人相聚后,同时加一番描写也。玉楼为作者特地矜许之人,故写其冷而不写其淫,春梅又作者特地留为后半部之主脑,故写其宠而亦不写其淫。至于瓶儿、金莲,固为同类,又分深浅,故翡翠轩尚有温柔浓艳之雅,而葡萄架则极妖淫污辱之怨。
这说明《金瓶梅》在性描写中,根据人物身份、心理、性格及在小说中的地位,采用了不同笔法。事实也是如此。第七十二回描写潘金莲委曲迎合西门庆时,作者就说:
大抵妾妇之道,蛊惑其夫,无所不至,虽屈身忍辱,殆不为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岂肯为此?
如果不怕有“屎里觅道”之嫌,单就《金瓶梅》性描写与人物塑造的关系也可以作一篇论文的。至少,张竹坡要求人们把性描写与全书联系起来看是有道理的。与崇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且趣味有失雅正相比,更是如此。
崇批与张批的不同,说明人们对《金瓶梅》的接受态度、方法及其效果、评价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在《金瓶梅》的接受史上,崇批的特点是以作品为本位的,由于缺少必要的审美距离,显得激情有余而分析不足。它大体上代表了《金瓶梅》第一代读者的眼光。张竹坡则是以读者为本位的,他表现了一种发掘作品潜在意义的冷静,有时又不免有些固执己见。正如接受美学的创始人所说的那样:“一部作品的艺术特点在其初次显现的视野中不可能被立即感知到。……一部作品实际上的首次感知与其本质意义之间的距离,或易言之,新作品与其第一个读者的期待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它需要一个较长的接受过程,在第一视野中不断消化那些没有预料到的,出乎寻常的东西。”〔19〕“而任何阅读都不可能穷尽全部潜能”〔20〕,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揭示了《金瓶梅》的本质意义。所以,我们乐于相信,阅读使文学作品展开它的内在的动态本质,作品的意义也应从它被接受的全部历史来考察。《金瓶梅》正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和对象。
注释:
〔1〕见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4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引用明清人对《金瓶梅》之评论多据此书,不另说明。
〔2〕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2— 4 页, 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参见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36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袁宏道《与董思白》。
〔5〕谢肇淛《金瓶梅跋》。
〔6〕〔20〕沃·依塞尔《阅读过程:一个现象学的方法》, 《当代电影》1988年第5期。
〔7〕参阅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193—194页,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8〕刘小枫选编《接受美学译文集》,240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9〕吴红、胡邦炜《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何满子序, 巴蜀书社1987年版。
〔10〕顺便说一句,近年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影响研究深入下去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古代小说理论的民族特点重视不够,往往比附于西方文论。这固然也能在相互阐发中说明一些问题,却有明显的局限。因为二者的理论重心不一样。就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来说,它的重心偏重于接受即“读法”。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张新之、张书绅、刘一明等都分别就他们评点的小说写过《读法》或类似的文字。至于具体评点更是处处从阅读着眼,而且它通常伴随小说刊印,对读者有直接的诱导作用。因此,欲发掘古代小说理论的精髓,应当从“读法”加以开拓。
〔11〕参见徐朔方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30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2〕〔14〕〔18〕张竹坡《金瓶梅读法》。
〔13〕《竹坡闲话》。
〔15〕《竹坡闲话》、《第一奇书非淫书论》。
〔17〕《第一奇书非淫书论》。
〔19〕周宁、金元浦泽《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43页。
标签:金瓶梅论文; 西门庆论文; 文学论文; 期待视野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人物分析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张竹坡论文; 春灯迷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