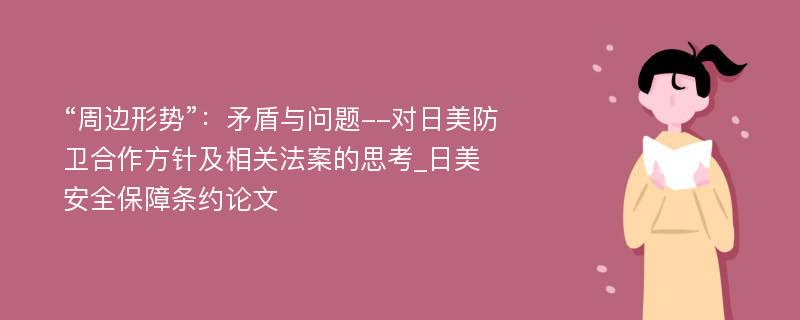
“周边事态”:矛盾与问题——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相关法案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美论文,法案论文,事态论文,指针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1996年4月的“日美安保共同宣言”、1997年9月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的指针相关法案, 冷战后日美两国终于完成了安保体制的再造过程。在这三个日美防务合作文件中,“周边事态”问题始终占据了核心位置。日美加强双边军事同盟、并以此作为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支持的做法,明显违背了冷战后地区安全发展的客观规律。
“周边事态”的本质性
“周边事态”的本质性问题,实际是日美扩大联合军事行动的问题,是日本军事与安全体制突破宪法束缚、从战后的宪法和平主义转向“大国主义”的问题。这是区分新、旧日美安保机制的重要标准。
1952年4 月生效的第一个日美安保条约没有提到日本“周边”概念,只是规定美军对日本本土安全提供军事保障义务,日本对美国履行这样的义务时予以协助。日美军事同盟起初确立的“范围”只局限于日本本土。1960年,针对当时美苏冷战的现实,日美两国对安保条约进行修订,将日美安保条约更名为“日美相互协助及安全保障条约”,(注:室山义正:《日美安保体制史》,有斐阁,1992年版,第24页。)新安保条约首次提到了日本的“周边”问题。同年2月8日,日本岸信介政府就“远东”的地理范围发表政府声明,提出日美安保条约所涵盖的远东是指菲律宾以北、包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内的日本“周边”地区。(注:高坂正饶:《详解:日美关系年表》,日本PHP研究所1985年版,第 75页。)这是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唯一对日本“周边”所作的公开、正式的声明。1978年11月日美签署了“日美中期防务合作指针”,规定,“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为了日本周边海域防卫目的和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应该实施共同的海上作战”。(注:圭下酋彦:《安保条约的成立》,岩波书局,1996年版,第58页。)由此“日美安保机制出现了从日本本土防御向着东南亚地区安全保障方面的转化”。(注:古川纯 山内敏宏:《战争与和平》,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45页。)1981年, 日美发表共同声明,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防御巡弋范围扩展到1000海里。
冷战结束后,美苏全球性战略对抗的结束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同时也改变了日本防卫需求。为此,日本加速了“战后总决算”的步伐,争取在本世纪“告别战后时代”和确立“大国化”地位,在防卫和安全体系上竭力谋求突破“战后限制”。1992年日本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 派自卫队参加了联合国主导的重建柬埔寨UNTAC活动, 其后还参加了若干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和维和活动。“PKO法”和自卫队海外维和派遣, 是日本以“国际贡献”为由松动战后宪法所规定的非武力和平主义。日本有权行使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集体自卫权”成了其国防观念的主导思想。
1996年4月日美首脑发表了“日美安保共同宣言”, 以政府间法律文件形式确认了日美军事同盟继续保持和发展的必要性,同时又以日美安保“再定义”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冷战后两国军事同盟关系调整的新方向。“再定义”的基本内容是:即使冷战的威胁消失了,日美军事同盟仍是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保障。为此,日美安保已经不再局限于对日本本土的防卫,而是以日美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合作,通过美国在东亚仍保持10万人的前沿军事力量部署和日本的支援和配合,实现两国所需的地区局势的稳定、和平与安全。(注:船桥洋一:“日美安保再定义的全面剖析”,日本《世界》月刊,1996年5月号,第24页。 )“共同宣言”从实质上改变了以往日美安保条约的性质,为新日美安保机制的形成确立了基本原则。1997年9月, 日美两国就修改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达成协议。新指针的核心问题是“周边事态问题”。当“周边事态”出现、美国决定进行直接军事干预时,日本则负责后方支援。桥本政府虽签署了指针但要具体贯彻和落实指针内容,使指针与现有日本法律和条约义务相兼容,日本政府还必须以国会通过新法案的形式,完成指针的法制化,使日本整个防务和安全体制“大转向”合法化。1998年4月,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出了“周边事态法案”、 “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及劳役协定”, 要求国会审议通过。 1999年4—5月,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相继审议并通过了指针相关法案。日本军事和防务体制的“大国化”以及所谓“正常化”转型从此大大加速。
“周边事态”的矛盾性
“周边事态”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周边事态”的内涵,二是“周边事态”的范围。“周边事态”从整体看可以拆解成三个相互关联部分:“周边概念”,“周边有事”,“周边事态”。“周边概念”是指“周边的范围”,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有事,日美将采取共同行动。“周边有事”是指日美军事同盟行动机制问题。具体说,日美安保条约是一个双边的军事同盟条约,日美军事合作原则上不包含“第三国”,但是,新日美安保机制所确立的就是当“周边范围”内“有事”时,如果美国进行军事干预,日本将提供相应的军事配合与合作。“周边事态”是指“周边有事”的性质,即规定“什么样的周边有事”日本将向美国提供军事支援与配合。换言之,“周边事态”的性质将决定日本是否将之视为“周边有事”,并进而根据指针相关法案采取行动。目前,日本政府在这三个方面的解释和立场经常自相矛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一、“周边事态”的范围。1997年9 月的日美中期防卫合作指针并没有就“周边”范围作出定义。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周边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事态性质的概念”,也就是说对在日本周围地区发生的武力纠纷,日本可根据它对纠纷性质的判断履行“周边事态法案”中所规定的条款,“周边并没有特定的地理范围”。随着国会对指针相关法案审议的进行,日本对“周边事态”的立场发生了微妙变化,从原来的不是“地理概念”转变成了“地理/事态复合概念”。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国会答辩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自卫队)不会到地球的背面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周边事态’有地理的含义。”(注:《每日新闻》,1999年1月25日。)小渊今年1月26日在国会咨询答辩中表示,“周边事态”的范围不超过日美安保的范围。“周边地区限定在日本的周边,不能想象是中东、印度洋、地球的背面。这一周边不超过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注:《朝日新闻》,1999年1 月27日。)所谓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就是指1960年条约中规定的“远东”地区。执政的自民党和自由党1999年1月26 日在两党政策负责人会议上一致认为,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中的“周边事态”的定义“不是完全没有地理要素,但不是指事先特定的地区”。自民党政调会长、前外相池田行彦在政策负责人会议上解释说:“支持政府的统一见解,但是,如果说这一概念完全不含有地理要素的话,缺乏说服力,应含有地理概念。考虑到对日本内外的影响,政府才将这一概念不特定指某地区。”(注:《读卖新闻》,1999年1月27日。)显然, 这些都是日本为了平息中国在内的邻国的不满和疑虑而做出的“解释”。
“周边事态范围”最突出的问题是,是否包括中国台湾在内。1960年的“周边声明”则明确包括了“台湾地区”。日本政府“事态性质概念”的模糊说辞并没有真正澄清指针的实际范围是否包括台湾的问题。1997年8月,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声称日美防卫范围包括中国台湾,引起中国舆论强烈愤慨,为此,东盟九国驻日大使也要求日本就防卫范围问题做出解释。1998年4月27日, 在桥本政府将“指针相关法案”正式送交国会前一天,日本报纸对“周边事态”的政府立场进行了突出报道。《朝日新闻》引用政府人士的话说,“为了让法案得到国会批准,将地理范围作某种程度的限定有其必要”。(注:《朝日新闻》,1998年4月27日。)报道指出, 新指针将以日美安保条约架构为基准,把根据该条约所涵盖的“远东地区”,再加上远东的周边地区,确定为日美防务合作的地域范围。这就不但包括朝鲜半岛,也包括中国的台湾,是菲律宾以北的整个远东地区。1999年1月14 日刚参与联合执政的日本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此前一日晚在东京会见记者时声称,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中提到的“周边事态”范围当然包括俄罗斯、朝鲜半岛、中国及中国的台湾,“周边”不是地理概念是可笑的,并表示使这一概念的范围明确化即使暂时会遭到有关国家的抗议,但从长远来看是有利的。(注:《读卖新闻》,1999年1月15日。 )小泽的狂妄言论引起中国等国的强烈反对和抨击。1月18日,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野中广务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关于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有关法案中提到的“周边事态”的看法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日美安保体制和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完全是防御性的,并非针对特定国家。当天,日本政府还根据野中广务谈话的精神,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就小泽的言论一事向中国方面作了澄清。(注:《人民日报》,1999 年1月19日。)但是,就在国会通过指针相关法案后不久,1999年6 月中旬,日本众议院指针相关法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山崎拓又公然声称,“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在内是不可能的。
二、“周边事态”的内涵。指针和指针相关法案只是明确了“周边有事”的日美共同行动机制,但对什么是“周边事态”只作了一个宽泛的定义。指针对周边事态的定义是“对日本和平与安全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态”。1998年4 月桥本政府提交给国会审议的“周边事态法案”沿用了这个说法。1999年5月19 日日本国会通过的“周边事态法”对此修改为“在对日本本土发生直接军事侵略,或者在日本的周边发生了对日本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态”,也没有就什么是“周边事态”作出准确和清晰的定义,而只是进一步强调了“对日本的直接军事攻击”,以便在外界感觉上,使新日美安保机制不要过于“滑出”日美安保关系只涉及日本本土的这个原定范围。然而,“对日本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又由谁来解释和运用这样的标准?显然,“周边事态”的宽泛和模糊定义只是给日本政府和美国提供在东亚一起推行军事干涉主义的借口,定义的弹性只能被视为是提高了日美军事干涉主义的可能性。日本政府表示,即使有指针和指针法,也会考虑是否提供支援来同美国一起介入“周边事态”。这一点似乎证明日本政府会独立判断“周边事态”而采取不同于美国的“独立立场”。然而,日本政府一贯立场总是十分注重同美国的协调和一致。远的不说,就拿最近几年美国军事行动时日本的立场来说,1998年8 月美军袭击拉登在阿富汗的藏身之地,1998年12月美英空袭伊拉克,1999年3月, 美国和北约空袭南斯拉夫,每次日本政府的立场都是表示“遗憾”,但可以“理解”。日本国际关系评论家山本刚士为此提出,当美国也在东亚采取军事行动时,“又能期待日本政府在‘周边事态’问题上能够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呢?”(注:山本士:“‘周边’的范围”,日本《世界》月刊,1999年4月号,第75页。)
三、日本对美国直接军事卷入的支持仅仅局限在“后方地域支援”。指针和指针相关法案所规定的日本仅仅提供“后方支援”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一旦发生“周边事态”,美、日和冲突的第三方事实上都会处于“交战”状态。日本政府现在抓住国际法上有关“中立”问题的通行说法,将侦察、监视和运送等海外支援活动视为非参战行动,以此来解释新指针不违背日本宪法。但现实是,日本从事海外支援活动的自卫队当然有可能受到军事攻击。这时,日本政府怎么办?“周边事态法”第三条规定,“在日本领域内有战斗行为时自卫队可以出动,在公海及上空的支援应该是在没有战斗行为时进行。”这并不现实,现代战争后方和前方本身很难区分,也难以限制。第二条规定,“对应措施实施时,不能使用武力威吓和行使武力。”第11条又规定,“为了保护身体和生命安全可以使用武力”。事实上,“周边事态”发生时,日本是主动介入军事纷争,所以,“周边事态法”的这几条规定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
“周边事态”的危险性
“周边事态”从概念到具体操作过程都隐藏着对东亚地区安全的危险性。
一、日本国会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指针相关法案后,“周边事态”已蜕变成了日本在“周边地区”介入美国的军事干涉和采取支援行动的“合法依据”。它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宪法和平主义,也有可能导致日本“自卫队体制”的崩溃。早在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时, 由于当时考虑有可能卷入战事而冻结了这一法案中有关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从事隔离交战双方兵力、监督解除武装等活动的条款。而指针法案通过后,已经明显带动起了日本国内“修宪”声音的扩大。指针法1999年9月生效, 日本“周边有事”的法制化暂时告一段落。但所谓新日美防务机制的“国内有事”法制化进程还刚刚开始。围绕着自卫队从本土防御走向应付“周边事态”而必然的军备扩张、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和自卫队先制攻击权等方面的问题,将会出现一系列新的法律。日本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内有事法制化”的核心,就是要用新法代替旧法,来确立日本不受和平宪法约束的新防务与安全体制。对日本来说,“周边事态”概念的确立,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还有一系列的后续手段有待跟进。它明着是巩固和发展后冷战时代日美安保机制,而暗地里却是借此说服公众舆论,大力推进日本军事体制“大国化”和“正常化”的步伐。为此,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曾强烈要求使“指针法”成为废案,认为指针法“完全违背了日本宪法”,通过指针法是“无理”的。
“周边事态”的模糊性质和日本政府解释中的暧昧立场,很难说服日本的邻国相信日本在日美新安保机制上纯粹的“防御性”。日本政治人物认为,指针法的通过和日美安保机制的加强,可以对日本周边有可能发生的冲突起“威慑”作用,因而有助于地区稳定。这真是奇谈怪论。关键是,新日美安保机制到底想“威慑”谁、针对谁以及对付谁?自从1998年8月后,日本政府大谈来自朝鲜的“威胁”, 指针法也被说成是对付“朝鲜挑衅”的重要手段。但是,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装备的技术程度,朝鲜根本不可能构成对日本安全的现实威胁。日本政界和学界一个并没有挂在嘴边、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问题是,指针与指针法最大的对象就是中国,特别是为了对付中国不承诺对台湾放弃武力来实现在亚洲的“扩张主义”。指针与指针法在“周边事态”上的弹性定义,同美国当前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战略性模糊”政策如出一辙,而且是以日美新安保机制的形式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政策的“战略模糊”立场,以便以存在“可能性”的日美国际干预来“威慑”中国的统一进程。
中国政府一向反对日美加强双边军事同盟的做法,认为此举违背了冷战后地区和平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中国政府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内政”这一严正立场出发,要求日本政府明确将台湾排除在“周边事态”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如果日本将台湾纳入日美安保的范围,不仅违背自1972年两国建交公报发表以来日本政府一贯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同1998年11月日中首脑会晤后所发表的联合宣言的原则背道而驰,也必然破坏日中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最根本的基础。
二、“周边事态”中引伸出来的日美“周边有事”的共同军事行动机制,加强了美国对东亚地区事务采取军事干涉主义和日本协助美国在东亚制造新的“伊拉克化”和“南斯拉夫化”的可能性。指针及指针法的通过,加强了日美双边军事同盟在东亚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上增大了日美共同在东亚地区进行军事干涉主义的可能性。“周边事态”的模糊定义,使得美国可以主观地将东亚地区中出现的任何问题,按照自己的意图“定性”为“周边事态”,而日本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将被迫接受。日美防务合作中的所谓“周边有事机制”更是对未来东亚地区安全走向人为地增加了新的紧张因素,有可能为今后东亚地区局势的恶化埋下隐患。美国在冷战后军事与经济力量独步世界,屡屡进行军事干涉,推行强权政治,插手地区事务。但其结果往往是加剧了地区性问题的进一步动荡。最近在科索沃问题上对南斯拉夫所策动的空中打击更是造成了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在东亚同样存在着推行军事干涉主义的可能性。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台湾海峡危机”都已经证明,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干涉只会带来新的地区冲突,招致地区安全状况新的恶化。根据指针和指针法,日本对美国在地区军事行动中承担支援义务。美国在欧洲和中东问题上有许多帮手,在东亚,美国无法指望北约的帮助。现在,日本开始发挥美国在东亚的北约成员国的作用了。如果日本和平宪法走向崩溃,日本是否想充当美国在东亚推行“伊拉克化”和“南斯拉夫化”时英国所扮演的角色?
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并不稳定,一些传统的地区热点问题依然存在。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不能依靠加强军事同盟,更不能依靠武力和军事强权。只有在双边以及多边的层次上不断推进平等对话,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消除紧张局势,促进整个地区的共同繁荣和稳定,才是解决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的基本方法。任何建立在武力和军事强权基础上的“霸权和平”不仅抹杀了东亚地区安全问题多样化和复杂性的事实,也只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和动荡。日本强调日美安保架构在过去40年间维持了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今天冷战已经结束了将近10年,东亚的地区安全局势同冷战期间相比,已经出现了巨大变化。以“周边事态”扩大日美安保范围,加强日美在地区问题上军事力量的主导地位,只是在变化了的时代继续推行没有实质变化的安全问题上的日美“冷战构造”,这绝非建设性的思路与方式。新日美安保机制客观上是在推行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新东亚“均势战略”。但是,“均势”的安全架构很可能进一步刺激有关国家追求军事力量的发展,挑起地区国家间新的军备竞赛。日美在1998年9月决定进行TMD联合研制和部署,就是一个极有可能触发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信号。日本学者丰田利幸就指出,“指针加大了东亚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丰田利幸:“对新指针的忧虑”,日本《军缩》月刊,1999年8月号,第3页)
标签: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日本国会论文; 自卫队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同盟论文; 地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