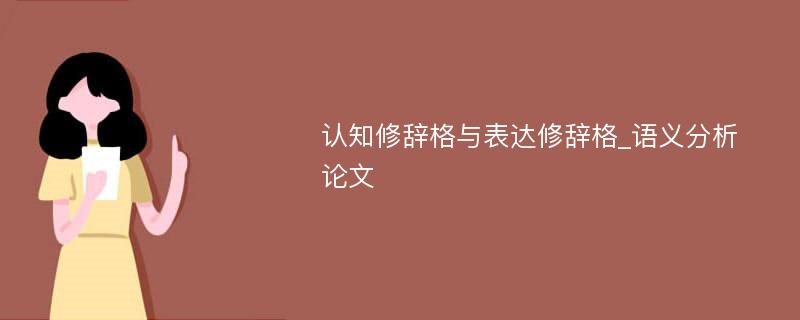
认知性辞格与表达性辞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性论文,性辞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修辞学对辞格的研究,其实还停留在材料收集的阶段——只是在一只百宝箱内放进了各种各样表达价值特殊的语言格式;严格地说尚未进入研究的阶段——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具有理论控制力的观点,能够将这些杂乱的材料置于统一的理论目光的审视之下,以及专属的研究方法的操作之中。不找到这样的理论和方法,修辞学的研究便举步维艰,永远盘桓在常识的视野之中。
我们注意到有一些辞格的使用不仅引起了语言意义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些语义的变化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关系,它们的修辞价值正是在这些认知关系改变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的辞格大致有比喻(包括明喻、暗喻、借喻等)、比拟、借代、移就、拈连、夸张六种,再加上象征、通感所涉及到的语言现象。它们与其它辞格有着明显的差异,可以单独作为一个类来研究。为了便于称说,我们把这些现象非正式地称作认知性的辞格。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只是想借用这些名称所指的语言现象做研究的材料,以及利用人们对传统修辞学的熟悉程度方便地找到一个对话的基础,而决不希望我们的研究局限在这些传统的辞格中。有些学科对认知性辞格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作过一些很有价值而且很深入的研究,但是很遗憾,它们不是语言学的。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们的成果,但是作为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修辞学目前更需要的是自己的研究范式。由于缺乏这样的范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修辞学就其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在现代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山穷水尽、寸步难行。所以我们的更大目标,是想通过认知性辞格的研究,对修辞学研究范式的建立做一些尝试。
1.必有特征、可能特征、不可能特征
以上认知性辞格的使用所引起的语义变化,最终都反映在某个词语意义的变化上。因而我们的思路首先被引导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用什么样的语言学方法,能够将辞格运用后词语意义的变化清楚地显现出来?
现代语言学中的语义特征分析法,又称义素分析法,将一个词的意义分析为一组区别性的语义特征。这种方法不认为词义是词所指对象的本质属性的反映,而认为某个词的词义就是该词的所指对象相对于其它对象的最低区分度,它表现为一组区别性的语义特征。任何对象只要完整地具备了这组特征,就足以与其它对象区分开来,其语言表现就是可以用这个词去称呼它。如果说一个词所能指称的对象是一个集合的话,那么进入这一集合的唯一标准就是必须具备这组特征。例如“杯子”这个词可以用来指各种各样的具体对象,它们也组成了一个杯子的集合,但不管其中哪一个,都必须具备以下的区别性特征:
/杯子/:[+实体、+具体、+无生、+固体、+容器、+圆柱体、+盛放液体、+饮用器具]
前三个是范畴性的特性,它取决于一个词所属的语法上的词类及次类,这里的“实体”、“具体”、“无生”就与“杯子”一词的名词性有关:后五个特征是经验性的特征,它们决定于这个词的词汇意义。
然而仅仅依靠语义特征分析法只能对一个词的语义构成进行分析,并不能显示一个词的意义变化。如果说一组区别性的语义特征只是一个词的内涵特征(相当于一个概念的内涵),是词所指的所有对象的必有特征,那么这个词还会有它的外延特征——词所指对象的集合(相当于概念的外延)内每一个具体的对象除了必须具备该词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内涵特征,显然还会在这个共同的标准之外具备自己独有的特征——例如有的杯子是“带盖儿的”,有的却是“带把儿的”;有的杯子是“瓷质”的,有的却是“塑料”的;有的杯子是“缺了一个口”的,有的却是“结满茶垢”的;有的是“慈禧太后用过”的,有的却是“乾隆年间烧制”的……一组必有的内涵特征只能构成一个抽象的杯子,加上这样一些以至于无穷个外延特征才能形成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具体杯子。
任何一个物体,只要人们称它为杯子,我们就能预测它必定具有哪些内涵特征,但对任何一只杯子我们都无法预测它一定会具有哪些外延特征。内涵特征是必有性的,外延特征却是可能性的。由此我们将以上使用过的术语统一为两个:必有特征和可能特征,前者可与区别性语义特征、内涵特征替换使用,后者则可与外延特征替换使用。必有特征和可能特征用于词的意义分析,它们就是语义特征;如果用于对事物的认知,它们就是认知特征。
一个词会有哪些具体的可能特征虽不能预测,但它毕竟有一个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是不可能特征了。“叫唤了一声”、“发芽”、“里面放着三只书橱”这三个特征就不可能为“杯子”一词所具有。这样我们在必有特征和可能特征之外又有了第三个术语:不可能特征。
不可能特征是本文讨论的重点,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它可以分为两类:
(a)性质上的不可能特征。“杯子”的必有特征中有“无生”一项,说明它是没有生命的物质实体,而“叫唤了一声”及“发芽”却只能在“有生”的基础上发生,语义上的不相容决定了这两个特征是“杯子”的性质上不可能特征:
(b)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杯子”是“容器”,虽通常是用来盛放液体的,但置放固体的东西也是可能的。“书橱”具有固体的特征,从性质上说可以放到一只杯子中,但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一只巨大的杯子,所以“里面放着三只书橱”是“杯子”程度上不可能特征。
由此看来,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应该有两个前提:第一它在性质上必须是可能的,性质上可能了才有必要讨论程度上是否可能;第二则是程度上的扩展或收缩必须引起了认知关系的改变,因而这种不可能不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环境的不可能,而是事理上的不可能。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条具体的判断标准:
A.如果设想某一程度上的特征为真,必定导致不同事物建立在正常认知关系中的程度比例的变异,从而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图景,那么这一特征是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例如“非常长”是“白发”性质上允许的特征而“三千丈”也在“非常长”的范围内,但我们接受了“白发三千丈”的语句而试图将它想象出来,就必须调整正常认知中“白发”与人体各部分甚至与江河山川的比例关系,从而出现一幅怪异的图景。在这种情形下“三千丈”成了“白发”的一个程度上不可能的特征。同样我们也只有在完全摆脱正常认知方式带给我们的比例关系,才能想象一个人是如何面对一只可以装进三只书橱的巨大杯子的,想象“席”一般大小的雪花是如何在我们周围飘飞的。而以下情况就不同了——
(1)每分钟,都有十家影院同进散场│街道上着了火的人(黄亚洲《黄浦江》)
(2)她……赶明儿打个喷嚏也得事先请示领导。(王蒙《湖光》)
“每分钟都有十家影院同时散场”似乎在事情发生频率的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无须改变它与其它事情发生频率的比例关系,就完全可以想象这件事如果真实发生将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同样无须摆脱正常认知方式带给我们的时间频率上的比例关系,就能对“打个喷嚏也得事先请示领导”做出想象,可见它们都没有影响到认识关系。
B.如果设想某一程度上的特征为真,必定导致不同类别事物间差异的消除;从而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图景,那么这一特征是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
不同类的事物可以拥有相同的特征,但特征的表现程度却有明显的差异。例如人和狮子都可以具有“疯跑”、“狂跳”的特征,但狮子在这些特征上的表现有人不可企及的强烈程度,如果想象一个人真的和狮子一模一样地“疯跑”“狂跳”,人和狮子间这一点上的差异也就没有了:
(3)我像发情的雄狮子一样在宁静的大街上一边疯跑,一边狂跳。(刘毅然《摇滚青年》
因而狮子的这些程度上的可能特征就是人的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把这样的特征强加给某个人,势必会改变我们对这个人的认知。简单的说,我们会感到这个人有失常态,非常怪异。可以与下面的语例对比——
(4)今天的月亮和今天的太阳一样圆。
月亮和太阳不仅能共有“圆”的特征,而且在“圆”的特征上没有程度的差异,因而想象月亮与太阳一样圆并不会改变我们对月亮的认知。可以说“圆”既是月亮的又是太阳的程度上的可能特征。有一个方法可以对这两种情形进行鉴别,那就是观察有没有互逆的关系:“今天的月亮和今天的太阳一样圆”与“今天的太阳和今天的月亮一样圆”是等价的,但例(3)就不能说成“发情的雄狮子像人(‘我’)一样疯跑和狂跳”。
2.三种特征的相互关系
一个词有多少个必有特征应该是确定的,可以穷尽性地列举出来,因为它们是该词区别于其它词,因而也是该词的所指对象区别于其它对象的最低限度,借助语义特征分析法就可以将它分解为一个区别性语义特征的有限集合,以上我们列举的“杯子”的八个语义特征就是这样一个集合。当然不同的人分析同一个词得出的必有特征很可能会有差异,但这只是操作方法的差异造成的,理论上应该能够取得一致。正因为一个词具备多少个必有特征是确定的,必有特征的增加、减少或改变就会引起词义的变化而造成不同的词。例如对“杯子”来说“玻璃”是可能特征,但一定要将“玻璃”增加为必有特征的话,“杯子”就成了“玻璃杯”:在古汉语“騚”的必有特征中抽去“四蹄皆白”的特征,“騚”就成了“马”。
然而一个词可以拥有多少个可能特征,却是难以确定的,更无法穷尽性地列举。我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对词的所指对象产生新的认识,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语义特征成为这个词的可能特征。然而不管可能特征数量上有多少,我们都能够对它的范围加以控制。因为可能特征之所以是可能特征,就在于它相容于必有特征——不仅不与必有特征冲突,而且是在必有特征的基础上发生的:“瓷质”、“塑料”都有固体的属性,它们相容于“杯子”的必有特征“固体”,才有可能成为它的可能特征;而“缺了一个口”可以发生在容器的壁上而“杯子”有“容器”的必有特征,“缺了一个口”才成了它的可能特征……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必有特征来定义可能特征——
凡不与一个词的必有特征相冲突的语义特征都是这个词的可能特征。
一个词的必有特征实际上为这个词规定了一个可能特征的无限集合,它由一切不与必有特征冲突的语义特征组成。
可想而知不可能特征在数量上要比可能特征多得多,一种语言可能形成的所有语义特征减去一个词的必有特征和可能特征,剩下的都是这个词的不可能特征。但是由于不可能特征有性质上不可能和程度上不可能两类,对它的语义限定就要复杂一些。
首先我们也可以用必有特征来定义性质上的不可能特征——
凡与一个词的必有特征冲突的语义特征都是这个词的性质上不可能特征。
上文我们已经说明,“叫唤了一声”、“发芽”两个特征因为与“杯子”的必有特征“有生命”相冲突,只能成为“杯子”的性质上的不可能特征。因而性质上的不可能特征也是一个由该词的必有特征规定的无限集合,只不过与可能特征的规定相反,它由一切与必有特征冲突的语义特征组成。
然而如前所述,性质上可能了才有可能发生程度上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性质上可能就已经满足了必有特征的要求,这样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就不能用必有特征来定义,也不能用它来规定集合的范围。但围绕着一个词的必有特征,通常有一个量限范围,它的上、下限大致规定了这组特征在量上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和最低程度,而它的核心,则是这个词所指对象中最典型的那一些在量上的体现。虽然有人如果异想天开制作了一只楼房一样高大的杯子,我们也得承认它是一只杯子。但这可能微乎其微,几近于零,只能是“杯子”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量限范围对于程度上不可能特征不是严格的定义关系,而是依据现实给程度上的可能大致划定了一个范围,从而也给程度上的不可能大致划定了一个范围。
总起来说,一个词能以哪些语义特征为可能特征,决定于这个词具备怎样的必有特征:而一个词能以哪些语义特征为性质上的不可能特征,反向决定于这个词的必有特征;能以哪些语义特征为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则决定于这个词的量限范围。
3.词内和词外:语义特征的存在方式
语义特征分析法的理想是找到数量有限的一组语义特征,而且是最小的、不可再加分析的语义特征,利用它就可以对一种语言中所有词的词义进行周全的分析。为避免语义上的自我循环,这组语义特征不能用自然语言中的词语来表现,只能另外制定一套元语言。然而这一理想的实现技术上将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似乎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给一种自然语言设计出一套这样的元语言来。我们不能坐等这样的时刻到来之后再运用语义特征分析法,可行的办法就是直接用自然语言的词语来表现语义特征,而这一措施的采取,必然带来的后果就是无法再对“最小”做苛刻的要求。于是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固体”、“容器”是语义特征(尽管它们也不是最小的),而“慈禧太后用过”、“叫唤了一声”也可以作为语义特征。这样的做法虽不能说是真正的语义特征分析法,但它为语义分析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这样的处理带来的另一后果,是语义特征在语言中有了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在词内,以一个词的必有特征的方式存在。这时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它们——在“我买了一只杯子”这个句子中,所能观察到的只是一个整体的词“杯子”,必须经过语义分析才能意识到“杯子”的内部存在着以上列举的那八个语义特征。
另一种是在词外,以这个词的语义谓词的方式而存在。凡与一个词发生组合关系的另一些词语,都表述了这个词的某种语义特征,因而都是这个词的语义谓词:
(5)缺了一个口的杯子。
(6)杯子缺了一个口。
这两个句子的句法表现虽然不一样,但在语义上却是等价的,都对“杯子”进行了一次表述,表明“杯子”具有“缺了一个口”的语义特征。甚至——
(7)小猫打翻了杯子。
也是一次语义表述,表明“杯子”具有“(被)小猫打翻”的语义特征。当然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小猫”具有“打翻了杯子”的语义特征。
在词外以语义谓词方式存在的语义特征都是这个词的可能特征,如果必有特征跑到词外成为语义谓词,往往会造成永恒真的逻辑废话,这时语义表述的是词义本身已有的内容:
(8)阿姨是女的。
(9)杯子是容器。
“女的”是“阿姨”一词必有的语义特征,只要我们理解了‘阿姨’这个词就一定已经接受了这个语义特征。如果再将它作为表述内容,势必会因为未能传递任何新信息而成为废话,除非对方不理解这个词。“容器”对于“杯子”的关系同样如此。
不可能特征既然是不可能的,那它既不能出现在词内,也不能出现在词外。如果一个原先的不可能特征现在在词外与词发生了语义表述的关系,一定是该词的必有特征的集合或量限范围发生了某种变化,使得原先的不可能特征变成了现在的可能特征:
(10)潺潺的头发流遍全身(江河《向日葵之一》)
“潺潺”和“流遍全身”原来都是“头发”的不可能特征,现在它们分别以定语和谓语的身份在词外与“头发”发生了组合关系而成了它的可能特征。这种变化的前提是“头发”的必有特征中的“固体”被“液体”所替代。
4.认知性辞格:对不可能特征的追求
一个词语对可能特征的选择以及对不可能特征的拒斥,实际上就是这个词语的使用规范。然而词语一旦被认知性辞格的修辞方式所使用,这种规范就会遭到破坏,其中最突出表现就是对不可能特征的接纳,也就是将不可能特征变成了可能特征,标志是它们都能在词外与这个词发生组合关系而对之进行语义表述。对不可能特征的接纳方式可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而在分析之前需要建立本体、介体、本体词、介体词四个概念。本体对不可能特征的寻求往往要借助于一个中介对象,也就是介体。通常所说的喻体就是一种介体,但我们的讨论范围不限于比喻,所以有必要使用所指范围更大的介体一词。表现本体、介体的词语分别是本体词、介体词。
(a)零距/有距的接纳方式
“距”指的是语义距离。表现不可能特征的词语如果能直接加到本体词上而没有任何句法上的阻隔,语义距离为零。但在更多的情形下本体词与表现不可能特征的词语之间有介体词、表相似或等同关系的词语以及表示不确定性的“好像”、“似乎”、“仿佛”等词语的插入,它们之间的语义距离就加大了。既是距离,就会有程度的大小:
(11)太阳蜗牛似的爬过窄长的天空。永远的蓝瓶子一样的天空,稀薄的牛奶一样的天空。
(蔡测海《往前往后》)
这样一个明喻的使用,目的其实就在于将不可能特征“爬过”强加到“太阳”上,但强加经过了介体词“蜗牛”和比喻词“似的”的中介,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就因为这些阻隔的存在而显得比较疏远。而在暗喻中——
(12)老福贵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照他的话说,只要不缺吃缺喝,见天有散心的地方,
日子就是松花蛋,里香外不臭。(王愈奇《河上的诱惑》
虽然有介体“松花蛋”的阻隔,但“是”表明的等价关系让不可能特征与“日子”的联系又接近了一些。
(13)枸杞头放在一个元宝篮里,一种长圆形的竹篮,叫做元宝篮子,枸杞头带着雨水,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汪曾棋《故乡的野菜》)
“带着雨水”原是“女孩子的声音”的不可能特征,从句法上看似乎是直接加到了“女孩子的声音”上。但细加分析,就会发现仍然离不开介体词“枸杞头”的中介作用,尽管介体词在上文中。这正是拈连的特点,但与明蝓暗喻相比,语义距离毕竟更加缩短了一些。
(14)在山谷深处,丛林遮住的地方│两条年轻的小径胆怯地接吻(李钢《在山上》)
(15)只有清晨才具有的鲜红的阳光,正在那个天空里飘扬。田野在晴朗地铺展开来,树木首先接受了阳光的照耀。(孙文昌《夏季台风》)
例(14)中“年轻”和“接吻”是“小径”的不可能特征,它们能直接加到“小径”上,是所谓拟人的作用。例(15)中不可能特征“飘扬”、“晴朗”也直接加到了“阳光”和“田野”上,通常认为前者是拟物,后者则是移就。表面上看,比拟、移就和所谓的通感一样地对不可能特征的接纳都是毫无阻隔的,但实际上比拟、移就都有一个不露面的介体在隐隐地起作用,因而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语义距离。只有在所谓的通感和夸张中由于只有本体而没有介体,不可能特征对本体词的语义距离为零:
(16)他把它装进陶罐│铃铛似的系在腰间│清脆的响声金光四溅(江河《息壤》)
视觉特征“金光四溅”不经任何中介,加到了听觉现象“清脆的响声”上。但其中如果出现了“好像”、“仿佛”等表不确定性的词语,也会出现一定的语义距离:
(17)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经像下了火。(老舍《骆驼祥子》)
这是一个通常所说的夸张,由于“像”的存在,不可能特征“已经”“下了火”与“地上”之间还是有语义间隔的。
(b)隐含/显现的接纳方式
有待接纳的不可能特征可以以语词的方式显现在语言中:
(18)女孩子的喊声像火苗一样烧着他的屁股,他更快地往上爬。(莫言《枯河》)
如例中的“烧着他的屁股”。但经常又是隐含的:
(19)歌声像一只挂着白色帆的小船,我的心渐渐趋于宁静。(于坚《蛐蛐儿的年代》)
例(19)中没有指明该接受怎样的不可能特征,但每一个试图理解并体验这个句子的人都会在“像”的诱导下,努力在“挂着白色帆的小船”的众多可能特征中发现一个可以与“歌声”发生联系的,然后把它们加在“歌声”上。由于“挂着白色帆的小船”和“歌声”在语义上是两个距离甚远的类,前者的可能特征多半是后者的不可能特征,所以我们可以认定这里隐含着一个不可能特征。
(c)直接/间接的接纳方式
不可能特征如何能加到某个词语上去?大致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间接的也即有介体的途径,借助词语之间的语义联系——因为本体词A与介体词B之间在一定的语境中形成了某种语义联系,从而以这种联系为渠道,将词语B的可能特征(也就是词语A的不可能特征)转移到词语A上去。这种语义联系主要有相似、接近、构成三种:
(20)她的脸色蜡黄泛青像一条腌过的酸黄瓜。(北村《构思》)
(21)一只蓝蝴蝶、正停泊在│她那头发 流成的小溪里(维维《街》)
很显然,这里的不可能特征之所以能被词语A接纳,靠的都是本体和介体间的相似关系。例(20)的相似关系比较明显,发生在“脸色”与“酸黄瓜”之间,而对例(21),一定要发现主句中隐含着的“小船”和宾语中隐含着的“水流”,“蓝蝴蝶”以及“头发”的相似关系才有了落实的对象。
(22)(我正开着车)她突然在我的肩膀上咬了一口,她的牙狠狠地嵌进肉里,血慢慢地从衣服里渗出来。小轿车痛得左右乱晃。(吴滨《写给男人看的故事》)
因为“小轿车”与作为司机的“我”之间有空间上的接近关系,“痛得左右乱晃”才能加到“小轿车”上去。当然接近关系也可以是时间上的。
另一条途径是直接的也即无介体的,如所谓的通感、夸张,就是以人们心理感觉的现实为依据,将不可能特征直接加到一定的词语上。
(d)正向/负向的接纳方式
如果把本体词接纳不可能特征也即接纳介体词的可能特征的方向确定为正方向,介体词接纳不可能特征也即接纳本体词的可能特征的方向就成了负方向,以上所举的语例都是正方向的。我们已经指出,本体词与介体词靠相似、接近、构成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些关系如果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就会发生介体词对本体词的语义替代。为什么会发生语义替代,我们将在另文中探讨,这里研究的是——语义替代一旦发生,本体词就会失去语言形态而从话语中消失,不可能特征的接纳也就无从发生了。从另一角度看,语义替代意味着介体词将接替本体词在原先的上下文中起作用,而原先的上下文所体现的语义特征对本体词来说当然都是可能特征,对介体词而言却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特征了。所以语义替代必定会导致接纳不可能特征的方向发生改换:
(23)他提着铜锣,他提着一个太阳。手中的太阳沉甸甸的。他用橡木锣槌敲击太阳。(少鸿《黑松林》)
(24)异国情调的音乐。异国情调的咖啡馆。绿色的棕榈。金色的窗帘。黑丝绒旗袍迎面过来。猩红的嘴唇微微张开:“先生,用点什么?”(李晓《关于行规的闲话》)
过强的相似关系使得“太阳”同一于“铜锣”而取代了“铜锣”,介体词“太阳”于是就处在了本体词“铜锣”的上下文语境中,不得不把整个上下文——“手中(提着)的”、“沉甸甸的”、“(被)橡木锣槌敲击的”都作为不可能特征而负向接纳。同样过强的接近关系和构成关系也使“黑丝绒旗袍”、负向接纳了不可能特征“迎面过来”和“左右摇进”。
具体话语中一次不可能特征的接纳究竟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取决于我们对话语中相关词语是本体词还是介体词的判断。如果认为例(24)中的“小轿车”不是本体词而是介体词的话,对“痛得左右乱晃”的接纳就成了负向的了;而认为例(27)中“黑丝绒旗袍”是本体词而非介体词的话,对“迎面过来”的接纳也就变成正向的了。
换一个角度,还可以从所接纳的不可能特征的类型对接纳方式进行观察:
(e)性质/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的接纳
以上所举的语例中不可能特征基本上都是性质上的不可能,而以下两例中——
(25)女人如果会喝酒能像抽水马桶似的哗哗地灌。(刘毅然《摇滚青年》)
(26)柏油路晒化了,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好像也要晒化。(老舍《骆驼祥子》)
例(25)的“女人”和“抽水马桶”都能“哗哗地灌”,但“抽水马桶”所能达到的程度是“女人”永远不可企及的,所以是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例(26)中的“铜牌”被“晒化”,对于太阳来说也是一种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虽然因为有“好象”的阻隔使不可能特征的接纳间接化而降低了“晒化”的程度。
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这些词语接受了不可能特征后,语义上必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上文已经指出,一个词能以哪些语义特征为性质上的不可能特征,决定于这个词具备怎样的必有特征;能以哪些语义特征为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决定于这个词的量限范围。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一个词的某一不可能特征如果转变为可能特征,必定会改变这个词的必有特征或量限范围。对性质上的不可能特征来说,“雾气”如果能在词外接受“碰着黄麻叶子”为可能特征,它词内必有特征集合中的“气体”必然会被“固体”所替代;而对于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来说,“太阳”如果能将“铺户门前的铜牌”“晒化”,那么“太阳”量限范围的上限一定扩展了。所以要从语言学上认识这些辞格,就必须看到,它们的使用都通过迫使词语接受某一或某些不可能特征而最终改变了这些词语的语义特征集合。
5.认知性辞格与表达性辞格
综上所述,可以看见我们讨论的这些认知性辞格的共同作用,就在于促使词语接受一些它们原先无法接受的不可能特征。如果没有不可能特征的接纳,即使有相同的语言形式,也不是我们所讨论的认知性辞格:
(27)这只杯子像花瓶一样又细又长。
(28)这只杯子像一只花瓶。
例(27)中的“又细又长”不是“杯子”的不可能特征,因而这个句子所用的修辞方式是出于对描绘的准确贴切以至于鲜明生动的需要而打的比方,而不是一个认知性的比喻,尽管它有着与比喻一样的语言形式。例(28)虽没有表明“杯子”与“瓶子”的联系发生在什么样的特征上,但我们很难设想“瓶子”的哪一种可能特征对“杯子”而言是不可能特征,所以看来例(28)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比喻。
一旦使用了不可能特征做标准来衡量认知性辞格,就可以发现传统修辞学在设立辞格的过程中至少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一种仅仅以增强表达上的效果为原则——着眼点是如何使表达更准确贴切,或是更鲜明生动,或是更突现强调,或是更简洁明了,而没有认知上的变化为基础。这类辞格可称之为表达性辞格,如仿词、排比、对偶、顶真等。另一种却以表现特殊的经验感受,也就是对外部事物的认知关系的改变,尽管传统修辞学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这类辞格我们已经称之为认知性辞格,如比拟、移就、拈连以及象征和通感涉及到的语言现象等。前者仅是语言形式的变异,后者则主要是语义内容的变异。然而在有些格式——主要是传统辞格的比喻、夸张和借代上,两类辞格交叉在了一起:
(29)沉寂的午后,阳光烤热了整个河岸,远处的村庄,远处那些低矮密集的房子发出烙铁般微红的颜色。(苏童《棉花地稻草人》)
(30)月光像半张锡纸裱在炕上。(梁晓声《喋血》)
在传统修辞学中例(29)和(30)都是比喻,然而前者的“微红”无论对本体词“房子”还是对介体词“烙铁”都是可能特征,因而此例和“这只杯子像花瓶一样又细又长”是表达性的而不是认知性的,是在打个比方而不是在进行真正的比喻;后者的“裱在炕上”是介体词“锡纸”的可能特征,但对本体词“月光”来说却是不可能特征,因而此例属认知性的。
(31)天热得发了狂。(老舍《骆驼祥子》)
(32)真把人困死了,将来胜利回国,我非睡它个八天八夜不可。
从传统修辞学的角度看这两例都是夸张,但它们其实是不同的现象。任何认知性辞格的运用都带有夸张的意味,只不过夸张的程度有强有弱而已。例(31)是认知性的,例(32)则没有带来任何认知性的变化,是个简单的表达性辞格。
所谓的借代都利用了接近或构成的关系,如果把借喻也包括在内,那么还利用了相似的关系。然而它们究竟是表达性的还是认知性的,往往不能直接从话语的语言意义判断出来,而是决定于人们出于什么目的使用它。像人们经常举例的“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有‘青岛’不喝‘北京’”、“‘大团结’发挥了诱人的魅力”之类,很明显是为了让话语表达更加简明而特征更加鲜明,其作用其实相当于一个“的”字结构,如“长着花白胡子的(那个人)”、“青岛牌的(啤酒)”等。一定要对这些词语进行借代的还原,也就是在理解中与被借代的对象对上号,辞格的运作才是成功的,借代一词的字面意义正反映了这一点。而例(23)(24)中,发话者并不希望受话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已从话语中消失的本体的过程中,而是力图改变受话者的认知习惯,引导他们按认知处理介体“太阳”、“黑丝绒旗袍”的方式来处理本应以“铜锣”、“着黑丝绒旗袍的女子”、“有油腻胸膛的男人”方式处理的对象。认知关系的改变正体现为后者已经被同一为前者。
6.两种辞格与修辞研究的两种观念
认知性辞格与表达性辞格都是语言存在的事实,但它们的学术价值并不相同。表达性辞格没有触动人的认知和思维的深层次,仅仅把辞格看作是一种外在于语义内容的表达技巧,是一种为获得最佳表达效果的语言加工形式,是装饰性的而非本体性的——最流行的说法是:同一思想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而这些表达形式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表达效果。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提法与此正是一脉相通的。这就好比造一座房子要坚固实用,没有任何瑕疵隐患,这是消极修辞的职责;而这座房子造好后可以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装饰——涂上不同的颜色,贴上不同的墙砖,雕出不同的花纹,这是积极修辞,其中主要是辞格的职责。这种把语言表达割裂为本体部分和修饰部分而又自甘于修饰部分的做法,使得传统修辞学永远将自己放逐在学术殿堂之外,满足于一些雕虫小技的寻寻觅觅。其实在现代思维观念的大背景下,单纯的修饰观念早被抛弃,功能即形式这种认为本体与外部形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建筑学。建筑的本体是功能,而游离于功能之外的形式无论多么绚丽多姿都是毫无意义的。因而一门学科如果将自己的价值完全建立在这些雕虫小技上,其生命力和学术价值是可想而知的。
而认知性辞格所体现的观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概念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在通常的认知方式之外,人还拥有其它的认知方式,它导致人的认知经验发生变化。通常的语言形式适应于通常的认知方式,当认知经验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原先的语言形式无法适应它时,认知性辞格所代表的语言形式变化就出现了。认识性辞格不是随意点缀的装饰品,它是认识关系的改变与语言形式改变的统一体。而且更重要的是,通常的认知方式不能导致创造性思维,而认识中的创造性因素就最原始、最直接地体现在认知性辞格的语言变化中。认知性辞格的使用能力是人的语言能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能正常使用自己母语的人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说出一个精彩的比喻来,儿童尤其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创造性本能最早寻找到的释放口恐怕就是认知性辞格的运用,而在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中,创造性思路往往就是直接通过认知性辞格的运用或通过与之类似的认知活动而萌生的。近年来修辞学之外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文艺学对隐喻的研究正集中在这一点上,人的思维是隐喻的这一论断不是对思维所有侧面的概括,而是集中表述了其中的创造性的因素。因而反过来人运用认知性辞格的能力又是人创造力迸发的诱导因素,关注学生运用认知性辞格的状况也就是关注他的创造潜力。
不过认话性辞格与表达性辞格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可分的界限,认知性辞格往往也可以作为表达性辞格使用。因而缺乏对认知性辞格的强烈意讽,即使面对认知性辞格也会滑入后者的研究思路。
认知性辞格运用的稳定形式,一般会自然地转化为表达性的。认知性辞格既然是创造性因素的体现,而创造必定是一次性的,这就造成了认知性辞格运用的一次性特点。也就是说我们若在一定的语境中出于一定的意图使用了某认知性辞格,形成了一段特定的话语,确切地反映了我们某种认知经验的变化,而在另一语境中出于另外的意图我们若再使用这一话语,很可能原先那种由于经验变化而造成的强烈的、新鲜的体验不会再重复出现,认知性辞格也就转化为普通的表达性辞格。例如第一次将桌子的支撑物称为“桌腿”,将声音的频率高称为“尖”,可想而知一定会因为触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认知习惯,而引起从人或动物的角度重新认识司空见惯的桌子,以及将听觉现象视觉化的新鲜感受。然而生活中占优势的毕竟是习惯性的理性认知方式,认知关系的突变,特殊体验的产生依赖于词语新鲜组合的强大冲击力。一旦我们从刹那间新鲜感受的冲动中苏醒过来而再次面临已经熟稔的词语组合,已经接种过预防疫苗的理性认识方式完全有力量抵御这已经不再强大的冲击力。除了能带来一定的生动感外这些组合已经不再能触动我们的意识深层,尽管它们曾经是认知性辞格的产物。所以像“货币持续疲软”、“亚洲货币患上软骨病”之类的词语组合实际上被我们作为表达性辞格而不是认知性辞格来使用的。它们的使用频率如果继续保持下去,以至于因辞格运用而产生的意义稳定下来成了该词语的一个义项,这时词语的使用不仅不会引起认识关系的变化,连表达性辞格应有的效果也不会产生——有谁在使用“桌腿”一词时还会把它与人或动物的下肢联系在一起呢?除非我们去追溯语源,设想自己处在原初的新鲜状态中。
更多的情况下,认知性的辞格被人为地理解为表达性辞格。传统的修辞学把目光局限在表达性辞格中,而语言实践中尤其是文学语言中大量精彩的辞格实例都是认知性的。于是当这些精彩的实例进入修辞教学和修辞研究的视野时,势必会被表达性辞格的理解模式校正和曲解,出现了修辞学还原的现象。当受话者因为在激情中深信不疑地觉得有一个可能世界,在这里“夜和│失明的野藤│还在那里摸索着│碑上的字迹”,或者真诚地看见了“一只只疲倦的手中│升起低沉的乌云”而领略到诗的意味时,辞格却用冷静而平庸的口吻说,这是拟人手法,“夜”和“野藤”本来无法“摸索”,这里不过是把物当人写了;而“低沉的乌云”是一个隐喻,升起的不过是与乌云有相似点的纸烟的烟罢了……辞格无非是起了把感受逻辑还原为常识逻辑的作用,还原工作一旦完成,诗的可能世界也就消失殆尽了。确实,如果把比喻仅仅理解为“描写事物或说明道理时,用同它有相似点的别的事物或道理来打比方”,借代就是“换名”,就是“不直说某人或某事物的名称,借用同它密切相关的名称去代替”……而不去探索它们背后的认知关系的变化,那么再精彩的实例也将被扭曲成平庸的技术操作。
7.结语
表达性辞格与认知性辞格的区分其实是相对性的,如果停留在话语表层的表达效果上,一切辞格都是表达性的,我们所讨论的认知性辞格在传统修辞学中就都被处理为表达性辞性。然而表达效果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一旦追索到了原因,我们就能在一个更为深刻的解释性层面把握这种表达效果以及导致效果产生的语言形式,认知性辞格就是这样被概括出来的——它以它特殊的表达效果引起了们的注意,但我们并不满足于效果的本身,而是发现了效果的产生是因为认知关系的改变,并且进一步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从语言学上将认识关系改变导致的辞格特征归结为对不可能特征的接纳。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统一的理论和方法,将这一类辞格系统化。
由此看来,表达性辞格与认知性辞格是不同认知层次上的概念。前者都是由常识观察而产生,未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处理的表面现象,传统修辞学就停留在这一层次上。而辞格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可以比照认知性辞格的研究方法,在各种表达性辞格的背后寻找表达效果产生的原因,以及适合它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形成与认知性辞格平行的、具有理论解释力的深层次上的辞格。一旦所有的表达性辞格都被这样化解完了,整个辞格体系也就能建立起来了,当然还需要在各种解释性原因之间找到共同的支配因素,以及统一的语言学方法。
收稿日期:2001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