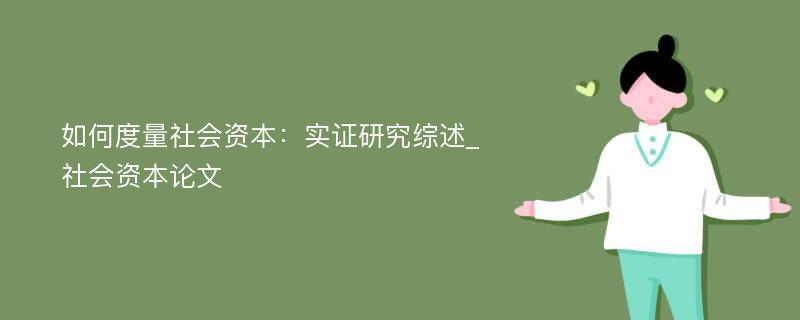
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测量论文,资本论文,经验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围绕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他的相关争论也日臻激烈,使得研究者对如何正确使用此概念大感困惑。其实要理清社会资本的理论概念,有一种简单可行的切入方法,那就是从理清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入手。(注:Portes,A.,1998,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4,pp.1~24.)在经验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社会现象的测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只有通过一定概念化和操作化的方式,把要研究的社会现象转化成一系列可度量的概念和指标,才可能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的分析研究。鉴于社会的复杂性,要对社会现象进行测量是非常困难的。卡普兰曾将测量对象分为三类:一类是可以直接观察的事物,另一类是不能直接观察,但可以通过间接方式进行观察的事物,第三类是从理论中产生的建构(construct),它产生于观察,但无法被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中观察到。(注:Kaplan,1964.)按照这个标准来划分,社会资本应届于第三类测量的对象,它是社会科学家们从社会生活中总结和归纳出的一种理论建构。因此在讨论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之前,首先必须对这一概念的理论建构与层次有所了解。
“社会资本”概念的层次
自从“社会资本”概念被引入学术研究以来,它表现出的强大解释力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社会资本”之所以具有强大解释力,部分原因在于其概念的定义比较宽泛,在不同研究中它可以有不同的含义。按照科尔曼(注:Coleman,1990,pp.302~304.)的定义,社会资本首先是社会结构中的“某些方面”,或是有助于“做成某事”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其次,它是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或是关系的社会结构而被创造出来的;最后,它产生了行动,而这些行动可以带来资源。后来的研究者们出于不同研究目标,又对这一定义作了许多引申和解读。布朗(注:Brown,1997.)将这些引申总结为三大类——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以及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微观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发现个人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通向所需资源——如信息、工作机会、知识、影响、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的途径,(注:Granovetter,1973;Erickson,2001;Baker,1994;Bian,1997;Uzzi,1996.)并区分了微观社会资本的三种构成形式——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使用。(注:Lin,2001.)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包括个人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注:Lin,2001.)而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关注的则是在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
与布朗这种三层次分类方法不同的是,阿德勒等(注:Adler & Kwon,2002.)采取了一种两分的分类方法。他们将微观层次和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合称为“外部社会资本”,因为它产生于某一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外部资源。而宏观社会资本则被他们称为“内部社会资本”,因为它形成于行动者(群体)内部的关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前者归属于个人而且服务于个人的私人利益,因此被列纳等(注:Leana & Van Bnren,1999.)归为一种“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后者则正相反,它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因为它归属于某一群体,而且服务于该群体的公共利益。
正因为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经验研究中,他们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本文中,我们根据阿德勒和列纳等人的概念,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社会资本”以及严集体社会资本”两种类别。前者即所谓的外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除了微观的个人关系及这些关系中所蕴涵的资源外,也包括个人所占有的网络结构位置能带来的资源。后者则是内部社会资本或公共物品,除了宏观的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结与互信外,也包括群体的结构方式是否可以促成集体行动并创造资源。
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
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注:Lin,2001.)在经验研究中,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几乎都集中于对个人社会网络状况的测量。社会网络分析是一套分析社会结构的理论和方法,其基本观点是将个人或组织之间的社会联系所构成的系统视为一个个“网络”,并认为整个社会就是由这些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注:Scott,1991.)研究者们在进行网络分析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指标、概念和分析方法,而对个人社会资本的测量在很大程度上就直接借助了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相关指标。目前测量个体层次社会资本时,研究者主要运用了“个体中心网络”(ego centered network)分析方法,个体网络可以视为整体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局部,它考察的是以每一个被研究者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网络情况。(注:Scott,1991.)
在经验研究中,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基本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调用(accessible)的资源总体的测量,这种方法重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mobilized)的社会资本情况,这种测量法侧重于个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情况。(注:Lin,1999;Zhao,2002.)
1.测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
(1)网络成员的生成方法
个体中心网研究的是以被调查者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网络情况,要了解这一网络成员的情况,必须确定网络成员的“生成”(generate)方法。在研究微观社会资本时,研究者主要采用的生成方法分别是提名生成法和位置生成法。
A.提名生成法(name-generator)提名生成法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具体做法是根据研究的要求,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相互关系等信息,关注网络社会资本情况的研究者们可以根据网络成员的相关信息,对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情况进行测量。这种方法在个体中心网的研究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因此,它也常被用来对个体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注:Campbell,Marsden & Hurlbet,1986;De Graaf & Flap,1988;Boxman,De Graaf & Flap,1991.)但以提名生成法作为社会资本测量工具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它的网络边界不易确定,而且被调查者更可能提出与自己关系较强的名单,弱关系容易被遗漏,从而有可能造成研究的偏差。(注:Lin,1999.)
B.位置生成法(position-generator)这种方法的着眼点不在于考察被调查者的具体网络成员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主要在于考察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这种测量方法假设社会资源是按照社会地位高低呈金字塔型分布于社会之中的,每一个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性地位。因此,通过对被研究者网络成员中出现的结构性地位的了解,就可以对其拥有社会资本的情况作出大致的测量。具体方法是使用一个或几个包含有若干标志社会地位的职业类型或工作单位类型等的量表。在调查中,首先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人符合表中所描述的特征,然后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然后用这些指标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情况。
位置生成法的优点在于它是内容无涉的和角色/位置中立的,同时它更少涉及到个人的隐私,因而在实际操作中较之提名法更为简便。(注:Lin,1999.)此外,这种方法还能较准确地测量出网络中不同地位和不同关系所提供的资源情况,避免了提名生成法集中于强关系的问题。它的缺陷主要是只能测量社会资本,无法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的具体构成情况,例如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无法通过该方法测量出来。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网络的结构本身(如网络的规模、密度等)即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希望对它也加以测量时,位置生成法就会表现出不足之处。
(2)使用的网络类型
个体中心的社会网络可以根据网络所涉及的不同社会关系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有的研究者关心的是与被调查者讨论重要问题的社会关系,他们重点研究的是“讨论网”(discussion network)的情况;有的研究者关心的是与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互动或交换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研究重点是“互动网”(interaction network)或称“交换网”(exchange network)的情况。还有对于个体“支持网”(support network)的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为被调查者提供物质上或精神上的支持,帮助被调查者应付生活中的困难与危机的社会关系情况。在关于个体社会资本的经验调查中,以上网络类型几乎都被研究者使用过。(注:Burt,1992;边燕杰、李煜,2001;Reingold,1999。)如果从定义上看,交换/互动网络和支持网络的内容似乎更接近于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研究出发点,因此可能更适合于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
(3)使用的网络指标
在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分析网络规模、结构、构成元素的较成熟的指标。但应认识到,并非所有的指标都适用于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因此,我们在利用网络资料来研究社会资本的时候,就需进一步确定:社会网络的哪些内容可以用来测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
布迪厄曾经指出,个人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地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二是网络中每个成员“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的多少”。(注:Bourdieu,1986,pp.241~258.)后来的研究者在测量社会资本时,基本上就是从个人网络的规模(结构)和网络中嵌入的资源数量这两个方面来着手进行的。首先是描述网络结构的指标,如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多少)、网络的成分(由哪些类型的成员构成)以及网络的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等。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假设,如网络规模较大、网络中弱关系所占比重较大以及网络密度较高的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可能更为丰富,并在经验研究中进行了验证。(注:Montgomery,1992;Lin,1999;边燕杰、李煜,2001;赵延东,2003。)其次是反映网络中嵌入资源的指标,在这一问题上,前面提到的位置生成法具有特殊的优势,它可以有效地测度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资源数量的多少。具体方法在前面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除了在上述不同形态的社会网络中拥有网络成员的规模以及网络成员拥有的资源外,个体在这些网络中占据的结构位置也具有带来资源的能力,而尤以下述两种位置最为重要:
A.中心位置(central positions)网络中心位置可以提供与群体中其他成员较好的联系。中心位置所传递的或是正式的权力,或是非正式的社会影响,(注:Brass & Burkhart,1992.)由中心位置带来的资源会创造出更好地控制外部环境并减少不确定性的机会,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处于中心位置的人是更值得信赖的。
B.居间位置(go-between positions)咨询或建议关系一般包含了信息的流动和知识的传播,因此在建议网中处于居间位置的个人可以及时地获取重要的信息和知识。(注:Luo,Chi & Lin,2002.)与此同时,交换此类社会资源还可以在交换双方之间产生信任。正如布劳(注:Blau,1964.)指出的,在社会交换中,个人不能预期得到实时的回报,因此他(她)必须寄希望于对方的善意并预期能在未来得到回报。在一系列成功的社会交换过程中,交换双方最终会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由此可以推测:在一个网络中的居间位置更可能产生社会资本。
综上所述,在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时,网络的结构、个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以及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都应是可供选择的测量指标。
2.测量个人“使用的社会资本”
在测量人们在某种工具性行动过程中所实际使用的社会资本时,研究者们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对于非正式网络途径的选择、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以及关系人的特征。
(1)对非正式网络途径的使用
在求职过程中,人们可以选择的求职途径可分为正式途径和非正式途径两种。前者包括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机构、报纸广告以及自己到单位面试等方式寻找工作,而后者则指通过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找新工作。这种分类方法最早由格拉诺维特(1973)提出,后被研究者们普遍采用。他们都认为,凡在求职过程中使用了非正式网络途径的,均可视为一种对社会资本的使用。(注:Lin;Ensel & Vaughn,1981;Marsden & Hurlbert,1988;Bian,1997.)
(2)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
格拉诺维特(1973)最早在研究中区分了网络中流动的资源,他指出,在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可分为“信息”(information)和“影响”(influence)两大类,前者指的是个人可以从网络中获得对自己行动(如找工作等)有价值的信息,而后者则指个人可从网络成员那里得到能直接帮助自己达到行动目的的实质帮助。这一分类法在边燕杰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挥,他研究了关系强度与提供资源之间的关系,认为有更高信任度和紧密度的强关系更有可能提供“影响”或“人情”,而弱关系则更可能提供“信息”,对网络中流动资源情况的考察也构成了测量使用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注:Bian,1997;边燕杰、张文宏,2001;Zhao,2002。)
(3)关系人的特征
关系人(contact)指的是能够在个人的工具行动过程中为其提供各项资源的网络成员。对关系人特征的考察一直是研究社会资本利用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A.关系人的关系强度 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中,格拉诺维特(1973)提出的“弱关系的力量”已成为一个经典命题,他指出由于弱关系更可能带来异质性的信息,因此它的作用可能比强关系更有力。后来的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尽管结果并不一致,但人们普遍认为,关系人的关系强度构成了社会资本测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格拉诺维特曾经明确指出,关系的强度是一个多维度指标,“是概述关系特征的时间量、情感紧密性、熟识程度(相互信任)和交互服务的(线性)复合体”,(注:Granovetter,1973,p.1361.)这就意味着对关系强度的测量不应采取单一指标的方法。但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者为简便起见,都在经验研究中采取了单一指标测量方法。常用的方法有互动法和角色法等。互动法是根据关系人与本人交往的频度来测量关系强度,交往越频繁,则关系越强;角色法则是根据网络成员与被研究者的角色关系来判断关系强度,如“朋友”被定义为强关系,而“熟人”则被定义为弱关系。在相关研究中,角色关系法由于简便易行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注:Lin;Ensel & Vaughn,1981;Lin & Dumin,1986;Marsden & Hurlhert,1988;Bian,1997.)
这种单一指标方法受到了韦格纳(注:Wegner,1991.)的抨击,他指出,运用角色关系来判断关系强弱的方法虽然简便易行,但却失之粗略。在研究中,他尝试着将格拉诺维特提出的多重指标测量法付诸实践,使用了以下一些指标:a.关系人的“角色类型”;b.关系人与被调查者的社会距离;c.关系人与被调查者认识的时间长短;d.关系人与被调查者的交往频繁程度;e.关系人与被调查者共同从事社会活动的情况;f.关系人对被调查者的关心程度。随后他又通过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将上述指标加以合并简化,以最后得到的几个本质因子来代表关系强度。
B.关系人的社会地位特征 按照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注:Lin,1982.)关系人所处的社会地位越高,其拥有的社会资源也就越丰富,能够提供的帮助也就越大。因此,对关系人社会地位的考察是了解被调查者使用社会资本情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表现为职业地位,因此对社会地位的测量一般是通过考察关系人的职业声望或职业地位得分等指标来进行的。研究结果大都证明,关系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对于求职者求职结果的积极影响就越大。(注:Lin;Ensel & Vaughn,1981;Volker & Flap,1996;Wegner,1991;Bian,1997.)
对集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
早期的研究者在考察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时,一般都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蕴藏于个人网络之中的财富。但自从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社会资本的集体层面,即不仅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个人拥有的资源,而且将其视为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整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和财富。这样,他们在测量社会资本时便不再拘泥于对个人网络情况的考察,而是将视野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
普特南(Putnam)是较早开始研究集体社会资本的学者,他在说明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减时,从两个方面测量了美国的(集体)社会资本:首先是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情况,用投票率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来表示;其次是美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用美国参加各种社会组织的人数来表示。他根据这种测量的结果,得出了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衰减的结论。(注:Putnam,1995.)这种测量方式受到了许多批评,如帕克斯通(注:Paxton,1999,p.101.)即指出,公民参与行为应该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非其构成形式。
根据科尔曼的定义,社会资本有三个组成元素:第一是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第二是作为这些“方面”载体的一种(或一组)社会关系;第三是由此生成的行动和资源。(注:Coleman,1990.)由于这些结果必须是有利于群体成员的东西,而非由消极情感所导致的障碍,故阿德勒等声称善意(good will)——包括同情、信任和宽容等——是构成积极的社会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或组织可以得到的善意”,(注:Adler & Kwon,2002,p.23.)善意可以使人际之间的关系产生有利于行动的转变。福山也指出,信任是一种有助于“使人们在群体或组织中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因素,(注:Fukuyama,1996,p.10.)因而是集体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那些能产生信任的社会关系的集体才能使行动者精诚合作,并自愿地与他人交换资源,因此在大多数有关集体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信任都被作为善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帕克斯通(1999)在研究美国(集体)社会资本时直接使用“信任”术语的缘故。
帕克斯通对集体社会资本概念的构建由两个部分组成:个人之间的实际联结(association)以及一种包含了积极情感的“人际间的”(inter-subjective)联系或关系。实际联结是在个人与邻里、朋友及其参加的自愿组织的成员们所共同进行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而积极情感则可以导致两种属性:对同事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帕克斯通使用了美国全国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中三个问题的结果来反映对同事的信任(这三个问题分别询问被调查者对于他人的善良、公正和诚实的信任程度);与此同时,她使用了人们对于有组织宗教的信任、对于教育体制的信任以及对于政府的信任的调查结果来反映人们对制度的信任。
怀特利(注:Whiteley,1999.)在研究国家社会资本的起源时使用了一种稍有不同的策略。鉴于只有那些包含了善意的社会关系才可能产生出合作行动,他认为只有两种类型的信任才可能构成社会资本——对于个人(包括家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他人)的信任以及对于国家的信任,因此信任应该是测量社会资本的惟一要素。
厄普霍夫(注:Uphoff,1996.)则提出了另一种分类测量方法,将集体社会资本分解为“结构性(structural)社会资本”和“认知性(cognitive)社会资本”两个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通过依靠规则、程序和先例建立起来的角色与社会网络来促进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它是相对客观的,表现为一种可见的形式,并可以通过群体的有意识行动来进行设计与改进。由于它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故可以直接观察到,而且容易改变或修正。而认知性社会资本则在共同的规范、价值观、态度与信仰的基础上引导人们走向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它反映的是人们的想法与感觉,因而更为主观。它是内在于个人的,驻留于人们的头脑中,故较难改变。
从以上综述可知,在测量集体层面社会资本时,研究者使用的指标集中于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这样几个方面,而这与测量个体层面社会资本使用的以社会网络为主的指标有相当大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差别正反映了社会理论中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之间存在的鸿沟。(注:Coleman,1990.)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们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正可以起到连通这两种不同层次社会资本测量的作用。正如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溯源到社会网络理论,以科尔曼、林南、格拉诺维特和博特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网络理论家们都分别在社会网络理论的框架内建构了微观和中观分析层次的社会资本概念,但是关系内容与网络结构等对于宏观层次社会资本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迄今有关网络结构的研究主要关注的还是作为“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的社会资本,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完全可能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分析。(注:Lin,1999;Adler & Kwon,2002.)这不仅能使我们在经验研究中更准确地测量社会资本,而且将有助于我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更清晰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