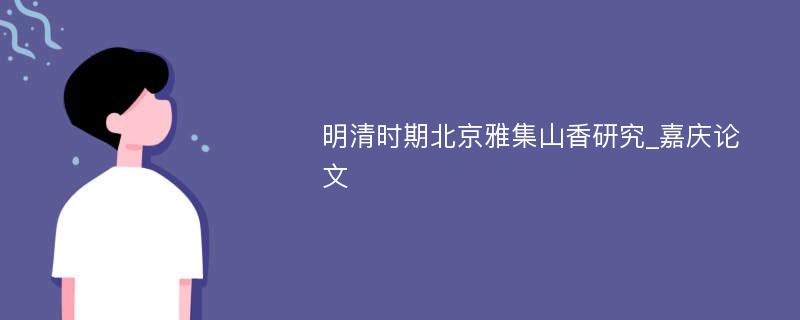
明清时期北京丫髻山的进香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北京论文,时期论文,丫髻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 [文章编号]1002-3054(2014)10-0098-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41010 一、背景、缘起与问题意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部分西方汉学研究者开始将进香研究作为中国宗教研究的新领域。①在此之前,家户宗教及社区宗教研究作为中国大众宗教研究的主体,进香研究被置于边缘位置。于君方、韩书瑞(Susan Naquin)、劳格文(John Lagerwey)等人的研究②更揭示了这样一点:中国大众宗教是社会各阶层共同享有的宗教实践,它构成了一个话语交织的场域。这个场域中允许一种多元文化的存在,并在历时性的维度内对多种意义进行叠加和复写(superscription)。就此而言,朝圣地及进香研究为探讨“第三领域”(the third realm)③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 中国学者对于进香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顾颉刚一行人对当时进香活动的考察就留下了丰富的民俗学及历史学资料。④社会学家李景汉及甘博(Sidney Gamble)调查亦留下了珍贵的资料。⑤在此时期,进香主要被视作一种民间风俗的典型例子,对其研究的方式以采录一手资料为主。此后,中国的进香研究一度沉寂数十年,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民俗学、历史学同仁重拾该议题,并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著作。⑥ 可以说,对于妙峰山及相关泰山信仰的研究一时间汗牛充栋,韩书瑞有关妙峰山的文章更为这股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①在其对北京寺庙与宗教生活研究的专著中,妙峰山更位于显要的位置,⑦似乎妙峰山成为中国北方地区进香研究的代言。然而,正如熟悉北京进香史的学者们所知道的那样,至迟于清乾隆年间,北京东部的丫髻山与妙峰山在民间并称“二山”,它们都是北京地区朝顶进香的圣地。但是,丫髻山的历史在上述论著中却显得支离破碎,它经常作为妙峰山的一种陪衬⑧,其形象变得模糊而不甚重要。 事实上,丫髻山作为京畿朝顶圣地还要略早于妙峰山,它在近代京畿民众的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⑨本文旨在借助现存碑刻(有官方碑刻、民间碑刻等)、口头传统、地方志、宗教经卷、文人小说及田野调查等多种资料勾勒出明清两代的丫髻山进香史,并将其置于京畿地区社会史的脉络之中,以此观照宗教在帝制晚期中国人公共生活中的角色。笔者认为,一部丫髻山的进香史,便是明清两代京畿地区社会变迁的缩影。仅将朝顶进香视作民俗宗教的研究领域并不足以展现中国宗教史的丰富内涵,它构成了帝制晚期中国人公共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代表着社会各阶层共同享有的宗教现象。 此外,本文在对丫髻山进香史进行完整叙述后,希冀对韩书瑞与吴效群的“富香-穷香”框架提出异议。受到汉学家普意雅(Georges Bouillard)的影响,两人在论及丫髻山与妙峰山时以“富香”描述丫髻山,而以“穷香”为妙峰山定性,并据此突出丫髻山与妙峰山进香群体之社会构成的不同。①(P333-377),⑥韩书瑞更认为,朝顶的参与削弱了丫髻山和五顶⑩的民间性,暗示这与它们日后的衰微密切相关: (译文)这种情况或许也是真实的,在皇室送礼、拜访使得丫髻山和五顶庙被纳入国家轨道时,这些庙在民间的地位却都在下降。皇室成员的来临毕竟赶走了普通香客,皇室的捐助排斥了社区的支持,朝廷所起的作用或许也代替了地方的管理者。而妙峰山则远离权力中心,也不是其路经之地,没有受到这种资助的阻碍,它的香会成倍增加。因而这就使得金顶在取代五顶的情况下获得胜利,这是因为民众倾向于不受官方和僧人注意的庙宇。①(11) 实际上,丫髻山与妙峰山的进香史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在“五顶二山”之中,妙峰山是较为晚近的,它于乾隆年间逐渐兴盛,但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其主峰“金顶”的位置显然要胜过其他的庙。①(P333-377)相比之下,明代就已存在的五顶,大多在清中叶以后便日趋衰落。也就是说,“五顶二山”的格局到了晚清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通过对丫髻山的考察可知,丫髻山的进香历史中有过两个香火的巅峰时期,第一个时期在康乾时期。在这一时期,皇室的捐助和驾临确实给予了丫髻山极大的支持。然而,透过对于碑刻的考察可知,最晚于道光年间,丫髻山进香的主要力量已经重新开始转向民间。在这个时期,香河、天津一带的香会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甚至创立了自己的家乡神王二奶奶。 光绪年间是丫髻山香火兴盛的另一个高峰期,这与民间社会对于丫髻山进香的支持密切相关。因此,将丫髻山界定为“富香”是有待斟酌的,在其整个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民间与皇室(不一定是代表着国家)的力量交相主导,最初由民间兴起的香火后来得到皇室的支持,最后又回归到了民间社会作为主导的状态。下面我们看看这些历史脉络在地方史志及碑刻中是怎样呈现的(本文的碑刻注释使用英文字母编号,其对应关系参见文末)。 二、晚明时期的丫髻山(1521-1643) 丫髻山是北京东部一座不高的小山,有双峰,形如丫髻,当地人名之曰“大山庙”或“东大山”。它坐落于现今平谷区境内的刘家店乡。清代以来,隶属于怀柔县。丫髻山上有较完整的庙宇群。这些庙宇群的大规模修建主要是在清代康熙年间,中心庙宇是天仙圣母宫,以碧霞元君为主神。 在明代嘉靖年间以前,丫髻山上仅有三间不起眼的碧霞元君庙,具体始建的年代已不可考。近代最早可见的修缮记载出现在康熙《怀柔县志》,它记载了明嘉靖中,王姓老媪发愿修建庙殿的事迹。(12)(P50) 至迟在明嘉靖年间,丫髻山的香火来源主要依靠民间。在王姓老媪的带动和众多施者的捐助下,铁瓦殿才得以完成。在此时期,已有庙会,正日为四月十八,会期五天。在此之后,丫髻山的民间香火似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近来出土的嘉靖年间“敕封护国天仙宫匾额”证实了这点。这对万历以后丫髻山的兴盛也许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至明万历年间,丫髻山的碧霞元君庙已经在北京颇有影响了。万历年间的《灵应泰山娘娘宝卷》中已将丫髻山列入泰山娘娘的重要行宫之一,尊之为“北顶”,并明确提及丫髻山娘娘即泰山娘娘之分身,以考察人间善恶,惩恶扬善。(13) 丫髻山在民间的名气吸引了当时宫中宦官党羽的注意,有人便建议在丫髻山为魏忠贤修建“崇功祠”。而未等该祠建成,魏忠贤便已失势。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丫髻山天仙庙碑记》中将这段历史描述为天仙圣母福庇善类、祸族佥邪的神功: 当明之季,有台谏欲建魏珰祠于其山者,赐名崇功祠,未成而珰败。人咸称元君褫其魄而速之诛,其威万英爽类如此。士民因钦崇奉祀,笔其事于石,以志元君之福庇善类、祸族佥邪,神功乌可没哉?(YJSBK KX07) 三、康熙-乾隆年间:丫髻山进香的繁盛(1662-1796) 有清一代,丫髻山的香火由康熙年间起逐渐兴盛,并达到顶峰。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明清易代之时的丫髻山进香已不可考。在天启(1621-1627)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近70年的时间内,丫髻山是否还存在进香活动?它是否受到明清易代的政治冲击?从清代康熙年间最早的两块民碑来看,至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依然有一些民间进香团体的朝顶活动(YJSBK KX01、YJSBK KX03)。这一时期的丫髻山仍主要依靠民间香火供奉,还未见皇室力量或官方力量的涉足。 此后,康熙驾临丫髻山,(14)(P50-52)这为丫髻山进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期间,丫髻山的庙宇群日渐完善,于康熙六十年(1721)达到了历史上的极盛。康熙四十三年(1704)及五十五年(1716),康熙曾两次驾临丫髻山,这为丫髻山带来了大量的赐金和赐额及题诗。(12)(P50-52)然而,康熙对丫髻山娘娘的合法性问题却是避而不谈的。1713年一块记载着丫髻山玉皇庙修建的御制碑中,康熙对大帝之仁爱斯民大加歌颂,却对碧霞元君甚至民间所谓的丫髻山娘娘不置一词(YJSBK KX11)。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康熙关注的是(玉皇)大帝,而民间关注的依然是丫髻山娘娘。然而,只要皇帝(及皇室)对于丫髻山进香的态度不是明确禁止,对丫髻山娘娘的崇拜活动便拥有着很大的空间。在康熙年间现存的十四块碑文中,民碑占了十一块。这些民碑的立碑者主要是各种香会,全部为文会(15)(YJSBK KX06\YJSBK KX09\YJSBK KX12\YJSBK KX13\YJSBK KX14)。 康熙四十三年(1704)可以视作丫髻山进香的一个转折点。现存康熙四十三年以前的丫髻山碑刻只有三块,全为民碑。康熙四十三年皇帝亲临之后,民碑及官碑的数量均有巨大的增加。文人阶层对于丫髻山娘娘的表述也发生了转变。在康熙四十三年之前,文人对于丫髻山进香的性质是表示疑虑的。康熙四十三年后,大量碑文之中开始歌颂丫髻山娘娘(天仙圣母)的神品,并讲述了若干种她的成神故事(YJSBK KX04/YJSBK KX07/YJSBK KX12/YJSBK KX13)。 康熙四十三年(1704)至康熙六十年(1721)的十七年间,在皇室、士人、普通香客、道士群体(16)(P189-195)的共同作用下,丫髻山的庙宇群规模及进香活动达到极盛。在康熙六十年《怀柔县志》的丫髻山图中,娘娘宫、玉皇顶、钟鼓楼、三皇殿、行宫、万寿亭、巡山庙、三宫庙、菩萨殿、回香亭、东岳庙、灵官殿、观音堂、虫王庙、紫霄宫均已建成。(12)(P50-51) 康熙五十二年始,皇室每十年要去丫髻山进香一次,丫髻山由此真正取得了“畿东泰岱”的地位(YJSBK YZ01)。需要注意的是,皇室诣香的主神为东岳大帝,并非民间所追捧的丫髻山娘娘。但从这一时期的碑刻材料可知,丫髻山娘娘还是备受民间香会及香客的推崇。 现存的雍正朝(1723-1735)丫髻山碑刻只有一通,立碑者为国子监祭酒王图炳(YJSBKYZ01)。按照韩书瑞的说法,这位皇帝对于北京进香朝山的行为较之前朝是更为容忍的。⑧(P556)他对民人于名山寺庙中礼拜的行为是支持的,且着礼部和直隶巡抚对于“其禁止太过之处”应查明,在《雍正上谕内阁》中可以看出他对丫髻山进香的态度。(17) 然而,为什么现今可见的雍正朝民间进香碑刻一通都没有?(不排除毁坏过于严重的情况。)难道是该时期他对京城至丫髻山沿线的驿馆征收税款的政策,阻碍了进香团体的活跃?⑧(P556) 乾隆对于北京民众对碧霞元君的热情是默许的。他登基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了近两个世纪的香税(1736)。(18)这直接导致了乾隆年间北京碧霞元君庙的剧增,向这些庙进香的香会也越来越多了。现存的丫髻山碑刻中,乾隆年间的有十三通,数量与康熙年间的相近,均为民碑。 从碑文来看,这一时期前往丫髻山进香的香会在数量、种类及覆盖范围上较之前有着极大的发展。香会之间的分工愈加细致,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香会名称,如“报恩源留放堂老会”“如意攒香供献鲜花寿桃胜会”“如意掸尘净炉老会”“福寿香茶斗香老会”“四顶源流子孙老会”“永远帘子老会”“龙灯老会”等(YJSBK QL01\YJSBK QL02\YJSBK QL03\YJSBK QL07\YJSBK QL08\YJSBK QL09\YJSBK QL11)。 这些香会基本上来自北京内城及内城城门周边,如东安门(YJSBK QL01)、朝阳关门(YJSBK QL03)、朝阳门外(YJSBK QL07)、正阳门内(YJSBK QL08)、地安门内(YJSBK QL09)、东直门外三条中街(YJSBK QL11)。乾隆时期,来丫髻山进香朝山的文会最远达至顺天府的大宛二县(YJSBK QL12)、大兴县(YJSBK QL07)和怀柔县(YJSBK QL06)等地方。 丫髻山进香团体的组成人员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既有以旗人为主的进香队伍(YJSBK QL02),也有以汉人为主的团体(YJSBK QL04\YJSBK QL08),更有旗人与汉人杂处的(YJSBK QL12)。这些香会之中,女性成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的甚至全部成员皆为女性(YJSBK QL04)。多数的香会都是男女共处,且女性成员在其中的比重不可小觑,如纯善源溜老会(YJSBK QL07)、四顶源流子孙老会(YJSBK QL08)、龙灯老会(YJSBK QL12)。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至迟于乾隆末年,丫髻山庙会已经发展至其鼎盛时期。在乾隆六十年(1795)的一块碑文中,曾将丫髻山与普陀山、天台等名山宝刹并举(YJSBK QL13)。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丫髻山已经是京城著名的进香中心了。它较之五顶及后起的妙峰山,尽管离京城相对较远,却越来越多地卷入北京市民(包括城乡结合地带)的公众生活之中。这从该时期香会的构成上可见一斑。 丫髻山在乾隆年间的繁盛亦反映在乾隆至嘉庆时期的三部文人笔记小说之中。(18)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及袁枚的《新齐谐》均记述了“孝女”的故事。丫髻山在其中以其灵验、繁盛的面貌出现,作为孝女故事的背景。丫髻山的“上头香”被屡次提及,它专属于京城的官宦阶层;在另一部笔记小说《梦厂杂著》中,丫髻山娘娘更是被塑造为一个惩恶扬善的灵爽之神。 然而,即便在丫髻山最为兴盛的时期,丫髻山娘娘的信仰范围也并未超出北京城乡的范围。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宫中的宦官、旗民、妇女群体在进香人群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一时期朝廷及王室进香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如前文所述,康熙帝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的两次驾临,最终使得丫髻山成为其政治表演的重要场所之一。自康熙以降,内务府有请派拈香人的体例,这些人或皇子,或亲、郡王。宫廷中的女性成员更是热衷于来丫髻山进香。(19)(P90-91) 乾隆曾三次驾临丫髻山,这为丫髻山留下了数个御制题额(对联)和两首御制诗。乾隆七年(1742),乾隆皇帝亲自到丫髻山进香,(20)为丫髻山的诸殿题额。(21)乾隆十二年(1747)及十八年(1753),乾隆为丫髻山留下了两首御制诗。(21) 这些赏赐和驾临极大地刺激了北京的碧霞元君信仰。然而,我们不应该机械地认为皇帝是额外偏好某一处碧霞元君庙的。事实上,他们对所有的庙宇都很慷慨大方。(22) 此外,切不要认为这种慷慨就真的使丫髻山和五顶的碧霞庙真正纳入到国家的轨道之中。换言之,不要以为皇室的资助便必然削弱了丫髻山的民间性。没有任何数据表明王室的参与驱走了民间的香客或香会,或者说宫廷机构取代了地方社区对于丫髻山的管理职能。康熙至乾隆一百余年的长时段内,丫髻山逐渐走向了鼎盛,这与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说,韩书瑞和吴效群等人对于“妙峰山(穷香)/丫髻山(富香)”的区分和界定是值得商榷的。 四、嘉庆—咸丰年间:丫髻山进香的衰落(1796-1861) 总体而言,嘉庆至咸丰朝的六十余年,丫髻山进香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衰颓之势。对丫髻山一山神灯兴衰的考察为这种衰颓提供了最直接的例证。乾隆二十四年(1759),京城德胜门内绦儿胡同的信士袁士库同妻钱氏为丫髻山娘娘顶捐募了一百零八盏金灯,并在山下置地七十五亩,用其租银作为补修金灯的费用。自此,丫髻山便有了“一山善人”灯会,该灯会以小灯排成“一山善人”四个字,为夜晚进香的香客引路(YJSBK QL05)。此后的五十余年中,该灯会逐渐衰落,分裂成两股。因其经费筹集困难,两股分别维系“一山”和“善人”二字灯。至嘉庆初年,虽然“一山”灯勉强维持下去,“善人”二字灯却已中断。直到嘉庆十三年(1808),王勋等信士的捐助才使得“善人”二字灯得以复燃。《一山善人灯会记事碑》记述了这一始末(YJSBK JQ01)。 嘉庆初年,长达七年的白莲教起义爆发了。在此之前,北京附近就有好几支白莲教派在活动,如老理会、大乘教、李五的荣华会、白阳教、红阳教等。(23)(P63-126)1813年,一股天理教起义的成员攻入紫禁城,另一股则意图拦杀从热河回程的嘉庆皇帝(此时,嘉庆皇帝就在离北京五十英里外的地方,那里临近丫髻山行宫)。(24)对于嘉庆皇帝而言,这是对他个人的极大冒犯,而且在离朝廷如此近的地方居然有这样的危险团伙存在简直是不能容忍的。 天理教起义事件之后,史料中未见对嘉庆皇帝亲临丫髻山的记载。但嘉庆皇帝曾十余次命当时在藩邸的旻宁(后来的道光皇帝)往丫髻山诣山瞻礼。在道光皇帝的这块御制碑中,简要提及了嘉庆朝丫髻山进香的情境,“四方之民,岁时祈报”(YJSBK DG01)。虽然对嘉庆朝丫髻山进香的数据掌握非常有限,但我们依然可以推测,该时期较之康乾时期的情形要冷清很多。仅存的那块嘉庆记事碑的立碑者也不是香会组织,而是捐募香火的信士(YJSBK JQ01)。 嘉庆至咸丰年间,前往丫髻山朝顶的北京香会越来越少已经成为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丫髻山娘娘信仰就此便淡出北京市民的宗教生活。事实上,直至20世纪,丫髻山娘娘仍然被奉祀在一些北京城内的公庙之中,一处位于北京东岳庙东院的丫髻山娘娘殿,(25)(P46)皇室女眷及年老体弱者在不便前往丫髻山的情况下便在此处进香;(26)(P39-41)一处是崇文门外的南药王庙,它被视为丫髻山娘娘的一处行宫;(24),(27)(P178)此外,在丫髻山的口头传统中,崇文门外南岗子天仙宫是丫髻山娘娘的娘家。该天仙宫的庙会会期与丫髻山在时间上衔接紧密,有的香客在丫髻山进香朝顶后会循例到此处谢香。(28) 五、晚清以降的丫髻山进香(1862-1937) 1838-1863年间有关丫髻山进香的历史记录已不可考。这是否意味着丫髻山进香在这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内就此中断?连年的战乱,使得丫髻山不再是那个太平盛世下的宠儿。当北京的皇室、达官显贵及京城的香客们逐步退出丫髻山舞台时,丫髻山进香又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自19世纪40年代,作为京畿进香中心的丫髻山开始与帝国的结构框架相疏离,并最终被重新纳入到民间社会的运作机制之中。这个历史过程是渐变的,历经约三十余年。1837年,道光皇帝的母亲特别关照过火灾后的丫髻山娘娘庙的重建,并参加了是年的开山典礼(YJSBK DG01)。(29)然而,这并未给丫髻山的香火带来多大的刺激,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是民间社会而非朝廷的眷顾为丫髻山的维系提供了必要的支持(YJSBK TZ01/YJSBK TZ02/YJSBK TZ03/YJSBK GX01/YJSBK GX02/YJSBK GX03/YJSBK GX04/YJSBK GX05/YJSBK GX06/YJSBK GX07/YJSBK GX08/YJSBK MG01/YJSBK MG02)。嬗变的进香群体赋予丫髻山新的内涵,他们在这里建构新的神祇,将丫髻山与他们的保护神和信仰——王二奶奶及四大门(30)信仰——穿凿附会。与之相应的,丫髻山娘娘正是在这种民间话语的作用下被得以重新塑造。 (一)京东的香会及王二奶奶:丫髻山的新主人 同治以来,丫髻山进香的主力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来自京都顺天府东路的香河和武清二县的香会后来居上,将丫髻山变成他们宣示地方权力及文化的场域。这个历史过程与天津人将妙峰山作为其表演舞台是基本同步的。(31) 同治年间,北京城的居民在丫髻山的舞台上变得愈发缄默。这时期三块存碑中,就有两块来自顺天府东路的香河和武清这两个县(YJSBK TZ01/YJSBK TZ02)。这些来自顺天府东路的信徒们基本上全为汉民,他们以地域组织为单位来丫髻山进香。较之康乾时期异质性的进香群体,这时期的丫髻山更像是香武二县社区集体仪式的一种延展。在一块碑文中,他们来自同一个村落(名为窝头村),是邻里、亲戚,也可能是农事的合作伙伴(YJSBK TZ01);在另一块碑文中,他们既有来自同一聚落(名为大后家湾)的乡邻,也有临近地区的信士组合(YJSBK TZ02)。 同治年间的丫髻山信仰基本全赖民间社会的支持。香河、武清二县在丫髻山的事务上初露锋芒,但直至同治后期,他们才独占丫髻山。住庙道士的募化和京郊各县的善人仍起着一些制衡的力量。同治十二年(1873)的一块碑文记载了这些社会力量对于丫髻山的捐助。他们以捐银置租生息,“以备每年干果素烛与人工之费”(YJSBK TZ03)。 晚清的丫髻山,在经济上更多地依靠民间信士的捐助。他们或是捐银置租生息(YJSBK TZ03),或是为丫髻山置香火地以租生息(YJSBK GX01/YJSBK GX02/YJSBK GX08)。这些信士多数并非北京城市居民,而是来自顺天府各县:顺天府大兴县、京东怀邑寅洞里、京东顺天府三河县。与此同时,北京城内的居民也并未完全从丫髻山的事务中退出。光绪十二年(1886)的一块碑文便表明,他们协力为丫髻山捐助香火钱(YJSBK GX02)。只是就同治以降的香会碑来看,京东的各县——香河、三河、宝坻、武清——确实成为了丫髻山进香中的中流砥柱(YJSBK TZ01/YJSBK TZ02/YJSBK GX03/YJSBK GX04/YJSBK GX05/YJSBK GX07)。至光绪时期,北京城的香会已经基本绝迹于丫髻山。 晚清以来,京东各县着实成为了丫髻山的新主人,他们更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塑造丫髻山。最晚于光绪十九年(1893),一位叫作王二奶奶的新兴地方女性神祇出现在丫髻山之上(YJSBKGX03)。她出身于香河县,以一个老婆子的形象出现。其性有仙根,作为丫髻山娘娘的忠实信徒,最后在丫髻山修成正果。并且,她被视作香河人的庇佑者(YJSBK GX03)。 这个新兴的地方性神祇在此后便稳稳地占据了丫髻山的庙堂。与丫髻山娘娘一样,她一同享用着丫髻山的香火。迄今,她的神像依然被供奉于碧霞元君殿后的斗姥宫中。来自香河的进香者们在四月五日前后,会先去拜谒昊天上帝、天仙圣母,次谒王奶奶懿座(YJSBK GX03)。此后,香河的进香者们不断将王二奶奶的形象地方化、个性化,使她俨然成为香河人在丫髻山的代言。香客们坚信,王二奶奶就是那个嘉靖朝的王姓老妪,是她发愿修建了丫髻山的铁瓦殿。(32) 东山奶奶(王二奶奶)在北京地区的四大门(或五大门(33))信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围绕这几种灵性动物的信仰和实践构成了中国北方民俗宗教的重要形式之一。香头(34)们普遍认为,丫髻山是天下四门仙家的总门,该处由王奶奶(王二奶奶)直接统御。而老娘娘(即丫髻山娘娘)又是王奶奶的直接上司。事实上,对于王奶奶和娘娘的敬奉,贯穿于四大门信仰中的各个环节。例如王奶奶在香头的完成典礼(跪表、赐号、安龛、开顶)中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降神和朝顶的重要对象。(35)(P25-26、P29、P42-67、P76-81) 丫髻山成为帝国晚期香头们获得职业认可和合法性的圣地。只有在丫髻山的娘娘驾前,京郊的香头们才最终完成入会的开顶仪式。(35)(P56-58)对于四大门的信仰者和香头来说,丫髻山是最为重要的圣山。这里成为他们每年定期朝顶的最佳去处。至迟于民国年间,丫髻山已经与天台山、妙峰山、里二寺、潭柘寺一同被这些香头们视为“五顶”。(36)因丫髻山的“老娘娘”与王二奶奶被描述为四大门的掌控者,其东南端的黄花岭被认为是四门仙家的总参修处,故丫髻山在这香头的“五顶”系统之中又最为核心。来丫髻山进香朝顶是这些香头和四大门信奉者们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典礼。香头的各“门”(分门别派)以坛口(37)为单位,组成“会”,每年定期向丫髻山朝顶进香。香头在这些会中扮演着组织协调的角色,同社区中的善男信女们一并前往丫髻山。在焚香、跪拜、焚“开山表”之后,他们先去黄花岭的黄花洞进香,次日再朝娘娘顶。(35)(P76-81) 可以说,晚清至民国时期,丫髻山信仰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个原本在帝国“五顶二山”宇宙图式之内的圣山,当帝国的国家意识和精英文化渐渐失去影响力时,被一些新兴的社会群体重新塑造和定义了。这个社会群体应当被看作是一些异质团体的组合或杂糅。他们既有来自京东香河、武清、三河一带的香客,也有四大门的信奉者和香头们。这些新演员在十九世纪末的最后二十年间登上了丫髻山的舞台,赋予丫髻山以新的象征框架。 显然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京东各县及四大门信仰的共同作用下,丫髻山着实又兴盛了一回。正是在四大门信仰的运作逻辑中,丫髻山维持了它京东进香中心的地位,即便这时期它已不能与声名大噪的妙峰山相提并论,(22)但至少未像五顶那样完全淹没在近代史的尘埃中。当天津的香客把他们的代表——王二奶奶——安插进妙峰山,并且意图以之取代妙峰山娘娘时,(31)北京东边的丫髻山,也发生着类似的历史桥段:以香河为代表的京东各县把王二奶奶送上了丫髻山。巧合的是,这位王二奶奶似乎早已在华北四大门(38)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使得北京的香客们对此似乎并未产生多少抵触。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他们甚至对此极为接纳。毕竟,对一般的老百姓而言,灵验与否才是至关重要的。 (二)丫髻山与近代化 将丫髻山与妙峰山置于同一历史脉络中进行比对,是饶有趣味的。在同一时期,妙峰山的情况是怎样呢?至清末民初,妙峰山的香火已经远远胜过先前的五顶和丫髻山。一方面,朝廷的巨额封赠确实刺激了妙峰山的香火。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慈禧太后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站在颐和园里一个独特的视点上观望园外过路的香会。(39)(P204)慈禧太后在非正式场合中叙说她1886年到过丫髻山,并在此后携一皇子经常来拜山。(22)虽然如此,却未见到这一时期丫髻山受到封赐的记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之形成,使得天津和北京西边的交通更为便捷。早先天津往北京要通过大运河然后绕到城北。1895-1896年的铁路(津卢铁路、卢汉铁路)使得天津和京西的卢沟桥成为重要的枢纽,这极大地缩短了天津香客前往妙峰山的行程。而京东的交通并未及时在这场近代铁路革命中获得长足的发展,较之京西地区,它更为依赖传统的交通网络。(40) 当国家意识和精英文化渐渐退出丫髻山时,它选择了一条怎样的路?在这点上,妙峰山和丫髻山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显得如鱼得水,更被赋予了民俗文化的意义;而后者却被纳入到一个更为边缘且传统的文化框架内——四大门。在那个迷信现代化的年代,这样的传统资源却被更为晚近的“宗教/迷信”(41)范畴与框架敌视与贬低着。 在20世纪的前30余年,丫髻山在四大门信仰的框架内维持着它圣山的地位。对丫髻山附近的村落而言,这就是他们进行村落祭祀的“大山庙”;对京东八县的香会来说,这里是他们的护佑者王二奶奶的飞升之地。在日本人到来之前,丫髻山的影响范围也只是在地方层面,甚至都没有充足的证据论证它对北京东部其他碧霞庙的支配地位。(42)事实上,它与其他碧霞庙(娘娘庙)的关系很难说清,“分香”或“分庙”这类说法并不适合于描述其关系。香会仅在每年的庆诞日才把大庙和小庙相联起来,它们之间并没有等级隶属关系。(43) 1937年,当日本大举侵华时,丫髻山的进香之旅几乎断绝。1953年,平谷县政府意图恢复丫髻山庙会,却只是昙花一现。此后的半个世纪,丫髻山经受不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庙会活动中断。在2004年“人文奥运”的口号下,丫髻山的庙宇群才逐渐得以重建并恢复了庙会活动。但正如萧凤霞笔下的小榄菊花会(44)(P121-137)一样,21世纪的丫髻山庙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并内化了社会主义的国家话语。 六、结语 一部丫髻山的进香史,就是一部近代京畿社会变迁的缩影。进香不仅是一种民众宗教实践活动,它更与地方政治、文化、权力和经济变迁息息相关。进香史所呈现的是一种多元文化,它几乎囊括了参与其中的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丫髻山作为一座圣山,与进香活动存在着共构的关系。它亦为展现这种多元文化提供了历史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个参与者各抒己见,每个社会阶层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些声音不断交织在一起却形成一种共鸣。或许,丫髻山的例子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即大众宗教在帝制晚期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附:丫髻山碑刻材料(含缩写) 1.YJSBK KX01康熙三十五年《丫髻山进香碑记》 2.YJSBK KX02康熙三十五年《丫髻山天仙祠碑记》 3.YJSBK KX03康熙三十五年《新建丫髻山圣母娘娘行宫普义门勒碑序》 4.YJSBK KX04康熙四十五年《怀柔县丫髻山天仙圣母庙碑记》 5.YJSBK KX05康熙四十六年《丫髻山进香老会碑记》 6.YJSBK KX06康熙四十七年《诚意会碑记》 7.YJSBK KX07康熙四十八年《丫髻山天仙庙碑记》 8.YJSBK KX08康熙五十二年《工部献灯老会碑记》 9.YJSBK KX09康熙五十二年《京都正阳门外猪市口迤南天桥元宝老会碑记》 10.YJSBK KX10康熙五十三年《丫髻山行宫碑文》 11.YJSBK KX11康熙五十四年《丫髻山玉皇阁碑记》 12.YJSBK KX12康熙五十五年《福善圣会朝山碑记》 13.YJSBK KX13康熙五十六年《二顶放堂老会碑记》 14.YJSBK KX14康熙六十年《永远胜会碑记》 15.YJSBK YZ01雍正元年《丫髻山进香碑文》 16.YJSBK QL01乾隆七年《报恩源留放堂老会》 17.YJSBK QL02乾隆十年《如意攒香供献鲜花寿桃胜会碑记》 18.YJSBK QL03乾隆十七年《如意掸尘凈炉老会》 19.YJSBK QL04乾隆二十年《景山南府灵官庙年例福善香茶斗香老会恭诣宝宫酬愿答报四恩碑铭》 20.YJSBK QL05乾隆二十四年《制造引路一山神灯序碑》 21.YJSBK QL06乾隆二十九年《京都顺天府昌平州怀柔县寅洞里地方》 22.YJSBK QL07乾隆三十二年《纯善源留老会》 23.YJSBK QL08乾隆三十五年《四顶源流子孙老会酬恩碑记》 24.YJSBK QL09乾隆三十八年《永远帘子老会》 25.YJSBK QL10乾隆四十五年《永远放堂济贫舍饭碑》 26.YJSBK QL11乾隆五十一年《合意进供鲜花老会》 27.YJSBK QL12乾隆五十九年《京都龙灯老会挂灯献茶》 28.YJSBK QL13乾隆六十年《子午香长香会碑记》 29.YJSBK JQ01嘉庆十三年《一山善人灯会记事碑》 30.YJSBK DG01道光十七年《重修丫髻山碧霞元君庙碑文》 31.YJSBK TZ01同治二年《香河县南窝头村合义会碑》 32.YJSBK TZ02同治三年《香武大后家湾恭意老会碑记》 33.YJSBK TZ03同治十二年《立众善供俸干果素烛以及照善士拜顶碑文》 34.YJSBK GX01光绪元年《京东怀邑寅洞里众善引右各村人等永远济贫放堂老会碑记》 35.YJSBK GX02光绪十二年《敬献翠冠碑序》 36.YJSBK GX03光绪十九年《天仙圣母九位君灵感显应碑记》 37.YJSBK GX04光绪二十三年《顺义县助善老会碑》 38.YJSBK GX05光绪三十一年《宝坻县城南如意老会碑记》 39.YJSBK GX06光绪三十一年《万诚老会碑》 40.YJSBK GX07光绪三十二年《大后家湾恭意会重建碑记》 41.YJSBK GX08光绪三十二年《立施舍香火地租碑记》 42.YJSBK MG01民国十年《诚意圣会碑记》 43.YJSBK MG02民国二十年《□□京西海甸圆明园外□□□□□□善住前北丫髻山朝□□□□》 44.YJSBK MG03民国二十四年《重修回香亭殿宇以及盘道碑记》 注释: ①Susan Naquin.The Peking Pilgrimage to Miao-feng Shan: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Sacred Sites[C]//.Susan Naquin,Chün-fang Yü.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②Chün-fang Yü.P'u-t'o Shan:Pilgrimag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Potalaka; John Lagerwey.The Pilgrimage to Wu-tang Shan; Susan Naquin.The Peking Pilgrimage to Miao-feng Shan: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Sacred Site..以上诸文均收录于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一书中. ③Philip C.C.Huang.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J].Modern China,1993(2). ④顾颉刚.妙峰山[M].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硏究所,1928.1925年,顾颉刚用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基金,协同四位同事上妙峰山,他们的文章在两期民俗专号上 结集出版,参见《民俗》,69-70卷,1929年7月. ⑤李景汉.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J].社会学杂志,1925(2). ⑥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吴效群.走进象征的紫禁城:北京妙峰山民间文化考察[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叶涛.泰山香社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王晓莉.明清时期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庙会[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5). ⑦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⑧这种倾向集中表现在吴效群、王晓莉、叶涛等人的著作中,甚至影响到了海外学者的叙述口吻,集中体现在韩书瑞对于北京庙宇的研究之中.Susan,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⑨徐天基.“标准化”的帷幕下:北京丫髻山的进香史(1696-1937)[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4(84). ⑩五顶是对老北京五座碧霞元君庙的俗称,具体言之,就是东直门外的东顶、左安门外弘仁桥的大南顶和永定门外南顶村的小南顶、西直门外的西顶、安定门外北顶村的北顶,以及右安门外十里草桥的中顶. (11)Susan Naquin.The Peking Pilgrimage to Miao-feng Shan: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Sacred Sites[C]//.In Naquin,Susan,Chün-fang Yü.Pilgrims and sacreds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译文部分参考了周福岩、吴效群对该文的译稿,韩书瑞.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J].民俗研究,2003(1). (12)怀柔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清康熙)怀柔县志[Z].北京市:银祥福利印刷厂,2000. (13)灵应泰山娘娘宝卷(第二品)明刻本[Z],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民间宝卷.合肥市:黄山书社,2005(4). (14)据《(康熙)怀柔县志》记载,康熙曾于康熙四十三、五十五年亲临丫髻山,《清史稿》《(光绪)顺天府志》《东华录》等书的记载印证了这个说法。详见:(清)张之洞.(光绪)顺天府志·卷24[Z].清光绪十五年.该书记载了康熙四十三年和五十五年的皇帝驾临,《(康熙)怀柔县志》基本上沿用了该书的说法;另见(民国)赵尔巽.清史稿·本纪八圣祖本纪三[Z].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清)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七十三[Z].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15)中国的民俗学界在对北京地区香会的研究中,普遍接受将香会范畴化为“文会”“武会”两大类别.其中“文会”又名“善会”,它们为进香民众提供各种慈善性质的服务。“武会”又称之为“花会”,是具有表演性和娱乐性的组织,常见的包括秧歌会、狮子会、大鼓会、中幡会等。参见:隋少甫、王作楫.京都香会话春秋[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16)丫髻山曾作为正一道周祖灵宝派的祖庭,是明清时传承周祖灵宝派的重要地方。通过碑文考证得知,丫髻山的道士按照周祖灵宝派的谱系传承。自第十三代李居祥,按照“居、士、显、一、嗣、永、承、宗、德、大、传、家、久”的排序,一直传承到第二十五代陈久东。详见:北京市平谷区文化委员会编.畿东泰岱——丫髻山[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17)(清)胤禛.雍正上谕内阁.卷十八[Z].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和邦额.夜谭随录.卷三[C]//.民国刻笔记小说二十种本;袁枚.新齐谐.卷六[C].清乾隆嘉庆间刻随园三十种本;俞蛟.梦厂杂著(卷一)[Z].清刻深柳读书堂印本. (19)吴振棫.养吉斋丛录[Z].北京:中华书局,2005. (20)(民国)赵尔巽.清史稿[Z].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另见:(清)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Z].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21)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九[Z].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韩书瑞著,周福岩等译.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J].民俗研究,2003(1). (23)韩书瑞著,陈仲丹译.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24)《平定教匪纪略》一书的卷首收录了嘉庆皇帝的御制文,从中可以看出嘉庆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参见:(清)托津.平定教匪纪略.[Z].清嘉庆武英殿刻本;另见:(民国)赵尔巽.清史稿.本纪十六仁宗本纪[Z].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清)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朝).[Z].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25)东岳庙共有五处供奉娘娘香火:广嗣神殿、后罩楼北侧靠西的三间娘娘殿;东廊的玄坛宝殿和丫髻山九位娘娘殿、西廊的妙峰山九位娘娘殿.这些娘娘,虽各有名衔,实际上都是碧霞元君的化身。陈巴黎.北京东岳庙[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2. (26)叶郭立诚.北平东岳庙调查.(民国廿八年初刊)[R].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第三辑).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1年(再版).北京的东岳庙东院有丫髻山娘娘殿,而西跨院有妙峰山娘娘行宮. (27)北京市平谷区文化委员会编.畿东泰岱——丫髻山[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28)感谢北京平谷县文物部门的岳清立先生提供这一资讯。笔者于2011年在丫髻山访谈期间,也在当地民众的叙述中印证了这种说法. (29)另参见(清)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朝)[Z].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卷35;(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180[Z].民国景十通本;(民国)赵尔巽.清史稿·本纪十八宣宗本纪二[Z].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 (30)有关北京四大门信仰的田野调查情况,请参阅Li Wei-tsu.On the Cult of the Four Sacred Animals(Szu Ta Men)in the Neighborhood of Peking[J].Folklore Studies,1948(7). (31)吴效群.文化的冲突与较量——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与天津民众之关系[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李世瑜.妙峰山与天津[J].天津文史.1995(1). (32)香客们的这种观念显然是康熙《怀柔县志》等书面记载与口头传统长期混杂的结果.参见,怀柔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清康熙)怀柔县志[Z].北京:银祥福利,2010;尹玉茹.王二奶奶与丫髻山庙会[C]//.欧大年、范丽珠编.香河庙会、花会与民间习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笔者在近年丫髻山的田野调查中,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33)在北京及周围有些地方,除“四大门”外,亦有“五大门”或“五大家”的说法。“五大门”究竟是哪五种动物,说法不一,除“四大门”四种外,或加兔子、或加老鼠,因此“五大门”亦被称作“狐(狐狸)、黄(黄鼠狼)、白(刺猬或兔子)、柳(蛇)、灰(鼠)”. (34)香头在这种民俗宗教中充当着仪式专家的角色,他(她)被认为是替四大门的仙家服务的,以行道的方式来修福。他们与仙家存在着主从的关系,常自称为是某仙家的“当差的”或是某仙家的弟子,用医病、除祟、禳解、指示吉凶等方式行道(行好). (35)李慰祖著,周星补编.四大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6)香头眼中的“五顶”概念与上述“五顶二山”之“五顶”的指涉对象不同. (37)在香头的家中,往往设立神坛,用以从事降神治病等活动,坛口是描述神坛的计量单位。 (38)有关北京四大门信仰的田野调查情况,请参阅Li Wei-tsu.On the Cult of the Four Sacred Animals(Szu Ta Men)in the Neighborhood of Peking[J].Folklore Studies,1948(7).在北京城及其周边地区,某些寺庙的偏殿或神坛一角,有时会建一座小神楼,供奉狐狸、黄鼠狼、刺猬和蛇,俗称“四大门”或“华北四大门”. (39)顾颉刚编.妙峰山[M].广州:中山大学民俗丛书,1929;内务府掌仪司承应各项香会花名册[Z].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 (40)逆旅过客.都市丛谈[M].北京隆福寺街文奎堂书庄石印本,1940;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历史纪年[Z].北京市:北京出版社,1984;苏生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1);许洵.当代北京铁路史话[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马里千等编.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1881-1981)[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5:4-5,178-186.在1895年通车的津芦铁路线中,天津东站和卢沟桥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1896年建成的芦汉铁路线中,卢沟桥同样充当了要塞。在1907年和1915年开通的京绥铁路京门支线和京绥环城线中,北京的西直门作为起点。可见,晚清至民国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建设中,北京西部和天津的地位较为突出。较之京西卢沟桥等铁路枢纽的崛起,京东依然较为依赖传统的交通网络. (41)一些学者论述了1898年以来中国社会如何接受“宗教”这一西方概念的过程,并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了精彩的回顾.参见:Rebecca Allyn Nedostup.Superstitious Regimes: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Yoshiko Ashiwa and David L.Wank.Making religion,making the state: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M].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Palmer.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 Vincent Goossaert.1898: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Chinese Religion?[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6(2);陈熙远.“宗教”——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字[J].新史学,2002(4). (42)现有的文献和当代的田野考察均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论证丫髻山对众多碧霞庙的支配地位,只能说丫髻山是京城东部最大且有影响力的碧霞庙。林玉军和岳升阳两人对丫髻山的研究,使用朝拜圈的概念却并未加以界定。他们所使用的地方志材料仅能证明京东各县碧霞庙的普遍存在,却不足以论证“朝拜圈以丫髻山为中心,并在区域中形成诸多次级朝拜中心”的结论。参见:林玉军,岳升阳.明至民国北京东部碧霞元君朝拜圈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07(5). (43)在闽台的神庙关系中,这种联系是普遍的,参见:Paul Steven Sangren.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M].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44)Helen F.Siu.Recycling Rituals:Political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C]//.in E.Perry Link,Richard W.Madsen and Paul Pickowicz.Unofficial China: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London:Westview Press,1989.标签:嘉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