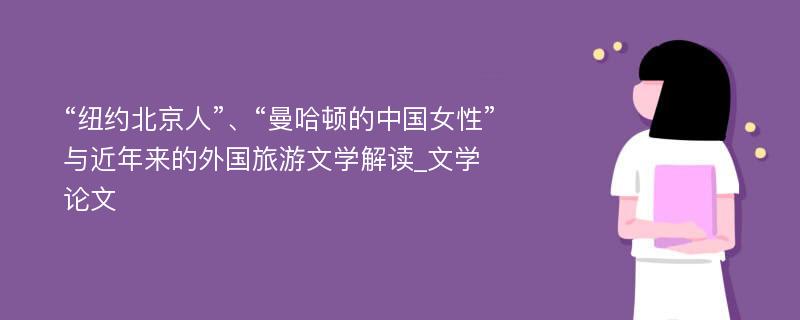
《北京人在纽约》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评析——兼及近年来的旅外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曼哈顿论文,北京人论文,中国女人论文,文学论文,在纽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评析《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主题,奋斗精神,芜杂的价值观及其艺术上的不成熟;兼而论及近年来旅外文学创作潮流形成的背景,和它所反映的中西方碰撞的文化现象。
本世纪20年代,“民主斗士”、爱国诗人闻一多在旅美期间曾写下一首著名的爱国诗篇《一句话》,“爆一声:‘咱们的中国!’”。70年后,当我们翻开《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时,在该书的最后一页又一次听到了这一回声。时隔70多年的两次呼唤也许有着许多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由留学海外的我国学子在异国他乡“爆”出的,都写在中国旅外文学作品上。
一
1847年,当容闳、黄宽、黄胜等人由英国人办在香港的教会学校校长布朗带往英国留学,揭开近代中国留学史的序幕时,也许就预示着中华民族在与西方文化碰撞的同时将给中国文学史添上一朵瑰丽而却苦涩的奇葩——旅外文学。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从两个世纪交接点的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清末的《苦社会》,到本世纪初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老舍、冰心、徐志摩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们所写的表现他们旅居国外期间所见所闻的一大批作品,再到80-90年代的《我的财富在澳洲》、《留学生心态录》、《日本留学一千天》、《上海人在东京》、《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在美国当律师》等等,一批批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文学作品,都使中国文学史上的这朵奇葩璀璨而痛苦地展现了近现代中国人面临中西方文化碰撞、唤起人民觉醒、“导中国人群以进步”时所经历的磨难、艰辛和不屈。
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里反映的产物,是作家根据他们彼时彼地的生活创造出来的。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到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去反映。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们笔下的许多旅外文学名著,正是本世纪初的留学热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大半个世纪后,在几经涌动的“出国潮”中,大批中国大陆青年再一次负笈远游,他们在国外留学、打工的生活经历,在国外商业竞争中谋求生存发展的际遇,面临异邦文化时的失落心态、痛苦选择和重新寻找自我价值的种种艰辛和苦难必然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拿起笔记录下来这些经历、际遇、心态、选择、艰辛和苦难。这是形成近年来以留学生在国外生活景况为特点的旅外文学创作潮流的最直接的原因。
其次,国门打开以来,生活在国门以内的许多中国人迫切地渴望探知了解国门以外的世界,旅外文学作品正好能够提供域外生活的各种信息。而且,广大国内读者与旅外文学作品的作者曾有着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感受、判断、选择和价值取向上极易产生共鸣。这种异域性和共鸣性是形成旅外文学创作潮流的又一客观原因。
80年代后期纪实文学的兴起是旅外文学创作潮流的另一原因。近年来人们对虚构艺术的厌倦和冷淡,使纪实文学和旅外文学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即给读者的感受是作者在讲述一个具体真实的故事,比虚构体裁更令人感到真切。大多数旅外文学作品似乎都在讲述作者在异邦的亲身经历,这种亲历性更能引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在这里,接受美学的作用帮了旅外文学作品的忙。旅外文学创作在客观上是对纪实文学热的一个策应。
本文所要评析、比较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以下简称《曼》文)和《北京人在纽约》(以下简称《北》文)两部具有代表性的旅外文学作品,及近年来出现的其他旅外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有着上述相同的背景。
二
清末民初,在“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的思想指导下,一批批留学生告别家园,蛰居异邦,为了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博采众国之长,“师夷制夷”。从写下《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的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先行者严复到后来赴日、法、俄、美的一批又一批留学生,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人文思想的同时,抱着一个共同目的——富国强民。这种传统奠定了旅外文学的爱国主义基调。
爱国主义是个永恒的主题,尤其对飘泊异乡的旅外游子来说,这个主题更是最敏感、最显而易见的。在《曼》文和《北》文两部作品中,我们都很容易地发现,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永远是他们直接倾诉的对象。民族归属意识与祖国观念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是非常强烈的,虽然作品并没有明确的社会理想与政治远见,而只是从一个朴素的、基本的自觉意识出发:“我是中国人”。
《北》文中,财源广进事业有成春风得意之时的阿春会有这样的愤怒和感慨:“你再努力干,拚命地做,可就是因为你的面孔是黄色,你就永远不会有升迁的机会。美国人天天大叫人权,可骨子里,浸透了那种族歧视,我受不了那种气”、“这里毕竟是人家的国家呀”;在失意和痛苦中倍受思乡折磨的郭燕会有这样的联想:“外面好黑哟,又冷又黑有什么好的,多可怕呀!还是家里好呀,家里有粉肠、豆腐干儿,还有拌生白菜心儿”,自然而然地蒙生出“想老家了”的念头;弥留之际的宁宁和她父亲王启明在生死离别之时的唯一对话主题也是“家”:“我要回家”,“爸带你回老家,爸带你回北京”,在那种特定的客居他乡的环境中面临死亡的一瞬间,父女间多年的恩怨、误解顿时全部消除了,金钱、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一切其它问题上的争执、矛盾也都不重要了,都毫不含糊地被唯一重要的概念“家”——北京(祖国)所代替了。可以说,《北》文中的全部人物,都没有忘记“我是中国人”,都有着强烈的“家”(祖国)的意识。
思念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在《曼》文中就更无处不见了。当遇到外人凌辱时,主人公的态度是:“这种视中国为肥肉,却对中国人民没有丝毫感情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从(客户——笔者注)名单中划掉”;在商业激烈竞争中取胜时的感慨是:“当看到这些中国生产的商品标上昂贵的价格,摆设在装潢考究的名牌橱窗中,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安慰和自豪”;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当看到“中国的古董,在这里成了价值连城的珍藏物!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留学生、访问学者、医生、教授……却骑着自行车,拎着一袋袋的饭菜,穿过车流,送着外卖,打着苦工”时,主人公也没有忘记对这两种互为反差甚至讽刺的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反省而“陷入沉思中”,这之中自豪和悲哀被无奈地捆绑到一起;而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当西班牙商人故意刁难国内贸易公司,企图敲诈时,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维护来自她的父母之邦的贸易公司的意识就更强烈了,她首先通过种种努力竭力帮助国内贸易公司避免了损失,不仅如此,还在事后给西班牙商人打电话,义正辞严地斥责说:“你这个坏家伙,你听着,全中国今后都不屑再与你做生意。”并又一次把这个客户从电脑上的客户一栏中划掉了,这里也许不无幼稚的赌气,但并不是为她个人,而是因为她的祖国受到了伤害。
如果你爱他,
就把他送到纽约,
因为那里是天堂;
如果你恨他,
也把他送到纽约,
因为那里是地狱。
上面的这段引文是《北》文中两次出现的一首美国流行歌曲,并且被作为全文的结尾。《曼》文中也提到过一首风靡一时的美国流行歌曲,在歌的开头、结尾反复咏唱着“这个世界有一点冷……”。细细品味、不难发现两首歌所表达的情感是有共同之处的。与其说这是两文作者在写作中的偶然巧合,不如更准确地理解为两文作者对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必然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的认识当然不仅仅体现在两首流行歌曲上。《曼》文中常出现这样的带有诅咒性的词句:“美国这样一个以金钱物质为上帝的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富裕文明而又极端罪恶的世界(指美国——笔者注)”。《北》文中这种诅咒则变成更为理性的分析批判:“原来,美国人只崇拜三种人,并认为这三种人才是正的英雄:一、体育明星,二、电影明星,三、成功的商人。因为这三种人的身后财产都具备天文数字。这真是赤裸裸的拜金文化、美国文化。”虽然两文作者对美国及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谴责都是出于朴素的感知,并不具有某种明确的社会理想与政治见解,但却都是准确、深刻和一针见血的。
奋斗精神是两文的又一思想倾向。横跨大陆与海外两地的人生,给了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体验。凭借不尽相同的特有的人生体验,两文作者不约而同地通过文学形式描述了新一代中国人对社会、人生、世界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和勇于向命运挑战、与命运抗争的创业精神,展现了留学海外的游子们历经磨难的奋斗历程所带来的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
但是,奋斗精神在两文中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曼》文中所张扬的奋斗精神更多地纠缠着个人奋斗、个人成功意识和实现“美国梦”之时的得意情绪。《曼》文中随处可见象序言中所写的“而我——一个在1985年夏天闯入美国自费留学的异乡女子,虽然举目无亲,曾给美国人的家庭做过保姆,在中国餐馆端过盘子,却能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这样大段的不加掩饰的文字。“他们有时真的奇怪我这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东方人,怎么就在蓝眼睛金头发的西方人中成了中心!”类似这样的描述,在宣泄作者个人成功得意情绪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种自卑的心态。作者举起的这杯庆功酒实质上是一杯混合着自豪与自卑的鸡尾酒。《北》文代序《写在前面》中,也同样有一段关于“美国梦”的描述:“虽然我在美国有不少财产,和不小的生意,可我在精神上只是个零。”两文的主人公在生意上都是成功的,一个“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一个“有不少财产,和不小的生意”;但是在精神上一个充满自豪和自信,坚信“只有奋斗,才能创造出人生的价值和尊严,创造出激情和人生快乐”,另一个则“我他妈的是‘内伤’”。更值得注意的是,《曼》文主人公的自豪自信和价值尊严是令人怀疑的,掺和着个人奋斗哲学和骨子里的自卑;而《北》文主人公却把“精神上只是个零”的“内伤”真实地袒露出来,毫无掩饰地向他的祖国倾诉出来。两文对奋斗精神不尽相同、各有偏颇的理解,实际上都缘于两文主人公共同怀有的“美国梦”。
思想、价值观的芜杂和自相矛盾,在这两部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体现。苏联解体之后,《曼》文主人公曾为此“眼睛哭得肿肿的”,因为“红场、列宁墓、涅瓦大道、莫斯科郊外河畔的晨曦,曾经给了我多少梦想,曾经给了我一个多么光辉灿烂的金色童年!”正缘于此,她才能在叶利钦向全世界宣布苏联解体时做出一个令她的亲友们难以接受的决定——去苏联。克服了来自亲友的重重阻力,她踏上了奔向“儿时的梦”的路。在去苏联的途中,她一直沉浸在“儿时的梦”中,回忆着德伯拉金娜的《黑面包干》、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中的句章和马雅可夫斯基的爱国抒情诗。在东欧,当她“一看到列宁雕像、头像或全身像就喜形于色,并且立即跑上去和列宁雕像一起合影,或者是把这些屹立在花丛中的大理石像、花岗石像拍了又拍,有时还抱着列宁那著名的宽大光洁的额头吻一下,好像我真的见到了列宁一样。”然而,当听到一个“从苏联‘逃’出来五次”的苏联老人的故事时,她感到困惑了,迷茫了,产生了“也许童年的梦根本不存在的”的怀疑。这种思想、价值观含混的情况在《曼》文中多处可见。再比如,作者一方面在宣扬她的奋斗哲学,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生活”,一方面又以“他们(指美国人——笔者注)已经完全把我看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而得意自豪。不难看出,主人公把“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认为是她的命运的改变和事业的成功。这种表述说明作者理解的东方文化的价值只有得到西方文化的欣赏才能被确认,或者说,作者的终极价值尺度不过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嘲弄。在面临着一场触及灵魂的命运改变时,《北》文的思想、价值观也是混乱和矛盾的。《北》文主人公王启明在产生“打你进入纽约那天起,哪天不在赌哇!整个纽约哪儿不是赌哇”的迷茫的同时,又发自内心地承认“钱,代表不了一切”。而对于成功的认识和理解,《北》文并不象《曼》文那样单纯,《北》文在《写在前面》的一节中对成功的理解有这样一段描述:“虽然那座通往成功的桥,又窄,又长、又艰险,但毕竟有人通得过,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桥那边,并不是一片乐土。桥那边却是荆棘丛生,满地陷阱。一不留神,你会全他妈玩完。”这种对成功复杂矛盾的理解既包含着“我就是其中之一”的自豪,又透露出成功之后的惊悸:“满地陷阱”。《北》文价值观的模糊不确定还表现在,初踏上美国国土的王启明曾看着他本来是拉小提琴的手却因打工洗碗“已被白水泡得没了血色,手指的皮肤像是一团被捏紧又散开来的破纸”而哀叹、惋惜,并渴望“一定要寻找机会回到本行”,回到他原本从事的艺术中去。然而当他的生意有了起色之后,就再也没有想起他的艺术,他的拉小提琴的艺术价值在织毛衣赚大钱的生意价值面前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概括地说,爱国主义是两文共同的主题,对资本主义金钱社会的认识两文也有共同之处,而在奋斗精神、价值取向上,两文却有着各不相同的芜杂混乱的理解和认识。这也是大多数近年旅外文学作品的情况。
三
当代旅外文学历史较短,作者群有限,作者的文学素养普遍不高,所以,整体上的艺术水准还不够成熟。《曼》文和《北》文也同样存在着艺术上不够成熟的问题。
缺乏艺术构思的整合提炼,是《曼》文比较突出的问题。全文对故事情节的发展结构得混乱,前后进程的发展脉胳不清晰,缺乏艺术的剪裁和布局,故事情节是零散的,叙述进程是散乱的,典型细节的选取也不够精炼,很多笔墨是一个又一个生意过程的赘述,而且前后重复,有时甚至是莫名其妙的,给人以鸡毛鸡肉剁在一起的庞杂感。另外,众多生意过程的赘述、频繁的大段大段的感情宣泄替代了典型细节的描写,以及缺乏深入细致的人物形象刻画,使洋洋洒洒39万言、提及了几十个人物的《曼》文,在很具典型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却没能塑造出几个生动鲜明的典型形象,是其又一大遗憾,也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刻性。
《北》文虽然塑造了王启明、阿春、宁宁、郭燕等一系列人物,但王启明和阿春之间的婚外恋情发展过快,他们之间究竟是两个移民孤独寂寞灵魂的相互慰藉还是有真正的爱情,作者没能写明白。宁宁思想性格的发展就更概念化了。她从16岁来美国到演变成一个吸毒、性观念堕落的18岁少女,这之间仅有的铺垫,一是她初到美国时在机场表现出的对父母的冷漠,二是要求买部新跑车。而仅有的两个铺垫细节也让人感到说服力不强:一个与亲生父母阔别多年的女孩在异国他乡的机场再次见到父母时怎么会如此冷漠?缘由何在?作者没有交待明白;要求买部新跑车的细节也同样不能为她后来的堕落起到铺垫的作用。相反,她16岁前在中国所受的全部教育和已形成的人格文化,以及这种教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碰撞,在作品中竟没有一点痕迹,让人感觉她天生就是一个虽然在中国生活了16年却完全是为彻底接受美国腐朽方面文化而概念性地设置的一个人物。宁宁的性格发展和阿春与王启明之间感情的发展都让人感到不真实,都远不如后来改编的电视剧中塑造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
当然,由于两文的作者都有着特殊的异域生活经历,叙述时又都饱含着真情,所以在整体上给读者的感受是作者在讲述个人的亲身经历,象是真实的故事,只是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还很粗糙。
四
如果说近几年的旅外文学并不具备纯文学文本分析的艺术价值,那么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文化现象。
近几年的旅外文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产生的。十年浩劫结束后,人们对原有文化造就的价值判断产生了怀疑,精神上出现了困惑,开始了重新反思(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文学表现)。大多数中国人仍在原来这片土地上反思,少部分人借助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留学等现实生活提供的机会飞往大洋彼岸,当他们或是带着精神上的困惑,或是抱着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报效祖国的美好理想,或是怀揣“淘金梦”去寻找新的生活环境,落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摩天大楼之间的时候,也面临着新的文化,开始了新的自我寻找。表面上这是一种命运的改变或寻找新的命运归宿,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归宿的寻找。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新的文化造就下的范式与他们个人的自我要求是相对立或偏离的,这种对立或偏离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而且更是精神上的痛苦和迷茫。抛开社会制度原因和政治原因,从文化角度讲,这反映了中西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如果说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之间的人性是可以相互沟通和理解的话,那么文化的差异却更难以弥合,因为文化不是衬衫,可以穿也可以脱,文化是血液,彻底大换血是不可能的。中西文化在这些旅外学子身上碰撞(打工、求学、生存、婚恋、道德等一系列中西文化碰撞)的后果必然是出现新的文化选择的价值判断。
《曼》文和《北》文在不同程度上都反映了这种新的文化现象。《北》文中的主人公是“在一股出国热潮中”,“几经周折”,“脸上流露出激动、喜悦、渴盼的神情”,“告别亲友,飞往大洋彼岸”的。当他们乘着“波音747,这20世纪人类文明的结晶”落地异域机场,穿过“高入云端的现代桥梁”、“雪白如镜的海底隧道”和“那一座连一座的摩天建筑”,来到只有“一只超级市场上用的装水果的空木箱,两只没了后背的皮椅子和一张肮脏的双人床垫”的地下室,接过阿姨借给他们的500美元时,就注定要带着精神上的困惑和失望开始新的一系列漫长的自我寻找过程,也同时开始了与西方文化的激烈撞击。撞击中,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留下的价值判断竟是一个残忍、严酷的问号,如文中开场白所写的那样,“有不少财产,和不少的生意”的成功,是否一定要以“精神上只是个零”的“内伤”为代价?《曼》文中的主人公是怀着更强烈的不愿回到原来“生活轨迹”的决心和“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生活”的愿望来到美国的,这种愿望已明显地表明了对原有文化下的价值判断的否定,和对新的命运归宿、文化归宿的自我寻找。然而,当《曼》文主人公心甘情愿、满怀极大热情积极地闯入新的文化环境中,第二天就开始“穿上了象英国小说中女仆穿的那种白色抽纱围裙”、“跪在地上擦厨房的地板”时,也同时不得不开始经受一系列中西文化差异的撞击。值得思考的是,《曼》文所描述的商场上的成功和对成功的理解是否是其留给读者的新的文化选择下的价值判断呢?两文所刻画的主人公都处在两种文化的交错下,因此两文所描述的心态也是夹在两种文化缝隙之间的“边缘人”心态,从某种角度上体现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探寻,这种揭示虽然并非完全出于自觉,但作为文化对比的反映却非常强烈。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重点转入到经济建设上来,尤其是近几年的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使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热点发生了转移,而《曼》文和《北》文所张扬的自我寻找及雄心勃勃的奋斗精神,所描写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的思想感情与价值观念,正与这种转移相契合。这也是近年来旅外文学作品成为畅销书,在读者中引起轰动的文化现象的根源,是生活选择文学和文学选择生活的双重实现。
面向21世纪,世界文化正在走向一个多媒体时代。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都在设计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这个面向未来的庞大计划意味着地球将更加缩小,世界更加信息化,我们将与世界同步。在此情况下,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多层面、多角度的。在我们面对中西文化交缠矛盾的现实时,近几年的旅外文学作品并没能如本世纪早期创造社作家的域外作品为五四新文学带来新的价值尺度那样,为我们今天寻找中国文化自己的声音带来新的价值尺度,这是遗憾的,也是短期内旅外文学作品所达不到的。但是,它为展现中西文化再次撞击的新状态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初探。它终于发出了一声叩问:这片土地,这个时代,究竟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指令,使我们如此坐立不安?在这一点上,《曼》文、《北》文和近几年其他旅外文学作品一样,肩负了相同的使命。同时,也为在中西文化交错的现实下文学自己的思考和选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价值。
五
在结束这篇拙论的时候,让我们再听一听爱国诗人闻一多先生的呐喊,这是他在1925年4月踏上多年怀念的祖国大地时无比沉痛地发出的一声哀鸣: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喊着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对过去文化怎样地动摇,怎样地困惑,又无论在中西文化撞击下怎样地重新进行文化选择的价值判断,我们都不会也不愿再发出这样的一声哀鸣:“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当上面那首诗的哀鸣刚刚从我们的耳畔远去的时候,另一首更遥远的山西民歌《走西口》却又突然从远处飘回。那是一首被许多描写黄土高原的文学作品多次引用过的哀婉凄楚的情歌。但是,如果仅仅只把它理解为一首伤别离的情歌,则是对历史的浅薄和不公正。事实上,它更是几百年前山西农民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以外更辽阔的天地,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轫筋骨走出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而唱出的壮行歌。从情歌的理解到壮行歌的认同,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理性和真实。正因为历史的艰难,正因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那首壮行歌才被唱得更凄楚,几百年前山西农民“走西口”才显得更悲怆。“走西口”的历史虽然发生在几百年前的山西,却又远远超越了山西,从文化意义上理解,由这里发出的感叹,应该属于我们父母之邦的更广阔的天地。今天,虽然我们不会再如闻一多先生一样迸着血泪发出那一声追问,但是,当年山西农民“走西口”的悲怆在我们又一次走更广阔的“西口”的今天却依然追随着我们,并且,也许将追随很久。然而,我们期待的是,我们的父母之邦将尽快地从悲怆中走向辉煌。这也是一切旅外文学作品最终的希翼和支撑点。
标签:文学论文;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北京人在纽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