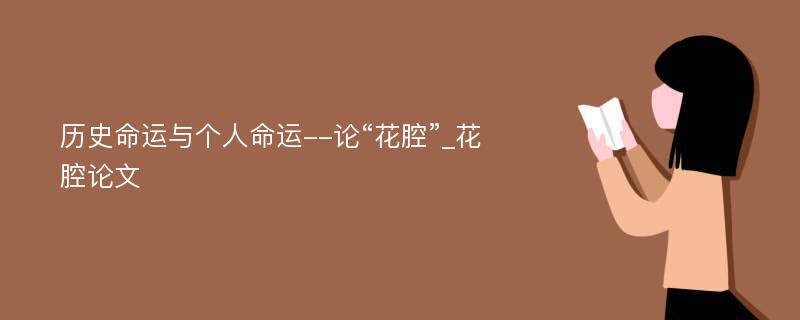
历史际遇与个人命运——论《花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腔论文,际遇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作为一种自我超越的《花腔》
作为一位长期恪守于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的青年作家,李洱一直专注于对中国知识分子 潜在心迹的揭示与展露。他的很多作品都可视为一种“遮蔽的艺术”,即,通过各种潜 隐的叙事话语,不断地剥离和展露当下知识分子在种种繁杂的生存秩序中被遮蔽了的人 性状态。李洱的叙事很少追求人物的命运结果,他总是津津乐道地徘徊在那些看似边缘 的生活状态,让人物尽量蜕去知识分子角色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隐秘的、碎片式的 庸常生活中一步步地袒示自己的生命真相。他尤其擅长的是,将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域投 置在十分复杂的文化体系和权利体系之中,以种种充满反讽意味的语调,对他们的精神 生活(尤其是价值观念、伦理观念以及欲望本能)进行尖锐的表达。在《导师死了》、《 遗忘》、《破镜而出》、《饶舌的哑巴》以及《午后的诗学》、《现场》、《缝隙》等 等代表性的作品中,李洱都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许多悖谬特征,然 后以十分冷静的叙事语调,不断地对这些悖谬特征进行精细的演绎。
在这些作品中,人性的卑微欲求、自私本能、怯懦个性以及失落与焦灼的情绪,总是 与知识者的社会身份、伦理规范形成了无法协调的对抗关系。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 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流价值代言人角色的退位,他们的生存秩序与伦理秩序都发生了 巨大的改变,并由社会上显赫的中心位置不断地转移到特定的社会结构体系中。尤其是 在市场经济的杠杆支配下,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生存境遇都较 之以前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内心冲突与焦灼,也是一种必然性的精神过渡 现象。李洱的意义就在于,他不断地潜入这些知识分子的内心,以往返而非递进的方式 ,带着足够的叙事耐心沉迷于他们的精神深处,反复地搜索、品味、抚摸、推衍他们在 庸常生活背后所凸现出来的种种反常性,并以此展示出人性丰富的内在层次,从而使叙 事常常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深刻。正是在这种叙事策略的引导下,我们看到,李洱笔下 的那些知识分子,从学者、教授到研究生、大学生,他们不断地寻找着属于自身价值体 系中的权威地位或者生存的优越感,但是,在世俗性的现实面前,这些看似纯粹、实则 庸常的生命理想总是显得不堪一击,甚至支离破碎。李洱或许也正是想为这个特殊的阶 层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留下一个沉重而又不无荒诞的精神参照。
但是,他的长篇新作《花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却一反这种叙事追求。在 这部作品中,李洱不仅摒弃了对知识分子生存现实的关注,而且抛却了他所惯常使用的 知识分子话语方式,以一种彻底的民间化的叙事手法,对历史中的个人命运进行了多方 位的还原式探求。从故事层面上说,小说力图通过对各种当事人的实证采访以及史料补 充,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在第一现场还原主人公葛任的死亡真相。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 以及对各种史料的综合,在小说的内在结构中,我们终于发现,历史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它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权力冲突的纠葛方式,彻底地掏空了葛任的命运自主权 ,并赋予他以虚无的英雄称号,瓦解了他的生存选择。这种探求,看似为了揭示历史的 真相,展示个人命运在历史记忆中永难把握的迷离状态,其实质却是对历史自身以及个 体生命的终极价值进行了尖锐的质疑。它所透视出来的,不只是个人与历史之间无法抗 衡的无奈状态,还有人们对强权意志的盲目膺服,对生命价值的盲目推崇,以及对传统 文化伦理秩序的根本性的怀疑。
尽管这种思考的深刻性与有效性在《花腔》中还没有得到更为丰饶的体现,但是,就 李洱自身的创作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超越。这种超越,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不仅显示了一个作家寻找新的叙事激情和审美挑战的热切愿望,而且还表明了李 洱开始对个人的存在命运以及历史境域进行着更为广阔的思索。
2.个人命运与历史真相
文德尔班曾说:“人是有历史的动物”。(注: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史》第378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任何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也是 一种文化的存在。科林伍德甚至说道:“严格说来,没有人性这种东西,这一名词所指 称的,确切地说,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人类的历史。”(注: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 史》第3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尽管这种论断的科学性有些让人生疑,但是 ,它也的的确确道出了历史与个人之间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任何个人的命运,都将 无法彻底地脱离于历史自身的拘囿,也不可能彻底地摆脱由其自身的文化传统所构成的 种种价值观念的制约。《花腔》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作者不仅将主人公葛任的命运 际遇自始至终地安置在广袤复杂而又动荡不安的历史境域中,使他无法挣脱历史的种种 潜在规约,还将他的生死选择不断地纳入到一个繁富驳杂的文化伦理体系之中,让他完 全失去了对自我生命的主宰能力。这是人类生存的双重困境,也是生命存在的两难现实 。李洱就是企图通过葛任(其实也包括故事的讲叙者白圣韬、赵耀庆和范继槐等人物)在 这种两难之中的绝望式挣扎,来展示人类存在中的某些无法逃离的悲剧性本质。
这种存在的悲剧性,首先就体现在个人与历史之间永难协调的尴尬状态。历史作为人 类群体性活动的产物,它的演进并不是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自由和理想为前提的,相 反,它常常是以削弱个人的特殊性为代价,以便在更大层面上谋求人类的共同性来维护 自身的合理性,推动社会在不断协调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尤其是在各种重大社会事件频 发时期,不同政治群体为了各自的精神目标、政治利益以及现实需求,总是要对任何个 人的言行进行更为严密的规范,并要求个人对集体(即各自的政治群体)作出无条件的膺 服和顺从。因此,作为边区马列学院编译室译员的葛任,当他置身于异常复杂的民族冲 突和阶级冲突的历史境域中时,他也就无法保持自我生命的理想形态。在延安整风即将 来临之际,边区正在批判托洛茨基,可是潜心翻译列宁著作的葛任还是凭着一介书生的 诚实和天真,毫不避讳地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朋友”。这话虽然是一句真理,“可 在特定的历史场合,真理就是谬误。”历史以及历史背后的权力意志,决定了任何言论 的是非标准。葛任的“真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无疑成了一种反动分子(或曰托派分 子)的罪证。他的命运正是由此被历史推向了失控状态。为了让葛任能逃离这场历史劫 难,作为朋友兼上司的田汗便派他前往宋庄传递情报。对此,田汗的理由是:“借这个 行动让葛任暂时出去躲躲风头。因为那时候,整风运动就要开始了。当然,最坏的结果 我也考虑到了:葛任可能会死。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就是死到日本人手里, 总比被自己人冤屈强。”这里,田汗试图通过一种消极方式,来帮助葛任消除他与历史 之间的冲突,化解历史背后权力意志对葛任的盘压,但是,最后传回来的消息却是:葛 任被日本鬼子发现后杀害于二里岗。面对这种结局,田汗的感受是:“我的左眼流的是 痛苦的泪,右眼流的是自豪的泪”,因为作为边区锄奸科副科长的他,在历史的权力法 则中已经清醒地看到:“如果他(葛任)不死,他不光会被打成托派,还会被打成特务, 遗臭万年。”所以,田汗的行为,实际上是以文化伦理中的“英雄价值观”对葛任实施 了一次合理性的谋杀,而在这种谋杀的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内在的强权逻辑 对一切异己化的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否定。
这就是历史对个人命运的强制性规约。透过这种表象,我们可以发现,在那种特定的 历史背景中,权力意志实际上是主宰一切合理性价值秩序的重要法则,甚至是唯一法则 。这种强大的权力意志,也就是福柯所反复强调的、在一切现实生存秩序中起着决定性 作用的“价值的眼睛”。福柯就说:“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 。”(注:福柯《权利的眼睛》第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他认为,知识由于 受到权力的影响而不再是对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它成了非中性的、具有权力特征的东 西。在福柯看来,权力无处不在,它充斥于各种知识领域。对于知识来说,权力已不是 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东西,“权利关系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经济过程、认识 过程和性关系),相反,它们内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之中。”(注:福柯《性经验史》第 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这种权力对知识的强制性渗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 知识本身独立性和科学性的丧失。因此,当边区的权力意志决定了“托洛茨基就是混蛋 和反动派,绝对不可能成为列宁的朋友”时,如果还有人不能认识到这种“知识”,个 人生存的合法性就必然要受到动摇。葛任的悲剧就出现在这里。当历史背后的权力与知 识背后的真理发生冲突时,葛任并没有意识到权力话语的主宰力量,这使他必然要成为 权力意志的牺牲品。所以,在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方式后,作为一个毫无 战斗经验的书生,葛任却要肩负起在战争前沿递送情报的工作,这有点像一个不懂武功 的人背着长剑去笑傲武林,看似颇具荒诞意味,其实质却是生动地展示了权力对知识( 也即真理)的一种异化和扭曲。它所演化出来的具体表征,便是历史对个人命运的悲剧 性摧毁。
然而,更富意味的是,葛任并没有在这场历史与个人的争斗中死亡。他侥幸地躲过了 这场既是历史又是命运的双重劫难,逃到了一个叫白陂的地方安顿下来,并期望东山再 起。但是,历史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以及葛任自身的身体状态,都决定了他不可能再度 获得边区政府的信任和重用。这时,历史再次发出了更为可怕的权力信号——由边区人 员去秘密杀掉葛任。对此,李洱尽管没有在小说中提出明确的理由,但是透过不同叙述 人的回忆,我们还是不难得出结论:一是让葛任的一生“圆圆满满”,(“葛任的代号 是0号,取的是圆圆满满的意思。”)即,让他以牺牲在二里岗的战斗中作为生命的历史 终结点,因为此后的生命不仅对于葛任自己已没有任何文化伦理上的“价值”,而且对 当时的权力体制也没有了使用价值。二是葛任的继续存在,不但会消解他已经在不知不 觉中建立起来的“民族英雄”的历史角色,还会对边区的权力意志以及历史自身的演进 构成潜在的威胁。同时,来自敌对势力的国统区和日本鬼子也都发现了葛任存活的迹象 ,并开始对葛任进行不断的追踪与捕杀。葛任再次陷入了更深更大的劫难之中——历史 以其戏剧性的方式让他逃过致命的一劫,却又将他不动声色地演化成各种政治权力的共 同击杀对象。
在这种万劫不复的历史境域中,李洱突出的不是故事自身的传奇性和神秘性,而是葛 任必须死亡的“合理性”。他试图通过每一个叙述者的不断叙述,为葛任的死亡建立起 一种强大而有力的文化伦理体系,凸现个人死亡在历史中的独特价值以及在中国传统伦 理中的生命价值。在这个伦理体系的表层,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民族英雄的神话,即,以 生命的丧失为代价实现自身作为民族英雄的人生目标,而它的潜在意图却是历史背后的 权力意志对自身利益的自觉选择——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日本鬼子,似乎都希望 通过葛任的死亡来圆满他的人生价值,而实质却都是为了铲除危及自身利益的遗患。所 以,奉命去执行这项任务的范继槐就认为:“最好是川井来把这事给办了。那样一来不 管谁赢谁输,不管历史由谁来写,民族英雄这个桂冠葛任都戴定了。……天地良心,我 是因为热爱葛任才这么做的呀。当时我就想,这事最好不要传出去,如果真的传出去了 ,那我就可以给别人说,没错,葛任确实死在了大荒山,不过,那是日本人干的。”他 对日本鬼子川井也这样说:“葛任现在已经病重了,我给你一个帮他的机会,你去把他 杀了。一来葛任就成了我们的民族英雄;二来等你回到了武汉,你可以对你们领导说, 你把葛任干掉了,这样你也就成了你们大和民族的英雄。”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阴谋, 更是一个权力的阴谋,它成功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中对死亡价值的倚重,也成功 利用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爱和友情,并以此作为谋杀的“合理性”依据,来实施对历史 与生命的双向颠覆。《花腔》的核心意义也正在这里。它不仅为我们撕开了历史与权力 、个人命运与历史命运之间的背谬性状态,还将笔触延伸到我们的历史文化中,对我们 长期恪守的伦理价值体系与个人生命的真实意义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李洱在《花腔》里所要表达的这种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对峙状态,使我想起了博尔赫斯 的短篇小说《叛徒和英雄的故事》。那个名叫基尔帕特得克的爱尔兰民族起义领袖,因 为充当了叛徒和英雄的双重角色,当他的手下人诺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时, 与会者一致要求将基尔帕特得克判处死刑。基尔帕特得克本人也亲自签署了这项判决, “他还请求大会对他的惩罚不要危害祖国的利益。”于是,“基尔帕特得克在扮演这个 既能使他赎罪又会使他丧命的角色中,不止一次地用他那些即兴动作和语言丰富了他作 为法官的台词。”最后他成功地利用演出完成了自己作为英雄角色的死亡。《花腔》与 这篇小说在审美内涵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3.故事:诉说与呈现
对于李洱来说,《花腔》的超越还体现在它的叙事方式上。他试图通过诉说与呈现的 双向互补,为小说建立起一种完整而严密的文本结构,同时又利用诉说与呈现的不同安 排,将故事自然分离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作为诉说部分的鸰和作为呈现部分的&,既 是一种相互补充和印证,又是一种相互独立和分离。它们作为一种整体,起着结构故事 、完善叙事的支撑作用,倘若以它们各自为单元进行新的组合,则又可以生成为两个相 对独立的文本。尽管这两个文本显示出各不相同的审美情趣,一个因为人物性格和身份 的不同,在饶舌式的口语化过程中,呈现出强烈的感性特征,一个则由于“史料”的引 用和串联,在推理和分析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理性特征,但是,这两个文本的审美 目标却完全一致,那就是:在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与历史之间的无奈 状态。
就“诉说”部分而言,李洱充分利用了一种民间化的叙事法则,通过极具个人化的“ 讲述”方式来对历史进行民间性的追述和重构。三个不同的叙述者,既是葛任命运的直 接参与者,又是整个历史真相的见证人;他们一方面在诉说历史真相,以相互补充的方 式从不同角度、不同时空中还原葛任的命运际遇和人生轨迹,另一方面又在这个过程中 自然而然地展示出自身的命运轨迹和人生际遇——这些命运轨迹和人生际遇同样也构成 了对历史的尖锐质疑。无论是白圣韬、赵耀庆还是范继槐,他们的命运同样也处在种种 无法把握的失控状态,他们的信念追求与历史之间同样也处于永难调和的尴尬状态,这 也进一步强化了作者对葛任与“个人”之间的隐喻,即《花腔》的葛任其实是指历史中 的任何一个个体的人。而就“呈现”部分而言,李洱又套用了某种考据学的思维逻辑, 不断地为历史设置种种富有情趣的“史料”,让叙述者不停地徘徊其中,并做出种种发 现、甄别、分析和判断的“严谨”姿态,借以强化叙事话语自身的严密性审美效果。
但是,随着叙事的发展和故事情节的自然延伸,我们终于发现,历史的真相永远是一 个迷津。“好多事用阿庆的嘴说出来是个样,用范老的嘴巴说出来是另一个样。”不仅 故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的“诉说”相互矛盾,而且大量的“史料”也同样呈现出相互抵 牾的情形。李洱的真实用意也许就在这里。他或许根本就不相信历史的真实性。一切历 史都是人心中的历史,都是以个人的记忆和判断为前提的历史。尽管从本体的角度上说 ,历史是客观的,它是一种独立的和外在的东西,不为人的意志和行为所左右,对历史 ,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改变和增损它的分毫。但从认识的角度上说,历史又是主观 的,历史只存在于个人的记忆和思考之中,历史怎样,取决于个人对它的记忆和思考。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看,认识历史就是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本体,但是不幸的是,人 类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主观认识上的局限,个人所知道的历史始终只是 某时某地他所能达到的历史认识,而不是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既然历史本身就充满了 这种迷津,那么历史中的个人命运以及人生情怀,又如何能获得完整的还原?因此,一 切历史的真相,都永远地站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遗憾的是,李洱的《花腔》虽然触及 到了这种人类历史的荒谬性本质,但是,它并没有对这种根本性的荒谬做出更为清晰的 审美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