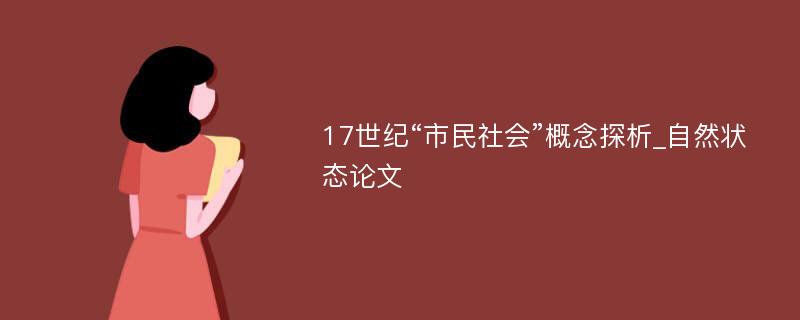
17世纪“公民社会”概念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概念论文,世纪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近代公民社会理论的形成初期是17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再度流行,并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注:在当代使用公民社会概念的西方学者中,不管是二分法(即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视为各有其领域、价值、作用方式)还是三分法(将公民社会视为国家与家庭或个人之间的第三领域),也不管他们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对抗、制衡的,还是看作共生共强、合作互补,在将公民社会视为与国家相对的概念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在国内的一些研究与介绍当中,“公民社会”被视为反对“国家”的专制主义与对市场干预的有用理论,而近代公民社会理论也被认为是以“国家与社会分离为基础”的、“反对专制主义国家和重商主义国家”的“重要武器”。[1]但实际上,在作为近代公民社会理论形成时期的整个17世纪,"civil society"一词不仅不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基础”,而且与政治社会,甚至国家同义。在17世纪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那里,公民社会概念并不是“反对专制主义国家……的武器”,而且在一些思想家的学说当中简直是维护专制主义国家的武器。在17世纪的政治话语(或学术话语)中,与公民社会概念相对的,不是国家,而是“自然状态”。由于"civil society"概念将是世界、尤其是中国“新世纪的学术话语”,正确处理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成为21世纪中国人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追根溯源,探讨西方近代公民社会理论形成初期的公民社会概念,显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Civil society"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约在14世纪开始为欧洲人采用,其含义则是公元前一世纪为西塞罗所提出的。它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的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态。这些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典(市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性(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相互合作,依据市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享受着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2](P125)在拉丁文中,与此词含义相近的还有civitas,意指政治上组织成共同体的一群人,而特别指城市国家。
17世纪政治思想家继承拉丁语中的"Civilis Societas"与"Civitas"所包含的“共同体”含义。所谓共同体,它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或家庭的聚合,而是一种有机的联合。正如普芬道夫所指出的:“公民社会不仅仅是聚在一起,而且是联合在一起。”[3](P204)或如霍布斯所说的“全体真正统一于唯一人格之中”。[4](P131)
何以判断人们是聚合还是有机的联合,如何判断众人的意志化为了一个意志,众人的判断化为了一个判断?只有通过建立一个最高的统治权威,使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体都服从于它。在霍布斯看来,只有存在主权这一最高权力,并通过主权者对这一权力的代表,公民社会才算是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法人,而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的松散集合[5]。洛克同样将家庭之间的社会及主仆之间的社会与公民社会分开,认为只有在“置于一个有最高统治权的政府之下”的情况下,才算是形成一个公民社会。[6](P54)虽则他并不主张这一权力是绝对的(absolute),但他毫不怀疑它必须是最高的(supreme)。以最高统治权即主权的建立与人们对最高政治权威的一致服从作为公民社会概念的核心要素,是17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对原有的公民社会概念的一个重大改造。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大改造是公民社会的范围与基础。17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摒除了将公民社会局限于“城市”共同体的意思,将公民社会的范围与基础扩展并固定在新兴的近代民族国家之上,从而使其真正地成为近代公民社会理论。霍布斯将"Civitas"与英语中的"State"(国家)、尤其是"Commonwealth"即国民共同体或国民的整体等同[5]。洛克则更为明确地排除将"Civitas"视为一般共同体和将共同体局限于城市的可能,指出英语中的Community(共同体)、City(城市)都不恰当,只有"Commonwealth"才能“最确切地表达人们的那样一种社会。”[6](P81)洛克反复提及公民社会拥有立法权和执行权,并曾在《政府论》下篇中,两次将“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并提,称"Civil or Political Society"(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这就是说,在17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的心目中,“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意义基本相同。而17世纪政治理论普遍认为,一群人当中建立起公共政治权威,有了命令与服从关系及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也就建立起了国家。[7](P200-201)这样,“政治社会”又与近代“国家”的含义基本相同。霍布斯与洛克等思想家有社会契约论而无政府契约论。[8]在其描述中让人们通过契约直接从自然状态进入到公民社会状态,亦即政治社会状态或国家状态,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家与社会的未加区分。这些事实表明,17世纪的一般思想当中,并没有后来的学者们对公民社会与国家所作的那种严格区分。公民社会与国家都意指政治社会,而不象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后来的众多思想家所指的与国家相对的经济社会(社会的经济领域或非政治的民间社会)。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主要是黑格尔改造了公民社会的内涵,他的"burgerliche Gesellschaft"具有多义性,它一方面保留了17世纪思想家“公民社会”的内涵,即指国家,黑格尔有时称它为“外在的国家”,“知性所理解的国家”(与理性所理解的国家相对);另一方面,它又被赋予与国家相对的特殊性领域(国家是一般性和普遍性领域)、经济生活领域、私人领域等涵义。[9]该词再译为英文时含义不定,有时意指资产阶级社会,有时意指市民社会。[2](P126)但"civil society"一词从此作为特别意指经济和社会秩序,或非政治领域的一个术语,却为西方学者所沿用。从该词意指经济或社会领域这一意义来说,将之译为“市民社会”应是妥当的。而从该词在17世纪意指公民由自然状态下的人进入或加入政治社会会成为“公民”这一意义来说,将之译为“公民社会”同样妥当。因此,"Civil society"一词之翻译成“公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恐怕不是因为前者是中性,后者带贬义[10],而是因为其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二
与当今西方学者将“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对立的作法不同,17世纪的公民社会概念有着另一个为思想家们一致认可的对立概念,那就是“自然状态”。如果说17世纪的重要思想家们在对公民社会的具体描绘方面尚存差异话,那么,在将公民社会与自然状态相对立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毫无例外的。
因此,要理解17世纪的公民社会概念,必须首先理解“自然状态”说。事实上,17世纪的思想家们提出自然状态说,其最终目的都在于论证公民社会之必要与优越。正如普芬道夫所言:“因为仅从自然状态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组成公民社会的必要性与理由,发现权威与义务源自公民社会的本质,最后发现从公民社会中产生的优越性与特别的意义。”[3](P109)
自然状态是人们自由、平等、独立的状态。但是,这又是有着严重缺陷的人类状态。相应地,公民社会则正是对这些缺陷的弥补。因而公民社会的意义首先表现在17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对自然状态的缺陷之认识与对自然状态的贬抑之上。
首先,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野蛮状态、有严重缺陷的状态,而公民社会则是文明状态、相对完善的状态。自然状态“是文明社会中生活所使用的所有发明与风俗习惯均被祛除的一种状态”,[11](P110)就这一方面而言,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绘具有典型意义。他认为,自然状态即是一种战争状态,是一种每个人都有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可以将一切事物和其他一切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的状态,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4](P94-95)自然状态、战争状态之缺陷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自然状态下的人类被他描绘成“正如狼对狼”,而政治社会状态下的人类状况则被描绘成“正如神对神”。[12](P24)其所以有如此截然的对立,是因为自然状态缺乏和平与安全,拥有的只有“战争的两个女儿:欺骗与暴力”;而公民状态下人与人(此时是公民与公民)得以拥有“正义与仁爱”——“和平的两个孪生姐妹”。[12](P24)普芬道夫同样对人类社会的这两种状态进行对比,并在强烈的对比当中抑此扬彼,显现政治社会之必要与优越:自然状态中是激情在统治,那儿存在的是战争、恐惧、贫困、卑贱、孤独、粗俗、无知、野蛮;而国家中是理性在统治,存在的是和平、安全、富裕、显赫、社交、高雅、知识、仁爱。[13](P118)洛克不同意霍布斯和普芬道夫将自然状态的缺陷描写得极其严重,而将国家视为“最完善的社会”,[14](P202)但他们之间的差别是程度上的而非实质性的。因为洛克同样不得不承认自然态有着“许多缺陷”,留在自然状态当中的“情况不良好”。[6](P77-78)因而人们要么组建一个公民社会,要么加入一个已经存在的公民社会。脱离有缺陷的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社会状态,是17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给人类指出的唯一合理的选择。
自然状态的根本缺陷,或公民社会之有异于自然状态,并且在于有无政治权威及对权威的服从。就17世纪(特别是前期)政治思想的典型特征而言,和平、安全与秩序是首要的政治价值,而这些价值只能在公民社会当中,通过建立与服从一个最高的政治权威才能拥有。在霍布斯等人看来,有了政治权威对每个人相互之间的破坏性欲望与倾向的威慑,以及人们通过契约对主权权威的让渡,得以保持人类的和平与安全。[4](P132)普芬道夫还特别指出,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进入国家,其原因不是因为贫穷(因为初级社会中家庭即可缓解这一困难),而是因为自然状态下几乎不能保证安全。简言之,“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只凭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在国家中可以通过所有的人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自然状态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得到保卫,而在国家中每个人都可以确信乎此。”[13](P118)洛克也要求人们要“设置一个明确的权威”以定分止争,要“置于一个有最高统治权的政府之下”以进入社会,组成民族和国家。只不过他不像霍布斯那样主张将自然权利交给主权者,而是主张交给社会,交给公众。格劳秀斯、塞尔丹,霍布斯、斯宾诺莎、普芬道夫虽对自然状态、契约论、国家形式等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将政治权威视为公民社会或国家之根本要素,在将有无政治权威视为公民社会或国家与自然状态之间最大的区别这一点上,是大致相同的。
三
原来,公民社会的存在,正是人们为了避免倒退到自然状态,丧失和平与安全以及人类文明所拥有的一切成果之所必需。那么,为什么17世纪的思想家们没有社会与国家区分的意识,却都将公民社会与国家等同于政治社会,而与自然状态相对呢?
对17世纪上半叶的人来说,“似乎社会本身处于危机之中,而且这种危机在整个欧洲都十分普遍。”1643年一个英国牧师说:“当今正是摇摇欲坠的岁月”,“而且这种摇摇欲坠十分普遍,巴拉丁领地,波希米亚、日耳曼尼亚、加泰罗尼亚、葡萄牙、爱尔兰、英格兰”,整个欧洲似乎同时陷入了同样巨大的悲惨境地之中。[15](P252)30年战争开始后,甚至“有不少人在谈论社会或者世界的解体”。30年战争使欧洲哀鸿遍野,其惨状更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英伦二岛上胆小而敏感的霍布斯的感受自不待言,洛克所遭遇的也好不了多少。17世纪中叶前开始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止,凶猛的宗教世俗战争,以及宗教迫害、瘟疫和其他种种不幸也将英国折磨得遍体鳞伤。“面对这样的经历,难怪普芬道夫和17世纪其他的主要思想家会在他们的社会理论中着力于所谓的‘自然状态’”,也无怪乎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国家权威存在偏好,对社会解体有着真正的、理由充足的恐惧。[17](P4-5)
正是出于对文明社会解体的担心,正是为了防止文明生活中断或倒退到类似于自然状态那样的境地,为了使人们能够拥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繁荣发展之基,17世纪的思想家们普遍地诉求于公民社会或国家。他们求助于国家这一架构来维持文明社会(甚至直接把国家状态当作文明社会),而以政治权威及对政治权威的服从来维持国家。为达此目的,有的思想家(如霍布斯)甚至不惜让人们托庇于绝对权力之下,公民社会理论在他那里成为维护绝对主权(即一般所谓专制主义、绝对主义)的武器。而斯宾诺莎、普芬道夫等虽然并不赞成绝对专制的国家形式,对于臣民的自由也有着比霍布斯更为开明的主张,但他们政治思想的重心却都是通过维护国家的政治权威来维护国家或公民社会。即令他们明知公民社会中国家权力有着种种不自由、不方便之处而难以忍受。公民社会的种种不便一方面可以通过诉诸西方关于人与人类制度的传统观念而得以消解,如霍布斯即说,凡人的东西总没有十全十美的;斯宾诺莎、普芬道夫同样以此劝说人们忍受公民社会的不便;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可将这种难以忍受与另一种更难以忍受的人类状态对比。自然状态说即有此种功用。这一点在思想家们的头脑中有着清醒的认识。将自然状态描绘得最为详尽的普芬道夫即坦言:“我本人认为面对大众关于公民国家状态的负担与缺陷的抱怨,没有比给他们描绘自然状态的缺陷更好的方法。”[17](P588)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17世纪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加以区分,而是热衷于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即国家状态)之间的区分。在整个17世纪乃至其后的18世纪,当代学者所称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在近代西方社会当中均有如尚未成年而又处于患难之中的兄弟,共同面对的是防止类似“自然状态”那样的状态出现,需要的是二者的相互支持与帮助。不仅“公民社会”的发育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促进,而且“公民社会”的存在本身即需以“国家”的建立与维持为条件与基础。公民社会、政治社会与国家甚至是同一的。因此,认为近代公民社会理论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甚至以公民社会对抗国家,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也不符合近代公民社会理论,至少是17世纪公民社会概念的真实状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