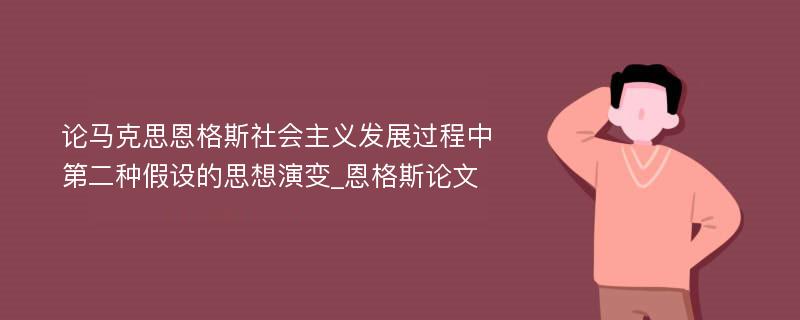
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第二种设想的思想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第二种论文,发展进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5)02-0012-07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否形成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问题,在我国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学术争鸣,取得了不少十分可喜的成果。意见与看法尽管不统一,甚至相左,但对我们这些对此问题没有专门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来说,还是很有教益的,至少启发了自己的思考。对于这场争鸣本人未参与其中。然而,最近看到有的同志发表文章,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有无“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像做结论似的、斩钉截铁地予以否定:关于东方社会道路的争论理应终结,理应走出“东方社会道路”的理论误区,理应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理应剔除已写入教科书的所谓“东方社会道路理论”。这倒引起了我的一点兴趣,并决定把自己在完成《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课题过程中,形成的一篇粗浅的东西,即“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第二种设想的思想流变”,送出发表。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缺乏专门研究,无能力参与争鸣,发表这篇东西的目的,完全在于争取同行、特别是对此问题有过专门研究的同志的批评指正。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从资本主义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历史进程的设想有两种:一个是主要的,属于一般范畴,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同时发生和取胜;另一个是,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主要的,并属于特殊范畴,即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第二种设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经过长时间艰难探索的结果。从他们的第一种设想到第二种设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时间约40-50年。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中下叶至1883年3月逝世前夕,一直进行探索;思格斯对此问题的探索,一直延至1895年。
第一阶段:开端与早期(19世纪40年代中下叶,特别是整个50年代)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问题探索的结论是:民族历史必将走向世界历史,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论文与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主要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问题,是因为此时的亚洲正爆发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民族解放高潮。当时,英国在亚洲各地正进行着疯狂的侵略,英国国会经常就其侵略和殖民政策展开辩论。马克思开始研究这些辩论的材料,并阅读了詹·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英属印度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理·琼斯的《政治经济学导论》和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帝国最新革命史》等著作。他将研究的初步心得于1853年5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作如下表述:“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第256页)恩格斯在1853年6月6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表示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并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他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的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它是19世纪对中亚细亚和土尔克斯坦的一部分地区的称谓)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1](第260-263页)由于任何个人都无能为力承担灌溉任务,所以,这一地区一开始就排斥了任何土地私有制,只能实行土地公有制。
马克思在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他研究的理论成果作了更充分的论述。他认为,和土地私有制形式完全不矛盾的是,“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实际即是以专制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引者注)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因为这种统一体是实际的所有者。……而在这些单个的共同体中,每一个单个的人在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对这单个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通过这些单个的公社而赐予他的。因此,剩余产品(其实,这在立法上被规定为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2](第473页)在这里马克思把村社、土地所有制与君主专制国家三者紧密结合为一体,看成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东方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主要特点。当时,马克思把具有上述特点的东方社会与国家之封闭、落后的种种表现描述得淋漓尽致。他指出:“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服的猎获物。……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他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3](第765-766)
那么,在马克思看来,东方落后国家走向何处呢?材料表明,马克思认为,这类国家唯一的出路是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前资本主义历史都是狭隘的、地域性的民族历史;世界历史是指各民族、各国家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普遍交往、打破民族封闭与孤立状态,进入相互依存、相互交往的世界整体化的历史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在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先于东方落后国家,但它本身并不是世界历史的终点。在未来共产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人类彻底解放,才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标。东方落后国家如何才能走向世界历史呢?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冲击下,将东方落后民族及国家卷进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头的世界文明的历史中去。资本主义冲击有两条途径:一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自发冲击。比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3](第88-89页)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轰开东方落后国家的大门。就像征服印度与中国那样。对此,马克思虽然对被英国征服的印度、对被英国侵略的中国表示极大同情,但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他还是认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无论一个古老世界的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3](第766页)
基于马克思早期对东方社会的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发展之普遍规律对东方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抗拒的制约作用,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国之崩溃是历史的必然,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必要条件。
(2)世界历史的发展并非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中通过这惟一的道路走向人类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之最终目标,更不能像资产阶级学者那样,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人类世界历史的终点。
(3)东方社会各国、各民族由于具体情况有差异,其完成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途径与方法不会完全一致。
第二阶段:中期(19世纪70-80年代初)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处理西方先进国家与东方落后国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由东方从属西方、特殊从属一般转变为更加关注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提出俄国等东方半东方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使其早期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取得了新突破。
马、恩早期对东方社会的探讨,虽然发现了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即村社、土地公有与君主专制三位一体,但是,他们又强调,在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要走向世界历史将失去自己的特殊性。很显然,马、恩当时还是受“西方中心论”和用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来框架东方社会的。用现代时髦的话说,他们当时在分析东方社会发展问题时,尚未自觉地将自己的学说与东方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没有“东方化”。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还未提供更丰富的材料。比如,马克思在1859年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还把亚细亚社会形态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第33页)可是,到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问世后,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就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证明不是亚细亚社会形态了。
马克思在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大量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版与发表的人文历史文献之后,认为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与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类型。相对于最初原生形态的氏族公社,那种割裂了血缘的联系、农民在公社内享有一定的私有财产、土地属于公社所有的农村公社,如东印度、俄国的农村公社,往往是古代形态的最后阶段或最后时期。为此,马克思便从此开始把出现私有制社会以前的原始社会称为“古代社会”,使“原始共产主义”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处于人类社会史的初始地位。
当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认识较为清楚之后,就十分坚决地反对以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作为惟一标准来衡量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反对把世界历史挤压到单一的欧洲模式中去。他认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开创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转向世界历史的条件下,落后民族与国家可以实行某种跳跃式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认真研讨了俄国农村公社及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的大量资料之后,集中论述了他们的第二个科学设想。反映这一设想的科学成果,主要体现在马克思1877年10月至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2月底至3月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及《复信》,恩格斯1874年5月至1875年4月所写的《论俄国社会问题》,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合写的1882年俄国版序言等著名文献之中。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马、恩特别是恩格斯,在同俄国有关人士讨论俄国村社是否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时,对于他们一贯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即必须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点,毫不动摇。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这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力提高到以至于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不致在社会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倒退的水平。“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5](第273页)马、恩对某些俄国人认为像俄国这样的“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更容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表示坚决反对,认为那就不过证明,他们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第二,科学地回答了像俄国农村公社那样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其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的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第251页)很清楚,马、恩的共同意见是:用假定方式,有条件地肯定了像俄国农村公社这样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可是,从研读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马、恩有关这方面的文献看,恩格斯虽然赞成《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的基本观点,但他本人更倾向于不轻易肯定。从其《论俄国问题》一文中,就能看出这种倾向。首先,他认为,劳动组合即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合作社,明确指出:“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自担风险、有利可图地经营大工业(如兰开夏郡纺织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它甚至必然要亡于大工业。”[5](第279页)其次,恩格斯批评哈克斯特豪森、赫尔岑、巴枯宁、特卡乔夫等人利用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宣传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指出,“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作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的威斯特伐利亚故乡也能找到不少公社所有制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有义务确切了解这种残余的情况。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并把他们同西欧的共产主义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5](第279页)恩格斯认为,农村公社,“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远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5](第278页)说俄国人是“社会主义的选民”、“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纯粹是胡说八道。[5](第282页)最后,恩格斯一方面断言:“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渡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另二方面又不把问题说绝对,即不否认它有可能转变为高级形式。然而,他认为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条件”。[5](第282页)
我们从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及《复信》中所看到的情况是,马克思比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积极方面肯定得较多。比如,他说:“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的观点,则反问题道:“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5](第762页)同时,他还要求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说明下面的问题: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这种可能性的条件:“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要靠农民来偿付)向那些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提供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么,现在谁也不会再臆测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大家将都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和一种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5](第762页)马克思还论述了俄国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另一方面,俄国农村公社的房屋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原始的公社条件下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
这样,俄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前途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容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两种可能都有。“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利于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5](第765页)
从以上马、恩的分别论述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两人虽然基本观点如《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所阐述的一样,但就各自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论述来看,他们的倾向性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这一设想时,是同他们对当时国际环境的科学分析有密切关系的。
自1848年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大约四十多年的时间内欧洲处于革命风暴年代。当时,国际环境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沙皇俄国始终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掩蔽部和保护伞,是反对革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内)的最后支柱。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欧洲工人运动一直未能取得胜利,除了其他深层、浅层的内部原因外,沙皇俄国在欧洲各国进行革命时,总是帮助官方反动政府镇压革命运动,是几十年来欧洲每次大的工人运动总是失败的重要外部环境。然而进入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俄国以民意党人为主发动的革命恐怖活动,闹得沙皇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情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很有利于欧洲乃至世界的工人运动。认为,如果在沙皇俄国闹起革命来,那么不仅沙俄再也不能充当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后备军,而且还可能俄国发出革命信号,西欧各国无产阶级相继进行革命,二者互相补充,使西欧与俄国的革命形势高涨,有可能加速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与胜利。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可以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使他们一直保存的农村公社就可能变成共产主义的起点。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基本思路。这也是马克思为什么在晚年身体多病的情况下,还专门学习俄文以关注俄国等东方、半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的前景及其道路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阶段:后期(19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在这一阶段,恩格斯结合马克思逝世后发生的新情况,对俄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问题作出了总结。总结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恩格斯1894年1月所著的《〈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以及1892年6月和1893年2月24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等文献中。
其一,恩格斯将20年前在其《论俄国社会问题》一文中关于赫尔岑及其追随着特卡乔夫以及伟大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社会问题的幼稚观点,进行了新的概括: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在俄国则已经解决;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限地接受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限地好;旧的经济世界不是从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从俄国农民的最内在的东西中得到新生的。恩格斯说,“我的抨击也就是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6](第438页),“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6](第440-441页)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6](第441页)
其二,较低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能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产生的问题。对此,恩格斯依据其唯物史观作了精辟论述,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是完全适用的。”[6](第442-443页)
其三,东方的一切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并避免在西欧开辟社会主义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恩格斯说:“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精神,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6](第443页)
其四,俄国日益迅速地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大国,很大一部分农民日益迅速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公社日益迅速地崩溃。对此,恩格斯论述道,马克思在1877年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跳进资本主义,其原因是民粹组织、土地与自由社和民意党的势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支柱,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6](第447页)然而,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民粹派、土地与自由社和民意党人。在马克思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后的17年,即1894年间,俄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6](第448页)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越来越接近民粹派、民意党人所没有达到的“让沙皇制度投降”的目的,因为沙皇制度需要钱,没有钱沙俄就要破产,其外交政策就要完蛋。“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这样一来,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6](第450页)
其五,只有在俄国实现了推翻沙皇制度的人民大革命,才可能使农村公社得以挽救。恩格斯说:“这种公社是否还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我不能予以回答。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想保存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6](第450-451页)
前边,我们已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19世纪70年代时,马、恩对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积极方面,尚予以重视,同时,也批判了他们认为“在俄国农村公社基础上可以直接长出社会主义来”、“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是“上帝的社会主义选民”等错误观点。19世纪80年代,先前是民粹派成员,后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普列汉诺夫,“是给了民粹派错误观点一个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第一人”。他一方面,给民粹派观点以一针见血的批判和致命的打击;同时,又光辉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然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俄国资本主义已获得巨大发展、而农村公社接近瓦解的时候,有一部分信奉民粹主义的青年,仍然坚持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坚信将来在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粹派的余孽多方阻碍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于是,此时登上革命舞台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承担起了从思想上彻底粉碎民粹主义的历史任务。
列宁在其《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彻底揭露了那些冒充“人民之友”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真面目。他指出:90年代的民粹派,实际上已根本放弃了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主张同沙皇政府妥协,已由革命的民粹主义者堕落为自由主义民粹派;自由主义民粹派还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者,诋毁、曲解马克思主义观点,硬说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农村破产,想把每个农夫都拿到工厂锅炉里去受煎煮;然而,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望”,而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过程,无产阶级的人数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大大增加,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俄国,愿意消灭资本家、地主压迫和沙皇制度的真正的“人民之友”,绝不是民粹派,而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早,我们可以看出,当列宁走上革命舞台之时,俄国已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当然特点是军事帝国主义,是比欧美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在俄国搞革命应是工人阶级领导、同广大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先搞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基础上适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设想。但是,当苏东剧变后人们重新反思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斗争的道路时,有人否定十月革命,把苏东剧变归罪于列宁和列宁主义。
我们反对这种非科学的态度,但非常赞成做“事后诸葛”,以科学态度总结经验教训,以使今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得更健康。比如,反思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维克党举行武装起义,发动十月革命是正确的。但是不是列宁从芬兰回到俄国一下火车,就一定非喊“社会主义革命万岁”不可?把十月革命的性质定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成熟呢?我认为,发动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武装夺取政权是正确的,但夺取政权后,完全可以继续执行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的理论与策略,先搞“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在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里奉行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那样的政策,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当时,如果这样决策,也许前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与结果和现在会有很大不同,有可能避免像苏联剧变这样的大失误。当然,革命不是“算命先生”,更不能假设,历史就是历史,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消极地埋怨与后悔,甚至全盘否定列宁主义,则是形而上学的非科学方法,是不可取的。
标签:恩格斯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