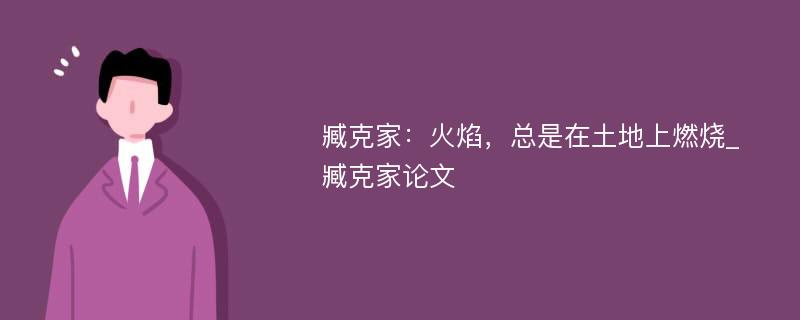
臧克家:火焰,永远在泥土上燃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泥土论文,火焰论文,臧克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平
“世纪诗翁”
2004年2月5日晚,被国际诗人笔会授予至高金奖的“中国当代诗魂”臧克家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9岁。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认为,臧克家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一位对新诗做出重大贡献的诗人”,并且指出,臧克家以及另一位重量级老诗人辛笛的相继离去,说明“中国诗歌史的辉煌一页落下了”。
臧克家1905年10月生于山东诸城。1946年至1948年任上海《侨声报》文艺副刊、《文讯》月刊、《创造诗丛》主编。建国后,历任华北大学三部研究员,新闻出版总署编审,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理事、顾问,《诗刊》主编、编委、顾问,中国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至三届理事。
诗路漫漫,何其修远。从1929年12月在青岛《民国日报·恒河》上发表《静默在晚林中》始,臧克家在中国新文学的土地上耕耘了70多个春秋,共出版诗歌、散文、评论、小说等70余部;他在诗歌领域的成就更得到高度评价。2000年1月20日,中国诗歌学会在人民大会堂授予“世纪诗翁”臧克家“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这是诗歌界史无前例的荣誉。
艺术
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
综观臧克家的创作历程,其艺术世界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光明与黑暗二元对立的审美精神模式。他不仅是一道照亮了诗界的“火光”(王统照语),更是一个一生都在追逐光明、鞭笞黑暗的诗人,有人称他“用诗歌点亮一个时代”。在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臧克家诗选》第二卷的“序”中,年过七旬的臧克家说“我想用自己几年前的两个旧句,来给这个选集的序言作结:‘年景虽云暮,霞光犹灿然’。”而在1984年花城版的《落照红》的卷首,年近八旬的老诗人又一次说“我有两个旧体诗句,足以表现我的心情:‘年景虽云暮,霞光犹灿然。’”
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人情感世界的真实写照。无论是《老马》、《老哥哥》、《罪恶的黑手》等揭露下层现实、以忍辱负重劳动者的悲剧形象闻名的早期抒情诗,还是“放开喉咙”、“高唱战歌”的抗战诗;无论是“用一支淡墨笔,速写农村,一笔自然的风景,一笔农民生活的缩影”,与《烙印》一起被诗人视为“我的一双宠家”的《泥土的歌》,还是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所创作的、大多收在《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等诗集中的大量政治讽刺诗,都呈现出这样一种强烈的精神诉求——“当眼前没有光明可以歌颂时,把火一样的诗句投向包围了我们的黑暗叫它燃烧去罢!”(《刺向黑暗的“黑心”》)。
黑暗与光明的对立成就了臧克家的诗歌特色,但也由此坠入了一种模式化的窠臼之中。在《臧克家文集》所收录的诗歌中,“太阳”与“火焰”的意象随处可见。以其本人以及研究界最为欣赏的30年代诗歌创作为例,据笔者统计,1929-1931诗收录6首,而有此类意象的3首,占到50%;收1932年诗26首,其中16首诗有此类意象,占61%;1933年收诗21首,14首诗有此类意象,占66%……所收1936年的14首诗,只有5首没有此类意象。
可见,臧克家对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式的揭示的确情有独钟,这未免有单一化之嫌。迄今为止备受推崇的经典之作《有的人》,其实正是这种二元对立审美情趣与思想方式的极端体现。在这一点上,终其一生都未能超越自我。
贡献
不可替代的“泥土诗人”
在中国现代诗史上,有两位青年诗人曾经于1933年自费出版了首部诗集,他们后来都成了诗界的名人。其一是北京大学学生卞之琳,自费出版了诗集《三秋草》;另一位就是当时还在山东青岛大学上学的臧克家,其第一部诗集《烙印》在闻一多、王统照等人的资助下得以出版,并很快被抢购一空,好几家书店争相抢夺其再版权。臧克家在创作上受到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影响,他尤以《死水》为楷模,在实践中体味与琢磨闻一多倡导的“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等艺术主张,努力克服当时流行的过于散文化、口语化的创作倾向,注重锻字炼句、着意谋篇,对想像、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亦煞费苦心,形成了一定的艺术特色。
然而臧克家作品更引人注目的是其所呈现出来的贴近人民大众,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风格及忧患意识,这一点在其后的诗歌创作(如《罪恶的黑手》、《运河》等)中得到了一脉相承的贯彻。以茅盾的说法,他关注的不是女人的“酥胸玉腿”,甚至也没有所谓“玄妙的哲理”以及什么“珠圆玉润”的词儿,而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笔下多为捡煤球的姑娘、难民、老哥哥、贩鱼郎、炭鬼、补破烂的女人、洋车夫等下层民众。
这种创作姿态与艺术风貌正迎合了“五四”以来所涌动的“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等虽为启蒙口号所遮蔽、却一直深潜暗流的民粹主义思潮。臧克家由之被冠以“泥土诗人”的称号,也因此得到了不少名重一时的文学史家、评论家的青睐:茅盾称他是当时青年诗人“最优秀中间的一个”;朱自清说“从臧克家开始,我们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闻一多先生在为《烙印》所作的序言中对臧克家“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一句所代表的人生与创作态度非常激赏,称赞“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也被后来的诗歌评论界推崇为“诗与精神的完美结合”(孙玉石语)。
民粹主义不像启蒙思潮那样以启发民智为己任,而是以“民”(尤其是农民)为“粹”为尊,将农业文明的非物质性因素道德化、理想化、审美化,崇尚自然,鄙薄工业文明。这一点在臧克家的文学观与创作实践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他说自己的“血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我的诗生活》),真诚宣告“我昵爱、偏爱着中国的乡村,爱得心痴、心痛,爱得要死,就像拜伦爱他的祖国的大地一样。我知道,我最合适于唱这样一支歌,竟或许也只能唱这样一支歌。”(《当中隔一段战争》)
臧克家1946年所说的这一句话果真成了预言,他的确始终没有走出忍辱负重的“老马”的神话,也始终没有走出农业文明的幽光。在为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六卷本《臧克家文选》所做的序言中,老诗人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他对抗战时期以及解放后的作品不太满意,“抗战期间……作品情调明朗而爽快些了,但不少是浮光掠影的,精粹而具有时代特色的不太多”;建国后三十五年来“也写了一些比较为读者所熟知的长诗、短诗和散文;可是写出的诗篇,不论就时代意义或是现实意义上讲,已经比不上30年代初、抗战末期那种势头了”。不过,作者对《烙印》以及40年代初期创作的诗集《泥土的歌》则一直怀有由衷的喜爱,他认为30年代的作品很有分量,而《泥土的歌》则“是一本关于我心爱的乡村的歌,一本关于我亲爱的农民兄弟的歌,一本从我心底流出的真诚的、热情的、纯朴的歌。”他的小女儿苏伊回忆说,父亲跟农民朋友感情最深,在他80多岁第三次写到他的老哥哥和六机匠时,痛哭得写不下去,不得不到卫生间去洗脸。他说自己就是个泥土的人,是在这些穷苦人中长大的……可以说臧克家的独特贡献也正在于此,他对土地、对农民、对农村生活的热切关注与揭示的确构成了不可代替、具有独特意义的时代文本。
反差
社会声名与其文学史地位
作为中国现当代诗歌界的重量级人物,臧克家社会声名日隆与其文学史地位的日益下滑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反差,我们姑且称之为“臧克家现象”。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和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三个时段的文学史著作为例进行对比便可发现,臧克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逐年下滑。唐本以“中国诗歌会诸诗人和臧克家等的创作”为专节标题,对臧克家的创作评价颇高;黄著虽以“臧克家和戴望舒的诗”为专节标题进行了介绍,但评价趋于客观;而程本仅在一节“冯至及其他诗人”中以“臧克家对乡土题材的探求”为小标题做了简短介绍。这种倾向与其所获“当代诗魂”、“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等荣誉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笔者曾经亲耳听几位治文学史的老先生说过,自80年代以来,臧翁对现代文学史编纂者在他身上过于吝惜笔墨颇为不满。
“臧克家现象”的出现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道德文章所得到的认同过于强大,由此遮蔽了其艺术上的缺陷与不足。随着近年来思想、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重写文学史”口号日见深入,一旦人们以审美的眼光重新审视臧克家诗歌的艺术性,评价自然会有变化;而其道德文章的声誉则一直未落反升,其间出现落差也就不足为奇了。
臧克家有“苦吟诗人”的称号,然而与他所获得的高度评价一脉相承,他自己更为关注的是诗歌创作的“战斗内容”,在晚年他还特别强调:“新月派、新月派诗人给我的影响很大,但必须紧跟一句:只是在表现艺术上!我是从贫苦破败的农村来的,我是从武汉大革命战场上来的,在生活经历上,不但和新月派不一致,而且是大相径庭!”(《我与“新月派”》)
其实,早在发表于1934年《文学》三卷一号上的《论新诗》一文中,他就曾经批评过徐志摩:“……他只是从英国贩过一种形式来,而且把里边装满了闲情一爱和风花雪月。他那种轻灵的调子也只适合填恋歌,伟大的东西是装不下的。因此,徐志摩虽然造成了一派的潮流,然而对新诗的功绩是不甚值得歌颂的”。他讲求从现实中提炼诗意,凝构诗思,即使如“老马”这样寄寓了“浓郁而悲愤”的心境的意象,也强调“首先要经过对它们的仔细观察,寻出特征”,再行之成文。他虽然反对苍白直露的呐喊,却更反感陷在一己小天地里的浅吟低唱,他甚至认为“这时代需要博大雄健的大音节,只要有了伟大的生活经验,给你铸成了坚实的内容,在技巧上,就是再粗一点,也可以原谅过去。”(《新诗问答》)
从此可见,“苦吟诗人”虽然在谴词造句上很用心,但其“苦”更多来自思想内容方面的良苦用心,他所获得的高度评价与尊重也多是缘于后者:诗人李瑛说,他关心劳苦大众,80多年来我们国家历史的风风雨雨在他的诗里都有反映;魏巍认为其特点就是“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诗人杨晓民称他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诗人”;叶延滨甚至将他与艾青相提并论,称誉二人在中国诗歌史上营造了新诗的“两个高峰”。艾青对中国新诗的贡献是把中国新诗和世界接轨,臧老则是从传统诗歌的角度,体现了新诗的现实主义和关注民生的特点。
有关臧克家道德文章的颂扬之辞及回忆在老人西去后更是连篇累牍,人们从中不难看到一个和蔼可亲、关心民众、童心未泯的可敬可爱的老者形象。然而许多文章对其诗歌的艺术价值却往往用简单的话语一带而过,更遑论严肃、理性的学术探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追思
“盖棺难以论定”
臧克家1930年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数学得了零分,作文只写了三句新诗:“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由于很幸运地碰上了慧眼识才的主考官——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臧克家被破格录取。臧克家的这三句新诗蕴涵着深刻的含义:有理想的人是痛苦的。可是它也恰恰预言了这样的事实:老诗人既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追日的夸父,却又因为这种执著而阻碍了对个性解放、对自我意识的深刻理解与追求,使他始终走不出属于自己的年代,一直无法走出国家、民族、革命、解放、阶级等宏大叙事、中心话语以及意识形态的笼罩。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汹涌澎湃的以人道主义话语为内核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臧克家对表征着新型个性解放与自我意识的“朦胧诗”创作思潮提出严厉批判,认为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门户开放以后……有一些外国资产阶级腐朽落后的文艺思潮和流派,在我国也泛滥起来,这是‘朦胧诗’等产生的国际方面的影响”。也许在他看来,“朦胧诗”朦胧的不仅仅是艺术形式,更是黑暗与光明之界限的朦胧,——他已经很难走出二元对立的审美定势。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对干校生活的诗化回忆,把知识分子的磨难看成“回归自然”的磨炼,甚至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当时在鄂南咸宁向阳湖的生活异常艰苦,盖房、开荒、种地、喂猪、筑堤、犁田、插秧……精神更是备受压抑。但是在臧克家的笔下,却是“袅娜翠苗塘半满,斜风细雨助精神”,“烟雨蓑衣稻满湖”,艰苦的劳动改造被描述成动人的劳动场景,“头顶阳光散白银,田里黑泥没脚趾,手上汗珠成串落,镰刀底下拾黄金”。回京后,臧克家又将在咸宁写的50多首旧体诗辑成《忆向阳》,以“留恋干校的战斗生活,回忆干校的战斗生活”,并在1978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由此引发了争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为“世纪老人”的巴金的真诚“忏悔”及对自我的痛彻反思构成了鲜明对比。
臧克家在1934年开明书店版《烙印》所作的《再版后志》中曾经说过:“老早心里就写诗定了个方针。第一要尽力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面(于今看来,当然觉得这还不够),再就是写人生永久性的真理。”实际上他未能意识到,并不是其“尽力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面”做得不够,而是没有能达到“写人生永久性的真理”的思想艺术境界。当然,这已是无法弥补的缺憾。
有评论家认为,“臧克家在解放后由一个诗人变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在80年代提出的写诗要‘顺口、顺眼、顺耳’等文艺主张对诗歌本身的发展并没有积极影响”。有的人将他视为“一生分成两半的诗人”,认为这一代人长期生存于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夹缝之间,不同方向的两种力,造成其话语的严重断裂,也导致了他们的人格的分裂。一位年轻诗人偏激地说,“一个像他那样怀有钢铁般的信念和眼光的人,除了捍卫与这种信念和眼光有关的秩序外不会再关心什么。他不会困惑,也无意寻求任何意义上的对话,因为他的耳朵中早已充满同样坚硬的真理结石。”甚至有人刻薄地用“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讽刺他的后半生。
然而,“九九归一”,主流评论界发出的则是“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挽歌。臧克家的学生,曾经在“朦胧诗”风波中遭到臧老批评的谢冕先生这样说:“我对他的敬重并未改变,我对他亲切的印象一如既往”,他认为“怎样把克家先生毕生奋斗的事业继续下去,是我们后来的人要做的。”孙玉石先生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时也指出,“在诗歌的各种潮流中,即使是包括后来先锋的、浪漫的潮流,臧克家所代表的那种贴近现实的风格都是不可替代的。他一直都坚持诗歌贴近现实,坚持诗歌和传统的联系,即便后来者对他的诗有种种其他看法,但就这一点而言,则是公认的”。
这真是“盖棺难以论定”。其实,在21世纪的今天,对于一个在本质上属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老诗人,无论溢美之辞过甚还是过分之苛责都是没有必要的。诗人的成就与缺憾恰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难以像《有的人》那样区别出两个阵营来。臧克家晚年曾经写过一首诗《我》,只有一句十字:“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笔者认为这正是臧克家的审美精神与心路历程的写照:光明给了他理想,也束缚了他的理想;火,成就了他,也限制了他。他的诗就像那团火焰,永远在泥土上燃烧,也只能在泥土上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