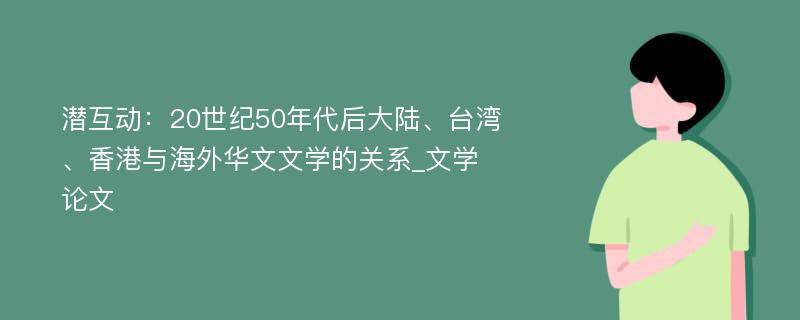
潜性互动:五十年代后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台湾论文,香港论文,五十年代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前,海外华文文学基本上可视作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延伸,而台港文学也远未形成其“ 自足生存”的体系,它们跟中国大陆以京、沪等地为中心的文学时常保持着“同步呼应”, 整个华文文学格局基本上置于中国大陆新文学单向幅射机制的影响下。但从50年代起,这种 格局开始被打破。一方面,各地区华文文学间仍血脉相通,尤其是台湾、香港文学虽跟大陆 文学走向相异,但仍属同一整体,另一方面,各地区华文文学间的多向幅射、双向互动关系 开始形成,其本土化进程显著加快,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进入了独立的国别文学的过渡时 期,世界华文文学格局雏型由此呈现。
共和国在大陆成立,蒋介石退守台湾,香港仍归英治,这种政治格局使得海峡两岸三地互 有隔绝,但一脉相通的血却更浓于水。刚刚进入50年代,后来名垂台湾诗坛的郑愁予就写下 了大量“血脉相通”之作。一声“飘泊得很久,我想归去了”,天老地荒,刻骨铭心,最终 的归宿是在“汩罗江渚,像清浅的水涡一样,在那儿旋泛”(《归航曲》,1952),而时年作 者才19岁;“挨近时冷,远离时反暖”,这种星月对话中的“乡音”,是人类本真状态上的 思乡之情(《乡音》,1954);“是时间的古人”,“又是宇宙的游子”,“这土地我一方来 ,将八方离去”,这在流浪中寻求归宿的偈语,浓缩起游子的心愿(《偈》,1954);随后是 那首奠定他诗坛地位的《错误》(1954),江南的意境演化成恒久的等待和思恋,灵活变通的 句法,熔铸扭曲的诗行形式,叠合起“莲花”、“柳絮”、“青石街道”、“跫音”、“春 帷”等东方古典意象,浓聚起万千飘零的心绪……这些诗构成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梦土上》 (1955)。跟他取意于“江晚正愁予”(辛稼轩《菩萨蛮》)、“目渺渺兮愁予”(屈原《湘夫 人》)的笔名一样,郑愁予的50年代诗作,虽跻身于台湾现代诗行列,但又都是跟祖国母体 “血脉相通”之作。这种文化血脉畅通于几乎所有的作家中。在海峡两岸长期被阻隔的年月 里,50年代却是某种转折点,构成着两岸文学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相通,使两岸文学始终是 一个内在的整体。
如果讲,郑愁予等人的诗作流淌的都是从大陆延续到台湾的血脉,那么,台湾本土文学在 光复后对母体文化的强烈皈依,则更表明了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的一体性。光复后,国民党 政府接收台湾,历史的隔膜、现实中的轻视,引发了本地人和外省籍人之间的一些矛盾。在 文化层面上,这种矛盾包含有对台湾文化特殊性重视不够的因素。但当时台湾社会文化、民 众心理的基本取向是回归祖国,一些本地人和外省籍人的矛盾实质上是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 制和腐败。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发生的关于台湾新文学 的热烈争论,在半个世纪后重新引起海峡两岸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就是因为这场争论呈现出 战后台湾社会矛盾复杂交错的情境中,台湾本土和外来作家对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共同构想, 其中的主线就是摆脱日本殖民文化的阴影,培育台湾文学的自立品格,成为中国文学中的重 要一环。在“二·二八”事件后对国民党政权极度失望的特殊环境中,台湾作家,尤其是台 湾本土作家(如杨逵、吴浊流、黄得时、赖明弘等)仍抱持着台湾大陆史缘血缘皆不可分的信 念。这种信念,历经半个世纪殖民统治而不灭,也将在两岸隔绝的年月中绵延不尽。
如果具体地考察,那么50年代后的台湾文学跟“五四”新文学传统几乎是一脉相承。
日据时期的结束,大陆作家的迁台,使台湾文学跟“五四”后大陆文学精神上一脉相承、 艺术上源流相通、文字上相关相续的关系变得明朗。尽管国民党当局封杀“五四”新文学和 30年代文学,但“五四”文学传统在台湾岛上仍显得血脉畅通。以创作最丰盛的散文为例, 杨牧等曾细致考察指出,台湾50年代后散文和大陆现代散文的承继关系和发展流脉大致是这 样的:第一类为小品,其奠基人为周作人。这种小品“上承晚明遗风,平淡中见其醇厚的一 面”,但往往又注入作者日常生活的经验,也有其激情。这类散文在台湾的承继者有梁实秋 、思果、庄因等。第二类为记述散文,以夏丐尊为前驱,其《白马湖之冬》为奠基之作。这 类散文清新透明、朴实无华,在台湾的承继者有琦君、林海音、许达然等。第三类为“寓言 ”,许地山为开山人。这种散文多为学者所作,“博学沉潜”、“神韵无穷”,在台湾的继 承者有王鼎钧等人。第四类为抒情散文,徐志摩为源头。这类散文潇洒浪漫,草木人事莫不 有情,激越飘逸,旋转自如,在台湾的继承者有张秀亚、胡品清、余光中、张晓风、陈之蕃 等。第五类为议论散文,林语堂开风气之先。这类散文“所议之论平易近人,于无事中娓娓 道来,索引旁证,若有其事,重智慧之渲染和幽默人生之开发”,继承者有邱言曦、吴鲁芹 、夏菁等。第六类散文为说理散文,胡适为源头。这类散文辩论雄健,说理透彻,创建现代 学术散文文风,继承者有叶维廉等。第七类为杂文,鲁迅为祖师,其泼辣深幽为柏杨、李敖 等所继承。(注:古继堂,《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序》,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
杨牧本是台湾散文名家,后定居美国,他的分类有两点很有文学史意义。一是其所言7种散 文类型(风格)50年代后在大陆都沉寂多时,大陆散文中起“鼎足作用”的杨朔、刘白羽、秦 牧三模式虽各有相异,但都笼罩在“一天一地一圣人”(王鼎钧语)的严肃、宏大之中,而正 是台湾散文,使“五四”至40年代散文“千山千水千才子”的丰富性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二 是其所言前6种散文类型在大陆文学史观念中都并非主流,而它们却成为台湾散文的主导力 量,这种互补关系表明对“五四”后新文学可以有不同侧面的继承,并流变出不同的主流文 学形态。台湾文学跟中国大陆文学的这种互补关系,构成了50年代后华文文学的一种基本格 局。
台湾跟大陆的文化血脉,成为50年代后台湾文学突破“反共八股”拘囿的最大驱动力。钟 理和的《原乡人》绝唱,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忆想,都以本土作家的情愫,勾连起北平、 台湾两种故乡的思恋,漫出地域的局限,超越时代的郁结,深植于历史因缘,升华了“乡愁 ”母题。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堂堂正正地让台湾岛上陆氏家族的祖孙几代,一头延 伸进儒家传统,一头接纳着山地同胞,成为台湾人民族多源血缘的历史象征。而对于“军中 作家”来说,“回归原乡”成为对他们文学生命的拯救。朱西宁《铁浆》那样的血性乡土小 说,司马中原《狂风沙》那样的乡野传奇作品,都是依恃故乡回忆的乳汁,而成为“战斗文 学”的内部反叛。总之,相通于母体的血脉,使50年代的台湾文学给后世提供了这些“经典 ”之作。
50年代的台湾由于继续承认“双重国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海外文化政策,吸引了数以 千计的东南亚华人子弟到台湾留学。但战后的东南亚华侨社会已逐步过渡到华人社会,华人 关 注的重心也已由母国转移到居住国,所以尽管东南亚各国中不乏反共国家,但华人社会文化 建设上的政治色彩在消褪,此时台湾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产生影响主要是在现代主义文艺 思潮和华文主流社会语言传承两个层面上。前一层面的内容我已在《横的移植:50年代台湾 文学引发的文学传承和转换》中述及。在后一层面上,台湾既是移民社会又是华文主流社会 的状态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影响颇大。无论是“国语”,还是闽南、客家等方言,对台湾岛而 言,都属于“移民”语言,但它们在台湾岛生存繁衍,又成为社会的通用语言,并且有着丰 富的形态。汉语在变化中的传承,跟台湾岛上的社会政治、宗亲文化、经济转型等紧密相连 ,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维系着全岛的一统性,并勾通着跟母土的血脉联系。50年代后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显然相当多地从台湾文学的语言中汲取营养,这大概主要是因为台湾文学跟东南 亚华文文学不仅有着相近的原乡情结、漂泊心态,而且在文学模式上(如言情、写实等)也较 为相同。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香港的文化空间在当时海峡两岸之间, 是最开放和包容的。不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右倾或亲左,甚或是不见容于海峡两岸的托派 ,都能够在香港自由活动。香港文化人均可自行选择,并各自宣扬信念或落实创作理想。因 此,就当时两岸三地的政治及文化情况来看,香港可说是一种‘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 ,容许歧异的声音同时争鸣,接受相互排拒的论述和辩争。香港文化空间这个特色,使得60 年代成长的青年文化人,更能自主独立,在没有干预下自行摸索。”(注:郑树森,《遗忘的历史·历史的遗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
。郑树森长期任教 于香港中文大学和科技大学,极为关注香港文学,他对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这段描述有着 被遗忘了的历史真实。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一方面左右翼分化鲜明,对峙激烈,右翼文 化势力以由“亚洲基金会”资助的人人、友联、亚洲等出版社及其刊物(如《人人文学》、 《中国学生周报》、《亚洲画报》等)为主要阵地,接纳了一大批包括黄思骋、力匡、余英 时等在内的颇有写作潜力的作者。而左翼文艺阵营则以《文汇报》、《大公报》、《今晚报 》和香港三联、商务、中华等出版机构为核心,虽资金短缺,但声势也足以抗衡。但另一方 面,由于港英政府在左右翼意识形态角力中的“缺席”,又没有推行殖民地语文教育政策, 左右翼文化势力皆未受到政权实体的压力,华文生存发展的空间也很大。因此,左右对垒反 而使香港文坛在一种自由度较大的空间容纳进各种创作。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等武侠小说 首先是在左派报纸《今晚报》亮相的,而张爱玲50年代的小说、剧本创作则跟“绿背(美元)文化”的背景不无关系。至于左右翼文艺阵营中能摆脱意识形态桎梏者,无论是南来作 家,还是本土新锐,都大有人在。因此,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其气候既迥异于独尊“工 农兵文艺”的中国大陆,也不同于倡导“反共复国”的台湾地区,可以说,它是华文创作最 不受外界干预的地区。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香港文学在五六十年代的华文文学格局中扮演了一种特殊的中介角色 , 并由此开启了华文文学之间的“互动”局面。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上,右翼文化势力是借重 香港“地理、政治、文化”上的“边陲”位置,“向中原‘喊话’”,而左翼文学家则是“ 努力利用边缘”在香港“确立新核心和新中原”(注:郑树森,《遗忘的历史·历史的遗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
。这种“边缘和中心”的轇轕,构成 香港和内地的“互动”,但难免延缓香港文学的本地化。对台湾,香港文坛主要是在现代主 义思潮上构成呼应和互补。香港的现代都市性、中西双栖性,使它对现代主义的共鸣比台湾 更多一些感知形态,所以其现代主义文学形态也比台湾的“更为多元和新颖”(注:郑树森,《遗忘的历史·历史的遗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
。香港和 台湾的现代派文学,都延续了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余脉(例如台湾的痖弦、香港的西西, 早期诗作皆师法卞之琳、绿原、辛笛等),源头相近又各有异趣。台湾解除军事戒严前,对 香港报刊管制极严,政治色彩深的报刊即便带反共倾向的也难以进口,所以沟通两地文坛的 就主要是现代主义渠道了。香港的《文艺思潮》、《好望角》、《盘古》等刊物皆以孤绝的 存在主义式的呼喊进入台湾文坛,而台湾的《现代诗》、《创世纪》也以相近的声音出现于 香港。50年代赴台就学的香港青年如叶维廉、刘绍铭、张错等后来皆在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 创作上颇有建树。即使是余光中所作回归古典传统的努力,也是强调“有深厚‘古典’背景 的‘现代’和受过‘现代’洗礼的‘古典’”(注:余光中,《莲的联想·后记》,台湾文星书局,1964。)
。而这一主张通过香港留台青年诗人温健 骝、羊城等传播到了香港。应该说,台、港两地的文学交流,一开始就避免了政治意识形态 的制约,而呈现良性的互动。这其中,香港的马朗、刘以鬯、也斯、卢因、林以亮、戴天等 ,台湾的余光中、张晓风、董桥、痖弦、叶珊、商禽等,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此时期的香港文坛,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也形成了某种幅射影响机制。一是,一些香港文化 人到东南亚国家创办刊物,建立出版机构。例如,50年代初,姚拓、黄思骋等从香港到马来 亚创办《学生周报》和《蕉风》杂志,培养华文青年作者。尤其是《蕉风》,创刊后45年未 停刊,其对新马及邻国华文文学的影响功不可没。二是,香港此时的一些刊物直接为东南亚 华 文文学作品提供园地。据不完全统计,在香港《南洋文艺》、《文艺世界》、《海洋文艺》 上发表过作品的东南亚华文作者都不下百人,几乎覆盖了40年代至70年代好几个世代的作者 群体,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所在国华文文坛的中坚力量。三是香港完善发达的出版业成为东 南亚华文文学作品的集散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杨松年先生曾指出,战后20年中,“ 新马华文文学书籍的出版有三个中心地,那就是新加坡、马来亚与香港”(注: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南洋商报社1982年2月版。)
,而其中在香 港直接出版的华文文学书籍多于马来亚出版的。即便是在新马两地编辑出版的华文书籍,也 往往运往香港印刷,香港的地理、文化位置促进了新马作品在各个华人社会的扩散。五六十 年代在香港出版的《新马文艺丛书》、《赤道文艺丛书》、《南方文丛》、《新马戏剧丛书 》、《星洲文艺丛刊》等,都称得上五六十年代新马华文文学中的扛鼎之作。四是东南亚华 人青年作者赴港就学从业,并依托香港的报业出版机构等发展本国华文文学。尤其是对一些 本国华文生存环境恶劣的作家而言,香港几乎成了他们的“大后方”。例如越南,华人知识 分子大部分是在二次大战期间,香港沦陷后流亡越南的,当时的法国当局允许其在堤岸市谋 生,越南的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办起来的,所以其跟香港的关系一开始 就很密切。在后来的越战及至南北统一后,越华文学生存一直很艰难,而此时香港文艺刊物 刊登的越华文学作品却多了起来,尤其是《当代文艺》成了越华作家向世界传达其心声的主 要阵地。《当代文艺》的主编徐速60年代从越华作家来稿中发现了女作家李锦怡的长篇,大 加赞赏,交由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并为该小说集取名《系》。60年代后,当印尼国内政治 形势日趋反华,华文生存陷入绝境,印尼华人作家也一直利用香港的环境来发展印华文学。
此时期,香港文学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产生影响,一是现代主义文学思 潮,二是都市消费文学。例如,《蕉风》1961年起大力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少方面是 以香港文坛为中介的,而温瑞安(马来西亚)的创作从现代主义起步,之后转入新武侠小说创 作也可视为香港文学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
50年代后的海外华文文学已开始以一种“只要是落地生根的地方,便是自己的家园”的心 态去寻求跟居住国文化的认同,逐步形成一种迥异于传统移民文学“落叶归根”的新模式。 中国社会的沧桑变化,中华人文的悠悠历史,在海外华文文学中逐步“退”而成为创作的一 种背景、一种潜在影响。但由于当时世界冷战架构造成的华人生存的严峻局势和华人探寻参 与建立国民新社会的方式的艰难过程,增大了华人融入居住国文化的难度,也一再迫使华人 致力于居住国领土上华人传统社会的建设,文学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传承中华文化薪火的重 任,因此,文学必然要千方百计去沟通自身跟母国文化的联系。50年代初,大批大陆文化人 因 各种原因辗转到达海外各国,他们原先的文化积累使他们可以较为从容地将母体文化的营养 糅进居住国现实生活的土壤,从而使海外华文文学本土化的过程成为强烈认同中国文化的历 史进程。例如,50年代的马来亚,就聚合了近百人的中国南来作家群,他们的创作使马华文 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特色。
五六十年代政治的、地理的隔绝使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开始进入一种“各行其是”的轨道, 并各自开始了其本土化进程。然而,“隔绝”并未割断,各地区华文文学之间仍有着种种沟 通,而那种内在的相通就更有意味,它实际上提供了民族新文学的一种新的整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