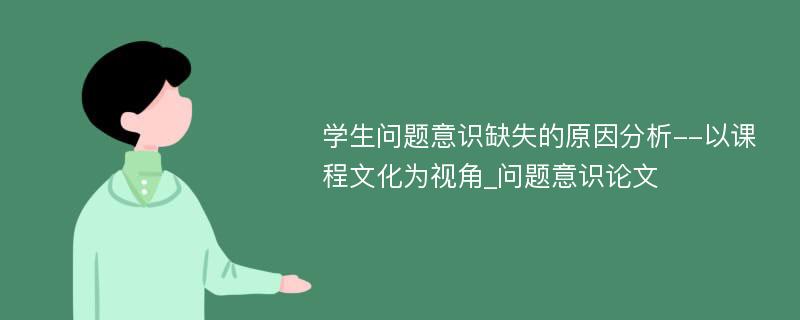
学生问题意识缺失的根源分析——基于课程文化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根源论文,视角论文,意识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儿童从会说话那一刻起,凡事都要问个究竟:为什么月亮是圆的?火车轨道有什么用?我怎样才能飞到天上去?……其中不乏科学领域的深奥问题或是人类面临的终极问题。但不知从何时起,“问题”在中小学生的世界中逐渐被遮蔽和消解,人们不禁发出感叹:为什么如今的学生难以提出有价值的问题,甚至根本提不出问题?他们对于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到哪去了?这种令人堪忧的现状不得不引发我们进行反思:到底是什么样的课程,是什么样的课堂教学让学生失去了问题意识?这涉及到学生问题意识缺失的根源问题,本文试图从课程文化的视角对学生问题意识缺失的根源进行探讨。
一、学生问题意识缺失的课程文化根源
(一)塑造与被塑造——成人文化的框定
在学校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要将学生塑造成某某样的人”。其基本逻辑是学校成为塑造者,通过课程来塑造他们所期望的学生;学生是被塑造者,他们原来各不相同,但是经过学校高温高压的塑造,都变成了铁水,被传送带放进了同样的模子,变成了对社会有用的铁块。那么这个模具是按照怎样的尺寸,由谁来设计制作的呢?在这里,成人们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游戏规则制定了模具,他们挑选出多年来的经典文化和符合社会秩序的文化,将这些所谓的最优秀的文化作为学生们的学习内容,因为在他们看来,学生们只有经过这样的文化的熏染,才能将文化传承下去,才能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思维方式。课程文化的选择和制定者将儿童和学生看作单纯的学习者,他们要学习的是过去的经验和文化,其学习方式就是通过成年人的灌输,使学生对原有的文化进行默记和摹仿,至于学生自身的经验和文化是不值得关注的,学生的自主的文化创造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样的课程文化被“他者文化”所充斥,学生是文化传承中一个小小的链条,他们成为被灌输的别无选择的文化客体,他们距离自身的文化、距离主体性文化、距离自己的生活世界越来越远。
在这里,学生被认为是不成熟的,所以他们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没有贡献。因此,他们理应按照成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去做,并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如果有学生斗胆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成人们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评估,如果通过了他们的价值评估则有可能获得正向的反馈,否则这些问题会被纳入无意义之列而被一笑置之,于是学生们在课堂上逐渐学会了自行消解自己的想法,因为这样的想法在成人的视野中显得那样稚嫩而缺乏深度,于是他们宁愿将自己的话语掩藏起来,以免受到外界的消极评价。学生逐渐认识到了成人原来并不喜欢被诘问,也不喜欢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只有等待现成的答案是最妥当的了,于是他们开始采用成人惯有的方式来想问题、做事情,儿童的本性——对问题的迷恋和探究逐渐减退。
(二)以教科书为准——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在课堂上,我们常常能够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当学生对某个问题莫衷一是时,教师自然成了学生心目中的裁判与法官,教师也从来不辱使命,能够找出非常权威的法典为自己的判决做支撑,那就是:“不要争了,以教科书为准”。于是,教科书在老师和学生心中成为了“权威”的代名词,以至于在学生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教科书上认可的就是对的,而教科书上没有涉及的问题就是没有意义的。教科书中的知识是法理知识,它奠定了课程的逻辑基础,由于课程的不断强化,教科书从教学的辅助材料走到了中心位置,而且还带上了神圣的光环,成为客观、正确、无疑问的代表。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话说:“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秩序,由于取决于特殊类型的合法性,知识生活——是由外在的合法化权威决定的”。[1]于是课程成了“教教科书”的同义词,学生对教科书深信不疑,当作经典去背诵、去消化,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自觉地到教科书中去寻找答案,如果自己的想法与教科书不相符,只能说明自己还不够聪明、智慧,教科书中给出的标准答案才是正确而完美的。于是自我思考的兴趣和冲动逐渐被教科书的理性与逻辑所战胜,学生在课堂中找不到自己了,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学生们逐渐成了玛丽·杜莉-柏拉(M.Dubar-Bellat)笔下的“驼背人”,他们在教科书的学习上成为“苦力”,终日埋头于没有把握的学习活动中,[2]由于学生的学习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所以他们在认知活动中就开始表现出倦怠,随着年级的增加,他们的眼神中增添了更多的疲惫和无奈,而少了好奇、惊异和感动,有些学生开始逃避学习,厌倦思考,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消失殆尽。
(三)最终要比拼考试成绩——对外界评价的遵从
作为评价的重要手段,考试在学校课程和教学中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考试不但关系到“要教什么”以及“怎么教的问题”,而且还担当着鉴定出“优等生”和“差生”的重任。这一评价标准不但关系到儿童和家长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关涉到教师的威望和待遇,因此与学校相关的任何人都不敢怠慢。他们在拼命地向这个标准膜拜、靠近,考试的权威和神圣由此诞生,留给学生许多心悸的回忆。在一次次考试经验的积累过程中,学生们了解了自己在班级中所处的地位,教师也更加明确自己的责任,教师和学生都心知肚明,“如果你不能考核它,它就不值得知道”。[3]于是儿童们尤其在构成为微型社会体制的课堂上,发现了一个比家更加漠然、更加功利、更加可以操纵的社会空间。[4]在激烈的考试竞争的压力下,学生们已经没有时间体味名家作品中令人心灵感动的意境,没有时间了解数学王国的神奇魅力,他们按照老师规定的教学大纲和考试重点,背诵、计算、再背诵再计算,周而复始,在课程给出的漫长跑道上,艰难地跋涉。
在各种压力的作用下,学生们对问题的探究兴趣转移到提高分数上来,他们学会将有限的资源和时间用于提高学习效果,学生在高分中得到的正向反馈远胜于其他任何东西。于是对问题的探究逐渐让位于记忆、让位于计算、让位于考试分数。学生在繁忙的学习和考试中,丧失了学习的内在动力,也消减了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神往。
二、学生问题意识缺失的逻辑推断
(一)遮蔽了真正的课程文化主体
在这种课程文化中,成人和社会文化成为唯一的合法文化,取得了优势地位和特权,在学校的课程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文化是规则性和框架性的,课程文化中的其他因素只能在这个文化中扮演被塑造、被约束的角色。这种被神圣化了的社会文化,具有发放信号的能力,而个人只能在其中学习和接受有意义的信号,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人们在“角色扮演”实践中,从“一般性的他人”的反应中,逐渐形成了关于自身的一般概念,并且逐渐地将自己作为客体来对待。[5]实际上,教师和学生才是课堂真正的主体,他们有自己的经验和思想,他们有主动学习和创造的潜力和能力。而在专制性的课程文化中,他们只是社会文化的继承者,也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他们按照社会性的、法理性的文化所主宰,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慢慢地走向了文化的边缘地位,师生的身影虽然占据着课堂的空间,但是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课程权力,他们也没有办法将自己的经验和想法纳入合理的课程内容当中,他们能够反映的只是社会文化的期望,而不是自身的意志;他们只是社会规则的遵循者,而不是制定者。在与强大的社会文化的交锋中,个人失去了反击的能力,被彻底打败,压在课程文化的谷底,真正的课程文化的主体却没有发言权,他们的经验与智慧被抹杀了,形成了布迪厄所说的“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现象。
(二)否认了课程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
课程文化的主体——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处在课程文化的层级当中,虽然他们在专制性课程文化中都处于较低的地位,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主要是课程文化的专制性所造成的,教师的个人经验虽然也被忽略,但是教师被赋予了新的角色,他成为社会性和法理性文化的代言人,这些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更大,内化更深刻,他们掌握了社会和文化规则,并自觉不自觉地从社会的、法理性文化的立场出发,通过传授显性的教材知识或者传达隐性的缄默知识,将社会文化的思维方式、逻辑形式、文化表达传递给学生。
在这种课程文化中,教师个体在面对学生群体时,往往将学生看作是受众,学生个性化的喜怒哀乐在这个庞大群体中逐渐式微,教师在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体会到了自身的伟大,自我主体性认知不断膨胀,学生则愈加渺小,师生之间呈现出了一种“我与它”的关系。学生群体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并没有取得合法的话语权,他们的精彩观念甚至被看作是“恶作剧”、“扰乱课堂秩序”,他们更像斯金纳心理学试验中小白鼠,他们在文化的迷宫中寻找出路,幸运的是他们不需要自己去寻找,只要根据教师的领导找到出口,并一次一次地强化和训练就可以了,但不幸的同样是这一点,因为无论他最后以多快的速度找到出口,他必定是在别人垒砌的迷宫中行走,而且它毕竟只是一只小白鼠。
(三)忽视了学生对课程文化的创造性
这种课程文化的另一个重要逻辑起点是:现有社会文化是完备的、完美的,因此最有资格成为课程的主宰者,而课堂中的人也总是教师与学生,这种文化的接受者也是固定的,因此只要把这种完美的文化通过某种传输、记忆、模仿和强化的过程,就可以将文化完整地传承下去,这样课程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之所以要选择经典文化,之所以要采用自上而下灌输的方式,不都是出于这种考虑吗?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纰漏。
一方面,任何文化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和进化当中,自命不凡、自诩为经典的文化,不过是固步自封。文化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用皮亚杰的图示理论来解释,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图示,在外界信息的刺激下,一部分符合原来文化的信息被同化到原来的文化图示当中去,而另一部分不符合原来文化的信息,也并不会浪费,文化图示会调整自身的状态,顺应新信息形态的需要,在同化和顺应的过程中,文化得到了进步和发展。与文化的这种包容性和流变性相对,专制性的课程文化采用非常威严的态度,无视社会文化的发展,将一种确定的社会规则以知识和技能的形式固定下来,反对其他因素的入侵,任你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在本质上是与文化的发展性相违背的。
另一方面,教师与学生也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的生活环境、外界的信息刺激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而课程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却是陈旧、固定的材料,他们的探究愿望和创造欲求得不到满足,他们感到了自我的渺小和无奈,于是学生可选择的道路一般只有两条:要么压抑自己,顺应这种课程文化;要么逃离这种文化的束缚,寻找别的空间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对课程文化应对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两种学生,即“驼背的人”与“嬉皮笑脸”的人,他们都是这种课程文化的牺牲品。
三、追寻催生学生问题意识的民主性课程文化
专制性文化对课程文化场域有着深远的影响,场域中的人们为了在他者的规定性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就要忽略自身的存在性和主体性。他们对所灌输的文化和课程的一味接受,使其自己的思考和反省能力不断地被剥夺。学生开始害怕反思,害怕自由,他们宁愿在不需要思考的环境中等待答案,于是沉默的课堂、没有问题的“成问题”的课堂越来越多,这样的课程培养的人只能逐渐走向平庸,缺乏批判和反思的勇气和能力。教师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他们在这个固定的模式下,越来越心安理得,由于经验的丰富,他们对课程的范围的圈定越发狭窄,他们认为无价值的知识,不会列入考试范围的知识统统剔除,使课程内容更加纯净,然而这样的提纯造成了课程的“营养不良”,学生在承受着文化的“饥馑”之苦。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改变这种文化环境。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使课程文化形成新的生长点,让新一代的课程文化走向丰富性、走向对话性、走向创生性。
(一)以课程文化的丰富性拓展学生的经验来源
由于课程文化的严格预设,课程文化的来源不断缩小。学生所得到的不过是简化了的、概念化、抽象的成人社会的间接经验,使其形成了“唯书”、“唯上”的思维方式。其实课程文化的内涵应该是丰富的,不但文本课程还包括非文本课程;不但包括成人世界的间接经验,也应该包括儿童世界的直接经验;不但包括学术世界的知识,还包括生活世界的知识。在课程的隐喻中,常常忽略了非文本、忽略了儿童也忽略了生活世界。其实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儿童的成长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儿童的交际、探究、制作和艺术的兴趣和本能,这些兴趣和本能的自然展现就是儿童的生活。[6]儿童的生活世界应该是丰富的,这个丰富的、个性化的场域中包含了大量的与儿童相关的知识和经验,这是他们需要了解的,也是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的重要途径。倘若人们在童年时期接受的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文化教育,而他们与其他文化成员的接触又甚少、并充满敌意或鲜明对比,则他们的深刻的认同意识就似乎是无法改变的。[7]在专制文化的束缚下,学生们得到的并非是通过深刻的思考和体验得到的对真理的认同,而是对专制与服从的认同,这是我们作为教育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二)以课程文化的对话性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专制性的课程文化中,只需要教师的独白和教科书的呈现,而不需要学生的出现,也就缺少了对话的前提条件。即使学生们得到了所谓的讲话机会,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是对教师提问的回答。在课程中最一般的对话单位是“教师主导的提问与提示”、“学生的应答”、“教师的评价”,可以用完结的封闭的单位——IRE结构——来表达。这种连续的循环是课堂对话的极其显著的特征。[8]在IRE结构中,教师和学生存在明显的地位差异,他们的对话不过是对教师灌输教学方式的一种补充和认同的标志。
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认为:对参与者来说,话语必须被认为是真实的,必须被认为是真诚的。[9]而对话真实与真诚的前提条件就是教师与学生之间人格尊严的平等。当课程文化的内容得以丰富,学生的经验被纳入到课程中,那么教师不是唯一的文化来源,他也成为一个学习者,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一种“互喻文化”。课程文化在对话中产生新的意义,形成新的思考,激发出智慧和生命的力量。只有通过交流,人的生活才具有意义。只有通过学生思考的真实性,才能证实教师思考的真实性。教师不能替学生思考,也不能把自己思考强加学生。真正的思考,即对现实的思考,不是发生在孤立的象牙塔中,而只能通过交流才能产生。[10]教师与学生进行对话的基础是他们在人格上的平等,师生之间的关系并非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是课程文化的真正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性的关系,他们在相互的交往中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具有建设性的,不是灌输,而是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一种协商,只有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对话,这样的对话逼近了教育的本真特性,否则只能叫做训练或规制。
(三)以课程文化的创生性激发学生的批判意识
多年来人们对文化的传递性特点的强调,甚至使人们遗忘了文化的另一个本性——创生性。文化在不断地被批判、反思和质疑的过程中,不断地引入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行为模式以及新的物质形式,课程文化也理应如此,在课程文化保持相对的开放性和平等性的同时,课程文化的创生性就会日趋明显。这种创生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学生的批判和思考能力的生成。英国学者巴罗(Barrow)认为“我们在对我们的年轻人进行社会化时不让他们变得毫无批判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培养他们以一种批判的、理性的和自主的方式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的含义是以人的心智既倾向于又能够对文化传承过程中提供的一切信念和假设作出理性反思这样的方式来培养人的心智。”[11]人的思想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当课程把思考能力还给学生的时候,学生活跃的思维就会开出更多的思想之花。而且以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片云触动另一片云,当这种创造性环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学生的创造力是如此丰富,他们的世界是如此广阔,在这个广阔的空间中,教师是和学生合作,共同探索和追求的同行者,他们相互交流经验,享受思想的快乐。如果环境允许,没有人拒绝自由,也没有人拒绝思考,在批判、思考和引进的过程中,课程文化场域中的人们得以自由,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主体的学生,在民主的课程文化中,懂得了珍惜自己的观念和经验,他们了解到了自己作为文化创造者的神圣地位,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贬低自己,也不再愿意在课堂上保持沉默,这样一种思路开阔的、思维活跃的、敢于表达自己的学生群体,是我们的文化值得宝贵的火种,文化如果成为一种固体,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只有燃成火,才能照亮学生,同时也照亮文化自身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