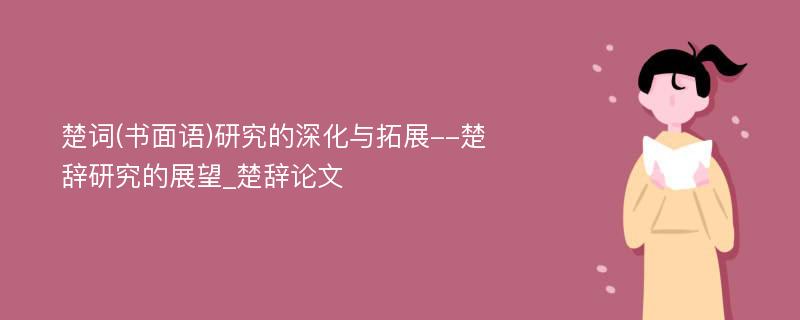
楚辞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笔谈)——楚辞研究前景的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笔谈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1-0038-05
主持人语:目前的楚辞研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与其他古代文学的研究课题一样,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困惑,“楚辞研究走向何方”就是其中一个关乎研究本身的根本性的问题。20世纪末的几年里,在各领域有关研究史的“百年回顾”与“世纪展望”这个宏大命题的观照下,楚辞研究的学术史反思也受到了热情关注,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思考,并涌现出许多高水平的专题论文。不过,现在重新审视起来,则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非但没有结束,而且还有进一步持续、深入下去的必要。为此,我受《甘肃社会科学》主编董汉河先生的委托,组织了本次“楚辞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笔谈,希望能对今后的楚辞研究有所裨益。本期推出四篇文章: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崔富章先生的《屈骚精神,亘古常新》,对屈骚精神的内涵作了细致分析,并将它的现代化作为今后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毛庆先生的《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使命和新楚辞学构建》,具体阐释了他所提出的构建“新楚辞学”的问题;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方铭先生的《游国恩先生的楚辞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是从研究史的角度对游国恩先生的楚辞研究所作的个案研究;我的《楚辞研究前景的展望》一文,则是在肯定楚辞研究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对未来研究所作的前瞻性的思考。整体看来,本组文章的涵盖面是广泛的,视角是多样的,其关注的重心也因此各不相同,而这正是本次笔谈所企盼的。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们还约请了褚斌杰、张正明、周建忠等先生参与笔谈,他们的文章我们将在收到后陆续推出。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楚辞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是一些老一辈学者几十年研究积累的成果得以问世;二是出版了一些带有总结性的或集大成性质的大部头论著;三是文献方面有新的发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突破,解决了一些历史悬案;四是成立了中国屈原学会,迄今已召开了11次年会和学术研讨会,前后参加过的人员超过千人,在楚辞研究和楚辞作品的普及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二十多年中发表的论文之多,出版的注本、研究专著之多,远远超过上世纪前80年的总和。而全国各大学中文学科(现在没有中文学科的大学已不多),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尤其是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没有不研读屈原作品的,读了自然就会有些看法、想法。海外的学者中,也有些从事楚辞研究的。总的来说,是队伍大、成果多。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屈原作品总共二十多篇,宋玉赋今存也不足十篇,已研究了两千多年,近二十年又有成千的人写了数千篇论文,出版了数百种书,各种可以想得到的话都说过了,今后还需要研究吗?如果今后还研究,究竟怎么去做?这是很多楚辞学者都考虑的问题,也常常听到一些人发出类似的疑问。第一个问题关系到楚辞研究的前景,如果真没什么干头,可能有的人便会洗手不再干;第二个问题关系到今后是否能健康发展,是否能取得成果,取得大的进展。这里就此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
先看第一个问题:楚辞研究今后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我认为它永远具有研究的价值,也有继续研究的必要。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说。
(一)还有些问题未能解决,或者解决得并不完满。其中有些问题很难得出可以验证为惟一正确的结论,个别问题恐怕以后永远也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以论定它。这当中既有内部研究方面的问题(主题发掘、内容阐释、意境、表达方式、节奏格律、文体等),也有外部研究方面的问题(作者生平、创作背景、当时的文化、艺术、文学发展状况等),也有两者结合与联系方面的问题(当时政治、经济、文学发展同作品主题、内容、形式、风格的关系,作品对以前创作的继承及对以后的影响等)。如《九歌》这一组诗,每首诗究竟表现着怎样的一种思想,在歌舞祭祀中起着怎样的作用,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包括:名为“九歌”,为何是十一篇),学者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湘君》、《湘夫人》两篇,学界对湘君、湘夫人的身份、本事,这两个人物的关系看法首先就很不一致;关于其演唱体制,也有较大的分歧。古人之说且不论,即今人之说,郭沫若以两诗都是前半为“翁”所唱,后半为“女”所唱;陆侃如、高亨、黄孝纾《楚辞选》则以为每首都是对唱的(《湘君》篇唱的次序是:湘夫人、湘君、湘夫人、湘君,《湘夫人》篇唱的次序是:湘君、湘夫人、湘君、湘夫人)。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两首诗都通篇为一个人物所唱,即是说:它们的抒情主人公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因为郭沫若先生的解说没有任何的依据,只是发挥了他诗人的想象;陆、高的划分也过于任意)。但即便在两篇都由一个人唱到底的这一点上,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湘君》篇为湘君所唱,《湘夫人》篇为湘夫人所唱,而明代汪瑗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湘君》篇是湘夫人所唱,而《湘夫人》篇是湘君所唱。只从篇题上看,似乎前一说对,但如果不把这两首诗看作文人诗那样的东西,而考虑到它们是祭祀歌舞词,则后一说有理。朱熹《楚辞集注》于《湘君》篇说:“此篇盖为男主事阴神之词,故其情意曲折尤多。”①汪瑗之说即由此而来。这样理解便同篇中的指代之词一一相合。既然此说正确,为什么到今天学者们的看法还如此分歧?我只能说一句:正确的东西被人们所普遍接受,要一个过程,那多种错误的说法就像天空中的尘埃,要使其很快落定,是不可能的,何况总有人在不断地煽起一些尘埃。学术认识的转变同专家们的认识、选择有关。关于这一点放到第二个问题来谈。
再如《九歌》的功用时,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而作《九歌》之曲。”朱熹《集注》基本取王逸之说,只是认为屈原“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朱熹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感到它们的主题、情节、语句不像是屈原独立构思,而似乎是有所依据:不仅民歌的风味浓厚,而且其中有些完全是表现男女爱情的。所以现在学者们大都取朱熹之说。但从清代何焯、马其昶以来,也一直有学者认为是屈原奉怀王之命而作,唯较早的意见主要是依据了桓谭《新论·言体》中所说“楚灵王信巫祝之道,躬执羽绂,起舞坛前”,《汉书·郊祀志》记汉成帝时谷永上疏中所说“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的记载,及陆机《要览》中所说“楚怀王于国东偏起沈马祠,名飨楚邦河神,欲害祭祀,拒秦军”的话,加以牵合,并不能肯定楚朝廷就举行祭祀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等神灵的大型活动。周勋初先生有《九歌新考》一书,对相关问题有总结、辨析,对民间祭歌说、楚郊祀歌说有所辩驳。周先生认为是屈原死以前作于江南之野。而近年整理出版的江陵望山一号墓、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和荆门包山二号墓楚简,其中有些神名如太一、司命、司祸、云君、大水、东城夫人等同《九歌》中的大体可以对应。这些墓主人大体与屈原同时,也都是楚贵族,身份与屈原相当。汤漳平先生在利用出土文献以研究《九歌》方面用力甚勤,多有所获。他的结论是:《九歌》是楚王室的祭典。应该承认,周勋初先生的《九歌新考》和汤漳平先生的《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都是严谨而甚见功力的学术著作,也都有其正确的方面,前者思路之开阔,材料之扎实,后者对新出土文献的充分关注,都令人钦佩,也给人以启迪。他们的结论有一致的地方,如都认为是屈原所独立创作(与朱熹之说不同),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周先生根据《山鬼》所描写背景同《涉江》所描写自然景色的一致等认为“《九歌》之作,应当是在去世之前不久的时候”②,而汤漳平则认为郭沫若的观点正确,从《九歌》歌辞的清新、调子的活泼断定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他们二人的共同点反映出学术的发展、思想方法的进步与研究工作逐步走向学术规范。胡适、陆侃如都认为《九歌》作于屈原之前。胡适说:“若《九歌》也是屈原作的,则楚辞的来源便找不出,文学史便成为神异记了。”陆侃如说:“我们若懂得一点文学进化的情形,便知这个历程绝不是一个人在十年二十年中所能经过的。……故这不但是‘与其’与‘宁可’,简直是‘可能’与‘不可能’的话了。至于他们的时代,大约在前五世纪;因为在形式上看来,他们显然是楚语古诗与《离骚》间的过渡作品。”③在当时他们也认为是运用了最科学的方法,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主观臆断。这里既有思想方法的问题,也有时代的局限问题,有整个学术风气的问题。现在学者们都认为《九歌》同屈原有关系,便是学术的进步。他们之间的分歧,也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轻易判定其正确或错误的。
楚辞其他篇的创作背景、创作时代问题,真伪与作者归属问题,及楚辞同南楚其他体裁作品的关系,楚国某些作家作品的挖掘,楚国文学的整体面貌和共同风格等,都还需要进行讨论、研究,在这种讨论、研究中,使正确的见解得到更充分的证明,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可与接受,使一些不正确的看法逐渐被淘汰。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有些问题的较完善的解决,有待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也有待于古代文献和先秦史、先秦文化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孤立的。哪怕同时有多少人从事于楚辞的研究,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这里有一个整体条件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学者说:“某个问题我可以解决。”是,你可以提出一种看法,但它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这不是就已知的材料作一种推想的问题。胡适将《九歌》摆到屈原以前很早的时代,解决了《离骚》的出现过于突兀的问题,但今天看来并不可靠,道理一样。
(二)楚辞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它既标志着我国在公元前四世纪和三世纪中文学发展的高度,又是后代诗歌和辞赋的范本,同时也是我国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宝贵的思想资源。那么,我们就应该不断地研读它。由于社会是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在不断转变之中,楚辞研究也会不断地继续下去。
首先,由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发展,文学研究的方法也在转变之中。古代研究《楚辞》者,侧重于名物训诂、校勘考释和忠君爱国思想的阐发,从艺术方面进行分析的很少。明代黄文焕的《楚辞听直》,清代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注意同屈原生平及楚国历史联系起来阐发诗意,而论艺之处不多。明代陆时雍的《楚辞疏》,清代林云铭的《楚辞灯》比较注重揭示其艺术感染的力量,后来的学者对此两书评价不高,也不甚注意。近几十年来从艺术方面分析的论著很多,但比较泛,深入研究有所发明、发现者,如汤炳正先生的《屈赋语言的旋律美》、《屈赋修辞举隅》等④,使人对屈赋的艺术成就有新的认识,对先秦诗歌的成就有新的认识者,还是不多见,我认为应该从社会历史的、心理的、语言的等各个方面对楚辞中的作品进行研究,既要注意传统的方法(音韵、文字、训诂、校勘和文献学其他方法如旧注辑佚、恢复原貌等),也要用一些新的方法多角度、多层次加以审视与分析。80年代以来先后兴起的欧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理论、叙事学理论、原型批评理论、阐释学理论、接受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等,也都可以引入。当然,一切以认真研读作品为原则,以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为条件,不能凭空想象,借着楚辞放野马,也不能拿了一定的理论程式,对旧说重加衍释。但无论怎样,将来还有不少工作可作,则是肯定的。
其次,任何一个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者们根据当时的观点(政治的、美学的、文艺的、社会的等),对此前文学作品作新的审视,因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有着不同的企盼。读者阅读古代文学作品,除了娱悦心情和想了解过去之外,也有意无意地想从中取得一些社会经验,至少愿意读一些同自己的阅历、情感有一定契合点,比较能引起心灵共鸣的东西。所以,研究者在文本所包含的思想和艺术的因素中,会有选择、有重点地述说其中的某一些问题,也会对一些问题作出新的阐释。比如,屈原的美政理论,政治改革的实践与理论,在新时期就很引起我们的关注,汤炳正先生的《草“宪”发微》对有关问题有所辨证,并引述屈原作品中能反映其思想者,探索了屈原草拟宪令的内容。我将《大招》也放在考察的范围之内,又联系吴起变法的内容,在汤先生基础上对宪令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勾稽和概括。至于屈原的美政思想,对一些官吏搜括人民的行为的揭露与抨击,不断加强个人修养的品质,同腐朽势力势不两立,不随波逐流的精神以及对真理的不懈追求等,在今天也都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难道在明天、后天、将来,屈原赋中的思想就会和读者完全格格不入?我认为不会,它当中所表现的高贵品质与伟大精神永远具有感召力,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中依据人们的习惯等,要作新的阐释罢了。
总的来说,屈原楚辞永远是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课题。欧洲人说:“说不完的莎士比亚。”我们说:“说不完的屈原。”
二
那么,楚辞研究将来应如何进行研究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既不能认为以后没有什么搞头了,也不能认为反正是拾遗补缺的事情,想起来写一点,怎么办都成。我觉得以下几点是应该注意的。
(一)要关心地下出土的材料。战国时代数百年时间,留到今天的文献太少太少,所以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在认识上完全是空白,只依据现有的材料来推断当时的很多事,是有困难的;有时也难免会牵强附会。材料少,话说到什么程度,这决定于学者的学风、治学态度,有的人急于求成,向前多跨了半步,便成为谬误(至于一些人缺乏文献学的常识和古代文史的基本训练,信口胡说,那是另一回事)。新材料是学术上取得突破的基础之一,所以要注意新材料的利用。比如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相马经》,一些学者认为它内容有重复,并且残缺不全。我研究的结果,发现这是一章完整的文字,章名即在篇首,名“大光破章”(学者们将此四字连下读为正文),第一部分为经文,全是四言韵语,多用比喻的手法描述观察马的眼睛的办法;第二部分为“传”,论述全章大意、要点;第三部分为“故训”,是对经文的解释⑤。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离骚》等作品比喻象征表现方法产生的文化背景,看出屈原创作风格同楚文化的关系。《汉书·淮南王传》中说刘安入朝,汉武帝“使为离骚传”。王念孙以为“传”为“傅”,与“赋”古通,是使约其大旨而为赋。一些好奇妄人因而作哗众之说,言《离骚》为刘安所作。其实,“传”乃是论述大义的文字,刘安《离骚传》论述《离骚》大意,给予评价,这正同班固、刘勰所引刘安《离骚传》内容、形式和语言风格一致。我们看了《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中经、传的特征,更坚信刘安只是给《离骚》作了《传》。
(二)研究楚辞应对先秦其他文学、历史的文献有较深的了解。要广泛阅读先秦、尤其是战国一段诸子、历史著作、礼俗制度之书。治楚辞者都是只读历来研究楚辞的论著,怎能跳出前人的樊篱?如《礼记》、《周礼》、《仪礼》、《大戴礼》等,1949年以后的大半个世纪中评价不高,以为全秦汉以后所伪造,或认为是记载封建统治阶级的礼制的,没有什么价值,礼学成了绝学,这些书也没有人看。我读这几种书解决了《橘颂》的创作动机和创作年代问题,也为确定左徒之职的执掌找到了依据,对于屈原的“娴于辞令”,从历史上加以考察,认识到从春秋时代,辞令作为一种独立的散文文体在先秦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于辞赋问对和后代议论散文的影响。“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前人说“功夫在书外”,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说功夫在于书本知识之外的阅历、经验和生活素养,一种可以理解为在你研究的书之外,研究什么便只读什么书,是打基础阶段的功夫,如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也一直这样,便是画地为牢,很难有突破的;有之,也可能只是牵强附会之言,甚至只能是引人发噱的奇谈怪论。因为还要研读其他的东西,楚辞学者也便不能在短期内出很多成果,写很多有新见解的论文。这看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可以减少很多低层次的重复以及搅浑水的东西,使学术正常、稳定发展。
(三)最好具备音韵、文字、训诂、历史名物和文献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是产生在我国最早阶段的文学作品,语言上障碍最大,人物事件、典章制度方面,也距离最远,很多记载有歧异,不少文字理解上也有分歧。不仅如此,流传中产生的错误也很多。由近几十年出土的一些材料可知,汉代以前流传的文献,传抄中用同音字代替的情况很普遍。如《战国纵横家书》中“赵”作“勺”,“韩”作“乾”,“梁”作“粱”,“尾生”作“尾星”,“曾参”作“增参”等。连这些人们常说的国名、人名也用假借字,而且也并不尽合“从简”的原则,这是学者们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如果没有传统“小学”和文献学方面的基础,难免郢书燕说,尽管讲得天花乱坠,最后仍难免不能成立的结果。如果只是个人谈感想,则无论怎样也无所谓,但写成论文发表或写成书出版,就会混淆视听,不仅于学术无益,而且有害。这些年来,有不少论著实属此类,所以不能不注意。
(四)要注意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情况。意识形态各个学科之间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古代文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要弄清某一时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问题,就得了解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张正明先生主编的《楚辞学文库》包括《楚史》、《楚国哲学史》、《楚国文学史》、《楚国经济史》、《楚辞文化背景研究》、《楚国艺术史》、《荆楚歌乐舞》、《楚国的城市和建筑》、《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楚系青铜器研究》、《楚系墓葬研究》、《楚系简帛文字编》、《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以及《中原楚文化研究》、《楚文化的南渐》、《楚文化的东渐》等,执笔者都是专家,对有关楚文化的研究成果分类做了阶段性的总结。另外如《楚文化史》(张正明)、《楚史新探》(宋公文)、《楚源流史》(何光岳)、《楚灭国研究》(何浩)、《楚国宗教概论》、《楚国思想史》(徐文武)等,也属此类。就楚辞论楚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有不少人是读读楚辞的注本和谈楚辞的文章,便在其间比较异同,寻找漏洞,利用其中的材料,发表看法。这样的论著充其量是重复了前人的某一个说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学术研究在求真的前提下要做到创新;没有创新,没有增加新的知识、提供有益的看法,便没有学术意义。近二十年来中低水平的重复太多,其原因便是研究者读书少,阅读范围狭窄,所以也就难出新意。
(五)要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学术创新,除了依赖新材料,便是依赖新的方法、新的研究手段。新方法中实际上包含了新的观察角度、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探索目标。古代研究论著虽然很多,但思想局限较大,方法单一,陈陈相因者多。游国恩先生主编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将前人训释《离骚》、《天问》的精要拈出,并加按语,可以说是嘉惠士林,功德无量。但我们看前人的一些解释,其看问题的角度,思维方法,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有些学科、有些研究方法是近代以后才有的。所以,在这方面还可大有作为。要注意的是不能仅套用一些名词术语,也不是用了现成的理论去套研究对象,对旧的结论作一番新的演绎,而首先要真正将这个理论弄透彻,以之用于楚辞的研究。
这里同时有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问题。楚辞中的作品,包括汉代的《招隐士》、《哀时命》等在内,也只有不多的几十篇,大家都去谈形式、谈内容,则难免重复和无谓的标新立异。采取多学科的研究,发挥学者们各自的特长,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开拓楚辞研究的范围,也是推进楚辞研究的重要方面。
多种研究手段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开拓了楚辞研究的范围,也可能会解决一些以往未能解决的关键问题,从而形成楚辞研究的新突破。
(六)要有一个好的学风。屈原的《橘颂》中说:“淑离不淫,梗其有理。”(淑:善。离:通“丽”。淫:过分)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这四句话,可以作为学者们坚持好的学风的座右铭。研究方法要新、要好,但不能追求奇异,耍花枪;下结论要实事求是,论证要有理有据,推论要严密,要能顶得住社会上浮躁奢华、急功近利的风气。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但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我们的看法不断地接近真理。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追求真理,或者说是为了追求客观的真实,使我们的看法更符合事实。因此,我们就应该继承前人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这就有一个守正的问题。某一问题前人或今人已经解决了,我们就应该加以肯定,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向前推进。如果猎奇好异,取非而弃是,那就背离了正确的目标,其目的性也就成问题了。只有在已有正确结论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的突破,而在正确结论基础上哪怕我们的贡献只有一点点,也是对学术的贡献。证据不可靠,推论不严谨,结论无论如何惊人,也没有价值。所以学风问题至关重要。楚辞学会的会长褚斌杰先生和老一辈学者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也做了不少工作,学会也还可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七)从整体上说,要形成一个创新、综合、普及互相协调的合理机制,形成三股力量,出三类成果。哪三支力量、三类成果?
一支是着重于研究前沿性的问题,解决楚辞和屈原研究中的难点。研究论文和专题性论著应主要侧重于这方面。我们以上谈的一些意见,主要就是针对这一方面的
第二支队伍对此前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梳理,这更具有学术史的意义。既有对现当代学者成果的总结和梳理,也有对古代研究的总结和提炼,所以,这里更多地体现着守正的重要性。总结性、概括性的论著,各种文学史著作和工具书主要属于这一类。有的学者治学不追求有什么突破,但学问渊博,根底扎实,著述、讲授引述前人之说,择善而从,有理有据,论述公允而可信,这也是很大的贡献。为什么?因为前人之说或是只就某一方面言,并未论及全体,或是维护自己已有之成说,在某些方面总会有所不足。要在各家基础上作系统论述,成一有机整体,亦非有大学问、有好的识力不能:采前修时贤之说而无遗珠,要大学问;取舍适当而无偏颇,要有学术眼光。这看来只是“述”,其实也是“创”,是以述为创。我认为,这类学者同那些缺乏一定学术积累信口开河的所谓学者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任何一个领域的学者,当其初入该领域之时,都是靠了那些严谨的通论性著作而奠定了基础的,所以也不能小看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支队伍,主要是普及的工作。但普及要普及正确的东西,不能用错误的东西来误人子弟。这一支队伍主要依据第二类的论著,也可以从第一类的论著中直接吸取新的成果,以比较通俗的形式介绍给大家。一般的普及性、鉴赏性书籍属于这一类。这方面的工作要作好也很不容易,楚辞方面,文怀沙、马茂元、聂石樵、金开诚、汤炳正等先生的一些注本,都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赏析性读本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楚辞鉴赏集》(1988)、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先秦诗歌鉴赏辞典》(1994)、上海辞书出版社《先秦诗鉴赏辞典》(1998)和巴蜀书社《楚辞赏析》(1999)等,而上海辞书出版社一套鉴赏性书籍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不仅有袖珍本《先秦诗鉴赏辞典》,还出了《名家品诗坊·楚辞》,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文史知识》和《古典文学知识》两个刊物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好的工作。实际上普及工作也是很重要的,第一、二支队伍中,也都应有人时时来作些这方面的工作。
上面说的三支队伍并不能截然分开,实际上是三个方面的工作,学者们在这三个方面以某一方面为主而已。同时,第二类、第三类的工作之中,也不是没有创造的成分,第三类也不是不含有创造和总结、提炼的因素。严格说来,任何工作要做好,都要发挥创造精神。如姜亮夫先生的《楚辞通故》,洋洋数百万字,既是楚辞学研究的总结,也有创新和突破。崔富章先生主编的《楚辞学文库》也是同样;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既有对以前学者成果的总结、吸收,又体现着自己的学术创新,而不少学者学习楚辞的入门书也是它。所以上面的划分只是大略而言。
我相信,楚辞学的研究工作会越来越好,中国屈原学会在汤炳正先生、褚斌杰先生的领导下健康发展,在这二十年中做了大量工作,毛庆、方铭等负责具体工作的先生也操劳有功。二十多年中涌现出了大批成绩显著的中青年学者,形势是喜人的。近年又出版了《中国楚辞学》丛刊,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楚辞学的不断走向繁荣是没有疑问的。
注释:
①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②周勋初:《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③并见陆侃如:《屈原评传》,《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第289、290页。
④见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
⑤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