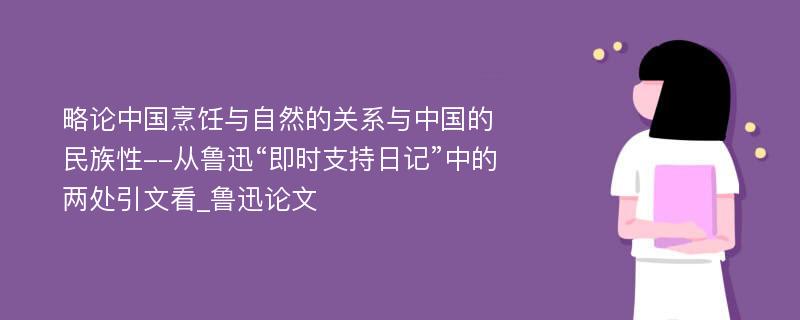
中国菜与性及与中国国民性之关系略识——从鲁迅《马上支日记》中的两段引文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国民性论文,引文论文,中国论文,两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马上支日记》①是鲁迅1926年7月写的日记体文章,记录当时的经历和感想,虽非精心组织之作,却也保存了一些生动有趣的材料。文中提到,7月2日②,他在北京东单一家兼售日文书籍的商店东亚公司购买了安冈秀夫著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鲁迅一向重视外国人所著研究中国国民性的书籍。在日本留学时期就阅读了涩江保翻译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Arthur H.Smith,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③,印象深刻,颇有助于他思考中国国民性改造问题。④鲁迅读了安冈秀夫的书,认为该书受到史密斯著作的影响。他评论道:“(著者)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气质》——引者),常常引为典据。”语气里含有视其为模仿之作的意思。接下来,鲁迅没有对这本书做更多的评价。但在8年后的一个场合,他又谈起这本书时说:“《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⑤显然就是当时的印象。
购得此书一个多星期后,鲁迅在7月4日的“马上支日记”中,又谈起阅读安冈氏著作的感想。这次的话题关乎中国的饮食。安冈著作最后一章《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中引用了威廉士(通译威廉斯,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中文名卫三畏)所著《中国》(The Middle Kingdom)一书中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推论其为好色的民族一段话:
这好色的国民,便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也大概以所想象的性欲底效能为目的。从国外输入的特殊产物的最多数,就是认为含有这种效能的东西。……在大宴会中,许多菜单的最大部分,即是想象为含有或种特殊的强壮剂底性质的奇妙的原料所做。……⑥
鲁迅说,他对于外国人指摘中国缺点的言论,向来并不反感,但对这段论述却大不以为然,视为奇谈怪论,不合情理。鲁迅此处的原话是:“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于是,他从两方面加以反驳。一方面,“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另一方面,“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
这位美国传教士是在自己有限的见闻基础上做出这样的论断的,如果对情境加以限定,用词更准确一些,或许不至于引起鲁迅的反感。这段论述中“最多数”、“最大部分”等词语,使他的论点显得偏激,尽管从原文看来并没有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⑦鲁迅的批评,自然也是从自己的经验和见闻出发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分明体会出他在为中国菜乃至中国人(至少是广大民众)辩护的意思。但他从以上两方面进行的反驳,看起来不很有力。接下来,又没有进一步的论述——这里应该考虑到,鲁迅这篇文章是日记体的随笔,而非逻辑性很强的论辩文字。
安冈秀夫引用的威廉斯的《中国》,是一本西方汉学名著,篇幅要比《中国人气质》大得多,而且成书时间也早得多。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出版后几十年间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然而,也许是因为史密斯的著作简明扼要而易于流传的缘故吧,他的著作在中国倒比卫三畏的大部头著作名气大。⑧鲁迅显然没有读过《中国》一书,对威廉斯的生平缺乏了解,他的著译中提到这位传教士只此一次。《鲁迅全集》注释对这位美国传教士的介绍也显得简略:“威廉士(S.W.Williams,1812-1884)美国传教士。1833年(道光十三年)来华传教,1856年后在美国驻华公使馆任职。《中国》一书出版于1848年,1883年修订再版。”⑨单看这条注释,读者对这位传教士难得较深的印象。如果因为这段引文,使鲁迅,并且通过他,使读者对这位美国传教士留下坏印象,则对威廉斯是不公平的。其实,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中至少五次引用了卫三畏的著作,足以证明史氏将其视为经典作家。例如,在“孝道”(Filial Piety)一章中,他引用卫三畏的话道:“把中国人的‘礼’的观念译作英文的‘ceremony’是不周密的,因为‘礼’不仅包括外部的行为,而且涉及了所有规范理解及其行为动机的正确原则。”使读者既见识了卫三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顺便感受一下他作为英华词典编纂家的严谨。又如,“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Polytheism,Pantheism,Atheism)一章引述的是:“我们对孔子作为圣人所产生的影响,和其思想对民族产生的束缚作用的估计,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过高的。他确立的道德标准在其后的年代里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所有有良心的人都要接受这道德标准的评判。”读过《中国人气质》的鲁迅,对这本书所受卫三畏的影响应当有所觉察,但可惜的是,在《马上支日记》及其他文字中,却没有留下更多的论述。鲁迅将其名字译作“威廉士”(当时也有人译作“卫廉士”),可能不知道他还有“卫三畏”这个颇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名字。如果当时鲁迅能够得到和阅读《中国》这样比较全面和公正的著作,他对《中国人气质》以及对美国的中国研究水平的看法也许就会有所不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在后来几十年间,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及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卫三畏对西方中国学研究的贡献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⑩直到2004年,他的巨著《中国》的中译本才与广大读者见面。(11)
2
卫三畏1812年9月2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由提卡的一个印刷商之家。19岁入本州特罗伊市仁塞勒技术学校学习。1833年被美国新教组织美部会派往广州,担任传教组织的印刷工。1838年至1851年,在广州负责印刷《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同时他也是丛报的编辑和撰稿人。1835年,他到澳门,完成了麦都思(W.H.Medhurst)所编《福建方言辞典》(Kok-keen Dictionary)的印刷工作。1837年,他到日本访问,目的是送几个遭遇海难的日本水手回国。与这些水手的相识和相处,促成他学习日文。几年间,他们合作,将《圣经》中的《创世纪》、《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等译为日文。1837年至1841年,他负责印刷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的《广东方言中文文选》(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其中将近一半内容由他本人撰写。1844年11月,他返美度假。因编辑《中国丛报》的需要,他计划购买一套新的中文字模。为筹集资金,在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介绍中国社会生活、历史及风俗。这些讲稿后来成了他的《中国》一书的雏形。1853年和1854年,他作为译员参加了佩里(Perry)将军对日本的远征。1855年,他到了北京,担任美国驻华使团的译员和秘书。1858年,协助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S.R.Reed)同中国谈判,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在担任使馆秘书和译员期间,他九次出任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1876年他返回美国,次年就任耶鲁大学新创设的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这是美国首个汉学教授职位。1848年,他的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及晚清社会现状的著作《中国——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出版,1883年修订再版。卫三畏因这本书被美国联合学院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LL.D)。该书分上下两卷,凡23章(增订本26章,副题改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历史及其居民概观),从中国的历史地理到风土人情,从政治经济到文学艺术,几乎无不涉及。尽可能客观地评价中华文明的成就和落后之处,是作者为本书确定的目标。卫三畏在序言中说,他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在西方读者中“为中国人民及其文明洗刷掉如此经常地加予他们的那些独特的几乎无可名状的可笑印象”,他要客观地评价中国文明,将它“放在适当的位置”、“努力展现其国民性更好的特点”。他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巨大影响,因而对孔子的学说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赞赏孔子的政治清白必须建立在个人正直的基础上的主张,以及孔子肯定的自省、自强不息的精神。他甚至将孔子的儒家学说和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这个观念的阐释在西方研究者中是首次。书中对鸦片战争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视角与材料都比较新。他指出,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人是贪婪的,他们与其说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勿宁说是从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可见,卫三畏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是公平的。在《中国总论》修订本中,他还对刚刚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进行了分析。在中国长期生活的卫三畏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境况,谴责腐败、犯罪和各种非人道行为。1859年,他用中文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卖身他国者的警告》,揭露葡萄牙人欺骗中国劳工签订卖身契的卑劣行径。他写道:“这本小册子已经印刷了六次。……两周间卖出了六千册。中国劳工在那些人贩子手中所受的虐待可谓骇人听闻。在澳门,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到葡萄牙人家中或船上工作,他们很担心被绑架并被偷偷卖掉。1858年被掳往境外的中国人达一万多人,今年从这里被掳走的已有五千人。葡萄牙人异常残忍并且肆无忌惮,他们利用本地人作为打手,其残忍超过他们十倍。”(12)晚年,他对美国国会提出的非人道的驱逐华人的《中国移民法案》深恶痛绝,因为这激起了他心中最深刻的情感:对中国的尊敬和爱。他写道:“在加州和内华达州,对中国人的恶意已经在许多党派的议案中提出来。其中,来自阿拉巴马州的雪莱要求把十二万五千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关在蛮荒的区域中,使其‘尽可能远离白人区’,在那里给每个人土地四十英亩,禁止他们离开,美国人,除牧师和传教士以外,不得进入这个区域(七千八百平方英里),否则将被处以剥夺公民权和五年以上牢狱的惩罚,并且不能获得赦免。这样,我们发现了什么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至少对一个美国人而言。这个议案是具有同类性质的企图以不光彩的手段驱逐中国人的议案中的一个。在十八个月中它们的数量达到六百个。”(13)年老体衰的卫三畏,放下修改《中国总论》的紧迫任务,撰写了一篇严正驳斥这些荒唐观点的论文,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尊重和热爱,同时也对美国政界人士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隔膜程度感到震惊。其中有这样一段:
加州法庭想以立法来反对中国人时,草率地将中国人同印地安人等同起来,颇有些离奇古怪。生理学家查尔斯·皮克林将中国人和印第安人归为蒙古人,而加州的最高法院却认为“印第安人包括汉族和蒙古族人”。在发生概念错误的同时,它还支持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它把现存最古老国度的臣民和一个从未超越部落状态的种族相提并论;把这样一个其文学早于《诗篇》和《出埃及记》、用一种如果法官本人肯于学习就不会视之为印第安语的语言写作的,而其读者的数量超过了其他任何民族的作品的民族,与最高写作成就仅为一些图画和牛皮上的符号的那些人混为一谈;把勤奋、谨慎、技艺、学识、发明等所有品质和全部保障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物品与猎人和游牧民族的本能和习惯等同。它诋毁了一个教会我们如何制作瓷器、丝绸、火药,给予我们指南针,展示给我们茶叶的用处,启示我们采用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的民族,将其与轻视劳动,没有艺术、学校、贸易的那个种族归为同类,后者的一部分现在还混迹于加州人中间,以挖草根谋生。(14)
当然,卫三畏毕竟是一个传教士。他一生活动的目的,是把基督教传入中国,让他的上帝在中国这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获得更多的信众。
顺便提一句,卫三畏在技术学院的同学达纳(J.D.Dana,1813-1895),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矿物学家,著作颇丰。鲁迅青年时代学习采矿,读过江南制造局印行的达纳的著作《金石识别》,并在书上写下不少批注。(15)卫三畏和达纳通信频繁,友情甚笃。但因为鲁迅不谙英文,无缘看到相关材料,对卫三畏也就没有产生连带的亲近感,文章中就这样一笔带过,的确是遗憾的事。
卫三畏还著有《简易汉语教程》(Easy Lessons in China,1842)、《英华分韵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1856)、《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1877)等。卫三畏于1884年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去世。
3
卫三畏对中国菜颇涉性欲的论述并非无中生有。他曾标榜说,他的著作基于自己在中国的见闻。以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中国南方地区论,饮食上追求滋补强身的风俗可能盛于北方。直到今天,中国南北饮食中都不乏这样的观念和实例。卫三畏初到中国,由于新鲜感和好奇心,在给父母的信中,将品尝中国菜的感受写了下来。例如,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详细描绘了参加中式晚宴的见闻感受,并兴味盎然地列举一些菜品:燕窝、莲子、猪舌、鱼肚、鱼翅、海蜇、鱼头等。(16)但在中国生活几十年后,他写《中国》一书时,就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烹饪艺术还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他指的是很多细节并不讲究。(17)后来,因为看到中国传统中医药中使用的种种奇怪的药引,及某些地区餐桌上的各种爬行动物乃至与人类亲近的猫、猴子等,好奇心转为厌恶感,再加上所见所闻菜与性能力之间关系的种种讲究,获得了深刻的印象,遂有了上引那段论述。鲁迅也曾到过华南——在那里他是被视为“北方佬”的——但短暂的生活,并没有留下多少有关饮食的记载,但可以推论,他对食用生猛的习俗,是厌恶的。至少,对中医使用的一些奇怪的“药引子”,鲁迅当能与卫三畏发生同感。卫三畏书中罗列的药引,很可能会使鲁迅想起小时候为父亲治病的老中医让他踏破铁鞋去寻找的“平地木”、“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对”之类。
从《马上支日记》上下文看,威廉斯的观点遭到批评,还因为受了安冈观点的牵累。因为紧接着,鲁迅引述了安冈书中的一段文字,在他看来,就不止是奇谈怪论,而简直是荒谬绝伦了。安冈为了证明威廉斯的上述观点,进一步举例并发挥道:
笋和支那人的关系,也与虾正相同。彼国人的嗜笋,可谓在日本人以上。虽然是可笑的话,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象来的罢。
鲁迅批判的重点就是安冈的这段话。卫三畏的《中国》,鲁迅未曾寓目,而这本日文书却是刚刚买到和阅读。鲁迅说,笋是中国南方人民常吃的一种菜,他自己在故乡就吃了十多年,“现在回想,自省,无论如何,总是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爱它‘挺然翘然’的思想的影子来。”鲁迅总结道:“笋虽然常见于南边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头的电干和屋里的柱子一般,虽‘挺然翘然’,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还说:“我没有恭逢过奉陪‘大宴会’的光荣,只是经历了几回中宴会,吃些燕窝鱼翅。现在回想,宴中宴后,倒也并不特别发生好色之心。”
应该指出,鲁迅的批评部分地依据个人的体验,既然是个人的,也就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完全否定中国菜与性欲的关系,无疑要走向另一个极端。既然阔人有大餐可吃,有“饱暖思淫欲”的条件,也就有条件将滋补品加入菜肴,而“上行下效”,社会风气也就不能不受影响。例如,关于虾与性欲的关系,连鲁迅也承认,“在中国也听到过这类话。”上层社会的实践会衍化为一种普遍的风气,这类事例屡见不鲜。此外,因为形状相似而想象其有刺激性欲效果的物品,日常生活中也是存在的,例如鲁迅文章中提到的肉苁蓉。鲁迅辩解说,那是药,不是菜。但既然可以入药,根据中国“药食同源”论,也就有可能被加入食品,端上餐桌。实际上,肉苁蓉今天仍被广泛使用,其中多有以滋补强身为号召者。
安冈氏在引述《中国》一书时,并未注意到,该书第六章谈到在中国普遍被食用的笋时,有这样的描述:和尚们也大量种植竹子,竹笋可以使用,竹节中提取的竹黄可拿到市场出售(18)。如果照安冈的说法,则寺庙里早就应该禁止和尚们种植和食用竹笋了。
但鲁迅在文章中对卫三畏还有更进一步的批评:“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诛心之论,略显刻薄,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中国社会上常常有此类性心理曲折表现的事例。正如鲁迅所说,在《红楼梦》里,“道学家看见淫”,因为心中有鬼。攻击别人,往往是在暴露自己。安冈氏在书中就举出中国小说《留东外史》攻击日本人的事例:“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地描写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地费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鲁迅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批驳了安冈关于笋与性的论述,“并不足证明中国人是正经的国民”。在现实中,中国人的不正经,正表现在有些所谓卫道士“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
鲁迅并没有进而对这位一门心思想象着“挺然翘然”的研究者和那位夸大中国菜中性欲成分的传教士做更多的抨击,而是点到为止,遂即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中国的“正人君子”了。
卫三畏是一位美国新教传教士,父母都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他从小受到的是禁欲的教育。1875年,他从中国回美国,途经欧洲,参观了许多教堂。他的观感是,那些雕像、绘画和装饰对加强教徒的虔诚心起不到任何作用。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对欧洲大陆那光辉灿烂的宗教艺术的教育作用提出质疑,从中可窥见其清教徒性情之一斑。他说,一个人站在安特卫普大教堂里,关注更多的是鲁本斯的《耶稣受难图》,而不是布道或《圣经》。他庆幸自己不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接受宗教的。他还写道:“最近我又饶有兴味地重读了上帝传给摩西的命令:将迦南的绘画和肖像全部销毁,以免使以色列人堕入偶像崇拜。……有纯洁信仰的团体一旦与登峰造极的雕塑、绘画等艺术结合在一起,精神的东西便堕入世俗的色情和肉感。”(19)“不见可欲,使心不乱”,颇类中国“道学家”的口吻。他之批评中国饮食中的性欲成分太多,正如同批评欧洲教堂里宗教绘画和雕塑太肉感。
4
关于安冈秀夫的生平和著作,《鲁迅全集》的注释更为简略:“《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 1926年4月东京聚芳阁出版,是一本贬损中华民族的书。”(20)安冈秀夫生于1873年,1892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1893年开始供职于《时事新报》,1923年任该报主笔。安冈对神学、文学、历史和美术等感兴趣。著有《日本与支那》(1915)等。《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从中国元明清三代小说中寻找例证,罗列起来,说明中国的民族特点。该书取材甚广,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炀帝艳史》、《今古奇观》、《痴婆子传》等等,都在引用之列。虽然有些材料运用得不一定贴切,但总的来说,显示出作者对中国文学的熟稔。如所周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有《中国小说史略》行世。他在囊中羞涩时选购了这本书,说明他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的确,小说中很多描写民间生活习俗的详细而生动的材料。在7月5的“马上支日记”里,鲁迅这样写道:“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因此,鲁迅并没有抹杀这本书的优点。他说:“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而且,鲁迅在日记的开头就承认,他看到安冈著作批评中国国民性的缺点,例如,过于注重体面和仪容等,的确说到了痛处,自己看了,也不免汗流浃背。他说:“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应该提一句,关于中国菜讲究滋补性功能的观点,安冈在著作中不但引用了威廉斯的《中国》一书,而且还援引另一位美国人桑格的《妓女史》中的结论,即“支那人是世界上最淫荡的民族之一,……最显著的证据是,他们在食物原料和烹饪方法的选择取舍方面,很大程度上受性欲的目的支配。”(21)可见,这种印象在那时的外国人舆论中有一定的普遍性。
勿庸讳言,直到现在,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实践仍然相当盛行。所谓药膳,已经并非只出现在阔人的餐桌上了。但维系生命、强身健体是菜肴的主要功能,各国都在这样实践,本不足奇。食色,性也。把食品和性联系起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注重饮食中的滋补强身功能,因而得出中国人特别好色、最为淫荡的结论,是过分的。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民,并不比中国人轻看性事。当今,充斥市面的各色保健食品中,就不乏以提高性能力为号召的舶来品。再如“伟哥”之类尖端科技成果,被广泛服用,也是铁一般的事实。菜肴既然可以健身,那么,再进一步,其具有增强性功能的作用就是题中应有之意。比起专事刺激性欲的药物,已是小巫了。
我们不能因为外国作者的夸张的论点而否定事实的存在。鲁迅这篇漫谈式的文字,论点也有不周到之处。他在批评外国作者的偏至时,不自觉地完全否定了中国食物与性的关系,显得是在为中国民族性辩护,与他一贯的严厉批判国民性的态度形成了矛盾。
5
鲁迅抓住安冈著作中一段话进行严厉的批评和尖刻的讽刺,使该书名誉大受损害。直到现在,中国读者大多仍以鲁迅的意见为指归,对该书采取轻蔑态度,使其几不可与威廉斯的《中国》和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同日而语。在8年后那封谈及安冈著作的信中,鲁迅还连带批评了日本的中国研究:
……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斯密司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22)
从鲁迅的藏书中可以大概知道,鲁迅一生始终关注日本的中国研究成果。这里可以略举几种他购买的日文原著:河野弥太吉的《支那研究》(二册,1924-1925)、后藤朝太郎的《支那文化研究》(东京富山房,1925)和《欢乐的中国》(东京,日本邮船会社,1925)、木下圶太郎的《支那南北记》(东京改造社,1926)、日本支那学社编的《支那学》(1929)、池田龙藏的《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研究》(东京,池田无尽研究所,1931),橘朴的《支那社会的研究》(1936),等等。(23)应该说,上列诸书中不乏资料扎实、态度平正的著作。但晚年的鲁迅,越来越不喜欢在某种政治目的驱使下的日本中国学研究。例如,关于上列书目中提到的后藤朝太郎,鲁迅在给陶亢德的信中也曾提及:“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后藤朝太郎曾到上海观察研究,所著《支那的男人女人们——现代支那的生活相》将上海作为“销金窟”、“花花世界”进行渲染。因为是戴着放大镜来看中国城市某一角落的生活,当然越看越丑陋,越看越淫秽。该书因为太多涉及性事,被判定“有伤风化”,曾在日本遭禁。鲁迅在日本时即感受到一种普遍的贬损中国的风气,后来更看到某些怀有政治意图的著作,因此一直对日本的中国研究保持警惕。像《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这类怀有恶意的著作就无疑是给鲁迅带来坏印象的重要原因。
鲁迅关注日本的中国研究,但他这方面的系统论述并不多。对安冈秀夫著作,他却多次提及,算是一个例外。除了在《马上支日记》和给友人的信中抨击外,1935年,他在给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一书写的序言里,又重提此书,并且连带嘲笑其他一些所谓“支那通”的做法:“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24)可见鲁迅对“竹笋性欲说”的印象有多深,近十年过去,犹存余愤。鲁迅的序言中透露出这样的意见:日本的中国研究呈现出每况愈下的情形,这个喜欢结论的民族在明治时代有关支那研究的成绩,基本上受着《支那人气质》的影响,而后来,就有了上述这些五花八门的“结论”。因为所持的是轻蔑的态度,所怀是轻薄的情绪,所抱是险恶的目的,这些结论究竟怎样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为内山完造的著作写序,对鲁迅而言,是一项颇为艰巨的工作。他不得不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有所论列,不得不先将那些谬论提出来给予批判,以衬托出自己老朋友的著作中所怀的善意。但即便在这样一篇应酬文字里,鲁迅还是坚持他一贯的态度,在批评日本中国研究的谬论的同时,更注重中国人的自省。他一生很少谈及日本民族劣根性之类的话题,正与这种态度相符。在序言中,他提醒读者,内山完造这本书“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25)他后来亲自把这篇序言译为中文,在编入《且介亭杂文二集》时,又在后记中特意说明道:“《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里,我在对于‘支那通’加以讥刺,且说明日本人的喜欢结论,语意之间好像笑着他们的粗疏。然而这脾气是也有长处的,他们的急于寻求结论,是因为急于实行的缘故,我们不应该笑一笑就完。”(26)他也是在提醒自己克制,不以同样的轻薄态度回击日本“支那通”们,而要善意地指出其他民族的缺点,更要把功夫多花在自我的反省和改造上。
同样是1926年7月,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在东亚公司购买了安冈的这本书。(27)当时周氏兄弟已经决裂,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合买一书,并交换看法。但两兄弟的意见却惊人地一致。周作人看了书,也立即写了文章,给予严厉批评。(28)他的文章与鲁迅的“日记”几乎同时发表在《语丝》周刊上,而比鲁迅批驳“竹笋性欲说”的那一节稍早。(29)周作人虽没有提及竹笋,但火气甚大,因为他看出了日本作者的恶意。当然,同鲁迅一样,他首先承认,作者嘲骂的“都的确是中国的劣点”,“汉人真是该死的民族,他的不长进不学好都是百口莫辩的。我们不必去远引五六百年前的小说来做见证,只就目睹耳闻的实事来讲,卑怯,凶残,淫乱,愚陋,说诳,真是到处皆是,便是最雄辩的所谓国家主义者也决辩护不过来,结果无非只是追加表示其傲慢与虚伪而已。”接着,笔锋一转,周作人说,他不希望日本人写这样一本书,并不是说中国人的缺点只能由自己来列举,或者说日本也自有其缺点,没有资格来指责中国人。“我只觉得‘支那通’的这种态度不大好,决不是日本的名誉。……我们不要日本来赞美或为中国辩解,我们只希望她诚实地严正地劝告以至责难,但支那通的那种轻薄卑劣的态度能免去总以免去为宜。我为爱日本的文化故,不愿这个轻薄成为日本民族性之一。”对安冈的轻薄态度,周作人从总体上给予谴责,鲁迅则通过实例予以嘲讽。周作人这番批评,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对日本中国研究的评价。
6
相比之下,鲁迅对西方传教士的著作更有好感,尽管实际上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也一样存在贬低中国人的倾向,正如鲁迅在那封信中指出的:该书“错误亦多”。曾有研究者认为,鲁迅的思想方法颇受外国传教士的影响,其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正是用外国传教士的视角来看中国,客观上起到了贬低中国民族的效果。但从这两段引文来看,鲁迅又曾坚决反对传教士恶意贬损中国国民性的观点,甚至矫枉过正,走了极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饮食中与性有关的事实。
从总体上说,鲁迅文中关于笋的那段论述是颇有说服力的。它抓住对方的弱点施行猛烈攻击,有时暂且不顾其他相关事实,为的是达到制胜的效果。这是鲁迅文章修辞手法的一个特点。虽然如此,鲁迅并非一味偏激,尽情嘲弄对手,毫不顾及相关事实。便是在这篇较为随意的文章中,鲁迅的持论也还是顾及全体,有分寸感的。其表现就是,在严厉批判日本作者的谬说时,也指出其著作的优点。史密斯著作所持态度是较为平正的,这一点给鲁迅留下了好的印象。他的《中国人气质》书前列出三句圣贤语录,为其著述的宗旨。其一,孔子《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宣示了善意;其二,欧文·霍尔姆斯的“有关人的研究乃所有学科中最艰深者”,显示着谨严;其三,托马斯·卡莱尔的“我们坚信这样的格言:在指出一个人的缺点之前先看到他的优点。这对于正确判断任何人和事都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既实事求是,又全面周到,更显出忠厚宽恕之德。相比之下,安冈的著作分为9个部分,其中竟有8个部分指摘中国民族劣根性,只有“能耐能忍”一章有些正面肯定的材料,难怪给人以过分挑剔、心存不善的印象。
鲁迅在逝世前十四天还写道:“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30)揣摩鲁迅给陶亢德信的语气,可能他在回答对方的询问,大约陶亢德正在寻找这本日文书,也许还有翻译出版的计划。鲁迅不但未能提供样本,而且还表达了负面的意见,使该书失去一个在中国出版的机会。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卫三畏的《中国》一书已经有了中文版,中国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西方汉学家怎样评价中国。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如果去除书中一些缺少根据的、偏激的论点,也不无参考价值,如能翻译出版,至少,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当时日本中国学研究的标本。
注释:
①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367页。
②据《鲁迅日记》,该书实际购买时间应为6月26日。《鲁迅全集》第15卷,第625页。
③亚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894.日译本涩江保译,东京博文馆,明治二十九年[1896]版)。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可能读过这个译本。参见李冬木《关于羽化涩江保译〈支那人气质〉》,《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4、5期。
④参见张梦阳:《鲁迅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第二辑(1980);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二章“国民性理论质疑”;李冬木:《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
⑤鲁迅《致陶亢德(1933年10月27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468页。
⑥安岡秀夫:“小説から見たゐ支那民族性”,东京聚芳閣、大正十五年版,第160-161。
⑦鲁迅“日记”中的引文系他本人所译。译文中出现了“最多数”、“最大部分”这样的词语,与原文稍有出入。试比较英文原文:“Many articles of food are sought after by this sensual people for their supposed aphrodisiac qualities,and most of the singular productions brought from abroad for food are of this nature.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numerous made dishes seen at great feasts among the Chinese consists of such odd articles,most of which are supposed to possess some peculiar strengthening quality." (S.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Vol.2,Ch.13,p.50,New York:Wiley and Putnam,1848)安冈书中的日译文为:“此多情なる国民は、食物の原料を求めるに當りても、多くは其想像せる性欲的効能を目標として居る。国外より輸入せられる特殊產物の最多数は、右の効能を含むと認められた物である。…大宴会に於ける数多き献立の大部分は、或特殊の強壮剤的性質を含むと想像せられる奇妙な原料から成り立って居る。”显然,原文的用词不如两种翻译文本的用词绝对化。鲁迅译文,比日译文多了一个“最”字,比原文多两个“最”字。尽管如此,原文语气的夸张性仍是明显的。
⑧涩江保在《中国人气质》的译本序言中比较两书时,也指出此点。
⑨《鲁迅全集》第3卷第358页。
⑩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人气质》中文译本的译者评析中有这样的论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长期积累,才于1894年出现了史密斯这部最系统、深刻、独到的研究著作——《中国人气质》。”没有提到史密斯的这位老前辈。见张梦阳、王丽娟译《中国人气质》,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1)中译本名为《中国总论》,陈俱译、陈绛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2)Frederic Williams,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LL.D,New York:G.P.Putnam's Sons,1889,reprinted 1972,SR Scholarly Resources Inc.,PP.325-326.
(13)Ibid,PP 427-428.
(14)Ibid,PP 428-429.
(15)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说:“属于科学上的古典之作的,则有……代那的《金石识别》……。”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325页。《金石识别》原名《矿物学手册》,中译本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藏版,木刻线装,十二卷。鲁迅所有的一部现存六卷,藏绍兴鲁迅纪念馆。
(16)Frederic Williams,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LL.D,P 69.
(17)Middle Kingdom,Vol.1,P781.
(18)Middle Kingdom,Vol.1,P358.“(Bamboo shoots) are cut like asparagus to eat as a pickle or a comfit,or by boiling or stewing.Sedentary Buddhist priests raise the Lenten fare for themselves or to sell,and extract the tabasheer from the joints of the old culms,to sell as a precious medicine for almost anything which ails you.”竹黄(tabasheer)作为药品,这里说“几乎包治百病”,似也可做强身之物。但据药典,并没有特别说明与助长性欲有关,否则将不但增添“淫风炽盛”的例证,而且连带损害寺院的名誉。
(19)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LLD,PP 408-409.
(20)《鲁迅全集》第3卷第356-357页。
(21)William Sanger,The History of Prostitution:Its Extent,Causes and Effects Throughout the World,New York,Harper,1858.转引自安冈秀夫:《小説から見た支那民族性》,第180页。此处使用了“很大程度”,及“最淫荡的民族之一”,语气上就没有卫三畏那段话的译文绝对化。
(22)《鲁迅全集》第12卷,第468页。
(23)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部资料),1959年。
(24)(25)《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75、276页。
(26)《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65页。
(27)《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中册,第533页。
(28)周作人:《我们的闲话(二十四)》,载1926年7月19日《语丝》第88期。收入《谈虎集》时改题为《支那的民族性》。
(29)《马上支日记》连载于1926年7月12日、26日,8月2日、16日《语丝》第87、88、90、92期。
(30)《立此存照(三)》,《鲁迅全集》第6卷第648-6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