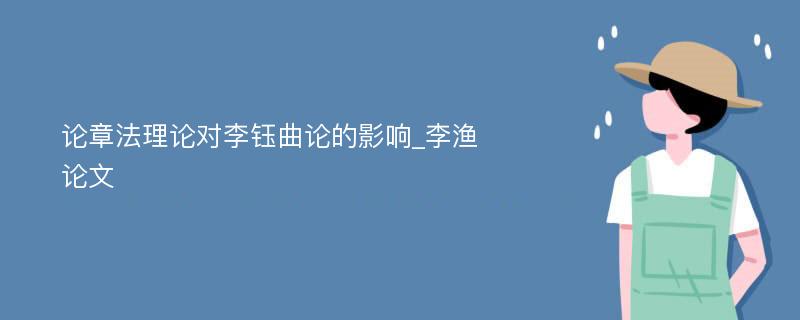
试论八股文“章法理论”对李渔曲论的浸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渔论文,章法论文,试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股文的“章法理论”对李渔曲论的浸染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的:一,由此及彼,以八股文“章法理论”作为建构曲论的逻辑起点;二,取类引譬,直接援引八股文“章法理论”的理论成果,丰富曲论的理论内涵。这种“浸染”使李渔的曲论得以突破前人曲论“散金碎玉”的缺陷而建立起严整、完备的体系。
八股文作为读书人仕进的敲门砖,早已淹没为历史的陈迹。但是,这一曾经存在了五六百年并几乎为所有的士子所习用过的文体,却必然会在文体发展的河床上留下自己的印迹。为便于士子应举,写出为主司所好的八股文,有人便着力研究八股文的写作方法、技巧,八股文的“章法理论”因此而臻于极度成熟。这一理论尽管并无多少鲜活的思想,但由于它影响广泛,对同时存在但理论却相对晚熟的别种文体(如小说、戏曲)的理论建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就八股文“章法理论”对李渔曲论的影响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本质上源于宋元经义的八股文,在明朝成化年间已具备了完整的功令程式,并于明末清初达到了无施不可的高度成熟境界;同时,以明清传奇为代表的戏曲也继元杂剧之后登上了另一个高峰。两种同时存在高度繁荣的文学样式之间呈现了很强的互通性:一是内容上有所交叉,不仅出现了以八股笔法作曲、以经义题材入戏的现象;而且,戏曲题材也进入了八股文写作的视野,出现了一大批为戏曲中人物立言的游戏八股文。二是技法上的相互借鉴,八股文和戏曲都是代人立言,这一共同特征使得它们都必须善于体会,妙于想象,以俳优之道,抉发他人之心。因此,熟谙戏曲有助于写好八股文,精通八股也有助于涉足戏曲。
与这种文体的互通性密切相联系的,是八股文的地位要明显地高于戏曲。八股文作为朝廷选拔人才的官定文体和读书人进仕的敲门砖,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广泛重视,高居于其他文体之上;而戏曲则历来被视作“小道”、“末技”,即使在戏曲极度繁荣的明清时代,它在许多人眼中仍然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而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卑下对高贵的膜拜与服从的民族文化心理及“异中求同”的民族思维方式,则使这种地位的悬殊表现为八股文对戏曲的浸染及戏曲对八股文的借鉴。
八股文的“章法理论”亦比曲论略显早熟。八股文严苛的功令程式及代圣贤立言的特征,使得八股文写作特别重视技巧,这很有利于八股文“章法理论”的建立;而明清两代众多八股名家的潜心研究和索求,亦使八股文的章法理论堂庑日大;适应士子应试的需要,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一大批书商,也以选、刻的方式,将繁芜的八股文章法进行系统化和理论化,促进了八股文“章法理论”的早熟。与八股文相比,戏曲的理论虽显得丰富多彩,亦不乏精微之见,但即使是代表着李渔以前曲论最高成就的王骥德的《曲律》,也难称体系完备。因此,比起八股文的“章法理论”,曲论略显稚弱。
上述诸种因素的客观存在,无疑为曲论家从八股文“章法理论”中获取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料,建立完备的曲论体系提供了可能。而自幼习举业和丰厚的八股文功底,则使曲论家李渔具备了这种能力和条件,从而使他能够历史地承担起建立系统、完备的曲论体系的任务。
出生于明末的李渔,自幼即在父、师的督责下学习八股文,于30岁左右曾经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面对满人的入侵和时局的动荡,他摒弃了仕进的念头,全心投入小说、戏曲的创作及组织家庭戏班的演出。当时有人指责他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技”,他就以年青时“独以五经见拔”的经历进行反击:“侯官夫子为先朝名宦,向主两浙文衡,予出赴童子试,人有专经,且间有止作书艺而不及经题者,予独以五经见拔。”并声称:“予之得播虚名,由昔徂今,为王公大人所拂拭者,人谓自嘲风啸月之曲艺始,不知实自采芹入泮之初,受知于登高一人之说项始。”[1]事实上,八股文对他的影响确实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影响已渗透到他的戏曲创作之中。他的戏曲作品非常重视结构布局的完整、严谨,前后情节的照应、埋伏,开头结尾的新奇、炫目,等等,这些都是八股文中最常见的技法、技巧。此外,他还经常将八股文的有关术语直接运用到他的作品中去,如《怜香伴》传奇的第一出就被直接命名为“破题”;《巧团圆》的第八出“默订”中姚克承的唱词也引进了“破题”二字:“我本加病从今起,究竟前番是破题”;及至第十六出“途分”中尹小楼的唱词,也有“破题”一词:“漫道受不惯凄凉滋味,只怕这凄凉还是承题破题”[2],如此等等。李渔在建构自己的戏曲理论体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眼光转向了当时已臻于无施不可之境的八股文“章法理论”。
二
将八股文“章法理论”援入戏曲理论体系之中,并不是李渔的首创。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时已经开始尝试借用八股文法剖析《西厢记》的结构艺术,只是由于他将戏曲完全纳入了八股文“章法理论”的框架并带有浓厚的八股气息,同时也未能在借用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戏曲理论体系,因此常常受到后人的批评。李渔在建构他的戏曲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虽也同样是将眼光转向八股文法,但他的借用却高明得多,既无整体枢架上的生搬硬套,亦无行文中浓重的八股气息。概而言之,李渔对八股文“章法理论”的嫁接、转换,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的。
一、由此及彼,以八股文“章法理论”作为建构曲论的逻辑起点。
李渔之前的曲论已取得丰硕成果,明人王骥德等曲论大家的成果对李渔曲论的影响是很深的。然而,此前的曲论在体系上尚不及八股文“章法理论”那么完整。李渔有感于此,立志建构新的曲论体系,八股文“章法理论”便成为他建构曲论的逻辑起点。八股文“章法理论”对李渔曲论这种既相当深刻又不着痕迹的“浸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建构曲论体系的动机得自于八股文“章法理论”的启发。在“结构第一”中,他说:“近日雅慕此道,刻欲追踪元人、配飨若士者尽多,而究竟作者寥寥,未闻绝唱。其故维何?此因词曲一道,但有前书堪读,并无成法可宗……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载之于书者,不异耳提面命,独于填词制曲之事,非但略且未详,亦且置之不通。”这一论述清楚地表明了李渔之所以进行戏曲理论的建构,是有感于曲坛上无创作成法而导致戏曲创作不振的局面,试图探寻出可供人们参考、不异耳提面命的创作法则;而这一创作动机是在别种文体所具有的创作法则的诱发下产生的,即“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由怪而思,由思而作。这种有“法脉准绳”之文字在清初虽包括诗、词、古文、时文等多种文体,但时文却独以其章法的具体、明确及现实功用明显等原因而影响最深、传播最广。因此,可以说,李渔正是在八股文“章法理论”的启发下而开始他的戏曲理论探索的。
其次,对作品结构的空前重视亦源于八股文“章法理论”。八股文自创立到衰亡,一直都讲究鲜明的功令程式,破题、承题、起讲、八比、大结等几大部分为八股文不可移易的宏观结构框架。这种严苛的功令程式表现在创作中,就使结构成为第一要义,行文之先必须对全文的结构布咎有个宏观的构思。如何破,如何承,如何敷衍成篇,如何谋篇布局,都必须了然摆回,务必做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评价一篇八股文,首先也是看其结构的优劣。如俞长城评于谦的《不待三然,多矣》:“看此文上下绾合,何尝有一毫造作”;方苞评崔铣的《夫世禄》:“以世禄起,以世禄结,中间井田学校对举,极剪裁之妙”;韩求仲评茅坤的《无曲防》:“其股法断续无端,其气脉跌宕有势,大文章也”;李光地评王锡爵的《〈诗〉云不愆不忘》:“结构可观,字详亦典切”;王弱生评胡友信的《小人之使为国家》:“逐段洗法,逐段项接,不做一字过脉,非有大力者不能”[3]等等,都是以结构作为评价的准绳。八股文对结构的高度重视,对李渔的曲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渔之前的剧论,普遍地“首重音律”。虽然也有一些人认识到结构对于戏曲创作的意义,如凌濛初在《谭曲杂劄》中就指出:“戏曲搭架,亦是要事,不妥则全传可憎矣”[4];王骥德亦以“工师之作室”为喻,阐明“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数,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后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的道理[5]。然而,直到李渔,才一改曲论“首重音律”的成例,第一次明确提出“结构第一”的美学观点:“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之百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工师之建宅亦然……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从而开拓了一个审美创造与欣赏的新天地。
第三,戏曲结构理论的提出亦立足于对八股文结构理论的化用与嫁接。李渔所标举的“结构第一”,并不仅指狭义的艺术结构,而是指包括结构在内的整个的艺术构思,其中只有“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三款是专论戏曲结构的。这三条为人所称道的戏曲结构原则与“格局第六”中的格局理论共同构成了李渔的戏曲结构理论。而这些理论创造多是在化用八股文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完成的。虽然这种化用十分巧妙,一似羚羊挂角,但只要我们细心检索,仍可从中寻得踪迹。
李渔提出的“立主脑”一词,是从王骥德的《曲律》和沈德符的《顾曲杂言》中使用过的“大头脑”一词转化而来,而“大头脑”的用法又早见于倪士毅的《作义要诀》:“或题目散,头绪多,我须与他提一个大头脑。”这种提起“大头脑”的章法就是八股文写作的基本要求。李渔的“立主脑”原则显然受到了这一章法理论的影响:“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只是他将“主脑”一词借用到传奇中之后,又重新界定了它的含义,即是指构成传奇的“一人一事”。与“立主脑”的原则密切相关,李渔又创立了传奇创作“减头绪”的原则,强调传奇要“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如孤桐劲竹,直上无枝”。我们且不论李渔这一理论概括是否符合艺术创作的丰富性规律,单就它与八股文章法的关系而言,则明显地是从后者借用而来。八股文非常讲究“逐段相衔,一线赶下,通篇还它一句口气”[6],后来刘熙载则将它总结为:“主脑既得,则制动以静,治烦以简,一线到底,百变而不离其宗。”[7]李渔所强调的“一线到底”正是八股文的基本要求。同时,他提出的“密针线”结构原则也是从八股文章法中借鉴而来。八股文对针线细密的讲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从明清之际的八股文评点中可窥一端,如胡思泉评唐顺之的《克伐怨欲不行焉》:“又妙在后二句,连带讲下,细密精透,圆活转折,自不可及”;前人评方应祥的《〈诗〉云节彼南山》,亦称“前节追后节,后节拘前节,局法甚紧,古气郁盘。”[8]事实上,针线细密之法,在元倪士毅的《作义要诀》之中就有了明确的规定:“有开必有合,有唤必有应,首尾当照应,抑扬当相发,血脉宜串,精神宜壮。如人一身自首至足,缺一不可。则是一篇之中,逐段、逐节、逐句、逐字,皆不可以不密也。”“要是下笔之时,说得首尾照映,串得针线细密……一篇之中,凡有改段接头处,当教他转得全不费力”;这也就是启功先生在《说八股》中所概括的“挽”、“渡”之法。李渔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密针线”原则:“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细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务使承上接下,血脉相连,即于事情截然绝不相关之处,亦有连环细笋,伏于其中。”
在结构原则之外,李渔在戏曲格局理论上也在许多地方不着痕迹地借用了八股文的“章法理论”,像“格局传奇……开场用末冲场,用生开场,数语包括通篇。冲场一出,蕴酿全部,此一定不可移者。开手宜静不宜喧,终场忌冷不忌热”,“上半部之末出,暂摄情形,略收锣鼓,名为‘小收煞’。宜紧,忌宽;宜热,忌冷。宜作郑五歇后,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这些都是八股文的作法技巧,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八股文的章法、技巧,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二、取类引譬,直接援引八股文“章法理论”,丰富曲论的理论内涵。
李渔的戏曲理论中不仅有与八股文章法暗中相通、彼此契合的论述,而且他还常常直接将戏曲与八股文相比,运用人们习知的八股文“章法理论”作为自己论曲的理论资料,建立起自己的戏曲理论体系。这种以此喻彼式的建构在李渔的曲论中比比皆是。在“家门”一款中,他以“时文之破题”为喻来论述词曲的开场:“予谓词曲中开场一折,即古文之冒头、时文之破题,务使开门见山,不当借帽覆顶。即将本传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与后所说‘家门’一词,相为表里。前是暗说,后是明说。暗说似破题,明说似承题。如此立格,始为有根有据之文。场中阅卷,看至第二、三行而始觉其好者,即是可取可弃之文。开卷之初,能将试官眼睛一把努住,不放转移,始为必售之技。”通过比喻,用“时文”开篇的重要性论述了“家门”对于传奇的重要性,若开光之于佛面,点睛之于画龙,直接关系着全剧的成败。因此,剧作者于此,务必要使出浑身解数,以使戏曲开篇即能牢牢吸引住观众或读者。对“家门”前的小词,李渔亦是通过用八股文作比喻来论述的:“然‘家门’之前,另有一词。……大凡说话、作文,同是一理:入手之初,不宜太远,亦正不宜太近。文章所忌者,开口骂题。便说几句闲文,才归正传,亦未尝不可。”以八股文的忌开篇“骂题”为喻来说明戏曲不能于开篇即就家门说起,而应于“家门”之前有一闲文性的“小词”,从而为戏曲创作的开头之法提供了规范。
李渔有关戏曲收煞的理论亦是以八股文为喻而建立的:“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入彀之法。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留连,若难遽别,此一法也。收场一出,即勾魂、摄魄之具,使人看过数日而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亏此出撒娇,作临去秋波那一转也。”众所周知,八股文适应考试的需要,务求于结尾处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以求见赏于试官。戏曲亦是如此,不仅要做到收结自然、水到渠成而无任何勉强之态,即无“包括之痕”,而且要于“水穷山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这样,才能给观众或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
在对情、景关系的论述上,李渔同样采用以时文喻剧曲的方法。他用举子作文来比喻剧作家对景物的描写:“发科发甲之人,窗下作文,每日止能一篇、两篇,场中遂至七篇。窗下之一篇两篇,未必尽好,而场中之七篇,反能尽发所长而夺千人之帜者,以其念不旁分,舍本题之外,并无别题可做,只得走此一条路也。”李渔进而指出,对景物的描写也是这样,景有千景万景,不知从何说起,“咏花既愁遗鸟,赋月又想兼风。若使逐件铺张,则虑事多曲少;欲以数言包括,又防事短情长”,如此犹豫踌躇之际,精力、时间俱费,笔下却依然无物。但是如果能够围绕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性格的刻画来描写,则不仅取舍容易,而且因念不旁分,景有所依,反能写出精妙之文,绘出绝佳之景。正是在这一番比喻的基础上,李渔得出了“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的结论,并提出了“戒浮泛”的作曲原则。
三
八股文章法理论对李渔曲论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是,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类同关系。一方面,八股文作为明清时代许多士子自幼所习用的文体,对文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以致他们登堂入室之后,在从事诗、词、古文、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创作或理论的建构时,都难以摆脱它的影响,“工于八比者,以其法推求古书……唯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终也欲摆脱八比气息,率不易得耳。”[9]李渔也是如此。但是,李渔曲论体系的建构并非只是单纯借用八股文“章法理论”的结果。
李渔的《曲话》是中国古代曲论史上的集大成之作,他的曲论体系的建立,既有对丰厚文化遗产的广泛继承,更得力于丰富的创作和舞台实践经验。
前面说过,李渔以前的戏曲理论虽然多是散金碎玉、不成体系,但是元明两代曲论家的探索已涉及到了戏曲美学的许多方面,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这些丰厚的曲论成果为李渔建构系统、完备的曲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李渔对传统的“古诗文辞”也相当内行,他的诗文直抒性灵,不同凡响;在小说领域,他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因此,对这些领域的理论成果他也相当熟悉,他在戏曲批评中自觉地对古典诗、文、词乃至小说理论进行广泛的吸纳。
丰富的创作和舞台演出的实践是他的曲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这种实践既包括他之前的曲学先辈的创作实践,更是指他自身所进行的大量的剧本创作和舞台演出。正是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李渔在前人尚未涉及的领域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对“戏”的观念的空前强调,对导演理论的详细阐述等等方面,都使他的霞曲理论呈现出与前人迥柔瞎异的特色。
总之,对八股文“章法理论”的借用虽对李渔曲论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李渔曲论体系的全部。可以说,如果没有明清之际臻于高度成熟的八股文章法理论,李渔的戏曲理论也许不可能具备那样一个自成体系、思维缜密的理论框架并呈现出一种空前的理论自觉;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将传奇与八股文作简单的类比,则李渔的曲论就根本没有产生的可能[10]。
同时存在于封建社会后期的两种文体——八股文和戏曲——之间理论批评的不平衡,必然会造成理论体系相对晚成的戏曲批评对八股文“章法理论”的借鉴,李渔的戏曲理论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历史特色。他曲论中创作论部分的完成,固然是对前人理论成果的继承,是曲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但八股文“章法理论”在其中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注释:
[1] 李渔:《〈春及堂诗〉跋》,《李渔全集》第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34页。
[2] 《笠翁传奇十种曲》,《李渔全集》第4卷、第5卷。
[3] 《八股文观止》,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69、304、429、493、507页。
[4] 凌濛初:《谭曲杂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4),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版,第258页。
[5]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4),第123页。
[6] 吕留良评《钱吉士稿》
[7] 刘熙载:《艺概·经义概》
[8] 《八股文观止》,第384、652页。
[9] 包世臣:《艺舟双楫·或问》
[10] 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引自李渔《闲情偶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7)。
标签:李渔论文; 八股文论文;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