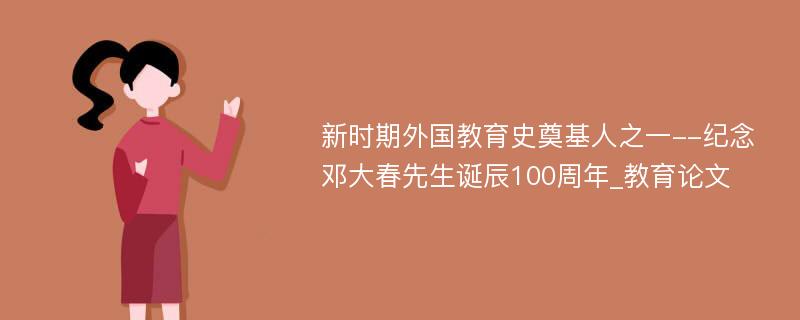
新时期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纪念滕大春先生诞辰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史论文,奠基人论文,诞辰论文,新时期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09)05-0001-04
滕大春先生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著名的教育学家,他对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新时期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滕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从此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他当过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师,曾任教育厅职员,国立编译馆编审,1947年赴美留学,主修比较教育及教育史,1950年获科罗拉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河北大学(其前身为河北师范学院),长期致力于外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我国教育学科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滕先生常常庆幸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其主要著述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从古稀之年到年近九旬,是他一生最多产的时期,这恐怕也是学界罕见的。
滕先生的学术工作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意义,其代表作已成为教育科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一些主要观点被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
滕先生在教育学术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
作为教育学分支的教育史在中国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学界通常把教育史分为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部分,滕先生主要致力于外国教育史的研究。1949年前,外国教育史习惯上被称为“西洋教育史”,这是因为当时我国教育模仿的主要是欧美等西方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上全盘苏化,“西洋教育史”改为“世界教育史”或“外国教育史”。但严格说来,60年代以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并未形成。196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批准组成《外国教育史》编写组,滕先生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其中,完成了编写提纲,但由于“十年动乱”,撰写工作中断。“十年动乱”结束后,滕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之中,先后主编了《外国古代教育史》(1981年)、《外国近代教育史》(1989年)、《外国教育通史》(六卷本,1989—1994年出版)等教材,牵头编纂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外国教育”分支(1985年)和《教育大辞典·外国教育史》(1991年)等权威工具书,撰写了《试论“外国教育史”的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试论外国教育史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展望》等一系列论文。滕先生身体力行,对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滕先生认为“外国教育史并不是西洋教育史,也不是欧美教育史,乃是世界范围的教育发展史”[1]2。他根据国外学者的考古发掘和大量史料,认为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不但堪与古代西方国家相媲美,而且是早于西方而发达的。因此,“东方古国的教育史应和西方古国的教育史同样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由它们共同组成教育史的框架”[1]2。他还对佛教教育和伊斯兰教育进行了深入探索,认为“东方盛行的佛教、伊斯兰教和西方盛行的基督教是三教并列的,由于在历史上教育和宗教一向是紧密联系的,三教对于教育都是立过功的,而且三教的教育都是影响广远的”[1]2。从而破除以往仅以基督教教育为主体的狭隘性和片面性,纠正了多年以来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所造成的误解,扩大了外国教育史的学科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滕先生认为“众多声名不太显赫的国家和教育也常有其强点和特点”[1]2,同样值得研究,这就进一步拓宽了外国教育史的传统边界和领域。
第二,滕先生认为:传统教育史竭力阐述教育在阶级斗争方面的作用,以至于变成了在教育范围的阶级斗争史,这是极为片面的。他提倡“教育史的领域还该在叙述人类教育在阶级斗争所扮的角色的同时,叙述它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史上所扮的角色”。“尤其是对于教育在生产斗争和文化斗争方面的往事,不加分辨地避而不谈,就必然忽视教育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就必然起不到‘鉴古知今’的作用,也就必然无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发挥‘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效能”[1]2-3。
第三,滕先生认为国外教育史学者根据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教育现象,即“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是非常符合史实的,他主张以“文化多元论”取代“文化一元论”。我们绝不应孤立地看待各时代和各国的教育,而应着眼于人类教育的整体性,“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借以使人领悟人类教育史的整体性,是颇有助于清除闭关主义的缺憾的,是更能使人理解开放政策的英明的”[1]4。
第四,在如何看待教育史的作用上,滕先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一方面不赞成把过去和未来当作截然对立物、抹杀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坚信人们可以从众多教育往事中揭示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也不赞成用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理解教育史的效用,“教育史不是技术性或实用性科学,要求教育史这种基本理论学科给处理某些具体教育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是要求过当的”[2]534。然而,“教育史却能培养人们较为远大的教育眼光和对于教育课题的领悟能力,而这种眼光和能力每每能产生人们意识不到的威力。所以教育史对实际工作的效能常常是迂回的,而不是直线进行的,是须经过较长时期才能显明其伟效的”[1]4-5。
滕先生在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上的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迄今仍是一部外国教育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二、美国教育史研究
美国是当代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在近代大部分时间,美国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深远。1847年,容闳等三人赴美学习,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1872年,经容闳倡导,清政府向美国派出了30名幼童,成为中国首批官派留学生。1922年,民国政府“新学制”(壬戌学制)采用美国六三三学制,几乎沿用至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直是1949年以前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思想。身处这样的时代,又加之四年的留美生涯,自然使滕先生把美国教育作为研究的重点。然而,在50、60年代,外国教育史“以俄为师”,敌对的美国只能作为批判的对象,深谙美国教育的滕先生无法施展才能。“十年动乱”后期,当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之时,滕先生的目光重新聚焦美国。他从兄弟院校借来珍贵的外文资料,潜心研究,终于撰成《今日美国教育》,并于198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内对美国教育非常陌生的情况下,《今日美国教育》产生的震撼和影响可想而知。用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的话说,“当时我们就是通过这部书对美国教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3]5。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当时还是学生的王英杰教授曾带着这本书远渡重洋,他曾说:“今天,这本书已经陪我度过了25个春秋,书页已经泛黄,但是仍在我的案头,我仍时时翻阅,从中寻找研究的课题、文章的灵感、解释的工具和理论的依据,我仍然把它定为我所教的美国教育课的必读书。今天已经有大量的有关美国教育的著作出版,但是我仍然认为滕先生的这本书是经典,是所有研究美国教育的学者的必读之作,是研究美国当代教育的起始点”[3]29。
完成《今日美国教育》之后,滕先生即着手撰写《美国教育史》,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参阅国外权威版本,吸取精华,经十数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完成了53万字的《美国教育史》,于1994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出自中国学者手笔的第一部美国教育通史。这一年,滕先生已逾85岁高龄。关于研究美国教育史的意义,诚如滕先生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美国教育以三百余年走过了欧洲国家千百年走过的道路,并非得之偶然。它之跃进腾飞是因为它所采取的道路是基本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正因如此,它不啻给众多国家继续发展教育提出了可供参考的范例。就是说,研究美国教育史和研究其他国家教育史比较,应更能起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作用”[4]2。
顾明远先生曾评论说,《美国教育史》“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美国教育与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它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轨迹,对美国教育作了详尽的剖析和评价,是我国最有权威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著作”[3]5。
三、对卢梭、杜威等教育家的研究
卢梭和杜威是滕先生情有独钟的两位西方教育家。对两位教育家的偏爱,体现了他对更新传统教育观念的迫切期望。
滕先生认为: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人们在教育思想理论部分简单地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为分水岭,肯定后者的教育贡献而否定前者的功绩,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仅凭唯心或唯物二词来判断一切和评价一切。一些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如柏拉图、夸美纽斯、卢梭、杜威等等,都是唯心论者,因此,对于这些教育巨人常常未能进行科学分析。这些偏激的态度是必须纠正和避免的。科学阐述和评价是必须提倡的”[1]3。有意思的是,滕先生曾着力研究的卢梭、杜威等人,均属唯心主义阵营。
早在1947年,滕先生就撰成《卢梭教育思想》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他曾说,之所以对卢梭产生兴趣是因为杜威的启发,因为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称道在世界各国近代教育的始创时期,卢梭是关键性人物,贡献巨大[3]425。1984年,《卢梭教育思想述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从结构上看,两书没有显著差别,但在内容上,前后两书区别明显,体现了作者研究方法及指导思想的根本改变。撰写前书时,滕先生还是一名西化的旧知识分子,撰写后书时,已成为一名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研究教育史的成熟学者。
《卢梭教育思想述评》成为国内研究卢梭教育思想的经典著作。作者对卢梭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对卢梭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天性论的阐述,对卢梭教育目的论即培养自然人的理想的描绘,以及对卢梭有关感觉教育、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女子教育等思想的阐发,均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尤其是最后一章对卢梭教育思想的评价,入木三分,客观可信,反映了作者对卢梭的深刻理解。全书语言严谨,文风洒脱,文笔优美,视野宽阔,一气呵成。原本是一部理论性很强的著作,但读起来毫无枯燥之感,把卢梭写活了。
杜威是对滕先生影响最大的西方教育家。早在北大求学期间,滕先生即刻苦钻研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十分仰慕杜威在中国的弟子胡适等名师。大学毕业后,滕先生任教于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并兼任附小主任,他自觉把杜威“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改造”和“从做中学”的理论落之于实际。留学美国期间,通过大量阅读和广泛接触美国社会,滕先生对杜威教育理论的理解更趋成熟完善。
上世纪50年代初,杜威在中国成为学界批判的靶子,其“余毒”亟待肃清。迫于无奈,滕先生写了几篇应景的批判文章,当时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以至于当形势稍许好转,他便急切地希望改弦更张。80年代后,他撰写了《杜威论道德教育》、《杜威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批判》、《杜威和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文章,又在《外国近代教育史》、《美国教育史》等著作中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而客观公允的评价,认为杜威“反映美国社会政治的急剧转变,在哲学上否定永恒不易的真理;在政治上号召自由民主和开拓精神;在教育上批判传统学校既抑制天性又远离社会现实,提出全新的教育理想和理论,从而促成美国教育的深入变革”[4]53。杜威教育思想中含有的正确因素是无法抹杀的。“杜威为人类教育发展史的巨人,在人类教育的革故鼎新中树立了丰碑”[4]530。
四、对比较教育的研究
负笈美国期间,滕先生主攻比较教育,博士论文题目为《中美英法四国师范教育的比较研究》。他说:“美国大学把教育哲学、教育史和比较教育三者组成了一个学域(Division),我从自身经验觉得是很合适的安排。因为三者脉络互通,不易割裂;否则知古而不知今或知今而不知古,或则仅知当前而既不知古、又不知外,或仅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仅见其表而不知其里,都会陷于一隅,或流为浮薄,不能得窥全豹和真豹”[3]426。这段话反映了西方学术传统对滕先生的影响,也是严谨的学者所秉持的治学原则和方法。
滕先生在著述中自觉体现了古与今和中与外的结合。《今日美国教育》是一部介绍当代美国教育现状的书,但全书几乎天衣无缝地把历史和现状有机融合在一起;《美国教育史》是一本教育史的著作,但全书始终贯穿“古为今用”的写作意图。正如作者所说:“美国教育的现状是经过历史演进而成。欲深入一步通晓美国教育的今日,必须通晓美国教育的昨日”[4]1。“在教育上,它的一切原则、理论和做法遂都前后呼应,不知其当初就不懂其现在”[4]2。“仅就各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和现行的学校实际进行比较,不从其历史演变和哲学基础,深入分析论证,就容易只知其现状和外形而不知其底蕴和本质,就容易流为只是教育事实的粗浅描述和介绍而缺乏应有的申论和评价”[2]579-580。
滕先生的比较教育思想,体现了一位史学者的博大精深和睿智。
滕先生多次强调,“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文教交流古已有之,今后更甚,企图闭关自守而不行开放政策,在教育建设上抱残守缺而与别国老死不相往来,就是闭目塞听,闭耳塞闻,是违反科学的,是逆乎历史规律的”[2]572。这就需要加强比较教育的研究。他进一步指出:“进行比较教育研究不是为研究比较而研究比较,是为了掌握教育规律和发展教育事业。具体说,就是‘洋为中用’”[2]573。他还对怎样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要对外国教育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探讨;要结合国情,取法外国先进经验,既不能闭关自守,也不能东施效颦,盲目取法。
滕先生认为“建立和发展高水平的比较教育学,一方面要奠立史的基础,一方面更要抓紧现代和面向未来”[2]580。他号召比较教育研究者不要仅靠信息和书本,而要深入现场,实地考察,他相信“通过较深和较久地现场实践,能使人对问题辨析全面而透彻,必然会由感性认识而提高为理性认识,由平泛的常识臆断而提高为科学论述”[2]581。滕先生对我国比较教育给予了极高的希望。他深情地说:“党在当前的‘开放改革’,特别是‘扩大开放’和‘科教兴国’等几大方针,将使比较教育研究进入黄金时代”,我们要“借助比较教育的武器,快快地跑在前边去,成为世界上位居前列的教育先进国家”[2]582。作为一名爱国的知识分子,滕先生希望祖国迅速强盛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
滕先生是20世纪后半叶对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教育名家,他一生致力于教育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成果丰硕,桃李满天下,年近九旬还有“出师未捷”之憾。滕先生一生最崇敬的教育家是杜威,他认为“在教育史中既能提出新颖教育哲学,又能亲见其实施之获得成功者,杜威是第一人”[2]485。巧合的是,杜威活了93岁(1859—1952),滕先生也活了93岁(1909—2002)。杜威是10月生人,滕先生也是10月生人。两人至少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大家共同的风范。
收稿日期:2009-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