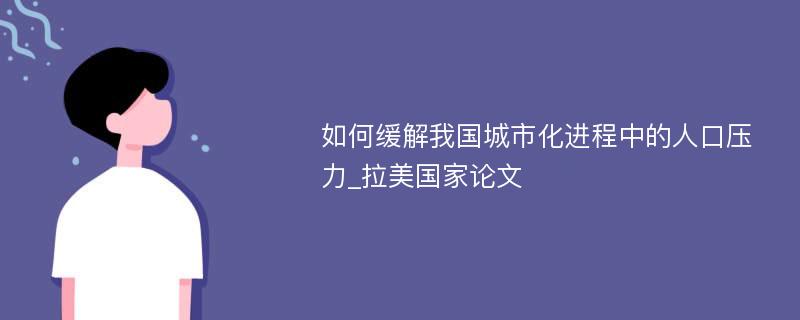
如何缓解我国城市化中的人口压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压力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效的人口控制与北京城市的发展
国务院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北京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北京城市的发展建设,要按照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指出:“由于环境、资源的制约,北京市应着力于提高人口素质,防止人口规模盲目扩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第10条:“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
截至2004年底,北京实际居住人口1492.7万,其中户籍人口为1162.9万。仅在公安局办理暂住证登记手续的外来人口就达360万人。2003年北京人口密度为668人/平方公里,是亚洲人口密度117人/平方公里的6倍,是世界平均水平45人/平方公里的15倍。2005年在全国100个城市中北京的居住质量排第83位,综合环境资源成本排第11位。
1990-2003年北京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2%,而北京市发改委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北京市全市户籍人口已超过1170万。2005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口规模继续增长,6月底,全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170.6万,同比增长2%,高于1.5%的全年计划调控目标。如果保持目前人口年均增长率,北京2020年总人口将突破2100万。实行有效的人口控制,已经关系到北京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这座千年古都最终的命运。
人口流动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调节
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制度,确实有它的有效性。但是不是人类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用市场来解决?市场对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是否都具有有效性?按照亚当·斯密的论述,市场无非是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客观上就形成了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大家都连在了一起。后来,“人们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由看不见的手自行控制”的思想竟成为一种涵盖西方社会的教条。实际上,西方社会的现实并非如此。任何社会都有他的道德、情操和文化,西方社会也不例外。人的价值实现中包含着利他,人类活动中必然也就包含了利他活动,利他是人类的一种社会需求。市场不能做这种利他主义的满足。还有些经济活动,它所侵犯的客体并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没有人格代表的公共环境、公共利益。比如公害、污染、过多地侵蚀地壳,过度地开发资源,致使地面沉降、气候变暖等等,这些问题不能靠市场、靠“看不见的手”来解决。市场的原则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由此而产生的贫困和失业问题,更不能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目前发生在法国的40年来最严重的骚乱证明了单纯依靠市场是无法解决贫困和失业问题的,而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和不稳定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此,在纯粹的市场状态下,很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市场不能覆盖所有人类活动,市场不是万能的。
“计划生育”是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成功范例。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口将超过16亿,超过了现有社会经济、科技水平条件下可能承受的人口规模。尽管这方面看来是侵犯人权,对中国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现在我们要实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同样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世界上运用政府行政力量解决人口流动问题的国家不乏其例。最典型的是英国和日本。英国政府正是通过强制性的“圈地运动”完成了农村人口的非农化。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成功地完成了农村非农化的转变。相反,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农村人口大规模无序地涌向城市时,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遏制和引导移民潮。
借用唐钧先生的话:从实践中看,迄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完全由“看不见的手”来运作的纯粹市场经济的成功例子,而二战后在西方普遍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倒是证明了“看得见的手”的不可或缺性。这样讲,并没有排除市场的重要性。对于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尤其需要,必须尽快形成、尽快完善。但同时必须看到市场也有它的局限性,市场不是万能的。中国需要的是现实中能够产生的市场,而不需要教条的、情绪化的市场。否则就会与国情不符,与实践有害。
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与加快城市化进程
有观点认为主张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违反了城市化的潮流,因为它限制了农民进城。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的实质是创造、普及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它不仅包括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还包括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城市化并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也不仅仅是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这只是城市化的一个表象。
因此,城市化的实现要求城市的非农产业必须具备足够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要求城市必须具备促使进城务工农民实现其生活方式转变的基本条件,即除了城市资源、环境、城市基础设施之外,还有住房、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保障等等。农民自身也必须具备完成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农化转变的基本素质。因此,城市化的进程必须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同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农业人口城市化的规模应该与城市第二、三产业提供的就业量大体平衡,与城市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体相符。
在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如果城市不具备相应吸纳能力的非农产业,不具备保证进城务工农民实现生活方式转变的基本条件,换句话说,人口的过度增长超过了城市的接纳能力,那就是过度城市化了。这种城市化不是建立在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是一种畸形的城市化。城市化的质量很低。城市无力为过度增长的居民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其结果是进了城的农民并没有实现非农化,城市却因严重超载以及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城市危机和城市病而无法发展,甚至社会倒退、经济被拖垮。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拉美国家的城市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拉美国家农村人口向大城市大规模迁移。拉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据统计,欧洲的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增长到60%经历了50年的时间,而拉美国家仅用了25年的时间。1995年,拉美地区城市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如委内瑞拉为92.8%,乌拉圭90.7%,阿根廷88.1%,智利83.9%,巴西78.2%,墨西哥75.3%,其城市人口比重几乎都超过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低得多。
过度城市化不仅没有推动拉美经济持续发展,反而使拉美各国都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病之中。城市人口严重超载、失业率居高不下(2002年阿根廷高达25%),城市贫富差距拉大,几乎所有拉美的大城市都为贫民窟所包围,墨西哥城有近一半的人居住在贫民窟。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社会失序、政局动荡,资源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拉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如今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拉美城市化始终是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这种过度集聚化的城市发展,使得人口、私人投资向大城市集聚,而为了应对大城市人口无节制的增长,政府只能加大对大城市的投资,于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又引发新一轮的人口迁移。这种恶性循环是加剧拉美过度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拉美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长期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而政府的态度先是放任自流,后是束手无策,这是导致其城市化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和拉美国家一样同属发展中国家,但拉美总面积比我国大一倍多,人口不及我国一半,自然资源却比我国丰富多了,仅有世界8%的人口,却拥有世界27%的淡水,40%的森林生物量。相比起来,我们连犯错误的资本都没有。中国城市化任务之重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中国城市化的人口规模堪称世界第一,超过了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拉美总人口5.4亿,而我国现有农民就是8亿。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决不能走大城市扩张之路,因为靠几个甚至几十个大中城市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城市化人口压力。我们不能重蹈拉美过度城市化的覆辙。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城市化任务,需要大中小各类城市共同分流。因此,最近中央领导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确实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历年北京总人口和人口密度的变化
(单位:万人,人/平方公里)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03年
总人口923.1
1081.9
1356.9
1456
人口密度
547 642 808 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