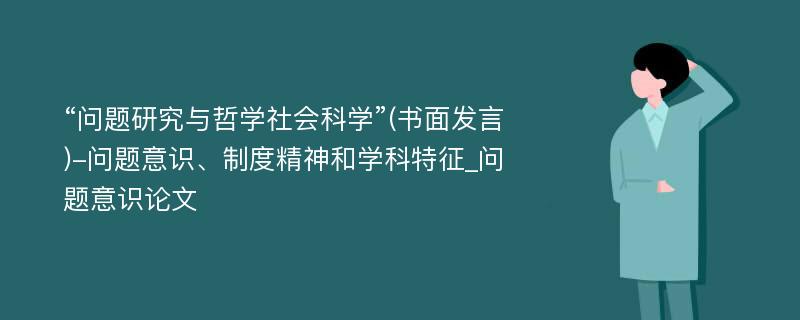
“问题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笔谈)——问题意识、体系精神与学科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学科论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特性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话题与论题:问题的两个层次
体系都是学科的体系,学科也都是面向问题的学科。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对问题的研究 ,没有问题,也就没有学术研究。那么是否可以反过来说,任何问题也都是学术研究的 问题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一否定同时意味着,在我们看来,学术研究所探讨的 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部分,而非全部。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学术研 究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问题,而其他问题却不能成为学术研 究的问题呢?换言之,决定是否成为学术研究所探讨问题的标准是什么?
在提出这些问题之时,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问题可以分为不同性质的 两类,其中一类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另一类则是非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这两类问题的 差别,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有所认识。例如柏拉图就认为,“什么东西是 美的”和“什么是美”是两类不同的问题。关于前者,可以用一个个具体的美的东西来 回答,而后者则不能用任何具体的东西来回答,而只能着眼于使美的东西成其为美的那 个美本身,亦即美的共同本性。这个美本身,美的共同本性无疑不再是感性具体的存在 ,而只能是一个思想性、观念性的存在——概念。在这里,柏拉图初步区分了两类问题 :第一类是纯粹感觉经验意义上的问题,对其可以用感性具体的存在来回答;第二类问 题则超越了感觉经验的层面,进入了思想的领域,因此对它只能借助于思想性、观念性 的存在——概念来完成。由于前一类问题完全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人人都可以 在常识的意义上加以谈论,因此我们将其称为话题;而后一类问题建立在抽象概念的基 础之上,只有运用概念范畴的方式才能予以专门的研究论证,因此我们将其称为论题。 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后一类问题——论题,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柏拉图哲学在最深层 意义上影响甚至决定了整个哲学的发展方向,“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 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注:《海德格尔选集 》(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44页。)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又源于哲学,于是 ,话题与论题的划分也“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
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化,话题与论题也“有所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话题逐渐挣脱 感觉经验的“完全”束缚,在某些“侧面”进入了抽象概念的层面。即人们在日常的谈 论中,也越来越多地借助于概念范畴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于是乎话题与论题的界 限似乎日趋模糊。你的论题使用概念,我的话题也使用概念;你在学术研究中研究正义 ,我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谈论正义;……这是否意味着话题与论题的日趋融合呢?绝非 如此。事实上,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日益专门化,话题与论题的距离不是更近了 ,而是更远了。所谓更远了,就是说学术研究与常识意义上的谈论逐渐分离为完全不同 的“两件事”。如果说在柏拉图那里,学术研究与日常谈论还都采取了相似的形式—— 对话的话,那么到了现代,随着学术规范的日益完善,学术研究已经完全从日常生活中 独立了出来,成为了一项特殊的工作。随着这一“独立”的完成,话题与论题的差距进 一步拉大了。
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曾以对芝诺“飞矢不动”命题的分析为例,深刻阐释了话题 与论题之间的根本差别。借用黑格尔的论述,列宁认为,“芝诺从没有想到要否认作为 ‘感觉确实性’的运动”,而“问题仅仅在于运动的真实性”,也就是如何以“概念” 的方式来说明“运动”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来 表达它。”(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6、167页。)可见, 在列宁看来,有没有“感觉确实性”的运动,乃是一个常识意义上的话题,并非理论研 究的问题,理论研究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它”。这就揭示了话题 与论题之间的根本差异,即是否“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而“概念的逻辑”,亦即概 念的辩证关系,“概念的相互依赖”,“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一个概 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过渡”,“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过渡”。(注:列宁:《哲学笔记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6、167页。)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概念的框架或网络。 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框架或网络之中,概念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离开特定的框 架、网络,概念就不再作为概念,而仅仅作为一个“名称”而存在。所以,严格意义上 讲,话题中的概念,由于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概念框架或网络,因此,它不再是一个概 念,而仅是一个“名称”而已。
至此,我们就可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即只有建立在“概念的逻辑”基础之上 的论题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判断一个问题是否为论题的标准就在于其是否建立在“概 念的逻辑”基础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话题与论题的差异,并非实体性的,而是关系 性的。也就是说,一个问题属于话题还是论题,并非天生注定并永世不变的,而是随着 其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自由问题,当人们在常识意义上进行谈论时,它就 是一个话题,而一旦人们将其纳入特定的概念框架之中,比如探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 由问题时,它就变成了一个论题。可见,同一个问题,既可以是话题,也可以是论题, 决定是话题还是论题的关键,在于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它。
二、体系自身与体系精神:体系的两种形式
在学术研究中,与问题研究相对应的是体系建构。在普通意义上,人们往往以为二者 是对立的,即进行问题研究就意味着反对体系建构。进入20世纪以来,学界出现了一股 反体系的浪潮。M·怀特在其《分析的时代》一书开头第一句就说:“几乎20世纪的每 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 始的,……我心里指的是黑格尔”。(注:怀特:《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 》,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页。)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一向以其恢宏 而庞大的体系而著称,“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 (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9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黑格尔的批判也就是对建构体系哲学的批判 。
这一批判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致它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学界对体系的看法。 “我甚至认为,‘体系崇拜’已经成了理论界最大的障碍。因为到头来这些体系不过是 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一版不如一版的翻版。”(注:范景中等:《理想与偶像》,译者 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页。)这段颇具代表性的文字鲜明展现了我国学界 反体系的呼声和倾向,在这一倾向的作用下,任何建构体系的企图都被视为一种“不自 量力”的狂妄和无知。事实上,彻底否定体系既无必要,更无可能。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借助于“概念的逻辑”来进行的。而“概念的逻辑”又必然暗含着 一个特定的概念框架或网络,这样的框架或网络本身就是一个体系。只不过这样的体系 往往是以“潜在”的形式出现并发挥作用的,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最终意义 上引导并决定着学术研究的系统化和整体性的基本走向。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 “内在”的“精神诉求”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所以我们将其称为体系精神。与体 系精神相对应的乃是由“外在”的具体的概念、范畴组成的体系自身。体系精神与体系 自身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完整的体系。
如果说体系精神乃是体系的内在形式的话,那么体系自身就是体系的外在形式;如果 说体系精神作用于一切研究过程之中的话,那么体系自身则仅作为一部分研究成果的构 成形式而存在。这也就是说,体系自身乃是一种特殊性的存在,而体系精神则是一种普 遍性的存在。因此,从理论上讲,否定体系的最大限度仅在于否定体系自身,而绝无可 能否定体系精神。否则,这一否定只能是零乱的闲谈,而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从事实上看,即使在那些试图彻底否定体系的研究之中也同样贯穿着体系精神,甚至在 那些宣扬思想的碎片化和片断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所隐含的趋 于整体性和系统化的“建设”维度。因此,任何彻底否定体系的努力都像试图抓着自己 的头发腾空一样荒谬和自相矛盾。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当“德国知识界”“平庸的 模仿者们”把黑格尔看作一条“死狗”而予以抛弃的时候,马克思却“公开承认我是这 位大思想家的学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 2页。)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都有一个长 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 社,1976年,第196页。)至此,我们就可以知道,问题研究与体系建构并非水火不容的 两极,而是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
三、以合乎学科特性的方式进行问题综合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问题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日趋呈现出一种复杂化 、综合化的趋势。与这一趋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科内部的分化却越来越细,这意味 着单凭任何一个学科的资源已经无法解决这些综合性的问题。(注:参见孙麾《从学科 综合转向问题综合》,载《光明日报》2004年1月8日C1版。)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应 当也必须实现一个研究模式的转换,建立一种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跨学科、自觉沟通和 配置哲学社会科学各学术资源的综合研究模式。应当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需要经过 我们长期实践摸索的问题。在此,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基本的方向或原则,即必须以合乎 学科特性的方式来进行问题综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 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 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2卷,第104页。)马克思在此提出了人类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问题,并且认为每 一种方式都以其“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具有普遍的指导意 义。具体到学术研究来说,就是每一学科都应当也必须运用其“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 ”,亦即以合乎学科特性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这一观念对于我们所要建立的以问题为 中心的综合研究模式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这一研究模式必然要涉及到多个学科,这就意味着在研究过程之中很容易出现那 种不顾学科特性,盲目综合的现象。在此方面,我们已经有过太多的教训。比如在上世 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一些学者在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旗帜下,不顾美学自身的学科特性 ,盲目引进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一味热衷于系统层次的繁琐划分 和信息流程的简单比附,从而把美学理论变成了数学符号、公式、图表和数学推导过程 的堆积。在文艺学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同样打着跨学科综合研究的 旗帜,热衷于借助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手段分析大脑的机制,力图揭开形象思维的秘密 ,结果却把这一艺术创作中的重要问题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问题。这些事例对于我 们所欲建立的问题综合研究来说,无疑是前车之鉴。
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在论述围棋时曾做过一个比喻,他说布局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跑车 ,布局好了就像跑车的方向对了。只要方向对了,无论快一些还是慢一些,总会到达目 的地。但是如果方向错了,开得越快,离目的地就越远。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研 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