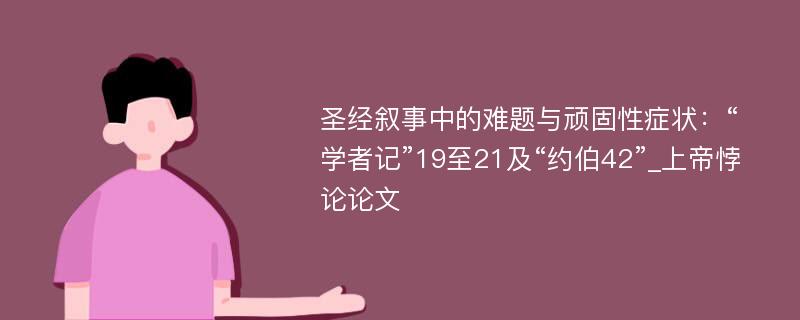
圣经叙事中的难题与顽症:“士师记”19至21章及“约伯记”42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顽症论文,圣经论文,难题论文,士师记论文,约伯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0)02-0013-07
30年前,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这样定义叙事“难题”(difficulty):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协定受到文本中各种障碍的破坏。一般而言,“难题”是作者希望读者能够解决的问题。只有当我们找到那把打开文本之锁的钥匙后,文本才让我们对其做出阐释。在发现恰当的符码之前,我们无法解释那些明显不能自圆其说的文本现象。然而找到钥匙之后,那些阻止读者理解的文本因素就会各就其位,融成一种统一的阐释,同时通过阐释循环证实这种阐释的有效性。
当然,也存在这样一些文本,它们不仅仅是难题,而且无论如何都无解——或者说作者本来就不希望读者解决这样的难题。斯坦纳提出了“本体论难题”这个范畴,这类难题使我们面临关于语言、意义以及文学交流之本质的“空白问题”,从而打破作者—读者之间的协定。在我自己的修辞叙事学框架内,这些难题大体上对应于我所谓的“顽症”p[1]文本(这个词源自拉丁语“recalcitrare”,指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或驴子那样对着某物“倒踢”[2])。
顽症文本不仅仅体现为模棱两可。相反,那些貌似可以将文本捏合在一起的不同阐释方法相互抵牾,似乎讨论的不是同一阅读体验。[3]不确定叙事中的这种极端的含混最终导致的不是融合,而是拒斥并否定中心意义的离心式真空。詹姆斯·费伦在托尼·莫里森的《宠儿》这样的后现代文本中发现了顽症,而我近年来则专注希伯来圣经中的顽症,鉴于《圣经》在西方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这些顽症就显得更令人无法忍受。我正在写作的那本著作列举了圣经叙事中的一系列顽症,并在最后粗略讨论了过去两千多年里出现的各种阐释方法(这些方法旨在消除那些顽症给依赖圣经的文化造成的毁灭性威胁)。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仅简要探讨其中两个例子。
“基比亚人的暴行”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头的:“那时,以色列还没有国王”,而故事的结尾也基本相同:“那时,以色列还没有国王,每个人各行其是”。这里给出的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大致时间(在“约书亚”之后,“扫罗”之前)。这两句话呼应了“申命记”(12:8)中的话,一旦上帝[4]选择了做礼拜的地点,“你们就不要像我们今天这样,每个人各行其是。”只要有了主庙,就应该有正确和错误的礼拜方式。“士师记”的中心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民事权威:以色列没有国王。这样,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事犯罪而不是邪说。因此,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它想要揭示的道理了,或者说我们自认为如此。
当以色列中没有国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
在“创世纪38”,有另一个被认为是荡妇的女子名叫塔玛,她的公公叫人把她带出去烧死在木桩上;“利未记20:10”摩西法典中也明确记载了因为通奸而遭受惩罚的事件。然而,这个利未人既没有惩罚也没有驱逐而是原谅了她。
她的丈夫起来,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她父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地迎接。
重归于好后,他们返回北方,日落时,夫妇来到基比亚附近,准备在城市广场搭棚住下,这时一个老农夫留他们过夜。他们进了农夫的房子,得到盛情款待。忽然,“城中的匪徒包围了他们的房子,用力敲门,对房主老人说,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可能认得他。”这些描述跟“创世纪19:5”中记载的所多玛人袭击罗得的房子的情景大致相同,那些急于下结论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袭击会以同样的结局收尾,即魔鬼比勒会被天使弄瞎眼睛,但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罗得把自己的两个少女送给那些所多玛暴徒蹂躏,而不交出客人,同样,农夫也把两个女人交给那些暴徒,而不交出利未人。然而,虽然这两个女人中有一个是他的闺女,但另一个却是利未人的妾,而后者是他无权交出的,因为她跟那个利未人一样是他的客人。
如果说农夫是理想房东的滑稽翻版,那位利未人的行为则反常得更让人惊异。当基比亚人拒绝老农夫送出的女人时,利未人“抓住”他的妾,将其推出房外,整晚任其被市民谩骂强奸。过了一个看似平静的夜晚之后,他“早上起来,打开房门,继续上路”,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然后,他看到妾“手抓着门槛倒在房门口”,便对她说:“起来,我们走吧。”
这就是该叙事的怪异之处。斯图尔特·拉辛曾如是评价:那个利未人“好像要急着上路以避免早上的交通拥挤。其荒诞不经的话语足以使读者以超然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场景,这一心态反过来又使得读者无法为那个侍妾所受的苦难感到‘悲悯’”[4]。我并不很赞同这一观点:拉辛只看到了读者阅读困境的一个方面——没有领会到那个利未人行为之荒唐的读者一定极度缺乏幽默感,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我看来,拉辛忽视了另一面。在这个没有什么细节描述的故事里,利未人的妾倒在地上,一只手搭在她被推出去的门槛上这一姿势,正是为了唤起读者的悲悯之情。但是,悲悯之情和黑色喜剧很难相伴而行;故事至此,唤起的情感已经前后矛盾,“作者的读者”分裂为二:一类“作者的读者”继续将这个叙事读成阴森可怕的故事,而另一类“作者的读者”则怀疑这个故事可能只是个低劣的玩笑。
让我们暂时把利未人及其侍妾的故事放在一边,来看看另一个同样古老的故事。有一个总在每星期天早上七点出门去打高尔夫的男人,有一次没有在午餐时间而是在深夜才回家,他老婆很生气。“你先听我解释”,他说:
这可不是我的错。你也知道我的朋友弗雷德吧,我们正在第二个草地,忽然下起了暴雨。弗雷德正要推杆时,被一道闪电劈中。暴雨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后来我一整天都在一边击球一边拖弗雷德,边击球边拖弗雷德……
这是一个笑话。在笑话中,虚构的人物行事诡异:他竟然一边拖着死在第二个草地上朋友的遗体,一边打完一轮高尔夫。理解这个笑话要求我们加入“叙事读者”,将这个故事看成他晚归的真实原因,同时还得加入“作者的读者”,将这个故事看成一个讽刺性的虚构叙事,讥讽那些狂热的高尔夫迷,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他们都要坚持打完球。
利未人及其侍妾的故事不只是个笑话,但在故事的这个时刻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笑话。那个利未人原谅了他出轨的侍妾,长途跋涉去接她,后来却把她扔给一群暴徒摆布,第二天早上面对她倒在门边的尸体,竟然兴高采烈地说“起来,我们走吧”,这个利未人与那个一边击球一边拖弗雷德的高尔夫球手同样让人难以置信。这就让读者很难做出选择。如果故事是个玩笑,那么就根本没有死去的侍妾,如果我们还去同情她,那我们就是傻瓜;但是如果不是玩笑,而我们却把它当作一个笑话,那我们就比傻瓜还要蠢。
士师记这一章的结尾部分继续了“作者的读者”的这种分裂,并且程度更甚。
然后他把她放到驴背上……进入房间后,他拿出一把屠刀,抓住他的妾,连着骨头一起,把她的身体切成了十二块,然后把这些部分分别放到了以色列的边境四周……
这段对于身体动作的描写迫使我们去关注她是如何被肢解的,甚或可能思考,人的身体并不那么容易被切割成齐整的12块。
如果追随一类“作者的读者”,我们从这个利未人和他小妾的故事中感受到的同情和恐惧此时达到高潮,但如果参与另一类“作者的读者”,我们则会遁入更为超然的态度,因为这个玩笑此刻为这位无名的利未人找到了外在的对应物:他的所作所为让人想起以色列各部落首次集合成为一支国家军队的那个时刻(1撒母耳11:7):
于是[扫罗]将一对牛切成块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全境,说:“凡不出来跟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
此刻,读者肯定也会想起,正如犹大的伯利恒是大卫王的家乡,便雅悯的基比亚就是扫罗王的家乡,而撒母耳正是来自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
随着故事在“士师记”20-21章逐渐深入,这个叙事的节奏及主体发生了变化,个体被部落政治中的群体声音和行为所取代。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欲报复基比亚的暴行。然而,复仇并不容易。便雅悯人拒绝将基比亚的罪犯交给其它部落,并且集结了自己的军队。激战三场后,以色列才取得胜利,共有65,000名以色列人和便雅悯人丧命。最后一次战斗之后,以色列人屠杀了整个部落地区所有无依无助的老人、妇女以及孩童,那个死去的侍妾便有了许多同伴。
对于把这个侍妾的故事当作一段正史来读的“作者的读者”而言,这后续的故事表明,一个罪行是如何引发一场以罪治罪殃及无辜的战争。但是,对于另一类“作者的读者”来说,这后续的故事则加剧了对扫罗的讽刺:米斯巴这个集合地点正是当初撒母耳给扫罗加冕的地方(1撒母耳10:17),当时人们发现他藏在器具中。此外还有一个辛辣的讽喻用典,残余的600名便雅悯士兵藏身在临门石,暗合了在密抹之战前扫罗王的残余军队藏身于基比亚:“扫罗在基比亚的尽边,坐在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1撒母耳14:2)。对于把这一章当作滑稽讽刺——作为对军队总指挥撒母耳的讥讽作品——来读的“作者的读者”来说,这当然不过是一个加引号的恐怖故事,那些大得惊人的人员伤亡纯属虚构。然而,这个叙事根本没有让我们放弃任何一种解读。
在最后一章,由于消灭了那600人之外的所有便雅悯人,而且由于没有“留下他们的妻子”,他们将不会再繁衍,以色列人为此懊悔不已(21:3-6)。便雅悯的妇女和儿童都被杀了,而这600名幸存者也不能娶其它部落的女子,因为文本通过倒叙告诉读者,以色列人早在米斯巴就发誓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然而,有一个解决方案。有一个以色列城——基列雅比人——之前没有参加在米斯巴的集合,因此那里的人并没有发过誓。现在,可以派遣12,000士兵到基列雅比去杀掉所有的男人、孩子以及曾有过性经历的妇女,留下的400名处女嫁给便雅悯人。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因为400名新娘不够嫁给600名便雅悯人。当看到在为上帝举行的宴会上跳舞的“夏伊洛的女儿们”时,“教堂会众里的长老们”发现了一个最终解决办法:那200名没有新娘的便雅悯人可以等候在葡萄园中,当那些女子出门不注意时将她们偷走。每个女子的父亲想必都发过誓,但是,由于那些女子不是父亲自愿献出而是被偷走的,因此也就没人违背誓言。于是,这个以一位长老怂恿的轮奸而开始的故事,以另一场由一群长老怂恿的大规模轮奸而结束。
这一幕正史颇具讽刺意味,但是对另一类“作者的读者”而言,还别有讽刺之处。在“士师记”第21章中被摧毁并屠城的基列雅比恰恰就是在“1:撒母耳:11”中那个毫发未损之城。此城受到外敌威胁,为了御敌,扫罗果断地将一对牛切成块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全境,以集合军队。扫罗代表的基列雅比人的勇气,以及基列雅比人对于扫罗王权的忠诚似乎都体现在他们拒绝帮助其他以色列人惩罚基比亚的淫徒以及杀人者。我们不想把这二者的联系视为历史,可是不管如何解读,“士师记”最后三章所散发出来的恶臭都会玷污扫罗及其最忠诚的支持者。
这个故事,以及整个“士师记”,以下面曾经沿引过的短句收束:“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人人各行其是。”对于同时属于两类“作者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在诠释上充满悖论的“诘言”。如果“基比亚的暴行”这个故事是段“正史”,那么,它记录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不知名的侍妾如何被强暴和被谋杀,同时还显示了在君主立法、社会稳定之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以色列人挥霍生命的荒谬:一个人只有在自己部落的领地里才能安全,而且在上帝神谕的指引下,部落可以使自己遭受种族屠杀。如果“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那么,国王的登基受敷就不会来得太快。但是,如果基比亚侍妾的故事是个“戏拟”或者“讽刺”,那么,它讽刺的对象只能是故事中没有出现的君主制。故事中的残暴行为反映的只能是那些君主的行为,他们性情暴戾,滥施法律,全凭一时兴起就拯救或摧毁基列雅比人,不假思索就牺牲夏伊洛处女,就像扫罗牺牲挪伯的祭司一样。由此看来,“士师记”最后一句要么解读为野蛮的历史真相,要么为辛辣的讽刺揶揄,除此别无他解。
我想重申对“基比亚暴行”的解读。我认为这个文本意义含混,而且只有在抽象的元阐释(metainterpretation)层面才能得到最终解决,除此别无他法。作为叙事,它同时产生了两种“作者式读解”,这两种读解不仅互相矛盾,而且情感反应也大相径庭。“有血有肉的读者”可以自由拒绝任一种解读,但是该文本同时召唤了这两类读者,即使是拒绝加入一种解读的读者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这种解读的诱惑。对于一类“作者的读者”而言,那个侍妾是一个“真实的”人,因此能够体验她的死亡及肢解带来的恐惧;对另一类“作者的读者”而言,那个侍妾是一个讽刺叙事中的符号式人物,并不比格列佛在他的第四本《格列佛游记》中跟我们讲述的人形兽更真实,当听到这些人形兽即将被慧髎国(Houyhnhnmland)那些贤马所消灭或阉割时,我们完全无动于衷。
“基比亚的暴行”可以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来解读,就像那张著名的兔鸭图,既可以看作是一只面向右边的兔形,也可以看作是一只面向左边的鸭形。多数人都能看出这幅图是一只兔或者是一只鸭,但不能同时看到兔和鸭。尽管如此,人们知道兔和鸭同时并存在“那里”。我曾经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如此含混的形式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有成千上万种关于行动、人物塑造以及语言的选择,让每个选择都同时作用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是难以想象的,而皮特·拉比诺维奇(Peter Rabinowitz)的“配置规则”理论则让这些不合常理的“同时作用”变得毫无必要。一种形式或体裁,一旦被读者感知,就会“点亮”语言、人物以及行动中的重要因素,同时抑制那些不适应于该形式或体裁的因素的影响。如果感知到的是另一种不同的体裁,就会有不同的细节被凸现或抑制。视觉艺术中,这类“兔鸭”并不常见,同样,叙事艺术中也难见如此“顽固”的文本,其迥然不同的两可解读方式之间的张力体现出的意义是其他任何方法难以做到的。
在兔鸭图中,你可以一开始就把它看成是兔或鸭。然而,在“基比亚的暴行”中,故事的开头却没有线索让读者将其读成戏仿/讽刺。每位读者都把它当作正史来读,直到第19章结尾的那些细节才让读者返回叙事开端,开始意识到讽刺的存在,并获准对文本做出一种不同的阐释。换言之,在兔鸭图中,所有人一开始就看到兔或鸭,而在“基比亚的暴行”中,许多读者开始时则根本看不到还有别的选择。即使是那些把这个文本配置为讽刺小说的读者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其讽刺的对象,当然到19章的结尾,他就完全能够看出两种可能的形式了。
因此,读者还要站在“元作者的读者”(meta-authorial audience)的位置上来思考该叙事的两种不同阐释。也就是说,因为文本既没有为“正史”,也没有为“戏仿/讽刺”提供明确的依据,两种读者都不能完全解释文本的所有细节。这样一种阅读立场,即同时站在两个“作者的读者”位置和“元读者”位置,听起来似乎非常复杂,然而这正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听到一个故事(无论是真还是假)时的立场。例如,我的一个学生在解释他不能按时交作业时,讲述了一个难辨真假的家庭悲剧。这个故事令我忐忑不安: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我肯定会表现出同情,但如果这只是个精心编造的谎言,我完全有理由为该学生试图利用我的感情而愤怒。我这种忐忑不安就是“元阅读位置”。这个案例与“基比亚人的暴行”(乃至其他暗含反讽的文本)的差别在于,后者中的读者为“作者的读者”,而不是“叙事的读者”。我们应该判断的不是故事本身的真假,而应该判断叙事要求我们按字面去理解还是从隐喻层面去理解,以及躲在叙事背后的作者是否在对我们挤眉弄眼。
“约伯记”的结尾同样引起了读者的忐忑不安,但是其根源却大为不同。“约伯记”是一个“破碎的文本”,它在叙事动机层面和主题层面的前后矛盾要求读者想办法去填补和修整。由于“约伯记”的主题——人类苦难之意义和上帝的公正——涉及到人与人、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方方面面,这种修补工作就显得更为迫切。然而“约伯记”让这种修补工作难以进行。修补叙事动机,就会在主题层面留下漏洞,反之亦然。我将这种情形称作“顽症文本”一大特点,不过,我们也可以更粗略地说,“约伯记”解构了自身,当然这里的“解构”不是纯德里达意义上的“解构”,在他看来,所有语言都在自我解构。
关于“约伯记”的起源、历史和语言,学界的猜想可谓汗牛充栋,但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因此我不打算引经据典,仅仅陈述自己的观点。“约伯记”是一篇丰富而难懂的诗文,“序”和“跋”均用简洁的散文体写成。据我推测,“约伯记”的作者只有一人,完成于“第二圣殿”(the Second Temple)时期,即公元前5世纪初期。作品背景不详(但不是以色列地区),约伯居住的乌斯似乎与伊甸(Edom)有关联,约伯朋友的名字也不是希伯来语。约伯不是以色列人;他信仰只有一个上帝,但除了懂得牺牲,对礼拜仪式一窍不通;除了知道伦理行为,对神律概不知晓。与其朋友交谈时,他称上帝为El,Eloah或者Shaddai(伊勒,伊罗亚或沙文,中文大意泛指神或神明),而不是敬称“主”(Lord)。
“约伯记”成书前,有一个关于约伯的传说。传说中的约伯与写于6世纪的《以西结》(Ezekiel)(14:14)中的诺亚(Noah)与但以理(Dan’el)一起广为人知,代表着以往世纪中有正直心的人。这个传说的大致轮廓出现在今天“约伯记”的前两章,是这么说的:主赞赏他富足的仆人约伯的正直,却招致撒旦(此处的撒旦不是后来神话中的魔鬼,而是在耶和华天庭中担任类似督察长一职的官员)的嫉恨。撒旦问道:“约伯是无所求地敬畏上帝吗?”他实际上是在质疑约伯到底是因为虔诚而富裕还是仅仅因为富裕而虔诚。撒旦继续追问,如果将约伯拥有的一切都拿走,他还会如此有操行吗?主接受了撒旦的挑战,将除约伯的身体之外的一切交由撒旦处置。仅仅一天之内,约伯便失去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仆人以及牛、羊和骆驼等巨额财富。约伯无比悲痛,但立场却仍然坚定:“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之后,撒旦开始第二轮挑战,约伯虽然免于死亡,但其肉体却因为疼痛难忍的皮肤裂口而备受折磨。约伯的妻子建议他诅咒上帝并就此赴死。但约伯仍然毫不动摇,没有“以口犯罪”。这位传说中的隐忍的约伯在钦定本新约5:14中也有提及。
今天的“约伯记”与传说的前提大致相同,但随后的叙述重心从撒旦与上帝的斗法转变为约伯及其朋友们对整个事件的反应。在约伯哀叹自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后,他那些坚信神圣正义的朋友料想约伯是由于犯下罪孽而受罚,而约伯却拒不认罪。于是,他们开始谴责约伯,起初还言语委婉,旁敲侧击;之后则义正词严,最终干脆振振有辞,似乎他们亲眼见证了约伯的罪行。读者此时不难跟上他们的逻辑,但他们的言辞,不管多么虔诚,只要与先前对约伯正直品德的描述进行对比,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当然,虽然约伯和他的朋友无法理解,但我们读者却可以从“序”中得知约伯之所以遭受苦难的确切原因。
约伯的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琐法彼此之间没有区别;他们注定永远扮演修辞角色,成不了鲜活的戏剧人物。约伯则不同,在“序”中他似乎只是一个代表正直的样板,后来却按照心理现实主义的方式得到了发展。他在开篇的哀哭是符合逻辑的,但在与朋友的交谈中,他逐渐走入迷途,开始崩溃。他的世界离他而去,原则也不复存在,他变成了空心人。在我看来,体现约伯失魂落魄的关键时刻(也是他最糟糕的时刻)出现在第9章第21节七个简单的字眼中:
我纯洁;我不了解自己;我厌恶自己的人生。
这是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人,因为他的灵魂已经开始支离破碎。但不到十个诗节之后,约伯又跌跌撞撞地转入另一个心路历程,而这个新角色重塑了他的人格,使他能够直面此前遭遇到的种种不平,并像原告一样驳斥朋友们的指责,妄想与上帝辨个是非。
这种妄想以不同形式不断出现在约伯的话语中。比如,“仲裁者”这个字眼纠缠着约伯,他一次次提到它,然而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能够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做仲裁的只能是某位“超上帝”。再如,约伯希望他可以暂时死去,这样,当他不再愤怒时,上帝可以让他复活。然而约伯当然知道,这仅仅是个幻想,因为死亡是永恒的。他还幻想,他死后会出现一个复仇者代表他去质问上帝,而他还要在躯体外活着,并有思考能力,以目睹发生的这一切。
约伯在指责同伴们的陈词滥调过程中不仅重拾勇气,也重塑了个性,恢复了自己反对上帝的角色。约伯争辩道,有他那样遭遇的人还不止他一个,尽管人人都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但是只要环顾四周,人们都会看到坏人发达,丰衣足食,寿终正寝,而那些正直的好人早早就丧命了。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赌咒发誓,自己从未犯过同伴们指责的种种罪状,最后他几乎是在用心呼号:
哦!但愿有一个人在聆听,我就在这里,上帝啊,请回应我吧!让我的敌人写一纸控诉吧,我将披之如勋章,戴之如皇冠!
几乎就在此刻,上帝现身了。一阵飓风刮来,这是神车的先行官,上帝出现了,是上帝本人,不是他的随员“椰洛因”(Eloah)或是“裟代”(El Shaddai),他以激昂的诗歌回应约伯。然而他对约伯的抱怨却只字不提。事实上,我们也并不指望上帝会因和撒旦打赌让约伯家毁人亡而向约伯道歉。不过,我们期望上帝也许会回答约伯与其同伴争论了整整30章的人类苦难和世间正义这个问题,然而我们的期望再次落空。回应约伯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创世纪中的上帝,世间秩序之主,而不是世间正义之主:他为地球奠基,将海洋关在门内,将昴星团串联,为猎户星座松绑。待展示完自己是大地、风、天空、雷电的主宰之后,他带着约伯游历生机勃勃的地球奇观:约伯,瞧那狮子、野山羊、马、牛、鸵鸟、猎鹰、秃鹫,你能创造出它们吗?还有两章是描写巨兽和海中怪兽的,既可能是河马和鳄鱼,也可能是上帝创造和驯化的野兽。有趣的是,在这份地球奇观的清单上,独独缺少人类的名字。
上帝斥责约伯“被无知的话语蒙住了心智”,很显然,上帝无意(甚至是拒绝)与约伯对簿公堂,但上帝并未明确指出约伯到底说错了什么。来自旋风的回应说的都是约伯从未否认过的东西,即上帝无所不能,却没有争辩约伯此前一直坚持的主张,即上帝创造的世界并不公正。上帝最接近于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是他在40:8-14中说的话:
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
你有上帝那样的臂膀吗?你能像他发雷声吗?
把恶人践踏在本处,
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
我就认你右手能救活自己。
当然,和以往一样,上帝再次把关于公正的问题转化为关于力量的问题:只有在力量上和上帝匹敌,才能质疑上帝的做法。
因此,尽管上帝回应了约伯的抱怨,但是圣灵显现与约伯所说的(即,上帝创造的世界并不公正)之间并无明显矛盾。如果有矛盾,那也是来自旋风的诗歌和“序”之间的矛盾。和撒旦打赌的上帝显然认为约伯是一个卓越非凡、诚信正直的人,他关心(或至少是关注)人类的道德品质。我们也许期望,上帝(也就是那个在西奈半岛发表“十诫”的上帝)是出于纯粹的目的才关注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但我们也许错了,需要重新思考这个“序”。在“序”中,上帝对约伯感兴趣,这是不是仅仅因为约伯是人类的一个杰出标本,就像上帝也会对千里马或悍狮感兴趣一样?如果是那样,追问上帝的正义就显得荒唐了。
但是,约伯在面对这一切时,心理是什么状态呢?他想与之辩个明白的对手如此强大,他自然应该感到惊慌失措,担惊受怕,只有俯首称臣。他应该对上帝言听计从,以免陷入更大麻烦。他应该称自己人微言轻,从此闭嘴不言。最后,他应改邪归正,不再指责上帝。
他是这样做的吗?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从约伯嘴里蹦出的最后一句话,那是表达判断的唯一一句话,他能判断是因为他现在亲眼看到了上帝:
Al-ken em’as v’nichamti al afar va’еifer
钦定本把此句话翻译成:“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其他多数英文翻译也都与这个意思大同小异。
但这行诗要表达的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先说最后两个词,afar va’eifer(尘土和灰烬),这是在创世纪18:27中使用过的一个暗喻,当时亚伯拉罕正向上帝求情,因为那些正直的人可能同恶人一起毁灭在所多玛城。亚当来自尘土,因此当亚伯拉罕说他是尘土和灰烬时,他的意思是表明自己虽然只是一个凡夫俗子,但可以质问上帝的是非,他这样问道:审判世界一切的主,岂能不行公义?
第二个问题是nichamti,它的意思不是懊悔或放弃,而是为某事感到难过,因此第二小句的意思应该是“我为人类感到难过”[5]。
最后还有em’as,这是最大的疑难。这个动词在“约伯记”中出现了12次,比在其它任何圣经文本中出现的次数都多。它的意思宽泛,既有拒绝的意义,也有轻视、厌恶的意思。钦定版中“厌恶自己”的译法来自早期的希腊文圣经译本,其中的反身代词不见于希伯来语的马索拉版本和《圣经注疏》中。一般来说,em’as是用作及物的,比如在我已经引用的诗句9:21中,约伯所说的“em’as chayai”的意思是“我厌恶生命”;在此处和7:16中,它是用作不及物的,其意思就应该是“我感到恶心”。我们的分析大概就只能到此为止了,而约翰·柯蒂斯则更进一步,他认为这个动词实际上也是及物的,只不过宾语给隐去了;柯蒂斯认为约伯最后说出的话:
因此我感到极度厌恶和反感
(对你,啊,上帝)
我为弱小的人类感到难过。
这个饱经磨难的受害者曾拒绝“诅咒上帝,然后死去”,现在却同情他的人类伙伴,因为他们的上帝也不公正。
如果我们分析正确,那么我们只能假设上帝没有听到约伯最后说的这几句话,因为如果他注意听了,我们就很难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第38章中,约伯认为上帝的世界没有正义,对这个世界表示极端轻蔑,因此受到上帝指责,但到42章,上帝又完全推翻了自己先前的指责,称赞约伯一直都是正确的。上帝龙颜大怒倒是针对约伯的那些朋友,虽然他们坚持认为上帝的公正和旨意早晚会降临。这些人的性命将取决于他们的献祭和约伯的祷告。的确,我们能期待什么呢?大权在握的上帝想宽恕谁就可以宽恕谁:基于权杖的神的想法不需要前后一致。当然凡读过“序”就知道,约伯不知内情的朋友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弄错了,因为约伯的不幸的确与他犯的任何罪孽毫无关联。可是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离回答撒旦最初提出的问题还有多远:约伯是因为正直才富有呢,还是因为富有才正直?因为约伯说得“正确”的地方恰恰是正直和财富均毫无关系。
“约伯记”的最后一幕似乎把我们带回到民间故事的世界,在那里隐忍的约伯因坚韧而得到公正的上帝的赏赐,恢复了所有财产。但是,从3:1到42:6,约伯诗歌却全然没有“隐忍的约伯”或“公正的上帝”这样的概念,因此最后七行诗提供的不是一个进程的完结,而是一个辛辣的讽刺。约伯拥有的家畜数量是以前的两倍,在房屋被狂风刮倒时死去的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们也被相同数量的男女孩子所替代。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佐西马神父(信仰的化身)读到这个结尾也错愕不已:
神再次垂青约伯,再次赐予他财富。许多年过去了,他又有了孩子,并且很爱他们。但是当以往的孩子都已不在,当他已经失去他们,他怎么能爱现在这些孩子呢?想着他们,不管现在的孩子多么可爱,他又怎能全心为这些孩子感到由衷高兴呢?但是他能,约伯能。这就是人类生活的神奇之处,以往的悲伤逐渐逝去,化成悄悄的、淡淡的喜悦。
佐西马所谓的“悄悄的、淡淡的喜悦”补偿了约伯。但谁来补偿那些因为上帝与撒旦打赌而骤然死亡的孩子和仆从呢?他们依然是无辜的牺牲品。像佐西马那样相信复活的人也许能找到些许安慰,但关于复活的信仰大约三百年后才传到朱迪亚,“约伯记”的作者和早期读者不可能有这些信仰,对他们来说,死去的孩子不可能再活过来。
把“约伯记”捏合成一个整体就更难了,除非运用“考据式批评”(Higher Criticism)才能解释这些完全不同的动机和思想。“序”假定了一个公正的上帝和一个隐忍的约伯,可被视为第一层,在此基础上,五世纪的诗人增加了对话,塑造出一个愤懑而残忍的约伯,以及圣灵显身的情景,塑造出一个充满创造力但对人类无辜受难无动于衷的上帝[6]。尾声部分不仅没有调和这些道德与动机方面的系列矛盾之处,反而最大限度地加剧了这些矛盾,让读者莫衷一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一切表明,“约伯记”的体裁既不是埃斯库洛斯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也不是柏拉图的《对话录》式的哲学对话,而是讽刺体。如果需要找一种概念来解释这个讽刺诗的形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反圣经”,因为正是《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塑造了一个无所不能、超越尘世的造物主,而不是“创世纪”(Ⅱ)中那个更具有人性特征的上帝,更不是那个在西奈山大叫十诫、寓居在耶路撒冷方舟中的部落神。
这个“超越尘世的上帝”的概念促成了今天的情形,即三大宗教都遵从一神论,分别是主(Adonai)、耶稣(Lord)及阿拉(Allah)。早在第二以赛亚(56:6-7)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观念:“那些外邦人皈依了耶稣……我将带他们到圣山……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但相信一个超越尘世的上帝也有不利的一面。上帝不再关心尘世公道,公道就得由尘世社会自己来主持,于是无辜的苦难就成为永恒的问题,而且不得求助上帝。如果不小心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去读读“约伯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