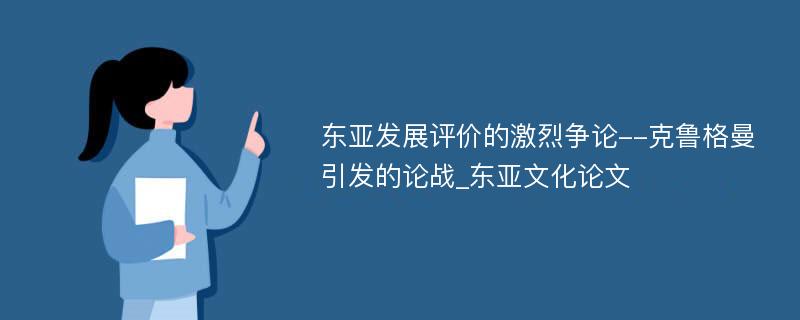
一场关于东亚发展评价的激辩——克鲁格曼引发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鲁论文,东亚论文,评价论文,格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是一家专门探讨国际问题、登载名家学说的有影响的刊物。该刊在1994年11/12月号这一期,引人注目地安排了若干篇似乎意在破除“神话”的文章,其中一篇,题目清晰,名曰《亚洲奇迹的神话》,作者为史丹福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文章起始,克鲁格曼笔锋指向西方舆论关于东亚(广义的指称,含东南亚诸国,下同)高速经济发展的“常规智慧”,即那种感到东亚经济一方面给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让人心存恐惧的见识。不过,他无意深究流行西方的这类复杂心态,而是笔锋一转,摆明自己的思路;东亚经济的增长没有什么东西真正令人印象深刻,实乃一种神话,因而也无需为之恐惧。借用当年毛泽东形容美国的一个说法,他认为东亚诸“虎”其实是“纸老虎”!
克氏进而举出30年前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奇迹”作为类比,并称之为“谨慎的寓言”。他提醒读者,当年苏联“共产主义”的经济增长也曾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增速既非奇迹,也注定要滑落下来。他认为,尽管当年的苏联与今日的东亚在政经体制、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上如此不同,但于经济增长模式上,则有惊人相似:两者都是高投入带来的高产出。这种高产出包括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大幅度的就业,大面积的提高教育水准与高水平的积累——简言之,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所有资源,而不是生产效率的实际提高。于是,按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即可预断,这样的增长不会持久。
作者以新加坡为例,说明其发展若以效率论,与西方的差异仍有相当距离,因而它的经济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减缓;而日本也并未向某些人预言的那样,人均收入在80年代超越美国,截止到1992年,其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82%”。
论及中国,他指称有关发展数字不尽可靠,而且如此大的增幅,与原有的低起点与起算的年代有关(他认为,假如以1964年做起点,则中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就明显变缓,而与东亚诸虎近似,且其发展的本质与后者的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无异)。克氏更例举出这个地区近来资金外流的情形,警告说这是一个衰落的信号。
据此,克鲁格曼进一大步,提出如以现在的速度预测到2010年的未来发展,将一似60年代时预测苏联—东欧的发展一样“愚不可及”。
克文一出,《外交事务》读者反响强烈,不少专家学者致函编辑部,力图反驳克鲁格曼的论据与思路,因此也否认其观点。1995年3/4月号这一期,选刊了部分代表性意见。
太平洋盆地研究所总裁吉布尼(Frank Gibney)援引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尽管HPAEs(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高超表现的亚洲经济)有2/3的增长来源于“投入驱动”,“其余1/3不能由积累去解释,因而应归于生产因素在效率上的提高”。
吉布尼指出,对亚洲国家来说,资金的引进也带来了知识与技术的引进,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则意味着要从竞争对手那里学习更多东西,这与苏联当年不惜代价的进口替代之经典例案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这些国家持续发展的教育机会,较好的组织与改进了的工作实践,都是独到的;而更为重要的则大概是各大自由企业间的协同,政府的财经干预与悉心指导的技术官僚;如此灵活的工业政策与苏联式的指令性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
吉氏进一步强调,东亚诸国正在摆脱由投入驱动型经济带来的增长制约,由劳力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分化或转化。政治改革与工薪的提升也在诸多例案中有良好记录。他对克文中专门拣出经济上最不具有代表性、政治上与西方距离感最大的新加坡为例感到不解,并补充说即便是该国最近也在渐渐摆脱迟滞的局面,在产业服务业创出两位数的增长。
吉布尼还分析了日本经济增长陷入困境的原因,认为该国政局的困厄要负主要责任。他认为日本依然可看作亚洲国家现代化的范例,一个结合对现代技术的适应、企业界推动与政府支持的国际化市场经济,是可以走出自己道路的。这里,他对于“所有经济都只能走一条路”(即“我们的路”)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提出了批评。
美林(日本)公司研究部经济学家比瓦夸(Ronard Bevnqua)在信中指出,把亚洲“奇迹”经济与60年代的苏联做对比,克鲁格曼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苏联的计划者不顾市场而高速扩张投入,而亚洲的决策者则以市场引导民间的能量通向国家发展的目标,苏式增长的致命伤是由于计划者与生产者都缺乏市场的刺激以增加效率,而今日亚洲国家则恰恰相反,决策者与生产者都对市场给出的信息做出回应。
比瓦夸认为,克鲁格曼试图纠正某些人关于东亚发展的歇斯底里,其用意不差,但他未能区分亚洲的市场应用型与苏联的市场取消型两种工业政策之根本区别,这将误导美国对东亚政策的重新评估。
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Ishrat Husain)在信中指出,当克鲁格曼热衷于向关于HPAEs的“常规智慧”提出批评时,他忽略了东亚经济的一个中心议题,即HPAEs在高速增长与高水准平均收入分配与降低贫困表现,是独一无二的。一项对40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分析资料显示,所有的高增长、低不均记录,都出在这一地区。对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条件——社会的合谐与稳定也都存在于这一地区。尽管大的外部经济动荡与内部政治动荡都有可能会影响这个地区的持续进步,但这并不能推理出东亚的奇迹就是泡沫。
这位经济学家还列举大量研究资料,批驳克鲁格曼的核心观点,即东亚的奇迹仅是投资的高水平,而没有综合生产力的提高。他特别指出,该地区多个国家在技术发展上已跟上主潮,而其它国家也正在迎头赶上,并显示出有能力赶上。他强调说,这一点在与非洲与拉美国家做对照后,尤为明显。
侯赛因提出,更为重要的,是HPAEs能否在未来提升或保持其生产增长势头。他认为,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国家均能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避免高通货膨胀,并实施财经纪律。他还指出,东亚经济的表现可以从他们连续并越来越多地共享世界出口上,观察出来。
根据全球经济增长的材料分析,世界各国的发展高度不稳定,但东亚则是例外,在稳定性这一点上,HPAEs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
侯氏在结论中说,尽管奇迹并不会无限期延续,但当东亚许多国家经济仍在上升中,另有许多国家的巨大潜力尚未开发时,就预期其终结,对于一名经济学人来说,未免太急切了。
东西方中心国际经济政治计划高级研究员克洛易克斯(Sumner La Croix)和李(Chung H Lee)两人共同来信指出,克鲁格曼的生长力研究未能抓住一个紧要过程,即从60年代起,东亚的工业与出口从劳力密集到技术劳力密集到资本密集的转型。他们质疑说,如果只是就劳力投入的比率来计算、预期未来,那么例如非洲的加蓬拥有比四“虎”更高的劳力投入率,难道未来加蓬会比后者有更高产出吗?
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弗里德曼(Edward Friedrnan)在信中说,克鲁格曼不自1978年起计算中国的增长,而是从1964年,因而推论说中国的经济表现出不高的效率增长。但是1978年前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连续的,怎么可以用作评价一种模式的资料?他质询到,如果评价里根经济的表现,却从约翰逊年代算起,这合适吗?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来信指出,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表现评价上的“神话解构”工作,做得不错;那种认为东亚会不可抗拒地领先全球群伦的广泛关切,是错误的。但是,克氏文章的腔调,可能会误导读者。
他指出,经济学家可以比他人更熟悉、了解投入与产出的数字,但这并不等于“神话”就可以消解。他认为,东亚国家的持续高额投入是事实,但为什么其它(发展中)国家却达不到如此持续的高投入?为什么这些国家决定如此持续的高投入?如果仅以投入型经济去解释,则东亚的增长依然是一个神话(而未被解释清楚)。
罗德里克写道,回顾东亚经济史,有一点很清楚,政府做出努力以确保创造稳定气候、资助与协调投资决定。我们不很明白,为什么东亚干预主义途径并不导致其它发展中国家通常遇到的灾难,但东亚“奇迹”与政府的政策有关,这一点并非(克鲁格曼)轻易能化解的。
最后,原文作者克鲁格曼教授以“(对)我观点的神化”为题,答复读者说,他很高兴看到这么强烈的反响,即便是有人对他故意做出的挑战方式进行了攻击。他辩解说,说到底,文章的主要用意在于摇撼时下这样一种思路上的循环,即“我们知道东亚式政府有效,因为其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我们知道这种增长会持续,因为他们的经济遵循了政府有效的政策”。他指出,当年评价苏联经济时,就有过这类循环思路。
克鲁格曼重申三点论争:1.许多人认为“增长会计学”(growth accounting)的理论框架过于简单,但理论研究往往先从简起始,而他本人的假说即为:诸“虎”的增长是投入型(而非技术型),并无神秘可言;2.文章本着治学中的“奥康剃刀”(Occam's razer)原则,尽量用一个最简单的理论去解释未知问题;3.该文的写作也是一种自律,正因为时下潮起的关于政策关于文化的讨论更有兴味而不是更切中会计学运算,身为一名学者更应努力给出哪怕是令人生厌的解释。他认为许多人的反驳实际上多少是支持了他的观点,即东亚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技术、效率上的差距。就经济发展的投入型本质而言,一个人应该对其它一长列附加于其上的种种其它美德持谨慎态度。
在答词的末尾,克鲁格曼结论说,东亚经验对西方社会来讲没有什么可供学习、借鉴之处。虽说对不同观点之人,有人认为它显示出市场经济的作用,或显示出工业政策的效率,或显示出权威主义美德;但就他个人而言,只是高投入带来高产出。
贯串整个讨论,从狭义的学术意义上看,中国读者可以略窥对东亚经济这类热门话题,在批评、讨论与研究上存在的不同方面与层次,并由这些方面、层次,理解西方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在分析、理解问题上的长处与短处。
就广义的宏观思考而论,我们也可于这场激辩中读到美国(或许包括更多西方国家)对这个题目不懈热情的原因所在,这至少包括:1.从全球战略意义考虑,准确乃至精确把握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制订未来国家决策(外交,国防等)至关重要(如克鲁格曼所表达的,中国方面几个百分点的年增长差异,将影响到下世纪中国是否超越美国);2.东亚的发展,对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的理论研究,是否提出新鲜的经验,激发新的思路,开拓新的领域,或带来新的动力;3.在意识形态—思想层面,东亚的发展,是否构成了西方的社会—文化—信念体系之外的独立参照系(上限是对后者提出正面批评,下限是向人们指出另一条发展道路)。这样的“大是大非”,是西方扩张史500年来所仅见,我们由此不难想见,上述激辩(及其它许多类似讨论)何以其热度、烈度远远超过一般学术讨论。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并且不应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