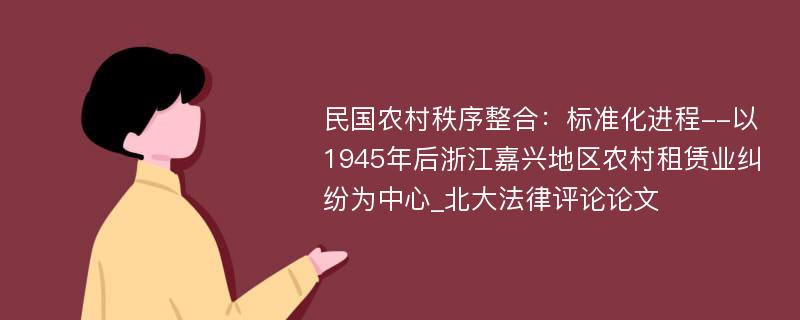
民国乡村秩序的整合:规范化过程——以1945年后的浙江省嘉兴地区乡村佃业纠纷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嘉兴论文,浙江省论文,民国论文,纠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学者们对于中国民间纠纷调解方面的研究颇多,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论点:梁治平强调,法律条文无法体现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在具体审判中要遵循人情。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现代法律观和秩序观是完全陌生的,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存在受理性训练的官僚,他们不可能完全通过运用法律来实施管理。(注:梁治平:《法意与人情》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第149页;《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2页。)滋贺秀三从中国法文化的角度,认为清代民事审判将“情、理、法”三者相结合,把情理作为主要依据,取相关的法律条文作为参照;(注:(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王亚新、梁治平主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85页。)该论点与梁治平的观点相一致。黄宗智认为不同层次的官方有不同的表达,民间的表达与官方更是不同,因此存在一个实践与表达相背离的现象;并提出民事审判的第三领域,即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存在一个半官半民的纠纷处理过程。(注:(美)黄宗智:《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5、130页。)
寺田浩明对滋贺秀三和黄宗智的上述论点均提出批判,他从民事法秩序的角度指出,要区分和理解民间纠纷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注:(日)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审判:性质及意义》,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1999年,第616-617页。)从民间纠纷的普遍性出发,来探究民间秩序的具体运作,确实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但限于资料,大多数学者只能从县级民事审判等资料作判断或推论。赵晓力利用《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通过分析近代中国农村土地交易,认为法制的近代化没有彻底改变原有大小传统之间的博弈关系,新传统企图改造民间,反而被民间规避或弃置不用或否定。(注:赵晓力:《中国近代农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与国家法》,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第495页。)张静分析乡规民约,认为乡规民约代表的社会建制强化了村级组织的权威,并造就了基层组织和农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形式,因此国家法律要想代替乡规民约的地位使自身在乡村占有决定性的地位,是非常困难的。(注:张静:《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1999年,第46、48页。)
然而,随着中华民国国家权力的下延,乡镇公所及保甲等行政组织深入乡村,难道乡村习惯法的力量将国家法置之不理?乡村秩序还是沿袭传统而无改变?本人利用档案资料,以乡镇组织处理土地纠纷为中心,进一步探讨民国乡村秩序的整合过程。
一、佃业双方:面对面的争执
水稻为嘉兴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缴纳赋税的主要科目。按照水稻种植区,嘉兴县分为南北两区,嘉南为早稻区,早稻大都60天熟,称作早尖;嘉北为晚稻区,120天熟,称作晚粳。嘉北地区也种早稻,80~100天熟,80天熟的称壬尖,晚者称洋尖。(注:嘉兴县档案馆:304-3-9。本文其他部分资料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该卷宗。)
1926年国民党做出“二五减租”的决定,正产(注:正产,即一年四季田地的主要种植作物,如水稻等;其他作物的收益则为佃农的。)农业收获量的50%为最高租额,租额依照最高租额减25%,即佃农缴纳正产收获量的37.5%作为租额。1927年11月,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和省政府联合通过了《浙江省本年佃农缴租实施条例》,首次从组织上确保了国民党“二五减租”的政策。基于缴租比例是固定的,租额的高低取决于收获量的多少。每一乡镇的收获量由乡镇、农会等组织人员及业主决议,后为避免业主有意抬高数额,取消了业主的参与权。许多学者认为,大部分省均未认真执行“二五减租”的政策,只有浙江省喧嚣了若干年,其中1928年被称为“浙江减租运动的黄金时代”。由于减租法规存在诸多操作上的问题及国民党派系斗争等原因,1932年后则开始衰退了。(注:金德群:《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1905-1949)》,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189-199页;诸葛达:《浙江“二五减租”述评》,《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王合群:《国民党派系斗争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的兴起》,《民国档案》2002年第2期。)
1945年10月,国民党行政院颁发《二五减租办法》,在已免收田赋的省份,佃农应缴地租在原来基础上减少四分之一(注:《大公报》1945年10月31日,万仁元、方庆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67)》,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即佃农交给业主的部分,按收获量的37.5%计算。按规定国家田赋为每亩收获量的五分之一,1947、1948年嘉兴各乡镇的国家田赋也在此基础上再减去四分之一,即国家田赋为收获量的19%,称为“五四折”。收获量的标准,由各乡镇召集佃业双方协商定量,最后由县政府根据各乡镇的上报数核定缴租数额。通过佃业双方面对面的商讨,政府希冀减少佃业纠纷,并借此顺利完成田赋缴纳任务。
各乡镇公所召集佃业双方代表开会商讨应上报收获量。1947年11月,八字乡、双云乡、新北乡三乡均召集佃业双方开会。出席人员有乡镇公所人员、保长、业方和佃方代表。11月3日,八字乡举行的第八次联席会议上,除了乡长、保长等,乡农会也派人出席会议,与会业方代表5人,佃方代表19人。同月13日,新北乡的第八次佃业双方会议上,乡长、保长、乡代表会主席和县参议会议员均出席,佃方代表有23人。虽然会前已通知各业主参加,但与会的业主代表仅1人。乡镇公所、保长乃至乡镇代表会议、县参议有关人员参与会议,确保会议的公正性,并给以适当的建议和指导。
收获量上报方法,八字乡依照佃业双方代表所报之收获量取平均数计算;荡田赋额按成数折扣缴纳。由于会议申报结果切关自身利益,佃业双方皆从各自利益出发,发表意见;甚至出现激烈争执。
佃方:陈实海:早稻在五斗左右,晚稻在九斗左右。
韩桂湘:本人意思和陈代表相同。
程锦兰:本年度收获量较好的地方亦有,歉收的地方亦有。本保(十四保)则受灾较深,故收获量在四五斗间。
王掌林:早稻五斗左右,晚稻九斗差不多。
潘长林:本保(九保)受风、虫、旱三灾的影响,早稻在四五斗左右,晚稻在七八斗之数。
王茂舟:早稻在四五斗,晚稻在七八斗。
佃方代表所报数目相差不大,并强调自然灾害对各保产量的影响。因为上报数量与佃农上缴业主数量直接挂勾,业方代表意见自然与佃方代表不同,有的业主表示强烈反对。
业方:赵鼎:我不能代表全体的业主,只能看到本保(十四)的情形,大概在五六斗至一石之间。谢廷琦:在未发言前先得申明,本人本来是列席,但是因为有少数的田放租,所以亦代表业主说一句话。今年的收获量平均大概在六七斗至一石之间。
闵仕年:照情形看来,今年的收成总较去年为好。但是佃方各代表说比去年逊色,则无言可说。以良心而论,本年的收获量,早稻在一石五六斗,晚稻在一石八九斗。
业方赵鼎与佃方程锦兰同为十四保,赵鼎所报下限五六斗与程锦兰的四五斗,且相差无几,但上限一石,则相差一倍。赵鼎和谢廷琦所报数字未将早稻与晚稻加以区分,若将佃方所报数字进行平均,则在六七斗之间,也在他俩所报范围内。只有闵仕年所报数字过高,如果其田地的收成确实受天灾影响,则他有故意报高的嫌疑。最后会议取佃方和业方报数的平均数,决议每亩收获量为八斗八升五合。该结果让业方大为不满,业主们以集体退席表示抗议。
1948年11月29日,洛浦乡公所召开佃业代表联席会议,佃业双方较快地达成了一致意见。
主席报告:该年本乡田农秋收因被虫灾水浸,损害颇重,并且稻谷大部出芽,已经县府派员查勘予以证实。
佃方代表陆琴奎:本乡早晚稻较上年收获量确是减少。原因是为地处低洼,秋雨生芽。与各乡相比,洛浦收获量最短,须求业方谅解体恤佃方困难。且以本人估计每亩实收平均不过一石之谱耳。
业方代表钱伟丞:查本年歉收情形确是实在,至于正收获量似稍有出入。以缴租而论,不妨简单的说,除田赋征实外,由业主实收数,究何标准定义,希公决。
鉴于天灾水稻减产的实情,在减少收获量标准方面,业方和佃方并无异议,关键是提出一套较为公允的方案。佃方代表徐一仰提出按上、中、下三个等级分别计算收获量,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可。
佃业双方争执的焦点,还在于收获量的数目。有佃方代表称今年每亩收获量最高应为九斗。业方代表朱捍伯提出质疑:“依照佃方所称本年缴租标准最高以九斗为准,则业方除田赋及土地登记费外,所收实数不过一斗余。此项尚希加以考虑。”
朱捍伯的分析确属实情。该年收获量按每亩九斗计,国家田赋“五四折”后为一斗七升一合,土地登记费为一合八勺(注: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41),1946年《土地法》第三章第65条,土地登记费按地价的2‰缴纳。黄山书社,1999年,第400页。)[2](P400)。按“二五减租”计算,佃农交给业主的田租为三斗三升八合,除去日赋和土地缴纳费外,业主的利润约为一斗六升。最后会议决定,上等田每亩收获量一石一斗,中等田九斗五升,下等田八斗五升。如果佃农代还田赋,则每亩除去二斗五升。最终县政府核定该乡收获量,取其中间值为九斗五升。
当政府将“二五减租”法规用佃业双方代表会议这一组织形式确定后,佃业双方就可以根据各自的实情,通过面对面协调或争执的方式来决定缴租数额。至少在制度层面上,佃业双方有了一个可操作的解决方法。正是由于实施“二五减租”,嘉兴各乡镇的佃业双方才会在会议上力争自己的权益。
二、升级的纠纷:秩序再调整
正如县府所述,召集佃业双方代表会议,是为了避免佃业纠纷,维护社会安定。在一定程度上,该制度较为公正,能够维护佃农的利益,并完成田赋上缴任务。如果决议结果出现偏斜,就会出现有的业主不参加会议,或是对决议不满而集体退席的情况;或者佃农认为决议的数额过高,而集体上访。如此,佃农与业主的矛盾就有可能上升到集体对抗的程度。
县政府核定1946年度嘉南地区收获量为一石六斗,嘉北地区为一石八斗。后因嘉北地区上报灾荒,嘉北新塍区各受灾乡收获量减为一石一斗八升至一石零五升。这引起了新塍区业主们的抗议,他们认为若照该收获标准纳赋,则业主们将无丝毫利润。至1947年,嘉南收获量定为一石四斗,嘉北尚未公布收获量,新塍区有的乡镇决议收获量在一石以下,这愈发引起了该区业主们的反对:
查本年晚稻实际收获数量,当在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以上,此为尽人皆知之事实。但闻有少数乡镇,竟有报收获量每亩一石以下者,显系为少数人操纵,抹杀事实,别有用心。倘序届立冬,田间行无立稻,应请钩府会同党参各机关迅赐履乡察勘,藉明实际,或临田分割,稍示公平。召集佃业两方代表,酌理衡情,公同议决,以上裕国赋,下恤佃家,兼顾业方权益之中,予以核定,以资遵循,而免纷更,实为公便。抑(斐成)等尤有言者,二五减租,国父手定平均地权初步之准绳,新塍一区,与绍属萧山遵行历二十年,从无牴牾。耕者有其田,原为极则,而产权之转移,应有相当之过程,似不应再于收获实数任意出入,遽在国家未明令以前,先为消灭私有制度之举。况吾新塍各乡,往往有数口之家,种租田三十亩以上,乃至百亩者,数在不少。驱遣傭工有如牛马,租籽所损,悉为已有。致不惜蒙报灾荒自定收成数量,利已损人,莫此为甚。假佃农之名,行包佃之实,均地权而不平佃权,于广大农民初无裨益,浸致驯者寒心、黠者张目。(注:佃农可以将田地转租给其他人种,将在下面部分述及。)
很明显,无论丰收歉收,业主们都想坐收渔利。他们认为,1946年党团机关下乡核定灾情时,水稻已割,“真相既泯,无从察看,乃指微瑕以掩全璧”,业主们“吃了亏”。既然如此,1947年嘉北各乡镇的收获量就应该比嘉南高,意即补回1946年的损失。在此,虽然业主们声称一直贯彻实行“二五减租”的规定,但他们不愿意承认各乡镇收成有差异,因而有国家是否要“消灭私有制度”的恐慌。
对拥有成百上千亩田地的业主们来说,收获量最好与相邻乡镇一致,以保证收租的余利。而对于佃农们来说,有的仅租有数十亩甚或数亩田地,分区分保来核定收获量更为公允。
1947年12月,双桥乡一至五保128名佃农联名上书县政府,指责该乡晚稻收获量的决议违法。佃农们举报,11月14日双桥乡举行佃业双方代表会议。但在会议前,一至五保的佃农没有接到通知,因此无一人出席会议。而该会议上决定六至八保收获量为一石三斗,九至十二保为一石一斗,唯独高估一至五保为一石五斗,只有一至五保内东西昃字圩(西所)部分减为一石一斗。佃农们指出一至五保除东西昃字圩外,均为业方代表吴鹤鸣家族的田产,而吴鹤鸣为省公务员。佃农们认为:
在省之公务员又何从以知一至五保之直接收获量,故业方配以任公务员(吴鹤鸣)之为代表,殆为预有组织,弄此玄虚。……予东西昃字圩以内之佃农表示恩惠,予昃字圩以外之同保佃农,加重负担,以遂多收租息,尤不胜使人忿恨。同在一至五保以内,而地势气候相同,环境遭遇相同,独东西昃字圩减低其收获量,显然对一至五保内东西昃字圩以外之佃农,独特增重缴租数量,其成为偏见,有意欺压,无可掩饰。
此外,双桥乡佃业双方代表会并没有把会议上决议的收获量呈报县政府,按照规定,应由县政府依四邻各乡镇标准核定。双桥乡四邻乡镇:加秀镇收获量为一石二斗;新北乡为一石;王江泾为一石三斗二升半;据此,双桥乡的收获量也不可能超过一石三斗。
128名佃农上书,并派代表前往县参议会请愿,县参议会把文件转发各机关。县府派代表前往双桥乡核查,与县党部、参议会、县农会共同商决,定于12月15日下午二时重新召集双桥乡乡长、代表会主席、乡农会代表暨佃业双方代表开会商讨,最后决议租额为四斗三升一二五,即收获量为一石一斗五升。但据第一保农会会员王金观、王潘氏汇报,决议并未发生效力,业主们态度强硬,每亩仍照五斗六升二五收租,即收获量仍按一石五斗计算。同时对于未缴纳地租的佃农,有的业主向嘉兴地方法院起诉追租。法院未采用新更正的每亩四斗三升九合一二五的标准,而是判决佃农照五斗六升二五缴付。判决一出,其他业主也拒绝按照新标准收租。最后,佃农们报请乡农会设法救济,乡农会据此请县府令法院依照新定标准判决。农会的职责本在于维护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利益。这里的农民,自然应该包括佃农和业主。但在实际操作中,农会在调解佃业双方的纠纷时,一些支持佃农的措施,使得业主们颇有怨言,认为农会偏袒佃农。
1948年11月28日,双桥乡农会召开理监事及各小组代表联事会议,认为佃业纠纷缘于1947年参照旧属双南、双桥两乡分保上报收获量,以致同一乡内数额悬殊,这也是引起北乡一至五保佃农反对的主要原因。该乡土地并没有高低肥瘠之分,只是业主籍居情况有所差异。南乡六至十二保的业主多为客籍,北乡一至五保的业主多为本籍。客籍业主参与会议的比例较低,而本籍业主大多参与会议,对决议结果也能较快做出反应,这也是该乡收获量出现南北两乡之差的一个原因。鉴于此,农会认为应统一全乡缴租标准,以免争议。
此外,该年双桥乡早稻“霪雨为灾,遍成芽谷,以至无可救药”;晚稻正当“发育滋长之际,突遭飓风侵袭,虫害骤起,多成枯苗,且愈施月巴而受灾愈烈。灾象已成,群情惶惶,无可走告,影响收获,当为任何人无法否认之事实”。农会认为,应照去年收获量减收20%作为缴租标准,即早稻晚稻平均收获量为九斗六升。同时,鉴于“预租”和“特殊租额”“确已不适宜于目前行宪时期,且早为政府所厉禁。际此政府重颁彻底实行二五减租之际,本会同人自应急起拥护予以实行”,取消“预租”和“特殊租额”。(注:“预租”,即提前一年缴纳租额。“特殊租额”,即定额租,无论该年丰歉,均依照约订租额缴租。)
该年双桥乡佃业双方又有争议。双桥乡迟迟未报收获量,经县政府一再催促,定于11月28日召开佃业双方会议,因出席人数未合法定人数,定于12月2日再次召开会议。但该日县政府已在《嘉兴商报》刊登各乡镇收获量,其中双桥乡数额系,根据四邻乡镇平均,定为一石一斗三升九合,该数高于乡农会决议的九斗六升。由此在佃业代表会议上,佃农群起责难农会稽延会报之咎,认为县府所核标准失之公允,与农会决议相差悬殊,表示难以负担。业主们认为应该按照报纸所刊标准执行。
由于双方争执不肯妥协,当天会议不欢而散。农会调解不成,只得上报县政府。县政府批评其不按县府规定及时上报,认为此时再起争议,是“故弄玄虚”。既然确立了佃业双方代表大会作为佃业双方协调的平台,乡镇未能及时利用大会避免佃业纠纷,有权未用,当决不决,自然是犯有失职之责。
乡镇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使得佃业双方的纠纷得以上升,双方各执一词,不肯相让。有些乡镇只是恭候县政府的决议。
1947年12月,就荡田收获量,八字乡佃业之间又起纠纷。虽然县政府下令荡田粮赋额按七折缴纳。但自1946年该乡农会就明确荡田按荡粮成数纳租。该年收获量每亩核为一石,依照减租规定,业主应得三斗七升五合,扣去一斗九升一合国家赋税,业主每亩净得一斗八升四合。荡粮赋额按七折计算,则上缴国家赋税为一斗三升三合七勺,计减少五升七合三勺。但每亩荡田少收的五升七合三勺,究竟为谁所有,成为佃业双方争执的焦点。佃农们认为,少收的赋米应归佃农所有。业主则相反,认为按照上述算法,扣去代缴赋米一斗三升三合八勺,业主们每亩应净得二斗四升一合二勺。乡长提出折衷的办法,将少收的赋米由佃业双方平分,则业主们每亩净得二斗一升二合六勺。如此一来,业主们荡粮的利润比一般田地还多,佃农自然不愿意,坚持按七折缴租。
政府的优惠到底要归谁?1948年关于增收区域收益的争执又将该问题抛出。1948年8月20日,县参议会作了明示,布告各指定增产区域,增产收获利益应划归佃农,不列入缴租标准。增产区域的成本投入均由佃农负担,如果夺取佃农的增产收益,无疑会挫伤佃农生产的积极性。在县参议会第一届第八次大会及第六次会议,刘先正算了一笔帐:
该年度农行贷放豆饼每张共市价相仿值米二斗五升之数,普遍每亩施肥一张。如果效果特别好的话,可能增产收获四斗米,除去二斗五升加息外,还得扣除因增产而加工本一共约七升左右,剩余不到八升。如果依照土地法1946年计算,四斗米须还租一斗五升,明显是亏损到增产的成本。如果增加的收获(是否一定增加还不知)一并列入收获量标准中议订租额,反受业主的无端剥削。再者,增产区的每一农户,不能尽其耕种的田亩全部获得政府贷放,则不受贷的田亩变法随着增产的美名,无得到增产的实际而增加还租的顾虑,则政府的厚意受惠了业主,反亏损了佃农。
综上所述,纠纷的产生均从佃业双方商讨收获量产生,当政府把“二五减租”通过组织贯彻到乡村时,佃业双方的关系得以完全改观,从原来业主定租,到佃农、业主面对面争执,乡村秩序重新调整。如果乡镇农会、乡镇公所对佃业纠纷不能定夺时,纠纷将会升级由县府解决,县府的裁决将再次把政府的法规、意图重新深入乡村,乡村秩序得以再次整合。
三、纠纷调解:情与理
学界对乡村纠纷的研究,如寺田浩明所说,不能触及纠纷的普遍性特点;缘于所用资料主要是上诉至县府一级的纠纷。本人前文所述升级的纠纷,虽然也活生生地再现了乡镇之间的争执,但最终纠纷的解决还是受县政府的影响,即也要遵循政府法规,从中无法看出乡村内部秩序的整合过程。
在1945年后的浙江省嘉兴地区,乡镇一级确定了由乡镇民代表大会决议全镇事务,对乡镇公所形成制衡关系。保民大会上选举出的乡镇民代表组成乡镇民代表大会,在乡镇民代表大会上选举或推选公正人士组成乡镇调解委员会,由调解委员处理乡镇日常纠纷。[1]
乡村佃业之间的纠纷,一般先在保内由保长或保内德高望重的人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未成功,则佃业中一方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由调解委员会召集双方调解。乡镇调解委员会处理的纠纷,只是保内未能解决的案例,不能代表全部,但与县级调解相比较,前者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嘉善县干窑镇十三保的俞星元家,拥有水田三亩,租用一凌姓田主的田地十亩。后因无力耕种,其父俞顺庆将十三亩地租与张顺福,张顺福又转租与庞三和。1931年,庞三和直接向俞顺庆顶种,交顶首20元,立下收据,但没有租票。关于租期,俞星元称当时言定为2年,期满后庞三和托人续租,议定俞家要自种时可收回田地;庞三和则称租期为12年。1945、1946年俞星元两次向庞三和要求收回田地。经保长从中调解,商定由俞星元偿还庞三和20元的顶首,折合糙米四石。当初言定,十三亩租田的租米,七亩交与俞星元,六亩交与凌姓田主。经保长调解,俞星元免收当年七亩的租米。后因庞三和不愿意交出田地,俞星元向镇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
1946年12月30日,镇调解委员会的董鹏飞、沈元贞、戴文珍、朱春年、管为甬等五人,在镇公所调解俞星元和庞三和之间的纠纷。经了解,庞三和拒交田地,是因为已在田内种植草子(注:草子,即紫云英等,浙江省农民习惯于冬季在田内种植草子,作来年肥料用。),不愿意白白将田地连同草子一齐交还,提出再续种一年。虽然俞星元和庞三和论述有所差异,如租期,两人的说辞相差10年,由于没有租票,无法判定谁是谁非。但是很显然,至1943年租期已满。因此镇调解委员会认可了俞星元的撤佃权,规定撤田期限为1947年芒种节。鉴于庞三和多年垦种和田内已种植草子的事实,镇调解委员会提出由俞星元贴还庞三和十一石糙米,包括顶首折米及垦荒酬劳。(注:嘉善县档案馆:285-1-70。)
该案例事实比较清楚,佃业双方争议的只不过是撤佃的时间早晚和补偿费用问题。镇调解委员会只是据情理,适当延长了撤田期限,并增加了赔偿费,最后双方表示接受调解结果。
在此案例中,俞星元将自家田和租借田转租与张顺福,而张顺福又转租与庞三和,田地耕种权一再易手。在浙江省,田地有田面权和田底权之分,业主将田地租与佃农时,佃农则有耕种田地、缴纳田租的义务,业主收取田租。佃农可将拥有田面权转租与他人,有顶田票或赁田票的称呼,(注:施沛生:《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二编物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99页。)即庞三和顶种时,要交付俞星元顶首。
按照嘉善县的惯例,佃农将田面权出让与他人时,需取得业主的同意,业主和佃农分别收取“大租”和“小租”。(注:《嘉善县志》(第五编经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91页。)但是佃农们私下将田面权抵出,以从中获取差额利润的情况在各地均非常普遍,由此往往引发佃权纠纷。(注:施沛生:《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二编物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99-400页。)
嘉善县大云乡第十一保朱来福将六亩田租与同保沈阿虎,但后者又将田顶与同保叶永根耕种。经乡调解委员会调解,由叶永根直接向朱来福进租票,朱来福欠缴1942和1943年田租,由叶永根缴付。同时叶永根与沈阿虎的顶立关系,确认有效。照原定七年的顶期,朱来福将田租与叶永根,七年后才能收回田面权。
在此,沈阿虎私自出顶,丧失了田面权。同保内浦阿三,于1946年冬将田私自转抵给王金宝,业主张康祺认为其为“盗卖行为”。1947年5月11日,经乡调解委员会调解,浦阿三和王金宝协同向张康祺订立租约。
在订立租约时,业主往往预先申明,佃农转租要告知业主。嘉善县西塘镇调解委员在处理业主陆咏梅与佃农宋苏氏欠租纠纷时,即指出如果佃农出让田面权,应事先征得业主陆咏梅同意。
业主可以分别出卖田底权与田面权,即如前所述买得田底权的田主,享有收租的权利;买得田面权的佃农可以租种,也可出卖。1947年3月12日,经嘉善县西塘镇调解委员会调解,田主范寿林将田底权出卖于吴德金,吴德金须按时缴租,如果欠租一年即收回,而郑书庭从业主处获得田面权。(注:嘉善县档案馆:255-1-70。)
乡村田地之间的买卖,“一田二主”和永佃权的概念和实际意义并不一致。(注:许多学者对该方面作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因其太多,不一一列举,仅在下面讨论时会说明。)田地之间的买卖,在浙江省桐乡县有大卖与小卖之分,大卖即所有权转移,小卖即永佃权转移。在买卖时注明这两种情况全买断时,买主即拥有了土地的全部所有权,可以自由出卖或出租。如果不注明,则为大卖,即买主拥有田底权,是为田主;业主拥有永佃权,租票上写明若有欠租情形,业主可以随时收田,田主只有收租的权限。佃农可从业主处获得永佃权,可以自由出卖或转租他人,此为小卖。佃农将永佃权视为祖权,世代为子孙所享受,该田称为客田。佃农再将田转租与他人,则田主收租时的佃农与业主租票上的佃农往往不是一人。(注:施沛生:《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二编物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11-312页。)基于此间几经转手,佃权不清,佃农们争夺永佃权的事情也常常发生。
嘉善县大云乡第十保徐汤氏,从孙姓业主租种田地九亩,于1943年将田转租于张贵昌,订立五年的租约。1946年张贵昌从业主处买得佃权。1947年期满,徐汤氏想收回时,张贵昌不肯。经调解,除了付给徐汤氏顶首费外,张贵昌还以糙米二石,取得了永佃权,而张贵昌与徐汤氏的转租关系亦即结束。
1946年,大云乡第三保张大观从业主顾少蓉处买得田底权,立有书契。由于其自1935年起一直租种顾少蓉田地,因此1947年继续耕种。但春耕之时,前佃农沈富金却指出其拥有永佃权,是为祖业。张大观请业主为其作证,但业主无从调和。因为沈富金已脱佃12年,调解委员会调出由张大观交给沈富金糙米一石,作为收回永佃权的补偿。沈富金不接受调解结果,因此调解未成立。
佃农将永佃权视为祖业,轻易不会放弃,这就使得佃权纠纷繁杂异常,但也有放弃永佃权的情况。嘉善县大云乡七保顾金成,1944年从蒋炳先处转顶了徐庆华的二十一亩水田,租期为5年。1947年4月7日,顾金成正在田中进行春耕,徐庆华突然将其铁搭夺去。顾金成以徐庆华妨害佃农生产,申请调解;徐庆华以蒋炳先拖欠1945、1946年两年田租要求收回佃权。经调解,徐庆华愿意豁免1945年至1947年的田租,由顾金成耕种至1948年芒种时收回,蒋炳先表示放弃永佃权。同保的包顺昌租种谢雪纯田地长达8年,后因租佃纠纷由乡调解委员会调解,谢雪纯放弃永佃权与包顺昌。(注:嘉善县档案馆:285-1-70。)
乡镇调解委员会也仅属于民间调解机构的性质,和传统乡村调解人的权限一致,他们只能按惯例或利用个人威望进行调解。调解笔录显现的更多地是事实和情理层面,而缺少法律的概念和判断。
虽然法律对永佃权的情况也有明确规定,但基于各地情况的复杂性,正如黄宗智所指出,国民党立法在永佃权的问题部分地反对习俗,如永佃权不得将土地出租与他人,(注:赵晓力也指出法律在该方面往往犯了指鹿为马的错误。参见(美)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赵晓力:《中国近代农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与国家法》,《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第491页。)而上面所述蒋炳先即将永佃权转给顾金成。正因为法律条文不能涵盖生活和事实的丰富性,乡村佃业纠纷调解时,就不可能完全依律进行。
同时,由于乡镇调解委员会只是民间调解组织,没有司法权限。即使当事人接到开会通知而不愿出席时,乡镇调解委员会不能强迫当事人参加(注:嘉善县地方法院指示,出现此种情况时,被害人可以向法院提出上诉。嘉善县档案馆:285-1-70。),更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结果。
1945年春季,嘉兴县新塍镇第十保朱瑞元和朱金松租借本保钱东华九亩水田,包田费白米四石五斗,租借时钱东华先付一石一斗,后扣掉前一年的租米一石五斗,余一石九斗言定等1946年农田作业如耕耘施肥等完毕后清算。但当朱瑞元和朱金松向钱东华清算时,钱东华称还需扣除当年的租米。当时田间作物尚未成熟,朱瑞元和朱金松等急需工钱度日,而县政府也未核定缴租数额,“骇异之下”,他们向镇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1945年8月14日下午三点,镇调解委员会召集双方进行调解。朱瑞元和朱金松均到场,而钱东华由母亲钱陶氏代替出席。调解委员会询问情形时,虽然没有证人和租票等证据,双方对事实经过并无太大的分歧,田主对于预收地租也供认不讳。
除了担保金,耕地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这在《土地法》里有明确规定。(注: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14),《土地法》第四章第120条,黄山书社,1999年,第406页。)如前所述,各乡镇农会也宣布要取消预租。这在乡村佃业双方之间,至少调解委员看来,是熟知的道理。因此,调解委员告知钱陶氏,预收当年田租是不对的,并指出新谷尚未成熟,要体恤承租人的生活困难,劝其早点结算。
在此,调解委员没有详细解释关于取消预租的相关法律条文,而是以“这个理由是不对的”直接作了道理上的判断,这在乡村纠纷调解过程中应是常情。乡村调解,更多借助于调解人的威望和地位,调解人根据乡村惯例或者了解的法规,对当事人进行道理上的规劝。因此,当钱陶氏表示要等到新谷上场时再结算时,调解委员用了“我劝你”这样的话语。当劝解钱陶氏不成,调解委员无权强制其执行,而是采用了折衷的作法,反过来劝说承租人。(注:嘉善县档案馆:286-8-121。)
最终双方均不愿意让步,调解不成立。如果出现双方不接受调解结果或者调解不成立的情况,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或相关机关上诉。
嘉兴市余贤镇第十保的朱大观,租种本镇叶韫玉的九亩水田、八亩桑田,连同三间平屋和竹园,约定每年田租为六石米,地租为五斗米。1947年2月4日,叶韫玉以朱大观屡次拖欠田租,向镇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要求追还1946年度的租米并将田地于秋收后收回自种。朱大观称已于该月12日送四石糙米交于叶韫玉,但叶韫玉要撤佃,因此拒不接受。1947年3月13日,经镇调解委员会调解,朱大观交纳1946年度租米四石八斗一升,允许种至1949年秋收后交还业主。同月18日,朱大观先缴纳四石至调解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家,由其代交。叶韫玉表示一定要撤佃,拒收朱大观缴的租米。朱大观也不愿将租米带回,并与保长成福祥一同至镇公所,言明四石租米先交由镇公所保管。
1947年3月20日,叶韫玉向嘉兴县佃业仲裁委员会再次提出撤佃申请,并指出镇调解委员会的笔录不实:其一,调解时讲明田租部分为四石,笔录写为四石八斗一升;其二,允许朱大观再租种一年,即1947年秋收后撤佃。笔录写为1949年,应是笔误(注:据笔者判断,乡镇公所上交的调解笔录记为,允许朱大观再续种一年,即三十八年(1949年),并没有涂改的痕迹;显然应该是笔误。)(民国三十六年误为三十八年)。
根据《浙江省佃业纠纷暂行办法》规定和《土地法》的减租规定,由欠租而发生的业主撤佃纠纷,由佃业仲裁委员会仲裁。佃业仲裁委员会召集双方了解情况,叶韫玉却不能自圆其说。
问:朱大观欠你几何租米?
叶韫玉:从(1937年)八·一三以返,每年零散交租,至多一二石,共欠多少无从记得。
问:为什么调解笔录只谈欠三十五年(1946年)一年租米?
叶韫玉:我不识字,不知道。
问:他欠你租米,有帐否?
答:没有帐。
问:三五年你有没有收到过米?
答:三五年已收二石米。
既然叶韫玉称自己不识字,申请书中却提出镇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笔录有误。即使叶韫玉不识字确为事实,申请是由别人代笔的,但申请书与他本人的陈述却不一致,矛盾之处非常明显。再次询问时,他又否认了上述陈述。
问:叶韫玉,三五年,你到底收租米多少?
答:实在没有收过,刚才说收过二石,是三四年(1945年)的。
相比之下,而朱大观的陈述颇让人信服。
问:你每年租还清么?
答:每年都还清的。
问:三五年租米有无还过?
答:三五年第一次还三石,他不收,因他要十石零五斗。经镇公所调解还租米四石八斗一升,
我已在前两月(即三月)十八日送过四石送到郑永年家,请求代交。
问:还有八斗一升有无缴过?
答:郑永年说代向田主说情,到今年早稻收取时交清。
郑永年坚持撤佃因此拒收租米。根据《浙江省佃农“二五减租”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第三款,声明要撤佃自种的业主,须以耕种为主要方式维持一家人生活,如果租金是贴补家庭生活之用而不是主要收入,则不符合撤佃自种的条件。
问:还有他种收入过活么?
叶韫玉:我做衣服女工度日。
问:你说收回自耕,是否确实自己耕种?
叶韫玉:我自己种不来,雇人耕种,如若租出仍租与朱大观。
问:朱大观,你另外有田种么?家里有几人?
朱大观:我另外没有田种,家里有妻、女、女婿、外甥女,连自己五人。女婿是入赘的,我田是要种的。
问:叶韫玉,你家里一共有几人?
叶韫玉:我自已及小女,共二人。(注:嘉兴市档案馆:307-8-71。)
如上所述,叶韫玉与朱大观的家庭条件相比,叶韫玉不以耕种为生,不符合撤佃条件。相比之下,朱大观更需要田种,况且叶韫玉又表示以后仍要把田租与朱大观,即收回了撤佃的要求。佃业仲裁委员会自然驳回叶韫玉的撤佃要求,但从法律上,仍然保留了叶韫玉再次申请复裁的权利。
从佃业仲裁委员会的仲裁书来看,其对事实的判断,每一步都要寻找法律依据。乡镇调解委员会调解却是根据公正或者情理来解决纠纷,不拘泥于法律,更多倾向于固有的习俗。
黄宗智指出,正是因为国民党的产权理论认为,是供需而不是劳动投入决定乡村交易市场,收益应归承担风险的不动产投资商而不是种田人;才使得其在立法上拒绝田面权,用永佃权确定地租。[2](P110)但如前所述,“二五减租”法规本身只是固定了缴租标准,而未确定缴租数量,风险由佃业双方共同承担。虽然国民党立法不能涵盖佃业关系的丰富内容,当纠纷上诉至县时,县政府根据佃业之间这样简单的分类,即可依法判决。但是大多数纠纷只限于乡镇调解委员会这一民间组织来调解,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乡镇调解委员会委员由乡镇之中具有一定威权或者地位的人士担任,基于乡镇调解委员会本身只是一个民间调解组织,不具备司法机关的权力,其调解方式更贴近于民间日常生活纠纷的常态。从上述调解笔录可看,调解委员虽然把法规寓于调解结果,但其调解基本是从情理的方式劝告当事人。这在不知不觉中,将法规灌输于乡村。调解委员本人这种潜意识的影响,当事人在申请调解时也就会运用法规术语,如顾金成认为业主妨害佃农生产。乡间的秩序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中得以整合。
四、规范化的秩序
费孝通指出,传统社会中,乡村社会关系是从个人逐个推出的差序格局,[3](P28)即绅治的乡村社会更注重于以道德威望维持秩序。当中华民国政府将国家权力深入乡村时,乡村秩序得以重建,政府法规被纳入其中。如前所述,政府推行“二五减租”,佃农借助这个法律平台,改变了传统上由业主控制租额的局面。佃业双方由面对面的争执商议收获量,到矛盾激化时集体对抗,寻找县级政府组织的法律支持。
基于乡村社会秩序的传统,法律不可能完全由条文直接移植到丰富的乡村生活中。这就出现了乡镇调解委员会中调解时,还是以情理服人,做出合乎法律或习俗的调解。1946年嘉善县西塘镇第一次镇民代表会议上,县政府委派社会科科长孙蝉鸣与会指导。孙告诫镇民代表:“请各位代表为事须顾到情理法做去,就是政府也按情理法做的。本人认为,情理法三者是联贯而不可分离的”。(注:嘉善县档案馆:286-8-93。)
相对于乡村内部组织来说,国家法是外来物,它或承认乡村内部某些秩序的合理性,或引发内部秩序的冲突,如“二五减租”法规。该法虽然不能涵盖乡村租佃形式的多样性,但正是由于其把佃农和业主之间的关系简单化,在佃业双方发生较大冲突时,法律才有可操作性的空间。固然如寺田浩明所述,无论官或民,在习惯法书的编纂、裁判的援用和判例法的形成上,都不具有足够的成文化和操作化,而是始终在社会中浮动[4]。不可忽视的是,正是因为存在解决冲突的规范,无冲突的秩序才可以维持。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乡村秩序在发生改变。调解委员会委员拥有传统乡村中的地位和威望,其运用传统的调解方式,贯行国家法的理念,这就使得整合乡村秩序的过程在缓慢进行着。
规范而不是法律规则,是乡村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5](P63)将法律制度和观念简单地移植于乡村反而会适得其反(注:李曙光指出,直接移植国外的法律观念和制度容易落入“东施效颦”式的简单模仿陷阱。李曙光《中国法律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探讨》,载于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现代化——'93中国法律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164页。),根本改变或者借助其内部力量对乡村秩序进行整合,即对乡村秩序不断进行新的规范化过程,现代国家才能实现将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相统一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