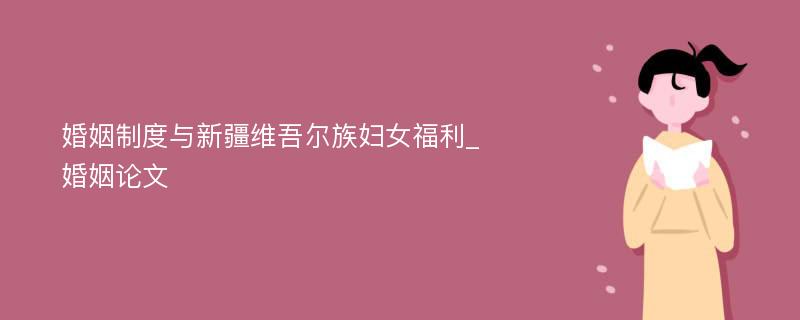
新疆维吾尔族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福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利论文,妇女论文,婚姻论文,制度论文,新疆维吾尔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80年每千人口就有4.02对夫妻离婚,是全国平均数的11.5倍,远高于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而居于首位。1999年与全国的差距已明显缩小,但粗离婚率仍是全国平均数的约3.5倍,依然位居第一。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97%的和田地区,1999年的离婚数是结婚数的48.5%,每千人口有6.29对夫妇离婚,即粗离婚率高达6.29‰,在世界上也居前列(见表1.2)。对和田市拉斯奎镇巴什拉斯奎村1325位已婚男女的统计表明,曾离过婚的占91.1%。其中,离婚1次的为75.1%,离婚2次的占6.1%,离婚3次以上的为2.6%。所深入访谈的有离婚经历的40多位男女中,男性平均结婚3.8次,女性为2.0次,最多的一位曾结过12次婚(其中3次是与前妻复婚)。由于社会的刻板印象往往以为经济发达、观念现代开放的大城市离婚率较高,因此,维吾尔族的特高离婚率既出乎常人的意料之外,也引起学术界的浓厚兴趣。本研究将全面收集该地区的有关资料,并通过对和田市法院离婚案及其下属拉斯奎镇巴什拉斯奎村的实地调查,从伊斯兰教的婚姻制度层面来分析该地区的离婚状况与女性福利的关系。
(一)早婚制:女孩不堪忍受的婚姻重负
伊斯兰教认为女孩子天生孱弱,无力保护自己,早早出嫁可以避免婚前失贞。于是,维吾尔族普遍流行“一帽子打不倒就结婚”的习俗,假如女孩在月经初潮前还未选定婆家,本人和家庭都将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维吾尔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在全国百万以上人口各民族中为最低,仅19.4岁(包括城市)。不少勉强维持温饱的农村家庭,早早打发姑娘出嫁,也是减轻女方家经济压力的一条捷径。我们对和田地区离婚案的抽样调查和访谈结果也显示,即使是1990年以后,初婚的女性不到法定年龄的仍占25%(男性为8%)。国外不少研究都证实早婚将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如导致青少年失学、高失业率、低收入、高生育率、婚姻满意度低以及离婚率高(埃尔伍德·卡尔森,1979;罗伯特·舍恩,1975;克里斯汀·A·穆尔等,1981;加里·R·李,1977)。我们在和田农村对当事人的访谈也表明,十四、五岁的未成年女孩对婚姻的权利和义务缺乏心理准备,往往难以适应婚后的多重角色的转换,尤其是女孩的辍学、新婚的性恐惧以及难以承受多子女家庭繁重的劳务和协调婆媳关系,从而引发夫妻裂痕。早婚也使父母控制子女婚事成为必然,而女性提前进入婚姻围城的比重更高,她们的婚姻自由度更低,在夫家所遭遇和经历的痛苦也更甚。
(二)内婚制:影响女性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
维吾尔族不仅严格禁止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通婚,并实行民族内婚制,尤其是和田村民极少有与汉族或不信伊斯兰教者通婚的。同时维吾尔人还具有亲邻内婚制的风习,即与近亲及近邻婚配。据对伊干其乡302对登记结婚夫妻的统计,双方同乡的占56%,该地区近些年仅有两例是维汉通婚(李晓霞,1993)。据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535对夫妇的调查,维吾尔族近亲结婚占8.23%,1977年后更多,为10.76%。平均近交系数为所调查的5个少数民族之最。异族通婚离仅占2.47%(艾琼华等,1985)。我们对巴什拉斯奎村40多位离过婚的男女的访谈也显示,近亲结婚占15%左右,而且都由父母包办,家长常常对子女说是为了家里的财产不外流,或认为从小一起长大可靠,或看中男方会做买卖、经济条件好等等。当地人还认为邻里、同村、近乡的小伙姑娘知根知底更可靠、放心,而对外乡、外地人缺乏信任感。拉斯奎镇1998年107对结婚登记夫妇为同乡镇的高达77.6%(其中同村占31.3%)。
通婚范围狭窄和近亲结婚较多,加上早婚多育以及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对维吾尔族的人口素质尤其是妇女及其子女的身心健康不无损害,也加剧了婚姻的不稳定性,减少了妇女的婚姻收益。有调查表明,近亲结婚所生子女7岁前的死亡率、先天性生理缺陷及遗传性疾病发生率均明显高于非近亲结婚对照组(艾琼华等,1985)。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不少女性因近亲结婚造成不育或子女低能、残疾或由于早婚多育、承担繁重劳务等身患疾病,为丈夫所嫌弃而离异。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均显示,新疆的男性老年人口明显多于女性,其中少数民族老年人口的男性比例更高,且维吾尔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明显低于汉族,女性甚至低于男性(李小霞,1994;黄荣清,1993)。女性健康状况较差还在于当地的生活质量和卫生保健福利水平低,一些丈夫宁愿另觅新欢也不愿为妻子的健康投资(仅指医疗和照料而言)。
(三)低投入经营制:女性婚姻的低收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认为,人们结婚的目的在于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按照经济分析框架,当事人(包括其父母)在步入婚姻前往往会对自己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经济“核算”,力图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尽管这种趋利避害的权衡常常是潜意识的,也未必都计算得很精确(社会交换本身不如经济交换那样具有确定性)。W·古德早在《家庭》一书中也曾指出:“人们不会为一桩经不起长期考验的婚姻投入很多资本”。维吾尔民族简单、便捷的婚姻建立和终止的风习,无疑将使当事人减少对婚姻的投资,而结婚和离婚成本的低廉,也导致婚姻离散趋势的居高不下。其婚姻投入少、成本低主要表现在:
1.选偶成本低。维吾尔人的初婚由亲朋介绍、父母做主并很快步入洞房的较多,而再婚双方自己认识的明显较多。但即使是双方自己结识,也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偶发性较高的特征,即大多是在偶然的场合,如在集市交易、一方到另一方的加工处磨面或到其铺子里买东西、理发等,或在朋友处邂逅相遇并很快同居结婚。据对和田市法院1998年100例离婚案的统计,男女双方当初萍水相逢、偶尔结识的高达60%以上,而其他地区最高不到5%;此外,样本夫妻平均恋爱时间不到半年,为各地区之最短。大多数人从离异到再次结婚的间隔时间也较短,我们所访谈的对象两年内再婚的占2/3(其中一年内达65%,最短的不到1个月)。
2.结婚费用省。男方的彩礼主要是衣料和首饰,女方陪送的大都是床上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随着年代的推移,男方彩礼中的衣服已从单件到多件套(按被访者的说法是“冬夏替换”)、饰物也从头巾到耳环、戒指、项链(项链很少或按被访者的说法“不是真金的”),但即使加上婚礼酒宴花费也不过一、二千元,女方只花几百元即可,再婚的费用则更少。如一男子初婚时给女方买了一件呢上装,离婚时又要了回来并作为再婚对象的礼物,第三次结婚再如法炮制。一女性嫁到男方后,婆婆和小姑将结婚时给她买的衣服都藏了起来,丈夫拖了很长时间才再给她买,但买后又给她们藏起来。她没有衣服穿就回了娘家,丈夫既没有再给她买衣服,也没有来接她,结果就分了手。由于结婚的直接成本投入较少,离婚时的沮丧感也低,婚姻的稳定性也相对较差。
3.婚后投资少。由于婚前相互了解少、感情基础差,维吾尔人的夫妻关系十分脆弱,婚姻收益也较多地停留在生儿育女和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上。不少当事人在婚姻生活和家庭关系出现一般性挫折或矛盾时,就会考虑分手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克服、解决。我们可以从当事人下述的离婚理由中了解其低投入、低风险和低收益的婚姻经营理念:“怀孕时我反应很大,身体不好,丈夫不愿照顾就提出离婚”;“我们夫妻感情还不错,但婆婆和小姑把结婚时给我的衣服藏起来,丈夫说给买却拖了好长时间,买了后又被她们藏起来,我没有衣服穿就回娘家了。但住了一年,丈夫也没来接我”;“女方不会做家务,也不会干农活,我说了3次‘塔拉克’就分了手。现在我很后悔,想和妻子和好,但岳父不愿意”;“我上夜班时,婆婆不让我白天睡觉而让我干活,丈夫虽待我不错但仍顺从父母,要我辞去工作在家做家务。我想丈夫离了还可以再找,但工作辞了却再也找不到,因此宁愿离婚”;“丈夫因我与别的男人说话打了我,我回了娘家,他让人传话:‘是回来跟我过下去还是离婚’,我说‘离就离吧’”;“我离婚后两个月又找了一个,但她没有按我的要求做饭、洗衣,家务上合不来,8天后就又分了手”。众多当事人不仅谈不上对婚姻生活全身心的感情投入,甚至连起码的时间、精力、金钱和劳务都不愿投入,夫妻间缺乏起码的尊重、沟通、容忍和长期同甘共苦的诚意。据对不同地区各100个离婚案的统计,和田地区离异夫妻的婚姻延续时间为最低,平均不到5年(见表3)。而婚姻的预期回报不足也强化了当事人的低成本投入。
(四)母系庇护所:出嫁女儿的永久后方
维族女性结婚后都与男方家人共居,从妻居家庭只是特例(如男方为外地人的情况下),但却盛行回娘家生育头胎的习俗,即产妇坐月子由母亲照料,婴儿出生后也由娘家操办诸如孩子命名礼、坐摇床礼和满月礼,直到产后40天时,方由夫家带上礼物接女方和孩子回家。不仅女儿初产回娘家坐月子,而且女儿与女婿、婆家发生纠纷或离婚、丧偶等均可随时回父母家,兄嫂也少有讨嫌、冷遇之意。娘家是出嫁女儿永远的庇护所这一机制,无疑在维吾尔人的婚姻建立和解体中起着调节平衡作用。但妻方亲属支持系统的过于强大也有其负面效应,如女方动辄回娘家、一方或双方亲属过于热心的参与以及小夫妻分居时间过长等,加深了当事人双方及其家庭的隔膜。我们所访谈的一位26岁的妇女,当初就因为在为孩子举行命名礼时,母亲嫌男方带来的礼物太少(仅给女方买了一套衣服而没有给孩子买),尽管男方父母答应以后再补而要求先把媳妇、孩子领回,但其母硬是不同意,并纵容女儿离婚。而男方在众多亲戚面前丢了丑,自尊心也受到很大伤害,于是双方在各自父母的授意下无可奈何地分了手。该被访者当时仅17岁,总以为父母比自己有经验,说话有道理,因此什么也没想就顺从地说“离就离吧”。后来再婚生活不如意又离婚时,很后悔当初听家人的话,总觉得第一次婚姻才是最幸福的。我们所访谈的40多位对象中,自述因公婆或岳父母干涉而导致夫妻分手的高达40%以上。
(五)离婚自由化:妇儿权益的保障及其缺陷
维吾尔族的夫妻离合几乎不受社会限制,婚姻解体和重建司空见惯,其离婚的自由化表现在:
1.便捷的离婚方式。维吾尔人结婚由阿訇(宗教人士)主持作证,念《古兰经》并再次确认男女双方自愿结为夫妇即可。尽管《婚姻法》要求当事人需进行结婚登记,但对维吾尔人而言,宗教仪式往往比法律登记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尤其是一些未达婚龄的青年男女以及中老年再婚男女较多地以宗教仪式代替婚姻登记。他们的离婚方式也简单易行,“夫妇不和,随时皆可离异”,“夫妻若不睦,辄自离异”,“其离也,男女背相向,各前行数步,撮土洒止即离,谓之‘零乾’”(见冯家升等编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丈夫对妻子说“塔拉克”以断绝夫妻关系也无须证人作证或举行仪式。尽管目前夫妻离婚到民政部门或法院办理正式手续的已占大多数,但男方以“塔拉克”方式单方面宣布离婚的现象并未杜绝。据和田地区民政处的统计,1997年集中清理违法婚姻期间,共查处“宗教干涉婚姻”事件高达2912件,并为2929对夫妻补办了婚姻登记(1996年仅补办6件,1998年为26件),可见以宗教仪式结婚或男性用“塔拉克”离弃妻子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而无证结婚及离婚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无疑甚于男性。因此,加强婚姻管理、严格婚姻登记制度依然是一个难点和需花大力气抓的重点。
2.低廉的离婚成本。维族夫妻离婚无须举证对方的“过错”,一方提出离婚,另一方少有坚持不离的,但有过错一方往往会在财产上作些让步。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男方的离婚理由较多的是妻子不会干活、不会做家务、动辄回娘家、岳父母干涉多、不育等,女方则以丈夫酗酒、殴打本人、有外遇、性生活粗暴、经济条件差等为由提离,而婚前基础差、性格不合是双方的共同借口。约2/3的夫妻离婚时无未成年子女,多子女一般由父母分别抚养,一子女由母亲监护的略多些(尤其是年幼子女)。因男方的经济能力较强些,他们给付抚养费的较多(因当地生活水平较低,抚养费数额均不大),而女方很少承担子女抚养费。当事人很少为一方推却子女抚养责任发生纠纷。由于结婚时的彩礼和陪嫁不多,离婚时的财产纠纷也很少,大多只是由女方带走自己的衣物用品或获得少量钱款、粮食及牲畜。加上再婚费用又较低,因此,离婚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成本均不大。而继子女在再婚家庭中很少受歧视、嫌弃,也使当事人在作离婚抉择时减少了后顾之忧。
3.充分的再婚机会。维吾尔族男人宁愿选择离婚的妇女为妻,也不愿娶寡妇(社会普遍认为寡妇是克夫星,给寡妇的孩子当继父是一件晦气的事),因此,离异者再婚也较容易。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即使是初婚者在选偶时也并不在乎对方已离过婚。大量离婚男女的存在使再婚市场具有充分的交换潜力,而离异者在择偶时不象初婚者那样挑剔,也使其再婚机会递增。然而,正因为离异者再次婚姻的预期目标不高,择偶条件降低,加上社会交往范围的局限及出于对父母包办的反叛,他们与异性邂逅相识匆匆再婚的较多,由此也影响了再婚生活的质量,并使多次离婚成为普遍现象。女性往往对以往的痛苦婚姻经历心有余悸,或为了照顾年老父母,或因自己身患疾病等较少再婚,她们的平均结婚次数明显低于男性,如有研究表明,成年维吾尔人有离异经历者约在75%左右,一生中平均结婚3.5次(张立红,1988),百岁以上老年女性平均结婚2.6次,男性达5.0次(李晓霞等,1996),我们的访谈样本也显示,前者为2.0次,后者为3.8次。
4.无为的社会控制。维族人夫妻聚散的社会环境较宽松,人们一般认为婚姻失败是天意,离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平常事。被访者对我们所询问的“离婚对自己的名声、面子有无影响”的问题,大多回答“没有想过”、“这里的人经常离婚,没有人说”或“第一次离婚无所谓”,他们几乎无须考虑所谓有“舆论压力”。亲朋邻里还常怂恿或支持当事人分手,如劝说“你嫁人后反而吃不上好的,却有干不尽的家务,何苦在他家受罪呢”,“他这么懒,看他再娶什么老婆,我们帮你再找一个好的”等等。当然,一些父母在开始时也劝说儿女“能忍就忍着点”、“对方改了就好”或把回娘家寻求支持的女儿送回婆家,劝他们好好过日子。但一旦子女的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了,父母依然把孙子女、外孙子女当宝贝,并操心离异子女的再婚事宜。
社会对离婚的宽容无疑降低了当事人离婚的心理成本,离异女性少有担忧自己失去贞操或被视作“另类”而沮丧、压抑。但社会指导和控制的无所作为,也使草率结合、轻率离婚的现象难以杜绝,而离婚率的居高不下无疑对女性的身心伤害大于男性。这首先是因为失败婚姻中的男性过错者明显多于女性,如本研究样本中因丈夫暴力、擅权、酗酒、犯罪、性粗暴、无端猜疑、有外遇、不尽义务等过错致使双方感情破裂的占45%,而由于妻子总是回娘家、有外遇、不尽义务等引发婚姻危机的只占4%;其次,生活质量和卫生保健水平的低下严重损害了妇女的健康。新疆1995年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达196/10万和93‰,是全国平均数的3倍,妇女患宫颈癌、子宫脱垂等妇科病的比重是发达地区的数十倍,均位居全国前列,这无疑与维吾尔民族的早婚、多育风习以及妇女经济资源欠缺、家庭地位低下和婚姻收益不足密切相关。
由于维吾尔族聚集地区的高离婚率是伊斯兰教文化、民族风俗及其婚姻制度的演绎和延伸,因此,加强社会指导和控制的难度较大,但仍可作出一些努力,如在西部开发中重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破除婚姻陋习、弘扬先进文化。其中为增进妇女福利和婚姻收益、加强婚姻稳定性的政策性思路有:(1)严格婚姻登记制度,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婚姻登记管理人员要严肃处理,从而对早婚、包办婚、近亲婚、非法同居及男子的“塔拉克”离异特权等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2)提倡多种居住方式,如夫妇独居、从妻居等,以利于计划生育、协调家庭的代际关系和改善妇女的家庭地位;(3)提倡不同民族、地域的社会流动和融合、异性交往和沟通,以扩大通婚圈、提高人口素质,增进婚姻
表1 粗离婚率的国际比较 单位:‰
地区
美国
俄罗斯
乌克兰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荷兰
离婚率
4.33 4.513.712.89
2.86 2.622.68
年份 1996 199519971995 1996 19951997
地区
德国
匈牙利
法国日本
罗马尼亚
新加坡
韩国
离婚率
2.14 2.211.901.79 1.57 1.251.19
年份 1996 199619961997 1996 19971995
地区
波兰
泰国西班牙
南非
土耳其中国
离婚率1.02 0.900.830.76 0.47 0.96
年份 1996 199519961995 1996 1999
资料来源:各国离婚率根据1999年《联合国人口年鉴》,中国离婚率根据1999、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计算,新疆和田地区离婚率根据和田地区统计局、中级法院和民政局提供的有关数据计算。
表2 1998年中国各地区的粗离婚率 单位:‰
位次 123
4
5
6
7
8
9
地区
新疆
黑龙江
上海
吉林
辽宁
北京
青海
重庆
内蒙
离婚率 3.342.03 2.032.001.971.91
1.501.481.38
位次 10 1112 13 14 15 16 17 18
地区
天津
四川
宁夏
陕西
浙江
湖南
湖北
云南
河北
离婚率 1.311.14 1.040.960.890.88
0.820.820.81
位次
19 2021 22 23 24
25 26 27
地区
甘肃
江苏
贵州
河南
山西
山东
广东
福建
广西
离婚率 0.780.76 0.750.750.680.66 0.620.590.58
位次
28 29
30 31 平均
地区
安徽
江西
海南
西藏
全国
新疆和田
离婚率 0.580.52 0.430.370.96 6.89
资料来源:各地的离婚率根据1998、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计算,新疆和田地区的离婚率根据和田地区统计局、中级法院和民政局提供的有关数据计算。
表3 不同地区离婚者的婚姻延续时间
城
市农
村
上海 哈尔滨
厦门
广东
新疆 河北
平均值(月) 131.37 121.68 139.65 102.46 58.83
92.18
标准差(月) 70.13
76.26
95.15
64.84
56.48
64.99
样本数(个)
100 100100 100 94
98
当事人及其子女的身心健康;(4)妇联组织既要对妇女主体进行“四自”教育、灌输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又要配合教育、民政、卫生、司法等有关部门,为保障女孩义务教育入学率、婚姻自主权、平等的家庭地位以及获得基本的孕产保健和医疗福利,在反对早婚、提倡少生优育、减少家庭暴力和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中迈出更大的步伐。当然,由于维吾尔族聚集的农村社区尚处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边缘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语言不通等不利条件既制约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阻碍了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倡导和推进。因此,为提高婚姻质量、加强婚姻稳定性并增进妇女福利和婚姻收益的努力,将有待于西部开发中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