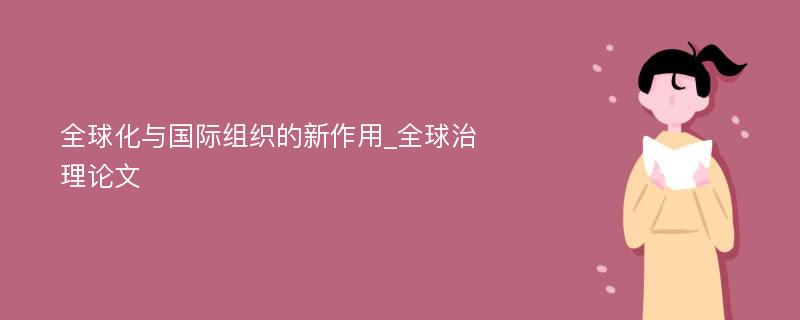
全球化与国际组织的新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组织论文,化与论文,角色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经常谈论的联合国体系通常包括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其他机构以及体系内专门机构(如WTO、IMF、世界银行等)和其他独立组织。近年来兴起的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 动,也纷纷与联合国建立起一定联系,并以联合国为核心组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网络。当今世界,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到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的“公共物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网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组织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角色似乎日趋尴尬。在发达国家看来,它们不能容忍超国家机构的权力膨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不能信任由西方掌控的机构;而在全球公民社会中的许多非政府组织眼里,国际组织几乎成为所有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替罪羊。本文根据对当代联合国体系治理模式的剖析,探讨国际组织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职能转变及其存在的问题。
国际组织的自治和权威及其与民族国家体系的互动
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兴起为国际组织尤其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有 利的契机。随着民族国家传统的政府权威在一定程度上的削弱以及国际组织的数目和种 类迅速增加,各国政府愈来愈倚重国际组织来解决安全、经济和社会问题。今天,国际 组织不仅是全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们自身也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行为体。 然而,国际组织是民族国家的竞争者还是民族国家实现目标的有用工具?对该问题的争 论实际上反映了对于国际组织的两种不同认识。第一种认识是,国际组织是一种机制, 国家借助它们从事各种活动,国际组织本身则是不具目的性的行为体。根据这种认识, 国际组织生存的依据仅在于它们能够改善和解决民族国家体系中呈现的大量问题。第二 种认识则相反,它把国际组织看作是仅次于国家的重要国际行为体,国际组织拥有独立 的国际人格和独特的利益和目标。从这种认识出发,国际组织虽然是国家建立的,但一 旦建立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在许多领域对国家主权构成挑战,实质上是国家的竞 争者。关于国际组织的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认识,同时还折射了对国际组织的两种不同研 究方法,即建立在工具理性和效率基础上的经济学方法和重点考察合法性和权力的社会 学方法。(注:See Walter W.Powell and Paul J.DiMaggio(eds.),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chap.1.)
经济学方法假设世界政治与充满寻求利益最大化个体的市场体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和市场一样,都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在市场经济中,我们需要建立一些组织来实现有效的契约,克服不完全信息和其他市场缺陷。在世界政治中,拥有主权的国家各行其是,同样需要借助国际组织来降低国家之间活动的交易费用、增进各国的共同利益并克服其他集体行动中的困境(如搭便车和囚徒困境)。显然,经济学方法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假设,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国际组织是为国家服务的,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国际组织的存在将会受到质疑。(注: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同意国际组织是国家为了方便而创设的工具。)然而,现实中的国际组织并非总与国家的意愿保持一致,相反,通常的情况是它们对国家的行为形成一定制约。那么,如果国际组织已经不是为成员国的利益服务,国家为何还要创造或继续支持它们?社会学方法则致力于解释这种现象。
在社会学家看来,经济学家忽视了国际组织拥有的权力和独立性。经济学方法过于重视组织间的竞争、交易和效率,而疏于考察组织生存的社会环境,尤其缺乏对社会规则、文化因素以及国家之外行为体的分析。社会学家主张广泛考察国际组织生存的社会背景,认为无论国际组织是否做到了它们所宣称的职能或者是否有效率,都只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而不是理论上预设的前提。组织不仅对在环境中寻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体做出反应,而且也要对决定其世界观和界定其行动方向的社会规范和文化做出反应。组织的环境能够以效率或其他竞争因素之外的原因选择或激励组织采取某些行动。例如,许多组织得到创建和支持就不是由于效率而是出于合法性和规范性的需要。它们的存在不是因为它们能做什么,而是它们是什么,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它们的象征意义。(注:W.Richard Scott,Organizations:Rational,Natural,and Open Systems,3rd e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92.)
从经济学逻辑或规制理论出发,那些把国际组织看作国家为促进自我利益而创设的众多学者认为,国际组织只是国家间互动的附带现象,它们可以通过国家间互动的性质加以理解。(注: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这些理论把国际组织简单地看作一种 空壳或者由其他行为体操纵的机制。这种机制也许可以约束国家的行为,但它本身却是 被动的。国际组织是不具目的性的政治行为体,而且从本体上来说,它们也缺少独立性。但根据一些经验性研究成果,国际组织的活动事实上并非如此。的确,国际组织受国家限制,但并非被国家所控制。国际组织也不完全是被动的。事实上,根据对欧盟的经验性研究,欧盟机构(eurocrats)的独立性就是一个例证。(注:Mark Pollack,“Delegation,Agency,and Agenda-Sett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7,51(1),pp.99—134.)对世界银行的个案研究也表明 它具有一个独立的组织文化和行动议程。最近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和重建努力的研究中, 同样可以发现联合国采取类似的独立行动而导致与其成员国的频繁冲突情形。不只是国 际组织有自己独立的行动议程,而且还可以具有多样化的行动议程。
事实上,国际组织可以拥有自己的独立和自治地位,它们可以从以下两个途径获取权力,一是它们所象征的理性—法律权威,二是它们拥有技术专长和信息优势。马克斯·韦伯最早探讨了官僚制度获取权力的途径,他的深刻观察为我们批判国际关系学者对待国际组织的态度提供了武器。理性—合法的权威预示着国际组织可以拥有独立的权威,不再受制于国家的政策和利益。如若国际组织没有独立性,那么在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或许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如果国际组织具有独立性,那么这种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很重大的效果。这方面的例证不难找到。联合国维和部队就宣称他们的权威来自他们是独立的,只是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联合国的官员也常常声称他们不是任何大国的政治工具,而是代表体现在联合国规则和决议中的国际社会利益。世界银行被普遍认识到它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影响力甚至超过它所提供的贷款,世 界银行的工作人员被认为是这个领域最好的专家,加上世界银行宣称的中立和非政治的 技术决策特征,使得它有力主导了过去50年来的全球发展政策。同样,联合国高级难民 署(UNHCR)拥有的“专家”地位和法律权威,也使得它们能够在不与难民甚至国家商量 的情况下就可以决定几十万难民的安排。(注:Liisa Malkki,“Speechless Emissaries:Refugees,Humanitarianism,and Dehistoricization”,Cultural Anthropology,1996,11(3),pp.377—404.)
国际组织在世界上拥有自治和权威,它们利用这种地位主要发挥了如下作用:①为世界分门别类,创造行为体和各种行为的新类别。例如联合国高级难民署对难民的划分,以及世界银行对农民、日劳动者等的划分;②确定社会化世界的意义。例如世界银行对发展的界定如乡村发展、基本需求和结构调整、冷战后对安全含义的重新界定;③在全球范围内阐述和推广新的规范和原则。所有这些权利都来自国际组织对知识的掌握。国际组织建立了规则和规范后,就要在全球推广它们。例如非殖民化。这样的例子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也很常见,如它们致力于把发达国家的市场规则推广到了发展中世界。
冷战结束后,开启了国际组织传播其规则和规范的新高潮,首先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扩,开始向东欧国家反复灌输“现代”的价值和规范。(注:William Perry,“Defense in an Age of Hope”,Foreign Affairs,1996,75(6),pp.64—79.)欧洲重建 与开发银行也加入其中,向东欧国家传播民主和私营企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 也同时大踏步地试图建立一个以民主和人权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共同体。而且一旦民主和 人权与国际和平与安全联系在一起,那么国际与国内事务的治理之间的界限就被抹杀了 ,这样国际组织几乎就握有以合法和权威的面目在任何地方进行干预的特许证。(注:David Keen,The Benefits of Famine:A Political Economy of Famine and Relief in Southwestern Sudan,1983—89,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 4.)
值得重视的是,颇多西方学者的著述,都把全球化将削弱国家的权力作为一个预设的 前提,有的甚至完全不顾及今日国际体系的现实状况,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原则和构 想。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对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不负责任的理论方法。在第三世界 的许多地区,国家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有的尚未完成建国任务,如巴勒斯坦,更 多的国家则在许多方面亟待巩固提高。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国家权威更为重要。 世界银行是最早提出治理概念的国际组织。在1989年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报告《从危 机走向持续增长》中,世界银行认为非洲国家更加需要的不是资金、技术,而是善治。 在某种意义上,当世界大部分地区因为全球危机和全球问题而出现了“全球治理危机” 的时候,非洲国家面临的更多挑战来自国家的危机。不难想象,盲目推行这些不切实际 的原则和构想,将对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正如克拉斯纳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性规则的最重大的影响将是:它们会改变国家行使主权的范围和空间,但不会造成政治生活原则的彻底改变,即不会导致国家主权的消亡。”(注:Stephen D.Krasner,“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World Politics,1991,43(3),pp.336—66.)全 球化世界中的国际组织角色调整亦当如是观。全球治理是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力量和 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但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会消失。国家组织应当朝着为国家的竞争提 供一个公平的法律环境的方向努力,并通过该法律环境调节个体、国家、全球公民社会 之间的关系。尽管全球化的继续发展将需要一个全新的制度体系,现有的国际组织无疑 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它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实 质性变化。
主权治理体系及其缺陷
为了理解人类社会组织变化的规律,探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管理目标和适当模式,国外不少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和划分国际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阶段。克雷格·墨菲(Craig Murphy)详细考察了自1850年以来世界组织的历史沿革。他认为自1850年以来, 这些活动都来自于自由社会力量的跨社会联盟促使世界组织在工业主义的连续周期中推 动领先工业的能力,而且世界组织在任一时期都为帮助开辟一个范围更广的工业资本主 义新周期创造了条件。(注:[美]马丁·休伊森、蒂莫西·辛克莱:《全球治理理论的 兴起》[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在英国学者克里斯琴·罗伊斯—斯 米特(Christian Reus-Smit)看来,过去的千年已经出现了异族统治、宗主统治(殖民统 治)和主权治理三种体系,它们都有不同的制度框架和机构设置。(注:Christian Reus-Smit,“Changing Patterns of Governance:From Absolutism to Global Multilateralism”,in Paolini,Albert et al,Between Sovereignty and Global Governance,Macmillan,London,1998,p.2.)15世纪之前,欧洲普遍处于中世纪的统治体 系之下。约翰·鲁杰(John Ruggie)称之为“他治”,即权威被分配给从封建主到罗马 教皇等众多成员,以边界的形式划分他们的领地,但领地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混乱。( 注:John Gerard Ruggie,“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World Politics,Vol.35,No.2(January 1983),p.2 74.)16和17世纪期间,伴随着中央集权化、边界明确化和等级制度的强化,中世纪的治 理体系为主权国家的宗主统治体系(殖民体系)所取代。直到20世纪中期,占世界人口多 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都处于宗主统治的治理体系之下。主权治理体系只是在最近 50年中——随着欧洲殖民帝国的崩溃和在亚非产生大量新独立国家——才囊括全球。这 一过程于19世纪中期开始“起飞”,在最近50年中得到了强化。最终的结果是联合国成 为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治理制度的核心。根据罗伊斯—斯米特视野开阔的历史划分,联合 国体系的确立显然是国际治理的一次飞跃,而且自联合国诞生之日起即形成了全球治理 模式的雏形。换言之,我们近年来才开始谈论的全球治理模式,早在50多年前就已出现 。全球治理不是我们正在构想的未来世界治理模式,而是我们早已生活其中、有着严格 历史依据的现实状态。
然而,以联合国为标识的治理体系并不等同于全球治理。联合国等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大都是酝酿和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宗旨是通过营建政府间合作机制来维持和平和促进繁荣。大国创建联合国的初衷,并非想得到一个对世界事务进行广泛管 理的超国家机构,而是要其为主权国家服务。半个世纪以来,联合国主要执行的还是协助或便利主要国家维护国际和平、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等传统职能。例如通过国家之间签署的条约和召开的国际会议,联合国分配国际社会中对各国政府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裁军、发展和国际安全。(注:Robert W.Cox,“The Future World Order and the UN System”,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2,Peace Research Institute,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1997,p.20.)在联合国大会中,民族国家无论大小拥有平等的投票权,在服从联合国宪章的前提下,相对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在重大问题上,联合国的作用往往是提供一个世界性审议论坛,或者为传统的双边外交提供一个多边协调的舞台。质言之,联合国体系是一种主权国家享有特权地位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尽管全球治理并不拒斥国家与国家间的治理,但当前人们对全球治理的理解显然与联合国体系确立的治理模式有着明显的反差。
联合国体系几乎完全是在国家层面上展开的社会正义目标和实践,已然不能适应世界日益多元的诉求。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体系在其身份和代表性上都遇到了挑战,特别是面对新的全球挑战,如在制止国内冲突、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和管理跨国公司等方面,它们的作用和表现不尽如人意。1999年3月,北约为制止科索沃塞族违反人权的行为,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北约显然侵犯了一个主权的国家领土完整,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尽管北约领导人声称这是对阿族科索沃人权的正当保护,但战争的实际进程证明北约既没能保护阿族科索沃人的人权,又伤害了塞 族和阿族的基本人权。显然,虽然北约采取行动的动机不错,但其结果却适得其反。而 且从根本上来说,北约的介入突破了国家主义的全球体系,不符合战后国际社会的行为 规范,本质上仍然是非法的。
从金融到环境治理的关键性领域,联合国体系的治理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管理缺陷”。(注:转引自[英]托尼·麦克格鲁:《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现有的多边经济机构一般以促进经济价值为目标,例如固定汇率,商品、服务与生产因素的自由交换,而缺乏直接处理世界性问题(例如能源、环保、海洋问题、有组织犯罪等)的组织机构,也缺少调节南北关系,包括世界就业政策、财富分配形式、扩大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以及机会平等(教育与培训)的国际组织。世贸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认为可以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驾驭全球化进程,进而逐步解决人权和环境问题为全体人民服务。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几乎无能为力,这就难怪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涌上街头,试图关闭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和世界银行华盛顿会议。抗议者们认为这些机构缺少公正,没有认真考虑“人民”的利益、福利和基本权利。
罗伊斯—斯米特这种国家间政策协调的分析方法,把以领土为原则的民族国家体系混同为全球治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无法克服“市场努力趋向全球化而支持市场的制度基本 上是有国界的”(注:参见[英]《经济学家》周刊2001年9月29日文章《全球化是否将使 政府消失》。)这一两难命题。芬克尔斯坦(Finkelstein)把联合国体系的“多边外交” 治理模式描述为缺乏中央权威,植根于或继承主权性国家的传统概念,国家对其不同意 的决议都有“免疫”权利。(注:Lawrence S.Finkelstein(ed.),Politics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8,p.27.)莫顿·卡普兰称 之为“单位否决”(unit veto)体系。由于“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权力不只是在地方的 、国家的或国际范围内组织与运作,而是逐渐获得了跨国的、区域的甚至全球的向度。 ”(注:转引自[英]托尼·麦克格鲁:《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2002年第1期。)罗伯特·考克斯把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归结为一种“多边主义危机 ”。一些学者如罗西瑙、理查德·曼斯贝奇(Richard Masbach)、耶尔·弗格森(Yale Ferguson)和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等因而希望突破国家间体系的局限,认为 这种建立在国家主义前提上的体系不再能够满足解决人类的需要和问题。(注:Robert Latham,“Politics in a Floating World”,in Martin Hewson,Timothy J.Sinclair (eds.),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New York,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pp.23—54.)
建立于1993年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长达410页的最后报告《我们的全球睦邻关系》中也对二者做了区分:“过去,全球治理总是被看作主要是与政府间关系相关的事情,但现在,不仅政府和政府间的机构,还有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跨国公司、学术界以及大众媒体都卷入其中。”(注: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罗伊斯—斯米特本人似乎也认 识到“在领土主权国家基础上的全球统治体系与潜在的社会力量推动下的迅速全球化之 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从一开始就对联合国造成了很大损害”。(注:Christian Reus-Smit,“Changing Patterns of Governance:From Absolutism to Global Multilateralism”,in Paolini,Albert et al,Between Sovereignty and Global Governance,Macmillan,London,1998,p.4.)尽管如此,罗伊斯—斯米特从更广阔的历史 视角为我们展示了考察国家之间治理体系的演变趋势。他的这一划分的重大意义在于, 把联合国体系与全球治理联系起来。联合国的历史性创建和在冷战后的“复活”,再次 证明人类能够更好地组织全球生活、全球社会关系和实现共同目标。
治理全球化:软权力、软规则、软立法
全球化是一个国界不断受到侵蚀、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文化、技术和治理的联系不断加强并且产生出诸多复杂相互依赖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管理日益增多的全球问题,对国际组织提出了严峻挑战。显然,面对变化中的世界,国际组织不能仅充当国家之间的协调者,而要担负起治理全球化的责任。
国际组织自诞生以来,它就被视为减轻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推动全球生活秩序化的重要工具。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国际组织所具有的超国家色彩,我们才逐渐改变了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并寄托了终结地缘政治纷争和实现全球治理的良好意愿。在国际理论中也有思考国家构成社会、民族大家庭或世界共同体的传统。由于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而且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人们便常常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比做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如果把国家进行拟人化处理,似乎在国际社会中也应该出现某种社会契约。因为对个体而言,无论是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还是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都会导致社会契约的形成。随着全球化的来临,通过赋予国际组织更大的权力,似乎可以进而导致某种“世界政府”式的管理模式。然而,由于国家不同于个人,主权国家间的社会契约不可能建立。对于这种周密构思出来的遐想,普芬道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 共存没有那些随纯粹自然状态而来的烦恼之事。(注:转引自马丁·怀特:《为什么没 有国际理论?》,载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M],浙江人民出版 社,2003年版,第34页。)国家间的公民社会决不像个体间的公民社会那样具有同样的 必然性。
实际上,战后以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机制,虽然囊括了从世界贸易到维护和平等众多议题,但它们都不是“世界政府”模式下产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经国家转让而拥有一些权力,具有了管理某些特定问题的能力,但这些权力毕竟是有限的。国际组织只是 大量国际机制或者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组成部分。它们由于拥有特殊的法 人地位和自治而成为国际体系互动的行为体,它们的角色既取决于它们自我的利益和它 们的服务对象,也取决于它们适应世界变化的能力。
面对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复杂的治理层次和治理网络,以及国际社会多种行为体发挥作用的现实,国际组织难以通过硬性的权力和规则发挥作用。正如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引起大批非政府组织抗议一样,国际组织不能继续作为政府的集合发挥作用,而就全球化的发展和当前遇到的许多具体问题而言,国际组织的治理必须是富有弹性的管理,即在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对软权力、软规则和软立法的运用。
所谓软权力(注:约瑟夫·奈指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达到目的的能力”。参阅Joseph S.Nye Jr.,“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New York Times,January 2,2000,p.19.)即是指国际组织通过其奉行的原则,其介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和其它跨国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多种渠道,对其他行为体产生的影响力。20世纪 后半期所谓的多边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富国俱乐部”形式。来自少数富国的内阁部长或 致力于研究同一议题的重要官员们召开会议然后制定规则。战后几十年来这种模式取得 了一定成功,但在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的推动下,这种模式的多边合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抨击。尤其在参与程度和透明度等问题上,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发展中国家和越 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都不喜欢富国在它们不在时制定的俱乐部规则。国际组织掌控着重 要的资源,但要求它们向更多的直接参与者开放的呼声也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 组织与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分享权力已是大势所趋。如果不能与关键的私人部门和第 三部门结成联盟,那么,它们的目标就不会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甚至失去合法性基础 。因此,随着公众知情度和全球问题的关联程度越来越高,国际组织在处理跨领域问题 的时候,只有更多地扮演整合的角色,建立开放的机制,重视软权力,即更多地发挥影 响力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等级权力,才能更好地适应今日世界发展的需要。
与软权力相关联的就是软规则的确立和运用。利用软规则的含义一方面是在传统的规则基础上加强这些规则之间的相容性和关联性,另一方面就是面对新出现的全球性问题制定广泛适应性的新规则。国际机制的目的是管理各种“问题域”,传统上各个国际组织根据授权各自独立地确定本组织正式的约束性规则,并依此进行管理。但是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种问题领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新的行为体,尤其是商业公司、工商协会、劳工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越来越活跃地参与进国际组织的决策过程,这就对分别处理问题的做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公民社会的多元需求和多渠道、多层次的沟通、协调,也要求确立新的制度原则、经济原则与社会原则,从而把个别国际组织的规则与更为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联系起来。因此全球范围的政治行为方式变革与确立更容易实 施的操作性规则和扩大规则的适用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当前对全球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如核扩散、生态、人权和发展,以及难民、移民、毒品和传染病等来看,国际组织的法律化应该继续得到加强。但鉴于国际组织目前的地位和职能,国际组织的立法活动仍处于“软立法”时期。在运转良好的国内社会中,大众政治和利益集团组织直接推动立法以及有关法律的实施,但是在国际事务中,国际组织通常缺乏类似民主社会的合法性,缺乏大众活动和立法活动之间的联系。例如联合国支持召开的讨论妇女社会地位的大会,并没有产生强制性的法律,因为不同的国家对这些大会的决议往往做出不同的解释。联合国的活动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公众的看法,也有助于在国内外发起运动,但是它们无法提供实现政策变革的“立法”。里约热内卢大会通过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就是一个软立法的例证,它没有条约的地位,任何国家也无遵守的义务。同样,联合国废除歧视妇女公约的多数条款都与女权相关,但至今没有成为全球适用的法律条款。
结论
全球化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从金融到环境治理、从非法毒品交易到有组织犯罪,以国家为中心的主权治理体系已难以有效应对由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产生的大量问题。实际上,每一时代都对应着该时代独特的机构设置和制度框架,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处理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管理模式必然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如果说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为特征的联合国体系治理反映的是20世纪中期的国际化发展特征,那么具有“后多边主义”特征的全球治理,相对应的就是由全球参与者而非单由代表国家的政府共同协调、管理全球事务的全球化时代。
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当今全球治理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目标预期、要求和活动背景的变异,必须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在变化的世界上重新定位。新要求、新规则的出现反映了冷战后国际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尤其是非政府组织、跨国社会运动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它们的崛起凸显了以国家为中心治理模式的缺陷和不足。理论上,随着全球相互依赖关系的扩大和加强,设若缺少一个强有力和全面的治理体系,全球冲突和全球问题的管理、控制和解决便无从谈起。但是在国家依然充满活力的国际体系内,国际组织的活动仍然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在由全球参与者构建的“世界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国际组织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大量问 题的介入和管理,只有通过充当联结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的纽带,推动全球的合作与协 调,重视并充分运用软权力、软规则和软立法,才能更好地满足全球范围内不断产生的 超国家治理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