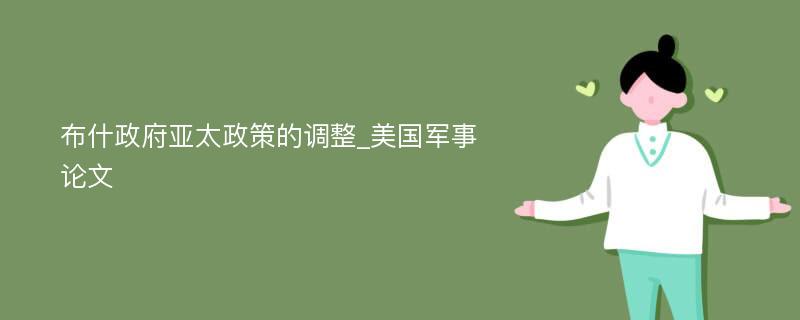
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论文,布什政府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后美国亚太政策经过初期徘徊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克林顿政府定型,并延续至布什政府上台。这套政策在地区秩序上突出美国为核心的“辐辏”(Hub and Spokes)式基本形态,即以美国主导和美与日、韩、 澳等国的双边安全联盟为核心,包括美军在东亚的军事前沿部署和远投力量“准入”机制在内的地区安全秩序;包括与中国、印度等亚太主要大国一系列复杂而特殊的双边关系在内的地区政治秩序;美国倡导的确保亚洲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机制为核心的地区经济秩序。在战略目标上,美亚太政策力图实现美在该地区的“力量主导”、“力量均势”和“力量协调”三大任务,“确保美国在亚洲扮演地区秩序主要保障者”的“轴心/枢纽”角色,防止出现所谓新的“地区霸权”而威胁美地区领导权。在战略手段上,美国把双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视为其政策关键。(注:Michael Mastanduno,“Incomplete Hegemony:The United States and Security Order in Asia,”in Muthiah Alagappa(ed.),Asian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51—153.) 进入21世纪后,影响乃至决定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和地区秩序的因素呈多元化趋势,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受到严峻挑战,迫使美国政府不断修正其亚太政策,以维护和强化美国在地区秩序中的轴心地位。本文将对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亚太政策的演化和特点作出梳理和比较。
“反恐”与“安全”:第一任期主色调
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对亚太局势的判断比克林顿政府要严峻得多,并曾誓言要重新调整亚太政策的重心,强调通过提升美国在东亚的双边联盟关系来应对中国为主的地缘战略挑战。(注:Condoleezza Rice,“Campaign 2000: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 79,No.1,January/February 2000,pp.45—62; Roberet B.Zoellick,“A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ibid.,pp.63—78.) 但“9·11事件”对美国新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安全利益重点的认识造成巨大冲击,布什政府对包括亚太政策在内的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具体实施均受到深刻影响。总体上,在布什总统第一任期内,由于“9·11事件”、阿富汗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牵制和干扰,亚太地区在布什政府外交中的重要性相对后移,其政策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政策调整主要沿着配合美国全球反恐战略、应对亚太日益多元威胁的方向展开,军事安全内容占据核心位置。二是在政治外交领域以求稳为主,防止地区危机干扰美国总体战略安排。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以东亚特别是以应对中国地缘战略挑战为中心”的政策调整设想未能有效实践。(注:Jonathan D.Pollack,“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East Asia:Does the United States Need a New Regional Strategy?”in Robert M.Hathaway and Wilson Lee(eds.),George W.Bush and East Asia:A First Term Assessmen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05,pp.107—109.)三是冷战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基本目标和利益诉求仍具有高度延续性和一致性,这决定了布什政府亚太政策延续、调整和深化的相互交织。
军事安全是其亚太政策的核心。鉴于亚太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布什政府的基本目标仍是保持在该地区的主导和力量均势,防止任何一个地区霸权出现而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2001年美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对亚洲地区可能出现美国领导权的“挑战者”极为关注,指出美国的战略就是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维持有利的地区均势”,并使敌人和潜在对手“望而却步”。美国防部在2004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和2005年初发布的《美国国家防务战略》都再次确认了这一战略目标。
“9·11”后,美国对亚洲战略利益的认识从以往相对单一的地缘战略角度, 扩大到了应对更为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在布什政府的亚太政策目标中,最大的变化是把“反恐”和“关注失败国家”作为美国亚太政策目标的重要一环。布什政府不但通过“反恐第一阶段”的阿富汗战争大幅提升了与中亚和巴基斯坦等处于反恐前沿国家的军事合作和战略利益渗透,而且在所谓的“反恐第二阶段”,宣称东南亚成为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第二战场并把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视为同它们改善政治、经济关系和向它们提供军事援助的主要前提。东南亚的安全战略地位显著提升。由于美国反恐战略的现实需要,布什政府至少在军事安全政策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亚洲各次区域相互分割的局面,而把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视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
在地区安全秩序建设上,布什政府不但延续了以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联盟为地区安全支柱的一贯政策,而且加速升级和改造与日、澳、韩的传统同盟关系,使之能支持新时期美全球安全战略部署。由于日、澳两国政府的积极配合,美日、美澳军事联盟的升级和改造被美国政府认为“最为成功”。(注:2005年1月笔者随团访问美国,美国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叶望辉和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拜登的高级助手詹努齐与中方代表团的谈话内容。)日本成功地借国际反恐对其自卫队海外用兵问题上的法律限制进行了重大修改,在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军提供了后勤补给,并在战后扮演维和等“安全协助”角色。澳大利亚政府自把国际恐怖主义视为其首要威胁后,便把积极支持、配合美全球反恐作为其安全政策核心,并在2003年底宣布正式加入美导弹防御系统。其中,美国通过创设新的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机制,进一步增强了其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在进行区域秩序安排时的协同功能。布什政府还把扩大与东南亚和南亚“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合作作为亚洲安全秩序新的发展方向,以双边同盟为基础,带动多边参与的“意愿者同盟”,配合美在地区和全球实施反恐、不扩散等项目。对此,2003年4月, 鲍威尔国务卿在“美国亚太委员会研讨会”上曾指出,同盟战略的升级和改造使得美亚太盟友及“意愿者同盟”,在帮助美国完成“全球反恐”和“战后地区重建”等任务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注:Speech by Secretary Powell to U.S.Asia Pacific Council Symposium April 24,http://www.usembassy.it/file2003—04/alia/A3042409.htm.)
与此相应的是,布什政府一方面继续强调美必须保持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以有效威慑、防止地区热点升级和失控,另一方面,与其全球军事部署调整相配合,开始调整美亚太驻军的态势和功能,以完成旨在打赢“新型战争”和“同时应对全球四个地区之不测威胁”的军事战略调整。在东亚,美国增兵关岛的同时,改造夏威夷以作为未来美亚太地区前线司令部;计划把驻华盛顿的美国陆军第一军司令部移至日本座间基地,提升与日本自卫队的协同,并使日本基地应对范围扩展到南亚、中东、海湾地区;对韩国,美国防部在计划削减驻韩美军的同时,设想把韩国军事基地改造为未来美军向整个亚太地区大量投送军事力量的海空枢纽。另外,美国从过去单纯重视在亚太盟国(主要是日韩两国)的“前沿军事部署”,转向与整个亚洲地区(包括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建立多种形式的军事合作伙伴关系。美国防部2005年初发表的《面向未来:应对21世纪的威胁和挑战》报告,全面总结2001—2004年美军事力量和部署调整的成效、挑战,指出在新安全形势下,美应继续扩大同各种安全伙伴达成“额外的灵活准入”和基础设施使用协议,获得外国军事设施使用权,凸显美军事投送能力的“灵活”、“快速”和“高科技含量”,以增强应对各类威胁的威慑力和打击能力。
在“反恐第一”和凸显军事安全的政策指引下,布什政府在处理亚太政治外交领域问题时以平衡、求稳策略和控制预防危机为主,避免地区热点问题升级干扰美全球战略部署。在大国关系方面,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曾突出了亚洲地区存在的地缘战略竞争关系,不但以提升日美关系来降低中美关系在其亚太政策中的地位,还否定了克林顿时期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经过“撞机事件”和“9·11事件”的冲击以及几年来两国关系的互动调整,布什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理解明显加深,并以“坦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重新加以界定,使之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布什政府把稳定和发展与中国关系置于更为重要和更现实的基础上。此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政府重新“发现”了与印度发展全面关系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价值。发展与印战略伙伴关系、积极推动印在地区乃至全球发挥大国作用,成为布什政府大国政策的重要一环。
布什政府对地区热点问题的政策也有明显的调整。在朝核问题上,美从最初中止与朝关系正常化步伐、拒绝进行双边谈判等高压政策逐步趋向务实,强调通过六方会谈形式解决朝核问题,尽管其谈判底线没有实质性松动。在台湾问题上,布什政府从一度宣示“无条件协防台湾”的所谓“战略清晰”重新回到“有条件保护台湾”的“战略模糊”轨道。(注:Asia Survey,Vol.41,Issue 1,pp.1—13; Vol.45,Issue 1,pp.1—13.)
在“民主”和“人权”等问题上,布什政府延续美国的基本目标和立场,认为亚洲仍处于政治和社会经济转型阶段,美长远目标是在该地区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实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体制改革。但在具体实施上,它显然把“人权”和“推广民主”置于建立国际反恐联盟这一更为紧迫的任务之后,着重改善同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等处于反恐前沿、却是美国眼中人权方面“问题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
维护美国对亚太经济秩序的主导权仍是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重要内容,但并没有排上政策议程的前列。布什政府坚持一贯立场,认为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美必须确保该地区的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机制,防止出现排他性(特别是排美)的区域经济安排,保证美在该地区的投资、贸易和其他经济利益。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曾在美国务院电子刊物《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上撰文认为,布什政府的经贸政策就是“全球、地区和双边三管齐下”,“以进攻性方式推动自由贸易”。(注:Robert B.Zoellick,“Unleashing The Trade Winds:A Building-Block Approach,”U.S.Foreign Policy Agenda: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Volume 8,Number 1,August 2003.) 2004年底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评估称, “保持亚洲市场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开放”是“布什政府地区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注:James Kelly,“George W.Bush and Asia:An Assessment”,in Robert M.Hathaway and Wilson Lee(eds.),George W.Bush and East Asia:A First Term Assessment,(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05,p.22.) 但在实际操作上,美国并没有着力于强化地区多边经济机制的建设。在绝大多数时间内,美国都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更多地看作是一个政治协商的舞台,如在2001—2003年的APEC会议期间,美方将反恐、不扩散等地区安全议题作为对话主要内容纳入会议讨论,这种情形直到2004年才有所转变。对于近年来亚太地区大量涌现的次区域多边经济机制,由于美国没有直接参与,布什政府的态度一直颇为暧昧。由于在外交理念上轻视多边制度的作用,布什政府显然更加重视通过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方式增加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布什政府还把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作为抵消地区经济一体化压力、拉动与地区国家全面战略关系的重要杠杆。经济政策主要扮演着军事安全政策的“侍从”角色。
综观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亚太政策,在维护美国在该地区长期战略利益和目标不变的主旨下,美一方面调整深化地区军事安全政策,谋取对其反恐战争的支持,使亚太各次区域在军事安全方面相互关联互动的整体化倾向加强,另一方面则着力于稳定地区形势。不过,“反恐第一”和以“求稳”为主的政策导向,加上战略资源和关注被伊拉克战争和中东所牵制,以及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的压力,使得布什政府对亚洲自身的经济整合和政治合作进程加速的新局面缺乏足够的政策敏感、心理准备和资源投入。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由于未能及时制订更为全面的地区战略,布什政府的政策与地区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发展节奏日益“脱节”,美国长期主导的亚太秩序和美国领导权有面临削弱之虞。(注:Hugh De Santis,“The Dragon and the Tigers:China and Asian Regionalism,” World Policy Journal,Summer 2005,pp.23—36; Jonathan D.Pollack,“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East Asia:Does the United States Need a New Regional Strategy?”in Robert M.Hathaway and Wilson Lee(eds.),George W.Bush and East Asia:A First Term Assessmen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05,p.100.)
“参与”和“塑造”:新任期政策重点
2004年底布什成功连任后,舆论一般认为美国对外政策仍以国土安全、国际反恐以及防、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中心,外交资源和关注重点依然集中在大中东地区,布什政府的亚太政策将基本保持其第一任期形成的战略目标和策略。(注:Ralph A.Cossa,“More of the Same...and The Some!”in Comparative Connection,Brad Glosserman and Vivian Brailey Fritsch (eds.),Volume 6,Number 1,2005.)刚卸任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甚至断言:布什第一任期内的美国亚太政策运行良好,没有改变的必要。(注:James Kelly,“US East Asia Policy,”PacNet 9,March 7,2005.)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和主流学者罗列出了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重点,例如继续推进美日等双边安全联盟的升级改造,保持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与中国保持全面接触,共同塑造“中国和平崛起”,推动与印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大参与亚太经济和政治进程的力度,平衡中国上升的影响,以及积极实施危机预防和多方管理,防止朝核、台海等地区热点问题失控等。(注:2005年1月和4月,作者分别随团访问美国,与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国会议员高级助手和华盛顿主要研究机构的学者座谈时,美方对第二任期内布什政府亚太政策重点的归纳。) 这显现出新一届政府在保持第一任期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前提下,政策议程和实施策略仍在不断调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布什政府在重点对大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的同时,明显加强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介入。除朝核、台海等问题将继续是关注的热点安全问题外,布什政府政策的重点和方向已经日益受到亚洲地区自身变化发展的影响。这一总体延续中的调整,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和各界对过去四年亚洲局势发展特点以及对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初步反思。
其中,如何应对和塑造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保持与中国“坦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是布什政府新亚太政策的焦点。美国精英层对中国国力以及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意义存在截然不同的解读。(注:最近有两篇文章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在亚洲拓展影响的不同认识。参见World Policy Journal,Summer 2005,pp.23—36以及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Winter 2004/2005),pp.64—99.) 2005年6月7日,美国参议院举行关于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在亚洲政治、经济、安全影响的听证会,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主流对中国崛起因素的认识。美国各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使用自己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以及是否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和立场”。(注: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2005年6月7日在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http://foreign.senate.gov/hearings/2005/hrg050607p.html.)
从政治和经济层面看,美国在中国发展对地区和美国利益的影响问题上的矛盾心态日益明显。特别是中美互动中涉及的地区、多边和全球性成分增加,加剧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一方面,美国政府指出“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上升是中国经济力量发展的一个符合逻辑的渐变过程,与美国利益之间并非一场‘零和竞争’”,中美在亚太地区“有很强的利益互补性和合作空间”;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则批评中国实施所谓的“重商主义外交”,忽视甚至不顾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美国希望中国在自身力量和影响上升的同时,能更多地与美国及其盟友一道推动所谓的“国际社会接受的行为准则”。借用美国学者的话,中国在发展战略中,“需要稳步增加资源,以履行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地区发展和人道主义的责任与义务”。(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兰普顿的主题发言,“全球化与中国对外政策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南昌,2005年6月7日。)同时,美国日益感受到中国在周边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影响力上升对美原有优势地位的压力,因而对中国在亚洲实施的“经济外交”同样抱着复杂的矛盾心态。美表示欢迎中国与周边地区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利益,但同时指出中国正致力于提升经济之外的政治、外交实力,削弱了美在该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将加强与中国在双方核心利益、战略关切、全球性问题上的“战略对话”,减少战略误判,增进政策协调;还将把扩大在政治和经济上参与亚洲发展进程作为政策重点,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影响。
从军事安全层面看,布什政府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误判日趋严重,正加紧在安全领域实施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美国防部根据《2000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每年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报告》,全面评估中国的军事战略、军事实力变化以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近两年出台的诸多报告显示,美国认为中国正全面提升海、陆、空、导弹、太空、信息和合成指挥系统方面的能力,并对所谓中国军力迅速增长表示出日益强烈的担心。美2005年出台的一些报告更是直接宣称中国正致力于准备在台海地区打一场高强度局部战争,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从长远看可能对该地区活动的其他现代部队构成实际威胁,并指出中国正处于“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注: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The Military Power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ffice of Secretary of Defense,USA,2005.)针对中国的“军事竞争”,美国对中国继续实施结合“劝阻”和“威慑”的安全政策。在具体军事安全部署方面,美国除加紧美台军事合作、强化以美日为核心的双边军事同盟功能外,正把与印度建立更为密切的战略关系作为其全球和亚太战略的重点之一,以保持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警惕、平衡。美国还向欧盟、以色列等国家施压,阻止它们同中国的军事合作。这种战略上的牵制和安全上的防范在性质上仍然以“防御性为主”,而不是要与中国“全面对抗”,(注:谭宏庆:“防范与遏制: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与中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280页。)但美国“防御性”防范的步骤显然在加紧。
如何应对亚洲日益涌现的地区和次地区多边机制和区域整合,是布什政府面对的另一个主要挑战。一方面,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和次区域各种多边机制合作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在东亚,东盟、东盟地区论坛、“10+1”、“10+3”、中日韩等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继续推进,2005年底将召开第一届东亚峰会;在中亚,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在2003—2004年得到长足进展;在南亚,南亚区域合作组织签订多项协定,为缓和南亚紧张局势发挥重要功能;此外,区域内非正式会议(如博鳌论坛)和区域间会议(亚欧会议)也日渐成熟,成为探讨亚太区域合作和跨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但另一方面,布什政府无论在地区安全事务还是经济领域都更加弱化了对地区多边主义制度的支持。由此,亚太正出现更多没有美国直接参与的次区域多边机制和安排。美国各界开始担心这种趋势会削弱美的影响,危害美地区利益。(注:David Shambaugh,Divided Diplomacy and Next Administration,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Alternatives,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82—83.)此外,中国积极推动亚太多边机制,并开始扮演关键角色,加剧了美国对地区多边合作的警惕。
对亚太区域合作和多边制度发展的担心已经显现在布什政府的政策调整上。美国政府各级官员开始不断通过各种场合强调美国历来是亚太的一部分,强调亚太地区多边主义的开放性和民主性,反对任何企图把美国排除在亚洲事务之外的观点和做法,用直接和间接方式干预亚洲多边进程方向。(注:美国国务卿赖斯、常任副国务卿佐利克以及希尔在今年对亚太地区的访问过程中,特别突出了“美国是亚太一部分”的政策宣示,参见Comparative Connection,Volume 7,Number 2,2005.)美国官员更加强调亚太各国应大力重视APEC能力建设,使之成为可持续的地区合作的核心机制,并且特别质疑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峰会目的、结构不清、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够、存在偏离APEC轨道甚至形成把美国排挤在外的亚洲政治联盟的可能。(注:2005年4月,作者随团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国会议员高级助手和华盛顿的主要研究机构的学者座谈时,美方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由于美国施压,东亚峰会接受印度和澳大利亚两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首次峰会。对于次区域合作机制,美国官员指出美国支持功能性合作机制,如能源安全合作等,以此决定由哪些国家组成,反对纯粹的地区性机制,以此确保美国的影响力。布什政府对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设想建立包括美、日、中、韩、俄的“5+X”机制,使之逐步成为处理包括朝核等地区安全和政治问题的核心机制。总之,布什政府日益关注亚洲地区多样化的多边制度发展,同时要求亚太各种次区域多边机制做出澄清,保证真正开放,防止美国利益受到排斥。
布什政府面临的第三大挑战是如何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进一步推动反恐战略的实施,以及如何在美亚太政策中给予反恐战略更恰当的定位。在总体肯定美国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反恐政策的同时,舆论也批评布什政府以前在亚洲过分关注反恐,延缓制定出更加全面平衡的亚太政策。(注:Jonathan D.Pollack,“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East Asia:Does the United States Need a New Regional Strategy?”in Robert M.Hathaway and Wilson Lee(eds.),George W.Bush and East Asia:A First Term Assessmen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05,pp.107—109.)美国内对此的反思和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自美以“先发制人”为反恐战争的战略手段以来,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亚太国家围绕对美反恐战争的支持出现了分裂。东南亚国家内部分歧尤其严重,部分国家担心美反恐战略已从最初“合作反恐”转向“进攻性单边主义”,从重视“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合作和情报交流等多种手段”转向“过度依赖军事手段”,将“引发东南亚国家内部穆斯林与政府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对立冲突和局势动荡”。(注:Rentato Cruz De Castro,“Address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A Matter of Strategic or Functional Approach?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o.2,2004,pp.193—217.)菲律宾政府因国内压力而撤出在伊拉克的驻军就是典型一例。第二,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后将东南亚称为其反恐“第二战场”,但并未获得东南亚民众的认同。(注:Robert M.Hathaway,“George Bush's Unfinished Asian Agenda,”May 13,2005,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此外,一些东盟国家对美国试图以反恐为名扩大在马六甲海峡周围的军事存在提高了警惕。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已经正式拒绝美提出的“地区海上安全倡议”。最后,批评者认为布什政府在聚焦反恐问题时,对亚太的发展问题、贫困问题、政治转型、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其他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关注不够。布什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固然有反恐的迫切和必要,但并不是以反恐为首要安全关切。一味把反恐问题置于美亚太政策最前列,反而使得美国的政策与亚洲各国实际利益诉求相脱节,不利于美国政策得到地区各国的长期支持。一些美国学者甚至把东盟国家加强与地区其他大国的合作视作它们对美国政策的不满。(注:Charles E.Morrison,ed.,Asia Pacific Security Outlook(2004),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2004,p.191.)
为此,布什政府明显提高了参与和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的力度。2005年初,美国政府在东南亚国家遭遇印度洋海啸袭击之际,大力展现美国的“实力”和“领导能力”。5月初,新上任的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访问了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6个主要东盟国家。 与第一任期内美国官员访问该地区颇为不同的是,佐利克把美同该地区的经贸关系放在突出位置,还向印尼等国承诺美新的灾后经济援助、基础建设项目,并不断强调其访问的主旋律是向东盟展示布什希望看到该组织“更加强大、健康和具有活力”,显示美国对地区合作进程的关注。佐利克的访问被当地舆论认为是展示布什政府对该地区的“积极外交”,并向该地区和中国传递“美国仍是地区老大”的信息。(注:Comparative Connection,Volume 7,Number 2,2005.) 同时,布什政府又软硬兼施,影响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区域性安全机制的发展方向,防止它们背离美国初衷。 此次佐利克访问的另一目的,就是以美国将拒绝参加今后ARF外长会议为要挟, 通过东盟其他国家向缅甸政府施压,迫使其放弃担任2006年ARF轮值主席。
评估与展望
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调整是在全球安全问题发生重大变化、安全威胁日益复杂多元,以及亚洲地区合作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展开的。从布什政府第二任期近一年来的政策表现看,美增加对亚太地区的参与和关注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布什的亚太政策调整是否能反映亚洲地区形势的变化和地区秩序的转型,以继续保持美主导的地区秩序,关键要看其是否能进一步参与并推动地区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赖,通过协商与地区大国形成一种新的权力和责任安排,而不仅仅依据其他国家是否符合美国的战略期待来判断地区秩序的优劣,更不是简单地依赖自己超强的军事实力来维持其霸权主导地位。
从布什政府亚太政策需要应对的挑战,尤其是中长期挑战来分析,美国需要在亚洲几个主要次区域间的互动和相互依赖明显加强、影响地区形势和秩序的因素日趋多元、新兴大国力量迅速上升(尤以中国为显著)、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制度蓬勃发展(许多都不包含美国)、新的地区秩序正在逐步显现、新的秩序范式正不断与旧有结构发生矛盾甚至碰撞的情形下,形成一项更为全面参与的地区战略。但目前尚无明显迹象表明布什政府会在近期出台一份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政策文件,以总结它执政5年来对亚洲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发展的总体判断,评估其亚太政策的得失,并为未来美国的政策导向提供原则和前瞻性建议。故此,有学者甚至怀疑在缺乏系统地明确阐述美国在新时期亚洲地区长远的利益标的和战略设想的政策文本情况下,布什政府恐难向世人表明在亚太地区秩序加速转型的今天,美国如何推进其长远利益。(注:Robert M.Hathaway and Wilson Lee(eds.),George W.Bush and East Asia:A First Term Assessmen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05,pp.99—100.)
就具体政策内容而言,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诸多近期、中长期热点问题和挑战仍处于政策磨合之中。除去朝核、台海等一些地区热点需要美采取理性而平衡的政策外,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如何保持稳定和发展、防止“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必然对抗”通过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现实;在地区多边制度发展上究竟继续以双边关系甚至单边行动加以阻挠,还是积极参与推动地区政治、经济合作进程;在地区反恐问题上如何避免目标和手段的单一性,以及如何更加重视地区国家对多元威胁的关切,等等,将继续成为困扰布什政府的严峻挑战。
更为关键的是,在亚洲地区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的转型期,布什政府怎样应对长期以来主导地区秩序的“辐辏”结构(美国主导的霸权结构)所面临的冲击。不可否认,“辐辏”结构是后冷战时期亚太秩序中较成熟也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亚太的力量格局,以及地区各国(国家集团)利益、政策互动后所形成的基本面貌。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目标仍然是保持和强化美国主导的“辐辏”结构,但它存在局限性和不完整性,且随着塑造地区秩序转型新因素的发展而日益显现。
首先,区域一些重要国家(如中国)无法也没有政治意愿参加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联盟,美主导的“辐辏”结构因而始终无法成为涵盖整个区域的安全制度。由于近年来美日等双边同盟在安全战略上牵制和防范中国的力度增强,中国将继续对这些双边同盟的性质保持怀疑和警惕。由此,以双边军事联盟为核心的这种“辐辏”结构加剧而不是缓和了地区大国间的战略不信任,阻碍了在大国协调基础上形成多边地区安全机制的形成。
其次,该结构强调美国主导和在地区大国之间保持“平衡”,美因而无意就解决地区国家间的长期矛盾提出长远的战略方案,甚至乐见一些长期性地区问题悬而不决,因为地区国家间的适度竞争甚至紧张反而促其分别寻求与美建立或保持“特殊关系”。故有学者认为,保持中日、台海两岸以及朝鲜半岛适度紧张符合美在该地区长期的战略利益。(注:Asia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pp.151—153.)
第三,该结构在应对地区安全新问题(如朝核与反恐)上暴露出局限性。从过去几年布什政府的实践中不难发现,在推动朝核问题和平解决上,中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地区性反恐问题上,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等的角色更为重要。
第四,美国与地区盟国之间关系发展不平衡增加了“辐辏”结构的不稳定性。例如美国与韩国、菲律宾的军事安全联盟关系发展远远没有美日关系那么顺利。韩国在朝核、美军驻韩基地等问题上同美国的龃龉一度使两国军事安全合作处于困难境地;而菲律宾因人质事件已于2004年7月从伊拉克撤回军队,使菲美关系蒙上阴影。
最后,对“辐辏”结构最为深远的影响来自中国整体实力的上升以及中国与地区政治、经济合作进程加速所形成的互动。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一再强调自己扮演着地区安全秩序维护者的“善意霸权”角色,而地区一些中小国家(如东盟)也乐意接受美军事存在,以保持其在中、日等大国间的平衡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包括ARF在内的地区安全多边机制,广泛融入地区合作, 并在东南亚地区提倡“睦邻、安邻、富邻”的新安全观,东南亚国家越来越多地视中国的发展和力量上升是地区发展的机遇而非挑战,希望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引发了美国内对华强硬派的焦虑,他们不断发出“中国威胁论”的呼声,试图在亚太地区引起共鸣。这一做法无疑加剧了地区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对“被迫在中美之间站队”的忧虑,(注:Catharin E.Dalpino,“US-Southeast Asia Relations:Summitry Hints of More of a Activist Approach,”in Comparative Connection,Brad Glosserman and Sun Namkung(eds.),Volume 7,Number 2,2005.) 也进一步说明了“辐辏”格局在应对中国力量上升和地区整合加速等新因素方面的内在缺陷。
标签:美国军事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乔治·沃克·布什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