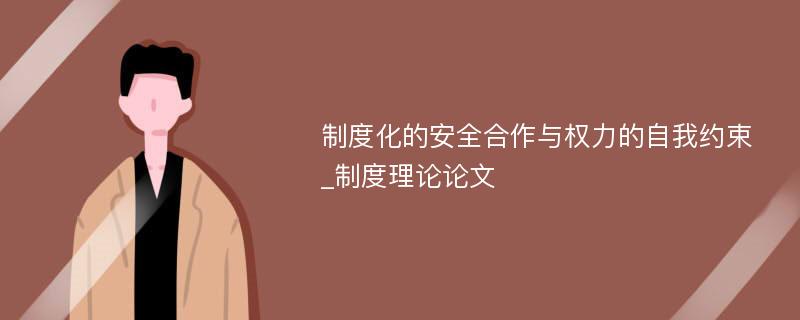
制度化安全合作与权力的自我约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以后的国际形势,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国际安全机制与权力自我约束之间关系的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制度可以促进合作,改善无政府状态,但是制度的建设与维持除 了利益相关和长远预期外,特别需要大国的权力自我约束。那么,在国际社会,权力自 我约束的条件是什么?大国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到权力自我约束?是外在结构压力使 然,还是国内体制动力下的产物?本文试图就安全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大国权力自我约束 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制度可以促进安全合作
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如果建立能够降低成本、改善信息不畅、增加透明度的国际制度,就会有效地促进信任,增进合作。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基欧汉指出,“有关国际合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在某种制度的背景下进行的”,“只有当最低限度的制度结构支持 合作的时候,合作的情景才会出现”。(注:Robert O.Keohane,“Neoliber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159.)
制度通常是指“在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围绕行为者预期趋同的一系列含蓄的或者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注: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基欧汉:《无政府状态下的战略和制度合作》,载[美]大卫·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 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制度的功能, 简单地说就是解决类似“囚徒困境”中的欺骗行为。国际制度一经建立,对国家行为体 就会产生重要影响。
制度理论反对在国际政治中区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因而强调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国际安全领域,制度都能够促进信任与合作。一些学者认为,在安全领域,制度理论只是演绎的结果,“没有足够个案研究的支持”。(注:Robert M.A.Crawford,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dershot and Brookfield:Dartmouth,1996,p.103.) 也有学者认为,安全制度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 杰维斯教授认为,安全机制的概念“不仅应暗含促进合作的规范和预期,它还应该是一 种超越仅仅追求短期自我利益的合作。”(注:Robert Jervis,“Security Regime,” in 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 173.)约瑟夫·奈则提出,“一个成功的安全机制必须包括关于重要变化的‘及时警告 ’,这样国家才不会对背叛行为完全无能为力。”(注:Joseph S.Nye,Jr.,“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41,No.3,Summer 1987,p.375.)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不可否认,在安全领域限制 竞争,减少安全困境,对相关各方都有好处,因而在安全领域和在经济领域一样存在着 建立制度的动机和需求。
一般地说,国家安全是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合作去追求的。如果“为了相互利益以相互认可的方式承诺对所有军事力量的规模、技术成分、资金投入以及各种行动进行管理”;(注:Janne Nolan,ed.,The Global Engagement: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in 21 Century,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4,p.4.)通过制定规范、规 则和程序,建立关于武器系统和力量结构的限制网络;并形成体现透明度和包容性,具 有总结、评估和反应能力,提供服务和惩罚功能的安全制度,就可以消除国家间的疑虑 ,建立互信,限制军事行动和武器扩散,防止冲突发生。因此,以预防为主的制度化安 全合作是完全可能的。通过制度的桥梁作用,会形成一种规范和制约行为的环境,使各 行为体在安全上照章办事,有规律互动,改善无政府状态,形成信任与合作。
二、制度建立需要权力的自我约束
制度能够减少竞争,促进合作,但是制度的最初建立在不同的领域却需要具备不同的条件。在国际安全领域,制度的建立与权力的自我约束有着重要的关联。
海伦·米尔纳在讨论国际合作理论时,总结了现有理论中影响国际合作的六个假设,它们分别是:绝对收益、相对收益和互惠的假设;行为体数量与合作预期相关性的假设;重复互动影响合作的假设;制度促进合作的假设;认知一致有助于合作的假设;力量不平衡与合作关系的假设。米尔纳认为,这六个假设的提出以及学术界关于合作概念形成的共识,是现有合作理论的“核心成果”。(注:Helen Milner,“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iong Nations-Strengths and Weaknesses,”World Politics,Vol.44,April 1992,p.480.)但米尔纳也指出,合作理论在无政府状态这一假 设前提以及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问题上存在着缺陷。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 界不断从这两个方面完善合作理论。一方面,“民主和平论”和“贸易和平论”强调国 内民主政体和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对外关系上易于采取和平与合作的路线;另一方 面,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提出了国家间互动造就了并非单一而是三种不同的无政府 文化体系,不同体系下国家间安全合作形成的难易程度不同,合作水平也不同。这些理 论从不同侧面突出了对国际合作条件性的研究,弥补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存在的不足,特 别是在对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上,减低了现实主义的刚性,突显了相互依赖对国家合作行 为的影响。
但是,制度合作理论为了追求理论的普遍性和完整性,对于制度的建立与维持、制度在不同领域的表现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集中论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没有重点指出制度的建立和制度的维持虽然相互联系,但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任何制度都是利益的产物,利益的相关性是制度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制度的建立 往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需要研究的是制度建立过程中的特殊性和个别性。第二 ,虽然有学者指出“制度的存在是为了解决特定事务,而特定事务是以在不同背景下存 在的不同利益分布为特征的。”(注:阿瑟·斯坦:《协调与合作:无政府世界中的制 度》,载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47页。)但大多数制度主义者 并不承认不同领域的制度是有区别的。而实际上,应该承认,不同事务领域有不同的制 度,制度在某些领域存在而在其他领域可能难以存在。第三,在安全领域,制度的建立 相对困难,这意味着安全领域制度建立的条件更复杂和更具特殊性。在这个问题上,自 由制度主义理论并没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缺乏个案研究。
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制度建设,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限制竞争,使各方按照规则和程序有规律互动变得非常必要,因而建立安全机制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但是,有了共同利益,并不意味着安全合作制度就能够建立起来。在安全领域,如同囚徒困境一样,即使存在帕累托最优解,行为体仍有可能选择自己的占优战略,也就是说制度合作的可能性要比在经济领域小。尽管这两个领域“都是以共同获益的机会和相互依赖但又独立决 策等方面为特征的”,但两者的关键性区别体现在欺诈的代价、监督的困难和安全事务 的竞争性三个方面。(注:查尔斯·利普森:《经济和安全事务领域的国际合作》,载 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76页。)由于安全领域与国家的生死存 亡密切相关,国家在安全上承受欺骗的代价要比在经济领域高,对他国的信任要小。一 次成功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可能有效地破坏对手的报复能力,这种情况使国家对安全领 域利害关系的考虑远比对经济领域的考虑谨慎小心。另外,“在军事安全领域,惩罚背 叛者的成本更高、监督更加困难、信息要求更加严格,特别是当成功的背叛严重地破坏 了未来的影响时。”而且,“随着成员国的增加,上述问题发生的可能性也增大。”( 注: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基欧汉:《无政府状态下的战略和制度合作》, 载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96页。)所以,杰维斯指出,“安全 制度既是非常有用的,也是非常难以建立的。说它有用,是因为单边行动不仅代价昂贵 ,而且危险;说它难以建立,是因为害怕别人正在或者将要违背共识和约定对每个国家 来说都是促使它自行其是的强有力动机,即使它看重制度的发展。”(注:Robert Jervis,“Security Regime,”in 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p.174.)
在这里,强国和弱国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国际政治中,虽然主权平等原则深入人心,但权力差异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安全制度由于目的在于通过规范和原则约束单边行动,从而限制权力政治的空间,这样一种机制往往会受到弱国的欢迎,而对于强国来说则较少吸引力。另外,安全机制对于追求改变现状和维持现状的国家来说也具有不 同的意义。追求维持现状的国家通常愿意通过建立制度来稳定现有利益,而要求改变现 状的国家则要挑战现有制度,或者反对任何“锁定”现状的制度安排。
因此,建立一种制度化安全合作机制至少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大国必须有意愿建立这种具有约束性的机制,而不是自行其是;第二,各行为体必须相信其他行为体也同样具有相互安全的观念与合作的意愿;第三,战争与追求自身安全被广泛认为成本过于昂贵。(注:Robert Jervis,“Security Regime,”in 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pp.176—177.)用建构主义的思维来理解,制度化安全合作, 从观念上说是建构一种集体身份认同。“这意味着把别人的需求置于同自己的需要同等 重要的地位,而这两者之间往往至少是部分地处于冲突状态。”(注:[美]亚历山大· 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 446页。)因此,制度化安全合作的成功建设,大国在自身利益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以及其 他国家相信大国能够自我约束是关键。如果大国不愿自我约束,制度建立就无从谈起。 由此,安全制度的建立与权力的自我约束是密切关联的。
三、权力自我约束的相关理论及其分析
权力自我约束直接关系到安全合作制度能否建立起来。这里,权力不仅应该在自身利 益的基础上做到自我约束,还必须能够使其他国家相信这一点。
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论,“国际政治可以界定为维持和增强本国强权、遏制或削弱他国强权的一种持续努力。”(注:[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第6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现实主义并非认为国际道德、国际法、国际组织和世界舆论无足轻重,但认为它们虽然是限制一国强权的因素,但其约束力不可能超越一国的主权。在现实主义者眼里,权力的自我约束只能产生于权力制约。也就是说,权力的自我限制是一种外力作用的结果,或者是一种胁迫,或者是一种力量制衡。因为,“大国不会把力量考虑放在一边而去建设国际和平,因为它不能确定这种努力是否会成功。如果努力失败,它将因忽视力量平衡关系而付出难以接受的代价。”(注: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p.51.)现实主义理论实际上强调了国际力量结构因素对国家间合作的影响,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但是,现实主义理论只强调了力量结构,忽视了观念结构的影响。而从历史经验看,共同的预期和共同观念对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影响。应该说,力量结构只是影响权力自我约束的一个方面,但是仅仅从力量本身解释还不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是全球远远超过苏联的最强大力量,但西欧各国并没有和苏联结盟以抗衡美国,却与美国结成联盟抗衡苏联,这说明观念结构影响了当时西欧各国的政策选择。
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国内政治对一国外交政策及其对外行为的影响,认为权力的自我约束是行为体在自身利益基础上的一种自觉主动的行为,主要源于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约束。贸易和平论提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权力的来源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土地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财富增加的决定性因素,贸易和投资成为比领土征服更加有利可图的办法。如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这样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它们不仅取得了经济繁荣,而且政治上稳定,其对外政策也表现为和平的取向。(注:Richard Rosecrance,“Force or Trade: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Two Paths to Global Influence,”in Charles W.Kegley,Jr.and Eugene R.Wittkopf,eds.,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
Perspectives(4th ed.),New York:McGraw-Hill,1995,pp.24—34.)民主和平论者则认 为,权力的自我约束主要是由于民主政体是基于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制度安排,而诸如私 有财产权、选举权、言论自由等个人权利从本质上是反对权力滥用的。民主制度的相互 制衡也有助于权力的自我约束。自由主义理论在解释国家间的同质性有助于合作持续方 面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力量在冷战期间和 冷战后对权力的运用显著不同。以对危机处理的方式为例,美国今天的先发制人战略, 在冷战时期是不可想像的。这说明在两极结构和单极结构下,权力由于所受制约的情形 不同,其运作的模式也不同,国内体制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的行为。
亚历山大·温特在他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认为“自我约束是集体身份和友好关系的最根本基础”。(注: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48页。)他对于国家怎样才能做到自我约束以及其他国家怎样知道国家是自我约束的 问题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回答:第一,国家通过不断地服从规范,逐渐将制度内化为自我 身份和利益,并形成为一种习惯;第二,民主制度有利于自我约束;第三,国家有可能 通过单方面自我束缚(self-binding)以“减轻他者关于自我意图的担心”,“这样做需 要通过明显地牺牲自我利益使他者相信自我的姿态”,而“不要求具体的回报”。(注: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49~451页。)温特更关注的是怎样使其他国家相信权力能够做到自我约束,因此,后两种回答提供了使国家如何赢得信任的主要办法。但第一种回答却并没有说明国家为什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服从规范,并愿意将规范内化为自身利益和身份。
如此看来,在无政府状态下主权独立的国家缘何愿意服从具有一定约束性的规范和原则,实现权力自我约束,从而使制度化安全合作建立起来,单纯从任何一个理论视角出发都不能提供满意的回答,应该给予综合分析。
四、影响权力自我约束的结构因素
在国际社会,权力的自我约束并非基于利他主义,而是基于自身利益。而自身利益是一种社会化需求,它是基于客观环境状况的需求。从历史经验看,权力自我约束主要是以结构因素为条件的。这里的结构因素,既包括力量结构,也包括观念结构,即硬实力 结构和软实力结构。
从力量结构来说,“国家之间的权势分布状况,决定了国家间互动的环境和国家政策选择的优先次序,因而也决定了国际制度形成的动因和预期。因此,应该把结构性因素看做组成制度基础不同利益模式的决定性因素。”(注:阿瑟·斯坦:《协调与合作:无政府世界中的制度》,载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47页。)那些“关于力量使用方面不言而喻的规范”,也是“以结构因素为条件的。”(注:Benjamin Miller,“Explaining Great Power Cooperation in Conflict Management, ”World Politics,Vol.45,October 1992,p.3.)基欧汉认为,当只有两个行为体的时候 ,关于相对收益的考虑会占上风。随着行为体增多,这种相对收益的观念“将变得模糊 ”,(注:罗伯特·基欧汉:《制度理论和冷战后时代现实主义的挑战》,载鲍德温主 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279页。)这其实是在谈力量结构因素对合作行为 影响的问题。总的看,多极均势有助于力量中心的自我约束。两极格局因为涉及各自在 国际社会的地位问题,行为模式趋向于零和游戏,不利于力量中心的自我约束。单极秩 序下霸权因缺乏制约,权力难以自我约束。力量中心外的国家则有可能在竞争中寻求合 作,以摆脱压力。
历史上,1815年以后“欧洲协调”的出现,正是在多极均势下形成的制度化安全合作,各国为这种合作主动约束自身行为,并建立和服从规范。冷战期间美苏力量均势出现后,也带来了缓和局面,但终因涉及地位问题和观念因素的影响未能发展为深入的合作。欧洲一体化运动在二战后展开,也是基于解决外部因素带来的竞争和压力问题。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因为力量的绝对优势而采取广泛的干预行动,甚至突破现有国际法的原 则规范,以战争手段推翻主权国家的政权。
除力量结构外,观念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权力的自我约束行为。国家对敌友的判断不同导致对权力的约束行为不同。对盟友或友邦,国家可能主动自觉地约束自身权力,采取磋商、协调、妥协的处理办法。对敌人则可能完全不同。因为“利益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注: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0页。)不同的身份导致不同的利益指向,导致对权力的不同认知。这里以温特所列举的广为人知的 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任何可能因素实现的几率取决于观念和观念建构的利益。500件 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还不如5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因为使这些武器产生意义的 是共同的理解。使毁灭力量具有意义的是这种力量置身其中的‘毁灭关系’(relations
of destruction),即构造国家间暴力的共有观念。”(注: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 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3页。)冷战结束后,美国在重新考虑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战略 问题上,共有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和平论和布什所谓的“新极权主义威胁”论,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人的观念。
力量结构和观念结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存在决定意识,但意识具有能动性,并不总是被动的。国际力量结构构成国家政策选择的限定环境,如何在一定的环境中对各种可能政策进行选择,则取决于观念结构的影响。二次大战后,欧洲的力量结构是两极状况。西欧各国面对两种威胁,一是德国复兴后的威胁,一是空前强大的苏联威胁。对此,西欧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解决之道:舒曼计划选择建立煤钢共同体的经济合作之道化解 欧洲各国与德国的矛盾;建立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并与美国结成军事联盟北约来抵御苏联 的威胁。两种解决安全的办法,显然主要是因为观念结构影响了不同的选择。近年来, 中国政府逐渐选择建立和融入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主张与东盟建立 自由贸易区,一方面从全局来说受制于美国单极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观念 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提出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突破了传统上 的单边思维和零和模式,强调安全的相互性和解决安全问题的协调与协作方式。正是这 种新观念推动中国主动约束自身权力,投身地区安全合作建设。
应该承认,观念结构与力量结构在制度的维护和制度的建立过程中都是重要的条件性因素,但是它们所发挥的作用还是有所区别。基于解决某个危机或某一类事务的安全合作,通常带有自发性和偶然性,其目标是为了避免共同担心的事情发生,这里力量的考 虑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当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各行为体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怀有希望制 度长期存在下去的共同预期,合作变成一种深谋远虑的行为时,则价值观的相容性、行 为的可预测性以及政治习惯的一致性就成为重要的支撑。制度形成后,认知因素对于维 护制度的有效运转具有关键作用。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壁垒分明,东方阵营在60年代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逐渐走向瓦解,而西方阵营虽矛盾迭起,但由于具有价值观和政 治体制上的一致性和共同命运而保持完整。因而制度的建立与制度的维系,其主导影响 因素是有区别的。
任何制度的建立通常都是某种历史机缘下的产物,安全制度往往与危机处理和冲突解决联系在一起。危机和冲突事件的爆发都是各种利益和矛盾的复杂交织,其处理和解决不论是讨价还价还是动用军事手段,都是与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因而,特定的历史条件催生特定的安全制度,在特殊性背后可寻找的规律性因素只能是结构性因素。
五、结语
安全制度合作相对困难,但也并非没有可能,这里大国的权力自我约束十分关键。大国能否做到自我约束,受结构因素的影响。力量结构构成大国行为约束的环境,观念结 构影响大国的具体政策选择。制度的建立需要大国怀有放弃单边行为的意愿,建立具有 约束性的制度。制度的维护更需要这种意愿转化为耐心和持久的行为,特别是将制度规 范和准则内化为自我身份和利益。当制度内的所有国家都内化了制度的规范和准则,放 弃武力解决争端、期待和平变革的安全共同体就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