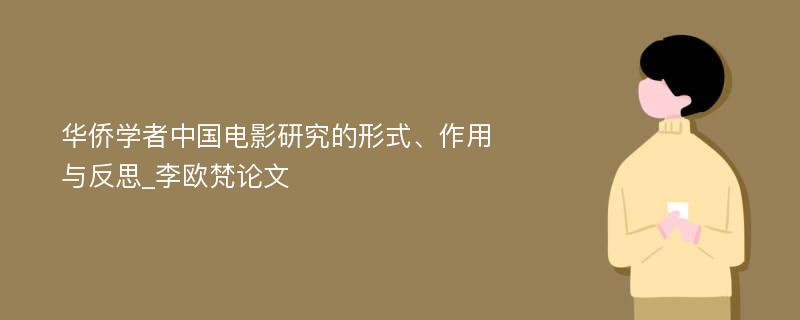
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电影研究形态、功能及其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外华人论文,中国电影论文,形态论文,学者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电影研究异常活跃,成为一股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热之后的新潮。刘康就感同身受地说:“许多文学专业的同行(尤其在美国)现在多转而研究电影。一时间,中国‘第五代’、‘第六代’电影成为美国现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一门显学。”① 与现代文学研究相比,中国电影研究在“文化转向”中聚焦了更多的社会热点。张英进介绍说:“西方电影研究当前的主流是意识形态批评与性别、身份(identity)政治等非电影本体的课题,而不再是美学(艺术审美),因此难以称电影美学为理论‘前沿’。”② 李欧梵甚至认为:“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用文化研究的方式探讨中国文学了。”③ 海外学者的电影研究基本上都是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存有宏大的研究主旨,而绝少限定在电影美学上。这和国内学界不同,除了戴锦华、王一川、张颐武等少数学者尚能较持久地保持电影研究的热情,大多数的文化研究者对电影的解读都仅是偶然为之;国内电影界的研究成果仍注重文本的艺术批评。这表明国内界限分明的学科建制、细化的学术分工以及研究思路的差异。
一、电影的政治性:从“自我民俗”到后殖民主义
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电影研究热,与中国电影在两岸四地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已然赢得的国际声誉以及在海外主流电影市场稳步发展有相当关系。当代电影在国际影响力方面远超出文学,并不是说前者的艺术成就超过后者,而是传播媒介的差异(影像媒介的视觉性、商业运作的跨地域性与无障碍的观影接受)使然。电影作为大众流行文化,成功翻越了国界、政治与文化樊篱,并以文化消费的方式让西方观众乐于接受。另一方面,电影界拥有如张艺谋、陈凯歌、侯孝贤、杨德昌、王家卫以及贾樟柯等等一批活跃在国际A级电影节的著名导演,其人其作在世界影坛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但是,在海外学者看来,与文学相比,电影文本与文化政治、国家形象关系更为紧密,电影研究构成了文化研究的核心。如王斑说:“二十世纪,凡是中央集权的政府无一例外地对电影制作颇感兴趣,这一点是司空见惯的。”④ 这种研究思路与海外的学科归属有直接关联。李欧梵认为,现在美国传统的汉学已经凋零了,新的传统注重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从50年代到现在是所谓的新的一代,搞的是中国学,这其实也有冷战的背景在里面。它以政治学为基础,又整合了其他学科,说到底是为政治服务的。”⑤
据李欧梵介绍,周蕾是目前已经进入欧美学界中心地带的“最走红”的华人学者⑥。这种“最走红”,正是因为她的研究符合“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注重意识形态论争与政治批判的学术传统。周蕾的专著《原始的感情:视觉性、性欲、民俗学与当代中国电影》⑦,被张英进称为“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电影和现代中国文化的论点最激烈的著作之一。”⑧ 之所以是“论点最激烈”,在于西方理论的殖民化特征最为明显,也就是以西方理论为本位,对极少符合理论思路的电影文本进行主观而随意的拆解与拼合(如《原始的感情》仅包括《老井》等六部“民俗电影”)。不仅如此,周蕾这种理论的“殖民化”,更与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民族国家及其政治的批判思路联系在一起,而这恰好是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的特征。她往往从文本某一碎片、某一相似点,联想或引用中国政治人物的言论,而后输入大量的西方理论,在横向空间的理论搬演中,这一碎片与细节被无限拓展开来,甚至可能被提炼成中国现代文化史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标本。如开篇论述的“幻灯片事件”因日本实证派学者没找到《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中提及的幻灯片,她为了与视觉文化衔接起来,便想象地将之等同于当时的新闻片/纪录片,与李欧梵、王德威等一致,不仅强烈地质疑其真实性,而且认为鲁迅虽认识到视觉文化直接而残忍的力量,但仍然用文字进行启蒙,由此得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视觉文化的抵制与压抑的结论。再如对陈凯歌的《孩子王》分析中,因出现牧童与“牛”,于是延伸到鲁迅著名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及毛泽东的“讲话”对之的政治阐释,最后认定牧童与牛代指与老杆等教育符号相对立的自然,但即便是这种批判“文化作为教学缝合功能的暴力”的自然,由于它的沉默,也和“该种暴力沦为合谋”,不仅如此,因其性别(男性未成年者)与出现排泄物(排尿与牛粪),认为“自然”(也是陈凯歌所激赏的批判性力量)是回避性别政治和性别化社会政治的自恋的男性文化⑨。在周蕾的后殖民理论看来,中国电影在一个“凝视他者在凝视自己”的过程中,主动地“自我民俗化”,这种“自我民俗化”就是中国电影创造出中国形象。因此,为了超越这种所谓的“文化中心主义”,周蕾更是主张瓦解“中国”这个中心符号⑩。在周蕾政治批判先行、随意比较、偏激评述的论著中,不顾电影文本及其文化语境而自说自话的现象可谓多矣。
吊诡的是,明明秉持西方文化“殖民”东方他者的学术思路的周蕾,却异常顺畅地运思、操持后殖民话语与理论,不仅积极置身于诸如后现代、后殖民等西方“后学”的文化背景,更在边缘批判中心的后学氛围中,顺利挺进美国学界的腹心。事实上,周蕾自认边缘、弱者、女性等等的后殖民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殖民主义的时髦外衣,遮掩起理论征服文本的强烈欲望,而完全无视于自身逻辑起点的边缘、“殖民地”等的历史与现状。从研究对象看,选择电影而停止追问它的文学来源,这是周蕾论述的一大特征,然而,这是否又反过来构成了崇拜视觉影像,压抑、抵制了印刷文化?表面上说,周蕾的视觉文化和鲁迅及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印刷文化,构成了女性/弱势/边缘与男性/强势/中心的对立,然而在当下欧美学界的语境中,两者强弱易势,视觉文化已经把印刷文化排挤到角落。就理论话语而言,周蕾批判国族的宏大叙事,以非主流的方式表现对“国家”、“统一”的疏离逃逸,似乎是一种弱势的少数话语;然而在西方学界正好相反,反国族宏大叙事的后学话语已成为主流,彼得·奥斯本就说:“这种‘反宏大叙事’修辞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且最不容忍异议的宏大叙事。”这提示我们,在全球化、后现代、跨国界的国际主义中,国族政治理论才是真正的边缘话语(11)。
具体说来,周蕾的研究立论选择电影而不考虑小说原本与民俗及其后殖民关系的原因,固然与电影传播力以及视觉呈现的感官刺激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应答自己的结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压抑”视觉文化的命题。我们可以理顺几者的关系:由于视觉文化在当下占尽文化优势,于是选择在西方引起广泛关注的第五代民俗电影为主要论述对象,然而为了适合欧美学界的“后学”语境,强化研究的后殖民性、后现代性,故而从鲁迅的《呐喊·自序》中挖掘出这一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周蕾得出鲁迅压抑视觉文化这一结论,并不符合事实;除文学外,鲁迅对美术、木刻、版画都给予了极大的甚至是拓荒性的关注),以此延伸到中国现代文化对视觉文化/电影的权力压抑上。由此,正好确立起自己从事电影/视觉文化研究的边缘性,而这一切都是从殖民主义心态开始。“殖民心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无视后殖民理论本应关注的“边缘”的历史与现实。如认为《老井》是“证明为社会幻想而辛劳努力,从本质上说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影片浓墨重彩地表现孙旺泉在打井事件中的个体激情与悲壮的自我牺牲,恰恰表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影片所构建的农村空间,交织着文明与野蛮、个体与集体、爱情与责任,在两元之间进退维谷,表征着大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状态。这种文明悖论,绝非周蕾所谓的“无意义”。而在《孩子王》对教育机制的文化分析中,她全然不顾知识、启蒙、教育对于农村孩子(特别是“文革”时期)成长的重要性,只专注于实践后现代理论中主流教育机制的权力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王福对抄字典的坚持,以及他后来终于‘成功地’写了一篇连贯的文章,其实正是那些被教学制度恰当地‘召唤了’(interpellated)的小孩子的病症。王福的坚忍、认真与耐劳的能力,只是学校作为意识形态机器,诱发参与者自动合作的过程中的组成部分。”(12) 这种结论与亨利·路易斯·盖茨(Gates)对同事的一个著名抱怨完全一致,当黑人准备去建构他们自己的主体性和文化史的时刻最终来临时,却被告知主体性和历史早已认为毫无意义的了(13)。周蕾既从现代性的价值维度上断定贫困落后的大陆在西方凝视中“自我民俗化”,又能从后殖民的角度审判现代中国发展的“无意义”,从这个角度说,张旭东对后现代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质问同样适合对周蕾论断的反思:“是谁或是什么要支撑(并从中获利)所谓的主体、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解构,又是谁或是什么可以高踞于不断变化的符号之上一再重复?”(14)
说到底,周蕾的论述始终与香港“非中非西”的边缘身份(即她所说的“夹缝意识”)的自我体认分不开,即是后殖民主义热衷的去国离乡者(diaspora)。但是有一个根本问题是,作为出生在香港的华人,到底是幸事,还是灾难?毫无疑义,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香港至今都是一块充满梦想的“飞地”。
二、电影的现代性、都市文化和“双城记”
国内电影界弱势的对外传播力在相当程度上使得海外学者没有任何“影响的焦虑”。除了极少数几位批评家(15),国内对海外华人学者电影研究谈不上任何影响,甚至缺乏可资引用、共鸣、争辩的研究议题。这给海外学者提供了更自由的阐释空间,甚或促使海外学者为国内电影界代言。张英进说:“在我看来,电影研究跟文学研究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那就是——作为一个学科,电影研究重视基本的经验,看电影时直接的一个经验,同时电影也是一个工业,研究者必须面对这个现实。”(16) 所谓电影研究重视基本经验,这主要是与文学研究过于理论化相比,但“看电影”仍然简化成“看故事”;阐释电影,仍然难逃文化理论的陷阱。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就是把电影研究纳入到文化研究视野的典范之作,单列《上海电影的都会语境》一章,探讨了电影院、电影杂志、电影观众与城市的关系,及其在构成都市流行文化、培育市民文化消费的习惯等功能,电影此时作为构成都市“声光化电”的例证而出现。电影的社会功能得到重视的同时,虽有文本故事的发挥(如对《马路天使》、《桃李劫》和《十字街头》的探讨,但显得随意),艺术研究却是大大削弱。张英进较早的一部英文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成》,也是如此,将《压岁钱》、《三个摩登女郎》、《新女性》等电影作为一种文本穿插在现代小说之中,论述电影构成城市的时空与性别的功能。两人都将电影作为文化文本加以考察,或多或少出现了放大夸张电影文本中某些文化痕迹、进而将文本的描述场景与自身的理论设想等同于历史现状的倾向。
有一点值得思考,李欧梵是在电影研究中发掘出上海与香港的“双城故事”。(另一位海外学者傅葆石虽然在李欧梵之前研究上海与香港的关系,并著有《双城故事》,主要从上海沦陷区与香港电影早期历史的资料中爬梳被政治迷雾遮掩的经济、人事关系,但这种双城关联比较松散与外在化;不同于傅葆石,李欧梵更注重沪港之间的殖民文化脉络,并以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声望有效地推广开来)。但同样,五六十年代,从上海移居香港的人群以资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力量,使整个香港都经历了“上海化”过程,那么,李欧梵为什么不从香港文学/流行小说等其他艺术发掘出“双城故事”呢?这并不能以研究兴趣简单地敷衍过去,恰恰反映出李欧梵电影研究存在的盲点。(1)沪港的“双城故事”受到了研究思路的先在性影响。由于李欧梵身处海外,思考的是西方现代性,城市文化即是现代性的结果,而电影又是城市的产物,成为现代都市文化最佳的载体(17)。因此,李欧梵的电影研究始终是现代性研究的一部分,由此得出沪港“双城故事”集中在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性上。换言之,他的研究仅能说明,在祛除了江南/吴越文化、华南/岭南文化等传统的在地文化之后,沪港在跨国、跨区域的国际大都市这一现代性脉络上具有共通背景;但是,现代性文化恰恰是一种同质性文化,这种同质性文化很难有效证明沪港在文化脉络、城市精神上的特殊关联。(2)也正因为舍弃传统在地文化的异质性,仅从同质的现代都市文化的角度研究沪港关系,李欧梵用以阐释双城故事的电影文本可谓极其有限。由于限定于“双城故事”,既排除了非香港题材的上海电影,也舍弃了非上海题材的香港电影,仅剩下少数的几部电影作品。即便是“怀旧”的上海电影,情况也很复杂,如《紫蝴蝶》、《茉莉花开》、《理发师》等,表述上海三四十年代的影片与香港并无什么瓜葛;而如彭小莲的《上海故事》的“怀旧”,则产生于建国之后五六十年代上海家庭的变动与当下新世纪的上海错杂、交织状态,自然与香港更无关系。不仅如此,上海电影也出现了所谓的“反怀旧”的商业题材的喜剧片,如《股疯》、《股啊股》等等;另一方面,大量体现岭南文化的香港电影(如王晶、周星驰的香港电影)都难以纳入所谓的“双城故事”。李欧梵的研究只能尴尬地一再出现《倾城之恋》、《红玫瑰白玫瑰》、《半生缘》、《长恨歌》等等(李安2007年的《色·戒》更成为李欧梵意义上的精品)。应该说,“怀旧电影”仅能证明在四五十年代香港“上海化”时期的关系,而在时隔半个世纪后,这种脆弱的联系早已折断;尤其是面对新世纪的上海与香港,再以这种“老上海神话”背后的殖民文化关联起来,缺乏足够的说服力。(3)无论是国内还是世界范围的“双城”现象,都是空间并置、城市文化与功能互补的表现,如彼得堡与莫斯科、巴黎与伦敦、上海与北京,等等。李欧梵发掘出的上海与香港的双城记,恰恰是同一种城市文化、功能(跨国的城市文化背景与所谓“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功能)在时间链条上的替换。上海因上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的强行灌注得到飞速发展,而在新中国的五、六十年代因政治迥异、时局动荡,殖民文化传统转移到香港,就在上海衰落的同时,香港步入经济腾飞的“黄金时期”。事实上,正是这种时间链条上“置换”(竞争),新世纪上海日益显示出超越香港的实力时,已引起了香港人的焦躁与不安,这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李欧梵所谓的“双城记”的虚妄性(18)。(4)从李欧梵选择电影而不是流行的大众文学研究看,是否因为香港即便是在五六十年代都未能在文学(或者扩展开来,即是传统艺术)上对上海有所超越,而香港电影与文化工业则出现过极其繁盛的局面?这为“香港经济、文化超越上海”、而“新上海的城市景观是镜像的镜像(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复制)”的论断事先埋下了论据的伏笔,最终为人生的现实选择(香港)铺平了道路(19)。
三、电影研究的学科意识、歧义及其话语背后
把电影作为一门学科,有意识地从学科范围架构中国电影研究,从思维方式上说,显示出宏观、超越的理性立场,可说是海外大陆籍学者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如鲁晓鹏率先提出“华语电影”(Chinese Cinema)的概念,不仅囊括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而且包括在海外制作的中文/华语电影,较合理地解决了意识形态的矛盾与目前海外华人电影创作逐渐活跃的新现象,这一概念在国内与海外形成一定的共识;其中,张英进算得上最具有学科意识的海外华人学者。他的学术成果不仅发表在欧美学界,而且促进了大陆对海外中国电影研究的认知。从个人研究的角度说,张英进积极从事中国电影研究以及海外中国电影研究的研究,正是自觉地补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电影学分支。
与其他海外学者运用西方理论进行散点的电影批评不同,专事电影研究十几年的张英进有着建立当前海外中国电影学科的冲动,他进入西方学界时正值学科大调整、中国电影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之时,对电影研究,具有填补学科空白的明确意识,正如他所说:“我个人对中国电影研究的学科建设比较关心。”(20)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外华人学者在学术力量上重建重组的现状。
张英进标举电影研究的学科意识,首先表现在,连续撰写了介绍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电影相关的论著,《审视中国:20世纪中国电影研究在西方的发展》、《西方学界的中国电影研究方法选评》、《西方中国电影研究中的权威、权力及差异问题》,等等论文,不仅收入《影像中国》(以章节的形式)、《审视中国》(以论文的形式)两本论著中,并以相似的文章名发表在国内《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上,而且应《电影艺术》的要求,主持了“新世纪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书评”,组织一些海外就读的博士研究生定期介绍海外电影研究的成果,将新成果及时介绍到国内来。其次,坚持从学科比较、学科意识以及学科史等层面撰写论文,并在学者访谈中阐述自己的学科观点,如发表于《世界电影》的《电影理论,学术机制与跨学科研究方法:兼论视觉文化》(也收入《审视中国》一书中)、《改编和翻译中的双重转向与跨学科实践——从莎士比亚戏剧到中国早期电影》,将电影与文学作学科比较;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的访谈《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研究的学科意识》,说到与内地合作,强调海外中国电影资料的整理,等等。再次,他撰写多篇论文,探讨中国电影的研究方法,进行方法论的反思,如《中国电影比较研究的新视野》、《中国电影与跨国电影研究》、《重思跨文化研究——西方中国电影研究中的权威、权力及差异问题》,分别对跨国/区域、跨文化、比较电影等研究方法等提出一系列的看法。标举学科意识的最后一个表现就是,论文写作有意识地以某一细节(如人物、情节)、特定时期贯穿前后史实中,透露出纵深的电影历史维度。如《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等等。
有意思的是,张英进这种学科建制的研究思路是在国内而不是在海外华人学者处引起共鸣。这是因为“海外中国电影研究”充满歧义,主要如下:(1)由于限定于“海外”,就排除了国内电影界的众多研究成果,并以欧美学界为学术标杆,但又由于是“中国”电影研究,无论是对中国电影的历史研究还是美学研究,海外学者的专著论述差强人意,难以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使这一“学科”缺乏必要的学术准备、资源与生产。(2)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之所以在国内引起热烈的反响,并不是因为研究成果有多大的学术价值(正相反,许多论断都需要经过审慎的理性反思,尽管这种理性反思目前尚未真正出现),而是以“海外”新式理论思路与工具之故,活跃了国内研究的气氛、拓展了视野。然而,张英进所谓的“海外中国电影研究”学科,是要在“海外”/美国建制,这种理论的新奇与刺激就大打折扣了,尤其在缺乏丰富而有效的中国电影经验的前提下,尚处批评阶段的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能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就打上了太大的问号;不仅如此,“中国电影研究”要顺利走进海外高等学府与人文研究领域,关涉到学术准备、理论话语、教育体制、学生资源等等的分配问题。如上所说,中国电影研究在海外的热潮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从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质变成新生学科,而且是让西方学界接受的一种学科,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办到。事实上,从目前的状况看,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仍处于薄弱阶段,即便是热衷提倡学科意识的张英进,在其专著中,恰恰缺乏自己吁求的学科意识。如前所引的两部专著,《审视中国》本身就是一本包括电影与文学的论文集,论题非常分散(电影部分,既包括西方的中国电影研究述评的三篇论文,也包括探讨西方国际电影节与中国电影形象、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等问题,既包括当代的城市电影,也包括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以及香港电影,还将根本不同范畴的独立纪录片也囊括其中),缺乏学科意识必要的串接与约束。《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虽以专著形式出现,但章节之间独立性强(除第一章导言、第八章结语外,第二、三、四章分别探讨西方电影节、中国电影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和西方批评话语中的权威、权力及差异;第五、六、七章分别探讨中国电影中持异见的“少数话语”演变、民俗电影与城市电影),缺乏学科意识的逻辑性。(3)海外中国电影研究如果落足于中国电影,理应细读中国的电影文本,梳理发展与流派,整理出中国电影历史规律及其指引发展方向。即是说,中国电影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不仅意味着研究主题是中国电影,而且决定了研究目标是中国电影的内在规律及其本质。然而如上所说,目前海外中国电影研究面向的是海外,属于典型的西方式文化研究,中国电影不过是西方理论的一个形象注脚而已,其落足点不外在于验证西方理论本身(无论是周蕾、李欧梵、张英进等海外华人学者还是毕克伟、裴开瑞等非华人学者,外文理论资料的引用远远超过了中文资料)。这大大降低了海外中国电影研究的学科价值。
毋庸讳言,在海外,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是电影研究,都归属于“中国”研究。海外华人学者从现代文学转向电影,不外是学术力量的内部转移,只是中国研究这一领域的迁移。作为一种边缘的区域文化研究,海外中国研究在研究人数与学术规模都受到限制,学科划分甚不清晰。这一“中国学研究”,“更多的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尤其是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层面的问题。”(21) 海外华人学者总是在有意与无意识之间承担起了“研究中国”的责任,既有主观的学术兴趣,也是客观的学术压力使然。如李欧梵从鲁迅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到城市文化研究,王德威的晚清小说研究、现代华语小说研究,王斑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到文学,都是跟随西方理论的热点议题而不断地嬗变与越界。这种学术领域的“随意”的扩展,正好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海外力量的薄弱、组织的松散、研究领域的模糊。从这个意义说,张英进明确提出“海外中国电影研究”的学科意识,无论从学术积累还是从现实可行性,都是难以做到的;这只是“中国学”内部又一次但已是习以为常的疆域扩展,彰显出学术创新的个体努力。张英进如此力求学术拓新,究其缘由,是和海外华人学者代际有关系,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港台籍海外华人学者构成了三代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他们的成就已然得到国内学界的追认,如国内学者季进就说:“是夏志清、夏济安,还有你(指李欧梵——引者注)和王德威,开创了也发展了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使得它从一个不被重视的边缘问题,逐渐成为美国汉学界的显学。”(22) 在港台籍学者的学术压力面前,从大陆留洋的学术力量要成为中国文化/文学/电影在海外的第四代“代言人”,必须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表明,海外华人学者内部,在研究力量、理论话语、学术突围等方面正在涌动新的变化。
注释:
① 刘康:《文化传媒全球化》(序言),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 张英进:《电影理论,学术机制与跨学科研究方法:兼论视觉文化》,《世界电影》,2004年第2期,第11页。
③⑥ 李欧梵、季进:《文化转向》,《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第16页;亦可参见《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④ 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8页。
⑤(22) 李欧梵:《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⑦ 目前国内没翻译出版周蕾这一专著,但其中一些章节以论文形式收在论文集中,如罗岗主编的《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郑树森主编的《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但在台湾,由孙绍宜翻译、书名为《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则已由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
⑧ 张英进:《影像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7页。
⑨(12) 周蕾:《男性自恋与国家民族文化》,郑树森主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0页;也可参阅孙绍宜翻译的《原初的激情》相关章节。
⑩ 参见张英进:《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7—80页。
(11) 奥斯本语,转引自张旭东《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第90页。
(13)(14) 张旭东:《东方主义和表征的政治——在他者的时代书写自我》,《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6页。
(15) 国内电影界对海外学者的影响大多仅限于历史资料的引证上,如程季华编《中国电影发展史》、陈播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张骏祥编《中国电影大辞典》、戴小兰编《中国无声电影》等工具类书籍。在海外学者中,张英进算是最熟悉国内电影研究状况的学者之一,不妨以他为例揣测国内对海外的学术影响。在《影像中国》中的中文参考论著除了以上工具书,仅限于陈默《张艺谋电影论》、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和《镜与世俗神话》、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4部;陈孝信、韩小磊(12篇)、胡克、黄式宪、刘德濒、吕晓明、马军骧、马宁(2篇)、倪震(2篇)、潘若简、祁海、汪晖、王群、尹鸿(2篇)、张颐武、仲呈祥、周政保与张东(合著)共21篇论文。而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以2万6千字左右的篇幅论述十七年革命影片(《青春之歌》、《聂耳》),只引用了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但居然有6次之多,鲁晓鹏在接受李凤亮的访谈中也赞赏戴锦华这本专著)、马德波和戴光晰的《导演创作论》、姚晓濛《中国电影:第三世界文化的一种文本》(《文艺争鸣》1990年第3期)这样少数论著,可参见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16)(20) 李凤亮:《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研究的学科意识——访张英进教授》,《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
(17) 李欧梵概述自己读书经历,从文学的现代主义,追溯到现代性与产生现代性的都市文化,再到上海文化研究,可参见李欧梵《现代主义文学的追求——外文系求学读书记》,《书城》2009年四月号,第13页。而在《上海摩登》的序言中明确说:“我从另外几本西方理论著作中得知西方现代文学的共通背景就是都市文化……那么,中国有哪个城市可以和这些现代大都市比拟?最明显的答案当然是上海。”《上海摩登·中文版序》,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18) 李欧梵在访谈中也谈到刚提出这一论题时的争议,尤其遭到香港学者激烈的反对。参阅《李欧梵季进对话录》“双城镜像”部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而关锦鹏的“上海三部曲”包括许鞍华的《倾城之恋》、《半生缘》等所谓“双城故事”的香港电影在香港票房方面仅为中下水平,这表现出这种城市文化、精神关联缺乏坚实的市民基础。事实上,关锦鹏一再说“我觉得其实大部分香港人并不关心上海这课题,对我个人来说,那也只是我于1990年拍《阮玲玉》时的得著……这种情怀关系到我个人特有的经验,因此才用电影来观照上海在1949年前的世界,但这题材不见得对香港人有多重要。”“没有什么人真的关心上海香港的双城文化,这就是香港本土观众的思想……可见香港观众对电影的要求是自成一格的,是很‘大香港主义’的”。具体论述可参见拙文《港台电影中的后殖民演绎:从“双城故事”到“台湾意识”》,《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第87页。
(19) 李欧梵在《中关村》记者的访谈中,明确谈到“退休后就到香港定居”,而被问到“为什么不选择回上海”时,回答是:“我喜欢边缘的、更国际化的、民族国家的声音稍微弱一点的地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香港还是比上海更国际化。”参见《他在城市游走,他为城市怀旧——访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李欧梵》,《中关村》,2004年1月号,第119页。
(20) 程光炜:《海外学者冲击波——关于海外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讨论》,《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第1页。
标签:李欧梵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海外华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周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