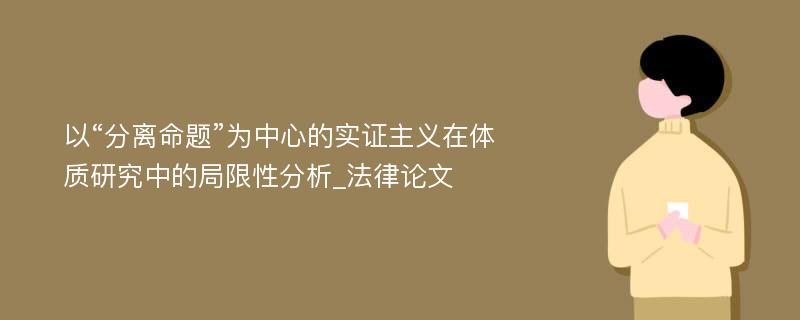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局限性论文,命题论文,宪法论文,法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03(2008)01-018-08
转型期的宪法学正在进行一场“祛魅”式的研究进路转换:规范宪法学成为宪法学中的“显学”,宪法解释学被理解为宪法学的起点和终点①,宪法学的意识形态研究进路正处于颓势。如果过去我们解释宪法过多地依赖意识形态路径的话,那么今天进行的宪法学研究正展开对“武器的批判”。展开对武器的批判同样依赖批判的武器,我们用什么样的武器去批判意识形态宪法学呢?有学者主张彻底摆脱过去的价值研究进路,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将宪法学构造为科学。[1]
强调法律和道德分离,从而强调法律屏蔽意识形态,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当然是我们无法摆脱的路径依赖: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核心命题就是强调法律和道德的分离,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分离,简称“分离命题”。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分离命题”能否适用于对宪法的研究?
法律规范不是自足的体系,而是我们建构的意义世界。宪法以下的法律规范可以在宪法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根基——因为法律合宪,所以法律正当。宪法为部门法提供了价值供给,因此,部门法可以只谈规范而不谈价值,但宪法却不可能:它必须在法律以外的意义世界里寻找正当性根基。于宪法而言,必然存在一些规范未曾言明的超文本假定,这些超越文本的假定就成为解说宪法文本正当性的精神家园。如果我们追问,宪法为什么是最高的法律?答案绝对不是:因为宪法规定宪法是最高的法律。这个问题如果可以这样回答的话,法律体系会混乱不堪——因为每一部法律都可以规定自己是最高的法律,宪法作为高级法的地位就岌岌可危。宪法作为高级法的原因,必然是因为其满足了宪法规范外的某种评判标准,这种宪法规范外的标准可以是“神启”,也可以是道德。但“神启”在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几乎没有解释力,而且,“神启”观念与宣称“信仰自由”的宪法规范不兼容,因此,道德就成了解释宪法正当性的普遍智识。于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中“分离命题”止步于对宪法的终极追问。纵览绵延至今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知识谱系,可以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分离命题”的证成路径分解为“命令说”、“纯粹法理论”、“规则说”、“制度实证主义”和“渊源论”。但无论哪一种学说,只要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力图从别的角度证成宪法,就会碰到逻辑上的悖论。
一、“命令说”:无法解释宪法对主权者的约束功能
“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这是边沁和奥斯丁一直强调的命题。“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能否证成宪法和道德的分离?
边沁作为功利主义的开山鼻祖,将功利作为评判法律正当性的唯一根据。边沁力图使法律远离那些正义、公平等价值,他将法律的定义表述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律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国家内的主权者认可或采用并经宣布的命令(volition)之总和”[2]
但边沁并不这样认识宪法。他认为,主权者对人民的让步不是法律,只是主权者的自我约束。[3] 法律是规定人民如何行动的规则,宪法是规定主权者如何行动的规则。[4] 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主权者的规则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适用于主权者,给主权者规定义务;第二类适用于人民,给人民规定义务。[5]
既然宪法是主权者制定的关于主权者如何行动的规则,有什么能够阻止主权者给自己解除义务?[6] 边沁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宪法的强制是一种道德强制。道德强制也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这种强制来自于人民,这种强制也可以产生约束力。而法律对人民的强制来自于政治强制,即一个选举出来的特定团体或个人对违法的个人实施制裁。[7]
人民对主权者的道德强制如何完成?边沁在《宪法典》中设计了一个“公意审判机构(public opinion tribunal.简称pot.)”,[8] 这个机构是一个“虚构的实体”(fictitious entity)。边沁借助“虚构的实体”、“公意审判机构”这些术语力图表达:公众可以通过对政府所为进行沟通而达成集体意见。“公意审判机构”在许多方式上类似于政府的司法部:它收集公共事件发生的证据。“公意审判机构”的判决即“公共意见”,如果主权者不服从公共意见,可能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是集体不服从。②
“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边沁提出这一命题时,目的是将法律和其他的规范分离,尤其是与道德规范分离。但边沁并不认为宪法是主权者的命令,宪法只是主权者的承诺。他也并不认为宪法和道德可以剥离,相反,宪法需要道德强制力才能实现。
奥斯丁力图“阐述法学修辞活动的语言问题的同时,提出真正意义‘法’的定义,并且,以此作为基础,说明法理学的范围,使这门学科成为纯粹的具有分析品格的‘实证科学’”。[9] 宪法的道德强制性在边沁看来也是一种强制性,但在奥斯丁看来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他者特征”,因此,宪法应该毫不容情地被剔除出法理学的框架。
奥斯丁的主权学说是一元论的,就是政治优势者对于政治劣势者的稳定的支配权。[10] 法律“是由主权者个人或主权者群体,向独立政治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制定的。主权者个人或群体,在这一社会中,享有最高的统治权力。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这些法是由最高统治者,向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制定的。”[11]
对于主权的性质,奥斯丁写道:“作为集合体来考虑,……一个主权者群体是至高无上的,并且是绝对独立的。”[12] 由于将主权作为最高的统治权力,作为限制主权的宪法就不可能在奥斯丁的法理学范围内苟活:“我使用‘宪法’一词,意思是指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或这种社会道德和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这两者相互结合的产物。”[13]
限制主权的宪法之所以不能列入法理学的范围,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违宪责任无法归结到法律责任的行列:如果宪法以惯例的形式存在,主权者的命令与惯例不一致,臣民会以不喜欢的心情来对待该法令,却没有十分肯定的理由说明其反对意见;如果宪法以成文的形式存在,主权者的行为与宪法不一致,应该修改的是宪法。[14]
在边沁的“命令说”体系中,宪法虽然也出自主权者,但它不再是命令,而是主权者的承诺,这种承诺如果需要用外在的强制来实现的话,这种强制只能是道德强制;在奥斯丁的“命令”说体系中,由于宪法是对主权者的限制,因此,宪法只能是一种社会道德。归纳起来,在“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这一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经典命题中,“法律”并不逻辑地包含宪法,从而,“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也没有证成宪法和道德的分离。
二、“纯粹法理论”:宪法的效力无法证成
纯粹法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分析实证主义进路的基础上,综合新康德主义哲学③,使奥斯丁以来的分析到达了“顶峰”。凯尔森发誓要斩断法实证主义与正义的最后一缕联系,使法“从正当的表象中解放出来”:纯粹法学“要回答法律是什么,而非法律应该是什么。纯粹法学是法律科学而不是法律政治学。”[15] 为达这一目的,凯尔森将法律体系设计成一个完整的金字塔结构:“法律秩序是一般规范与个别规范根据法律调整自身的创造这一原则相互联结的一个体系。这一秩序的每个规范,都是根据另一规范的规定,并最终根据构成这一规范体系的统一体,即法律秩序的基础规范的规定而创立的……这一回溯最后就导致其创造由预定的基础规范所决定的第一个宪法。”[16]
但当我们惊讶于金字塔图形之精致时,会免不了这样的追问:既然第一部宪法的效力来源于基础规范,那么,基础规范的效力从何而来?凯尔森回答道:基础规范是“一个最终的、自明有效力的规范”。[17] 也就是说,基础规范的效力并不来源于造法机关的创造,而是来自假设。至于基础规范的内容,凯尔森在《纯粹法理论》中做了一句话的解释:“人们应该按照历史上第一部宪法行为”,[18] 换句话说: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是有法律效力的。
凯尔森巧妙地用一个逻辑上的预设掩盖了纯粹法学的软肋:基础规范是一个纯粹形式性的规定。在纯粹法学关于法律效力金字塔的顶端,基本规范作为一种脆弱的、透明的“空壳”,吃力地维系着一个个通向它的“效力链条”。[19] 从这个角度看,对第一部宪法的研究其实不得不求助于被凯尔森强烈拒斥的法理学“杂质”,比如伦理学、心理学等。爱尔兰著名法学家凯利曾这样评价凯尔森的理论:“尽管将法律秩序化约为作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互赖规范的最低程度的实质内容,在其初始假设点上,凯尔森的模式恰恰不得不进入了下述等级越低越是激烈地拒斥的学科的领地,即心理学、伦理学、社会行为等。……为了衡量法律秩序得以存在以及基本规范得以预设的有效性,凯尔森又一次不可避免地要诉诸于外部因素。”[20] 在论及基础规范时,凯尔森甚至不反对别人将基础规范看作“最低限度的自然法”,[21] 而他曾经严厉拒绝自然法的“杂质”在其纯粹法理论中出现。
纯粹法学放弃了神圣价值对宪法效力的支撑之后,不仅在理论上无法解释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效力的来源,而且在实际上无法面对越来越多的作为纯粹法学反例的宪法文本:许多宪法文本并不宣称自己来源于基础规范,而是来自人民的同意。这些表述基本上出现在宪法的序言中。凯尔森为了使自己的纯粹法学纯粹起来,不惜将宪法的序言驱逐出宪法的疆域:序言“表达该宪法意图促进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各种观念。这一序言通常并不规定对人的行为的任何固定规范,因而也就缺乏法律上有关内容。它具有一种与其说法学的性质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性质。如果将它去掉的话,宪法的真正意义通常不会起丝毫变化。”[22]
凯尔森这段话主要是针对美国宪法有感而发。在《纯粹法理论》中,凯尔森将这一说法普适化:“一部严格按照宪法创造的法律,也可能具有非规范的内容,它们仅仅是宗教和政治理论的表达——如宣称法律来源于上帝,法律是正义的或者法律能够认识到全体人民的利益。”[23]
纯粹法学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悖论:一方面宣称自己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不加以价值的评判;但另一方面却以某些实在法不具备规范条件为由,将它们驱逐出自己的研究范围。
实际上,凯尔森也从不认为自己的纯粹法学是完美的,“纯粹法学理论尽管在细节上可能不完美、不精确,但是毕竟向这个任务的完成迈进了重要的一步。”[24] 这个不完美的细节之一就是对第一部宪法的效力证成,纯粹法学的“分离命题”在第一部宪法的效力证成过程中凸现了“天衣之缝”。
三、“规则说”:承认规则与宪法的关系无法理顺
哈特通过“规则说”来展开自己的“分离命题”。在哈特看来,法律就是规则,规则包含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法律就是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结合。初级规则是针对人的,是设定义务的;次级规则是针对规则设定的,包括改变规则、裁判规则和承认规则,其中承认规则是最重要的,它是规则的门槛——并非所有的社会规则都能成为法律,只有通过了承认规则鉴别,一个社会规则才可以称为法律。[25]
那么,承认的主体是谁?从理论上讲,包括官员和民众。但由于承认规则是在法律实践中被识别的,而且,普通民众没有能力去根据承认规则鉴别义务规则,因此,承认规则的主体一般是官员。[26] 哈特通过将法律分解为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并将对初级规则的承认理解为一个社会事实,巧妙地完成了法律效力证明负担的转移。
当哈特将法律效力最终效力的证明负担转移到“承认”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时,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营垒已经开始向法社会学松动,哈特不忌讳自己的理论向法社会学理论的松动,但绝对不能容忍自然法学分析方法向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渗透。[27] 为此,哈特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法律和道德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社会事实,但法律和道德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只有通过了承认规则之门的检验,道德义务才可以成为法律。哈特在此容忍的是法律与道德间“经过消毒处理的‘相互交叉’”。[28] 哈特能否在其规则体系中解决宪法的效力证明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证明那些肯定是法律的宪法基本条款真的是法?”[29] 这是哈特的天问,也是读者的天问。
哈特不能不承认:承认规则内部也有效力等差。“提供判准以衡量法体系内其他规则之效力的‘承认规则’,可以说是‘终极’的规则。并且当数个‘判准’彼此间呈现优越或从属关系时,其中一定有一个是诸判准中的最高者。”[30] 成文法国家中,宪法无疑是最高的承认规则——其他的法律都要服从它。在这里,一个循环的逻辑出现了:我们为什么说一个规则是宪法?因为法院在法律实践中说它是宪法;法院的判断为什么具有法律效力?因为法院的司法权来源于宪法。这意味着,宪法授权法院去判断宪法是什么。用哈特的语言表达:宪法作为最终规则需要法院来承认,但法院的司法权又需要宪法来承认——到底谁承认谁?到底谁才是终极标准?这一对宪法效力的颠覆性追问,被哈特这位谦恭的老者以粗暴的方式打断了,而且他认为对这种追问的打断是一个法律制度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记住虽然每一条规则的有些方面是可疑的,但并非每一条规则的所有方面都可追问,此乃一个法律制度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悖论就会消失。”[31]
即便停止这样一个纯逻辑的追问,我们仍然要面对经验世界里的问题:道德规则出现在宪法文本中如何解释?而这些道德规则并不与哈特所谓最低限度自然法内容重合。这个问题在美国宪法文本中显得尤其突出。最高法院有权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实体性正当程序”宣布国会的立法因为违反了一些立法的底线而事实上无效——国会的立法毫无疑问是一个社会实践活动,但这一社会实践无法超越价值判断。哈特对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这一规定颇有微词,他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国会制定的“清晰而完善,并且以绝大多数通过同时又能满足宪法的所有明确规定的程序性要求”的立法违宪,从而导致该立法事实上无效,“此信条一旦被采信,就保证了美国法院大范围的审查权,并且使得它们在一个有争议的价值判断上漂泊。……无论如何法院的所作所为在民主社会中都难说是正当的。”[32] 他将美国宪法中的这一规定称为“高贵之梦”。④
哈特的“规则说”遭遇宪法效力的追问,遭遇宪法文本中的道德条款时,要么说“不可追问——这是法律制度得以存在的条件”,进而强行中断逻辑链条;要么说“不正当”,从而撤离自己一贯的描述性立场。“规则”说的“分离命题”在遭遇宪法时,无法在体系内得到逻辑自治的解释。
四、“制度实证主义”:习俗的进路无法解释宪法的初始选择
以麦考密克和魏因贝格尔为代表的“制度实证主义法学”力图超越哈特的规则说,一方面强调对实证法的研究,另一方面强调制度不仅是规则的集合,同时也是社会事实的一部分。法律的规范性使法律成为思想的客体,同时,法律又是社会事件的一部分,这样,法律又作为社会现实而存在。制度事实在这两个层面来看,具有不同于原始事实的特征。[33]
既然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制度事实,那么,宪法作为制度事实,如果不求助道德假设,其效力来源于哪里呢?麦氏认为,宪法效力不来源于先验的道德规范,而是作为实践理性运用结果的习俗,而道德规范正是通过习俗进入了宪法,宪法是对习俗的明确化和标准化。但正如麦氏自己所言,对宪法的习俗解释进路只回答了宪法秩序的延续方面:对宪法的遵从和执行是行为累积的结果,但“最初采用宪法秩序时显然是不依赖于习俗的”。[34]
麦氏拒绝采用对宪法的价值解释进路,但却无法解释我们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宪法秩序。峰回路转,“制度实证主义法学”又回到了凯尔森曾经的困境:如何证明第一部宪法的法律效力。凯氏坚持自己的纯粹法学立场,认为第一部宪法的法律效力来源于基础规范的假设——“第一部宪法是有法律效力的”。凯氏对第一部宪法效力的解释还有假设存在,而麦氏连假设都没有。“纯粹法学”是一个纯形式的推演,尽管其假设削弱了纯粹法学的解释力,但在逻辑上还算有根的学说。但麦氏的“制度实证主义法学”由于坚持习俗作为法之正当性的根基,容不得假设。而且,从经验的角度看,美国宪法不来源于习俗,而是对习俗的反叛——五月花号上的几个“宪法之父”,他们的习俗是生活在英王统治之下,但“五月花号公约”刚好是他们对习俗反抗——《独立宣言》旗帜鲜明地宣称与英王决裂;法国的《人权宣言》以革命为背景,它们都是对习俗的背离。于是,我们当初采用宪法秩序的理由就成为“制度实证主义法学”的未解之谜。建立在“制度事实”基础上的分离命题无法解释宪法的效力来源,也无法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经验世界里宪法文本的由来。于是,“制度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遭遇宪法时,只能走入死胡同。
五、“渊源论”:“主要机关”说无法解释违宪审查制度
被称为“排他性实证主义”法学领军人物的拉兹,将其“分离命题”建立在“渊源说”和“权威说”的基础上: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是因为它构成了人们行为或者不行为的权威性理由,与道德无涉。同时,“一种法哲学理论,只有当它对法律的内容及其存在的检验仅仅依赖于人类行为的事实,而这些人类行为事实又能够以价值中立的术语加以描述,而其适用不求助于道德论证的时候,它才是可承认的。”[35] 法律与其他规则的区别是其权威性,而不是其内容的正当。⑤
如何鉴别一项规则是法律呢?拉兹提出了“渊源命题”(也称为“社会来源命题”),即主要机关适用的规则就是法律。什么是主要机关呢?“法庭、裁判所和其他司法主体是重要机关中最重要的部门。但是,其他官员(如警方)也可能是主要机关。”[36]“渊源命题”主要是以法院为核心展开的。
拉兹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说法可能遭到哈特曾经遭遇的追问:因为法院适用宪法,所以宪法是法律;法院之所以适用宪法,因为其权力来源于宪法——到底谁定义谁?于是,拉兹巧妙地避开了:“为了回答某种法律能否作为某一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的问题,人们必须追及到法理学的标准而不是法律的标准。最终,人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普遍的陈述,它不是对于法律的描述,而是关于法律的一个普遍真理。”[37] 也就是说,法院适用的规则是法律,这一原理不来源于规范本身,而是来源于“普遍真理”——凯尔森“基础规范”的幽灵在拉兹的学说现形了:凯尔森的“基础规范”是假设的,拉兹的“普遍真理”也面临着艰难的证成任务。
但即便拉兹的“普遍真理”无须证成,不言自明,拉兹也没有解决好其前辈在宪法问题上面临的尴尬。法院适用的规则不可能是随意选择的,法律包含着内在的评价系统,这些内在的评价系统决定了法院必须适用某些规则:法律是对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限制。[38] 主要机关的适用的规则不可能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为了法律体系的同一性需要,拉兹设计了最终规则的概念。最终规则和其他法律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渊源于一定的社会事实;最终规则和其他法律的区别是:最终规则有渊源——导源于一定的社会事实,但没有法律上的理由;其他法有渊源——导源于一定的社会事实,而且有法律理由,最终规则是其他法律的理由。法律适用机关有义务适用该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拉兹的最终规则显然指议会的立法,[39] 但他必须尴尬地面对这一事实:作为最终规则的议会立法尽管被主要机关适用,但却有可能因违反宪法中的某些条款而事实上被逐出法律体系。为此,拉兹谈道:“在某些法律体系内,有这样一些法律,它们的存在有助于阻碍某些机关把适合于某些条件的规范普遍适用,而且,还可能是这样,即使这些法律事实上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不过,即使这样的法律存在,这也不是通例。”[40]⑥
尽管我们无法考证拉兹这段话是否针对具有违宪审查制度有感而发,但美国等国家的宪法文本却为拉兹这段话提供了最好的注脚——议会通过的法律有可能因为违反宪法中的某些条款,从而无法普遍地适用,但它们又的确是法律。拉兹显然解决不了这一问题,用一句“这不是通例”虚晃了一枪。这与拉兹对主要机关说的定位倒是合拍:既然主要机关适用说是“普遍真理”,也就存在例外。宪法文本中关于法律正当性底线的条款,就构成了拉兹“主要机关适用说”的例外。
六、结论
自边沁、奥斯丁开始,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就力图区分法律和道德,“分离命题”是他们学说中的主线。边沁、奥斯丁看到了宪法的道德性,干脆将宪法排斥在其法律体系之外,“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并不是针对宪法而言的。在边沁、奥斯丁生活的时代,成文宪法的数量不多,他们将宪法排除在法律体系之外,其理论在经验的世界里并非荒谬绝伦。但到了凯尔森时代,“宪法是法律”已成为“集体无意识”,于是,凯尔森及其以后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在展开“分离命题”时,宪法的道德性就成了一道坎:要想将“分离命题”贯彻到底,必须逾越它。凯尔森将宪法的效力托付给了假设的基础规范,但凯尔森的“精神数学”在给现实的宪法文本求解时,终因解释力匮乏而遭诟病。哈特力图在规则体系内通过“承认规则”解决宪法规范的效力问题,虽然避免了宪法和道德的瓜葛,但却碰到了逻辑上的困难:宪法需要法院的承认,但法院的权力又需要宪法承认——到底谁承认谁?麦考密克和拉兹——两位哈特的得意门生从规则的框架中突围,求助于规则以外的标准。麦考密克求助于制度事实,进而求助于风俗;拉兹则从另一个方向突围,求助于“主要机关”,并认为“主要机关”标准不是规则内的标准,而是法理学的普遍真理。如果说麦考密克逃向了法社会学立场的话,拉兹就是逃向了逻辑论的立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方向的逃离并没有解决哈特的悖论,反而是从一个死胡同进入了另一个死胡同:两种路径都碰到了有力的反诘——很多宪法文本与风俗的延续无关,连麦考密克也不得不承认,第一部宪法的产生与风俗无关。“主要机关”说作为解释宪法的理由,在英国可能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在有违宪审查的国家则很难自圆其说——宪法中关于法律正当性底线的条款可能让某些法律无法被“主要机关”适用,拉兹只能用“那不是通例”来搪塞。
宪法的确政治性和法律性兼备,从而使文本融道德性和规范性于一炉,这就决定了宪法学的研究进路不可能是单一的。在意识形态宪法学时代,“宪法已经被推崇得更像一件用来膜拜的圣物,而不是一份用于阅读和解释的文件。”[41] 意识形态宪法学的缺失在于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宪法研究的唯一进路,同样,我们今天采纳的“祛魅”进路其实也只是一种可能的进路:从一个路径接近宪法,并不必然意味着屏蔽其他路径。任何武器都是有缺陷的,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可以帮助我们清理因对意识形态宪法学过分的路径依赖导致的神秘化和空洞化,但不可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宪法学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宪法学研究的多种路径,其中也包含意识形态的研究路径。⑦ 我们在倒洗澡水的时候,不能将孩子也倒了出去——“矫枉”未必要“过正”。
收稿日期:2007-10-08
注释:
① 规范宪法学力图区分事实与价值,满足于规范内部的自足合理性。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② 边沁这一思想很让人费解,对边沁这一思想的展开论述可参见Oren Ben-Dor.Constitutional Limits and the Public Sphere.Hart Publishing,Oxford Portland,2000,p.162。边沁的早期著作也提到过这一思想,但没有展开。参见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21页。在该书中,边沁从服从习惯的角度对宪法发生约束力的机制进行了解释——主权者之所以服从宪法,是因为他们有服从的习惯。
③ 关于凯尔森纯粹法学和新康德哲学之间的关系,凯尔森曾经公开宣布:“借助于柯亨对康德的解释,我获得了正确构造法和国家概念的决定性认识论观点。”可参见李桂林、徐爱国:《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④ 与之相应,哈特将霍姆斯的学说称为“噩梦”,因为按照霍姆斯的观点,“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这事实上是允许法官立法。参见哈特:《英国人眼中的美国法理学:噩梦与高贵之梦》,载《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⑤ 很多学者认为:拉兹虽然力图与哈特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理论决裂,但拉兹的学说其实与自然法理论有很多沟通的地方,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自哈特以来,自然法理论与分析实证主义理论的区分已经没有意义。See Cristobal Orrego.Joseph Raz' s Service Conception of Authority and Natural Law Theor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2005,vol(50),p.317.Keith C.Culver.Shiner on “Detached Legal Statement.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1995.vol(8).347.Jonathan M.Breslin.Making inclusive positivism compatible with Razin authority.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2001.vol(8).133.
⑥ 根据原文对译文作了适当修改。
⑦ 主张对宪法做意识形态研究的不单是中国学者,也不单是主张法之阶级性的学者。荷兰的宪法学家亨克·范·马尔塞文等就主张宪法学的研究进路包括:历史研究的途径、制度的研究途径、意识形态的研究途径、功能的研究途径、结构功能的研究途径、体系的研究途径等。他们还认为,只有综合通过这些途径,才能得出“深思熟虑的结论”。参见亨克·范·马尔塞文等:《成文宪法——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