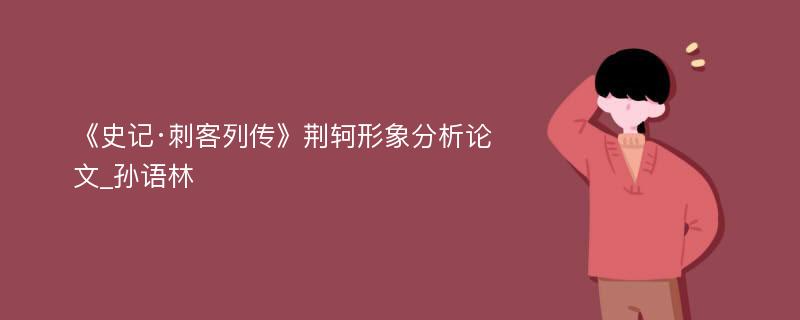
孙语林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形象是复杂多面的,他性格丰满、个性突出、情感丰富细腻,而历来对荆轲的研究往往把荆轲归结到典型游侠一类,忽视了太史公笔下荆轲形象的多面性。将荆轲形象跟其他刺客形象对比,可以看出荆轲形象具有特殊性。
关键词:荆轲;形象;多重性
荆轲,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在战国末期的秦庭之上嘎然而止,相对于浩瀚而残酷的历史时空,有限的生命只是一个瞬间的存在。《史记》、《战国策》、《史通》、《春秋战国异辞》等,一系列史籍中留下了他的事迹。在所有的历史典籍中,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关于荆轲的记载最具感染力、最为详细可靠,但不足四千字的记载也留下了诸多空白,加之司马迁在文中使用的暗笔,留给后世探索与想象的空间。因此,自太史公之后,世人从未停止过对荆轲形象的褒贬。种种争论恰好表明荆轲形象的多层次和丰富性。
一、《刺客列传》中刺客行为的基本特征及其与荆轲行为之区别
司马迁一篇六千余字的《刺客列传》,用在荆轲一人身上有三千字。在如此大的篇幅之中,司马迁生动地塑造了荆轲的形象,从而被人们视为中国古代刺客的重要代表人物而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历史人物之列。在《刺客列传》中,一共出现五个刺客,在司马迁对前四个刺客形象的塑造上,出现了很多共同点。这些特点表现出了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对人物和事迹的选择上的某些统一标准。
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这四个人物有着超越社会凡俗之人的特点。他们似乎没有七情六欲,所有的行为动机都是从刺客身份出发的,更接近于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提到的“扁平人物”,“他们用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1]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着墨不多,只叙述了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特点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某些特殊场景。因此,这四个人的共同性格特征,可以看作是司马迁对于刺客精神的归纳总结,但这种刺客基本特点在人物人格上的凸显,并没有从同一篇的荆轲形象上表现出来。《史记·刺客列传》中,叙述了荆轲的几件生平小事。第一件,荆轲与盖聂论剑,第二件,荆轲与鲁句践争道。从司马迁叙述故事的角度出发,这种对情节的选择有特殊目的。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面对正面争斗,荆轲一般采取逃避态度。他的言行,更像是一个“克己复礼”的儒生。荆轲面对挑战时的“嘿然逃去”显得有些懦弱。这种逃离与其说是“隐忍”,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对冲突的畏惧和对失败的逃避,这是第一个与刺客形象特点相违背之处。
另外,荆轲的犹豫和退缩不仅表现在他对待正面冲突的态度上,还体现在接受刺秦王任务过程中的几次犹豫上。第一次,田光相求,“欲自杀以激荆卿”,荆轲面对田光的死无动于衷;第二次,太子“避席顿首”亲自陈述原委苦苦相求,荆轲仍然推脱:“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直到太子“前顿首,固请勿让”,荆轲才“然后许诺”。在《史记·刺客列传》里,也有过类似的故事发生,聂政对严仲子的请求也曾经有推脱,他在故事开头拒绝了严仲子黄金百镒和刺杀侠累的任务。但聂政的推脱出于一定原因,当时聂政老母尚在,姐姐聂荣未嫁,刺杀存在极大风险,一旦被认出会直接连累到家人。因此,聂政这种推脱不仅情有可原,而且更加彰显了他的刺客风范。与之相比,荆轲的推脱就显得不够有风度气魄。
除此之外,荆轲形象的一些性格特征还违背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大义风范。《刺客列传》里写聂政接受任务,是从一开始就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刺杀完成后,聂政义无反顾“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更是用惨烈的死法来捍卫主人的安全。这些刺杀、自残、自杀的一系列行为是一气呵成的,更显示出聂政对自己的死亡早有计划。反过来看荆轲在刺杀时候的表现,他不仅缺乏“士为知己者死”的大义精神,甚至缺乏侠客应该有的同情心和仁义之心,这是第三处。
如果说荆轲对刺秦的最初拒绝是出于对献身与否的犹豫,那么接受任务之后表现出来的犹豫是不应当存在的。聂政拒绝严仲子馈赠的黄金,豫让为了刺杀赵襄子甚至自毁形貌,沿街乞讨。荆轲的行为不仅不符合刺客的基本行为准则,甚至算不上一个侠客的行为。《史记·游侠列传》记载朱家为了救济别人“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3]荆轲与之相比,就更加显得自私而畏难了,这是第四处。
二、解读荆轲隐藏在侠客身份之下的性格特质
比较其他侠客,荆轲的性格复杂多变,其他侠客的性格都相对单一。可见司马迁对荆轲这个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非常重视的。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刺客列传》里面对荆轲的特点有一些直接的描述:
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2]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 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 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2]
由此可知荆轲在《刺客列传》中的形象不仅是一个刺客,还是一个文人。他“好读书”“为人沈深好书”,和高渐离一起击筑高歌。荆轲既好文又尚武,这种游士与游侠相结合的身份有其特殊的形成条件。汪涌豪《游侠人格》里提到:“本来,古代所谓士,大都是武士,如前所说,平居时为卿大夫家臣,统驭百姓,战时执干戈以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他们都要学‘六艺’,‘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在庠序学校,接受全面的培养和锻炼。然而依个人的情况,总有长于文章辞令和长于射御攻战的区别。前者发挥其所长,宣扬礼仪教化而成儒,主张兼爱非攻而成墨,鼓吹现时功效以干时主而为纵横家;后者发挥其所长,则为奋死无顾忌的勇士,乃或替人打仗、任气尚义的侠士,是很自然的事。”[4]由此我们推知,荆轲应该也是在庠序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刺客列传》里,并没有单独说荆轲的剑法如何高明,而是把荆轲的好文和好武并列起来写,可见司马迁把荆轲的好文当作重要的性格因素。
司马迁笔下的荆轲与其说是一个能文的侠客,不如说是一个能武的文人。因为其性格因素里面,文人成分要更加明显一些。《刺客列传》中说: “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沈深好书”是司马迁描绘荆轲时的基调,是荆轲性格的基础。文中还说:“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2]荆轲这种狂放不是“十步杀人”的尚武的狂放,而更像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文人式的狂放。荆轲表现这种文人式狂放最典型的一幕就是在刺杀秦王失败后破口大骂的这部分:
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2]
这一幕尤其突出了荆轲这种文人式狂放。历史上这种有名的大骂, 都是出自于狂放的文人,比如 《三国演义》 里面有名的祢衡击鼓骂曹:
操曰:“汝为清白,谁为污浊?”衡曰:“汝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 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 吾乃天下名士,用为鼓吏,是犹阳货轻仲尼,臧仓毁孟子耳! 欲成王霸之业,而如此轻人耶?” [5]
对比两次大骂,相同点颇多。首先,两人姿势都极度不雅。荆轲是“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祢衡是“裸体而立,浑身尽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着裤,颜色不变”。另外角度也有相同点,都从褒扬自己的角度出发的。荆轲是“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祢衡更直接,“吾乃天下名士”直接说明了祢衡自视甚高的性格。李国文先生用很幽默的方式解释了文人的狂放:“狂是文人膨胀的结果,是成就感难以抑制的发泄,只要对别人不构成观瞻上的不舒服,感觉上不自在,心理上的不抵触,精神上的不讨厌,我们没有理由不允许人家自我感觉良好”[6]。荆轲本可以拥有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荆轲形象的塑造极其重视。首先这种重视出于他对刺杀秦王事件的重视。《刺客列传》里司马迁借描写荆轲,从文学上使人们对秦王朝的视角得到了特殊的转换,从被灭六国而不是旁观者的心理角度来审视秦王朝的兴起。司马迁在荆轲身上给予了复杂的情感,这些情感里面,同时包含着赞美与批评、崇拜与质疑。司马迁《史记》中的荆轲形象鲜明生动,极具感染力,是荆轲历史形象的集大成者,为其成为经典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英]爱·摩·福斯特著、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59
[2](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卷八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汉)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卷一百二十四)[M].北京: 中华书局,2005, 2415
[4]汪涌豪、陈广宏.游侠人格[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18
[5](明) 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00
[6]李国文.文人的性格[J].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1期,4-14
作者简介:孙语林,(1990-)吉林四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论文作者:孙语林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2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7/21
标签:刺客论文; 列传论文; 史记论文; 司马迁论文; 形象论文; 秦王论文; 文人论文; 《文化研究》2016年2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