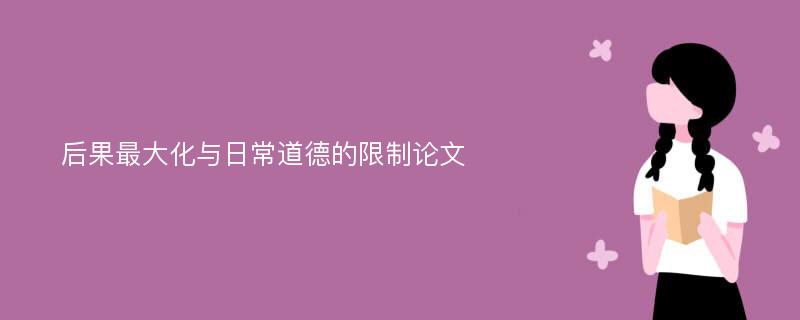
后果最大化与日常道德的限制
龚 群,靳娇娇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斯马特对于功利主义的后果定义的重新界定,从行为者中立的立场上提出后果事态最大化好作为评价行为的标准。威廉斯指出,如果人们遵循这一后果最大化好的标准行事,则将导致对人的完整性的破坏和人的异化。卡根指出,斯马特的行动后果主义的问题在于没有尊重日常道德的限制,日常道德要求我们关注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求我们所做的不超出日常道德的限制。然而,卡根同时认为,日常道德与直觉也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他的观点将后果主义与日常道德的要求相结合,从而提出了一种改进了的后果主义。
[关键词 ]行动后果主义;后果;日常道德
斯马特(Smart,J.J.C.)与威廉斯(Williams,Bernard)之争撬动了人们对于后果主义长期而热烈的讨论,从而推动了后果主义的发展。应当看到,斯马特的后果主义的后果概念是一种理想性的道德要求,然而这一概念一提出,就遭受了威廉斯几乎致命的驳难。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界,几乎没有人不严肃对待威廉斯对后果主义的异议。为什么威廉斯的异议会有力量?这在于日常道德与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追求之间的张力。
一、斯马特与威廉斯之争
1973年,斯马特与威廉斯合作出版《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 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一书,可以看作是功利主义和后果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在这一著作中,斯马特提出了一种新版本的功利主义——行动功利主义(Act Utilitarianism),由于其新颖的后果概念,又被人称为行动后果主义(Act Consequentialism)。行动后果主义所追求的是后果最大化好(善)。布兰特认为这个概念“大致是这样一个观点:行为者的责任(在客观意义上)在于,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履行一个特定的行为,当且仅当履行这样一个将(实际的或可能的)产生一种意识到的事态,这个事态与行为者可能履行的其他行为相比较,将产生最大化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worth)”[注] Richard B.Brandt,Ethical Theory ,New Jersey: Prentice-Hall.Inc.,1959,pp380-381.。实际上,斯马特的行动后果主义与以往功利主义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功利主义的后果概念。他对于行动功利主义的界定是:“大致地说,行动功利主义是这样的观点:一个行动(an action)全部的好或坏唯一地依据它的后果,即该行动对全人类的存在者(或一切有知觉的存在者)的福祉(welfare)产生的效果(effect)。”[注] J.J.C.Smart,Bernard Williams,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 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4.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斯马特的定义,行动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是在人类所有存在者的意义上提出的,他将人类行为实践者的任何一个行为的后果都将全人类所有存在者的福祉联系起来,从而是一个与古典功利主义有区别的后果论概念。在边沁等古典功利主义者那里,一个行为后果的好与坏,主要看的是这个行为对自己将产生怎样的苦与乐的后果。并且,在边沁那里,他所理解的社会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因而行为对行为者本人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贡献。但是,斯马特则强调将行为的后果直接放在整个人类存在者的维度来进行比较,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到社会利益的推论。斯马特强调:“为了建立一种规范的伦理学体系,功利主义必须诉诸他与其对话的其他人共同持有的根本态度,他诉诸的情感是可普遍化的仁爱(generalized benevolence);即寻求幸福的意向,或无论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寻求对所有人类,或对所有有感觉的存在者而言的好的后果。”[注] J.J.C.Smart,Bernard Williams,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 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7.
以全人类存在者的福祉或以对所有人类存在者、所有有感觉的存在者而言的好的后果来作为行动或行为好坏的评价依据,应当看到,纵观人类思想史,还鲜有人提出如此崇高的理想道德要求或道德标准(以往的功利主义也仅仅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并且这一原则也由于其内在蕴含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而可以给予不同的理解)。
这样一种后果主义的后果评价标准或界定,又可以说是行为者中立的立场,行为者中性价值立场又称“不偏不倚”(impartial)的价值立场(又可称之为非个人观点)。这是因为它不从行为者本身的立场,而是从所有他者或所有人类存在者的立场看待行为者的任何一个行动或行为。或者说,行为者应当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来考虑自己的行动或行为后果。谢夫勒说:“功利主义从一种非个人的立场来评论世界状态,从而使得行为者与其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行为计划和履行的承诺相异化。”[注] Samuel Scheffler,The Rejection of Consequentia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8.斯马特所说的“一个行动”,也就是说,行为者的每一个行动。他并不认为我们的某些行动可以不以这个标准来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是一个行动后果主义者,那就意味着我们终生每次行动都应坚守这样一个标准。人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案例:阿夫鲁特(Affluent)是发达国家的一个富裕公民,她已经为慈善机构进行了有意义的捐赠。她正坐在她的书桌前,桌上放在支票本。在她前面有两本小宣传册,一本是介绍有声誉的援助机构,另一本是当地剧院公司的。阿夫鲁特现有的钱,或者够捐赠给慈善机构,或者够买一张戏票,但不能两者都做。因为她喜欢戏剧,她买了票,虽然她知道,如果她把钱送给慈善机构,将产生更好的效果[注] Tim Mulgan,The Demands of Consequent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从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好来看,阿夫鲁特的决定和行为没有产生最大化的好的后果,因而不是一个在道德上正确的行为。从后果主义的要求(demanding)来看,后果主义必须谴责阿夫鲁特的行为。批评者认为,后果主义的这个要求太严苛,它违背了我们的常识道德。
威廉斯认为,以“对所有人类,或对所有有感觉的存在者而言的好的后果”这样一种后果事态最大化来要求我们的行动或行为,是对人的行为的严苛性要求,这样严苛的要求,将破坏人的完整性,并因此而导致人的异化。威廉斯以两个案例来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在他所举的两个案例中,吉姆的案例更能说明问题:
综上所述,从整体诊断效果来看,磁共振成像优于CT诊断,但是在具体的疾病征象诊断上,二者各自存在着优势,因此在临床诊断中,关键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来做出判断,可根据二者各自优势做出诊断上的互补,从而达到提高诊断准确率的目的。
我们假设吉姆从来没有杀过人,因而吉姆在情感上和道德良知上无疑是不会乐意充当杀手的。然而,在后果主义(功利主义)后果最大化好(善)的道德要求中,根本就没有情感在其中的地位。但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我们与他人的共在,都在于我们的情感。威廉斯说:“以一种纯粹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感情,它们就像是与我们的道德自我毫不相干,也就是说,因此失去了行为者的道德身份(同一性)的感觉,以一种近乎直白的说法(in the most literal way),失去了完整性。”[注] J.J.C.Smart,Bernard Williams,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 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104.在威廉斯看来,如果从行为者中立的立场上看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要求,吉姆就应当把他自己的情感看得一钱不值。
为了清理漂浮的水面垃圾,出现了各种水面垃圾清理装置,按动力来源大致可分为依靠燃油驱动和人工驾驶两种方式[1]。湖泊和城市河道大多采用人工驾驶的方式清除水面垃圾,人工驾驶主要是采用半舱式或甲板机动驳船,由相关人员用网兜将水面垃圾捞出水面,这种作业方式劳动强度较大,工作效率非常低,清除效果并不理想,并且作业环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2]。依靠燃油驱动的方式虽然能明显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清除效率并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但也存在体积较大,运行成本较高,能耗大,易产生大气、噪声污染等问题,并且其不适用于面积较小、地形复杂多变的河道和湖泊的水面垃圾清理。
二、行为者中心选择
我们看到,日常道德与后果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对总体善的促进。日常道德反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于促进总体的善,而后果主义则主张事实上有这样一种要求。然而,卡根认为,虽然后果主义强调我们必须对于总体的善要尽可能地做出最大贡献,但并没有承诺任何具体善的说法。或者说,没有说哪些因素或哪个因素会使得一个结果比另一个结果更好些。不过,卡根认为,无论是日常道德还是后果主义道德,对于善或总体善并不会有多大分歧,即这个人类善的中心成分是人的好生活(wellbeing)。卡根说:“表述和辩护一个适当的善理论对于道德哲学就说是重要的任务,但没有一个人强调这个工作。把这点记住是简单的:不论什么最可能的总体善的理论,都可结合进入极端主义的理论中。这样,极端主义者和适度主义者也就不需要被看作是在对于善的正确说明方面有分歧。宁可说,分歧点只是是否在道德上要求我们去做的,都在于促进总体的善。”[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7.卡根在这里所要说的是,日常道德与后果主义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促进总体善,而在于哪些具体善对于总体善来说是否是有益的。而人们常常认为,后果主义在这方面犯了错误。
吉姆来到南美的一个小镇中心广场上。广场靠墙处站着一排被捆着的20个印第安人,大多数印第安人看起来非常恐惧,只有少数印第安人面无惧色。他们前面站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其中一个是负责的上尉。上尉问了吉姆许多问题,当他知道吉姆是由于考察植物偶然来到这个地方后,向他提出要他亲手处决其中一个印第安人,上尉乐于将此作为一个特权来尊重到访者,那么作为对他的敬意,其他印第安人将释放。当然,如果吉姆拒绝了这一要求,这20个印第安人都将被枪毙。那些被捆绑的印第安人和村民们知道这一情况,他们显然恳求吉姆接受这一“殊荣”。那么,吉姆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注] J.J.C.Smart,Bernard Williams,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 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p97-99.
6) 2号加氢预警诊断模型。该模型可实现反应系统预警,高压分离器到低压分离器流程预警,分馏系统预警,机组预警,调节阀预警。
三、行为者中心限制
卡根认为,日常道德还有第二个特征,即“行为者中心限制”(agent-centered constraints)。卡根说:“第二个特征是它对我们的行动规定了确定性的严格限度,禁止一些类型的行为,即使是只有履行这些行为才可获得最好的后果。我不可为了继承富有叔叔阿拉伯特的遗产而谋杀了他,即使这是唯一的方法来确保获得他的百万财产去捐赠赈灾,虽然我这样的行动所救的生命远比我杀掉的人多得多。”[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4.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限制?卡根认为,这些限制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超出个人的一般权利,如反对有意伤害;二是由于行为者本身承诺着特别的义务,或者由于制度性角色而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对于这些限制或特殊义务在多大程度上是绝对的,或在压力足够大时是否可以违反,不同的提倡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都会同意这些限制一般不能违反。这种“行为者中心限制”也称为“道义限制”,即来自于道义原则的限制。因此,这也表明日常道德中有着道义论的成分。
日常道德的适度主义性质与后果主义的极端性,卡根认为这只是两种道德范型,他认为还有一种范型,即“最小要求”(minimalism),他称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为“最小要求者”(minimalist)。而所谓“最小要求者”,也就是类似于中国杨朱似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在卡根看来,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众多道德归并为这样三大类。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日常道德或适度道德受到这样两端的挤压,它或者倒向后果最大化的极端主义,或者倒向认为任何牺牲都是不必要的极端利己主义(最小要求)。从后果最大化的后果主义来看,日常道德要求太小;而从极端利己主义者来看,日常道德要求太多。如救人要弄湿自己的衣服,极端利己主义者甚至认为这样的牺牲也是不必要的。如2011年10月在中国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2岁的小悦悦7分钟内遭两辆车辗压,18个路人经过,无一人出手相助,最后死亡。应当看到,这18个路人都有着日常道德的信念,如果仅仅是一两个路人,我们可能可以给予他们道德品格上的质疑,但是,如此一个路人群体,我们不可能怀疑他们的整体人格都是极端自私的,然而,他们却不自觉地成了极端利己主义者,即使是费点体力的出手相救的行动也不作为。卡根说:“把这些多重可能性压缩到三种宽泛类型,允许我们集中到一种中心性的哲学问题:适度者处于两方面的相似的攻击之下。他必须对极端主义者和最小要求者辩护他的观点,或者承认失败。内在于他的观点的张力是明显的。通过放弃两端观念上的纯粹性,适度主义者有着内在不一致的危险。当然,这不是说,适度在于居中这个事实本身有理由设想,他的位置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适度主义者的观点不能给予一个连贯的辩护,它易受来自两方面攻击的脆弱性使得这个弱点更易于认识到。迫使适度主义者辩护他的观点以反对极端主义者的要求,而不使他的观点进入最小要求者的怀抱——这也暴露了它的连贯性的缺乏。”[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6.日常道德的信奉者成了道德冷漠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我们难道不应质疑日常道德吗?从另一方面看,卡根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可以看成是对后果主义所追求的后果最大化好(善)的有力辩护。
卡根认为,日常道德对于我们的行为要求,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后果主义那样,要求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追求后果总体意义上的最大化,日常道德的“道德要求我们做什么有一个限度。导致总体上的最好结果的许多行为,日常道德并没有要求我们去做,典型的是,因为牺牲太大了以至于不能要求我们去做它。不能要求我把我的自由时间贡献给为了政治压迫而去战斗,不能要求我放弃我的奢侈生活而去支持癌症研究。”[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换言之,日常道德的道德要求,给予了人们的自我计划充分肯定和相当的自由空间,但是这个要求并不是无限的,也不可能是无限的。尽管如果我捐赠我的资金去支持癌症研究更有利于人类幸福,但是,日常道德同样认为,个人把资金花在自己的生活上,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卡根说:“就日常道德的这个观点而言,允许我有利于我的利益,即使是我这样做而不能导致总体的最好后果。既然给了行为者选择履行行动的权利,并且这些行动从一种中立性的视域看并不是最优的,我就将这种允许称之为行为者中心选择(agent-centered options)。”[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3.卡根所说的“行为者中心选择”,也就是日常道德赞许做的,那么,这是些什么事呢?我的利益。那么,这是些什么利益呢?在卡根看来,不仅是我的福利、我的计划,而且还有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的好生活,以及许多个人所支持的合作计划,都在我的利益的范围之内。卡根指出,日常道德认可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利益选择范围,当人们的目光仅仅关注这些利益范围之内的事,并由此而决定其行为,日常道德并不持反对意见,或者说,日常道德是赞许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常道德不鼓励牺牲,但只是鼓励做出微小的牺牲,而不是有重大意义的牺牲。如在我前面有一个儿童落水了,我救这个孩子所要做的事就是用力抛一个救生圈,或水较浅,我可以下水去救他,但这无疑会弄湿我的衣服。这样花费些轻微的体力或弄湿自己的衣服即做出微小的牺牲,无疑可以得到日常道德的肯定。但是,如果为了帮助他人而做出重大的牺牲,虽然日常道德也鼓励我这样做,做并不要求我这样做。如果需要我冒着生命危险下水救人,虽然有可能把落水的人救上来,但也有可能救不上来,甚至有可能牺牲我的生命,那么,如果我因此没有下水救人,日常道德并不会因此而谴责我。即日常道德对于那些需要做出重大牺牲或有意义牺牲而因此产生更大善的后果的行为,虽然会鼓励,但同时也允许我们不去这样做,或者说,不要求我们去这样做。这也就是卡根所说的“行为者中心选择”。
日常道德既给了人们一定的行为选择的空间,同时也对于人们的行为确立了一定的道义限度。因而,它似乎不像有着后果最大化要求的后果主义那样对于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都给予了命令。因此,相比较于后果主义,日常道德可以称之为“适度主义”,而持有日常道德观点的人,可称为“适度主义者”。然而,卡根指出:“就日常道德的观点而言,那些符合规范地被禁止的行为,在某些压力足够的环境下(如有相当数量的生命处于危急中就是充分大的压力),可能就是被允许的。如果有这样一种临界点,超出它之外限制就被松弛了。”[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5.换言之,日常道德的“适度”,只是在一定条件范围内是如此,但是,如果处于非常规条件下,日常道德的标准就会突破,而就与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要求没有差别。如人们所熟悉的“电车难题”:司机在不可能刹车的情况下,突然看到行驶前面有五个人正在作业,而叉道上只有一个人在作业,因此,按照预定路线,这五个人必被轧死无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司机应该怎么办?大学中无数次的课堂调查表明,多数学生一致赞成司机把轨道车开到叉道上去,即认为杀一救五是正确的选择。多数人之所以会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无疑是日常道德给了他们理由。因此,看似人们以日常道德的常识来反对后果最大化,但实际上这两者并不是截然区分开的。卡根说:“在原则上,这些临界点(无论是否限制或选择)是极其低的。如果是这种情形,相应的限制和选择将是以一个非常有限的方式来追求善:不论何时,处于危急中(依据总体善)的任何东西的临界点将被穿过,行为者将被要求促进较大的善。”[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5.换言之,日常道德一般不要求人们促进总体意义的最大善,但在某些环境条件下,出于自明(pro tanto)的理由,则允许人们促进这个最大化善。因此,人们仅仅根据日常道德的一般要求来反对后果主义的最大化善的要求其逻辑依据是不恰当的。由此我们看到,卡根的论辩策略就是,先指出日常道德是一种对于行为的适度选择的道德要求,因而日常道德是与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是不同的,而人们反对后果主义,认为后果主义的要求过于极端,如威廉斯所说的,从而导致了对人的完整性的破坏。但卡根认为,当日常道德的适度要求的临界点被突破,那么,与后果主义最大化后果的要求就没有什么不同的。卡根的这一辩护是很高明的,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日常道德要求的临界点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被穿过,在正常的条件范围内,并非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此,卡根在这里就有可能是以极端情况来取代正常情况来为自己辩护。对于行为者中心限制的问题,已经激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在后面相关部分,我们将进一步讨论。
威廉斯认为消极(negative)责任的问题是后果主义的后果论的一个问题。所谓“消极责任”,即在一定的情境中,即使我们不做什么,也会产生相应的责任。在吉姆的案例中,吉姆不做什么比他应要求做了什么的总体后果更坏。因此,人们认为,这要吉姆承担责任。但威廉斯认为,不是吉姆的意图而是上尉的意图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如果由于吉姆的拒绝,上尉对他说“我别无选择”,那么,上尉就是在撒谎。因此,威廉斯认为他并不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后果主义恰恰就是要把主要负责放在吉姆头上。威廉斯认为,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所隐含的是,行为者对这个世界负有无限责任,而这个无限责任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后果主义把这样的无限责任强加在行为者身上是没有道理的。
威廉斯挑战的力量在哪里?卡根(Kagan,Shelly)认为日常道德(ordinary morality)或常识(common sense)与后果主义的冲突,是导致后果主义受到质疑的根源所在。在他看来,日常道德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在于两个方面,即行为者中心选择和与限制。在卡根看来,后果主义追求总体后果的最大化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质疑,根源在于人们对日常道德的道德观有着根深蒂固的信念。卡根说,后果主义的道德要求是:“你履行的行为不是被禁止的,否则不要求你履行,这些行动能够合理地期望达到最好的总体后果。”[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然而,卡根又指出,实际上,我们只有少数人相信这一学说,而很少有人按照这一道德要求来行动。因为这一学说对于人们的行为要求来说是很“极端”的。卡根说:“让我们看看这是如何地激进的要求。它要求我们的行动不仅仅关注我们自己的进一步的计划和利益,或者那些我们自己所赞成的个人的东西,而且要考虑所有他者的利益,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总体的善。它要求我问,如果所有事情都考虑,我如何能够做出我的最大的贡献,虽然这将施加值得考虑的重负在我身上,并且它禁止我做任何比这贡献更少的事。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我的大多数行动是不道德的,因为我都没有最佳地使用过我的时间和资源。如果我对我自己是诚实的,我承认,我持续地没有做到我所能做到的那样好。”[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换言之,在人们的想象中,后果主义的后果总体最大化,也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是从全球所有他者的立场出发,来考虑如何利用我和时间和资源。如我走进电影院,花费几美元来使自己享受几小时,这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快乐,但是,如果我把钱赠给饥荒救济机构,因为即使是几个美元也足够使得另一个处于食物短缺中的人得到解救。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花几美元去电影院享受几个小时的娱乐,在道德上就是不被允许的。还可设想如果我把这几个小时用来去看望孤独的长者,这在道德上应当比我进电影院更为可取。因而,如果是这样一种道德要求来生活,我的生活计划也就要被完全打乱,“依据这样一种要求生活将戏剧性的改变我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间、我的财物,我的计划都不是我自己的。就这个观点而言,道德的要求弥漫着我们生活的任何方面和时刻,并且我们都不可能满足它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中的少数人相信这个主张,而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是与之相符合的。这样严苛的要求简直就是非常极端,所以我称这个观点的辩护者为极端主义者。”[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
从日常道德的观点看,一个行为者如果事事都从最大化好的后果出发来考虑自己的行动,那么,也就意味着她任何时候都可能要做出牺牲,因而这也意味着她将“耗尽和穷尽她自己,最终毁灭她能够持续对总体善做贡献的能力(不过这是最终的理解)。因此,极端主义的观点被认为是自我挫败。唯有在要求上更适度,从长远看,行为者将能够做的是使得这个世界更好。”[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7.后果主义的主张真的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吗?如果这个问题不回答,日常道德的主张仍然是有力的。然而,卡根说:“这样一种异议依赖于对极端主义的错误理解,极端主义者并没有因他自身的缘故而要求牺牲,但只是就它们是产生最大可能善的代价而言。极端主义首先是主张,愚笨的蛮干或鲁莽的花掉自己的善物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这根本不是所要求的,这样的行为是被禁止的。每一个行为者被要求去做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去行动:它能够使她的最大努力贡献给总体的善(就她的特定才能而言)。这很可能涉及要认真考虑她的计划,因此要重新修改;至少这涉及对她的行为的长期努力的说明,不仅仅是更直接的行动,并且,这也足够解释了对资源的明智的分派和消费的需要。”[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7-8.换言之,后果主义的道德要求并不是一种愚蠢的道德要求或主张,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对后果主义的严重误解。在卡根看来,后果主义并不是像人们一般所误解的那样,在任何具体行动上选择那种据说是可以直接导致最好后果的行动。后果主义更多的是在这个方面,即首先承认限制你选择那些在道德上受到禁止的行为,如我不能谋杀我的叔叔以获得他的巨额财产去捐赠慈善机构,但是,后果主义在承认这一禁令之后指出,我仍然可以以我的财产捐赠慈善机构,使它产生最大化的善。对于道德所允许的选择,日常道德不鼓励进行最好的后果选择,但是,后果主义则主张在适度或没有禁止的范围内,仍然可以追求最大化的好的后果。换言之,后果主义的道德要求如果是在日常道德要求的可选择范围内实行,那么比仅仅从日常道德对人们的道德要求所做的,应当是更符合道德,并且并不会对人们的完整性产生伤害。这里我们认同卡根的分析。这是因为,日常道德不鼓励我们用可支配的资金去捐赠赈灾,但后果主义的道德要求则鼓励我们这么做,应当看到,如果这样做了,这既对我们的完整性没有损害,同时也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更高尚的事。
无人机遥感技术主要由无人机以及无人机遥控器构成,其中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地面系统,包括地面上的无人机遥控器等其他辅助设备。第二部分是任务的载荷系统,其中包括火控系统以及探测目标等有关系统。第三部分是无人机部分,主要指的是无人机主机。无人机一般较为轻盈小巧,结构较为简单,因此在飞行时极为灵活,操作较传统的航拍更为简单,并且可以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画面以及分辨率更高的反馈图像[1]。
卡根提问道,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时间和我们所承担的特殊义务与责任是完全对应的吗?在履行我们的特殊义务和责任之外,我们就没有可用捐赠慈善机构或进行饥荒救济的资源和时间吗?卡根指出,在人们的生活中,确实有些人所履行的特殊义务和责任将耗尽他的资源和时间,使他没有资金和时间来从事可以产生超出自我的利益或好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更多的人则不是这样,而只是有这种可能。卡根这样分析无疑是因为有着在像美国这样的富裕社会生活的体验。在美国这样发达富裕的国家,多数公民所拥有的资源无疑是超出了仅仅履行自己的特殊义务和责任所需的范围之外;而在履行了自己的特殊义务和责任之外,后果主义鼓励将这些资源或时间用于从总体上看能够产生最大善的后果的行动。并且,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这样的善行活动,日常道德虽不鼓励,但也不会反对。因此,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日常道德的道德要求与后果主义的最大化好的后果要求之间的界线也就消失了。
第一,观察斑块检出率,包括有低回声斑块、高回声斑块以及混合斑;第二,观察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检测结果左颈内动脉、左颈总动脉、右颈内动脉以及右颈总动脉;第三,观察血流动力学指标,包括有收缩期峰值流速、舒张末期流速、平均流速、搏动指数以及阻力指数。
对于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的批评,还有诉诸直觉的批评。人们往往会认为,追求总体意义上的后果最大化,是违反人们的道德直觉的,即道德直觉并没有告诉人们要从一种中立的立场而不是从行为者为中心的立场来追求最大化的善。但正如卡根的分析告诉我们的,行为者中心的立场规定了行为者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选择,虽然其特殊义务和责任也为其确立了界限或限制。这样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选择,其最大化就是行为者自身利益或好生活的善的最大化。人们对于自身利益或好生活的道德理解,受到不同直觉的支持。直觉则是来自于日常道德,或称常识(common sense)道德。而所谓常识,也就是在历史生活中长期形成的直觉。然而,恰恰就是因为直觉是在历史生活中所形成的,所以人们的道德直觉是混乱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卡根以奴隶制下的奴隶主对待黑奴为例:奴隶主要杀掉黑奴,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厌恶黑奴,而之所以厌恶黑奴,就在于他的皮肤的颜色。卡根还从直觉方面对于日常道德进行批评。在他看来,日常道德所产生的直觉是混乱的,靠不住的。卡根说:“设想对我们的直觉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如果诉诸直觉产生的直觉判断上的区别。道德,我们仍然需要知道是否不同应当产生判断上的不同。可能一个奴隶主发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将区别不同,它根据肤色产生直觉的正确判断,何时一个绅士在道德上被要求帮助那个被鞭子抽打的人,何时不需要。仅仅发现居于直觉的这个区别不能充分地为其辩护。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肤色的不同应当支持不同的对待。如果奴隶主没有提供解释,那么,这个区分就与他的道德理论的其他部分不相关联。”[注] 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3-14.卡根认为,奴隶主将会发现,他所承诺的其他原则与他对肤色的区分这两者的相关性水火不相容。也就是说,这位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奴隶主实际上有着相互冲突的直觉,而这些相互冲突的直觉也就表明,诉诸直觉往往是靠不住的。卡根正是以奴隶主对待黑奴这样一个案例来说明以日常道德的直觉来反对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是没有说服力的。马尔甘(Mulgan,Tim)说:“卡根认为,道德哲学中没有直觉的位置,因为它们缺乏适当的合理性。对直觉的拒绝常常为对直觉的起源的一种压缩性解释所支持。如果我们的直觉是进化、文化或自我利益的产物,那么,它们是不可靠的。”[注] Tim Mulgan,The Demands of Consequent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9.卡根以奴隶主对待黑人奴隶的直觉来说明这个直觉与他生活中的其他直觉是冲突的。但为什么会有冲突?因为他的生活中有不同的直觉来源。然而,卡根完全否定直觉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是否会成功呢?卡根是通过否定直觉所起的作用来否定日常道德的适度标准或日常道德的选择。尽管卡根以奴隶主的直觉是不可靠的这样的案例来否定日常道德的直觉的作用,但是人们仍然认为,日常道德的直觉并非完全像奴隶主的直觉那样混乱。卡利蒂(Cullity,Garret)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以下情形对我们的关系有道德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一个儿童在我们面前落水和在另一个国家中有一个儿童忍饥挨饿,但我们没有救那个落水的孩子是错的。因此,根据我们的直觉判断,我们将产生一个原则,采用它来较好地将这种直接可怕的急需的紧急情况与更遥远的地区发生的情况区别开来。”[注] Garret Cullity,“International Aid and the scope of Kindness”,Ethics ,1994,105(1):p104.换言之,日常道德或非后果主义的直觉是有效地支持这样的区分的。
我们看到,卡根对于日常道德与直觉问题的分析,表明他仍然是一个后果主义者。他不仅认为日常道德靠不住,而且人们的直觉也是不可靠的。不过,他已经不像斯马特的对于后果主义的规定那样,要人们事事处处都作为一个后果主义来行事。换言之,在卡根看来,如果人们在一定时候、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后果主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道德上是值得肯定的。卡根通过对一定程度上的日常道德要求的认可,已经形成了一种结合了日常道德版本的后果主义。
[中图分类号 ]B82-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11X(2019)01-0019-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后果主义伦理研究”(13AX03);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 龚群 (195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伦理学,道德哲学。
(责任编辑 万 旭)
标签:行动后果主义论文; 后果论文; 日常道德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