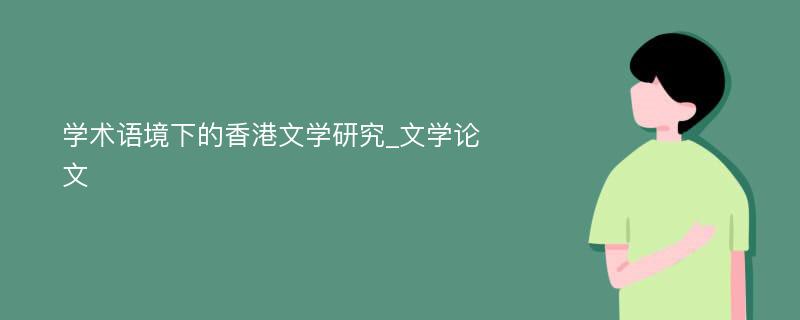
学术语境中的香港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香港论文,学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随着文学狂欢节的悄悄谢幕,是开始建立在自觉的文化反思基础上的良性调整。我们不依赖那种无谓的“批判”,也不趋附爆炒的喧嚣,严肃的作家和学者“临渊而不羡鱼”,回到淡泊自守、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常态。从根本上看,文学搞运动、闹轰动是反常的。文学立于社会和人生,是一种文明的调节,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心灵滋养。文学研究亦作如是观。
香港小说家王璞曾提及,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文学研究“像搞运动似的掀起热潮,热度达到热火朝天的程度”(注:王璞《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香港文学研究》,香港文学研讨会论文,岭南学院,1998年4月。),她因之而对其素质与成果有所隐忧和期盼。此言深获我心。对于香港文学研究,我们自然应当怀有睿智和投入的热情,但同时更需要提到学理的层面延展。不是不要主义,而不妨“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且将科学化的文学研究与通常的文学时评作必要的分工。这里,仅就当今香港文学研究中带有学理性的问题略举数端,一孔之见,敬献刍荛,就正于海内外同好。
一 “大中国文学”:整体的学术视野
学术研究自然不能缺少整体的文化背景。在思考香港文学时,提出“大中国文学”的概念,是出于民族利益和民族情感,也出于文学上香港与内地历史的、天然的关联。从学术思想上讲,整体思维、对待观点、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等,乃是中国思维的特点。由于长时间的地域、历史割断和学术、文化的阻隔,封闭性、偏向性的文学研究在大陆、在台港澳地区均有存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着我们提到整体的学术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文学中国。
“大中国文学”是纵贯历史,打通地域,以中华民族的苦难、奋斗、命运、理想为母题,以母语思维与传达为载体,多民族、多角度、多样态、多语种、多变化的文学,简言之是一体多元的文学。基于此,生长出两个理念:一是任何试图“圈地”的一厢情感或“画地为牢”的固执,都会给学术思想和文学研究带来局限;二是实行现代与当代之打通、主体民族与众多兄弟民族文学之打通、大陆与台港澳地区文学之打通、北方与南方之打通,即四个“打通”。
上述学术理念,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视野从“封闭的空间”→“距离的空间”→“共享的空间”的转移。从这里出发,我们看到的将是整体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地图。具体来说,我们就不至于把“大陆当代文学”等同于“中国当代文学”,而是合乎情理地把港台澳地区的文学包容进来,并寻求普适性与区域性的有机联系(不像目前有些著述是简单的添加与拼贴);我们也不至于把“中国当代文学”(实际是汉族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分离开来,而是建立统一的多民族文学的合理构架,内里互渗互动;我们也不至于把某种被夸大为历史的神圣的创作方法作为衡量一切文学(无论内地还是香港)的标尺,而是以“有容乃大”的襟怀鼓励多种多样文学的共存共荣;我们还不至于因袭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在诸如文学的“中央”与“边陲”、“北方”与“南方”、“主流”与“非主流”等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是处在同一地平线上进行真诚、有效、取长补短、既有差异又可能共融的对话,对和鸣与变体有更大的兴趣。可以确认的是,我们在同一天空下沐浴阳光、呼吸空气和经受风雨。任何一位作家和学者,所创造、所论证的不过是文学空间的一角,谁也难能拥有全部,独占话语霸权。自然,一旦进入研究,应当力求使思维向度、价值尺度、书写法度趋近科学。
联系到香港文学研究,有些概念、提法是否也需要调整或修正呢?
例一:“殖民地文学”的提法。我以为从法理和学理上是讲不通的。这一说法在不少论文、包括《香港文学史》中依然出现,其严谨性值得考虑。诚然,百年以来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统治,但不等于香港就是殖民地,更不能说香港文学是殖民地文学。这是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国统治和管辖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香港是一个地区,且始终是并未全部丧失主权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故“殖民地”概念不宜用于香港。28年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不久,当时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于1972年3月8日致函联合国非殖民法特别委员会主席时明确宣称:“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同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有关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上除去的决议。既然“殖民地”一说已不成立,“殖民地文学”当然也不能成立。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既出于法理的常识,也正视香港文学的历史与现实,即香港尽管华洋杂处,东西方文化交汇,但占主流与主导的是华人及其作为文化载体的华文文学——它无疑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学的历史延伸和区域流变。
例二:“中国性淹没了香港性”的说法。如旅美学者张错认为:“无论是早期伍廷芳的《中外新报》,或后期抗战的戴望舒或许地山在香港推动的文艺活动,都代表了两种极端趋势,对香港文学发展极为不利——一种是殖民主义下对国族的离心;另一种是民族主义下对国族的向心。尤其后者视之于戴望舒及许地山,更是照显,因为他们的国文学是以中国当时的北京或上海文化为依归。小岛气候的殖民地香港,自难产生任何本土意识及身分。”(注:张错《过客与还乡》,《香港文学节研讨会讲稿汇编》,香港市政局公关图书馆,1997年1月。)香港学者黄秉显也说,香港文学“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后,完全失去身分,缺少本来的个性,萌芽新的香港文学,已不能继续生长了。”(注:黄康显《抗日战争对香港文学的冲击》,《香港文学》第139期,1995年。)诚然,香港以及文化、文学都有其特殊性,文学也应有独特的个性,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尊重历史和现实;“香港性”反映了要求本土文学对香港的关怀与锲入,要求对百年风雨中生长的香港的特征与价值有深切的体认,要求艺术表达上有别于内地的香港色泽,无疑有积极的意义。但这一“香港性”与“中国性”不是对立的,更不宜被无限夸大乃至逸出中华民族文化母体去孤立地谈论。香港有些作家作品似乎总是微妙地在“暧昧自由”和“具体认同”之间寻求“边缘身分”。事实上,所谓文化身分,是版图意识、文化归属、地域定位及审美取向的综合。香港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命运,以独特性贡献了、丰富了全局,这并非身分之淹没和跌落,恰恰是身分的确认,且以“小沧桑”映现“大历史”而为香港文学增添厚重,增添光彩。也因此,正如香港作家冯伟才所言:“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香港在地理环境、历史源流、文化根源各方面,都是中国的一支,它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母体而单纯的‘本土化’”。(注:冯伟才《评“香港文学本土化运动”》,《文学·作家·社会》,波文书局,香港,1985年。)
“大中国文学”是一个视野,一种器度,是我们深化香港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
二 文学形态与研究话题
从“大中国文学”出发看待香港文学,我们坚持“和而不同”的学术思想。是和合,是和生,是从学理的高度去探寻共通的东西;却也首先从差异入手,去分析香港文学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的样态、性格与景致。应该注意到,除去地区差别外,香港文学本身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风尚、鉴赏趣味、语言形式等方面,与内地有历时的或人为的差异。这种差异,既为“大中国文学”提供弥补性的充实,也使我们在某种对于间隔的省思中不妨换一个角度审察,以获得更接近实际的判断。当某些正统的学人对武侠小说不屑一顾、视之为“地摊文学”时,金庸却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且在通俗的形式中写出严肃意义的华人文学家之一。当内地作家王蒙在80年代初以《春之声》《海的梦》等名噪一时并被大陆学人呼之为“中国当代第一批意识流小说”时,殊不知将“异”纳入视野,就会晓得早在1963年,刘以鬯就以《酒徒》在香港问世,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内心的开掘和手法的运用上,其“现代”的程度明显超过了前者。同样,香港都市文化、言情作品以及乐观、健康、轻松不僵的流行歌曲,以其反哺力刺激着内地的都市文学,亦证实着世俗化是现代文化的表征这一道理。看到“异”,通过分析比较,就为同一文化体内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契机,更好地辨证“中心”与“边缘”的歧异、共融与变体中衍生出来的文学现实的价值形态和意义,也展示一种特殊地区的文学如何被边缘化以及怎样重返中心的过程。
站在学术立场上看,我们承认香港文学研究有多种研究途径与选择的可能性。在这里,差异的确认使我们关注多元,差异的并存使我们承诺互补,差异的协调使我们寻求共识。这种差异,往往表现在对香港文学形态的观察与研究上。
文学形态是生态(文化氛围和接受情境)、心态(审美视点和心理意欲)、姿态(写作态度和叙事方式)和步态(历时性衍进或共时性生长)综合形成的可分性物化形态,是客体与主体交互作用,并在文学传播过程中始端、中介和终极诸环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实践的产物。文学形态因之而有类型的特点。西方一般把文学分为“雅”和“俗”两种形态。内地有些学者用纯文学、通俗文学、社会文学三分法解释香港文学。香港有的学者认为香港因缺少士大夫传统、战乱与革命以及作家职业化而不具有“社会文学”的特殊因素。这种区分法可以继续讨论。事实上,香港文学因有消费性的介入而难免雅与俗混杂、深与浅并存、文与野共生,有时大雅若俗,有时俗里透雅,也有时以文化外求造成“边界”模糊而一时难以确定。
当今的文学世界的确是不断地设立疆域——不停地左右移动——又不时地拆除界碑,人文心灵已难设防,学科之间鸿沟不再。不过,对于香港文学,若是以学术性、艺术性去体察,我感到可以考虑换一种视角,即姑妄言之为“诗性哲学”的角度去认知,是否可以区分四种文学形态:意识形态,意象形态,意绪形态,意义形态。
意识形态文学,在香港虽然不具有内地明显的“体制”、“主流”、“政治”色彩,但仍然不乏以文学面貌出现的道义文章、教化文学。这种形态的文学,属上层建筑现象,具有某种精神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在功能上主要作用于人的思想、道德、品格、理念。
意象形态文学,在香港突出地表现为大众文化的“意象”(形象)特质。由发达的现代科技孕育的大众传媒,催动着一类文学向直观性形象性靠拢的努力,且常常与影视、明星、竞技、衣食住行密切联系,多有感官色彩,更形而下地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感官”的、“图象”的和“视象”的,其本身就带有反精神反语言文字的倾向,却在大众文化发达之区迅速获得相应的公共性。
意绪形态文学,是作为香港的自由空间甚广和作为香港作家的书写空间甚小的矛盾的产物,表现在一部分作者走“短、小、轻、浅”的创作路线。短短的篇幅、小小的情思、轻轻的笔墨、浅浅的意绪,若是新人,再加上帅帅的照片和亮丽的包装。一缕清风,一湾池水,一重波纹,一点摆设,都萌生一份情绪和遐思,让读者在休闲中感受一些愉悦。这种形态的文学带有更多的消遣性。
意义形态文学,主要在追求精神、个性、人格、思想、心灵、理智的一部分香港人文型作家中运作。意义是人类以其精神对存在对象进行诠释的产物,是精神世界的核心,也是严肃的精英文学的一个关键词。意义形态文学不趋炎附势,不追求时尚,以其独立的文化品格与知识形态,以美学的和艺术的风貌呈示自己,直指精神的深邃之处,并具有鲜明的主体话语。这类文学在香港屈居于当下文化的边缘状态,却也成为作家走向“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注:陈寅恪挽王国维的碑铭。)的一个通途。
以上只是粗略的考察与划分。自然,需要具体的作家作品去实证。结合上述文学形态问题研究,我们还需要深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探讨,在带规律性和前沿性课题上做文章,并力求有更多的原创性。这里,我愿意提出下列题目,供同行参考:
(1)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香港的地位、作用及流播;(2)香港地区文化/文学发展中两极化现象;(3)香港文学在基座上的倾斜与调整;(4)香港都市消费型文学的得失;(5)从香港文学看“大都会”与“小市民”的文化冲突;(6)香港文学创作中“传统”与“现代”的分流与转换;(7)“香港意识”和“香港性”研究;(8)香港作家的文化身分及文学呈现;(9)香港文学的创作自由和艺术自津;(10)香港文学的母题与变奏;(11)基督教文化与香港文学;(12)香港文学作品的语言与叙事(包括方言书写);(13)香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14)香港文学中的现代主义;(15)后现代文化和新一代创作;(16)香港女性文化/文学研究;(17)香港经典作品“异”的问题之研究;(18)香港文学中的“文化驿站”问题。
上列的题目,有的可能较为宽泛,但因相对重要而难以规避,关键在于新思维的介入和新视点的切入。只要充分地占有资料,深细思索难点,是可以写出一批高质量的论文来的。不必重“史书”而轻“论文”,一篇有独到见解、殚精竭虑的论文,往往胜过拼贴叠加仓促速成的“专著”,况且论文的质地也为提升治史的品位提供了条件。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香港文学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空间中特殊的、有价值、有建树的一方天地,是文学中国的大树上优长与欠缺并存的繁富的枝叶。在文学研究中,不宜用普泛的、绝对的、大而无当的统一标准去评判香港文学;多种姿色、品味较高的香港文学作品,以其特异的姿态自然地融汇于文学大河中,共同创造着我们的东方话语。
三 主体操作的反思与学者批评的界说
对于香港文学的研究,我们是否需要一种以现代文化为基础的现代思维的建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思维基础而言,我们有些研究论文在思维的人类共通性范式(如因果律、矛盾律等等)上和中国传统的、特殊的一种唯圣思维方式上,程度不同地显示其屈从习惯与经验倾向。一方面,研究的思路是逻辑的,在普遍意义层面上有参与操作的价值,同时易陷于空泛,且常常为经验美学所局限;另一方面,唯上、唯书的阴影笼罩研究,在既遵从逻辑又排斥理性的特殊悖理语境中徘徊,往往浮在无方法(缺少多向度多扇面展开的方法)的直观体验上。这样,往往重视结果而不注意过程,侧重综合而不注重实证,惯于模糊把握而鲜有分析解剖。我们缺少“中介”、“过渡”的理论与研究。进入80年代以后,更出现了一个悖论:西学大量引进,批评实践却越来越多地体验化、实用化、散点化。若作反思,我们在香港文学研究中曾经有过的“拾到篮里便是菜”、“现炒现卖”、“郢书燕说”以及泛泛而论的“友情文字”等等,正是主体操作比较浮躁的证明。
文学研究的思维基础不能摆脱中国传统思维的合理性——那思维内里的辩证因素、统摄观念、“文以载道”、直觉体认、模糊特征、阴阳模式、主体意向等,都应当合理吸收。但是,既已进入现代,同样作为人类智慧成果的西方哲学中的认知结构、审美观念、本文策略及现代思维科学,也是不可忽视的学术资源。在文学研究中,我们应当有新的现代思维建构,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将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性交融,将历史的、美学的和文化的研究结合,将理论的结构性准则(包括细读的符码方法)和对象挂钩,并以开放的文化相对主义视角提出问题,进行现代人文精神背景下前沿课题的原创性研究。对于香港文学研究,自然也有现代思维的建构问题,要有所反思,有所调适,以更好地进入学术语境。
这些年来,中国内地对香港文学研究是重视的、颇有实绩的。已有多部“史”的著述问世,有若干作家专论出版,还有一批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发表,促进了内地广大读者对香港文学的了解和理解。在这中间,刘登翰教授主编的《香港文学史》,集思广益,求博求真,在探讨的广度和深度上具有一定份量。艾晓明博士对香港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令人钦羡的投入,她的张爱玲研究和《北望中国》等多篇论文,立意超拔,飞文梁翰,倘惊知己。广东占尽天时地利,广东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深圳大学的学者,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成果甚丰,读者随卷研读亦不难发现其中的新见。
作为国家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任务是对中国文学进行全面、系统、尽可能深入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包括各个历史阶段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地域文学等,并蕲求以文艺学去统领与提升。香港文学连同台湾文学、澳门文学(统称“港台澳文学”),是80年代以后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并由研究人员从事著述的。相对于沿海地区,作为后来者,我所于1989年3月7日正式成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1993年改称为研究中心。事实上,研究人员都带有“兼职”性质,因长期从事的分别为文艺学、现代文学或大陆当代文学研究,袁良骏教授就自我戏称为“票友”。不过,既然介入就要进入,即把香港文学置于学术层面上,以创造型思维和建设性品格展开研究,以心态的自立性、批评的学理性、阐释的规范性为追求,争取拿到一张香港文学研究合格的通行证。
基于对批评现状的反思,我们的研究需要“学术的转移”,即从“趋附性研究→原创性研究,单向性研究→多重性研究,封闭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平涂性研究→典律性研究,广告性研究→剖析性研究,移植性研究→重新语境化研究”,总之,不使研究浅表化和虚幻化。我们在研究人员中提倡“八字学风”:大气,凝重,实证,灵动。大气是指论著要有器度、气象,不小打小闹、小里小气;凝重是指有思想的深度和厚度,沉甸甸的,有精神的力量;实证是指言之有据,用七份八份资料才提炼出一个精彩的观点,而不是只凭一个材料就冒出好几个理念;灵动是指有灵气和才情,行文不可呆板,不要“土八股”、“洋八股”、“党八股”,少一些“正确的废话”,而多一些鲜活和亮泽。
我所涉及香港文学的研究成果总量不算多,总共一百五十万字左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杨义教授在其152万字的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三卷专辟“华南作家群”和“上海孤岛及其后的小说”两章,对黄谷柳、侣伦、徐訏、张爱玲均有专节叙述,将香港文学有机地纳入中国现代文学总框架中,此一研究思路是富有原创性的。他的专题研究成果之一的《金庸小说艺术论》,也有精到的剖析。袁良骏教授自1993年起全身心投入香港小说史料的收集与梳理,70万言的《香港小说史》经6年呕心沥血终于杀青,以其资料的翔实、理路的清晰和学术的灼见,弥补了香港分类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缺憾。赵稀方博士在三年攻读期间,以香港文学为主研方向,以城市文化与香港文学的关联为切入点,对香港都市文本进行文化学、文艺学与比较学相结合的述析,其博士学位论文《香港小说的文化身分》受到好评且行将出版。今后,我们的初步设想,一是在制订人文学科研究规划时,对港台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予以进一步重视,使之课题到位、人员到位、成果到位;二是以“当代文化学”介入香港文学研究,促进知识增长和学术推演;三是强化专题研究,要求做得更深入、更扎实、更有创造性;四是发现和培养研究港台文学的学术新秀,使这门分支性学科的研习后继有人。
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1874-1936)于1930年结集出版的《批评生理学》一书中(注:中译本更名为《六说文学批评》,即蒂博代于1922年作过六次有关文学批评的讲演,于1930年结集成书。中译本译者赵坚,三联书店1989年3月第1版。),依批评形态划分为“自发的批评”(读者)、“职业的批评”(教授)和“大师的批评”(作家)三类,并指出各有各的“地域”、“气候”、“物产”和“居民”。伏尔泰则把职业的批评比作“猪舌检疫员”,似乎教授们的批评与研究,先天地怀有“非我族类”的警惕。同样,在现时香港或内地许多人心目中,“职业的批评”——我们不妨称之为“学者批评”,这一称呼含有一种贬意,仿佛成了“学究”、“迟疑症”、“高头讲章”的代名词。然而,在香港文学研究的多种多样的批评形态中,作为对一种批评品质、批评风尚、批评话语和批评境界的向往,“学者批评”不仅应自成一家,而且是香港文学研究中可尊敬的部分。它属于认真的、自律的、尽心将“寻美”与“求疵”相结合、讲究学术风范的批评。它决非掉书袋,不是用凝固的结论或死板的知识先验地去框缚活跃的艺术生命。它不企图、也不可能占有真理的全部空间。根据我们的体会,“学者批评”应具有如下特点:
(1)在相当的文化背景下,对于对象和问题进行庄重的历史的与美学的透视;(2)从本土文学与异地、异域文学的比较中,从本学科与他学科的关联中,敏锐地发现和论证文学现象背后的重要知识命题;(3)汲取我们时代文化思维的最新成果,更新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使文学研究以思想的独立与开阔同世界对话;(4)不搞“破”字当头,“大批判开路”,而以“立”为本,执拗于探索,着眼于“建设”;(5)思想家的冷静、艺术家的悟性和解剖学家的精心相结合,用清爽的智慧滤选阅读行为;(6)批评者与创作者之间保持平等的真诚对话,也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不率尔操瓢随意“捧”“棒”;(7)潜心进行知识成果和学术资料的梳理,并不断“重读经典”,逐步形成在相关领域中可资运作的、带有一定规范性的理论模型;(8)做道德文章,不唯我独尊,对不同观点怀有学术雅量;(9)不尚空谈与包装,但求实在与厚朴,行文走笔,以“辉煌的枯燥”和“壮阔的简洁”为优雅的极致。
上述境界,我们实难为之,却心向往之。不管怎样,我们开始了对香港这片文学土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耕耘。香港文学对我们来说逐渐成为一个真实世界。我们怀有历史感和审美之心,自然而然地要碾碎、弄乱、裁剪这一现实文学枝叶和花朵。我们不倦地鉴赏、分类、读解、品味、整理、推论或建议。像历史学家拥有时间,像作家拥有血肉之躯鲜活跃动的人物,我们在共享的时空中将香港文学景象逻辑化、条理化,使之成为有机的生命体,正是学者批评的心路历程和守土之责。愿我们的理性和智慧的火焰,助燃这文学艺术之城应有的光亮。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香港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