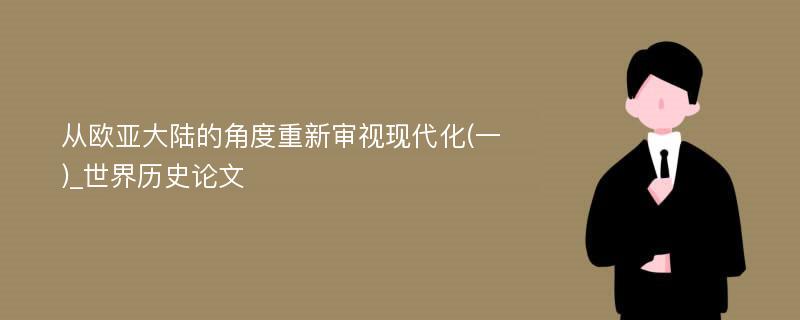
以欧亚视角重新审视现代性(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亚论文,现代性论文,视角论文,重新审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现代性》中,我试图揭示当代全球意识的含意,以期理解现代性之构成。在这里,我希望特别指出明朝(1368-1644)的发展,它紧接着蒙古的扩张,后者第一次为从整体来想象欧亚创造了条件①。受这种新的意识激励,历史学家开始推翻过去30年来对跨洲互动在“现代世界”形成中作用的解释,过去人们把“现代世界”看作主要是欧洲意图和行动的产物。他者亦参与了现代世界的形成,对这一点的承认已经挑战了深嵌于欧洲现代历史编撰学中的假设,即现代性是欧洲历史内部发展的产物——以欧洲中心来组织历史,这便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基本意义②。转向对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内在社会关系的强调,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仍然没有充分面对的复杂问题:对现代性形成的参与为我们理解其他社会提供了何种意义。它们是否也极大地改变了这些互动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将怎样解释这些变迁?
简单地说,发展是社会内在动力的产物,这是欧洲现代史学的基本假设,它已经成为以欧洲现代性霸权来探讨全球历史的基本思维方式。在现代化话语的两个主要变体——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扩散过程中,这是非常明显的,在民族主义史学中同样如此,后者将民族视为他们自身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假设激活了全部的中心主义,如欧洲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以及伊斯兰中心主义。
在这里,我们将评论这些中心主义的瓦解。全球化观念已经加入了在帝国主义和依附理论或者世界体系分析中出现的对这种中心主义的早期挑战,前者亦使关系处于比自主发展优先的地位,那种发展创造了历史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构型,并且是以先前历史为条件的。把超越民族国家的单位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这种再空间化的当代结果强调了所有那些介入关系中的社会的同时代性③。现代化话语的进化论假设已经被结构性时间的持续所替代。不只是追随某种内在逻辑,有些社会构型也被看作更大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服从在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基础上的创造或再造结构的那种动态力量。时间亦具有一种时态性维度。这并不否认为诸如国家和文明那样的历史构型的重要性。但是它拓宽了那些力量的范围,这些力量正在形成,或者更广泛地说,把一种更大的偶然性引入它们的历史构型中。它也改变了历史得以组织起来的边界,或者更彻底地,拒绝关注所有的边界,把它们视为历史理解的障碍④。
这是跨大陆理解现代性的重要性所在,通过质疑一个阶段是否早期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提出下述不同的主张——虽然以过去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但结构性关系参与了每一个阶段的形成,这种做法不仅为探寻其形成过程中更广泛的力量打开了空间,亦把一种结构的偶然性引入它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如果它不只是一种更复杂的欧洲中心主义视野——更大地关注欧洲现代性形成过程的外部力量——分析就要求更密切地关注其他部分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欧亚外围的其他主要力量的集中;从欧洲一极到中国和日本另一极,中间是奥特曼、萨非、莫卧儿帝国。无须强调,15世纪以来,更大的超大陆的语境包括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后者在政治上是边缘性的,但作为新的财富源泉在现代性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的主张如下,某些欧洲社会表现出惯常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点,与此类似,其他欧亚社会在它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特点上也经历着差不多的转型。所有的社会都承认,这是“早期现代性”属性。在诸如本雅明·埃尔曼这类学者的著述中,“早期现代”不同于现代,贯穿大陆的共同性是得到承认的。但是,这种区别也掩盖了一种目的论。在被作为现代性叙事写成的欧洲历史语境中,“早期现代”这个术语的意义是现代性的前奏,其承诺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实现——即使转型处于争论之中。因此,由这个术语描述的阶段并非只是“年代学的”,指某种时间的框架(如,公元1450-1750年)。它也是那些注定创造欧洲现代性的那些特点的“萌芽”(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成的比喻)。任何把这个术语应用到其历史的做法,也都具有这种目的论,再一次强调那些特点不能在其他地方产生。另一方面,如果重点是这个时期所有社会的共同性,那么欧洲的“早期现代性”或许将是成为问题的。我们必须因此追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只是在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及欧洲人在全球的纠缠是否同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兴起有什么关系,后者使欧/美的垄断主张合法了。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可能性,是对增强了的全球互动之力量的回应,它最终证明并不能适应通过殖民在全球扩张的资本力量。对现代性的这些“别样的”反应,不是现代性的前奏,它们也以一种事后之见表明了其他的特点(无论其是否关心自己的未来)。这些别样的方案,无论它们具有什么价值,都必然遭到欧/美现代性的压制,后者从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那里得到了力量。
为了回避目的论,最好把被标识为“现代”和“早期现代”的两个阶段看作现代性历史之矛盾的而非进化的阶段。欧/美现代性不仅建立在对他者的征服之上,而且需要征服自己的过去⑤。我们需要恢复亚历山大·伍德赛德所称的“失去的现代性”,不是为了反对的恢复或复兴目标,而是将其作为资源帮助解决已经变得严重的现代性难题。这意味,无论如何都得事先承认,正在恢复的东西不是“早期现代”、“前现代”或传统,而是在其最初阶段上的其他现代性方案。正是在这个阶段上,才有可能谈论“其他方案”,而不是当前,由于卷入资本主义现代性,今天我们已经放弃了其他现代性主张。如果欧洲注定要“地方化”,那么正是在现代性的这个早期阶段上,那时欧洲现代性只是多个现代性中的一个,而不是像当前这样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在全球为现代性提供基础⑥。
出于相同的理由,我在此表明,当前谈论“全球现代性”具有更大的意义,即比晚期现代性更有意义。当前不只是源自现代性早期阶段——“欧洲中心的现代性”——的发展,而且寻求根据多样的和别样的现代性来否定它。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它亦掩盖了自己在它拒斥的现代性之中的基础:现在已经变化全球化了,并且以根本的方式改变着其他社会(并不暗示着同质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对全球的两个世纪的统治或许终结了(尽管围绕它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再一次,我们面临着多种形态的现代性前景。但是,贯穿着现代性的这个时代被最近两个世纪的经验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标记。全球各地的宗教复兴都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宗教复兴试图否定既往被视为现代性的东西(在现代性起点上,它自身便是宗教的否定),它们利用了由全球资本主义提供的最发达的实践和意识形态技术,而他们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受益者。
从这一视角看,存在着好的理由保存描述蒙古入侵以来的世界的“现代”这个术语。然后,考虑作为跨大陆现代性的“早期现代”是有可能的,欧洲现代性阶段恰当地紧随其后,后者具有额外的便利条件来强调两个阶段为什么从全球视角来看如此地相互不同。因此,与欧洲(以及美国)霸权下的现代性不同,在这一个阶段的各种发展轨道被有益地视为不同于现代的形式,可以说,一种替代的形式,它曾被欧洲现代性的胜利排除在外。它们指明的未来之路并没有消失,这一点在不同现代性的主张中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主张已经伴随着全球现代性、现代性展开的最近阶段再度浮现。但是,它们也被改得面目全非而难以辨认。
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化和革命
如果我在今天转向帝国的中国,全球化已经激发了对中国发展之长期问题中的兴趣,最重要的是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兴趣,这是我描述为跨大陆现代性的阶段,与明清时期一致。尽管历史学们提供了可望不可即的符号证据,甚至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早期阶段的起源证据⑦,正是明朝时期,从16世纪开始,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最持久的关注,将之作为“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加以研究。这并不令人真正吃惊。正是在明朝,中国社会采取了耶稣会教士与其相遇的那种形式和范围,随后将其投射到整个帝国的过去。这是中国在现代历史学中的形象,亦是流行所称“五千年历史”的含义——这是一种与那种形象相当不同的形象:一个王朝接着另一个不断更替、松散的中央集权成功地把所有部分都统一起来、低人口密度。宋朝给后来的王朝留下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遗产,它成功地形成松散的统一,与两个游牧民族的君主共同统治着后来被称为中国的地域。在第一个1500年的帝国中国中,超过20个正式承认的朝代统治过中国(大多数时候,它们都是同时存在的),然而只有两个高度中央集权和“理性化的”长命朝代统治着其后600年的帝国,这一点是极具启示意义的。下述这点是相当真实的,过去的遗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全部的过去朝代中,存在着几个经济上的全盛时期,最显著的便是唐宋,但清朝却是彻底变化的阶段。然而,只是在这一阶段上出现的人口扩张,使它本身具有不同于先前朝代的特点,成为一个不同的社会。什么东西导致了这种变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们在研究中国与欧洲类似的发展时,试图找到新的数据来解释16世纪明朝以来的变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50年代达到高潮,人们把明代中国视为建立在不稳定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高度统一的社会,把那种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征兆。常见的推理是,生产力上的发展——即,14世纪以来农业技术的发达,包括谷物产量提高和农业工具的改善——导致生产的扩张。这刺激了商品经济的繁荣,接着推动了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在财产和生产的集中方面,变化是明显的。在农业中,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创造通过集中管理和雇佣工人的大块土地。土地的集中又导致对农民的大规模的剥夺。这创造了自由的劳动力,即资本主义的前提。一些没有工作的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而其他人则迁移到成长中的城市变成了工业工人、小商人(如小商贩),或最坏情况下,流浪汉。因此,中国社会从明代晚期开始便在农业中呈现出阶级分化,那是资本主义的特点⑧。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证明,那些一直租地的农民变成了佃户,即使在这些地方,他们支付的租金不再是“纯粹的封建租金”而是具有“资本主义本质”的现金租金。换句话说,地主-佃户之间关系也呈现出资本主义形式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工业中观察到差不多的生产集中。那些时代的大型工厂雇佣了几百号,有时是几千号工人。李之勤主张,在丝绸和棉纺织品生产、陶瓷和采矿业,明朝的工业都表现出资本主义“制造业”的特点⑩。这些结构变化为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包括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提供了基础。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和翦伯赞,都做出下述结论:反对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在17世纪后半期(明清过渡时期)是十分突出的,这被证明是中国的“启蒙”,实际上是一个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的新的矛盾的体现(11)。
马克思主义对明代变迁的评价受到了一种目的论的限制,该目的论植根于所谓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自从斯大林在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提出,它便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指导教条。通过把这种历史分期内化成所有社会的普遍命运,中国历史学家从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把中华帝国的社会看成衰落中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绝不会使中国向下一个阶段发展,即理论上必然的资本主义阶段。尽管许多人主张,晚至20世纪,中国社会仍然是封建的(半封建的),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现代表了一种与商品经济的在理论上的反常发展的相妥协的努力,这种发展是在假定为自然的、自足的农耕社会中进行的。然而,绝不会开花的萌芽,这暗示着,帝国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失败的历史,或者,如一个历史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讨论中滑稽地指出的那样,如果资本主义在2000年前就成为萌芽,并且到了明代还是萌芽,那么就可以说,种子确实种到了不毛之地上(12)。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发现普遍目的论的努力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揭示的那种变化的误认。然而,这并非证明不考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正确的。有点反讽的是,在中华帝国内在动态中“发现”普遍的目的论,这种做法巩固那种努力,世界转折以来,中国学者一直试图建构一个线性的历史来担保中华民族的连续性和持续演化,我将在下面讨论这个问题。附带说明的是,激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那个问题可能在多种方式上而非一种上不相关,然而它激发了在揭示重要数据方面极有创造性的研究。他们有关明朝变化的发现已经被何炳棣和狄百瑞这样的历史学家所证实,后者同样地在明代社会和意识形态中看到了深层的变化(13)。如一本更新著作的作者评论的那样:
……帝国晚期(16世纪至19世纪),实质性地不同于它的先前阶段,核心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相当明显的持续性表明了这一点……经济增长和变化,这导致了精英的组成和特点的变化;部分由经济增长引起的教育体系的扩大;以及教育的扩大的复杂激发了大规模的印刷术的发展。(14)
历史中的全球性意识打开了新的研究大道,以及解释这些发展的可能性。新意识明显地影响了我们观察中国历史的各种方式,以及历史工作。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他的航行的被视为中国历史之中的全球化趋势的证据。过去十多年来,有关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出版物显著地增长了。全球化激发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全新兴趣,对于中国历史学也有很大的意义。反讽地,从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换,也鼓励历史学家在比较研究和普遍理由的研究中超越民族范围。20世纪90年代,诸如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这样的现代化范式有影响的提倡者,认为现代化不是对革命范式的替代,而是能够说明革命以及更多问题的范式。他及其学生们试图概念化现代化来说明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环境,包括它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特殊方式,在这些方式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帝国主义机制。罗的开创性著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5),给人的最强烈的印象是他对现代化问题的全球理解。他的“一元多线”论令人想起“多样的”或“别样的”现代性观念,这种观念最近在美国学者中很流行;两者之间主要的差别在于他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社会的发展轨迹形成中的作用看法。他的学生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后继者们继承了罗教授的研究(16)。
尽管承认这些著作的多线性,但这一点是明显的:现代化话语在中国持续地支持理论上的非线性,而不是追随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以及其马克思主义先驱的现代化话语,那种非线性与它的全球化假设明显地抵触。发展是通过三个渐进的阶段进行的(原始的、农业的和工业的),每一个阶段都由技术革命作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话语对于“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不同的社会都可能在阶梯式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一点严格地决定了多线性主张的性质。在这个图式中,中国一直都是农业社会,直到在欧洲的影响下进行工业化阶段,而它在今天则迈向“知识经济”浪潮。在诸如何传启的著作中,别样的发展存在于这个下一步的发展阶段上(“二次现代化”或,“二次现代性”)。罗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话语综合起来(其著作明显地表达了由“四个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他几乎对生产力的独断式强调为马克思主义消融成稍有不同的现代化话语版本打开了道路。诸如董正华这样的后续者,继续主张更多地关注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而何传启等人,在把现代化看作是离开传统朝向制度和文化特点上的趋同过程时,则与海外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现代化鼓吹者几乎没有差别。同样的,在他的著述,文化似乎成为现代化潜力最重要的方面。一旦这些潜力实现了,社会就各自不同,但它们都是建立在共同的现代性基础上的(17)。
与这个脉络稍微不同的是诸如汪晖这样的所谓“新左派”。汪的工作大多归于思想和文化而不是政治经济领域,他显著地强调最好被描述成反现代主义的东西,对中国社会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攻击推动着这种动向。反现代主义本身并不暗示着如此远地脱离作为别样现代性源泉的现代性。然而,他的著述,就如其他同新左派联系在一起的著述,都试图坚持某种革命遗产来反抗由当代现代化引起的问题。反抗也提出某些与现代性起源有关的问题,而欧亚(与西欧相对)过程在那些源头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
现代化语言在非中国的中国史学家们中间甚至更加普遍。蒂莫西·布罗克最近一本关于德国与明清之间相互影响的著作便把全球化植入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植入全球化(19)。最近数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例如弗兰克《白银资本》、王国斌的《转变中的中国》、彭慕兰的《大分流》以及阿锐基等人编的《东亚的复兴》等等(这些著作都已经有中译,所以本书中采纳了那些流行的译名。译注。)。受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激励,这些著作中的某一些使我们回到马可波罗的视野,把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因此,问题几乎自动地形成了一个目的论导向:“如果它们过去是那样领先,那为什么后来又如此落后?”我们或许会想到,它们或许根本就不是在我们的方向上处于领先地位,即使他们呈现出许多现代性的征兆。今日中国追随的轨迹并不仅是“复兴”,而且是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是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果。弗兰克否定了历史资本主义,他坚持5000年世界体系视野。在《白银资本》中,他回到了资本主义是世界宿命这个古典经济学假设,但通过全球不同的空间及时绕过了它(20)。经济目的论同样明显地存在于王国斌与彭慕兰的著作中,特别是后者,忘记了社会的和殖民的关系,以及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巩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由于这些遗忘,他们的著作便因此压制了不同社会之间的重要差异(21)。
这些著作的框架建立在那些并没有明显地主张世界历史的早期中国研究之上,该框架极大地改变了一直流传的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看法。然而,这些著作以不同的方式遇到了两种需要批评性探究的直接对立的趋势。其一,以一种更新的伪装把欧洲中心主义永恒化了,这在他们把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测量其他地方发展的标准这一点上是明显的。另一点,与前一种相反,便是中国中心主义,把中国置于特权地位,这是民族主义的产物,国内中国史学者与之相关,但它同样也是一些非中国的历史学家的职业困境。最近几年里,由于诸如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这些受市场驱动的历史学家提出的肤浅而偏见的观点在当代中国的宣传,后者已经变得很流行。中国中心主义常常使得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历史学家都根据中国-西方两极来再现全球关系,而擦除了非洲-欧亚和太平洋语境。例如,所有上述提到的著作,只有弗兰克避免了这种对全球的两极再现,如果在一种高度特征化的意义上(22)。
尽管做出了相反的主张,这些著作中的多数都不知不觉地通过把源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现象和范畴普遍化而把长期的欧洲中心主义假设永恒化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框架也清除了那些隐含在表面之下的现象,这些现象对于解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是至关重要。对经济数据的形式主义解读在多数情况下都忽视了在资本主义制度、政治和文化条件的创造过程中欧洲三个世纪的探险和扩张的重要性,18世纪晚期,资本主义便成熟了(23)。除了忽视阶级力量和国家干预在资本制度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包括资本自身在公司的组织,它们注要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或许是,在这些世纪中,随着世界知识集中到欧洲的手中,欧洲人获得了较之其他人的优势,以至于18世纪晚期只有欧洲人掌握了全球视野(24)。其他人必定在根据欧洲想象和权力的命令而设计出来的世界地图中重新发现他们自己。正是这种知识,在今天受到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力量的支持,展示了以欧洲(以及美国)霸权为标志的新的现代性阶段,那一霸权仍然塑造着世界,而不管全球现代性的挑战。
在中国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这一点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观念,而欧洲和北美历史学家在很长时间里都因为其普遍主义假设拒绝认真地考虑它,这一是令人感兴趣的现象。今天,在所谓欧洲中心主义批判中,它受到了新的尊敬(连同儒家资本主义)。无须强调,当它的所为最终是根据源自欧洲现代性的标准来测量中国的变迁,这是相当令人困惑的。我所引用的弗兰克、王国斌、彭慕兰等人的那些书,全都以不同的方式遇到了这个问题。直到18世纪中期,中国都是欧洲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欧洲人在东亚必须紧跟当地实践,尽管这些主张看起来是新颖的,但实际都不是新的,甚至当代欧洲人自己也常常这么说。因此,欧洲人跑到前面有许多理由,但是,今天的中国,通过吸取教训,正急速向前,似乎再一次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中心。正是这种对当前的乐观评价(无论如何,是对中国的),及其假想自己在“后现代”时期具有基础,把那些著作与尹懋可、黄宗智等人的早期研究区别开来(25)。
关于中国发展的讨论过去被引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范式,今天仍然如此,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失败的历史、缺席和缺乏的历史、而不是充满不同可能性的差异历史的结果。此外,这种方法,只限于海外中国史学家们。这对于半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真实,而在当前,则由于新的现代化而永恒化了,那种范式在中国学者中挑战且很可能替代马克思主义。迷失在过程中的是那些替代范式,它们不仅注意经济而且注意政治、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实践。对这些替代可能的探讨在最新文本的经济主义中消失了,与其先驱相比,它忽视了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和政治组织。
通过后门引入欧洲中心主义,这对于所有别样现代性主张来说都是个难题。别样现代性主张似乎总是把欧洲/美国现代性作为它们的参照,并且正是以其“现代”这个词的用法中,甚至所有批评家都将之与欧洲和北美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将要否定的欧洲中心主义永恒化了。缺乏对一般现代性的再概念化——我在此指现代性的不同阶段——便主张别样的和多样的现代性,甚至在其关于差异的要求中,也注定会把“单一的”现代性主张普遍化。最重要的是,充满这些著作的文化主义掩盖了它们资本主义普遍性假设,没有这个假设,欧洲人或许仍然只是现代性之中大量种族中心主义一员。如果不能历史地替代资本主义,所有这些差异要求都是欺骗性的,因为欧洲现代性仍然为所有这些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指导范式是“发展”,对于它来说,模式仍然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26)。
在那些强调差异本身的著作中,存在着某种对这种目的论的抵制。那些著作强调的差异不是对合适道路的偏离,而是对不断扩散的现代性状况的替代反应,它同地方性的社会政治关系构造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我们都想居住在地方。其中一本著作便是大卫·弗里关于珠江三角洲的最新研究——《皇帝与祖先:南中国的国家和谱系》。这本书,在社会商业化的语境中,详细地研究了明中期以后现代国家的出现,及其与社会的整合。无须强调,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将其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的一个时期。另一本书是苏查特·穆素洁的《糖与中国社会:农民、技术以世界市场》。该书聚焦于技术与社会。受到对现代性和发展进行批评的印度批评家——诸如杰出学者拉吉尼·柯达里——的著述影响,这本书也强调别样现代性之可能性优先于它们被资本主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征服。本雅明·埃尔曼关于中华帝国晚期科学的研究(《以他们自己的术语:中国的科学,1550-1900》),以及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关于东亚社会的公共管理和审查体系的研究(《失去的现代性:中国、越南、朝鲜和世界历史之未知数》),也都承认现代性之中差异的可能性。埃尔曼的研究也是欧洲人和中国人在现代性生产中的一个合作范例——尽管是由欧洲知识分子从中做媒的。就其在更一般的文化水平上对现代性之中的差异的敏感性来说,值得关注的另一本书是罗克桑·普拉兹奈克的《跨文明对话:基于中国和欧洲经验的世界史概要》(27)。
使这些著作与众不同的,不仅是它们对差异的强调,而且是它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识别出来的差异使政治和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特点具有优先地位,这些特点与那些关系密切在联系在一起——在此,我们可以将之泛泛地描述为“生产关系”,这也是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文化和意识要素的位置所在。同样,它们也遇到了中/西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有意无意地抹杀了“中国”和“西方”这两个术语的复杂性、它们的历史性,且在知识上遮蔽了更具有创造性的空间化策略,那种策略包容了欧亚的其他部分并更密切地关注跨大陆关系。不过,对关系的强调表明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结构化的、辩证的理解,它不仅把它们理解成经济进步的胜利叙事,而且是对那种破坏过程的说明,从其起点开始,那种破坏过程便通过下述事实清晰可见:它成功地扼杀了对自身不断扩大的霸权的替代要求。对于以更复杂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回顾这些被扼杀的或清除的替代要求将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①John Masson Smith,Jr.,"The Mongols and the Silk Road",The Silk Road Newsletter,1.1(January 2003):1-9.大致同一时期,马可波罗从西方到东方,和烈班扫马从东方到西方,他们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这一旅行也许象征了那种统一。蒙古也创造了大陆范围的国际都市中心,那保证了这种意识的传播。参阅Gregory G.Guzman,"European Captives and Craftsmen Among the Mongols",1231-1255,The Historian,72,1(March 2010):122-150.在欧洲,新大陆意识通过探险和知识积累而得到持续扩大。它在16世纪早期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是一种事态问题。从那以后,它便失去了,直到耶稣会会员们从欧洲的到来才再一次恢复,接下来到19世纪,又一次失去了。关于“欧亚”的概念化,参阅Stephen Kotkin,"Mongol Commonwealth? Exchange and Governance Across the Post-Mongol Space",Kritika: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8.3(Summer 2007):487-531.
②萨米尔·阿明:《欧洲中心论批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③Johannes Fabian,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这同进化视角形成对比,在后者看来,差异似乎不仅是空间的而且是时间的,例如,进步对落后。
④近年来,产生了一些来自人类学家的经验,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各种“边界”(borders)或“界线”(boundaries)转移到“边界之地”,从“大地上的分界线”转移到人群间互动的空间。例如,参阅Willem van Schendel,The Bengal Borderland:Beyond State and Nation in South Asia(London:Anthem Press,2005)and,Stevan Harrell(ed),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Seattle,W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历史学的例子来自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s Southeast Asia(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对于了解无政府视角在历史学中产生的丰富成果,这本书也很重要。
⑤有关欧洲、西亚、印度和中国历史学家的讨论,参阅最近关于“前现代”问题的圆桌讨论。IIA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Leiden)Newsletter,No.43(Spring 2007):5-12.关于坚持“早期现代性”非欧洲中心主义用法可能性的替代性视角,参阅John F.Richards,"Early Modern India and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8,No.2(1997):197-209.理查德并没有表达目的论问题,而只是把“早期现代”视为全球现象。关于把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华帝国的讨论,参阅On-cho Ng,"The Epochal Concept of 'Early Modernity' a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1(March 2003):37-61.
⑥关于在拉丁美洲运用“跨现代性”概念,有一个与这里讨论类似的讨论,参阅,Enrique Dussel,"World-System and 'Trans'-Modernity",Nepantla:Views from the South 3.2(2002):221-244.受Naito Torajiro著述影响的日本“京都学派”在20世纪30-40年代对欧洲亚现代性进行成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Miyazaki Ichisada,他提出了一个类似于下文讨论的历史分期。在他看来,可以把工业化之后的欧洲描述为“后现代的”,它保留了14-16世纪的现代性。关于这些讨论的综述,参阅Hisayuki Miyakawa,"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Far Eastern Quarterly,14.4(August 1955):533-552.pp.545-546 or Miyazaki.
⑦例如,陶希圣主张,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追溯到帝国时期的早期阶段。关于他提出的不同的历史分期,参阅德里克的《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更有影响的或许是日本历史学家Naito Konan,参阅注释6。
⑧尚钺:《中国历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6-332页。
⑨⑩《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2卷本,第1卷,第52-68页,第565-608页。
(11)同上,第1卷,第91-125以及338-400页。侯外庐是中国启蒙的最重要提倡者。参阅他的《中国思想史纲》第2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68-116页。
(12)《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上海]新知书店1935年版,第207页。
(13)例如,参阅Ho Ping-ti,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and,Wm.Theodore deBary,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3).无须强调,后一著作揭示了不同的目的论。
(14)Evelyn Rawski in D.Johnson,A.J.Nathan,and E.S.Rawski(ed),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3.
(1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See,Dong Zhenghua,"The Modernization Paradigm Based on Monistic Multi-linear Theory:A Response to Some Comments",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1.2(2006):159-198.
(17)参阅,"China Modernization Report 2009:The Study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China Development Gateway,http://en.chinagate.cn/dateorder/2009-02/24/content_17327414.htm.
(18)参阅汪晖关于现代性的访谈,The End of the Revolution:China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London:Verso,2010).
(19)Timothy Brook,Vermeer's Hat: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Toronto:Viking Canada,2008).同时参阅Hans J.van de Ven in A.G.Hopkins,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London:Pimlico,2002).
(20)实际上,在欧洲之外发现资本主义,这一做法最近成为一种时尚。参阅Banaji Jairus,"Islam,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15.1(2007):47-74,and,Philip Beaujard,"The Indian Ocean in Eurasian and African World Systems before the Six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6.4(2005):411-465.
(21)公正地说,无论是彭慕兰还是王国斌,特别是后者,强调了阶级关系的重要性。彭慕兰也强调了殖民主义十分重要地为剩余劳动力和商品的销路提供了源泉。不过,这些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仍然是边缘的,作者的注意力主要在于“经济的”要素。特别是彭慕兰的引用隐藏在看起来并不恰当的对肥料和煤的着迷上。关于对王国斌的批评,参阅Ricardo Duchesne,"Between Sinocentrism and Eurocentrism:Debating Andre Gunder Frank's 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Science and Society,Vol .65,No.4(Winter 2001-2002):428-463.Hamza Alavi批评了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殖民主义的忽视,这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参阅Alavi,"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6pp,n.d.,资料来源于网站http://ourworld.compuserve.com/homepages/sangat/Colonial.htm.对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欧洲内部)的讨论,参阅Peter H.H.Vries,"Governing Growth: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Rise of the West",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1(Spring 2002):67-136.
(22)弗兰克也审查了这些发展的欧亚语境,他主张,这是一个“中国中心的”世界,他一直努力表述“5000年旧的世界体系”,参阅《白银资本》。
(23)关于批评,参阅Joseph M.Bryant,"The West and the Rest Revisited:Debating Capitalist Origins,European Colonialism,and the Advent of Modernit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1.4(2006):403-444.
(24)关于对商、商人政治权力和商业政策形成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参阅Robert Brenner,Merchants and Revolution:Commercial Change,Political Conflict,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1550-1653(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关于世界知识的系统积累,参阅Daniel J.Boorstin,The Discoverers:A History of Man's Search to Know His World and Himself(New York:Vintage Books,1985).
(25)在此,我提及一些最重要的研究成果,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hilip C.C.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日本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这种史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参阅Wigen,"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Time/Space of Modernity",paper presented at the XIX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Oslo,7 August 2000).For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see,Arif 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See,also,Arif Dirlik,"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and the Concept of Capitalism:A Critical Examination",Modern China 8,1(January 1982):359-375.
(26)Gilbert Rist,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From Western Origins to Global Faith,tr.by Patrick Camiller(London:Zed Books,1997).而且在其更实证的展开中,发展变成了某种可以计量的东西,它也使“科学的”社会比较成为可能。
(27)关于当代日本人对现代性形态的思考的有趣说明,参阅Karen Wigen,"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Time/Space of Early Modernity",paper presented at the XIX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Oslo,Norway,7 August 2000).Wigen在这些作品中提出的与“世界体系分析”相对“世界网络分析”是过度决定的,它忽视了两种方法组合的可能性,那种组合不仅为把握作为具有流动性和可变性的网络运行产物的形态提供了更好的可能性,而且使其轮廓屈从于世界体系结构化中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性。无须强调,这些关系也塑造着政治或“文明”单位的空间,它们在这个阶段组成了现代性的世界。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现代性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目的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