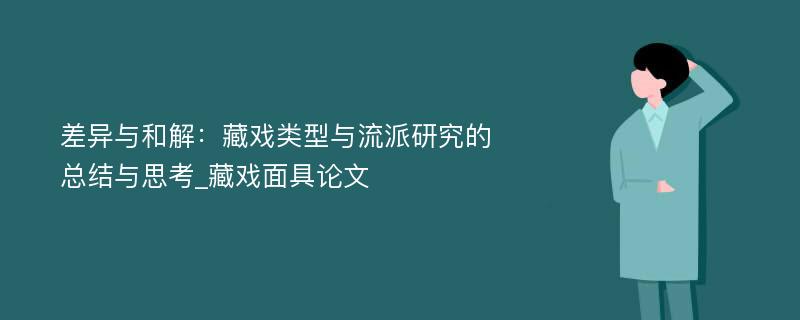
分歧与弥合:藏戏剧种、流派研究的综述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戏论文,剧种论文,流派论文,分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24(2012)01-0001-05
一、绪论
对于西藏农村阿吉拉姆藏戏的学术性研究虽然历史不长,然而与西藏的其他传统艺术的研究状况相比较,藏戏研究的成果显然是比较多的。藏戏研究经过其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十分薄弱”的理论研究基础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长足发展”时期,已取得了相对比较丰硕的成果。到目前为止藏戏研究关注的主要内容涉及历史起源、剧种划分、剧目分析、唱腔音乐、服饰面具、比较研究、形式美学以及对人物、机构的介绍等。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藏戏剧种、流派方面的研究成果,以综述的形式来提出笔者对于相关讨论的一点浅见。
二、我国藏戏理论研究的基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外只有极少一些藏戏艺术浅表面的介绍,其理论研究更是十分薄弱,许多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1]。20世纪40年代,在国内如《边政公论》、《康导月刊》、《艺文杂志》3个刊物上发表过一些介绍性文章,且内容仅限于康藏地区的藏戏。50年代,在《戏剧论丛》、《戏曲音乐》、《大公报》、《文汇报》、《云南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发表过数篇介绍藏戏的文章。如:1959年5月10日《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高原上的艺术之花——藏剧”,对藏戏的“传说”、“由来”、“别具风格的艺术”等有了初步的论述。另外,发表于《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的“评藏戏文成公主”一文,对传统八大藏戏举目之一的《文成公主》(实际为《甲萨白萨》)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论,已经具有了研究的性质,这些为日后的藏戏研究开始打下基础。60年代,在《光明日报》(1960年6月17日“今天的觉木隆剧团”)、《人民日报》(1960年8月13日“风和日暖花重开”)、《北京日报》(1961年3月3日“藏戏”)、《少数民族戏剧研究》(锦华,《略谈藏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出版)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60年代,还出版了蔡冬华《朗萨姑娘》(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出版),王尧《藏剧和藏剧故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出版)等编著。加大了藏戏研究的步伐。70年代“没有一篇关于藏戏的文章”。[1]
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藏戏研究成果比国内更少。20年代,在法国《亚细亚学会手册》(巴黎:1921年出版)上发表了《苏吉尼玛》(藏文与译文);同年,出版了法国人巴的《西藏的三种奥义书(包括有藏戏故事)》(巴黎:1921年版);1931年,法国高等艺术研究院史学文献部女导师麦克唐纳在《民俗学》第42卷上发表《西藏的传奇故事》(藏戏故事为典型代表);50年代,仅在香港地区的某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西藏的庆丰收戏剧》;60年代,仅在美国、英国、法国的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如:《西藏艺术》(帕尔,美国,1969年)、《再论西藏的庆丰收戏剧》(伦敦,1967年)、《西藏戏剧》(法国,1961年);另外出版了如《西藏:它的历史、宗教仪式和艺能》(岸边成雄,日本,1966年)、《顿月弟弟(藏文、图画、英译文)》(图本诺布(藏族)、埃克瓦尔,美国印第安纳大学,1969年);70年代,在法国、英国、荷兰等的刊物上也发表过少量的相关文章,除此之外,在如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等一些著作中也涉及到了相关的内容。
三、我国藏戏理论研究的长足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藏戏研究的系统性工作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民族宗教政策全面恢复贯彻,藏戏的抢救、发掘和研究工作也随之开展。尤其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开始编撰,其中《中国戏曲志·西藏卷》以及其他省区藏区相关工作的启动,“于是西藏和内地藏区的藏戏工作者对藏戏的理论研究,也就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展开”。[1]
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1、关于藏戏起源的研究;2、关于藏戏剧种、流派的研究;3、关于藏戏剧目或剧本故事的研究;4、藏戏民俗节日研究;5、藏戏唱腔、音乐、舞蹈研究;6、藏戏面具研究;7、藏戏演出机构和人物研究。
关于藏戏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佟锦华的《略谈藏剧》(《少数民族戏剧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王尧的《藏剧和藏剧故事》(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刘志群的《论藏戏的起源和形成》(《上海戏剧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论探我国藏戏艺术的起源萌芽期》(《艺研动态》1987年1月第3期);洛桑多吉的《谈西藏藏戏艺术》(《西藏研究》,1984年第1期);边多的《还藏戏的本来面目——试论藏戏的起源、发展及其艺术特色》(《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和《论藏戏艺术与藏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历史渊源关系》(“亚洲传统戏剧研讨会”1991年);姚宝瑫、谢真元的《藏戏起源及其时空艺术特征新论》(《西藏研究》,1989年1期);觉嘎的《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
关于藏戏剧目或剧本故事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霍康·索南边巴的《八大藏戏渊源明镜》(《西藏艺术研究》,1992年2期);卓仓·希纳多杰的《〈诺桑王子〉与〈召树屯〉》(《西藏艺术研究》,1994年4期);郑恰甄的《论藏戏〈诺桑王传〉的结构》(《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6期);康保成的《藏戏传统剧目的佛教渊源新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3期);刘志群的《我国藏戏与西方戏剧的比较研究》(《戏曲研究》,2006年3期);周炜的《宗教仪式与藏剧艺术》(《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4期);谢真元的《〈长生殿〉与〈诺桑王子〉思想内涵之比较》(《戏剧艺术》,2010年3期);丹正昂本的《佛教与藏族文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8年);曹广涛的《哈顿贝壳·罗伯特对藏族佛教戏剧的研究评述》(《学理论》,2009年6期);刘志群的《西藏祭祀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王俭美的《藏戏无悲剧心里成因论》(《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1期)等等。
藏戏民俗节日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志群的《西藏盛大的传统传统的雪顿节》(《艺研动态》5期,1987年7月);次仁卓嘎的《雪顿节与藏戏》(《西藏民俗》,2003年4期);娜仁卓玛的《藏族雪顿节》(《民族论坛》,2003年6期);强巴平措、饶元厚的《历史沧桑话雪顿》(《中国西藏》(中文版),2004年5期)等。
藏戏唱腔、音乐、舞蹈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更堆培杰的《略谈藏戏阿吉拉姆音乐》(《西藏艺术研究》,2004年2期);边多的《西藏音乐史话》(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2月);觉嘎的《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9月);刘志群主编的《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西藏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3年6月);胡金安的《对藏戏声乐的一点浅见》(《西藏艺术研究》,1986年2期);卢光的《论卫藏地区藏戏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4期)。藏戏舞蹈方面主要有,丹增次仁主编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0年9月)、《藏戏舞蹈》(《西藏艺术研究》,2003年4期);强巴曲杰的《略探藏戏舞蹈的审美特征》(《西藏艺术研究》,2003年4期);阿旺松热的《初论藏戏舞蹈艺术的起源于审美特征》(《西藏艺术研究》,2003年4期)等。
藏戏面具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文章有,宫蒲光、洛松次仁主编的《藏戏与歌舞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1月);洛桑多吉的《试论藏戏脸谱——“巴”》(《西藏研究》,1988年1期);刘志群的《我国藏剧面具艺术探讨》(《西藏艺术研究》,1986年2期)、《西藏傩面具和藏戏面具纵横观》(《西藏艺术研究》,1991年1期);张鹰的《西藏面具艺术浅释》(《西藏艺术研究》,1990年2期);叶星生的《西藏面具艺术》(《美术研究》,1990年2期);王娟的《藏戏和羌姆中的面具》(《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期);杨嘉铭、杨环的《藏戏及其面具新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4期);张虎生的《西藏文化中面具艺术的色彩象征》(《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4期)等。
藏戏演出机构和艺人研究方面的成果有,刘志群主编的《中国戏曲志·西藏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12月);雪康·索朗达杰的《雪康·索朗达杰论文集》(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刘志扬的《民族旅游与文化传统的选择性重构——西藏拉萨市娘热乡民间艺术团个案分析》(《开放时代》,2005年2期);扎西多吉的《从觉木隆戏班到全国著名戏剧表演团体——回顾近五十年藏戏艺术的发展》(《西藏艺术研究》,2001年3期);罗桑朗杰的《浅谈西藏几大主要藏戏班子的艺术特色》(《西藏艺术研究》,2006年1期);陆军的《论藏戏的现代转型——以西藏自治区藏剧团为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期);程杰的《觉木隆藏戏:带领我们奔小康的古老艺术》(《中国农村科技》,2007年7期);余茂智的《探访藏戏“拉姆部落”》(《中国西藏》中文版,2005年第4期);徐琳玲的《藏戏班主格龙》(《中国西部》,2007年第2期)等。
四、我国藏戏剧种、流派的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末,藏戏的研究重点从“起源论”逐渐转移到了“剧种流派”的探讨上来。之前,在80年初期,青海的刘凯先生注意到,包括在《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等权威书籍中,对“藏戏”一词的解释都是“按照西藏藏戏去分析概括的”,虽然在后一本中,刘志群先生提到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其他省区藏区的藏戏,却也只是提到而已。
同时期,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在其他省区藏区的巡回演出,让身处青海的刘凯先生很直观地感受了西藏和青海藏区藏戏的不同之处,甚至西藏的一些藏戏工作者否认青海藏区的藏戏(南木特尔)属于藏戏。“可是安多地区的青海藏戏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是藏族群众用当地的安多藏语方言以戏剧形式演出的,有唱、有白、有表演、有故事,当地群众都把它叫做藏戏,它又为什么不能是藏戏呢?这就更坚定了我(刘凯)要把用不同的藏语方言演出的两种艺术风格的藏戏,加以比较、区分、以使安多的青海藏戏也能取得其应有的艺术地位”。[2]为此刘凯在《青海日报》(1983年7月29日)发表《闪光的艺术、崇高的使命》一文,“提出西藏藏戏与属于安多藏语方言区的青海藏戏是两种不同的戏”。接着在《青海文艺界》(1983年第2期)发表藏戏交流报道文章,明确提出“西藏藏戏与流行于青海、甘肃、川西北使用藏语安多方言的安多藏戏,属于藏戏这两个不同流派(或体系)”。作为这种观点的后续,刘凯先生发表《浅谈西藏藏戏与安多藏戏——兼议新版〈辞海〉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藏戏”、“藏剧”条目》一文,“比较系统地对比了两种藏戏之异同”。这些论述成为藏戏系统、剧种、流派研究的铺垫和先河。
另外,由于“中国戏曲志”项目工作的展开,对于戏曲的剧种和流派的分门别类工作势在必行,这也就使得藏戏研究工作者“在我国广大藏区究竟有多少民族地方戏曲剧种?又如何定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为此,刘志群先生的《藏戏系统剧种论》[3]一文开启了藏戏剧种流派研究的大门。文章中认为“根据今年来的考察资料和各方研究成果,我(刘志群)认为我国藏区戏曲系统至少可以划分出如下八个剧种”,即1、“藏戏系统母体剧种:西藏阿吉拉姆白面具藏剧,简称‘白面具藏剧’”;2、“最繁荣的藏族大剧种:阿吉拉姆蓝面具,简称‘藏剧’”;3、“西藏昌都地方剧种:昌都强巴林寺朗达羌戏,简称‘昌都戏’”;4、“西藏门巴族戏曲剧种:门巴拉姆藏戏,简称‘门巴戏’”;5、“影响仅次于藏剧的安多藏区剧种:安多语南木特尔藏戏,简称‘安多戏’”;6、“川藏德格地方剧种:德格朗达羌姆藏戏,简称‘德格戏’”;7、“四川康定地方剧种:‘木雅戏’”;8、“四川马尔康地方剧种:‘嘉戎戏’”。文章中还对“藏戏”二字作了语用学意义上的“正名”。认为“‘藏戏’二字,本来在汉语文上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藏族的戏,藏区的戏,可是在过去一般是指西藏的戏,有时候专指西藏阿吉拉姆藏剧。现在我(刘志群)觉得可以给‘藏戏’正名,就是用它本身的含义,成为我国藏区戏曲系统的一个名称,把我国广大藏区各地方戏曲剧种,包括藏区内另一民族剧种门巴戏,概括称为我国藏戏系统剧种。而在藏戏系统中可以分出已经论述的确立的八个剧种,在有些剧种中又可以分出诸多不同的艺术流派”[3]。
刘凯先生撰文《对“藏戏”的重新认识与思考——“藏戏”名称规范化刍议》[4],他与刘志群先生一样,认为“藏戏”二字应该作为总称继续使用。另外在文中提出“在藏戏这一总称下面的第一个层次,是否可分为西藏藏戏(或称卫藏藏戏)、安多藏戏、康巴藏戏三个系统”,“由于形成或区别这三种藏戏系统最重要的因素,是它们使用着三种不同的藏语方言,我(刘凯)感到还是以方言区的名称来概括或代表这三种藏语系统为好”;“三种藏戏系统原来的藏语习惯称谓,仍可作为它们的藏语名称去对待”。[4]由此刘凯先生以“方言区”作为标准,提出了在“藏戏”名称总括之下的“西藏藏戏体统”、“康巴藏戏系统”、“安多藏戏系统”三个藏戏系统以及其属下的12个剧种和15个不同流派,形成“藏戏系统、剧种、流派”的分类模式。同时期,以刘志群、刘凯、马成富等为先后发表了《从藏戏名称的规范到藏戏剧种的划分——兼答刘志群同志的商榷》[6]、《藏戏剧种划分的误解——致刘志群、刘凯二同志》[6]、《论藏民族的戏曲剧种》[7]、《一个藏戏系统和诸多剧种、流派——藏戏概观之一》[8]、《浅论藏戏剧种系统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9]、《藏戏剧种研究的突破与深入——兼答刘凯、马成富同志商榷》[10]、《藏戏剧种的提出、分歧与弥合》[2]等一系列文章作为探讨,进行了激烈的学术商榷。
综上所述,这次“论争中分歧与弥合”的结论是“要不要将各地藏戏使用着的三种不同藏语方言作为划分藏戏系统和剧种的重要因素”的问题。刘志群认为在“藏戏”系统下面直接分八个剧种,而刘凯在“藏戏”分以三大藏语方言区分为三个系统,下面再具体分六个(蓝面具藏戏、白面具藏戏、昌都藏戏、康巴藏戏、德格藏戏、安多藏戏)剧种。另外分歧所在为:能不能把“门巴戏”归为藏戏范畴?嘉戎能不能成为独立的剧种?能不能将“白面具藏戏”看作藏戏的“母体”剧种的问题。弥合的部分为:刘先生“基本同意按藏语方言来划分藏戏剧种系统及其三个层次”,但认为只能作为“藏戏”系统下的子系统来对待;关于“康巴藏戏”(将康区的道孚、甘孜、理塘、巴塘等地方的藏戏,作为西藏蓝面具藏戏在康区的流派的观点,认为这些地方的藏戏,均属于康巴藏戏)这一提法也趋于一致。刘志群先生同意将原“藏剧”改称“蓝面具藏戏”;关于地方名称与戏之间加不加“藏”字的问题上觉得加也无妨,所以“分歧也不复存在了”。[2]然而,作为这些工作的总结成果之一,在由刘志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戏曲志·西藏卷中》中,把西藏的藏戏分成了“白面具戏”、“蓝面具戏”、“昌都戏”、“德格戏”、“门巴戏”五种。至此,随着“集成志书”工作的结项,关于藏戏“系统剧种论”也告一段落。
五、小结
关于藏戏各剧种、流派的划分和命名的问题上,前辈学者、专家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和探讨,消除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促进了藏戏研究的规范和统一。然而,笔者认为在对各地剧种流派的命名上,留下了不少的遗憾。很多前辈专家、学者在对各地藏戏剧种、流派具体命名的时候,没有很好地考虑保留各地原有的称谓,而是以地名来命名剧种,忽视了藏语自称当中本身蕴含的分类和地域特色的意义。例如:“昌都藏戏”和“德格藏戏”当地称为“朗达羌”(rnam thar' cham)即跳神性质的戏剧,点出了昌都、德格藏戏源自寺院的特色;“安多藏戏”当地称为“南木特”(rnam thar)即传记或唱腔,指出了其源于卫藏阿吉拉姆,因为卫藏阿吉拉姆藏戏的唱腔就叫“囊达”(rnam thar),藏语是一个词,只是由于方言的区别,汉语的音译转写变成了不同的字罢了;“嘉戎藏戏”当地称为“嘉戎鲁嘎尔”(rgya rong glu gar)即嘉戎歌舞,体现了嘉戎藏戏的歌舞性。因此,直接以地名来命名分类上比较简约,但已经失去了当地自称的文化内涵,因此笔者认为类似这样的问题上应该适当关注学术话语的民族主体性,尊重“地方性知识”本身的分类体系和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