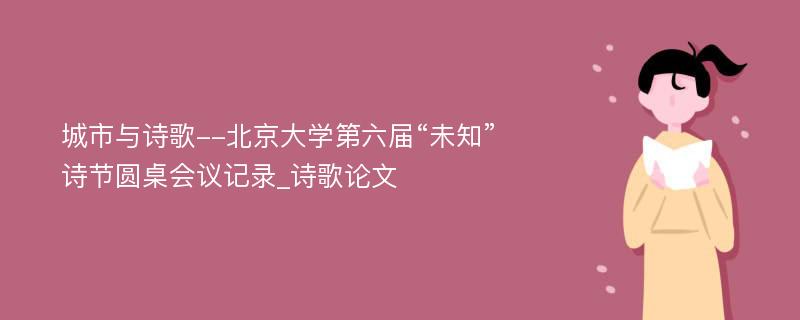
城市与诗——北京大学第六届“未名”诗歌节圆桌论坛实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节圆论文,北京大学论文,第六届论文,实录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洪子诚
参加者:王光明、蓝棣之、宋琳、王家新、孙文波、郭小聪、陈旭光、树才、周瓒、骆英等
纪录整理:邓庆周
会议地点: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会议时间:2005年5月4日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6)01—0005—06
洪子诚(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天这个讨论会,是北大“未名”诗歌节的活动之一。主要请大家就城市与诗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引发这个话题的契机是最近出版的一部诗集《都市流浪集》。当然大家的发言不必拘泥于这部诗集,可以围绕城市与诗这个话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与诗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都市记忆与乡村情结的相互纠缠本来是中国现代诗歌的一道风景。城市模式是现代化的温床,它是通往现代的唯一通道。当然,城市的面孔非常复杂,它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城市进入诗歌以后,首先诗歌想象城市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由自然意象转变为城市意象,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由对应转向对抗纠缠,同时诗的节奏也出现了调整。置身于城市里的诗人对城市的态度是复杂的、暧昧的,对于中国的现代诗人来说,他们与西方现代主义诗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是营造一个独立的文本世界与物化的世界抗衡,而是以移动的视点、变化的心情对答城市的变化,反思生存的真实。也就是说,他们不像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那样与城市决绝,那样沉迷于文本的抗衡性了,而是表现出与城市无法分割的关系,对城市的态度有着一种既反抗,又理解与包容的态度;这不是与现代工业文明妥协,而是从人性和精神出发,在主动理解、介入中,对城市文明加以调整和塑造。
树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18岁从浙江的农村考上北外,在北京一直生活到现在,中间又去了欧洲和非洲,这样国外的乡村和城市我经历了,汉语的乡村和城市也经历了。通常,人离开乡村到城市去的时候,不是人在城市里时体验到的那种情况,这是后来的东西把它覆盖过去了。人可能是这样一种悖论,在乡村里的人永远期待着进入城市;进入城市的人又觉得城市把他碾压得破碎,把他的血液的热度抽干,把人年轻时的理想变得微小,因为只要看看所有的立交桥的水泥和寸草不长的没有土地的气息的时候,在城市生活的人已经改变了——他自己不得不说服自己他是离开了农村。而农村是他渴望离开的,因为城市,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仍然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讲到文化,人们觉得它就是在城市。农村的人即便打工,受到莫名其妙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的歧视,也愿意进入城市。就是农村所能挣来的那份生活它是多么安静,城市里挣来的那份生活多么难多么挤压多么破碎,但是仍然是吸引不在城市里的人的一种力量。所以在城市里呢,我觉得人所体验到的远比他在诗里写到的要复杂、细腻。城市的经验需要有更多的肌质和肉感的细节来真正把一个诗人在城市的体验表达出来,一些城市生活的细节还需要像细节的发生那样被揭示出来。
洪子诚:刚才光明和树才都讲得很好。其中的一些观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在诗歌生成的过程中遗漏了什么?另外,就是对城市复杂性的把握问题,就是关注细节生长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在一首诗里面,我们能否辨别这是北京,那是上海,或是另外一些城市,这些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为以前我在一个讨论会上听过王德威和张旭东他们讲到北京的特点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描述(他们走过世界上不同的城市,会有一些比较):他们认为比较起北京和上海来说,北京更颓废些。当时我对这个观点印象很深刻。我长期生活在北京,别的城市没有去过或很少去过,但我感觉它们可能会有很多方面可作比较,比如北京的包容性、颓废性或者在文化方面、艺术方面所发展的那些空间,所以骆英的诗集——就像树才刚才提出的——对城市的经验能不能更复杂化一些?我想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好,下面哪一位来讲?
周瓒(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我想接着树才关于细节的问题谈一谈。我在想,既然要描写都市,为什么是一个文化的或者说是概念化的城市,看起来是一个抽象的城市?我原想象在这本诗集里读到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洛尔卡笔下的纽约——虽然是一个短章,却能清晰看到一个城市的独特性,我在这本诗集里更多地看到的好像是一个孤独的身影,让我联想起波德莱尔所谓的“城市的拾荒者”、“流浪汉”,但就是不知道这个城市在哪里,只是文化的概念化的一个城市。虽然我没到过许多都市,可能对都市的印象,就像我曾在自己的一首诗里描述过的:世界上的大都市都是一样的。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感觉是一种很初级的感受。也许就是一种光怪陆离、眼花缭乱,到了晚上,如果从飞机上俯瞰的话,就是非常明亮,像白天一样。有一次我和唐晓渡一起乘飞机的时候,他说,其实晚上飞机从都市上空飞过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哪个都市最亮就能显示出哪个都市是最繁华的,也许纽约的晚上是最亮的。北京是不亮的,尤其没有上海或其他都市亮。哪怕就是从光怪陆离感观这一方面比较,都市之间也是有差异的。根据我对生活在北京或上海的年轻诗人的文本的阅读印象,他们的作品无论是描写北京还是成都,它们都非常及物,有一种及物性就是说很具体。说到这里,我想起曾经读到过一本1980年代出版的叫《城市人》的诗集。那是上海以宋琳等诗人为代表的一个城市诗派,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意识地或很关注城市诗了。也许这个话题宋琳先生会讲得更有意义。我就讲这么多。
洪子诚:刚才周瓒已经点了宋琳的名,那么我们下面就请宋琳讲。宋琳在1980年代是城市诗派的发起人,和张小波、李彬勇、孙晓刚等人一起出了《城市人》这本诗集,所以在这方面更有发言权。我先介绍一下,宋琳现在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特聘教授。为什么是特聘教授?
宋琳(诗人,现居巴黎):那是因为我1995年定居法国,现在在北京找到这份工作,是以外国教师的身份。既然洪老师让我接这个话题,我就谈一点感性的认识。刚才洪老师提到我们四个人的诗合集《城市人》,当时我们初出茅庐,在诗歌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观念。但因为我从福建乡村考入上海的大学,我进入都市生活的感受就像波德莱尔的那种经验:他认为都市生活环境对于一个现代诗人的意味就是“震惊”。本雅明也特别总结了一种“震惊”的经验。我因为偶然的机会进入大上海,年轻时代的我体验了“震惊”的经验。我认为,诗人,毫无疑问是自然之子,对大自然的感受可能给我们一种天赋,这天赋来自于自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乡村生活对我的影响,那里有源头的东西:我们生命开始时候的经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城市成长的诗人就没有这种对自然的感受。我认为诗人天性中就有一种对自然万物的敏感。所谓“感物吟志”,古人已经说得很好。
城市诗,是现代诗歌的一种样式,最著名的代表是波德莱尔。实际上在波德莱尔之前,美国诗人爱伦·坡在小说里已经处理城市生活题材,处理一个作家和城市的关系,比如“人群中的人”就非常典型。我觉得“人群中的人”就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诗人,他们是一位旁观者——在咖啡馆,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的行人。他们有一种身份,就像一个侦探,他们观察生活,让自己处在一个相对隐冥的状态。据说天使进入城市也有一种隐身术,他们进入人群隐蔽在人群中,以便于观察,并传递上天的信息——诗人不是天使,我们是生活在人群中的人,那么在我们写作意识里面,可能就有一种跟侦探这种职业相类似的敏感。对生活中偶然发生的散乱无序的生活细节充满了一种好奇。我这里提出一个“难度”的概念,也就是诗歌从自然或田园发展到进入城市这样一个区间,它在美学上和诗歌感性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去年我受臧棣邀请到北大开了一个讲座,探讨了一个问题,也就是现代性和古代诗学的关系。这里面我面临一种困惑,可能诸位在写作当中也会碰到相似的困惑:现代性的获得是否要以与自然的隔绝作为代价?我们都市化的进程还没有完全实现,举北京为例,1950年代以梁思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城市的一种规划,到这种规划的破产(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原因)——导致了我们现在生活在梁思成规划版图之外的一个城市,也不再是王震时代以故宫紫禁城为中心南北完全对称的南北布局的城市。虽然这个“中心”作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现在还存在,但在我们的心里恐怕已没有这种“中心”的地位了。我们生活在北京,但要在总体上把握、描述出北京这座城市恐怕要比上海困难,就因为我们在文化上没法跟它面对。我每次从国外回到北京,开头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视觉上无法得到满足。我可能更多地带有一种挑剔,跟朋友聊天时经常会说起:你看,北京建筑的线条这么锋利,不柔和,在视觉上不能得到美感。相对巴黎这么一个特别“女性化”,还保留着田园风光的城市,北京的建筑就显得比较僵硬,在视觉感受上就很难唤起某种诗情画意的联想。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深入到北京内部了,我不再看,而我感觉北京的魅力恰恰就在于某种隐形的、微观的那些区间。
刚才树才的例子也谈到,骆英的诗触角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恐怕缺少一种皮肤的感受。我们对于城市的感受除了用目光、视觉也需要用触觉,也就是我们跟城市能不能建立一种亲密接触的关系。这是双方面的:城市本身是一种形态,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写作者,作为一个观察者能不能建立古代美学中的那种高度对应呢?比如李白面对一座山,同时山也在观察他。高楼大厦在我们面前,仿佛是钢铁和玻璃的森林,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视觉反应的确是疏离的、隔绝的。这是一种从城市的物质性的角度来考察的。另一方面,城市给我们的这种压抑,也可以转化为一种诗。现代诗歌不再像古代诗歌那样是一种原始的亲近的,可能这种压抑本身也在吁求在呼唤我们处理它,也就是现代诗歌或许在阅读经验中不再像古典诗歌那样让人舒服,这是不得已的事实。我想探讨的是,诗意应该如何在现代诗歌中重建它?我认为这是没什么答案的。如果追溯到波德莱尔、艾略特这些西方现代诗人,我就想波德莱尔正好是处在变化的时代,豪斯曼正在给巴黎一个规划、整治。波德莱尔正好生活在这个时期,所以他写给雨果的那首诗《天鹅》,第一句就是“巴黎在变”。而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处境:北京在变,上海在变,中国的城市在变化。诗人如果意识到这种变化本身是以建设的名义造成的一种相当大的破坏,然后以某种挽歌的方式歌咏或讽喻这种变化,或许我们还可以发现新的表达空间吧。当然这只是一个向度。
举个具体的例子,我去西便门爬城墙遗址,当时正好是落日,一眼看到夕阳,我的心情非常之难过。我就想象假若城墙还在,北京城又是另外一种风貌。我在想,这里面也在要求一种诗,正如古代“扬州慢”诸如此类的诗词,也就是挽歌式的处理。也许这是我个人的体验,因为我有一些国外生活的比照,对现代城市生活跟美感的关系有一些考虑吧。这是比较主观的。另一方面,诗人在一个城市中的位置,我觉得可以具体到诗歌中来,有时我们静观地描述一种城市,但另一种情况,我们在城市中移动的时候发生的种种事情,就像波德莱尔处理的那种“街头邂逅”的经验。我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就像洛尔加说的,诗歌是漫步街头的一种东西。我想他是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体验到的。移动的目光是在街头漫步的,我们只有在街头漫步才会跟生活事件遭遇。那么在街头漫步或者在城市中移动,这或许是比较好的一个视角,否则我们会停留在静观的层面上,角度可能会比较大。当然这属于技巧上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城市诗——如果存在这样一种诗歌的话(我们不妨这样命名)——还是刚刚起步的一种诗歌样式。诗人能否通过写作建立一种理想的城市的远景式的东西,这我不知道。不过惠特曼对曼哈顿等城市的处理的诗歌,正如谢冕先生曾在大连召开的一次会上提到的,是一种“举轻若重”的诗歌。惠特曼的诗歌与纽约是建立在文本上的一种关系,创造了一种美国精神。我们现在的诗歌可能更多地是在个人的或者“小我”的范围内来处理城市题材的。我想转型期呀,诗人可能有一种使命,就是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一些,可以稍稍越出某种题材的限制,比如说城市诗这种题材和自然山水诗这种题材的限制。把我们的触角回溯,回溯到古代去,有一天无愧于跟古人的精神相媲美。这是一种期待吧。
郭小聪(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在审美意识日益淡化、审美能力日益消失的情况下,骆英还能坚持一种诗性思维,无论如何是应该肯定的。兴趣本身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它所带来的心灵的愉悦就好像我们干活灰头土脸的时候谁能拒绝用清水来一次洗浴呢?心灵的洗浴也一样,所以这么长时间能坚持下来。一次次的创作过程中,一次次远离日常生活的繁复、重复和杂乱的纷扰,在情感体验过程中,人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慧,而且越来越在情感的深处,在回望自己过去的历程中,达到一种美感,一种绝对不会被任何人剥夺的享受。就有一点类似日本电影《沙器》中,青年钢琴家在反复创作的乐曲中一次次回到自己的人生。那种体验是剧中“部长”的女儿那些贵族青年根本就不能理解的。她只注重自己的名声,根本不理解自己的他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她永远不能走向世界。所以创作的兴趣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坚持”。
这本诗集中所呈现的酒楼、大堂、咖啡馆、酒吧、街灯以及车流、街头等等,使我想起1930年代新感觉派(当然那是小说)的一些印象:新感觉派被称为“头等列车上的看客”,他们是一个特权的阶层站在很高的一个阶层,从这方面看,骆英诗中的场景与这些有些相像,因为不是简陋的房屋、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肮脏的垃圾箱等等。毕竟一个企业家生活的环境不是这样的。不过这些意象、场景与新感觉派的相似仅仅到此为止。新感觉派是一种狂欢的性质,骆英的诗一点也没有这种气息,反而是一种孤独和感伤,而他所经历的场面越是豪华、繁复或者张扬,诗人的情感就越是孤独,也就是既身处其中,又置身境外的那种感觉,非常孤独。而且常常地把这种思绪抛向故乡的小河、归乡的小路、童年的乡音、母亲、小草等等感觉的那些东西。
我认为城市并不缺少诗,缺少的是发现诗的眼睛。如果不肯定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像社会学家讨论城市的功能,而不是在讨论关于城市的诗。其实城市是充满诗歌题材的。城市的巨大魅力是无法抗拒的。我不是生长在农村但几年插队的经历告诉我,在农村向往城市,一旦进入城市,就再也不想回到农村。但是农村毕竟是他终生都要回望的,越是成功就越会回望,这不是背叛城市,而是内心的自然皈依,包括路遥也是这样。我想起艾青的一首诗《村庄》,他道出了来自农村的青年对城市的复杂感受。他说,自从看到城市就再也回不到村庄。因为这里每一座房子都比整个村庄值钱。在城里转一圈,比在家乡过一生都有意思。所以艾青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假如他不是一只松鼠就绝不会回到那可怜的村庄!这是非常复杂的感受,绝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里头有千丝万缕的复杂的情愫。越是复杂的诗人,越能发现美,包括城市之美。
蓝棣之(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觉得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诗歌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有了情绪的触动之后,浪漫主义诗人马上拿起笔就写,而现代诗人则要在情绪多次来回冲击后才可以写诗——这已经不是当初简单的情绪,而是非常复杂的综合性的一种情绪了。诗歌是一种综合的情绪。所以我想,这本诗集如果是现代诗而不是简单的浪漫主义诗歌的话,是对于“我”的人生经验的综合的诗歌,它应该是综合了各种经验的而不是单纯的。所以张力是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加以综合,不论是艾略特,波德莱尔还是惠特曼都是这样。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另外一点我想到,很多人写过这样的句子“在现实中我低下了我的头,但在诗歌中我永远不会低下自己的头”。在诗歌中不低下头的人,也就是在诗歌中会批判现实的人,在现实中往往是个失败者,比如卡夫卡(当然他也不见得写诗),他的恋爱就永远不会成功,虽然后来他因为作品成为划时代的人。那么反过来说,现实中很成功的人就不大可能写出很好的诗,我不知道是否这样。因为太顺利了,做什么就成就什么。这样就不是语言在写你,而是你在写语言了。我理解的诗歌是这样的:诗歌的写作意念、想法不能太明确。
孙文波(诗人,现居北京):“城市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把诗歌分为城市诗、乡村诗,这大概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现代当代的诗,或者从波德莱尔以降的诗歌来说是不是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城市诗?如果把城市诗和乡村诗当作一种概念来看,它们是代表不同的文明进程所产生的东西。“城市诗”里灌注了一种不同于过去我们所汲取的诗的东西。因此,一首诗若能被称为“城市诗”则必须符合我们称之为现代文明进程中所包含的很多东西,比如都市化色彩,现代工业发展后人对自己面临的生存处境的种种认识以及产生的种种理念及种种困惑。如果没有包含这些东西,就纳不进“城市诗”这个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城市诗”应该称之为“现代诗”而不是古典诗、浪漫主义诗或现实主义诗歌。它就是一个当代诗或现代主义诗歌的概念。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东西:无论是城市诗还是乡村诗或者是古体诗,这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中是否包含了当代意识,你所处理的经验是不是被称作当代经验的经验。就是说它符不符合我们今天的人对我们置身的处境所理解到那些东西。至于你究竟写没写酒吧,饭桌或者楼群,这些都不重要,而在于你怎么处理、看待这些东西,最终把它描述为究竟跟人构成了什么关系。我觉得,现代诗歌一直试图处理的就是怎么描述我们和整个世界的关系。过去的诗人也在描述:杜甫在描述,李白也在描述,但是为什么我们和他们描述的不一样,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波德莱尔被称作城市诗的鼻祖,艾略特写的《情歌》其实也是城市诗。洛尔迦是西班牙乡土诗人,因为他写了美国,也成了城市诗人。洛尔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本土诗人,但是他处理了现代经验,他不写纽约,只写了马德里,他也写出了一种城市诗,所以城市诗本身不在于你描写了什么,而在于你有什么感触,用什么方式、理念去了解。我们在认识当代诗歌的时候,在贯穿概念化的情况下,都出了哪些毛病?为什么描述总是不准确?在称之为出了问题的方面都出了什么问题?我想通过“圆桌”可以得到很好的讨论。骆英作为一位企业家能够保持对当代生活的关注,并试图处理人和高楼呀汽车等等物的关系。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作为一个诗人最重要的。至于从诗意的角度,使用的语言是否准确,技巧是否娴熟,词汇新不新,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保持关注,这才是最重要的。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我简短地谈谈有关的感想。城市是人类社会向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集市到小镇到大都市,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是现代性的标志。在这里我愿采用迈克鲁翰的观点: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城市是人的皮肤和毛发的延伸,是房屋的向外扩展。所以城市其实并不是一种题材,因为它已经是一种现实,一种当下的生存状态。到了有现代化的大都市的今天,即使你不写都市,你也有一种都市以及都市的对立面,比如说农村这么一个价值判断,所以都市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领域,不仅仅是诗歌,其他艺术领域也非常关注人在都市里的生存状态。比如一月份在广州就有一个“视觉中国”的摄影,还有现代美术里面有大量的关于人和都市的思考。再比如说,第六代导演大量地关注都市中的边缘人的生存状态:那种人跟都市生活的不适应的状态的描写,那种个体主体性的觉醒所带来的个体的焦虑,那种异化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说,第六代导演是通过影像写作的都市诗人。
中国都市诗其实也不新鲜。我也是从研究中国现代诗下来的,曾读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徐迟、路易士等那种新鲜的都市美感,这种美感是古典诗歌从没有给过我们的:轻松、流畅、简洁、凝练……包括大量的台湾现代诗,像罗门他们。也曾经看到过1980年代初以宋琳他们为代表的“城市人”诗集。当然因为时代情况的不一样,文化主题可能是不一样了。我感觉1980年代的城市诗还是比较轻快的,因为都市是一个现代文明的象征,是当时中国一直要追求的现代性理想的寄托。可能到了今天,更多的是对于都市现代性的反思了,因为城市发展过快了,已经导致了对人的压抑。台湾对都市的描写,对都市和人的关系的理解,跟我们大陆诗人是大不一样的。20世纪初或者1990年代初所描写的人和都市的关系跟宋琳先生他们1980年代初所描写人和都市的关系肯定也会不一样。
另外我根据不同艺术领域对人和都市的关系的表达,今天在这边想到的一个没时间展开、可能也没想透的问题是:不同艺术体裁如何表达人和都市的关系。记得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论诗与艺术的时候谈到,同样的题材在诗歌这样的时间艺术和雕塑这样的空间艺术在表现的内容和重点以及给人的质感上的不同,我也感觉到第六代导演用摄影机镜头表现都市生活跟骆英先生用语言文字用诗歌的语言方式来描写都市生活应该有所不同,或者说怎么样才能更加的扬长避短。莱辛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诗可以非常详细地描写,非常直接地描写,但是因为它给人的感觉不是直接的,给人留下的想象的余地很大;但是空间艺术它是具象的,所以不能显得太丑恶等等瞬间张力太大的。
从某种角度来说,城市生活不适合于非常浪漫化的抒情,不适合那种跟主体非常接近的几乎没有障碍的直接的抒情。写都市诗需要一种经验的沉淀,是写经验而不是写感情。但是这种经验应该是经过非常独特的个体体验、个体感觉过的经验,并且沉静下来。要么更抒情一些,要么更客观更理智更冷静一些,这两个试验的方向都有可能比现在这种折中的复合的状态带来不同的景观吧。另外,其他不少老师也提到过,归结到一点,就是与经验的复杂性相关的是语言的复杂性。我的感觉是,透明了一点。对都市复杂的提炼最后必然表现为语言上的复杂、语言上的张力。这种状况的追求和生成好像有些欠缺。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城市给人一种空间感,创造了一种现代生活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是非常丰富、复杂,甚至难以为我们所把握的,难以为我们所看透的,是一种迷宫式的空间,所以我面对都市常感到一种迷茫,很难说我有一种能力能穿透它,它很多东西都超出了我的理解之外。骆英的诗在这一方面就显得过于单纯了些,当然这跟他的“诗歌就是一种宣泄”的诗观有关。他的写作注入了他的情感和激情。但是我想,单单靠情感和激情还很难把握现代生活的经验,它很复杂,有时还需要我们更大的关怀,更冷静更智慧的观照,或者更有耐性的承担。现代诗是一种承受,承受就是一切。
“当下经验”这个提法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也很认同。我们也要检点一下我们的“当下经验。”这是很丰富的,多种层面的。对我而言,既有城市生活的经验也有乡村的经验。我在昌平的乡下盖了房子,和农民住在一块,这是一种自我的选择。我特别需要这种距离感和多重的视觉——一种空间感,这是很奇妙的东西。我还是很庆幸作了这种选择。我后来写的一些诗歌片断就力求把多重的复杂的经验容纳进去,创造一个艺术空间,并在其间自由地出入。读者的自由度也比较大,可以自由出入。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也有更大的包容性;单一的视角,经验很难再使我满足,因为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非常复杂。我们能否找到一种形式,一种语言,把我们的经验都容纳、吸收进来,转化成为诗歌,这是我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想到诗歌与文明,诗人与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关系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视角。回顾中国新诗百年,当年闻一多特别赞赏郭沫若的《女神》的时代精神,主要还是从文明的角度而不像后来从反封建等等角度来肯定的。郭沫若有一首诗叫《笔立山头眺望》,是在日本写的。很明显他是把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作为一种新时代的曙光进行礼赞,最后把滚滚浓烟的烟囱比喻成现代文明之花,黑色的牡丹,对现代文明进行赞美。但是仅仅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你看,文明在作用于我们的诗歌。我又想到台湾诗人商禽写的一首诗叫《鸡》,说他在公园啃着公鸡肉快餐,啃着啃着,忽然想到已经很久没听过公鸡的啼叫了。那首诗写得很悲哀,让人难忘的是通过细节的描述,对文明的反思,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关怀。
收稿日期:2005—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