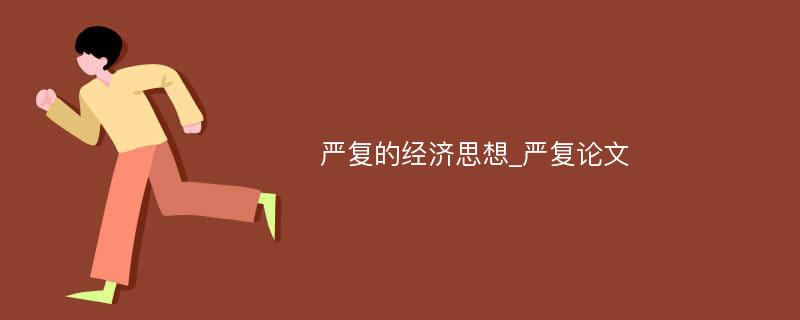
严复的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严复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1999)10—0071—05
严复(1854—1921年),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出身于一个普通中医家庭。1867年考入左宗堂创办的福州造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海军,1871年毕业,1876年被派往英国留学。留学期间,除学习海军外,他用很多时间阅读和研究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注意考察英国的政治、社会制度。 1879 年回国, 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 1880年被李鸿章调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升任会办(副校长),次年任总办(校长),在该校任职20年之久。这期间,严复积极宣传改革变法。1895年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批判封建专制,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严复的进步思想,受到当时先进人士的热烈赞扬,也引起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辟韩》发表后,张之洞曾指示人著文驳斥,并企图对严复进行迫害。反动势力的威胁,使严复失去了斗争的勇气,没有积极参与以后的变法维新运动,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著作的介绍和翻译工作中。1898年出版了他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1901年出版了以《原富》为名所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些著作为当时蓬勃兴起的反封建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对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
20世纪初,严复思想转向消极保守,他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主张复辟帝制,提倡复古尊孔,反对“五四”运动,由一个进步思想家堕落成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封建复古主义代表人物。
严复经济思想的积极内容主要集中在他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著作——《原富》一书的按语和他发表的一些政论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封建主义的压迫,特别是洋务派的官僚垄断政策,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束缚,争得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要求在经济思想领域里的反映。
严复首先借助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宣传经济自由主义。严复既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也了解当时流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并大量接受庸俗经济学观点。但严复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学时,却没有选择庸俗经济学著作,而是选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行翻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比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更适合中国的情况,“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注:《原富》译事例言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下同。)正是在其所译《原富》的大量按语中,严复借题发挥,对清政府和洋务派压制、阻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种做法,进行了尖锐地抨击。选择并花费极大气力翻译《原富》,是严复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严复指出,只有自由放任,社会经济才能发展,国家才能振兴。他指出,社会群体是由各个个人构成的。个人的状态如何,决定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面貌。只有使群体中每个人都积极求智求强求富,士农工商各业才能兴旺发达。人民要求于政府的,是能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而不是代他们经营其生计。除了兵刑二者应由国家负责外,其他一切事情,如礼教、营造、工商、树畜之事,“只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已多。”(注:《原富》第346—347页按语。)“凡一切可以听民自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注:《〈庄子〉评议》,《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以下简称《严复文选》第480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
严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各种理论和做法,都进行了批驳。
一种是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出发,对一些行业予以扶持,而对另一些行业进行限制。严复认为,财富是靠民力生产的。国家的支持和限制,必然要影响百姓生产力的自由发挥,从而影响财富的生产。所以国家用法术干预的结果,只能减少,而不会增加财政收入:“盖法术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狭,收成狭,少取且以为虐,况多取乎?”(注:《原富》第494页按语。)
一种是从平抑物价出发,主张对生产和流通进行干预。严复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驳斥说,物价如同流水,只要顺其自然,它就一定趋平,用不着政府干预。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平抑物价,如同在半山修水库拦水,库水虽平,但并非真平,所造成的水面其实远远高出自然形成的水平面。国家干预所造成的平价,实际也远远高于自然形成的水平价格,实际是官府垄断高价。只有自由竞争,才能不仅使物价真正趋平,而且能使物价趋廉。
严复还批判了行业垄断行为,认为这种垄断虽然可使该行业产品价高利厚,但却有损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世界各国相通的时代,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大门已被外国打开,外货已无法禁绝的国家,这种垄断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外国货物的低廉价格必定会将该行业的产品挤出市场,从而使本国该行业无法生存:“使其国已弱,力不足以禁绝外交,而他人叩关求通,与为互市之事,则货之本可贱者,吾既以法使之成贵矣,而他人无此,则二国之货,同辇入市,正如官私二盐,并行民间,其势非本国之业扫地无余不止。”(注:《原富》第142 页按语。)严复指出,洋务派在中国所推行的官僚垄断政策,造成的正是这种后果,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注:《原富》第509页按语。)使中国经济愈来愈从属于外国资本。
对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严复也主张任其自由。他十分赞赏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货币差额论与贸易差额论的批驳,认为“保商权,塞漏卮之说,无所是而全非。”(注:《原富》第478页按语。 )他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结合英国废除谷物法前后的情况指出,国家如果对粮食进出口加以干预,则弊端丛生,而允许粮食自由进出口,不仅可以调剂国内粮食余缺,保持粮价平稳,而且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英国自废除重商主义政策,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民物各任自然,地产大出,百倍于前,国用日侈富矣。”(注:《原富》第142页按语。 )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自由主义不仅应实行于一国之内,而且应通行于各国之间。
严复在宣传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也承认在有些领域,国家干预不能完全取消,取消了反而对经济发展不利。严复把国家应干预的经济活动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此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此如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趦趄。”(注:《原富》第724页按语。 )但同时严复强调,第三点“在上者为之先导”,应“必至不得已而后为之”(注:《原富》第724页按语。), 必须把它和洋务派借口“开风气”和“保护”而推行的“官督商办”划清界限。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实质是压迫、阻碍民族资本发展,与这里所说的“在上者为之先导”完全是两回事。
严复还指出,实行经济自由,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提高民力、民智、民德。民力不强,民智不开,民德不新,自由只能导致混乱,而不会导致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原强修订稿》,《严复文选》第29页。)而这三者,又取决于教育。所以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大力发展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二、变法改革主张
严复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证明,中国的贫弱是由于中国没有经济自由,是由于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发展遭到了摧残。是谁剥夺了中国百姓的经济自由,摧残了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发展?严复尖锐地指出,不是别人,就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法制礼教,即陈腐的封建上层建筑。
严复指出,中国历代封建君主都是窃国大盗。他们从人民手中窃取了政权,惟恐被人民重新夺回去,因此,他们制定了大量镇压人民的法令。封建法令的根本特点是防百姓之“奸”,而不是求人民之富,甚至为了防“奸”,不惜以破坏国家利源为代价:“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注:《辟韩》,《严复文选》第39页。),中国富强的根本障碍,就是封建君主专制与封建法制,这就是严复的结论。
严复认为,封建礼教也是中国富强的破坏力量。封建统治阶级在用封建法制压制人民的同时,还用封建礼教束缚人的思想,奴化人的灵魂。封建礼教同样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的工具。中国“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赢、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注:《救亡决论》,《严复文选》第57—58页。)绵延至今,造成“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注:《救亡决论》,《严复文选》第57—58页。)因此,中国要想富强,不仅要废除封建法制,而且要破除封建礼教:“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注:《辟韩》,《严复文选》第39页。)
严复还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紧迫形势论述变法改革的迫切性。他指出,历史上中国曾屡遭外族侵陵,但那时的外族都是些“游牧射猎”、未进大化的“无法”之邦,当他们占据了已进大化的、先进的“有法”之邦——中国,经过数代之后,都逐渐接受了中华文化而被汉化。所以,中国虽屡被外族侵占,但却始终未被灭亡。但是,现在入侵中国的西洋诸国,则与历史上的蛮夷完全不同。他们既有古代蛮夷之邦的长处,也有先进的“有法”之邦的优势,质和文都超过了中国:“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注:《原强》,《亚复文选》第13页。)在“国之富强,民之智勇”等方面,中国“无一事及外洋者”。(注:《拟上皇帝书》,《严复文选》第73页。)面临先进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如不改弦易辙,除旧布新,中华民族必将亡国亡种,这是先进文化必然征服落后文化的历史规律发挥作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严复还对“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传统思想进行批判和改造。他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天变地变,所不变者,独道而已。”(注:《救亡决论》,《严复文选》第54—55页。)但这个道,不是俗儒所说的封建统治之道,而是新的自由、民主、博爱的资产阶级之道;“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必兼爱克已,而后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物生人来不变者也。此所以为不变之道也。”(注:《救亡决论》,《严复文选》第54—55页。)而封建传统的治道人道,实际不是道,而是法,而法是必须因时变革的。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注:《拟上皇帝书》,《严复文选》第72页。)特别是陈腐的封建法制教化,更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候:“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注:《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文选》第64页。)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只有变法改革,学习西方,采用西法,才有出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注:《救亡决论》,《严复文选》第54页。)
严复详尽地比较了阻碍民力、民智、民德发展的中国封建教化与西方那些有利于民德、民智、民力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对立。他认为,西方制度的根本特点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注:《原强》,《严复文选》第14页。)这是和中国的封建专制完全不同的。由此产生了中西治道的各种差异:“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注:《论世变之亟》,《严复文选》第5页。)很清楚,变法改革,就是要取西方治道之长, 补中国之短,使中国经济的振兴和发展能获得像西方一样优良的社会条件。
严复非常重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认为西方“法令始于下院,……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注:《原强修订稿》,《严复文选》第34页。)是西方国家民力发扬、民气振奋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振兴,也必须采用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注:《原强修订稿》,《严复文选》第34页。)
严复主张富强要标本兼顾,本是民力、民智、民德,标是西学“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注:《与梁启超书》,《严复文选》第521 页。)因此,变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采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他认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注:《救亡决论》,《严复文选》第46页。)练军实,裕财赋,制船炮,讲通商,务树畜,开民智,正人心,所有这一切,“一涉其流,则又非西学格致皆不可。”(注:《救亡决论》,《严复文选》第50页。)中国要富强,“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是则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然则其事又曷可须臾缓哉!”(注:《救亡决论》,《严复文选》第52页。)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严复也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所以,他在赞美西法、西学和主张学习西方的同时,也批评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他指出,西方国家虽然富强,但决不是“至治极盛”的理想社会。大机器工业在西方二百多年来的发展所创造的财富,均为大资本家所垄断,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贫富对立的程度,要比中国严重得多:“夫在中国,言富以亿兆计,可谓雄矣。而在西洋,则以京垓秭载计者,不胜偻指焉。……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注:《原强修订稿》,《严复文选》第27页。)严复认为,这样一种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社会,是肯定不能长久的:“故深识之士,谓西洋教化不异唐花,语虽微偏,不为无见。至盛极治,因如此哉!”(注:《原强修订稿》,《严复文选》第27页。)
西方制度虽然有贫富不均的弊端,但西法仍然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因为严复认为,贫富不均的消灭,有待于整个人类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但现在的人民,包括西方国家的人民,其贤智程度远未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因此,富强与贫富对立相伴而行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三、对其他经济发展问题的看法
在谈论经济自由,谈论改革变法的同时,严复还用其从西方接受的资产阶级经济观点,对其他许多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严复认为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各种物质财富的第一来源,是各行各业之本:“国之财赋本于农”。(注:《原富》第858页。 )而工商各业则是对农业所获物质资料进行二次加工和流通,所以,相对农业,它们是末业。但是,严复虽然承认农、工商关系是本末关系,但他反对封建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然二者之事,理实有本末之分,古人之言,未尝误也。特后人于本末有轩轾之思,必贵本而贱末者,斯失之耳。”(注:《原富》第144页按语。)
关于农业生产方式,严复在极力称颂农民自耕其田的小生产的同时,也认识到只有采用现代大机器生产力,才能满足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要采用现代大机器生产力,则必须变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为社会化大生产,才有可能。“所谓民治小业,各自有其田,则农事以精地力以进者。……然自汽机盛行以还,则漫田汽耕之说出,而与小町自耕之议,相持不下。谓民日蕃众,非汽耕不足于养,而汽耕又断不可用于小町散畦之中,盖世局又一变矣,(注:《原富》第414页按语。)
严复对商业和工业在国家富强中的作用也很重视。
首先,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以商品流通和交通的发展为重要前提。如果交通不便,商品流通不畅,农产品没有销路,农业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他还用现代级差地租和土地价格理论分析交通运输对农业的重要意义:“吾闻计学之所以则壤也,其大较有二:土之腴瘠,一也;地之便左,二也。使其僻处陋荒,去都会市场窎远,而道茀涂险,不便转输,虽有膏腴,亦将久弃;必待水陆路涂既辟,而后树艺事兴,兴业者有子母相侔之望。 ”(注:《救贫》, 《严复文选》第297页。)所以,要发展农业生产,“自以推广交通为不二之要图, 交通又以铁路为最亟之营造。”(注:《救贫》,《严复文选》第298 页。)
工商业不仅关系到农业,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富强:“窃维十九稘以来,国之贫富强弱明昧,大抵视商政之盛衰。商政之盛衰,视制造之精窳、农桑之优劣。”(注:《原富》第769页按语。)20世纪初, 严复更大力宣传发展实业:“实业之事,将以转生货为熟货,以民力为财源,被之以工巧,塞一国之漏卮,使人人得饱暖也。”(注:《实业教育——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 《严复文选》第171页。)认为“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固当以实业教育为最急之务。 ”(注:《实业教育——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严复文选》第168页。)
严复认为,实业主要包括矿、路、舟车、冶、织、兵器等,而对当时中国最紧迫的,是路、矿二者。但路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严复主张利用外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国内许多人主张“拒绝外人资本之内流,而自开矿山,自造铁路”。(注:《法意》按语,《严复文选》第441页。 )有人甚至提出“宁使中国之路不成,矿不开,不令外国货财于吾国而得利。”(注:《法意》按语,《严复文选》第441页。)严复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 中国如果靠自筹资金办路矿,再过50年也办不起来。这不仅延缓了中国的发展速度,而且还会因为落后亡国而使自建路矿的理想化为泡影,因此,“使中国不以路矿救贫,则亦已耳;使中国而以路矿救贫,揆今日之时势,非借助于外力,固不可。”(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文选》第138—139页。)
严复指出,借外资建设中国路矿,外资所得的只是利的小头,利的大头是属于利用路矿的中国人民,所以利用外资是一件合算的事情。路矿办起以后,“往来之便,百货之通,地产之增值,前之弃于地而莫求者,乃今皆可以相易。民之耳目日新,斯旧习之专,思想之陋,将不期而自化,此虽县县为之学堂,其收效无此神也。故曰:路矿之宏开,乃用路矿者之大利也,而治路矿者之富又其次已。知此,尚何有利源外溢之事乎? ”(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 《严复文选》第139页。)
19世纪末,在译《原富》时,严复曾论述了帝国主义列强国内资本过剩和向国外输出资本问题。他指出,西方国家财富过多,投资场所不足,资本利润率低,劳动力价格高,所以就向国外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今日西国之患,恒坐过富。母财岁进,而业场不增,故其谋国者之推广业场为第一要义。德意志并力于山左,法兰西注意于南陲,而吴楚之间,则为英人之禁脔,凡皆为此一事而已。”(注:《原富》第114 页按语。)
可见,当时严复对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掠夺性、侵略性有明确的认识。在主张利用外资时,严复也没有否定外国资本的掠夺性,也承认利用外资有弊和害的一面。例如,由于外国列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约束,“故交涉之荆棘,常起于不可知,而为吾患。”(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文选》第 139页。)但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取消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这种“治外法权”,就可以避免这种弊害:“既居华之国中,斯为华法权之所治,则向者之患,又何有乎?”(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文选》139页。)显然,在当时半殖民地的中国, 严复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办到的。到1913年写《救贫》一文时,严复则不得不放弃利用外资的幻想,说中国祛贫,“独有母财,是吾所少,欲资邻人之富,则弊害孔多。”(注:《救贫》,《严复文选》第299页。 )因此提出了一个企图依靠小农经济筹集资本的主张。
严复还十分重视人的知识、技术对财富生产和国家富强的作用,认为生财不仅靠民力,而“民德民智之有关于生财尤钜。”(注:《原富》第330页按语。)“民智者,富强之原。”(注:《原强修订稿, 《严复文选》第32页。)所以他认为,如果农、工、商、贾是富国的四项事业的话,那么对劳动者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则应列为第五项事业。亚当·斯密把资本投资的生利之事,分为农、工、商、贾“四端”,严复认为这种分法是不足的,还应加上“民巧”一端:“后之计学家,谓民巧为国富之一,其始亦斥母积劳,而后能得其事,于斯密氏所列四端,又难定何属,固应更列一门。国富攸关,殆不可略也。”(注:《原富》第359页。)
严复还十分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全局之画”,“长久之计”,(注: 《法意》按语,《严复文选》第441页。)强调国家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政策。他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实行的常常是“无后政策”与“短命政策”:“无后政策者,谋仅及身,而不为子孙留余地也;短命政策者,快意当前,并不为己身计再往也。”(注:《法意》按语,《严复文选》第 439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腐朽的封建制度下,国家统治者和各级封建官吏只计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公利。只有民主制国家,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才可能“以一国为量,而作计动及百年。”(注:《法意》按语,《严复文选》第439页。)
严复还强调分配关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反对分配方面的绝对平均主义。他认为,如果贤、不肖所得报酬没有差别,就会挫伤贤智者的积极性,使愚不肖之人在社会上占上风。一个国家如果实行这样的政策,在“物竞天择”的时代里,必定亡国亡种:“盖家国砺世摩钝之权,在使贤者之得优而不肖者之得劣,则化民成俗,日蒸无疆。设强而同之,使民之收效取酬,贤不肖无以异,甚或不肖者道长,贤者道消,则江河日下,灭种亡国,在旦暮间耳。何则?物竞例行,合天下而论之,强智终利于存,弱愚终邻于灭故也。”(注:《原富》第149页—150页按语。)
严复还论述了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批判了中国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的崇俭黜奢论,提出了消费“以多为贵”的观点。第一,他指出,通过消费以满足人的需要,这是生产的目的。如果崇俭素,教止足,不消费, 则失去了生产的本意:“夫求财所以足用”(注:《原富》第350页按语。),“籍曰不用,则务富之本旨荒矣。 ”(注:《原富》第350页按语。)第二,只有不断增加财富的消费量, 人的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从生理上讲,这可以收到“厚生进种”(注:《原富》第350页按语。)之效。从社会方面讲,只有人民生活富足, 各种需要能得到充分满足,天下才会大治。第三,消费可以促进生产,如果光生产不消费,人民的生产活动就失去了动力,生产就不可能发展:“无享用则物产丰盈之后,民将缦然止足,而所以励其求益之情者,不其废乎?”(注:《原富》第350页按语。)
严复指出,在消费的问题上,关键是要正确处理“母财”与“支费”的关系。支费固然以多为贵,但如果危及“母财”即积累,就是应该反对的。相反,“俭”如果是为了增加“母财”即增加生产投资,也是应该肯定的。只讲积累不讲消费,就像农民把收获的粮食全部留作种子,行不通。反之,只讲消费不讲积累,则像农民把收获的粮食全部吃光而不留种子,也行不通。“独酌剂于母财支费二者之间,使财不失用,而其用且降而愈舒者,则庶乎其近之矣。”(注:《原富》第350 页按语。)
严复经济思想中这些观点,对我们的建设事业,显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收稿日期:1999—0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