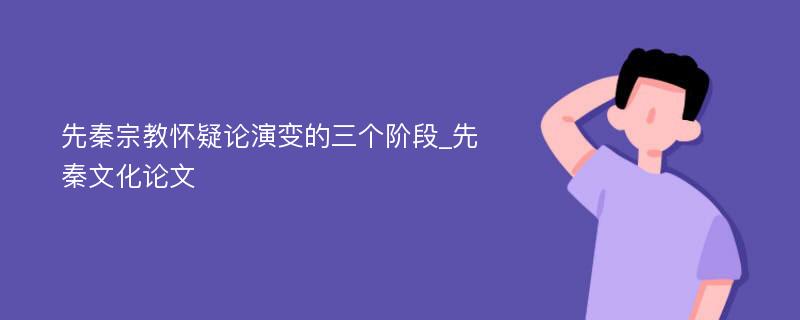
先秦宗教稽疑术演进的三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三个阶段论文,宗教论文,稽疑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稽疑”一词出自《尚书·洪范》,天赐禹洪范九畴“七曰明用稽疑”,蔡沈《集解》注:“稽,考也,有所疑则卜筮以考之。”《说文》有“卟”字:“卟,卜以问疑也。读与稽同。《书》云卟疑。”故知稽疑就是考疑、问疑,至于以卜筮考疑,则是商周二代才流行的。周人占筮,依据《易经》——《易经》“本为卜筮而作”。[1](卷66)本文将利用古代文献及民族学材料,对先秦宗教稽疑术的演进轨迹进行分析、梳理,认为先秦宗教稽疑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巫术通天神稽疑阶段、龟卜问祖先神阶段、易占人谋鬼谋阶段,以后随着宗教的伦理化,稽疑术便被抛弃而进入了所谓“神道设教”的时期。
一、巫术通天神稽疑
人类一直有稽疑的需要,先民更因其生产力低下而采取巫术通神向其求问的方法。巫术本是人神交通之术,巫为“神的代言人”,[2](P33)其证颇多。仅从文字上看,甲骨文的“巫”字表现的就是灵魂在天地之间往来的形象,张光直先生说:“天地之间,或祖灵及其余神祇与生者之间的沟通,要仰仗巫祝和巫术”;[3](P49)我国高山族的“人”、“鬼”、“巫”字的字形,同样表明巫往来于人鬼之间;[2](P32)先秦文献中也有丰富的材料说明我国上古宗教确曾经历过巫术通天神稽疑阶段。
《国语·楚语下》有一段著名的“楚昭王问观射父”,记载了我国上古巫术的发展史,据之可知上古通神的宗教的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民神不杂时期,由少数有巫术才能的人(觋、巫)主持宗教事务;二是家为巫史时期,人人都可通神,代神宣旨;三是绝地天通时期,不准一般人通天,只由“重”等少数几个大巫掌管通神事务。这里第一个时期泛称“古者”,表明其是来之传闻推测的,后两时期,即从“家为巫史”到“绝地天通”,确实合乎我们现在所见的民族学、人类学材料。
对社会发展程度较原始的澳大利亚土著的考察表明,“澳大利亚人都是巫师”,[4](P234)在参与宗教活动,行使致厄、祛病等巫术方面,人们是平等的,“任何人均可行之”;[5](P55)只是随着社会进步,才逐渐出现了垄断宗教事务的特定的祭司集团;[6]在部落走向联盟、政治走向集中的进程中,更有必要废止人人均可宣告神意的巫术,这正是颛顼帝“绝地天通”的真实含义。
但是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时已有很完备的部落联盟形式,政治也比较集中,何以到了其后任颛顼时反而出现九黎“家为巫史”的情况呢?这是因为九黎族的宗教乃是更古的宗教的遗存。
中国文化、政治最初的格局是东西对峙和融合的,东夷和西夏构成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最初来源,而南方的九黎、三苗却来自东方。东夷和西夏在中原交会,经过各部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原社会政治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宗教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楚语下》所称的“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的阶段。但南方的各部族生活在泽地之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发展迟缓,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一直到楚国兴起后,南方才逐渐赶上中原各地的发展),就宗教方面而言,它仍保存着东方各族古老的“家为巫史”宗教传统。
经过黄帝领导的几次部落联盟大战,基本上聚合了东西方各族,此后南方族群一直成为中原的心病。黄帝对南方曾采取高压政策,到颛顼帝时,情况则有变。颛顼是黄帝之孙,但同时又和南方人有密切的关系,他曾辅佐过东方的少昊族(而南方各族与东方族群有亲戚关系),南下后又娶了楚地华容女滕隍氏,生老童(卷章),老童是祝融氏吴回与重、黎的父亲。因为这些关系,颛顼改变了对南方的镇压政策,而从其宗教入手,颛顼帝认为南人作乱的主要根源是“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因而在南方进行了重大的宗教改革。
在此之前,中原的宗教到底是经过强制,还是经自然进化而达到“民神异业”呢?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我们无法断定,但是有一件事需要说明:据《山海经》记载,在帝颛顼以前,已经形成了很少的几处固定的可以通天的“名山”及几个有名的“大巫”来垄断宗教事务。[7](P80-82)颛顼帝在南方所做的,就是要实现如中原地区一样的官方宗教垄断,古人称之为“绝地天通”。
“绝地天通”在宗教上的含义就是“封天下之名山”,不准普通人随便登山与神相通往来,而将通天(神)作为颛顼、重等少数大巫的特权。
南方的宗教改革是很艰难的。颛顼之后,虽然从整个中国看,基本上实现了由人人可以通神的民间宗教到只有少数人被准通神的官方宗教的转变,但在局部地区,尤其是在南方,通神术仍很流行,所谓“自三苗国于洞庭始创巫教,颛顼正之而流不息。”[8](P64)《礼记正义》引郑玄注说:“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统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臣尧又窜之。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
这种垄断在宗教发展史上是一次大进步,但颛顼帝的改革只是将通灵(神)巫术由官方垄断了,并没有否定通灵术本身的价值,《史记·五帝本纪》称颛顼帝本人也是“依鬼神以制义”的,这表明在颛顼帝前后,巫术的主要方式是通神术,人若有疑,稽神之法便是登上高山、天梯,直接谛听神灵的启示,并将其旨意向世人宣告。
传说表明,登上“天梯”经过巫神交感,从而“下宣神旨,上达民情”的传统来自久远。《山海经·海内经》说:“建木……大昊爰过”,是太昊已能通神;《海内西经》说“巫咸国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登葆山亦为天梯。至于后代南方巫觋法事中的“赤足登刀梯”之巫术,学者还视其为古巫登天梯之衍变,[8](P43)可见通神术虽已被官方垄断,但在民间仍不绝如缕。
不过官方的通神宗教毕竟因垄断而丧失了人民的基础,它的命运就取决于巫师集团与世俗首领们之间的斗争结果,经过夏商两代,随着世俗贵族的得势,它就渐渐衰落了。而在民间仍存在着许多其他的求问神意的稽疑术,其中的卜筮法竟渐渐走入上层,且挤走通神术,成为官方稽疑术的主要形式。
二、龟卜问祖先神
通神的道路既被封起来,而民众又普遍地有求问神意的要求,于是另一些古老的稽疑术(如龟卜)就被民间巫师广泛地使用,且最后进入统治阶级的殿堂,成为一代风气,宗教稽疑术就到了龟卜问神阶段。
卜法的起原甚古。据考古发掘,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如在内蒙古乌达盟巴林左旗富河沟门、辽宁羊头洼、唐山大城山、山东曹县莘家集、内蒙古赤峰、蜘蛛山夏家店下层、赤峰药王庙、宁城南山根等遗址均发现了一些无字卜骨,以鹿、猪、牛、羊肩胛骨为原料。[2](P5)据民族学材料,现在在一些原始民族中还流行着各种占卜法,如蚂蚁卜、青蛙卜、鸡卜等,[2](P154-160)这些卜法和中国后来流行的龟卜术显然不是一个系统,当是远古卜法的残留。
在中国大陆,最流行的占卜法当然是龟卜和筮占。《尚书·大禹谟》载,舜在禅位于禹时,“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可见在舜禹时龟筮之法已在社会上有了很高的地位。不过从舜语中还可看出,此时之“鬼神其依”的通神术与龟筮之法是并行的,这种情况,由夏代的禹一直到殷商的盘庚时都还存在。
禹是古代有名的大巫,他与巫术的关系很大,第一种就是所谓“禹步”,这实际上是巫的舞蹈。《洞庭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第四》载:“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步。……然届南海之滨,见鸟禁咒,能令大石翻动。此鸟禁时,常作是步。禹模逐写其行,令之入术。自兹以还,无术不验。因禹制作,故曰禹步。”[2](P8)以舞事神,是一种通神术,既可召役神灵,更当能问神意。其次还有制作祭器,《韩非子·十过》记“禹作为祭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禹常以此种祭器稽神:“或有伏泉磐石,非眼力所及者,必召海若、河宗、山神、地祇,问以决之。”[8](P69)另外《拾遗记》卷二云:禹铸九鼎,“鼎中常满,以占气象之休否”[2](P8),这已是用器具间接地(而非直接通神)问神意了。《归藏·郑母经》还讲到鲧受命治洪水时,求巫作筮之占语为“不吉,有初无后。”[8](P68)另外“在相当于夏文化的龙山文化考古中,也发现不少卜骨”,[2](P8)可见禹时除通灵术外确已实行多种稽疑术了。
殷商代夏,宗教乃有一个重大的转折,这表现在:第一,问神术由问天神变成问祖先神;第二,盘庚前后,稽疑术由巫舞形式的通神问神阶段进入龟卜形式的问神阶段。
殷人信鬼已成公论,《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殷人所尊、先的鬼、神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墨子·明鬼》说:“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殷人所尊者是祖先死而为之鬼,殷人虽曾笃信天命,但对天鬼、天神却不大尊敬,甚至还有“射天”传统。
《史记·殷本纪》载商帝武乙“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戮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无独有偶,《宋微子世家》又载殷人后裔宋康王曾“盛血以韦囊,悬而射之,命曰射天。”殷人一改颛顼以来登山通天神之法,而尊祖先神,其向祖先神问事的方法也变为借助甲骨。侯外庐先生说:“殷人万事求卜,所尊的是祖先一元神。一切‘国之大事’,特别是‘祀与戎’(祭祀和战争)这样大事,都要通过宗教仪式以取得祖先神的承认。”[9](P23)“‘卜’这一观念是求祖先神降命的意思。”[9](P24)
这种稽神方法的改变约当盘庚之时,这点不仅可以从盘庚迁殷后为殷都的安阳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文中看出,而且还有文献可证。
据《尚书·盘庚》,盘庚迁殷前曾卜过,卜的结果如何呢?卜兆是不支持迁殷的,这从两处可以看出:一是盘庚迁殷后,老百姓虽不乐意(“民不适有居”),但其亲近的贵戚大臣却是支持的,“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刈。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氐绥四方。”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能互相救助,只是稽考占卜,那有什么用呢?”这是在为盘庚迁殷陈理,是用天命和民生来反对对占卜的完全依赖。二是盘庚迁殷后对大臣的训话,解释自己为何违背卜兆坚持迁都:“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盘庚将“吊由灵各”提到“卜”之上。“各”即“格”,“灵各”即神降之意,这是以通神术对抗卜法。
盘庚迁殷过程中有卜法和通神术之争,其最终迁都的结果是否意味着通神术高于卜法呢?其实正相反,迁殷的艰巨,正反映出卜法地位的升高,盘庚一定是将政治的压力和祖先神惩罚的威胁并用的。他既说:“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又反复警告和恐吓:“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汝悔身何及?……矧予制乃短长之命?”“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们将这许多话与盘庚吞吞吐吐的“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的一句相比,就得出一个结论:盘庚迁殷虽出于保存商人的目的,但是民众不支持,卜也不吉,唯有用政治上的高压了,为了对付在社会上已很有威信的卜法,不得不祭起更古老的通神术法宝来。
盘庚的“违卜”,虽然是卜法的失败,但这却是它对通神术的最后一次失败,我们从殷墟发掘出的十几万片甲骨中可以看出,迁殷以后的历代商王已是如何迷信甲骨卜法了,同时我们还有另一个有价值的结论:甲骨卜法也已经被少数统治者所垄断了。
对卜法进行垄断的方法不外是:一、对卜龟材料的高要求,要“宝龟”、“元龟”,使一般民众难以获得。二、对卜龟的复杂处理,甲骨经过修治以后,要钻出圆窝,即“钻”,并在圆窝旁边凿成凹槽,即“凿”,最后用火烧灼钻穴以得裂纹即卜兆,钻、凿皆用是晚商才有的,早商则只用钻,而民间的处理则更为简单,如彝族的骨卜所用材料为羊、牛或猪的肩胛骨,不经钻凿,直接烧灼。[2](P162)三、对卜兆的繁琐分类,《周礼·春官·宗伯》谓“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而民间对卜兆吉凶的判定却很简单,如上述彝族把灼处分为四个方向,上为外方,下为内方,左为自己,右为鬼神,如果左或下方裂纹既直又长,属吉兆,否则为凶兆。[2](P162)四、规定只由少数人集中在少数地点进行龟卜,《宗伯》谓“太卜掌三兆之法”,从今天的甲骨发掘看,甲骨的存放也是比较集中的。
既经许多限制,民间便难行此种卜法,同为卜法,其简单之法也渐渐不能得到正统的承认。但此时另一种古老的稽疑术——筮占法却在民间大行其道,并在殷周交潜之际进入庙堂,融入了“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泉。
三、易占人谋鬼谋
王国维说:“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10]就宗教稽疑术之变革言,此语亦不虚。夏殷之稽疑方式虽有差异,但皆不出“鬼谋”一途,而殷周之际则有两个剧烈变化:一是形式上以筮占取代龟卜,二是内涵上以易占的“人谋鬼谋”取代龟卜的纯粹“鬼谋”。下面我们就分析这两种取代的过程。
易占乃是筮法的一种,是藉蓍草以一定的方法得出数目,然后根据其奇偶性等而得出卦画,再对照卦爻辞由一定的规则来解释吉凶悔吝等。这种方法起源很早,传统说“人更三世”《汉书·艺文志》,最早上推到伏羲,从考古看,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淞泽文化遗物上,就有由数构成的数字卦,殷墟卜骨也有类似卦画。[11]《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古书云“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吕氏春秋·勿躬》及《世本·作篇》都记“巫咸作筮”,《路史》载“神农使巫咸作筮”,则筮法是夏商都有的。而古人所谓“三易”之说也主张神农、黄帝或至少夏商各有其易占之法,可见筮法起源甚古。
易占与龟卜,除去形式上的蓍数占与甲骨灼兆的不同外,更重要的是在释卦、兆时的解释体例的不同。龟卜是问神稽疑,得出卜兆后,直接查对图书,对号入座,吉凶立判,因而纯粹是“鬼谋”;而易占在得出卦画以后,还区别变与不变之爻,讲究在变化中见吉凶,且又强调人在事态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这种体例显然不仅是稽神断疑,而且更体现出人的理智运作及能动实践,前人谓之“人谋”。
有很多证据表明周人宗教稽疑术处于“人谋鬼谋”阶段。“鬼谋”还是有的,事实上周人有很深的神鬼观念,从稽疑术上讲,问神的卜法仍在使用,《周礼·春官》说:“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左传》僖公四年载卜人的话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即使《易》本身,到《易传》时代,《说卦》也还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将易占的有效性归之于神灵。王夫之《周易内传·系辞上传》论此最明确:“大衍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多寡成于无心,不测之神,鬼谋也。”
但是易占之变革在于“人谋”,王夫之说:“大衍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二,挂一,……审七八九六之变,以求肖乎理,人谋也。”“若龟之见兆,但有鬼谋,而无人谋。”“人谋”之关键,一在提倡变中见理,二在主张吉凶由人。
所谓变中见理,可由易占体例之“变卦说”看出。《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乃《周易》《观》卦六四爻辞,而由《观》之《否》即是《观》卦之六四爻由阴爻变为阳爻,可见是以变爻辞占断的。此种例子,《左传》、《国语》屡见,朱熹《易学启蒙》曾据之定七条体例。这种强调变化中见理的释筮法,大不同于龟卜之视兆对册,它是人的理智的安排。
所谓吉凶由人,是说易占虽然可以推测出未来的变化,但人事的吉凶,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人的德行。《左传》襄公九年记鲁穆姜筮往东宫,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左传》昭公十二年的南蒯叛季氏筮遇《坤》之《比》,僖公十五年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论者多按吉凶由人解之。无德之人问易,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所谓“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12](P332)此种例子还不少,入周以后讲“人谋”已成为时代潮流。
易占在周取代卜法,是有一个过程的。卜、筮的异途虽古已有之,但此次取代却有其直接的时代原因,那就是周人克商取得了统治地位,在制度、宗教上当然要有大变革。如前所言,筮法在夏商都已使用,《尚书·洪范》记殷人箕子答周武王问,谓“乃命卜筮”,可见殷人卜筮都用的,《诗经》则屡有“卜筮”连用者,如《小雅·杕杜》说“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卫风·氓》说“尔卜尔筮,体无咎言”等,可见周人也并用卜筮。至于卜、筮地位的高低,则有变迁。《周礼》说“先筮而后卜”,《正义》引贾疏:“筮轻龟重,贱者先即事。”卜法还高于筮法,而筮法的灵验性还曾一度试图建立在神龟的灵异性上。(《史记·龟策列传》)但到了上引《左传》僖公四年晋献公事,卜人虽云“筮短龟长,不如从长”,而献公还是“从筮”,说明时至春秋,筮法的地位已有提高,同时周人确实再也不象殷人那样“万事求卜”,甚至后来“卜筮”连称实际上也只是指易占筮法了。《逸周书·程寤》载太姒梦受商之天命于皇天上帝,“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用占不用卜,事非偶然,可见周人宫廷中筮占的地位甚高。
“人谋鬼谋”取代纯粹“鬼谋”,与周人思想的整体发展相吻合。“以周公为卓越代表的西周思想,以宗教观念和政治思想为主要内容,取得了殷商所不能比的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就宗教观念的角度来说,可以概括为:第一,天命无常;第二,天命惟德;第三,天意在民。”[13](P191)这种对命运的不可捉摸性的认识以及对人参与历史创造过程的觉悟,促使整个西周宗教转向了伦理宗教,易占作为稽疑术,虽免不了含有神鬼迷信的成分,但也不能不“唯变所适”,顺应世风。
这种“人谋”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及在逻辑上彻底化以后,必然要将易占中尚存的“鬼谋”思想清除掉,如果这样,易占也就失去了稽神问疑的功能,而成为劝诫之学了。这个过程,在历史上,是与掌握神权的整个祭司阶层的衰落相连的。
从逻辑上讲,宗教稽疑术虽意存问神,但其目的却是为解决人事的,在最初就存在着为了人的目的不惜违卜、违筮的事,《尚书·大诰》记载周武王逝世后,“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当时占卜是吉兆,故成王说:“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而群臣却反对说:“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这表明当时已有用现实政治的理由来“违卜”的观念了。以后随着科学文化的进步,宗教作为一种颠倒的世界观的面目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就出现了“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说法,出现了西门豹镇压巫婆的事件(《史记·西门豹传》),出现了“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礼记·王制》)的禁令。儒家更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系统提出了“神道设教”(《周易·观·彖》)的观点。
《论语·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用一“如”字暗示了对宗教的怀疑,到《荀子·天论》则明确说:“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而被保存下来。对于稽疑术,知识阶层还提出“复其祝卜”、“观其德义”、[12](P340)“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等观点,从而和统治者的“以为文”及民众的“以为神”区别开来,发扬了“人道”的精神,滋润了几千年的民族文化。
先秦宗教稽疑术经历了由巫术通天神稽疑到龟卜问祖先神再到易占人谋鬼谋的演化,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明确的。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民间是宗教发展的肥沃土壤,在一个时代的公共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官方宗教往往是对民间宗教以某种方式加以改造、垄断的结果,民间宗教虽不为正统社会所认可,但却一直不绝如缕,还保留了大量的宗教原生态的遗存。先秦宗教从非理性的情绪体验向理性化、从纯粹神灵宗教向伦理宗教发展,从最初的巫术通神到易传哲学,中国哲学终于“消灭宗教本身”,从宗教母胎中孕育出来,进入了辉煌的诸子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