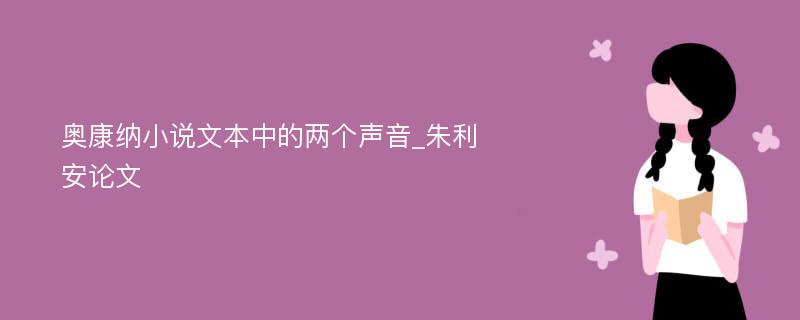
奥康纳小说文本中的两个声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音论文,两个论文,奥康纳论文,小说论文,文本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康纳是20世纪美国南方几位著名女性作家中的一个。她的作品不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小说,而是令人震撼的短篇故事。在她的故事中,丑陋的畸人和神秘的宗教、发指的幽默和病态的暴力交织在一起,使人读后惊骇迷惑,难怪《美国小说:1940—1980》曾这么评价奥康纳,说她是美国50年代文学中最有个性、最独特的声音,也是最不易为人理解的一位。的确,她的小说就像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女诗人艾米莉·狄更生的诗那样奇异、怪秘,令人回味无穷。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生活中的奥康纳也似乎是一个狄更生似的人物:深居简出,与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没有太多的联系。她那短暂的一生都是在南方渡过的:先是在萨凡纳,这是佐治亚州最古老的文化中心,它有着浓郁天主教气氛,在那里,传统的习俗和观念被保存得完好无缺;后是在一个有着150年历史的农场生活,那里田园式的风光、 黑人和白人帮工、能干的欧洲移民在她周围构成了一个昔日南方遗迹的缩影。但奥康纳生活环境上的传统性并不意味着她个人思想上的封闭。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文学硕士,大学时,她便立志,要么写小说,要么进行漫画创作,这两项都是非常富有挑战性的兴趣和职业。而且,她终于在这两者中间找到了一个折中的道路,那就是,用文学的笔来漫画人生。她曾经北上学艺,拜访那里的学者和教授,在她的文化朋友中有男性作家,也有女性知识分子,他们都对南方古老的文化有着特别的兴趣。奥康纳的这段经历对她以后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后来当她因病困居于南方的农场时,她仍支着拐杖,去各地讲学,并和外界保持着广泛的联系。所以,奥康纳并不同于狄更生,因为她毕竟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在现代的美国,是一个现代的知识女性。
多年来,国内外批评家们对她的作品的理解一直局限在传统的模式之中,强调其作品中天主教和地方作家的两大特点,人们对她作品的关注也是侧重于其文本的现实意义、讽刺手法、故事结束时突如其来的暴力以及她本人对畸人的偏好等等。除此之外,也有认为她的作品表现的是一种自我欺骗和逃避,是文明秩序和荒野的对立。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她作为女性作家这一点给她的作品所带来的影响,忽略了她作品中围绕性别而展开的奇怪现象:她的故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暴力事件,即一股外来势力旋风般地把现存的秩序打得粉碎。在这里,令人不解的是,前者多是男性,后者则几乎是纯一色的女性人物。这种男女角色的结构是巧合呢?还是有意的安排?它是否体现着男—女性别的矛盾呢?如果不是,它是否隐含着别的禅机呢?
奥康纳生活的时代背景中的确隐含着很浓的女性主义觉悟意识。进入本世纪以后,不论是在美国或是在欧洲,传统上的女性概念日渐受到人们的挑战,妇女开始觉悟到自身的价值和权利。30年代独自飞越大西洋的阿米莉亚·埃尔吟特就用事实向世人证明了:妇女有能力在一个完全由男子独占的领域里成绩卓越。到了奥康纳生活的50、60年代,这种朦胧的女性意识发展成为一种运动,这一运动的先锋女鼓励妇女们打破男性主宰的社会概念,勇敢地反抗传统上为她们规定的生活模式。
这样,我们在阅读奥康纳的作品时,就不能忽视其背景画面中的这种新思潮,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总是淹没在她的南方区域、宗教情绪像和她的畸人形象里,即不能淹没在男性主宰的主题中。她是南方作家,但她首先应该是一位女性作家,因此,我们在对她进行解读时,就不能忽视其作品在女性视角下的意义。
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一再强调,妇女有一个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学史,妇女的作品是表现和寻找妇女经历的媒介,同时,她们还指出,很久以来,妇女文艺所具有的艺术的重要性、历史和主题的连贯性均被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价值观所淹没了。所以,像勃朗特、沃尔夫和狄更生这样的女性作家只能在男性作家的夹缝里生存,而更多的妇女作者则像慧星一样,在一瞬间的辉煌之后,消失在人们的忘河之中。而事实上,女性作家有其自己的文学,虽然“她们习惯于、同时也善于运用男性的比喻和神话,然而,所要表达的含义却与原意相去甚远。”她们对妇女有着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看法和兴趣,这就是说,她们的声音“既不在传统之内,也不在男性传统之外”。用肖沃特的话来说就是,女子创作是“双声话语”,它总是体现了失声和主宰双重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因此,在这些妇女作品中,既有对父权制文学标准的顺从,也有对它的破坏。
在阅读奥康纳的小说时,我们不难发现,她的作品里也同样隐含着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是传统主流的声音,它向人们诉说着女性是弱者的古老故事;另一个则是奥康纳作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声音:在这一声音里,女性成为了关注的中心,一组和男人一样重要的社会存在,一种被置于时代大潮中进行研究的自然对象。从这一点上来讲,奥康纳的文本中便包含了一种妇性主义的情绪,但这种情绪不是狭隘政治意义上的女权主义,因为它不是强调女性的权力,而是对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身份和命运在进行探索。
男性主流文化下的影子
像所有女性作家的作品那样,奥康纳的小说讲得最多的也是女人的故事,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不仅是现有秩序的主要组成成分和情节中矛盾的焦点,她们还是矛盾高潮时暴力事件的承受者。比如,在《善良的乡下人》中,除了推销员庞特以外,其余的人物是清一色的女性:弗雷门太太和她两个没露面的女儿,以及霍伯尔太太和她的女儿乔伊。故事的主人公是乔伊,一个装有一只木腿的32岁的女哲学博士,内心自卑,她却因为拥有学位而变得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像火神赫尔嘎那样外丑内美,这种偏执盲目的性格使她最终在与庞特的关系中陷入致命、可怜的尴尬中。除了《善良的乡下人》以外,还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中的朱利安妈妈,《背井离乡的人》中的麦金太太,以及《好人难寻》中的老祖母,《格林里夫一家》中的梅太太和《启示》中的特平太太,在奥康纳的小说世界里,是她们而不是那些男性形象成为最令人难忘的一群。
传统上,人们总把妇女与家庭、孩子和丈夫连在一起,并用这些关系来定格出她们的身份和全部生活内容。虽然奥康纳的女性人物不是通常人们所期盼的温柔一族,她们多是些干巴巴精明能干的管家婆,和斤斤计较拥有帮工的农场主。但尽管如此,这些妇女仍没有脱离传统女性的特点。
朱利安妈妈是她们中最典型的一个,她出身于南方名门,幼时是一个有奶妈照看的受人疼爱的小姑娘,但当小说开始时,她已是一个家道衰败、守着儿子过日子的老妇人了。她省吃俭用,供她儿子成人并读上大学,她认定他会前途无量,虽然事实上,生活在精神泡沫中的儿子朱利安已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可她还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觉得他会成为一名作家,并能重振家风。她像《好人难寻》中的老祖母一样,属于昔日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女人。难怪,她在故事中除了朱利安妈妈这个身份以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即象征着没有自我)。其实,“母亲”、“妻子”和“寡妇”几乎是奥康纳故事中所有女性形象的身份。又如在《背井离乡的人》中,虽然女场主麦金太太总是对念念不忘她那已去世的丈夫的老黑人强调,“我是这一带掌握着一切的人”,可事实上,她和那黑人一样,也生活在她丈夫的影子里。小说中这样介绍到她:她曾经埋葬过一个丈夫,又和另外两个离了婚,她手中的那个农场则是她最后一次婚姻的收获,虽然她的这位法官丈夫已死去多年,他的话仍是挂在她嘴边的处世良言,他曾经处理过业务的那间房子对她来说更是神圣不可更改的地方。
所以,这些便是奥康纳小说中的女性:封闭的农场是她们的全部世界,婚姻、后代、财产是她们的生活内容,《善良的乡下人》中关于弗雷门太太两个女儿的无聊对话似乎给所有这些女性划上了一个符号,她们虽然性格不同,经历有异,但她们都没有跳出传统女性的定格。就是学问最深的乔伊也不例外。尽管她有三个学位,尽管她标榜自己是一位无神论者,但在骗子庞特的甜言蜜语面前,她马上真相毕露,想到要以身相许,和他私奔,现出她传统女性的本色。
当然,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的不仅是这些女性形象所表现出的传统性,而且还在于她们与男性人物所发生的冲突:她们在男性力量面前所呈现出的脆弱,和男性力量对她们的破坏都印证了奥康纳文本中的传统观念的一面。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多数奥康纳的小说都是建立在一对对男—女人物之间的矛盾上。最典型的有乔伊—庞特,此外,还有《背井离乡的人》中的麦金太太和肖特利太太—波兰男性移民,《格林里夫一家》中的梅太太—格林父子(和他们的公牛),以及《好人难寻》中的老祖母一名叫“不合时宜”的男性暴徒。而且,在这些冲突中,她们无一例外地扮演了失败的角色,她们不只失去了生活的平衡,甚至还陪进去了自己的性命。
如在《善良的乡下人》中,乔伊自以为是一位玩世不恭的天才,她要引诱“智力低下”、老实巴交的庞特,给他一个生活的教训。殊不知,他才是什么都不信的魔鬼玩主,他把她诱到无人的仓库,拿去她的假肢,然后扬长而去,而她则不得不无助地坐在荡满尘土的阳光中,饱受羞辱之苦。这一过程中,他们两个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一个方面向人们证明了,男人才是最后的赢家。而就乔伊来说,不管她的学问有多深,她身上潜在的女性特质仍是她栽在庞特手中的原因。
而在《背井离乡的人》中,麦金太太和肖特利太太这两个女性的命运也都是因为一个男人的闯入而受到冲击,虽然闯入者波兰移民在故事中也死去了,但女性一方所付出的代价更大,先是肖特利太太在极度狂乱中丧命,后来,波兰移民的死终于导致麦金太太赖于生存的环境散了架:她失去了农场,并疾病缠身,落得一个潦倒孤寂的下场。相比之下,《好人难寻》中的老祖母所面对的则是更具破坏力的男性力量,一个毫无理性的杀人狂,她的“母爱”无法打动他,他带给她的是莫明其妙的杀身之祸。
当然,这种男女性别双方冲击最为明显的则是《格林里夫一家》,对于女主人公梅太太来说,生活中一直使她烦心的事就是,总有些懒汉家的公猪不停地搔扰她家的麦地,而且,15年来,她和她的白人帮工格林利夫(以及他的两个儿子)的争斗也一直没停过,这一争斗最后发展成为她和他们家的公牛之间的仇恨,她最担心的就是这头公牛会弄杂了她的种牛。这头公牛不断地闯入她的农场,终于用一只犄角刺穿了她的心脏,在这里,公牛被比作是“一只狂热的情人”,而梅太太在死前的一瞬间似乎叙说着她最后的发现,也许,她终于发现了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在由“公牛”所象征的势力面前,她注定是一个弱者。到此,奥康纳故事中一再出现但却模糊不清的男女矛盾生动地凸现出来。在小说中,梅太太的话更突出了这一主题:“他们不来(指格林利夫的两个儿子)只是因为我是个女人,”“你跟一个女人打交道,什么事都能不了了之。如果换了一个男子汉……”这句话终于暴露了她强硬外表下的自卑本质,这种自卑也为奥康纳故事中男女人物矛盾和冲突的结果作出了注释,在传统习惯思想中,人们习惯于将男性与强壮、主动划等号,而将女性与弱小、被动相提并论,奥康纳人物的自卑情绪乃是她的作品中回响着传统男性文学中女性是附属的、可被征服的这一观念的余声。
女性主义的潜流
在“真理”性阐释已消解的时代,我们对奥康纳文本的理解当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这种传统的调子上。拨开表层的色彩,人们会发现,在它下面,还划动着另一个隐秘的世界。在这里,女人被置于现代社会的舞台上,她们的命运和困境成为文本显微镜下的焦点,它反映了作者对新时代女性命运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和思考不仅解构了奥康纳文本的表面附合,而且也表现出女性作家一种变相的反叛情绪。
首先,康奥纳的小说肯定了妇女的能力,在正常的生活秩序中,她们并不比男人逊色,虽然在精神上,她们对男人表现出一定的依赖性,但是她们中有不少在供养着男人,而不是男人养活她们。就像《识时务者为俊杰》中的那样,朱利安妈妈劳累奔波,养活着儿子,可她儿子朱利安却是一个沉湎于精神肥皂泡里的人物,虽然他总说,“早晚有一天我也会开始挣大钱的,”但他心里明白,他其实永远也办不到,他只能做做他的白日梦而已。同样,《格林里夫一家》中的梅太太也是守着儿子过的寡妇,她像奴隶一样地苦干,在下层白人日渐崛起的压力下,支撑着那个农场,而她两个儿子却都是不争气的货色,他们不结婚,不生子,一事无成,他们对生活和他们周围的一切除了憎恨,别的毫无兴趣。
另外,在奥康纳的作品中,还有一组女性是被放在夫妻关系的背景上出现的,如《背井离乡的人》中肖特利太太,一反传统上的“夫唱妇随”,她和她丈夫是“妇唱夫随”的一对,她有着庞大的身驱,总是腆着肚子,昂着头,像座山一样的神气。这一特点反映在他们夫妻关系上,表现出一种女方的权威和支配,在故事中,一向是她说,他做,她指挥,他行动,甚至当肖特利太太死后,麦金太太也是看在他死去的妻子的份上,才收留了他,可离开了妻子的肖特利却变得更加迟钝见忘,像没了魂魄一样。其实,在该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肖特利太太是最活跃的人物,她总在观察、省视、思考和不满,虽然她的思考由于她的主观偏见而完全陷入狂乱的地步,以至于她在歇斯底里中死去,但她毕竟是故事中思维最活跃、最主动的人。
那么,我们不禁会问,既然如此,她们为什么会成为悲剧的主角呢?奥康纳的文本所提供的答案是,那是因为她们太自以为是地沉湎于她们传统的角色中,太心甘情愿地接受已定的生活模式,以至于变得封闭,保守,默守陈规,排斥变化。阿瑟尔斯在《双重性格》中曾这样评价奥康纳的人物:他们是现代小说里“最不思考”的人,要么毫无意识,要么盲目自信;他们蛮横地握着狭隘、呆板的自我感觉,从不怀疑,从不反省。这种评价与其说是对所有人物的总结,不如说是对其女性人物的概括(因为她小说的主角多是女性),从霍伯韦尔太太、乔伊、梅太太、麦金太太、肖特利太太到朱利安妈妈无一不如此。
她们中很多人都有几句挂在嘴上的人生哲言,她们不时地会把这些老掉牙的几句话像宝贝似地说上几遍,这些重复得已流于形式的誓言只能说明她们的狭隘和闭塞,而这一点也正是她们的悲剧所在。如果乔伊能够清醒地对待自己和生活,她就不会那么轻易地对庞特自下结论,以至于受骗受辱;如果麦金太太没有拒绝外来移民给她带来的变化,她就不会毁掉农场兴旺的机会和前景;同样,如果朱利安妈妈不是抱着昔日南方对黑人的陈旧看法,她也就不会非要赐给黑人男孩一枚硬币,而受到他母亲致命的一拳了。
这些女人使我想到《你拯救的是你自己》中的那个傻女儿,该故事也由一位母亲和一个傻女儿构成。在故事中,一个残废男人闯入并打破了她们平静而混沌的日子,为了她们家的一辆破汽车,他答应了老妇人的要求,娶了漂亮的傻姑娘,最后,他却在离家几十里的地方,弃下睡梦中的傻姑娘,独自离去。在奥康纳的作品中,这个缺心眼的傻姑娘仿佛是其他所有女性处境的变相化身,封闭于传统角色中的她们和傻女儿其实没有两样,她们当然不可避免地会重蹈她的悲剧。
奥康纳的女性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她们是20世纪的女性。20世纪是技术不断更新、思想日新月移的时代。现代社会不仅带来了新的民主意识、生活的现代化等正面变化,同时也伴随着暴力和病态心理等负面的效果,所有这些无情地向安于现状的女性冲来。
值得注意的是,奥康纳使用旧瓶装新酒的手法,利用传统上男性等于力量(活力和破坏力)的联想,赋予男性现代社会象征的一个角色。一方面,《好人难寻》中的“不合时宜”和《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庞特分别代表现代社会中的凶残暴行和现代人的心理病态以及宗教意识的堕落;另一方面,《格林里夫一家》中的格林兄弟和《背井离乡的人》中的波兰移民吉扎克反映着社会发展中的新势力。格林家的崭新的红砖房以及最新最现代化的挤奶房与梅太太的保守思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机器”使格林兄弟同时拥有强劲的活力和摧毁旧势力的能力;而来自异国他乡的波兰人更是如此,他的金丝边眼睛、奇怪的欧洲礼节、名字和语言都使他成为一个外界新思想的象征。他精通先进的技术,“会开拖拉机、切草机……这地方拥有的任何机器。他是一个熟练的技工、一个木工和一个泥瓦工。他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仿佛是一台干活的机器。”他的出现是外部世界和现代意识对古老南方价值观的撞击,可惜麦金太太却把这种陌生的势力视作猛兽,以至于在他被害的一瞬间,她沉默了,她的沉默使她变成一个无名的帮凶,在此,她所毁掉的不仅是他给她带来的兴旺前景,同时也毁了为她生命中注入新鲜血液的机会。
从这一点来说,奥康纳小说中男女人物的矛盾便超越了性别的冲突。也就是说,虽然它们描写的是女人的故事,但在她的作品中,女人不只是性别上有异于男性的人,她们是和男人一样自然地存在的人群,奥康纳小说所要反映的是这一组独立的人格在时代变迁中所面临的迷惘、崩溃或新生的命运。
在奥康纳的小说中,女性最后的结局有以下几种。第一,像肖特利太太和麦金太太、老祖母和朱利安妈妈那种,她们成为时代大潮无情冲击下的牺牲品和被淘汰者。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偏见和固执,比如肖特利太太,她从一开始就已注定是“死定了”,因为,从一开始,她就以挑剔、充满敌意的眼光审视和想象着外来的闯入者,她像其他女性一样,深深地陷入无法自拔的主观世界里,而最终死于自己的偏见和虚幻之中;而麦金太太虽然在故事的开始时曾一度欢迎波兰人的到来,可她一旦发现波兰人的民主意识对她的现存世界构成威胁时,她便变成了另一个肖特利太太,所以,她的结局也是死路一条,只不过是一种慢性自杀而已。
相比之下,老祖母和朱利安妈妈在时代变迁的面前则选择了逃避的道路。在《好人难寻》中,老祖母带着她的儿孙去重访她旧时的老宅,正是在回归途中,她与杀人狂“不合时宜”相遇,这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她的悲剧是,直至临死的瞬间,她还在对“不合时宜”说,“你也是我的儿子。”她仍想以母性的温柔来拒绝现代社会的冷酷。与此相似,在《识时务者为俊杰》中,曾经是昔日南方淑女的老祖母在与黑人男人和黑人母子(两人都穿着入时,提着昂贵的皮包,他们已不是往日下贱的奴隶,而是和白人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的人)相遇之后,也是无法承受这种时代的巨变,最终减着“叫外公来接我”,“叫卡罗琳来接我”(卡罗琳是她小时候的奶妈)而死去,在这里,她和老祖母一样,试图逃避到往日的历史之中。
除了这些女性以外,另外两种女性人物的代表是:乔伊的母亲和乔伊。乔伊母亲属于混混沌沌的那一类,她已像老茧一样,被磨得除了几句单调的格言以外毫无思想和个性可言,现实中的变迁已不能触动她那不敏感的特质,她过去是怎样湖涂地活着,以后还将同样地活着,她已成为了一个活化石。如果说奥康纳的小说中对女性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便是乔伊。她是一位现代知识女性,她的偏执使她在故事中成为扭曲的畸人,但与骗子庞特的经历之后,她在震惊之余死一般的沉静中,不得不面对真实。庞特所拿走的不仅是她的假肢,同时也拿走了她一直沉陷其中的虚假自我,乔伊的结局也是奥康纳给女性所指出的唯一出路:必须走出传统上扭曲的自我,不管这一过程多么痛苦,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她们真实的自己,而不至于像朱利安妈妈和老祖母那样永远地消失在时代的脚步中。
这便是奥康纳文本中两个不同的声音,从表面上看,这两者之间是互相矛盾,甚至是互相解构的,因为前者反映了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一片屈从的凹地,后者却凸现了女人的存在,把她们提到和男人同等的地位。在这里,如果男人代表了现代社会,那么,奥康纳的作品向人们揭示了,如果女人继续沿袭其一成不变的老路,她们终将在20世纪社会变迁的大潮中受到毁灭的命运。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奥康纳作品中所写的不是女人的悲剧,而是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呼唤,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回响着50、60年代的女权运动的鼓声,是一种含蓄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