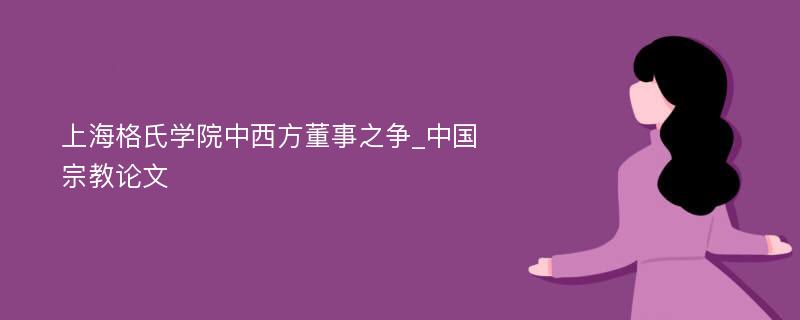
上海格致书院中西董事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上海论文,中西论文,书院论文,董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格致书院(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从1875年建院,到1914年被上海工部局收购,这40年的时间并不算短,而它所发生的作用也没有被历史湮灭。正当晚清上海文化发生变异的时代,格致书院在一定意义上领导了这个潮流,并且被视为“近代新思潮之启发”(注:详见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第五部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但格致书院章程中的三个目标,即:建成陈列西方机器设备的展览馆、开设图书馆和阅览室以及进行科学技术教育实践,都没有真正实现。而创建者传播西学的理想也不是以他们预想的方式实现的。这其中自然有很多原因,就格致书院的管理机构董事会内部而言,中西董事之间长达十余年的拉锯战无疑给它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障碍。晚清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在上海格致书院中西董事之争中有突出表现,因此这个案例十分典型。本文以上海格致书院为场域,以书院管理机构董事会内部中西董事之争(集中在初创的十年左右)为线索,主要关注的并非格致书院所倡导的科学技术以什么方式、如何传播开来,而是西学在传播的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和问题所在,希望借此作为理解晚清上海文化氛围的一个角度。
建院始末和宗教问题
格致书院最初是由西人首先倡议的。1872年《北华捷报》题为《世俗传教士》的文章,受到了驻上海英国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赞赏,他决定筹建一个陈列中文和中译科技书籍的阅览室。它“将最能对中国人的头脑发生影响,使他们了解并熟悉外国人的思想、生活和机械器具,在目前恰恰就是由于他们不了解而在这方面多少产生怀疑。”他认为中国的宫绅也就是所谓的“有所作为的中间阶层”(MIDDLE WELL TO DO CLASSES),在影响公众思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应该对他们进行教育”(注:参考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上海格致书院: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科学的尝试》,原刊《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潘琪译文载《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引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文同。)。1874年3月,麦华陀为传播西学,召集通晓科学的西人商议此事,四位西人即麦华陀、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傅兰雅(John Fryer)、福弼士(F.B.Forbes)被推举为董事,另选华人唐廷枢为中国董事。后又请江海关道翻译委员王荣和(锦堂)为董事,傅兰雅还提议请上海方言馆的副承办员徐寿加入董事会。
创建之初,关键是资金问题,由西华董事各向其国绅士募捐。当西商捐银980两已经到位时,华人捐银仍没有明确的数目。董事们讨论的结果:一是向英国征求各种机械仪器的捐助,二是希望得到中国政府官员的支持。结果,徐寿分别上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李宗羲的禀陈都得到了积极回应。徐寿之子徐建寅出精通科技,并从中多方努力,也被聘为董事。至此,董事会的最初创建人已经基本确定,西方四名,中方四名。所得资金超过了预期,建院有了基本的保证。西方的机器制造行也承诺提供各种器具及模型。于是房舍的问题提上日程。同时由傅兰雅重新拟订书院章程以广而告之,伟烈亚力开列了种种科学书目准备购买。此后,为了扩大影响,又增加了几位华籍董事和八位在英赞助董事。
随着社会支持的拓展,书院的建设也比预期规模扩大。恰好英国科学博物馆为扩建新馆,放弃了旧有设备。麦华陀听到这个消息后积极争取,终于得到这批机器,嗣书院建成后全部陈列于此。房屋地基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折,最后落定在跑马场附近的英租界。建筑样式悉用中式,由徐寿亲自绘制设计。在兴建院舍的过程中,英国方面积极配置了各种科学仪器机械,计有十大类,如生长之物、工艺之物、化纤饰物、建筑器材、机器工具、工程之物、照像绘画、枪炮弹药等等,因而需要专门的博物馆陈放。中国士绅则纷纷出资,绝大多数建设的费用是由他们捐助的。据《万国公报》所列捐款名单,一百两以上的捐助者,西方只有祥和洋行三百多两和英国公使一百两。个人捐款少之又少,华人则个人捐款非常踊跃。而在全部7700余两的建院款项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由徐寿募集而来。徐寿不仅为书院募集了足够的建设资金,而且在开院之初英国设备未到位时,把自己的科学仪器和设备贡献出来。可以说,在建院过程中,西人提倡之功实不可没,而华人鼎力支持助成其事也是有目共睹,真正可谓中西互补、相辅相成。
即使在中西董事戮力同心创建之初,矛盾也明显存在着。1874年3月24日的成立会议上,关于是否可以放置一些各个宗教社团出版的宗教刊物一事,董事之间发生了争论。华董自然反对此举,西董中传教士代表和非传教士代表之间也出现分歧。最后决定除《圣经》外,其他宗教书籍要经董事会讨论同意后才能放置。大部分人还是担心宗教读物会使书院带上宗教色彩,而把对西方文明感兴趣而对西方宗教有抵触情绪的中国人吓跑。事实证明,董事会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宗教问题无疑是中国董事和中国人最敏感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威胁到书院的成败。不久之后,在徐寿给李鸿章的禀文中,再次强调了书院与宗教无关,“其中存储诸件,惟是推算制造等项书籍及各种机器式样,与设立教堂,情形迥别”(注:徐寿《拟举办格致书院上李伯相禀》,《申报》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三日(1874年11月11日)。)。就在书院建成之前,为收购已故的原北京同文馆天文教习方根拔(J.von Cumpach)的藏书,徐寿与董事会主席麦华陀及伟烈亚力等发生激烈矛盾,他坚决反对收藏其中一些包括宗教在内而与科学技术无关的书籍,并因此遭到《北华捷报》的嘲讽。作为华董,徐寿代表着支持他的中国官商绅士,也就是麦华陀期待的“有作为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他必须坚持格致书院的独立性,才可能不被指责并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
财政危机与人事问题
格致书院建院共花去了8000多两银子,超过了募集到的资金,加上增添其他设备和维持日常杂物等所耗经费,很快就使它背上了一个不算轻松的财政债务。似乎是不言而喻,书院的财政问题就该由徐寿去解决。但是,继续募集的办法已经不能奏效并最终解决问题了。原董事麦华陀和伟烈亚力因故离开中国,继任的董事对经营书院的艰辛并不体谅,一心希望徐寿继续募集以维持书院。而这时恰逢山西、河南等地出现严重旱灾,赈灾一事牵动民心,国内上下艰难,难以给予书院更多的支持。中西董事之间被书院的进展掩盖的矛盾,也在书院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时凸现出来。
英文《北华捷报》代表英国传教士和绅商的利益,他们一直关注着格致书院的成长,但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对书院加以苛责。该报曾把格致书院的惨淡经营归于几个原因:
1、中国董事缺乏真正的热情;
2、由于董事会请求英国方面协助书院完成其目标的做法,引起了地方上对书院的反感;
3、地方上对李鸿章在书院的影响力不满,认为“李鸿章通过徐寿父子控制格致书院”(注:《北华捷报》1877年3月15日,徐星译,《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第232页。)。
如上所述,财务问题和现实局势是格致书院在经营初期出现严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事实上,《北华捷报》这种“自由”言论只能进一步激化董事会内部的矛盾,董事会的人事变动和中西董事之间的矛盾在这样偏颇的舆论导向下,更增加了各项事业进展的艰难。毕乃德教授对此也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的说法中后两者都是无稽之谈。对于华董的工作态度,毕乃德教授颇有批评。虽然华董确实常有缺席的情况出现,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国董事的热情。这可以从最初的捐款和徐寿及其亲友在此中的费心劳神窥见一斑。
书院要维持下去,迫在眉睫的仍然是财政问题。徐寿终于从红顶商人胡雪岩处筹到银元5000 (约合3600两银子),加上自己的1000两银,才使书院从债务中走出。1878年,徐寿在书院空地上又建成几间平房,成为一笔固定资金来源,这样才逐渐度过了财政危机。1878年6月,为了解决“由于中外簿记制度和其他原因引起的误会”,董事会同意徐寿担任司库。由于他的特殊贡献,到1884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书院的日常经费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徐寿利用书院的空地盖房出租虽使资金状况获得一定缓解,但他想出售闲置地皮以进一步解决问题,却未获得西董的支持。经过周折,西董作出让步,才使书院有了固定收入来源,最终摆脱了债务危机。由于徐寿对书院的重大意义,西董虽然对他的主张不满意,却无法代替他主持书院事务。特别当傅兰雅离开上海的时候,书院的管理几平全部由徐寿负责。徐寿请著名科学家华蘅芳担任书院山长,照料书院的日常事务,并且不取任何报酬。他的儿子徐建寅和徐祝三也在为书院的事四处奔波。即使如此,一些西董仍然认为这是徐寿在任用私人。
傅兰雅在徐寿与西董之间的矛盾中处境十分尴尬。作为徐寿多年的合作者和朋友,并且同是科技教育的倡导者,他深知徐寿在格致书院中的价值和意义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西董的不满虽然可以理解,也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不可助长其势。所以,当他1879年回到中国,《北华捷报》正在肆意批评格致书院毫无用处的时候,傅兰雅就致信该报编辑,予以澄清:“格致书院绝非毫不起作用,而是一直在缓慢而脚踏实地往前迈进着。资金在逐渐聚集,陈列用的科学仪器正从英国运来,一位有相当造诣的中国先生住在书院内照料,书院在每日从早到晚对外开放,这位先生向来访者讲解仪器的用途,或者,对他们在阅读书院藏书楼中的科学书籍时所遇到的疑难问题给予解释。是的,来院者目前还不多,但正在逐日增加。书院正筹备在春节之后开办学习班和讲座。这项计划并将以显著的形式向公众宣布。……尽管至今未能有幸得到你们的青睐,但却得到了大清帝国一些最高级官员的认可和支持。我们应当记住,凡是外国人能够给以教益之处,博识而多智的中国人自能善于洞察;但是,他们不愿俯受恩惠,也不愿有人强迫他们从命。他们愿意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办理自己的事。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急于求成。也许,还要再过几年,格致书院才能臻于成熟,或者能对大清帝国有较大的实际作用。”(注:《北华捷报》1879年10月17日,《中国的格致书院——傅兰雅1879年10月14日致〈北华捷报〉编辑部的信》。此处采用徐星译文,《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第235-236页。)
由于财政危机和人事问题导致的中西董事之间的矛盾,以傅兰雅对格致书院工作的客观评价和公正肯定,对外界进行了解释和掩饰。面对傅兰雅这种客观的态度,《北华捷报》也不得不承认,“上海在努力传播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方面仍然走在前列”(注:《北华捷报》1879年10月17日,《中国的格致书院——傅兰雅1879年10月14日致〈北华捷报〉编辑部的信》。此处采用徐星译文,《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第235-236页。)。这一个阶段以徐寿父子及华蘅芳等为代表的中国董事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得到了肯定和认同,他们对书院的管理坚持到1884年徐寿去世。
中西董事矛盾激化与“中国观念”
徐寿的去世使中西董事之间长期压抑的危机浮出水面。傅兰雅的态度也从默许徐寿等华董,转而支持西董。在徐去世之初,司库由徐华封和徐建寅负责,傅兰雅还提议徐建寅修订书院章程,以便于书院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带头对徐氏父子及此前的工作提出批评,并和西董一起通过了继麦华陀后任董事会主席的律师担文(W.V.Drummond)修改的书院章程,完全废弃了徐建寅的修订稿。1895年7月15日以前,董事会议几乎全部是西董自演自唱,徐建寅曾联合中方董事拒绝参加,但最后也不得不交出管理权和财政权,西董终于控制了整个书院。
傅兰雅《格致书院第四次报告书》(1883年3月到1885年3月)不仅否定了董事会此前的工作,也否定了他自己此前的看法:“书院成立之初的想法是,中外人士应联合兴办此院,随着其良好的开始,书院应逐步移交给本地人领导和管理。然而,实际情况相反,书院尚未立稳,中国的影响就任意扩大。……人们记得,麦华陀爵士得到上海外侨的协助,倡办了这个项目。在其居住上海期间,不言而喻,他稳操书院的大权,尽管十分之九以上的捐款来自中国人。由于老徐先生及其次子的大力募捐,中国人的全部捐款均来自大清帝国各地的高级官员。徐先生和他的次子被邀加入董事会。他承办了书院楼房的建造。渐渐地,他们将自己与书院划上了等号:中国人就是书院。”(注:这次报告书及格致书院其他的情况,《北华捷报》1885年已刊印。中译文见《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一书第247-249页,译者石继成。)很明显,他把矛头指向了徐氏父子,希望趁机把财政大权和人事大权夺回。傅兰雅指出,此前书院存在两个重大问题:一是财政危机及其解决;一是书院的看管。财政上,徐寿的成绩和手段自然有目共睹。在书院看管的问题上,最初唐廷枢按董事会的要求用薪水请来的广东山长很快就离任了,随后由徐寿提出华蘅芳负责一切事务。通过这两点,“老徐先生几乎掌握和领导了一切事务”。西董对徐寿个人把持书院的管理这种情况的不满由来已久,并且是董事会内部矛盾的集中反映。
除了对徐寿个人的专制不满之外,令西董不满意的还有他所代表的中国观念和中国习气。“他就其所能,立即着手,并按中国观念,领导书院。”西董所批评的“中国观念”其实是很含糊的,基本上,仍然集中在徐寿所代表的专制主义倾向上。其所举主要例子就是广东山长的离任,对此,傅兰雅说,“他想办的事均受到司阍反对而无法随愿。反对他的还有一些未经董事会同意、也未为董事会所知而擅自居住在院内的人士。”这种说法应该是有所依据的。一位曾住在格致书院的人,就见到来格致书院游览的“大半俱雅士文人”(注:一介微生《谈时务》,《格致汇编》第二年第十卷,1877年11月。),这些人谈锋很盛。另外,按照书院早期规定,积极捐款的士绅以及慕名前来的华人,也允许对书院事务发表言论。这种议论之风和西人所主张的民主,表面上似乎很像,因此,最初也得以在中西之间达成一致。但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魏晋清谈之风的延续,在中国名士中深有传统。既然格致书院为在上海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议论的场所,那些喜欢讥评、素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习气的才子名士自然可以在此畅所欲言。可以想见,这其中对书院事务的发言,对书院“主人”徐寿可能会客气一些,而对其他人自然会有不少批评和指摘。这种批评的声音中有开明的,一定也有保守的。
但这些聚集在格致书院中的知识分子的“众声喧哗”,仍然不能等同于专制。傅兰雅的意思是说,这些声音代表的,仍然是徐寿及其群体的态度和观念,与其相悖的言行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这只能说是舆论力量对比的客观结果。这种态度和观念确实是中国观念,代表的也确实是中国华人的利益。但不能因此就赋予它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制色彩。而徐寿自身的强制手腕也不能完全说是专制的个人独断,他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通过董事会一致同意的。而且,对于书院的维持来说,他的决策基本上客观可行,而不像西董所说的那样为了私人的利益。傅兰雅声称,由于徐氏家族和亲友的把持,“书院原有的公众性质和教育性质,无论从中国和外国人士的角度来看,不是全部也几乎丧失殆尽”。虽然,格致书院在这十年间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成绩,但这不应该完全归罪于徐氏家族。
书院刚刚建起,就遇到了北方罕见的自然灾害,书院的各项事务都被搁置了。此后,陈列仪器设备的展览厅即玻璃铁屋博物馆,由于资金短缺胎死腹中,而西方答应的机器也始终没有运到。阅览室里的图书筹备缓慢,迟迟未能充实起来。至于格致教育的问题,徐寿和西董之间未能达成共识,也被耽误了许久,并且难以造成一定的社会效应。而关键问题在于,除了最初在新奇的驱动下前来观阅的人们外,书院的常住人口和来往的客流量少得可怜。这在客观上与时代大环境有关。由于当时中国的科技教育状况极其落后,在上海的知识者对格致教育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认识。这个时候,推行格致教育是有很大难度的。
正如麦华陀预料的那样,西方科技文明所要传播的对象,是“有所作为的中产阶级”。因为输入西方文明这项工作不是西人能够独立完成的,而且事实上,已经接触到西方文明并经世致用的知识者,在外来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显然并未因此就完全脱离传统文明。西董对此也有一定的认识,“他们愿意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办理自己的事”。这些近于洋务派的开明知识者,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主张学习西方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以图本民族能自立于世界诸民族之林。从对本土文化的自我保护本能看,他们对“老大帝国”积淀下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崇拜,使他们格外警惕西方思想和观念以及各种不必要的东西的侵蚀。接纳西方的科学知识,对他们来说是为了自强求富,一切行动都以此为标准和限度。所以,在有选择地吸收的过程中,他们希望以最微小的代价和最有效的方式,把西方科技吸纳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熔炉中。这就是以徐寿为代表的开明知识分子所抱有的“中国观念”和中国方式及其背后的深层心理。他们这种痛苦的选择和挣扎,应该得到充分的理解。
西方人的态度却更值得深思。傅兰雅不经意间提到,“书院的外方利益已降低到最低点”,恰恰可见西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还是很明显,并且很强烈。在此之前,西人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和身份。麦华陀最初拟订的章程最为隐蔽:第七条有“此院均系中国士商所用,西人不在其列”;第九条有“中国各种经史子集,听凭各董议增列入院内”;在第八条关于书院的管理中称,“经理书院各务,须立董事,少则五人,多则七人,首先一年,可邀出捐西人一二位帮办”。由此看来,书院的事情就应该是中国人的事情,管理书院也应由中国人自己负责。那么,西董为什么却一直对徐寿主持书院事务耿耿于怀呢?事实上,在成立之初,西方人一直控制着书院。直到徐寿以自己的才干争取到管理权,西董就开始不停地为此事头痛,铁腕人物徐寿的死使他们吐露了心声。
很明显,西人最初的设想是希望通过传播西方的科技文明等西方文化,以便于西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人所了解并接受。如果仅仅出于这个目的,他们以上那些低调的声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始至终,他们没有明确书院的属性,这是他们的聪明之处。西人的利益显然是建立这所书院最重要和最终极的因素。如果能够按照他们的旨意来管理书院的事务,他们或许可以让中国人去做。但是,那是不可能的。西人既然把中国知识者作为影响的主要对象,就不应该忽略其文化背景。既然他们需要中国知识者在财力和人力等各方面的支持,就无法不顾忌中国人的力量。从传播西方文明的角度看,他们与传教士有共性,无论是出于对西方文明的虔敬之情,还是出于一种改造别人的欲望,他们都有一种强制别人服从、归顺、隶属的性质。其功利性和目的性只能掩饰到一定程度。以徐寿为首的华董的本土文化观念和抵触西方文明的情绪对他们是很大的刺激,尤其是当徐寿表现出突出的领袖气质和影响力的时候,西人的抱怨、恐惧、愤怒、拒斥、抵制等一系列的行为都透露了他们的本质。对徐寿和所谓“中国观念”的清算,使西方人一反过去的仁慈和友善,违背了他们的民主文明作风和客观理性态度,反而更加专制霸道。所谓的“中国观念”和中国方式,并不是很可笑或可鄙的,而应该去深入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西董表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科技教育与科技问题
毫无疑问,西方人发起格致书院的初衷是向中国人展示西方文明,强调“使中国人熟知中国的文学,科学和进步”。傅兰雅等致力于传播西方文明的人又赋予它中国人学习科学知识的引导者的意义。1876年6月22日,格致书院开院那天,发起人麦华陀说:“我的朋友傅兰雅先生,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所有已经获得的成就都应该归功于他,是他建议,我们将要兴办的不仅仅是一个阅览室,应该努力办成一所工业技术学校。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特别是徐寿先生的热烈响应。”(注:格致书院开幕时麦华陀的发言,见《北华捷报》1876年6月24日。译文转引自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第7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早在徐寿和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共事,翻译科学书籍时,他们就有推行科技教育的设想。由于没有当政者的支持和其他种种原因,此议未能实现。正如麦华陀所说,这两位对格致书院影响最大的人物,其最大贡献在于提倡科技教育。
格致书院两个主要董事对科技教育的提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未能实行。在书院开放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不成系统的讲演和讲座,徐寿和山长以及一些董事、热心人都曾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者,如狄考文(C.W.Mateer)1878年夏曾来讲解电学原理。但在财政危机稍有好转的时候,徐寿一直把大量的资金用于购买科学仪器,这一点令包括傅兰雅在内的西董都很不满。1878年初,担文继任董事会主席时,也反对徐寿把大量经费用于购买科学仪器,而主张用这些经费聘请欧洲的教员来进行科学教育。直到1879年,书院真正从财政危机中走出后,徐寿才开始尝试招生。招生公告分别刊登在《万国公报》和《申报》上。“本书院创设沪上,专为招致生徒究心实学,其提倡者半为中西积学之士。……一为学西国语言文字……一为讲求格致实学者……。”(注:见《申报》光绪五年九月十八日(1879年11月1日)。)。但其不菲的学费和押金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加上风气未开,招生的结果并不理想。收费的方法多半是出于书院经费短缺的考虑,而招生公告中所表达的“专为究心实学”的理想,却显然被时人对西方语言的需求冲淡了。实际上,从1880年开始的授课实践,由于没有固定的教师和工资,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影响。
徐寿虽然提倡科技教育,却对聘请欧洲教员一直不感兴趣。因为他是董事会中真正的科技专业人才,他特别热衷于购买仪器,以供研究和讲学之需。至于科技教育,或许他认为自己和他的畴人朋友可以胜任教职,或者受上面所提到的“中国观念”的影响,反而不信任西方教员,更不肯花钱请西人来教课。是否从西方请洋教员来教授科技知识,构成了徐寿与西董之间明显的对立,这个矛盾一直延续到徐寿去世。1885年,董事会为增进学务,又专门聘请通贯中西学的王韬担任山长,主持书院教学和日常事务。虽然王韬很热心讲授新知,他的社会声望也吸引了不少人,但仍然无法进行科技教育。于是,傅兰雅和王韬等商议,变通中国传统的课士方法,照中国传统书院之例,在格致书院设立四季考课,成绩优秀者给予奖金,以此引导中国知识者逐渐关注科学技术问题。这个办法主要由王韬具体实施,到其逝世为止,一共推行了十年左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和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传统的中国课士方式,实现了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引导中国士人的格致精神。
在格致书院课艺中,科学方面的试题仅有三分之一左右。傅兰雅一直对此耿耿于怀。1895年,傅兰雅开始在书院讲授算学。《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序》云:“嘉言谠论多发明洋务西学,此格致学为之一振。然此扰属纸上空谈,未必竟有实际。欲兴西学,犹未可于此已也。”1896年,在经费仍然不足的情况下,他自己拟订了西学教材,改用夜课的办法亲自授课。这次招生三、四十人,对他是很大的鼓舞。他的《格致书院西学章程》对所开矿务、电务、测绘、工程都有很详细的课程安排,另外,还准备讲解汽机和制造等。而《格致书院课艺》中,这些学科的问题也都曾出现过,可见,课艺的办法和科技教育的理想大致还是一致的。
西董传播西方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初衷始终未变,但华董在中西科学之间就不免有所摆动了。正如徐寿《拟举办格致书院上李伯相禀》表明的那样,“窃维格致之学,大之可齐治平,小之可通艺术,是诚尽人所宜求,今日所当急务。”虽然他代表了比较开明的知识者的意见,但显然已经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中国传统社会对外来事物的接受程度是有限的,了解中国官僚和绅士阶层的傅兰雅对此很明白,“他们不愿俯受恩惠,也不愿有人强迫他们从命”。对于外来的事物是否接受,他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判断。像徐寿这样领略到西方科技先进之处的知识者,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风气之先,获得经世致用之效,也就是通过“艺术”达到“治平”。从接受的角度讲,中国人期待的是能直接作用于中国的富强之策,而非西方的科学技术本身。因此他们也有强烈的功利性,那就是改造中国的现实是第一重要的,格致只是一个途径,而不是目的。在课艺的命题中虽然有不少西学内容,而大量的讨论仍集中在时事洋务。
中西格致观的不同和对科学精神的不同理解显然是格致书院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讨论在晚清中国存在了很长时间。早在1876年,《申报》就在论《格致汇编》一文中指出:“格致之学,中西儒士皆以之为治平之本,但名虽同而实则异也。盖中国仅言其理,而西国兼究其法也。”(注:《书格致汇编后》,《申报》光绪二年正月三十日(1876年2月24日)。)传统的格致观在西方科技传播中充当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沟通西方科技的桥梁,另一方面它又是阻挡西方科技的栅栏。在以西学为主的课艺中,命题人提出的问题有不少是出自或联系传统的格致学问。如在天文历算方面,李鸿章出的题目是《杨子云难盖天八事以通魂天说》、《以月离测经度解》,地学方面的题目是《〈管子·地学篇〉解》。命题人大多是占据要职、体现中国文化之精深的人物,他们虽然倡言科技,可多半还是滞留在格致的范围内。而答题人也借助格致学问在中国士人之间获得的一种认同感,不仅使他们能够倡言科学技术,而且更能被当道者所理解和赏识。但是,从传统的格致到西方的科学,中国的士人有段很长的路要走,除了专门的科技才人之外,近代知识者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还远远不够。中国的格致观已经形成轻视科学的传统,传统的格物致知本是儒家的观念,而儒家关心的是人世而非事物,并没有给科学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这种重本轻末的传统,使大多数的官僚知识阶层热衷于事理而不是物理。在这种情况下,傅兰雅也不得不变通,转而以中国的文字为桥梁,试图在传统的格致和西方科学之间进行沟通。“欲与海内人士结文字缘,由文字引伸之,俾进于格致”。(注:《格致书院课艺》丙戌卷,光绪十三年王韬序。)无疑,西方科技传播的对象,首先还是这些熟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他们擅长著文论史,以文字而不是严肃的课堂授受为途径来进行文化交流,显然更易于被他们接受。所以,传统格致观与西方科学观的差异,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教学方式的差异,这两个方面都是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不可回避的问题。
结论
毕乃德教授在《上海格致书院: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科学的尝试》一文中评价道:“与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同类学校相比,或者从它的缔造者原来的雄心勃勃的初衷来看,上海格致书院及其阅览室的成就给人印象不深,但考虑到中国原来在科技教育方面的落后,和19世纪末充斥全国的中国知识分子阶级的自我满足情绪,格致书院的这些成就就相当令人瞩目了。”(注:毕乃德《上海格致书院: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尝试》一文结论,见《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第463页。)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上海格致书院的不成功与中国科技教育方面的落后,和19世纪末中国知识阶级的自我满足情绪有关。“科技教育的落后”显然是一个事实,并且在文化上与传统中国的格致观对科学的不重视相关。而“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满足情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成立,但他对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如果完全如他所说,又如何会有1898年的戊戌维新和此后的新文化运动呢?中国知识阶层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文化保护意识是一种自然的文化屏障。进一步说,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冲突并不能完全归罪为中国的愚昧与落后。在本文所提及的宗教问题、人事问题以及对“中国观念”的定义上,西方显然有强制和霸权的倾向。毕乃德教授忽视这一点所下的结论,也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即使从西方中心的角度看,忽视这些问题,也不利于西人实现其在华传播科技的目的,更不能真正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上文所提及的四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影响格致书院发展的重要障碍,也就是解答格致书院的理想之所以未能实现的四个原因。但这些问题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却不尽相同,须分而论之。宗教问题和科技问题是中西文化接触早期,在交流的过程中最前线最直观的问题,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可回避的事实。特别是科技问题,在格致书院中所隐藏的问题与洋务运动不同,是其中很具体也深刻的一面。实际上,正是在中国观念革新的维新时代和新文化运动时期,采取以西方科学观等西方文化对抗传统文化的策略,并且与教育制度的改革一道,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接受才真正得以实现。而本文特别强调了上海格致书院的财政危机和人事问题等具体事宜,及其背后的“中国观念”这一现象,就是因为它是中西文化差异在中西董事矛盾纠葛中的集中反映。通过对上海格致书院早期历史的回顾以及中西董事的矛盾论争,可以了解到西方文化在上海遭遇的波折。而上海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当时尚走在前列,格致书院在传播西方科学方面也是领头羊。中西文化的强烈冲突在此可见一斑,而如何以客观的态度理解它是更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