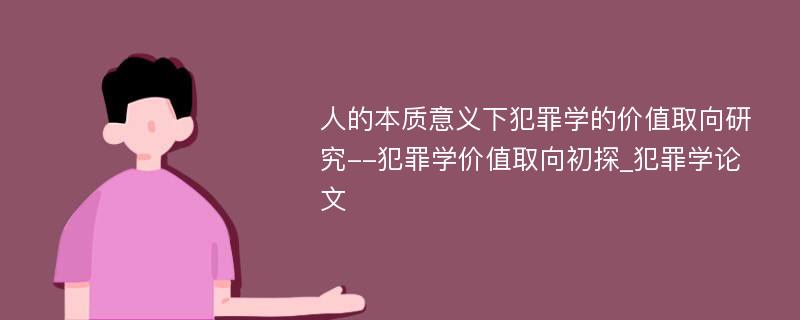
关注人本质意义上的犯罪学价值取向研究——犯罪学价值取向有无与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取向论文,犯罪学论文,人本论文,有无论文,意义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33(2009)03-0010-06
一、“有”或“无”——关于犯罪学价值取向存在与否的问题
(一)由“价值涉入”、“价值无涉”、“价值中立”引起的争论
犯罪学的价值原则一直是犯罪学界探讨较少的话题,直到有学者对我国犯罪学研究中一贯坚持的“价值涉入”原则进行批判,并且主张“价值无涉”原则,对于犯罪学本体论中的价值取向问题才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
以犯罪学研究中研究主体的价值观是否介入犯罪学研究过程为标准,可将犯罪学研究中的价值原则分为“价值涉入”与“价值无涉”两种。所谓“价值涉入”亦即以研究者主体的价值观先入为主地影响研究过程,形成在思维方式上被情感因素左右,支配科学逻辑,占据立论、推论、判断的主导地位[1]。主张“价值无涉”原则的学者批判“价值涉入”原则在认识论上的诸种弊端:1.以情感好恶为界,急于实现对犯罪现象的“严刑峻法”、“斩尽杀绝”。2.欲将罪犯定性为在心理过程和行为方式上完全不同于常人的人,以致对罪犯,甚至对青少年动辄冠以“极端利己主义”、“极端仇视社会”,表现出结论上的绝对化、非科学化。3.对犯罪心理,甚至包括犯罪人的正常需要层次给予近乎荒唐的标定,断言犯罪人的需要是“畸形的”、“强烈的”(实质上人的需要层心理动力源并无“畸形”可言,同样也无法一般性地判定罪犯的需要比常人更强烈。道德标定只能限于对犯罪人的认识范畴和外显性社会行为)等等[2]。继而认为这种认识论导致了在实际研究犯罪过程中产生了诸种不良的后果。
所谓“价值无涉”是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把自身的价值观和道德倾向排除在外,从而不至于戴上“有色眼镜”去认识客体,以保持对客体认识的客观性需要[3]。很显然,“价值无涉”原则与“价值涉入”原则存在认识上的根本差别。前者主张在犯罪学研究过程中,完全排除主体的价值观与道德倾向或者说是价值观与情感逻辑,保持对于研究对象——犯罪现象的完全物化的态度,坚持主体的中立性。后者则力主在犯罪学研究中的价值观和情感逻辑因素,以有感情的人的立场去研究犯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主张“价值无涉”的学者却并非要在犯罪学研究的全过程中贯彻该原则,也认为该原则并不是一种主导原则;在研究者确定工作方针,选择研究课题和扩展社会效益的过程中,必然要具备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的价值观和道德倾向,并以此来指导研究工作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在作出研究结论之后,即在实际开展研究工作之时,研究者应完全避免主体价值评价的先入为主,并以此形成研究者的主观差异性。也许恰恰是这种主观差异性才促成了研究成果的多样化,同时提醒研究者防止“价值涉入”的滥用,警惕其所蕴藏的危险性。
(二)对“价值无涉”、“价值涉入”的评述
讨论犯罪学研究中的“价值无涉”、“价值涉入”等原则,就无法回避对其渊源的考察。对于社会学研究中价值问题的探讨,在西方社会学界早已有过激烈的交锋。孔德之后,在西方社会学中主张“价值中立”的观点逐渐强化,终于成为社会学的主流。迪尔凯姆主张科学理论的价值只在于能说明或解释社会组织,而不在于改造社会;V·帕累托提醒社会学者不要因为个人的宗教、道德、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感情,不去报道“是什么”,而去报道“应当是什么”[4]。马克思·韦伯在肯定了研究者主张地位和主观差异的同时,又提出了“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原则。即强调了在对客体进行实际观察时,研究者的主观干预不应当发生在客体自身显示的过程和倾向中,也就是要求研究主体必须使自己客体化,成为相对于客体的另一个客体,这是为了防止主体以自己的主观意愿画线,决定资料和论据的取舍,把自己的价值评价直接转移到研究客体之上。马克思·韦伯一方面把“价值中立”视为社会科学的规范性原则,另一方面,又把“价值参照”当作社会科学的构成性原则,以避免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在社会认识上的片面性。马克思·韦伯对此的认识不免带有很大的含混性,引起长时间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犯罪学就对“价值中立”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一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西方犯罪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犯罪观加以批判。认为法律并不是公众合意的体现,而是掌握权力的立法者带有阶级偏见的产物。在这样的社会体制里,对于没有权力的常人来说,司法从来就是不平等的。他们嘲笑主流犯罪学家们所采取的“价值中立”立场,认为犯罪学应当有意识形态的基础,必须剥去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伪善外衣,揭露其真实的本质和目的。
探讨“价值无涉”、“价值中立”、“价值涉入”的问题显然不能局限在问题的本身。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价值中立本身就有理解上的矛盾性。他一方面主张犯罪学研究中的事实描述阶段要摒弃价值观的影响,一方面在理解人赋予行为的主观性时又不得不承认必须借助价值关系。因此,对比“价值中立”原则与“价值无涉”原则就可以发现,二者有共同之处。即后者同样认为“价值无涉”原则并不是贯穿在研究过程中的一种主导原则。事实上,主张犯罪学研究过程中的“价值无涉”原则,并非完全抛开价值的影响因素,而是主张有节制地使用。在主张“价值无涉”原则的学者眼中,该原则成为可以由学者的意志任意操控的皮偶,需要时则在犯罪学研究中导入,不需要时则把该原则抛弃。这样的做法貌似合理,却同样存在着诸多的问题:1.研究者如何判断?何时应当导入该原则?何时应当导出该原则?2.在研究资料的过程中,对于资料的取舍、选用就不需要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吗?3.如果某项被称为原则的东西不能贯穿在其所依存的事物的始终,那么它还能被称为原则吗?
除此之外,在探讨这个问题时,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理解“价值无涉”、“价值涉入”、“价值中立”之中的价值概念。在主张“价值无涉”原则的学者那里,价值被赋予了似乎与情感、道德相当的意义。而在通常的理解中,价值的概念是在与人类相关的某种终极意义上的东西上使用的,如人权、正义等等。因此即使该原则存在合理之处,似乎使用“情感无涉”在理解上更能为人所接受一些。我们并不否认该原则在保证研究结果反映事物本来面目中的作用。我们要质疑的是,该原则是否可以被提到犯罪学研究的过程之中。诚然,我国的犯罪学研究从建立伊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偏见,但是这种状况的发生是由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所决定的。犯罪学者无法跳出历史而独立存在,犯罪学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这种特征的转换并非通过某一项原则的确立就可得以实现,它更要借助于时代的进步。这样的原则与其作为一种原则在犯罪学研究中进行提倡,不如作为对研究者本人提出的一种要求。在诚实、正直的研究者那里显然没有提倡这种原则的必要。反之,它能否被遵守却未为可知,因为相对于法律而言,它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主张“价值无涉”的学者大多强调该原则在消除主观差异性上的作用。似乎统一的思想认识更加符合犯罪学研究的利益。但事实是,由于人的知识背景、境地的不同,主观上就必然存在着差异;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理论上的和谐统一并不有利于学科的发展;相反,理论上的争锋更能促进理论的进步。他们还主张主客体之间的置换,认为该种置换可以保证研究结果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真实。“是否可以认为价值中立就是实事求是地反映研究客体的特征。试作一回顾,过去那些在犯罪学界产生过持续影响的理论观点,大都是在探求犯罪客观特征阶段坚持了‘价值无涉’原则才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5]为了通过移情来理解行动者的行为,观察者就必然大致处于与行动者相同的标准和道德状况。假如他们观点歧异,信仰互不相容,那么移情的联系就不能充分实现[6]。犯罪学是一门研究人性恶性的发生机制的学科,要求研究者对人类的思想、行为和恶性作出贴切入理的分析。但许多研究者始终不愿也不敢变换一下自己的角度,不愿除去有色镜做个客观的观察者,而始终是远远地站在客体的对立面去观察和评论。这在犯罪学研究中似乎成为一种禁忌,似乎越过这一禁忌就会出现立场的问题,就会变得同犯罪人一样“龌龊”。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科学研究,不如说是在捍卫道德。但是就最通常的理解而言,我们用我们的知识足可以理解另一种事物,就如同我们要理解杀人犯的杀人动机,并没有必要亲自去杀人一样。事实上,无论是古典学派还是实证学派,都没有这样做过,但是其理论仍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综上所述,在犯罪学研究中是否引入价值观念因素,已经不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不论承认与否,它都存在于研究的过程中。但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并非就此打住,它提醒我们,在犯罪学研究中学者们忽视了对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面从更深层次上影响着对于犯罪的看法;对于犯罪学研究的结果而言,也并非仅仅具有使结果保持客观性的意义。无论是马克思·韦伯还是主张“价值无涉”原则的学者都没有把“价值无涉”或者“价值中立”中的价值概念进行深入的分析,而是简单地将价值的概念与情感与道德并列。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借助于历史的、经验的、理性的分析,就会发现我们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反映它的内涵,也无法用详细的列举的方式穷尽它的外延。因为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对于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发展,但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它又确实具有确定的含义;它更倾向于一种层面,在这种层面中存在着诸种可供选择的因素,这些因素反映着人类发展某一阶段对于自身的认识发展成就;这些因素彼此相互制约,哪种因素更占优位,已经为在先的条件所决定。但是,意志却可以对其进行调整,如果这种调整符合时代的要求,那么就会更有可能被时代所接受。
(三)不可避免的价值取向选择
“犯罪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说犯罪这种社会现象,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着,而且一直都为人们所关注,因此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遥远古代没有建立起研究犯罪的学科,但是散见于中外典籍中的犯罪方面的论述并不少见,许多历史人物对犯罪问题有精辟的论述。说它年轻是说,在国外真正就犯罪学的名称及其学科独立时间来讲,只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我国也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尤其是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学体系,可以说还只是刚刚建立,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7]如上所言,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犯罪学进行了界定,并且限定犯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如果对比国外学者对于犯罪的看法,不难发现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犯罪学研究中所产生的影响。仅以对犯罪产生的时间为例,西方犯罪学一般认为,犯罪自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人类,只要人类存在,犯罪就不可避免。而马克思主义犯罪学则把犯罪视为阶级社会所独有的社会现象,那么能把某种行为称为犯罪的年代就要大大推迟。在坚持这种观点的前提下,即使抛开阶级意识因素,某些看似与今天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没有两样甚至还要野蛮、暴力的行为也不被视为犯罪;而且认为犯罪会随着私有制度的消灭和公有制度的建立而消失,那也就意味着犯罪只是人类历史上某一阶段的特有产物而不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始终。从中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对于犯罪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仅仅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产生两种不可调和的观点。
如果有人认为在研究犯罪时可以不具有一定的价值前提或者可以抛开一切价值因素,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可以把犯罪视为一种纯粹的“现象”吗?因为它是恶的,所以需要被控制,所以才去控制。这就已经有了价值判断,更不要说又与人类社会扯上了联系,沾上了人类社会的属性。从一只脚踏入犯罪学研究领域的那一刻起,就必然会对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有这样、那样的评价,继而是对某种目标的设定。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会事先对犯罪作出否定评价,然后再基于预防或控制的目的去探索犯罪的成因以及对于犯罪的防控手段。把人类对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的思想与历史时代背景稍加比较,就会发现时代决定的价值取向是如何作用于学者的思想,从而影响学者对于犯罪的基本观点的。这种价值取向是某一时代的人类社会所共有的价值特征。因此,尽管个人会在具体价值冲突上有所不同,但是由于这种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对于价值取向的预先决定性,也就决定了研究者对于犯罪学研究所采用的价值取向。即使学者有意识地要摆脱这个影响,那也可能只是走到了时代的对立面或者在二者之间进行调和。因此,只要仍然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就不可能,事实上,也不可能摆脱这种束缚。即使在研究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犯罪现象,在潜意识中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所处时代的价值观点去评价某种社会现象,即使在主张移情和角色置换的学者那里,也不可能例外。
二、犯罪学与受限意志下的价值取向
人们对于预防犯罪的渴求,催生了犯罪学,因而预防犯罪就被顺理成章地视为犯罪学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正如学者所言:“犯罪学的出现,将人类对于犯罪学的关注提前到犯罪之前。力争预防犯罪,是刑事科学领域中的一大飞跃,犯罪学的基本价值在于此。”[8]这种论断回答了犯罪学是满足了或者说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出现的问题。但如果单独从这一角度考虑,那么为了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当然这是在犯罪学把预防犯罪作为毫无羁绊的价值目标的情况下,龙勃罗梭所主张的对一切有可能犯罪的人或者说具有犯罪倾向的人都予以隔离或者采取更为彻底的做法都将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价值本身解决的就是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问题。而这种做法满足了人们的预防犯罪的需要。但是,即使未曾对法理有过深层次探究或者根本对法律一无所知的人也会对这种做法抱有怀疑和抵触的想法。事实上,无论是古典学派的理论还是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甚至于把恶看成是人的本性,把人本身视为赎罪体的中世纪的犯罪学思想都毫无例外地主张要对不同的犯罪给予有区别的对待,而不是简单地把某些人一律处决,或者使另一类人完全与社会隔离。如果单纯地认为预防犯罪是犯罪学研究的基本价值而对其他的东西视而不见,则显然是忽视了其他重要的东西。预防犯罪如果是犯罪学研究的一种价值目标,那么另一面是什么呢?
尽管人们对犯罪恨之入骨,但是人们却无法对犯罪采取一种原始、野蛮或是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因为在犯罪学研究的价值层面中,在预防犯罪的对面存在着某种东西,影响着学者的思想,阻止学者用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办法去对待犯罪人,即采用更符合人类本性,符合人之为人的行为方式去控制犯罪。如果我们考察犯罪学或者说犯罪学思想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做法也是随着人对于自身认识的不断提高而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在犯罪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表现就在于有关犯罪原因的基本观点、对犯罪所主张的惩罚手段及对犯罪的预防手段。此处所使用的价值概念并非单独针对犯罪学本身的价值而言,它在更深层次意义上与学者在对犯罪学进行某种研究时的思想层面的东西相关。学者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他不可能跳出时代的背景而独立存在。在上层建筑中,尤其是哲学的发展对于犯罪学研究的影响更为明显。学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自己对于犯罪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并且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观点和看法带入自己的理论中,继而再用该理论去指导实践。因此在他的理论和实践中就会体现出他对犯罪所持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古希腊的哲人们在处罚犯罪人与维护正义之间的权衡、中世纪人性在神权面前的挣扎,以及现代社会中功利主义与人权之间的激烈冲突等等,无不反映出这种价值层面既相互依存又激烈冲突的景象。这种冲突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学者对于罪因探查的角度以及对于犯罪所主张的防控手段。这种冲突表现出的规律是:其一,功利主义主导下的预防犯罪一如既往并且会始终是犯罪学研究的目标;其二,这种价值目标越来越受到其他价值目标的制约,这些价值目标表现为正义、自由、平等、人权、人道主义。
三、关注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的犯罪学价值取向
犯罪学所真正关注的对象是人,这种对象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在研究犯罪时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人的情感。在应用某种理论去应对犯罪时,就不得不考虑犯罪人为人的基本立场。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一方面,为了防控犯罪就必须采用有效的手段去防止人产生犯罪的企图;对于已然犯罪的人采取适当的手段阻止其再犯罪。基于这种功利性的需求,这种手段显然越有效越好,也就是说这种手段有趋向于严厉的趋势。另一方面,因为防控手段的对象是人,这样就不得不去考虑犯罪人的基本权利以及自己作为人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说必须采用人的手段去对待人。这样的限制,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来看有日趋温和、人道化的趋势。这种矛盾反映到某一时代的学者的理论中,就是对二者的价值关系进行调整,选择在维持某一价值目标优位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照顾到另一个价值目标。尽管有时这种选择并不是研究者本人明确意识到的,但却在探讨某一具体问题,如对犯罪人采用何种预防、控制手段时不自觉地发生。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定哪种价值目标是绝对合理的。但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可以确定哪种价值选择因为符合时代的要求而突显其正确性。就现代而言,价值选择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这种选择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加体现人类社会进步的需求。
无需明言,对这种价值层面的神秘探讨会带有极大的风险性。但是,也正因为这种风险性才使得对于此层面上的犯罪学价值取向研究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直接与人性相关。它的着眼点在于提示是否存在有这种价值取向。如果有,那么是什么,又如何对犯罪学研究实施影响。事实上第一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如果现在有人提出对犯罪人采取龙勃罗梭所提倡的做法,则显然会遭到几乎所有学者的反对。为什么?原因可能会有很多种,但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可能就是不人道和蔑视人权。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颇具难度。但通过对于学派的历史分析就不难做到,尽管可能会冒有失偏颇的危险。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价值取向的作用机制的问题。其意义在于尽管研究者无法跳出历史的羁绊,无法摆脱一定条件下时代的特征,但是却并没有理由不努力使自己的观点更趋向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趋势。如果我们摒弃诸多因素的干扰,就会使这种价值取向的发展趋势有一个清晰的脉络。那就是从古希腊思想家朦胧的正义感到近现代越来越时尚的人权、人道。如果考察其发展路线,就会发现其间经历了中世纪神学桎梏下的人性的泯灭。在这里崇尚人权的砝码被完全加在了预防犯罪的一端,从而使得预防犯罪的一端完完全全取得了对人性的胜利。也正是因为人类有如此泯灭人性的历史,所以才唤起了人类对于自身价值的认识,人类才认识到人权和人道对于人类的弥足珍贵。这种认识如此深入地影响了后代的研究者,从而使一切有违人权、人道的犯罪学理论都将遭到无情的否定和批判。研究犯罪学价值取向,不仅可以提醒学者在犯罪学的研究中有意识地对于这种价值层面的问题予以重视,更能促使学者从该价值层面出发,去探讨预防、控制手段,从而使研究成果更加体现人类的理性。当然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人权、人道、正义等含义会不断地发展变化,甚至在人权、人道、正义之后人类还会发现更能体现人类本质的东西,这些都是犯罪学的研究者应注意的。
收稿日期:2009-03-05
